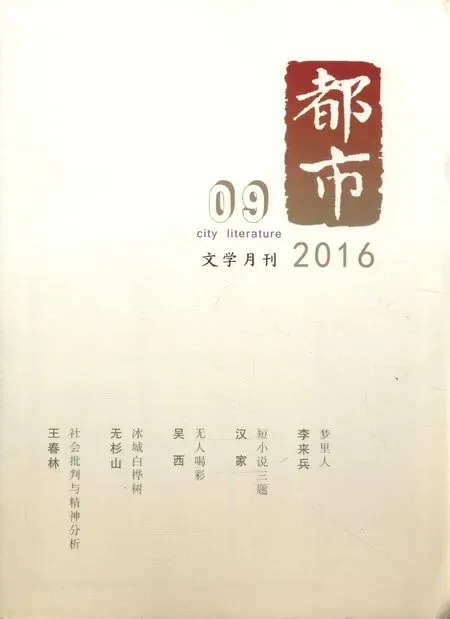故乡何处
2016-11-22贺虎林
贺虎林
故乡何处
贺虎林
我明白现在我是在往回走了。但是我不明白,我是该回哪里去?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几个地方漂泊,从北到南,从东到西,这里十年,那里五载,萍踪野鹤,天涯浪迹。似乎哪里都是家,又似乎哪里,都没有家。
我的故园,我的家乡,到底该是哪里?
晋阳古城里的那株古槐还在,而且是愈见沧桑了。脊背也不佝偻,鳞衣也支离得坦荡。它栖身的那条小街,街口的第一个胡同,也在。尽管,两边的那些四合院,那些跟老槐齐肩的高门楼、灰瓦房,还有那些光哒哒乌青的石狮石鼓石马墩,都不复存在,代之以突兀入云的高楼,它们让老槐一下变得矮小。那条小街,那支胡同,也变得从未有过的逼仄狭窄。但是,它们在我心中,永远是老样子。就连比邻的五一路,桥头街,钟楼街,柳巷,皇华馆,虽然已繁华得几至面目全非,我依然能一路走过如数家珍。一度,我闭着眼也能走到,我出生的那所教会医院,我荡舟的那个文瀛湖,还有那个香满龙城的益源庆……
然而,我只是这古城的一个过客。六岁那年,我离开了太原,随父亲工作调动举家搬迁,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不过还在山西。比之太原,那是一座小城,可它有个很有标志意义的名字,外省人走到这里,就知道是进入山西地界了。当年我们来的时候,也是从外省绕道抵达的,从正太线,经平汉线,再坐汽车,到河南焦作,然后坐铁轱辘马车,顺太行山的尾巴朝上攀爬。一路上的风景,颇为新鲜,山峰都像刀切斧劈,水流尽是飞崖跳涧,山道皆穿行在云中,草木全跻身石缝。那些地名,也叫得蛮有趣味,王莽岭,棋子山,逍遥村,斩龙台……最有意思的是“孔子回车”和“珏山”。我不懂“孔子回车”是怎么回事,赶车叔叔用浓重的方言给我讲了一路,我也懵懂未开。我问:“玉山有玉吗”?赶车叔叔很有学问地说,那个字不念“玉”,念“觉”(音)。当时我的脸就红了。我曾自信自己已识得不下千把字,怎么会把“珏山”念成“玉山”呢?
于是一到那儿,爸妈便把我塞进学堂。其实那时我才五周岁多。本来在太原时,父母就要我进学堂的,说整天爬公共汽车,迟早会闯祸。那时候太原只一条公交线,从五一路穿府东府西街。我们这些省交通厅的家属子弟,就优越地每天免费上车去玩,想上就上,想下就下,在那个老城区随意地兜风。爸妈就逼我提前上学,我不从,我已经被每天逼着认字认腻了。那天,妈妈强拉了我去学校报名,我瞅准机会挣脱了她的手,然后在桥头街钟楼街柳巷海子边跟她玩起“猫捉老鼠”,我在前边跑,她在后边追。那时候妈妈还很年轻,跑得也很快,眼看就要追上了,恰好驶来一辆公交车,我一挥手钻了上去,急得妈妈靠在电线杆上呜呜地哭。之后爸爸亲自带我去学校,就在刚办好入学手续的时候,他却被调离了。
我很高兴,以为搬了家以后不用上学,没想到还是“癞蛤蟆躲不过五月五”。我抗争说,这里没公共汽车。爸妈说,这里有山,有河,有狼,有蛇。我还是跑,顺着那个改作工厂的大营盘围墙转圈圈,最后门卫帮妈妈逮住了我。从此我只好背起书包,从那个三清观改作的五龙小学,到夹在老城幽巷中的城内三完小,再到樱桃满园的晋城一中,除六二年压缩回老家有过两年短暂的离开,我高中以前的学业,都是在这里完成。我少年青年所有的梦,都曾生发于此。不过也梦碎于此。高中毕业后,我随万千知青大军,落户到了农村。
我以为我的人生小舟,从此将永泊于此。然而岂料,一年之后,我又被一股汹涌而来的大潮从太行山一直裹挟到黄土高原的褶皱深处,漂向我的根脉——吕梁离石。
在未回吕梁之前,有好些年,我曾想象它应该像陕北的延安:绵延不绝的黄土梁,纵横交错的川壑沟,层层叠叠的土窑洞,风情万种的信天游。我也确曾有过像对延安一样的情感,向往的时候,哀伤的时候,经常会默念:“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这儿虽不是革命圣地,但也是抗日根据地,马峰、西戎写过这里的英雄。那本书,我曾珍藏到“文化大革命”。可是,当我十二岁第一次回到它身边,我的心一下就凉了半截。十九岁再被迫“扎根”故里,我简直要绝望了。
是因为穷山恶水、贫困落后吗?贫穷并不决定情感,能被贫穷左右的情感,内核一定也是贫穷的,狗还不嫌家贫呢。何况那个年代,中国不穷的地方有几多?
我两次回故乡,都是带着累累伤痕。第一次,爸爸蒙冤入狱,全家被“六二压”,母亲领着我们回到故土。多年漂零,落魄归来,多么期盼乡党族亲抚慰关心,可是族人乡党,与外地人一样冷漠无情,要不是姥姥姥爷接济,我们几近饿死。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父亲再次被“打倒”,我们又被撵回来。这一回,比第一次还惨。父亲是“阶级敌人”,我们子女,无辜地也跟着一起被“专政”。那些乡党,他们也很贫困,他们的地位也不比我们真正高多少,可是,挤兑欺负起我们来,却那么不吝邪恶。劳动不予同工同酬,弟弟妹妹不给上学;作为全乡唯一的高中毕业生,学校宁要小学、初中文化的人当教师,也不准用我;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更没我的份。甚至,八年之后,恢复高考,我高分考中,政审时竟又野蛮剥夺了我上学的权利。一次次背负委屈扑进故乡的怀抱,得到的却是伤口上撒一层盐再撒一层砒霜。茫然望着家乡支离破碎的山山水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一再地怀疑,这是我的故乡吗?
在那些杌陧岁月,梦中常常走进的,还是我的上马街,我的永安里,我的垂花门,我的海子边,还有那所,博爱医院。
尽管那时,它满目疮痍。首义门,大南门,水西门……都弹洞累累,好些街道,还有炸开的弹坑。但是,天是蓝的,湛蓝湛蓝,常常听到,悠扬的鸽哨从头顶飘过。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吆喝着歌不歌号不号的调子,叫卖泥雀哨、小糖人、虎头娃娃、琉璃喇叭,引逗我们把钞票丢进他的褡裢。父母也会打发我们,到不远的商号,“老鼠窟”、“认一力”、天津包子铺买吃食回来,店家用干净的麻纸包了递过来,还会嘱咐一声“小掌柜您走好”!也会跟了谁家的大人,去宁化府打醋,竹子做的醋量量,一下一小瓶,三下一大瓶。前后两院七八户人家,相处得像个大家庭,谁家吃什么稀罕和家乡食品或年节食品,都会送各家一点叫老人孩子尝尝。夏日的夜晚,聚在垂花门里外,听摇着蒲扇喝着凉茶的大人们,讲“三家分晋”、“程婴救孤”的古事。白天大人们上班走后,我们便结了伴与邻院小子们对阵,争抢石狮石鼓,颠扑老鹰抓鸡,比赛蛤蟆跳远,单挑斗鸡摔跤。最有意思的是竞爬老槐树,肚皮溜得生疼,一个也上不去。老槐树太粗了,七八双小胳膊都抱不住,叠罗汉也攀不上去。只有一次够着了它的枝桠,那天爸爸单位的小嘎斯车正好停在树下。站在车厢顶,攥着老槐树绿葡萄一般晶莹的籽实,兴奋得我们又蹦又跳……
然而,只能在梦里走近它了。命运把我死死拴在太行山、吕梁山中。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年里,我们一家人就在这两山之间三进三出。城市,农村,农村,城市;市民,农民,农民,市民。当我再次真实地走近双塔,已经二十七岁,我二度考取大学,来到省城。
记得报到的当天,收拾好床铺,来不及吃饭,就直奔我曾经的“伊甸园”。整整暌违了二十载,但无需指引,我径直就走到了老槐树身边。首义门不见了,取代它的是五一广场,不过大脑里所有的记忆,还是一下就鲜活起来:侯家巷、皇华馆、上官巷、桥头街、上马街,我霎时激动不已,几乎是跑步冲向街口,冲向古槐,冲进永安里,冲进“铁蘑菇”大门、垂花门。抱着老槐,抱着石狮子,我的泪水涌出来。
那天,我在老居里外逗留到很晚,跟老槐,跟石狮子,说了好多好多话。我看见老槐树、石狮子也流了泪。抚着也是伤痕累累的石狮子,真想号啕大哭一场。大学四年里,我每隔一周两周,就要身不由己去老屋周遭徜徉一趟。每次放假前和开学第一周,更是一定要去,披着溶溶月色,嗅着幽幽槐香,聆着沥沥细雨,踏着皑皑雪霜。
可是四年之后,我又回到了吕梁。本来学校要留我在省城做教师,但政策有规定,老区、贫困区学生,必须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吕梁既是晋绥革命根据地首府,又是全省最贫困地区。那时是计划经济,一切皆由政府决定。
兹后的年月,我心有不甘又不得不死心塌地在吕梁工作,然而却怎么也消解不了对那里的疏离违忤感。甚至升了“官”,我也并不由此而对它亲近起来。尤其是当年那些举着阶级斗争大棒,“修理”、“教育”过我们的村镇干部、乡党族人,这时都纷纷到我工作的“衙门”里来示好套近,更是让人觉得,这方水土,实在乖谬得可怖。于是若干年后,一俟有了选择的自由,我便惶惶“逃离”了那个令心灵无处安放的地方。
爸妈说,吕梁是根啊,那里埋着祖宗呢。我说是。不过,咱乡咱村的地下,都被煤老板掏空了,到处窑塌地陷,连老骨头都不得安宁了,四邻八乡的人早都作鸟兽散。乡已不乡,村已非村,还说什么叶落归根,怕魂灵都不知道该栖在哪棵树上!
父母无语了,只得随了我,到太原定居下来。终于又回到了童年的故土,这一回,我可以随时去凭吊我昔日的垂花门了。有时独自,有时陪着父母。父母也留恋昔日的瓦当,不过他们更牵挂当年的老邻里,可是他们都不在了。我在大学期间就曾问询过,只有前院南屋高伯伯一家还在。当年的小哥哥小姐姐们,都插队在农村,我毕业时,听说才回了城,安置在大集体小集体企业,如今也都不知都搬往何处了。
小街一天天变化,父母便不愿再来。他们更愿意回老家吕梁去住,或者去晋城。老家于他们,终有剪不断的乡愁,正如太原之于我。去晋城则有些迫不得已,那里也是我们一家曾经断肠的地方。但是父亲每年得到社保中心去年检验证,不管你老得能动不能动了,本人必须到。于是我又不得不陪伴他们来去。父母都很老了,我得照顾他们。
重新走进晋东南的这个小盆地,心情和对离石一样复杂隐忍。这里曾经编织过我青春粉红的梦,也在心灵深处,斫下无数伤痕。父亲无辜蒙冤,“文化大革命”中先遭批斗,再被流放,所受的折磨,较地狱只是左右。记得我们一同回去的那天,天正下着瓢泼大雨,车窗上哗哗如注的雨水,仿佛堰塞心头多年的泪水瞬间决口。三天之后,我才迈出门,本来是决计哪里也不去,什么人也不寻访的。无奈青涩的过往,像小兔子般在内心不住躁动。
那座三清观,费了好大劲才寻见,被现代校舍环绕其中,里头却塑了尊三清道长像,像个古董,但却没有了当年一丝模样。幽巷里的三完小仍旧被杂沓的民居所包围,只是小巷两边多了光怪陆离的酒旗商幌。而那座当年雄踞全省前三甲的中学,校园比过去扩大了一倍。这不关我的事,我要寻的是旧日的教室,旧日的宿舍,旧日的礼堂,旧日的图书馆,还有满校园那朱碧分明的樱桃。但是都不见了,樱桃树也不见了,连一株都没找着,叫人好不唏嘘。唯有寻访引我步入知识殿堂的恩师们了。这座小城留给我的,也只这份师恩了。
在一个偏僻小山村,我找见了最想看望的第一位恩师。跨进一所老旧四合院,我深情地抱住了她,像抱住久别重逢的母亲。当年她对我,就像对她的儿女一样慈严相济。老师孤苦孀居,且已失忆,但是却记得告诉我,语文黄老师的坟茔,歇在何处。他俩是我最早的启蒙先生。
黄老师豪爽厉害,当过志愿军,讲课讲得伤口痛了,便坐到讲桌上,绘声绘色给我们谝怎么打美国鬼子。所以中学时学到《谁是最可爱的人》,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便是黄老师,其次是,我的大舅,他也是志愿军英雄。
黄老师原是清华大学副教授,被错打成“右派”后,爱人跟他离了婚,他只好一个人孤零零地来到山西。他教的化学,每年能押中百分之八十的高考题。“文革”中却强迫他到学校鸡场去喂鸡,还要每天去写大标语。先生写得一手漂亮仿宋体,且从来不用尺子打米字格,面对偌大一面墙,拿起排笔,首尾定两个点,每字定四个点,然后万字不断头一笔就勾勒出来。“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城墙壁上的大标语,几乎都是他写的。早中晚,还得赶回鸡场喂养伺候那几千只鸡。
而对我刺激最大让我感伤最深的,是胡荣绵老师。胡老师是上海人,华东师大毕业。大字报上揭发他,家庭出身大资本家,几个兄长姊姊,都留洋海外。唯有他,出生得晚,身体又有残疾,做了教师,还被分配到山西这个小县城。但是我们学生却特别尊敬崇拜他。他态度谦恭,说话温和,又不卑不亢,以高尚的人格和渊博的学识征服学生。记得每周二周五下午,他都会在那个工字型理化教学楼前的小黑板上,工工整整写下当天的温度、湿度、风力、风向,然后写上,几点至几点进行航模试验,请同学们踊跃参加。届时,他和他的助手,将自己亲手制作的小滑翔航模机,用皮筋弹射到校园上空。随后再将航模的飞行时长,记录其上:ZG-010号,比ZG-009号,航行时长超过X分X秒。ZG,就是“祖国”的意思。这不是他的教学内容,但是他用这种方式,激发全校学生学习物理学习科学的热忱。追随着蓝天白云下的航模机,同学们也跟着放飞理想。大家都期待胡老师的课程。遗憾的是,我只听过他不到一个月的课,“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
胡老师自然是第一批被“打倒”的人。他身体本是那样孱弱,却受到比任何人都残酷的毒打批斗。那些造反派,似乎是专拣他最脆弱的部位拳擂脚踢!起初,他还保持着矜持,保持着尊严,但后来,就忍不住地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呻吟呼喊。记得最残忍的一次,是一天晚饭时候,大家端着碗,围在礼堂外的教工篮球场看球赛,不知为什么,一个身高马大的高三学生,突然就殴打起他来。只听见胡老师怯怯地说,同学,我怎么啦?我怎么啦?但是,话音未落,一碗和子饭已经连碗带饭朝他扣去。随后,那学生像一头暴怒的狮子,扑上去撕住他的衣领,将他像老鹰抓小鸡一般拎到空中……底下的人群像欣赏国王卫队毒打卡西莫多一样开心喝彩。歇斯底里中,那同学竟又将胡老师像甩鞭子一般狠命摔下。胡老师从一人多高的台子上重重落下,顿时头破血流,但他仍本能地试图站起,可是未等直起腰,一只大脚已经疯狂地踹在他的罗锅上。胡老师一下瘫在地上再不见动弹。那一刻,我浑身哆嗦,碗里的汤饭洒出来。我想躲走,又不敢,我怕造反派说我“兔死狐悲”。很多人却在高喊,“罗锅装死,不起来,就揍死他!”胡老师还是一动不动。那同学用脚尖踢踢胡老师的脸,瞅了瞅说,你小子装死,今天且饶了你一条狗命!
而今,我在医院见到了胡老师。令我惊异的是,除头发白了些,先生看上去,几乎还是老样子:洁白的衬衫,平静的表情,和蔼的态度,柔曼的话语。只是神情有些憔悴。我嗫嚅着不敢问他得的啥病,他立刻会意,告诉我,是给他爱人治。他快五十岁时才找了位普通女工结婚。眼下他的这位妻子不幸患了鼻咽癌,他悉心守候着这个愿意嫁他的普通女工。我诅咒上苍,为什么对老师这么不公!我问老师,怎么没回上海?或者,出国?许多人都走了。他仰望苍穹,仿佛盯着当年放飞的航模,然后说,雪泥鸿爪,哪里都一样,哪里都是一生。
我一时震惊。
直到现在,我也没完全想通。不过,我不再去想,我的家园何处,我的故乡何方……
(责任编辑贾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