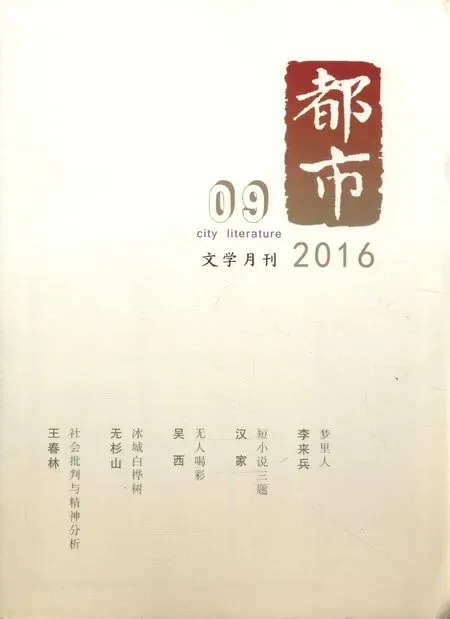萧然物外,自得天机
——李来兵小说综论
2016-11-22何亦聪
何亦聪
萧然物外,自得天机
——李来兵小说综论
何亦聪
“真正是与这个时代合拍”
在山西新锐小说家当中,李来兵向来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人所知,自2004年步入文坛以来,他的已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作品,共有五十余篇,散见于《人民文学》《黄河》《中国作家》《滇池》等杂志。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一天》《姑娘》《客人》《城市民谣》《拜年》《猫》《节日》等。李来兵不是一个以创作裁制之大或数量之丰见称的小说家,也无意于在其作品中灌注过多的时代、思想命题,在他的身上,我们看不到小说家所惯有的野心勃勃,也看不到面对时代与现实的强烈的问题意识,他的写作姿态,是背向繁华的,但也是轻松和自由的,这个僻处怀仁小城的小说家,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审美追求,予人一种“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整体印象。
李来兵于1972年出生在山西北部的怀仁小城,虽然我不愿以“代际”的方式来探讨作家,但是,作为一个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小说家,李来兵的确面对着“70后”作家所共有的困境。这种困境,正如许多论者所言,是在于一种夹缝式的生存状态:在以50、60后作家为主的文学体制和以80后作家为主的商业运作的夹击之下,70后作家事实上扮演的是一种“双重局外人”的角色,既在文学体制之外,亦在商业写作潮流之外。双重局外人的身份,一方面使得“70后”作家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压力,遭遇更多的尴尬;另一方面,也赋予了他们某种优势,使得他们能够既不为八十年代启蒙的宏大叙事所诱惑,也不致沦为商业文学流水线上的一个生产工,而是以一种相对冷静、独立的姿态来表达他们对时代、现实的思索。
王祥夫曾以“相信我们都没什么主义”为题谈论他对李来兵小说的印象,这一说法的确能够抓住问题的关键。规避“主义”,尽可能地避免一切先入为主的观念、见解、倾向,尽可能地以冷静、理智的笔触描摹现实,为此甚至不惜抽空作品中有可能呈现的一切主观思考和道德判断……这的确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小说家所孜孜以求的一种艺术风格,而这种创作倾向的出现,虽与知识分子启蒙热情普遍趋冷的时代背景有关,但具体到文学层面,也关乎我们对小说家身份定位的变化——小说家不再负责指引道路或者给出答案,甚至很难继续在价值层面发挥影响,一部《家》的出版就能够引发数以百计青年离家出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鉴于此,我们的确可以说李来兵的小说“真正是与这个时代合拍”。
揭示当下中国人的精神困境
言及李来兵小说予人的阅读感受,已有论者指出其外在形式与精神内涵之间的差异(诸如“冷面热肠”、“行走在现实与先锋交汇处”等说法),以及由此差异而拉伸出的艺术张力,但我以为,对于中国近二十余年的小说创作而言,无论是零度叙述还是符号叙事,抑或是以先锋之笔触行写实之目的,似乎都已不足为奇,我为什么要选择读李来兵,而不是拿出同样的时间去读罗伯·格里耶或者加缪,这首先必定是由于他的小说与我们中国人当下普遍的精神困境有关。李来兵生活在山西朔州的怀仁县城,偏僻小县的生活经历使得他的写作并不局限于乡村经验或城市经验的单一表述,而报社记者的身份更让他得以有机会将视线广泛地伸展到社会底层的各个角落,对于底层小人物的人生悲剧,他有着深刻入微的观察。
从叙事技巧方面讲,《拜年》在李来兵的短篇小说里面也许不算特别突出,但这篇小说中所蕴含的悲剧性,着实动人心魄。小说围绕一个名叫“大袁”的秧歌队鼓手展开,在王家场村,大袁算是一个有过“辉煌过去”的人物,他曾做过大队保管,获得过地区劳模称号,不仅敲得一手好鼓,更兼为人热情仗义,村里上上下下都把他看作是一个处事公平、能为人排忧解难的“场面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袁不仅失去了他的地位和光环,甚至也将失去他最后的精神寄托——敲鼓。小说一开始就描写大袁去找年轻的村支书借鼓,新旧两代人之间的对立渗透于字里行间,而尘封在大队库房里的那面鼓,恰恰象征着大袁今日的处境,其中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支书让他的女人带着大袁去库房里取鼓,库房里霉气很重:
一打开门,那女人就躲得远远的,捏住鼻子,门里扑出一股陈年的霉雾。她不知大袁怎么就不怕那霉气,迎面挺着,像一棵树,雾气滚滚从他的头上脚下,从他的身体两侧弥漫出来。她以为大袁被熏晕了,从斜面去看,猛看到大袁的脸上湿湿的,眼睛扑眨扑眨打转。您怎么啦?这个白白的女人小心问,没怎么,大袁赶紧擦一下脸,笑着,你看几年没开过它,都捂出味儿了。
可以说,小说的悲剧性从这一细节开始就已经埋藏下去了,而在此后的叙述当中,作者保持了尽可能的克制。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似乎看到事情正朝着明朗的方向发展,大袁在村子里重新组织起了秧歌队,秧歌队随大袁出去拜年也不无收获,重要的是,作者不厌其烦地将笔墨停留在一些无关宏旨的琐事之上,而这些琐事似乎又预示着“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按照这种叙事节奏,理应不会有什么突兀的事情发生。直到小说结尾,大袁带领秧歌队到化肥厂拜年,与“朱主任”为红包数额的多少讨价还价的时候,才出现了令人惊诧的一幕:
一个死人多少钱?朱主任忽然听到大袁问。
什么死人?
我问你死人多少钱,一个?大袁的眼就在朱主任的眼前,他的眼很大,牛眼一样。
大过年的你说什么死人?朱主任笑着,觉得这个农民真是扫兴。
朱主任看到大袁走开了,还看到大袁把烟扔了,把衣服也脱了,看到大袁把一个女人的扇子也夺过来。
人们都没见过大袁扭秧歌,都看到他的左脚往右边一丢,又是,右脚往左边一丢,然后整个人就像被风鼓荡起的衣服,飘飘着,飘飘着。飘飘着,飘飘着。
鼓声停了一下,然后猛地又轰轰烈烈其乐无穷地敲打起来。人们就在这鼓噪出来的混混沌沌朦朦胧胧中,看到大袁真像一片衣服,轻飘飘地向平台下飘去了。
如此突兀的了结,生命就在“轻飘飘”的氛围中“像一片衣服”被随意地丢弃了,看到这里,读者也许会心生疑惑:大袁为何要这样草草送命?如此安排,是否会影响小说的“现实感”?在我看来,这显然是一个蓄谋已久的结尾,十分精彩,它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马尔克斯的小说名篇《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结尾,所不同的是,后者更显自然、更具力量感,而李来兵的这个处理则让人意想不到,仿佛横来之笔,但细思前面的种种安排,又并非不可理解,小说的悲剧性底色本来淹没在层层日常琐事的铺叙中,到了这一刻终于不可阻挡地涌现出来。
《拜年》所书写的无疑是一种处于变动之中的乡村经验,而大袁的悲剧则似乎喻示着这种“变动”所可能造成的某种无从解脱的精神困境。乡村经验的书写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绝非新奇事物,然而撮其大要,无非两个路数:一是将乡村经验做“凝固”处理,经过这番处理的乡村,逐渐从现实中抽象出来,失去了历史感,成为一种永恒的、理想的情境,数不清的小说家追随着沈从文的脚步,试图以此种方式来对抗罪恶的、充斥着欲望的、已步入歧途的都市文明,然而他们所最终对抗的,却很可能不过是脆弱的、几经挫折的、屡遭威胁和挑衅的中国现代启蒙;二是试图将小说“报告文学化”和“纪实文学化”,又或者“方志化”和“民俗化”,以尽可能精确的手法传达一时一地的经验,这一路小说家往往信奉“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并据此推演出“只有地域的才是民族的”、“只有乡土的才是地域的”等一整套观念。对于当下的小说创作而言,如何将地域经验、乡土经验的书写植根于普遍的人性基础之上,如何使小说作品本身成为沟通地域经验、乡土经验和普世价值之间的桥梁,如何在固守某种文化品格的同时不致因此而消弭掉小说家面对社会现实所应有的问题意识……我想,这恐怕才是当务之急,值得欣喜的是,已经有部分小说家对此有所警醒并以他们的作品展现了新的可能性,而李来兵的小说创作,或许也可归入其中,小说《拜年》即是一例。
《拜年》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我想,关键之处在于,作者在这篇小说当中,能够超越纯粹的乡村经验来描写乡村,或者说,是能够将对乡村经验的书写建立在人类共同经验的基础之上。秧歌、鼓、大队、支书、劳模以及充满戏剧性的拜年形式,皆与乡村经验有关,大袁所引以为豪的种种过去的辉煌,更是只有安放在乡村经验当中才成其为“辉煌”,然而大袁的绝望是深刻的,这种绝望并不仅仅是由具体的现实情境造成,他之所以选择死亡,也绝不仅仅是由于往日的辉煌不再或者个人的尊严遭到挑战,真正纠缠着大袁并最终造成悲剧的,毋宁说是一种“生活在别处”的疏离感——他在眼前的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当中,已经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而这种疏离感,显然已非单一的乡村经验所能容纳,它是一种人的困境,或者说,是人类困境的一种可能。
在许多小说作品当中,李来兵都致力于去展现人的精神困境,他所展现的精神困境,一方面是“疏离感”,个体处身于现实世界之中感到无所适从、茫然无着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我们还可以在他的其他小说,诸如《城市民谣》《姑娘》《猫》等中短篇当中看到。《城市民谣》中的“隋他妈的”,无论是跟随师傅做学徒,还是在工厂里自己带一帮徒弟;无论是面对金纯、师娘还是荷花;无论他的生活境遇发生什么变化,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就是对于眼前世界的疏离,小说中有几句描写特别值得注意:
我没去上班,也没去师傅家去找师娘。也没回我母亲在的村庄。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能立即容得下我。我疯狂地奔跑,奔跑。大街小巷,田野阡陌。所有的人和动物都被我惊得四散而去。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种在旷野的中心。
这是一段颇具现代感的描写,描写的正是现代人所特有的孤独与茫然,“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种在旷野的中心”,这句话简直让人头脑中产生一种近于“荒原”的意象。除了人与周遭环境的疏离之外,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也是李来兵所欲着意表现的,《姑娘》中的“姑娘”,在经历了一场爱情的幻灭之后,出于现实考虑,嫁给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王四有,于是小说结尾出现了这样意味深长的一幕:
“四有,会不会说我爱你?”
王四有羞涩地笑了笑。“会呢,怎么不会,我爱你。”
他然后看着姑娘,姑娘看着白虚虚的一片墙。
姑娘一个字,一个字,每个字都吐得很真切。
“我,爱,你。”
虽然口中说的是“我爱你”三个字,但是她眼睛看的却是“白虚虚的一片墙”,这面墙,不仅象征着爱的无所依托,更象征着姑娘与王四有之间横亘的那道无法逾越的屏障。而在短篇小说《猫》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或隔膜感更是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王老师所养的爱猫“咪虎”走丢了,他焦急万分、食不下咽,寻找了二十多天仍然无果之后,却意外地在自己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所住的小房间里看到了它,而在此时,被他忽略多日的老母亲已经平静了,咪虎站在他母亲的床上,以一种凶悍的、带着杀气的目光看着他:“王老师看到床的四周横七竖八躺着几只死老鼠,它们都有那么大,大得简直吓人;就像要四面八方围攻这床一样,它们都头朝着床这边,但是都已经死掉了。只有猫活着,疲惫地,傲然地,像个武士似的,直挺挺在床头上。”“只有猫活着”,这句话意味着死去的不仅仅是几只老鼠,还有王老师的母亲,反过来说,他的母亲的境遇,与这几只老鼠相差无几——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在此处达到了极点。
走出零度叙事
李来兵小说的叙事手法常常被认为是受到西方零度叙事的影响,也有人认为他秉承了海明威“冰山文体”的写作原则,我并不否认这些评价,然而在用零度叙事与“冰山文体”关照李来兵的作品之时,我们也需思考他选择此种叙事手法的深层原因。
用李来兵自己的话来说:“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种在旷野的中心。”虽然我们不能将这句话武断地理解为对作者本人进行精神解读的唯一凭据,但它也足以为我们提供思路。作者在这句话中表明自己是孤独的,却又种在空旷的大地上。他希望自己能够种在旷野与大地上,却依然会感受到孤独。这是作者困境的形象表达。李来兵尝试着用多种叙事手法,尤其运用零度写作的自由去逃离小说叙事的传统,去试图创造小说的另一种可能,这不能不说是作者对自我的放逐。他不想重复传统的叙事模式,希望有所颠覆与创新,然而叙事的实践又使他成熟,使他将自己种在大地上,汲取厚重的文学经验,与土地和时代不无缺憾地相爱着,这就是他面临并试图逃离的矛盾困境,他对叙事题材的多样选择也是这一困境的例证。他徘徊于乡村、县城与城市之间,变换着叙事环境与主体,书写着多样的题材,却又从这些题材中逃离,永远渴求着新题材的创造。他选择的多种叙事手法都有自由宽阔的叙事空间,他每一次的选择与自由抒写都体现着对时代与传统的逃离,却又终会陷于时代语境的规训,沉入逃离不得的精神痛苦中。
从《客人》到《节日》《姑娘》、再到《跳舞的女人》,可以看出李来兵小说叙事的自觉改变与渐趋成熟。零度叙事的优缺点均与其极大的自由度有关。作者对文本的掌控既已达到任意而为的程度,那么读者在阅读之时就容易被文本中明显的违和因素打扰,期待视野受挫。李来兵早期的小说作品,如《客人》和《节日》,比较明显地体现出了这一叙事手法所带来的破碎感、断裂感。《客人》的故事发生背景是一个穷僻的小村庄,女主人只能用一碗豆面和一颗鸡蛋来招待客人,然而就在这样一种故事情境之中,却常常会出现颇富诗意的描写如“不想闻他满身风尘的味道”、“阳光下,客人这个词的形状是一架虚张声势的驴车”、“从一波一波推开的浪尖,看得出风是存在的”等,像这样的一些描写,皆与整篇小说的语言风格难以融合。这种叙事的断层虽在全知全能的叙事角度下得以缓和,但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正如契诃夫所说,一个农民对他形容海时说:“海是大的。”这很美,但如果这个农民对他说海是苍茫的、浩瀚的,那就不对。在李来兵早期的小说中,突兀的叙事每每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它或是一个人不合身份的言行举止,或是一件事不合逻辑的发展,或是没有足够的铺垫就突然爆发的结局,似此种种,都会造成读者不同程度的阅读障碍。比如小说《节日》的结尾:
这个院子的墙面,也都是白,他们好像都经常粉刷,或者呢,因为他们习惯地爱干净,连那墙也一样保持着这份质地。
看到这样的叙述读者可能就会下意识地思考其背后蕴含的深意,并希望能在小说的最后找到答案。然而紧接着的内容却是这样的:
吃饭的人是坐住了。只有大妹妹想着这边的两个,大概只吃了几口,就急慌慌提着饭盒回来,饭盒里是那种六畜兴旺的丰盛,还冒着热气,还有一瓶可乐,就把可乐倒开了,两个妹妹,不知是谁提议,她们也干一杯,大嫂先还忸忸怩怩的,后来,待她们一举,她也举起来了。
显然,在这个结尾中,读者的期待视野没有得到完满的实现。阅读李来兵早期的小说作品,常有类似的断裂之感,究其原因,应当即是作者对零度叙事的刻意追求所致,但他并未受限于零度叙事,其叙事技巧随着创作经验的积累而渐趋成熟,同时,零度叙事的影响亦随之淡去。在2004至2011年的小说作品中,李来兵尝试了对话叙事、倒叙、插叙等多种叙事手法,变幻了不同的叙事结构,运用了各具特色的叙事功能,他对文本的处理和掌控更为得心应手,作品精神内核的连续性和连贯性亦较前大有改观。如其200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跳舞的女人》,叙事明朗,故事发展流畅自然,人物的一言一动皆与其身份高度契合,随着情节的展开,读者在“跳舞的女人”的日常琐屑中逐渐感受到家庭妇女生命活力无处释放的困境,以及岁月的空旷和虚无。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汉珍去买老郎的猪头肉,她把脸伸进玻璃窗,左看右看,没看到一块合适的,掏出头来看老郎,表示她的失望。
……
十块钱都拿走吧。她转身,听到老郎发了一言。声音很闷,好容易从那些大豆沫儿中挤身出来的。
那么多肉,肥是肥了,也不是十块钱能买走的,但也不是就买不了,但汉珍终究是觉得自己赚了,窃喜喜的,却不表明在脸上,上了路,才腿上一阵发飘。
这段描写细致而真实,尤其是最后汉珍的“窃喜”,更是使得这个人物鲜活灵动、跃然纸上,读者可以从这小小的窃喜中体味到更深更广的意味——究竟是怎样贫乏平庸的生活,才会使得一个女人去为此等小事而窃喜不已?生活的真实就通过这样一个个微小的细节进驻读者的内心。
多种艺术手法的融合
李来兵小说叙事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结尾的爆发。因这一爆发所需力量过于强大,如何收束即成为一个难题,在通常情况下,作者不得不通过安排角色走向死亡来使之达到完整的高潮。李来兵小说结尾之前的叙事往往不显山不露水,平静而流动,而在最后一刻的震荡与撞击后,作品戛然而止,爆发出的力量瞬间收回,使读者陷于精神震撼的同时看到文本的空白。这种独特的叙事风格在其小说作品如《拜年》《姑娘》《猫》和《天堂伞》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李来兵早期小说作品之所以会为零度叙事所囿,大致是出于对传统叙事手法的怀疑。传统的叙事手法虽真实而细腻,但在抒写心灵、融入作家性情趣味、开掘人物内在精神世界方面却颇有欠缺。在李来兵早期的小说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为摆脱传统叙事的限制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一方面是零度叙事的引入,力图涤除文本中情感与思想的介入;另一方面,来兵本身又是一个有着强烈艺术个性的小说家,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他往往无法控制这种强烈的艺术个性对文本的渗透,在他的笔下,人物的精神状况总是被变形地强调,这精神状况却缺乏现实凭依,漂浮于乡村和城市上空,无法落脚和扎根于坚实的大地。
在后来的小说写作中,李来兵逐渐意识到零度叙事的困境,便开始将自己曾经试图摒弃的传统叙事手法融入其中,以期建造一个清晰、坚朗的叙事结构,“锁骨观音”般皮肉散尽骨架尽显,仍挺立如前,我们可以在其中篇小说《姑娘》中看到这一尝试。比之两年前创作的《城市民谣》《姑娘》体现出了明显的结构意识,两部作品分别围绕一个城市工人和一个乡村女孩的精神困境而展开。《城市民谣》的故事前后衔接基本上依靠男主人公的精神状态和意识流动来维系:
我从那儿钻进了另一片绿油油的地方。我不知道那是哪儿,但是那种无边无际让我放荡。我骤然膨胀,又倏地缩小
——
我变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田野,躺在大地上。一股股风。一股股风
——
每天上午,……一溜骑着自行车的女人,沐浴着满天金灿灿的阳光,像真正的鸽子一样飞翔,我那颗飘摇的心终于有些安定了
作家试图用男主人公的精神状态勾连没有足够叙事支撑的生活现实,通过对内心与外在世界的对等叙述凸显现代人的现代情绪,但破碎、零乱的现实描述不足以为其精神世界提供支撑,主人公的精神状态也就只能存活于小说中,无法化入读者的内心。《姑娘》的处理则更显真实厚重。传统的正叙、丰富而不造作的故事情节、来自未来的姑娘的声音,都将姑娘这个角色塑造得可亲可信。比如文中对姑娘的这段描写:
“宣栓林叔?姑娘,你是把我越看越远了啊。”宣栓林说。“你不如干脆称我大号算了,我还有个将就。”
姑娘低下头,娇俏地一笑,说:“叔,我是嫌你没动静,这大秋天的,满院的菜伙都等着你呢。”
宣栓林知道姑娘开玩笑了,这姑娘居然能开玩笑了。他的心就像被点了一把火,霎时通明了。
姑娘的声音、笑容,继父与姑娘的对话,都鲜活、真实,使姑娘的形象近在眼前。作者在小说中还时常插入不同年龄的姑娘的回想,如:
几年后,姑娘还会梦见这个梦,三十岁的时候,也梦见过。
这类插叙使得姑娘的形象在时空流动中显得更加真实。
李来兵在其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并未完全倒向传统叙事,他也尝试多种叙事手法,希望既能摆脱传统叙事的禁锢,又能融会其优势于作品中,《猫》和《活法》即是很好的例子。这两篇小说的潜在主人公不再是人类,而是一只猫和一条狗。在《猫》中,作者试图让这只猫成为控诉现代人亲情之疏离的象征,而《活法》中的狗二混子则完全成为了大老六的灵魂寄托,不可分离。这两篇小说初读虽颇令人感到吊诡、费解,但反复品味,却蕴含着异乎寻常的力量感。李来兵随后的短篇小说作品《跳舞的女人》再次回归现实主义的叙事传统,以细腻精致的笔墨成功地勾画出了生活在小城的家庭女性的精神状态。相比较而言,《天堂伞》的叙事则稍显失败,故事中已六七十岁还爱抽烟的老太太艾薇居然有一口洁白如玉的牙齿,二十多岁的朱米德就与这样的一位老太太产生了暧昧的情愫。虽然作者在小说中刻画了富有传奇色彩的爱情,小说的结尾也一如既往依靠死亡来展现人物的生命力量,然而故事本身既缺乏足够的现实感,其感染力亦不免大打折扣。整篇小说以“朱米德一直在低头听人们怎么说,也一直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计。他想,阁楼里老太太的故事他是一定要讲给人们听的。首先讲给妻子。但是怎么讲,他还没有想好。”黯然收场。作者最后似乎点破了他所面临的创作困境——他是一定要讲给人们听的,但是怎么讲,他还没有想好。
不管怎么说,李来兵在小说叙事上的种种尝试,突破也好,回归也好,都至少说明了他是一个具备充分的艺术自觉的小说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的“讲故事”传统的国度,特别是在山西这样一个“讲故事”氛围更其浓郁的省份,能够如此执着地去探求故事“怎么讲”的艺术,都堪称难能可贵。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小说的“启蒙叙事”坍塌以后,在当代小说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最具价值的努力方向,一是试图在叙事艺术上“回归古典”——此处之所谓“古典”,指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艺术,而不是二十世纪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叙事传统;二是继续寻求与西方先锋叙事艺术的融合,但其底蕴已与早前的“先锋小说”不尽相同。然而,时至今日,“文学生态”已大异于昔日,在网络写作、商业化写作、套路化写作的多重夹击下,在“纯文学”日趋庸熟、僵化,逐渐形成一套封闭的话语系统之时,无论是“回归古典”,还是“融合先锋”,都显得举步维艰。李来兵的小说创作,从题材上看,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从叙事上看,徘徊于传统与先锋之间。他试图超越城市与乡村的特定经验去观照城市与乡村,也试图超越传统与先锋的特定叙事模式去展开小说叙事,虽则出于视野的广度、思考的深度等方面的局限,他的小说创作仍存在些许不足,但是,在当代文学的大环境中,他的努力,他的探求,他的挣扎与突破,他的“萧然物外”的、不为潮流所动的姿态,始终是值得我们去肯定与珍视的。
(责任编辑梁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