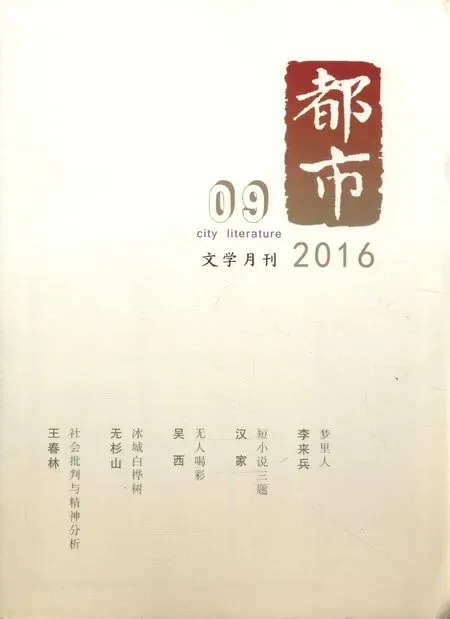那些在暗影中徘徊的灵魂
——解读美国经典小说《宠儿》
2016-11-22黄立全
黄立全
那些在暗影中徘徊的灵魂
——解读美国经典小说《宠儿》
黄立全
托妮·莫里森于1987年创作的《宠儿》是一部描写生活在美国19世纪70年代的“前黑奴”的小说,故事勾勒出非裔美国人沦为黑奴的集体记忆之外更直指他们破碎身份的处境,小说的题材来源于作家在做编辑时收集到的真实史料,作为199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获得了评委会这样的评价:“深入地探索了一种她期求脱离种族羁绊的语言,向我们展现了诗意的璀璨。”
《宠儿》以美国黑奴时期为小说背景,其中涉及到的身份问题值得注意,黑格尔关于主奴身份的论述认为个体的身份建构总是需要得到另一个人的承认;在这样的关系中,一个人会处于两者关系的上风成为“主人”,而另一方便会成为“奴隶”。此时“主人”是自存在的意识,他的话语就会支配“奴隶”的思想,从而使奴隶内化主人对他的身份认同。在多数白人否定黑人拥有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社会环境中,把黑人看做非人的牲畜的观念在黑奴解放后仍有遗留。《宠儿》中的“学校老师”(schoolteacher)就是这种价值观念的演绎灌输者,最终成为了美国种族主义的毒瘤。在这里,虽略有套用黑格尔的主奴关系为美国农场主与奴隶的关系的嫌疑,但是在整个被奴役的过程中,黑人遭受的歧视和打击,使得他们在身体的奴隶之外也沦为黑格尔主奴关系中的“奴隶”。
在奴隶主的权力话语下,几乎所有的非裔美国人都不由得内化或者扭曲了对自身的身份认识:在这个群体中有许多女性的心理是扭曲的,有些男性则丧失了男性气质,迷失了自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们在废奴之后仍然活在奴隶制的阴影之中,无法抛下作为奴隶的生活方式,更无法习惯这种不期而至的自由。
为了使自己的孩子免受奴役之苦,女主角赛丝残忍地杀死了自己的婴孩,似乎正验证了美国白人眼中黑人野蛮残忍的形象。赛丝还总是因为他人的身份误读而耿耿于怀,也正是这种误读在她的身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赛丝不能忘怀的一个创伤是在甜蜜之家留下的。赛丝有一次在甜蜜之家看到学校老师拿着他的画像教育他的侄子说黑人都如动物一般野蛮。虽然在理智上赛丝当即否认这个观点。但是考虑到黑人白人当时的历史社会关系,白人的科学话语已经被黑人所承认,连赛丝的丈夫黑尔也满怀热情地学习算数努力进步,因此当学校老师指出黑人的“野蛮兽性”的时候,赛丝便下意识地把这样的观点映射回自身,对自身的“人性”身份产生质疑。
赛丝的创伤和身份质疑因同族人保罗· D的指责而加深。在得知赛丝为了让孩子逃脱黑奴制的奴役而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婴孩后,保罗·D斥责赛丝是四条腿行走的动物,离开了124号。不单是小说中的白人和黑人对赛丝的母亲形象进行误认,小说的叙述者也模糊地暗示赛丝的“动物属性”。叙述者在描述赛丝和保罗·D亲密时,赛丝的姿势是“四脚着地”(莫里森:22),叙述者刻意模糊的描述指示了美国黑人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下丧失了作为有尊严的人的生存条件。
赛丝的“兽性行为”实际上是为了帮助婴儿摆脱惨无人道的奴隶制被迫而为。与其说塞丝的行为缺乏人性,不如说是罪恶的黑奴制泯灭了人性。在黑奴制中,赛丝根本就没有教育自己孩子的可能。与生儿育女的母亲形象不同,赛丝更像一个产仔的动物,她在六年内生了四个孩子。当赛丝把自己的肉体出卖给刻墓碑的石匠的时候,她的张开的两腿被描述为鲜红的“墓穴”,“像指甲一样粉红,比婴儿的鲜血更加令人悸动不已。”叙述者把女性的生殖器比作墓穴不难让人联想到赛丝弑婴的行为,实际上这里成为生命诞生和死亡的同一场所。
值得一提的是,赛丝的自己的母亲也没有能够“养育”赛丝。赛丝从小就是被自己的养母喂奶长大的。赛丝的母亲在生下孩子之后,杀死每一个白人孩子,只留下黑人孩子,赛丝是唯一被留下的那一个。赛丝婴孩时期缺乏母爱的创伤被学校老师再现,使得赛丝恐惧抛弃自己的“妈妈”,在这种恐惧中转而又怀疑自己的人性身份。
小说中不仅是个体的母性身份产生危机,集体的精神母亲形象也遭受到了质疑。“神圣的贝比·萨格斯”虽然在林间空地教导人们学会热爱自己的身体,得到了许多人的敬仰,但也遭受到了其他人的妒忌。在黑人晚宴中,许多人对学校老师到来之事瞒而不报,旁观萨格斯一家陷落,加之赛丝弑婴的刺激,贝比·萨格斯失去了爱的勇气,作为黑人社会中精神领袖的母亲形象也因打击而陨灭。黑人社会的母亲形象遭受的不仅是白人的误认,黑人群体自身不断强化这种认知,并传播和影响了以赛丝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个体和集体母亲形象的扭曲把黑人群体笼罩在黑奴制的悲伤回忆中,使得他们极度缺乏互相关爱的力量。
如果排除保罗·D暂时的意外逗留,124号事实上是一个“女儿国”,暗指了黑人集体都缺乏一种男性气质。小说再现了美国奴隶制时期,大多白人把黑人看做是男孩儿的话语环境。甜蜜之家的奴隶主加纳也曾夸耀自己“进步”,称自己的黑奴是“男人”,不是“男孩”。但讽刺的是,加纳的黑奴首先已经被剥夺了作为自由人的尊严和权利。加纳称呼自己的奴隶男孩或者男人,而不是其真正的姓名,这何尝不是对黑人进行的一种人格和身份的践踏。在甜蜜之家,他们被奴隶主称为:保罗·A,保罗·F,保罗·D,西克索(Sixo是“六零”的意思),这些以英文字母排序为姓氏的“保罗”们,像是编了号的商品,随时等待被出卖。保罗·D在戴着橛子准备被学校老师出卖的时候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他感觉自己被一直叫做“先生”的鸡鄙视,开始意识到黑人男性实际上已经被精神阉割,还不如一只公鸡。
保罗·D向赛丝求婚可以看作他为重建家庭而做出的努力,但这种意欲担当男性家长的一个姿态也仅仅只是一种姿态罢了,因为他还不足以具备承担男性责任的能力,保罗·D在进124号后与赛丝亲密仅仅出于他常年在甜蜜之家受到屈辱又无法接触女人的现实压迫而造成的性的渴求。在和赛丝亲密之后,她又对塞斯悲伤的疤痕表示反感,并未去主动抚平伴侣的创伤。不仅如此,在与赛丝的亲密关系中,他始终处于一种下风地位,未能获取主动,尤其求婚一事,更使保罗犹疑不决的性格得到凸显。在得知赛丝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婴孩后,保罗认识到赛丝因为黑奴制的压迫而极度扭曲时,他被吓坏了,然后匆匆离开了124号。当时的保罗·D缺乏勇气,害怕承担,注定不能担当黑人家庭中丈夫或者父亲应有的角色。
与保罗·D不同,黑尔在疯癫之前也许可以被称作是一个有担当的丈夫和父亲。如果说保罗·D由于不敢承担责任而不去爱的话,那么黑尔可以说是把自己的爱都奉献给了自己的亲人。作为一个母亲的儿子他用自己的苦力赎回贝比·萨格斯的人身自由;作为一个妻子的丈夫,他返回甜蜜之家,试图救走自己的妻子;作为黑人男性的先行者,他敢于尝试白人的科学技术,学习算数,试图摆脱作为苦力的命运。然而,在整个小说中这个最有担当的男性角色却因看到自己的妻子被人凌辱,看到自己在黑奴社会中无能为力而被逼得癫狂。从此,小说中这个在叙述中若隐若现,被期盼归来的男性形象消失了,犹如奥德赛迷失了回家的方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男性归途的迷失也是他们作为丈夫和父亲身份的迷失。保罗·D也在归途中迷失过方向,他犹如一个流浪汉,滞留在一个印第安部落不知自己应去往何方,他告诉赛丝,他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走路,吃饭睡觉,唱歌,哪里都成,只要有个地方待就可以。这种随波逐流,毫无目的和责任感的做法在与赛丝交往的过程中得到了体现。
从表面上看,史坦普·派德为整个黑人集体的逃亡做主了卓越的贡献,然而他也是一个被精神阉割的黑人男性。负了一身债后,他被迫把自己的妻子让给主人的儿子,改自己的姓为“派德”(Paid),意为“已经偿清”,使自己牢记利用妻子自由换回的“自由身份”。
因此,派德与保罗一样,是对丈夫角色的逃避甚至亵渎。其“自由的身份”与被迫失去妻子形成鲜明的矛盾和讽刺,即使是自由之身也遭受了精神上的阉割。他在渡船上对逃亡黑人的帮助是一种赎罪,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虽然不欠白人但是有愧于自己的黑人妻子。他远离家庭,在渡船上漂泊,也象征着他对自己身份的放逐。
扭曲的母亲形象和迷失的男性形象使得黑人在面对生活时丧失了生活的欲望。自由的重拾并不意味着个人身份的重获,更不意味着拥有自由身躯的人能够解开心灵的枷锁,过上真正自由的生活。与之相应,贝比·萨格斯也曾提及:非裔美国的家庭早已被撕裂成碎片。贝比·萨格斯的孩子全部不知所踪,以至于贝比·萨格斯认为自己几乎不能通过血亲找到自己的身份,作为“自己”进行生活。
虽然黑尔在赎回贝比之后,贝比还意识到自己的心脏在跳动,开始试图学会热爱生活并在林中空地教导其他黑人也这样去做。但是学校老师的抓捕,黑人集体的冷漠以及赛丝的弑婴再次扼杀了贝比对生的欲望,晚年的她只能躺在床上辨别颜色——因为生活对她失去了色彩。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更像是在“过活”,而不是“生活”。
对于痛苦的回忆,人只能麻木自我才能减少疼痛。塞斯的疼痛就如同旧日的伤疤一样,变得麻木了。她喜欢把自己关在124号不知疲倦地揉面团,以为“像那样开始一天的击退过去的严肃工作,再好不过了”;而实际上她一刻也没有逃离过去,只是把过去的痛苦揉得麻木,同时也拒绝了未来。赛丝把自己的身份自闭在过去的时空中,把痛苦变成麻木,逃避未来,拒绝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
这种麻木的症候可以追溯到赛丝的“妈妈”。根据赛丝的回忆,“妈妈”也曾经在嘴上戴过橛子,以至于让脸变了形留下了总是挂着笑容的后遗症。这种对黑人不人道的身体摧残,形象地以这种似笑非笑的后遗症进行了表现,也反映了以赛丝为代表的非裔美国人集体对过去非人道待遇回忆的麻木自慰。
正如“妈妈”会机械地“笑”对耻辱,塞丝幻想起甜蜜之家时会想起其“美丽”的一面,尽管那个“家”本应该令她“惊声尖叫”。非裔美国黑人为了抹去伤痕的痛处,总会想方设法地掩盖疼痛,麻痹自己,痛苦的回忆便成为挥之不去的抑郁,让这个群体不敢正视自己新的自由的身份,展望新的未来。
黑人男性其实也深陷在这样的困境当中。自不用说疯癫的黑尔因受到过度打击而无法自拔,理智的斯坦普也是深深活在内疚之中的一个人。他希望通过帮助逃亡黑人摆渡来赎罪;也多次试图拜访124号向塞丝赔罪。就连表面上看上去总是乐观的保罗·D也会把自己的感情藏在自己的锡烟盒里。同样遭受黑奴制压迫的男人和女人把自己的感情封锁起来,不敢面对自由和未来,更无力独自抚平创伤。
而生活在这种麻木创伤家庭中的孩子,一方面因为被笼罩在上一代悲伤的记忆中,难以通过亲人建立健康的身份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没有亲身体验这些磨难使得他们对未来有所期待,丹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母亲整天被“鬼魂”困扰,封闭在过去中;祖母也缺乏生气,艰难地在病床上数着颜色,父亲则根本不在家中,丹芙身边连一个身心健康的血亲都没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丹芙是被迫进入了上一代人的痛苦回忆之中,从而无法从外界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份体验。比如丹芙多次从赛丝的口中听到自己出生的故事,以至于塞丝给她梳头的时候,丹芙居然会害怕母亲会突然杀死自己。值得一提的是,在丹芙出生的整个故事中,丹芙既不喜欢整个故事的前半部分(赛丝受辱的部分)也不喜欢故事的后半部分(赛丝弑婴的部分),而只喜欢自己出生时赛丝受到白人少女艾米帮助的那一部分。虽然丹芙的身份被这样一个满是创、伤深受奴隶制影响的家庭所掐扼,艾米作为新生的血液从来没有放弃过一丝机会建立自己新的身份。她敢于离开124号,像他的父亲黑尔一样到新生的集体中去听课,学习新的知识其实就是获得新生的一种表现。虽然途中被一个男孩子拽回黑奴的恐怖悲惨的回忆中不能自拔以至失聪,但是最后丹芙还是鼓起勇气向社区求救,终于赶走了代表悲伤回忆的鬼魂“宠儿”。
黑奴制的痛苦经历导致的非裔美国人出现的身份认同问题在当下依然不是旧话,身份的焦虑在当下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在急速变换的社会中如何指认自我,是人人都该去考虑并且面对的问题。
(责任编辑高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