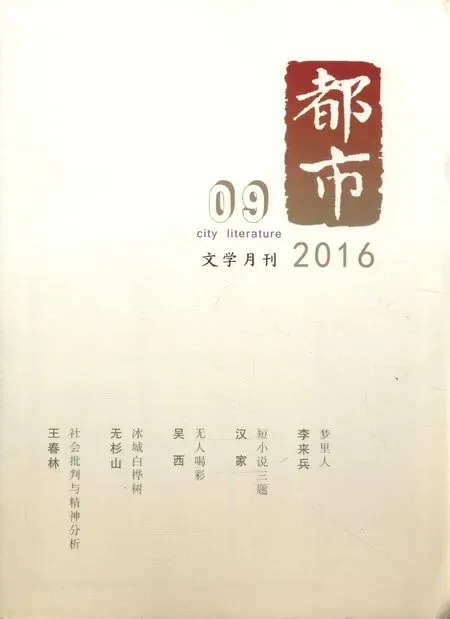短小说三题
2016-11-22汉家
汉家
短小说三题
汉家
澳大利亚
年少时的暑假,我喜欢上一个游走于山西的歌舞团,团名叫“新感觉歌舞团”,节目有唱歌、变魔术、穿三点式泳衣跳迪斯科、玩杂技、练硬气功,等等。
这个团在市中心广场搭了一个彩色帐篷,在帐篷里表演。我花了五元钱,买了一张票,进去一看,呵,好看!看完回到家,我对爸爸说,我想去乡下的姑姑家住几天。这个假期里,爸爸早嫌我烦了,就说去吧,待半个月就回来啊。我说好嘞。
爸爸给了我路费,将我送上了长途车。等他一走,我就下了车,跑到大帐篷里,问谁是团长。一个矮个子说我就是,你找我有什么事?我劈头盖脸地说,我不要工资,只想跟着你们演出,我可以抬道具、搭帐篷,团长,我什么都能干,带上我吧!团长正缺一个帮工,见我的个子挺高,看起来成年了,又不要工资,就说好吧,也许咱俩有缘,带上你就带上你吧,明天我们去晋南。后来,我才发现,袁团长的腿有问题,我们这儿管瘸腿的人叫“拐子”。
到了临汾,我们搭起大帐篷,搬出广告画,放迪斯科音乐,几个跳舞的姑娘负责卖票。我帮着搬这个抬那个。晚上演出,帐篷里烟雾缭绕,几乎全是男观众,姑娘们穿三点式跳舞时,一些兴奋的男人大声嚷着:脱、脱、脱!可是姑娘们令他们失望了,因为并没有脱。
散场时,观众们懊恼地摇着头,似乎不相信演出已经结束了。晚上,我们在帐篷里睡觉。那真是一个快乐的时刻,大家喝着啤酒,说着笑话,有几个男人搂着各自的对象。团里最美的姑娘叫李丽,一个高个子的男人搂着她,这人叫张帆,是一个魔术师。李丽是跳迪斯科的,她穿上三点式跳舞时,任何男人都不可能不盯着看她。团里演员少,李丽还在张帆的“大变活人”节目中充当那个活人。魔术没什么看头,但李丽穿着红色旗袍亮相的环节,却实在是看点,她美极了。旗袍分明是低档货,做工粗糙,但如此地适合她的身材,衬托着她的美丽——她的美丽使得这个魔术显得更加的无聊。
夜深了,我出去小便,听到隔壁李丽的呻吟声,没错,她与张帆睡在了一起——这怎么睡得着啊!
我们来到了运城演出,票房出乎意料的好。正表演迪斯科时,一个留寸头的、看上去挺斯文的人,突然冲着舞台喊:跳得好,再跳一遍!观众也跟着瞎起哄。姑娘们没有理会,下了后台。这个人又喊:操!到我的地盘不听我的话,你们还想不想活了!这时,有消息灵通的人告诉袁团长,此人是当地一霸,叫赖三,绝不能惹他。袁团长赶紧出来,笑着说,三爷来了,哎呀,得罪了得罪了!姑娘们,都给我出来,再给三爷跳一遍!姑娘们只得出来,又跳了一遍。跳完了,赖三说不行,还得再跳一遍。于是又跳了一遍。我在后台看着,姑娘们身上的那几块布已被汗水浸透,如透明的一样。这事似乎就这样完了。后来我才知道,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当天晚上,袁团长请赖三和他的小弟兄吃饭。赖三点名要李丽陪他睡觉,袁团长喝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他说三爷,在河南人们也称我一声“拐子袁”,都是道上混的,你是英雄,老子也不是狗熊!你喝多少酒,我就喝多少,只是这李丽还小,咱不能糟蹋人家小孩子么!赖三说好吧,你这个死拐子,我喜欢你,来,干了这杯!
——喜欢归喜欢,觉还是要睡的,只是陪赖三的不是李丽,换成了王霞。
王霞是袁团长的情人。
歌舞团到了晋城。原以为票房一定会好,袁团长头脑发热,竟然租下了一个大剧院,但没想到连日暴雨,上座极差。偏巧这时正赶上开工资的日子,人们问团长,说老袁啊,怎么还不开工资呵?袁团长说,对不住了,手里的钱都付了剧院的租金了,指望着演出能赚回来,你们也看到了,这鬼天气闹的,一场演下来,能收几个钱了!?大家再等等,再等等。
这一等就是一个星期,票房也不见好转,工资还是没有着落。午饭时,我听到张帆和几个演员商量罢演的事,大家都说好,就这么干!晚上八点正式开演,第一个节目是热带风情舞蹈。主持人报了幕,舞台上却不见任何动静。袁团长来到了后台,黑着脸说,咋了!不演了,撂挑子了!他狠狠地瞪了王霞一眼,看样子是埋怨王霞没有提前告诉他实情。王霞是个爽快人,说,怎么了?!不给大家发工资,你还有理了!众演员嚷着说,发工资发工资,不发工资就不演!就这样僵持到八点半了,观众们见还不演,就闹着要退票。袁团长有些下贱地笑起来,说各位祖宗,我老袁没求过你们,这次求求你们了,今天演了,最迟后天我就给你们开工资,我说话算话,我要是骗你们我就是王八!大家在一个锅里舀饭吃,我也不容易呵。说完这话,他的笑又似哭了。众人见袁团长的态度还算诚恳,就渐渐不嚷了。观众忍无可忍,有人已经开始砸座位了,情况极为混乱,可以说已到了失控的边缘。
终于开始演出了,第一个节目改为了迪斯科,为了平息观众的愤怒,6个姑娘在跳舞的开始就脱去了胸罩。我看到王霞的奶子的确比李丽的大一点,此时张帆与袁团长在后台亲切地聊着天——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掌声、叫好声、口哨声交集在一起,灌入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第二天,歌舞团取消了后几天的演出,改为去河北巡演。我偷跑了20天,也该回家了。工资发了下去,王霞对众人说,她也是刚知道原委,前段日子,老袁的母亲检查出癌症,老袁是孝子,将钱寄回了老家为老娘看病,现在发工资的钱,有一半是老袁向朋友借的。大家觉得袁团长这人还不赖。我向袁团长告别时,他摸摸我的头,说你是个好孩子,不给你钱,我总觉得心里不舒坦,这样吧,我送你一个笛子,当初我是个吹笛子的好手,这笛子就送给你吧,留个纪念。我说不用了,再说我也不会吹。袁团长硬塞给我,说不会吹难道不会学吗?我就收下了。
在歌舞团,张帆对我最好,我记下他的一个传呼号。再见了,我的“新感觉歌舞团”。
回到家,我才知道爸爸在我走后就联系了姑姑,得知我没有去乡下,急忙报了案,家里早已乱成了一锅粥。见我猛然间回来了,家里人喜出望外,反倒没怎么责骂我,只是反复告诫我以后再不能这样离家出走了。我一脸的愧疚,一个劲儿地说我以后不会了,我知道自己错了,以后真不会了。
我与张帆一直保持着联系。一年后,袁团长的老娘去世了,王霞回到了湖北老家,两个人终究没成。据说是因为袁团长离不了婚,但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大家也都不是很清楚。歌舞团解散时,袁团长没有欠大家一分钱工资,张帆说“拐子袁”挺仗义,还给多发了几个钱。
李丽与张帆去了深圳,在酒吧里演出。三年后,两个人分手,张帆说,李丽变了心,傍上了一个秃头老板。我考上了南昌的一个三流大学,整日浑浑噩噩,不知所终。笛子就带在我的身边,气闷了,我就吹几声,一概荒腔走板。张帆不当魔术师了,他的父母托关系把他安排去了地质队,成了一名勘测员。他定居在了太原。
十几年过去了,我现在定居南昌,结婚生子。张帆却依然独身。我和他在南昌和深圳见过两次面。在南昌见面时,他和李丽还没分手,他们从深圳过来看我,三个人喝酒喝到了天明,李丽靠着他的肩膀,样子很是幸福。在深圳见面时,李丽刚离开了他,他骂李丽是个不折不扣的婊子!我冲他吼,说张哥,你别骂了,你告过我,说李丽为你流产了四次,就凭这点,你都不应该骂她!他听后,果然不骂了,低下了头。
今天我们约好了见第三次面,我从南昌来太原见他。
见面后,我们都有些激动,相互之间又有些觉着陌生——也许就是因为这种陌生感,才使我们变得异常激动。我们拥抱在一起,用力地拥抱着对方。坐下来聊天时,我说,张哥,你还变魔术吗?他笑着说,当然变了,不变魔术我就觉得活着没意思,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变一个!说完这句话,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拿起了一个精致的帆船模型,将这个模型伸到了我的眼前,几乎是贴在了我的眼睛上。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变了呵,我变给你看,只要你上了这条船,你就来到了澳大利亚!
我瞬时感到了目眩神迷,浪头翻滚,雪白的泡沫四处飞溅,大陆的板块挪移,我似乎看到了悉尼歌剧院正在拔地而起,看到了铺天盖地的袋鼠向我奔来,晕眩在加剧,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今夕是何夕,我的脚步摇摇晃晃,眼看着就要瘫倒在地上——李丽正在阳光明媚的窗前喝着下午茶,显得怡然自得,她不再是那个魔术节目中变出的卖弄性感的大活人了,她移民去了澳大利亚,生活在悉尼郊区的一套公寓里,秃头老板对她疼爱有加。李丽无所事事的时候,总是喜欢把玩一个精致的帆船模型,记得在晋城那段多雨的日子里,她与张帆曾在类似这个模型的模型上做过一次酣畅淋漓的爱,这个模型虽小,但当时的张帆硬是在这个小小的模型上鼓起了一张真正的巨大的帆,而她当时涌出的那一道浪头竟然在电光石火之间勾起了此时此刻太原翻来的这一道浪头。
大东关绑架案
太原有一条大东关街,这里发生过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
大东关住着一位诗人。有一天,这位诗人与我喝酒,闲聊中他说,汉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说好呵,我正愁找不到素材写小说哩!他说好,我说了啊……再给我倒杯酒,不要啤的,要白的——故事是这样的:
南蛮子阿海是个批发文具的小老板,来太原五年了,也有人说十年,不过这不重要,就算他十年吧,反正我们又不认识他。阿海做生意发了小财,太原这个地方造就了很多南方来的老板,让他们发了财,本地人却没有赚钱的脑筋,绝大多数都过着紧巴巴的日子。人都有倒霉的时候,去年阿海被一个叫蒋原生的人连骗带借地掳走了15万,对于小老板而言,这可不是一笔小钱。阿海想尽办法去讨债,但这个蒋原生绝不是一个善茬子,每次讨债,阿海都得碰上一鼻子灰。阿海是个外乡人,也不敢与他来硬的,就这样拖了下去。后来,蒋原生干脆失踪了,杳无音信。去报案吧,这钱也算是笔借款,不太容易立案;去起诉吧,担心等着判决下来了,却不好执行。再说,去起诉了,以蒋原生的那德性,阿海又怕他暗中报复自己。一时间,阿海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中。
这时候,阿海的一个朋友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不行,就找黑社会讨债吧,又快又保险。阿海说,说得容易,怎么找?我是个生意人,从没和这些人打过交道呵。这个朋友就说,我给你联系,我认识红脸肉毛,这事交给他办,准行!
阿海想了想,确实自己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就说行,那就拜托你了,找红脸肉毛!
不出两天,阿海通过朋友的联系,就见到了红脸肉毛,嗬,这人果然长着一张红脸,脸上却无毛,也不肉——不管这人长得怎么样,一看就长得不像好人。肉毛在酒桌上对阿海说,这还叫个事了?!你交给我办就好了,绝对让你满意。阿海听了这口气,心里想这下算是找对主了。肉毛说,他欠你多钱了?阿海说,欠我15万,你帮我要回来,我给你7万。肉毛说行了,7万就7万,最多一个星期,我就给你闹回来,闹不回来我就白混了!阿海说好好好,咱们先喝酒,肉毛哥,你真是我的好大哥。
5天后,肉毛给阿海打来了电话,说阿海,你来趟东山,我们把那个王八蛋绑住了,他要当面还你钱。阿海一听,喜上眉梢,急忙开车赶到了东山。在一个隐蔽的空地上,阿海看见了蒋原生和肉毛,旁边还有肉毛的几个小弟兄。仗着肉毛在,阿海的胆子也壮,上去就先给了蒋原生一个耳光,接着一顿乱打。这时,肉毛过来拉开了阿海,说别打了,他能还钱就行了,以后大家还是朋友嘛。阿海觉着说得也对,毕竟以后日子还长了,别做得太绝了。他擦了擦手上的血,对蒋原生说,把老子的钱还给我!蒋原生用手抹了抹嘴角的血,以挑衅的口吻说,我没钱,拿甚还你了?!阿海愣了一下,看着肉毛说,肉毛哥,你不是说他当面还我钱么,这是怎么了?!肉毛一听也火了,大声骂道,我操你妈,你和老子说今天见了阿海就还钱,咋变卦了?!蒋原生说,少和老子来这套,老子就是没钱,咋了?!肉毛对着蒋原生就是一脚,将他踹倒在地,然后劈头盖脸地打他。正打着,没想到蒋原生顺手抄起一块石头砸在了肉毛的头上,肉毛火了,从口袋掏出一把跳刀,狠命地刺进了蒋原生的肚子里,鲜血喷溅在了地上。
蒋原生躺在地上不动了。这可把阿海吓坏了,嚷着说,这钱我不要了!转身想跑进车里。肉毛飞快地在阿海脑门上捣了一拳,这一拳捣得可不轻,阿海都有些晕眩了。肉毛说,你现在想跑了,闹出人命你就想跑了?!我们是从他姐姐家绑他出来的,他家人都知道是我出面绑的,你跑了,我给你抵命去!?你个傻逼南蛮子,就算我杀了人,也是你主使的,你也要挨枪子!!阿海已经懵了,不知怎么办才好,整个人呆呆地立在一个土坡前,像僵尸一般。一个叫二狗的小兄弟凑到了蒋原生的脑袋前,他突然喜滋滋地喊,肉毛哥,他还没死,还有气了!阿海听了,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大声对肉毛说,快,快送他去医院!我出钱给他看病,只要他不死就行!
分两拨人,几个小兄弟送蒋原生治刀伤,肉毛和另几个兄弟押着阿海来到了大东关街的一个居民楼里。治刀伤的那拨人没去医院,因为是刀伤,去医院肯定会暴露,报了警就麻烦了。他们去的是地下诊所,专治黑社会性质的重伤患者,诊所的外面是个小超市,外面的人绝对想不到这里面竟然是一个堪称专业的急救诊所。
肉毛对阿海说,你先拿20万,要不大夫不收这家伙。阿海说好,肉毛哥,我这就回家给你取钱。肉毛啪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你要是跑了咋办?!那个王八蛋没治好以前,你就在这里住着,哪也不许去!钱叫你老婆送过来!阿海点着头,浑身冒着冷汗,不停地抖着。阿海从此被锁进了一个小屋子,过了几天说,蒋原生动完手术了,快好了,又过了几天,说病情突然严重了,人快死了,还得拿钱,反反复复好几次下来,阿海已经掏了80多万医药费了。
阿海刚被押来的时候,肉毛还给他吃个盒饭,后来连盒饭也不给了。有一天中午,二狗喜滋滋地扔给阿海一颗大白菜,笑着说,你就吃这个哇,解饿又解渴!20天后,阿海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挣的钱全拿出来了,文具店也卖掉了,身上再无半分钱了。
二狗看守着阿海。最近几天,肉毛一直没有来,往常他每天总要来瞅一瞅阿海。
第二十一天,阿海昏死了过去。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接着门打开了,几个警察进来,其中一个摇着他的肩膀,对他说醒醒!快醒醒,我们是警察!阿海终于睁开了眼睛。到了刑警队,阿海才知道肉毛是因为前段时间的另一起严重的聚众斗殴案被逮捕了,审讯中他为了立功减刑,就一口气招了阿海的案子。阿海听了这些情况,依然胆战心惊地对刑警队的刘队说,刘队,可是可是……蒋原生现在怎么样了?刘队笑了,说你还蒙在鼓里呢,那个姓蒋的根本就没受伤,他们给你演了一出戏,是在耍你了!
原来,肉毛在接了这个活儿的第二天就找到了蒋原生。肉毛说,闹了半天是你呀!你不是旱西门的赖小么!蒋原生说,是了呀,肉毛哥,我就是赖小么,蒋原生是我起的个假名字,嘿嘿。肉毛说,少他妈和老子套近乎,还钱!赖小说,我吸毒两年了,钱都买了毒品,反正我也不想活了,肉毛哥,要不你弄死我算了!肉毛说,操你妈!你以为老子不敢弄死你!赖小说,来吧,弄死我哇,弄死我你也闹不出一分钱!肉毛看着赖小形容枯槁的样子和家里面的破败相,明白确实是要不出钱了——操,这不白忙活了吗?赖小这时说,肉毛哥,你听兄弟一句话,咱们不如联合起来闹那个南蛮子了!肉毛说,怎么闹?赖小说,你放心,听我的,保证让你合合适适的。
——他讲完了这个故事,对我说,汉家,这个故事怎么样?我说不赖。他说,还没有完了,阿海在得知真相后,突然就精神不正常了,疯了,唉。
和这位诗人喝完了酒,我在回家的路上想,阿海估计得到真相后,觉着人世完全颠倒了,一点儿也靠不住了,或者觉着自己实在是太傻了。我准备将这个故事写成一篇中篇小说,但以中篇的容量来看,这个故事好是好,就是内容太过单薄了,我想不妨这样写:把阿海作为切入点,从他的小时候写起,写他怎么辍学,怎么成长,怎么初恋,怎么跟着亲戚做生意,怎么来到北方,等等等等;由此展开一些社会思考,并从肉毛的身世入手,对黑社会进行点睛式的描写,再加入一段职业流氓的爱情故事……打住!我觉得我这是在滥用想象力,这样写小说是不行的——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有一种特别困难的意味,所以迟迟没有动笔写它。
后来,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我听到同学说李建明坐牢了。我详细一问,才发现李建明就是这个绑架案中的二狗。有个同学还去牢里看过他,据说他穿着一身合体的囚服,一副喜滋滋的样子。我记得,他曾获校运会1000米的跑步冠军,颁奖那会儿,他的样子也是喜滋滋的,美着呢。这个人总是喜滋滋的,好像他无论做什么都充满了奔头似的。
总的来说,他不是一个好人,但他总是喜滋滋的。也不知道这个混蛋到底为什么喜滋滋的,他凭什么?
我俩都是关西人
我是东京人,现住在岛根。
我可能是全日本最失败的小说家,这样说难免令我丧气,但这是事实。
我写了三部小说,通过朋友开的出版社才得以问世,一共也没卖出三百本,批评界对这三本小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尝试将小说寄给自己心仪的评论家,要么没有回应,要么就是诚恳地对我说,吉田先生,改行吧,你并不适合写小说。
我的灵感或许永远枯竭了,写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我毫无办法。在岛根租住的小屋里,我度过了难耐的冬季。心情好时,我常去津和野,那些遗迹不动声色地注视着我。
初春,我去旭川探寻一个幼时的伙伴,为了带给他惊喜,去时未通知他。到了他家,才得知他于两个月前得胃癌去世了。我免不了又感叹一番人世的虚幻,祭奠完他,我立刻回到了岛根——我只想尽快回到岛根的屋里。我对岛根以外的地方都不感兴趣,尤其对东京厌恶透顶,那里的房子我委托邻居照看着,已经很多年没回去了。东京对我来说,如同是妖兽出没的都市,它令我活着就像做着一个恐怖的梦。
我住的地方,只有安藤知道,他就是那个出版社的社长。有一天我接到安藤的电话,他告诉我有一个女读者想见我。安藤说这个读者是他在出版界的一个朋友,买过我的三本小说,名叫淳子。我不善于和陌生人交往,说不见,安藤还是想让我见一见,并说她在当编辑前是一个能剧演员。最终,我答应了见面。安藤知道我爱看能剧。
淳子来之前给我打了个电话,连说冒昧。我说谢谢。她的声音很动听,听起来似乎只有二十多岁。
没几日,她来了。我正在里屋呆坐着,听到了敲门声。我开了门,她看起来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清秀的样子,穿蓝色连衣裙。她说您是吉田先生吧?我说是的。她说我是您的读者,安藤先生介绍来的,我叫石川淳。进门后,她显得极为拘谨。我请她坐下,她孤零零地站了一会儿,似乎不情愿地坐下了。气氛有些尴尬,我自嘲说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买我书的读者,这个世上没几个人看我的小说。她急忙说我喜欢您的小说,一直想见您呢。您小说里的主人公行事都很滑稽,让我忍不住发笑,结局却悲凉得很,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我想吉田先生一定是个满头白发的人呢(她笑,低头,又笑),没想到您这么年轻呵。
我俩都是关西人,我的老家在姬路,她的则在滋贺。我问起能剧,她说自己不演了,现在一个杂志社工作。我们边喝茶边聊天,她粗通茶道,我卖弄了一些茶道的学问。看样子,她很快乐。黄昏时,她告辞,说已经订了酒店。我说好。
我们约好第二天去出云大社。
我多次去过出云大社。淳子是第一次去,她看什么都觉得新鲜。我对淳子说,据传到出云大社的人,可以得到良缘,此后婚姻美满。淳子的眼睛发亮,对着我说是吗?吉田先生,一定是的吗?是吗,吉田先生,是这样的吗?!她这样一连串的疑问句,让我莫名的有些惊讶。中午,我们吃出云面,这是本地的美食。她说起了家乡的鳗鱼烩饭,笑着说想起了就流口水。我问她多长时间回一次滋贺,她说,半年回一次,住在东京那个鬼地方,只知道每天忙着打转,像是被提线的玩偶。
离开出云大社,路过公园,一群小朋友由老师领着背诵地理名词,阳光照来,有一分年少无知的好处。淳子停下了脚步,我站在她的身后。“长野、富山、札幌、爱嫒、高知、香川、滋贺、福冈、佐贺、长崎、秋田、山形、姬路、鸟取、广岛、大阪、神户、奈良……”——孩子们背诵到滋贺与姬路时,我与淳子大声应和着,兴高采烈。淳子流出了眼泪。她对我说,吉田先生,我的妈妈住在滋贺,老人家喜欢小孩子,庭院里还有我种下的一棵苹果树呢,可是这棵树得病了,因为它从来都没有结过果子,哈,您要笑话我流眼泪了吧?
第三天她要回东京了,与我来告别。我送她一本唐诗集,她还是很羞涩,两手交叉着。我注意到她的手,真是纤细极了,就像是人体材料的艺术品。她忽然红了脸,好像与人争抢似的说,吉田先生,我要走了,您抱抱我吧。我说不好吧?
我还是抱了她,她很轻,我感觉像抱着一团棉花。屋里没有风,抱她时却感到起风了,整个人飘摇着。她出了门,笑着说吉田先生,您的家很久没清扫了吧?如果我再来拜访您,一定给您打扫屋子,再见!
我说我们还会见面的,再见!
在交代淳子的下落前,有必要先介绍我的三篇小说。第一篇小说,我写的是一个恋爱故事,写得很琐碎,男女主人公艰难地相爱着,最后男主人公死于一次大地震。这是一篇在技术上非常糟糕的小说,语言上明显不自信,但因为这是我的处女作,所以我对它依然充满着感情——内心中一种时光般的情意。第二篇小说,讲述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如何成长为一个黑社会成员,结局是这个青年在一次犯罪中被一个刚认识的女孩所感化而开始了新的生活。第三篇小说,是杀夫的故事,一个妻子对丈夫绝望后,用斧子杀死了熟睡的丈夫。三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地分别是东京、大阪和东京。
淳子大概走了一周,安藤打来了电话,说吉田啊,那个淳子,就是你的那个女读者淳子,她杀死了自己的丈夫。我大惊失色,忙问是多会儿发生的事?他说听人讲是在淳子来岛根之前,也就是说她在杀夫后才见的你,回到东京她就自首了。我接完电话,强烈地想见到淳子,就开车连夜赶回了东京。我心急火燎地找到安藤,托他打听淳子的下落,看看能否去监狱探望她。安藤忙着找熟人帮忙,折腾几天后,他告我你别去了,就在一小时前,淳子自杀了。这个悲伤的结果更加深了我对淳子杀夫的疑问。我拜访了淳子的一些好友,模糊地知道了她生前的一些情况:淳子考上了东京的一所大学,她的第一个男友是同学,死于多年前的一次大地震;接着她去了大阪,学习能剧,五年后她带着第二个男友的骨灰回到了东京;三十岁时,她与一个舞蹈老师结婚,从此不再演能剧,进入杂志社担任了编辑;夫妻俩没有生育孩子。
——九年后,淳子在丈夫熟睡时用一把斧子砍死了他。
淳子安葬后,我去墓地看她。墓碑上刻着她的名字“石川淳”,还有她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依然很羞涩,像是又起了风,她笑着,说抱抱我吧。我几乎确信淳子就是我写出的主人公——她的生活轨迹像极了我三篇小说的总体情节,但她分明不是我虚构出来的人物,而是无比真实的一个杀人犯,一切都发生在冥冥的创造中。我感到了莫名的紧张,为了延续这种残酷的真实性,我来到了滋贺,千方百计探听她的家。很幸运,我见到了淳子的母亲,她住进养老院里。我买了礼物,以淳子朋友的身份去探望她,向老人家求证那棵苹果树。她说是有一棵她种的苹果树,长得很茂盛,结很大很大的苹果。说到这里,老人家用手比划着苹果的个头儿,流着泪说,淳子还不如一棵树呢,她生不出小孩,那个男人总是打她,唉。
我特意去了当地一家有名的餐厅,品尝鳗鱼烩饭。我很失望,烩饭不仅味道偏咸,鳗鱼也不新鲜。我离开滋贺前,正是一年一度的大津烟花会,望着烟花染亮的夜空,我就要离开淳子的家乡——淳子,我知道你没有死,在我即将写作的第四篇小说中,你将是一个最终回到关西的女人。而安藤,这个在第三篇小说中与你偷情的人,我将不顾同学的情谊,让他在下一篇小说中身败名裂——他只配做一头不知疲倦的种马。
石川淳的丈夫叫山本一男,他天生不产精子。
那是一个原本无事的夜晚,山本一男被砍死前无意中看到了妻子做流产手术的交费单据。
(责任编辑高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