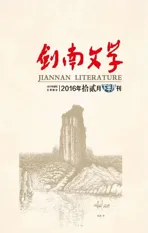严歌苓小说中关于“创伤”书写的独特之处
2016-11-21李丹
□李丹
严歌苓小说中关于“创伤”书写的独特之处
□李丹
引言:严歌苓在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下逐步构建起独属于作家自己的文化观,在面对故国“文革记忆”时能够采取越来越从容的态度,所以她的小说主要注重的是对那个时代人性的重新挖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审视和反省。
海外华人作家书写的作品在近年来一直受到国内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作家严歌苓便是个中代表,她的作品频频被改编成电影及电视剧,受到了国内大众的普遍欢迎。纵观严歌苓的作品,其在书写上与其他海外作家有着鲜明的不同,较为突出的便是对于“创伤”的书写。这可能与作家自身经历有所关联,在“文革”开始时,她尚年幼,孩童的记忆深深影响着她日后的创作,并且在移居海外后随着生存境遇的改变和文化观念的撞击,其创作态度与视角也随之悄然发生改变。严歌苓对于“文革”审视的视角由身在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静的反思。与此同时,严歌苓自身也实现了由国内到国外,从边缘人生到功成名就的过程。作家在作品中采用全新的视角进行文化身份上的建构,无论是故事视角还是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尽管都是对于“文革”题材的书写,但是严歌苓并没有像其他作家一般将曾经历经的各种伤痛与苦楚重新展示到众人面前,揭示自身的伤痕与心灵的创伤,而是用全新的视角铸就着成长的故事。严歌苓在此基础上无论是关于“创伤书写”还是移民书写都为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阅读体验与心灵触动。从描写《天浴》、《白蛇》中女主人公凤凰涅槃的自赎过程到《第九个寡妇》中如“大地之母”一样坚强的王葡萄;从前期作品中迷失自我的“我”到近年作品中不断突破自我的“我”,变化不仅体现在形象上更在于新奇多变的叙事视角。严歌苓在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下逐步构建起独属于作家自己的文化观,在面对故国“文革记忆”时能够采取淡然、从容的姿态,将自己从周遭的环境中剥离出来,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冷静而客观的书写曾经的全民族的疯狂。正如严歌苓对几位国外的移民作家的评价一样:“有许多作家都是在离开乡土后,在漂泊的过程中变得更加优秀的。康拉德、那布可夫、昆德拉、伊莎贝拉?阿言德……他们有的写移民后的生活,即便是写曾经在祖国的生活,也由于添了那层敏感而使作品添了深度和广度,添了一层与世界、其他民族和语言共通的襟怀。……这是移民生活给他们视角和思考的决定性的拓展与深化。”[1]
正是由于那无处不在的人性书写使得严歌苓“文革书写”能够被对于中国历史不甚了解的世界人民也能有所接受与理解。关于人性的讨论“使作品添了深度和广度,添了与世界其他民族和语言共同的襟怀”,这才是严歌苓“创伤书写”作品中最有价值之处。严歌苓的与其他作家关于“文革”写作的,都是讲述那段历史给无数国人带来的灾难与痛苦。但是她的小说却在叙述上呈现出另一种风格,她在叙述故事时态度更加理智、客观,侧重点更多的是在于展现历史事件中各类人所表现出的人性,而可以忽略其中的血腥、暴力。正如严歌苓所说,中国人喜欢用“血泪史”来讲述此类历史,或者用“血泪斑斑”等词汇。但这些带给读者的只是一时的情感宣泄,严歌苓认为越是控诉的声泪俱下,事后就会越快被人们所忘记。所以在她的小说中重要的是对那个时代人性的重新挖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审视和反省。严歌苓对于“创伤”叙事之所以能够采用全新的视角和更加广阔的视阈,其根源在于严歌苓在经历出国留学、定居他国远离故土后,在心理与时空上重新审视和回顾民族曾经的历史和自我生命体验时变多了几分疏离和冷静的忧伤。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