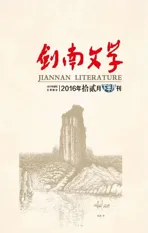二次降临
——以印度神话观念解析《悉达多》
2016-11-21徐展
□徐展
二次降临
——以印度神话观念解析《悉达多》
□徐展
引言:虽然《悉达多》的故事借用佛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之名,但选择从生活中体悟自我的悉达多最终与舍弃生活苦修证道的乔达摩殊途同归,实则更符合印度神话哲学中的入世修行理念。从神话原型理论的角度,以印度神话中主神毗湿奴的梵我理论解析文本,将感性至上的印度教青年悉达多与理性至上的佛教创始人乔达摩加以对比后,可以看出作者对印度古典的“梵我同一”思想——即自我与世界的一体共存的入世思想的认同。
《悉达多》是人道主义作家黑塞的第九部作品。作为德国浪漫派最后一位骑士,黑塞在这部作品中致力于寻求心灵困境的解脱之道。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作为主战场的欧洲西方世界满目疮痍,人们更是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很多人开始悲观厌世,黑塞亦陷入困顿之中。于是黑塞以写作的方式寻求“自我”,力求不再逃避。但在面对现实之前,他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找到“自我”的真正意义。于是黑塞开始探索东方觉悟之人——佛陀的解脱法门,但他的方法却不是佛教式的:将释迦牟尼的名字悉达多·乔达摩一拆为二,一个是已经觉悟成佛的佛陀乔达摩,一个是探索自身心路的婆罗门青年悉达多。这样的区分无异于让佛陀重走了一次人生之路,以不同于修行的方法在生活中觅道,最终与本有的正觉成道故事殊途同归。
而在印度神话中,主神毗湿奴曾扮演不同角色入世来拯救人间危难,佛陀本就是他在人间的一种幻化形象。黑塞可以说是在笔下令佛陀再次幻化,以印度神话哲学里的神祇入世游戏的方式,来阐述感性至上的生活探索与理性之上的苦修证道最终得到的结论是可以一致的,最后证明的都是梵我合一,即自我与世界的一体共存。
一、造化游戏
在印度神话中,主神毗湿奴性格温和,常化身成各种形象拯救世界于危难之中。他曾十次幻化入世,第九次便是化身为佛陀。这位美丽的神袛沉睡于蛇床之上,在宇宙之海中漂浮,从他的肚脐中长出了一株莲花,莲花绽放时发出了数千倍于太阳的光华,其中诞生了梵天,然后梵天再创造了世界——深受印度教影响的佛教经典《大正藏》有言:“脐中出千叶金色妙宝莲花,其光大明如万日俱照,华中有人结跏趺坐,此人复有无量光明,名曰梵天王”,记载的就是此事。[9]
但也有这样的说法。毗湿奴又名“以土地为胎者”,意为大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腹中。相传仙人靡坎德耶想要探知宇宙创造之奥妙,结果心念一动,便突然处于这个世界之外。他发现自己堕入茫茫黑暗,只有无边无际的水在四周,唯见一人躺在水中,身放异彩,驱除黑暗。仙人知道,这是毗湿奴大神,便努力向大神靠近。此时毗湿奴张嘴一吸,把仙人吞了下去,他又重新处于混沌之中。仙人以为刚刚遇见大神只是梦境,便继续寻觅,直至在混沌中重新遇到栖身于此间的孩童样貌的大神,才明白整个宇宙都是毗湿奴的表现。神是时间,是创造,是毁灭,是万物之源,息止之地,是无分别的永恒……在充满阳光和生灵的、运转不息的已知世界中,摩坎德耶已辨不清什么是幻梦,什么是现实了。他想:“这是我所呆过的世界,还是天神的幻想?或者说,这是那罗延呆过的冥冥黑暗,还是我的幻梦?”
实际上,在印度神话哲学中,虚与实是不需要分别的。在印度哲人看来,一切皆是造化所现,以土地为胎者,纳须弥于芥子。因“梵我不二”,神其实从未处在幻梦之外,更是在每次入世时全情投入于命运之中,如同出演一场戏剧。因此,持此思想的人提出了疑问:既然虚幻看起来如此真实,身处其中的人们又应如何行事,才能感知真正的真实?毗湿奴第九次入世为佛或许就是给予了一种答案——以苦修入道证破虚幻,而黑塞告诉我们,或许还存在着另一种。
二、梵我同一
据记载,佛陀乔达摩·悉达多是其母摩耶夫人梦白象而感怀,在无忧树下所生的。摩耶之名,在梵语和巴利语中意为“幻化”,在佛经中又被尊称为摩诃摩耶,即“伟大的摩耶”。在印度神话中,因梵天创世,神学家们就从梵天一词中概括与抽象出一个形而上学的实体“梵”,并将其作为世界的最高实在,一切事物的主宰,而现世为摩耶世界,即不真实,想要认识真实,就要进入梵我境界。[7]同时,婆罗门又称佛为梵,即清净者之意。《俱舍论二十四》曰:“真沙门性,经亦说名婆罗门性,以能遣除诸烦恼故。佛与梵德相应,是故世尊犹应名梵。由契经说,佛亦名梵。”[6]因此,摩耶夫人诞下佛陀乔达摩,就代表了生下作为真实之理的“梵”的,正是这无明幻梦的“摩耶世界”。
生下佛陀后的第七天,摩耶夫人就逝世了,佛陀由其父净饭王和续妃波阇波提抚育长大,作为太子娶妻生子后,某天中夜离城出家修行,后来发现所学的都无法解决他心中的问题,35岁终于放弃苦行,证觉成道。这位释迦族的圣人,足迹遍布恒河流域,说法不分种性高低。由摩耶所生的他最终破执而出,去无明(无知)生般若(智慧),只因从一开始他就失去了母亲,也就是与这世界的幻梦本质彻底分离,于是一生都走在理性至上的“梵”的道路上。
印度神话中,三相神梵天、湿婆、毗湿奴是梵的化身。因为梵是“非概念”的,是不能表露的,所以需要以游戏扮演,即化为人身实体的方式展现在世间。在主神毗湿奴化身为佛陀之前的一世,他曾化身为奎师那,代表性的姿态是以左脚坚定地立于地面,同时右脚轻轻触地。因为左半身是心脏所在的一侧,右半身相较更安稳宁静,所以在印度神话哲学中,这姿态表示他立足于物质实在,同时了悟精神实在,直到他死的时候才改变了姿势,换以左脚搭在右脚上,露出左脚脚底。因此哲人们认为,这意味着毗湿奴下一次入世成为佛陀后,选择了侧重精神实在而避弃物质实在,也就是以右脚为表征的内省式解脱之道。[10]
佛陀选择从内心寻解脱的方法是理性至上、脱离世俗。但,如果还可以再游戏一次的话,或许毗湿奴会选择另一种成为佛陀的方式。黑塞所描述的那个与佛陀同名的人,他的一生经历正是那第二种选择,他的选择代表了向外体验、感性至上,他的觅道之路其实就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婆罗门的儿子悉达多,从小便知道“梵”是世界的终极存在,它和作为内在原人、作为人的本质或灵魂的“阿特曼”在本性上如一,人生于隐藏着梵的摩耶幻世之中,应努力去认识“阿特曼”,这便等同于认识“梵”,只要亲证梵和我同一,便可从而获得解脱。想要获得解脱,就要摒弃一切,摆脱尘世的无明种种。为此,悉达多像佛陀那样出走了,他选择成为沙门。他离开亲缘,离开师承,甚至企图离开自我——但最终他发现的正是“我”。这个“我”独一无二,不可替代,也不能由模仿他人而摆脱循环,获得解脱。当悉达多离开衹园,走向自己时,那觉悟的一刻就像王阳明龙山悟道时一样,充满了欣喜与孤独。佛陀开悟,曾是因为一颗星星。当时他坐在一棵菩提树下,发下不开悟不起身的誓言,在第七天夜晚,身心放松时,抬头望见一颗明星,就此开悟证道。而悉达多那一瞬间的感觉,却是自身于无边无际的黑暗混沌中,成为了一颗星星。原来星即是我,因自己能发光,便可照亮自己,这样无论选择任何道路,都可以不惧前行。
三、生活修行
在意念中观星证道,是密宗中的“准提法”。据记载,佛门戒律森严,跟随佛陀的人更需严格遵守才能为僧,准提菩萨慈悲,忧虑学佛者少,便立下这一法门,使人可以在正常生活的同时进行修行。凡夫以菩提为烦恼,而菩萨以烦恼为菩提,可见生活本就是一种修行的方式,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需要统一于实践。
出走的悉达多不同于出走的佛陀,他在证悟之前还从未体验过生活。于是他去体会,去感受,他要亲自去渡过自己的生命之河。摆渡人将他带入红尘世界,他则把世俗种种看做游戏,因着自己是悟道之人,便将众生看轻。悟道之人,也只是人。此时的他,以为自己是在认知“我”,却不知自己是在远离“我”。因为,悉达多的入世实践只是在仿效着大众的生活,却未曾真正深入体会思考生活的真谛,所以是不同于毗湿奴入世的游戏人间的。
在《摩诃婆罗多》中,毗湿奴通过化身为奎师那而入世,实践外视式解脱之道。奎师那作为毗湿奴的最主要化身,是万源之源,是至极真理,但他同时是人生下的神,有着拥抱世俗生活的特征,幼年顽皮出众,惹人喜爱,长大后极富魅力,在战场上被所有英雄所崇敬,在生活中也受到一切女性的狂热爱慕,正如其名之意“黑天”一样,黑色能吸收光谱中的七种颜色,这代表了他具有一切的吸引力。[5](P175)他的一生都在冒险,各方面都战无不胜,他对一切生灵都满怀深情、一视同仁,世间的一切也都同样钟爱着他,这正是他的入世化现。[3](P59)在《博伽梵歌》中,他为了消除阿周那的疑惑,揭示了自己的宇宙面貌:“我是非人格‘梵’的基础。没有智慧者,不能全面认识我。由于知识浅薄,他们无法认识我永不消逝的、至尊无上的本性。人若能了解我显现和活动的超然本质,离开躯体后,再也不会降生于这个物质世界,他将晋升到我永恒的居所。在千千万万人之中,可能只有一人追求完美;在那些达到完美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真正了解我。伟大的灵魂,奉爱中的瑜伽师,到达我后,永不再重返这充满痛苦的短暂世界,因为他们已达到了最高的完美境界。”可见,只有出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才能达到梵我合一。
而悉达多则不同。他因对名妓甘玛拉的迷恋而进入生活,投入尘网中,一步步泥足深陷。对他而言,男女欲情是交易,世间其他事务也是交易,能够感知、得到、付出的都是物质的层面,而精神上却无法得到滋养。他拥有财富,但始终并不懂爱,不懂付出又谈何获得?即使是最初触动他选择生活的甘玛拉,也不能拯救他的精神滑坡。
摩耶世界的大千幻象令悉达多迷失了“我”,而作为毗湿奴化身的佛陀,却是在放弃摒弃物质的苦修后获得了绝对理性的证悟。不与女性相联系在玄学上意味着弃绝物质实在,但佛陀能够开悟不止因为准提法的明星,也是因为一位女子的帮助。如果他没有接受牧女苏耶妲的乳糜之供,是不能恢复体力开悟成为“佛陀”的。《毗湿奴的七个秘密》中记载,“《梨俱吠陀》中说,欲望是创造之源。因精神实在毗湿奴渴望了解自身,脐中生莲诞生出了梵天和梵卵宇宙。而为了脱离苦难,人必须断绝所有的欲望。随之而来的是弃绝一切行动,生命终止。这是禁欲式的修行方式和内省之道,最终达到佛教徒所说的涅磐之境,类似印度教的解脱,吹熄生命之火,超脱生死轮回。没有欲望,毗湿奴不会醒来,湿婆不会对原初物质张开眼睛,女神不被认知。没有摩耶,没有梵卵宇宙,没有主观实在,没有人对自然的观察,没有人类意识绽放,只有没有神我的自性。精神实在与物质实在分离即意味着毁灭。”生活是修行的道场,但不是修行的全部,舍弃生活的苦修同样也不是修行的全部,想要获得“梵我合一”,就需要和初证道的佛陀一样,放弃感性与理性的绝对二分化。同样在印度神话哲学中,在认识“阿特曼”与认识“梵”之间,意识到两者同一的唯一办法就是与世界和解,不逃避亦不沉溺,在如水的生命中获得真正的清净圆融。
悉达多疲于轮回,厌倦一切,开始赌博、掷骰子。这个举动同样本具有哲学意义。在印度神话里,三相神中与梵天、毗湿奴三位一体的湿婆,也是常与妻子帕尔瓦蒂掷骰子的,那是至高神夫妇在为时间和空间制定规则,而当他们争吵之时,宇宙的奥秘就会流泻而出。神的游戏不止是游戏,因此神游戏于世,并不至于迷失,而当人模仿神的行迹之时,便会迷失于自大之中。悉达多是幸运的,他还知道止步于生活。当老去的悉达多坐在芒果树下,仰望星空之际,他放下了人间的生活。在他看来,为认知生活而生活,不能带来认识,只能带来空虚,曾经的顿悟似乎只在一瞬间,离开那个时刻便无迹可寻。可是,并不是这样的,星星于白日将会隐没,但它依然存在于那里。可以说,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来源,正因为有了感性基础,才能在思考中深化、发展到理性认识,感性至上的悉达多。
四、回归自我
在作者黑塞的所生活的西方,人们相信的《圣经》哲学中说,“你们要像小孩子,才能进天国,因为天堂是他们的。”这一点东西互通。就像《西游记》中的唐僧,他的生命是顺江漂来的,围绕他的故事也就从此开始,直至他的肉身在灵山脚下的河中漂走,安稳渡过的唐僧已是不同的存在。成佛的是金蝉子,随水漂走的是江流儿,而唐僧这个称呼,不过只存在于中间取经的迢迢路途之内。那个一直存在的“我”,其实并不受任何形式所拘束。在文中,悉达多放弃了作为富翁的自己,放弃了作为浪子的自己,放弃了作为悟道之人的自己,重新成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得到了自由,又像一个孩子似的立于天地之间。因着亲身经历的这一切,他终于懂得了摩耶的无常,这无常中也包括他自己。在这个母亲缺位的故事中,悉达多以明悟找寻到了自己诞生的根源,并又一次诞生了。过去的他淹没于生命之河中,再次走出来的是一个新的他。之后,悉达多在河边停留下来。
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无论是这条河还是这个人都已经不同。”可实际上,生命之河无所不在,在它的河流里,时间只是幻象,没有以前,没有以后,只有现在和现在的实在。一切生命的声音全在它的声音里。再次回到河边的悉达多已经不再想渡过这条河流,而是选择倾听。这意味着他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寻找到了中立的点,不再以外界世俗标准要求自己,也不再以内心个人标准评论世界。放下分别心,悉达多得到了智慧,他找到了他所探求的,于是也成为了摆渡人。并帮助曾经迷恋的女子,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安宁的渡过了生命之河。在这一点上,他与将要逝世的佛陀之间,别无二致。
但,悉达多与佛陀之间,仍是有区别的。佛陀同样是人身,有父母妻子,他虽然离宫出家,但依然爱着他们,这是一种不自私的爱,因为他一直都是平等的爱着众生,在回报众生的同时,他也在回报着亲人。据记载,佛陀在证悟后,多次为亲人讲法,在父亲净饭王将离世之时,佛陀回到家中,给他讲了最后一次佛法,助他解脱。他的妻儿亦同时剃度出家,耶输陀罗为第一位比丘尼,罗睺罗为第一位小沙弥。在涅槃前不久,佛陀也曾到忉利天为摩耶夫人讲授佛法,并向她告别。佛陀以智慧回报这诞生他的摩耶世界,回报关爱着他的有情众生,便是以理性的力量,助感性的提升,既然梵我同一,那么与人分享智慧,就是一个照见自我的过程。最终他连梵我都一起放下,认定“无常故苦,苦故无我”,获得了彻底的清净。
而悉达多心灵上的平静是暂时的,他心理上的平衡很快就被儿子打破,且久久不能恢复。因着儿子的到来与离去,悉达多才体会到什么是付出,什么是爱。因为这份爱,他才真正感知到了自己的心,从而明心见性。父母恩重难报,但不养儿是不知父母恩的。悉达多深爱自己的儿子,爱到忘我的地步,这是人之常情,儿子不能理解父亲的心思,从而逃离了父亲,也是人之常情。任何事情,都要在亲身经历之后才能了解的最深刻。当悉达多失去儿子的时候,他才终于懂得了当年自己离家那一天,父亲的心情。爱给了他一个伤口,从此他有了同情心。有情众生,人同有情。同情心带来同理心,当他不再沉湎于自己的时候,他的伤痛也就被世界治愈了。原来生命之河即是摩耶世界,喜、怒、哀、乐,一切的一切,都在河流之中,“我”亦同样在万物之中,这便是一体圆融。这圆融显现于生命之河里,存在于毗湿奴的腹中,当人发现了无所不在的变幻神性,才能知晓梵我同一生灭,轮回即是永恒。悉达多最后显露给朋友的那个至善者的微笑,正是与至高神一样的笑容。
小结
与黑塞年龄相仿的希腊作家尼科斯·卡赞扎基斯,创作了《基督最后的诱惑》,让基督像黑塞的悉达多一样走下神坛,二次度过了作为一个人的一生。他在书中说,“人民就是弥赛亚——我,你,咱们每一个人。”想来,这也正是黑塞希望表达的。婆罗门的儿子悉达多的一生,就是佛陀乔达摩的第二种人生,作为人和作为佛,他们殊途同归。同样的,文中的他也可以是每一个人。人与世界相背离,希望能独立存在为人,这是不能成立的。想超脱出此世,就要先让自己与世界和解,不失感性亦不失理性,以同理心去爱去体会,才能感知到自己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中与世界共同前行,这便是“梵我同一”的真谛。从此可知,黑塞在笔下塑造了神的再次回归,是为了让神性——也就是真正的人性——能够不为艰险与创伤所限,二次降临到每一个人心中。
(山东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