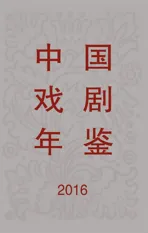中国音乐剧:在歌剧和戏曲之间穿越而过
——音乐剧本土化研究札记
2016-11-20周映辰
周映辰
深刻困扰着音乐剧创作界和研究界的最常见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看待音乐剧与歌剧和中国戏曲的关系。
音乐剧是现代都市文化中一个独特艺术现象。如今美国百老汇和英国伦敦西区,每天都有几十个不同的音乐剧作品同时上演,世界各地的音乐剧从业人员和数以百万计的观众蜂拥而至,使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成为世界音乐剧的创演中心和产业中心,并由此辐射开去,在世界各大都市遍地开花。作为一个新的艺术门类,音乐剧已经成为世界艺术舞台上的强势力量。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音乐剧属于全世界也理所当然地属于中国,但它毕竟不是中国的音乐剧。音乐剧要真正地在中国的文化艺术土壌上生根、发芽、成长,并在世界音乐剧史上留下自己的位置,显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与此同时,有一个问题须受到追问:我们需要如何廓清中国音乐剧自身的美学特点,以确立自身的创作与表演程式。这样的追问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哪一种类型的艺术,可以没有自身明确的质的规定而得到大众的认可,得以健康发展,并获得大众长久的认可与追随。显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若非从音乐剧的文化个性、艺术品质、风格演变,以及对当代城市化进程及大众文化消费心理等多层面多维度地进行探讨,不足以说清这一问题。
事实上,关于中国音乐剧的美学特点的争议由来已久。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早期的音乐剧研究,常常将音乐剧与歌剧混为一谈,中国的原创音乐剧,常被认为和轻歌剧没有明显的区别。而在当下的中国学界,还有观点认为中国的音乐剧就是中国戏曲的现代化表现。
我国权威工具书《辞海》,在“歌剧”词条释义中说:“综合音乐、戏剧、诗歌、舞蹈等艺术而以歌唱为主的音乐戏剧形式……有正歌剧、喜歌剧、大歌剧、轻歌剧、乐剧、音乐剧等类型。”它在“音乐剧”词条的释义却仅仅界定为:“美国的一种音乐喜剧。”不再提及音乐剧是“歌剧中的一种”。而从戏剧研究角度看,戏剧是融合了文学、美术、表演、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通过语言、动作、场景、道具等多种表现手段,把生活中的矛盾冲突集中地再现于舞台之上的艺术形式。因此,戏剧研究者多认为,广义的戏剧包含了话剧、戏曲、歌剧、舞剧、音乐剧等艺术形式。从其名称上看,当今美国人称音乐剧为MUSICAL,以前称为音乐喜剧MUSICALCOMEDY,英国人目前依旧称其为音乐喜剧MUSICALCOMEDY,而法国人则称之为小歌剧OPERETTE,从这些外文名称上可以看到音乐剧早期与歌剧艺术有些许关联,但是随着音乐剧的发展,人们逐步认识到,无论其内质还是其表现,音乐剧都有自己的质的规定性。
音乐剧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首先是由于音乐剧明确以戏剧为主导,强调歌舞的共同叙事功能,其更为重要的一个质的规定性是:音乐歌舞叙事的音乐语言,是以现代流行音乐为主要叙事语言。这是音乐剧与歌剧艺术被分为两大艺术门类的重要原因。1927年出现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音乐剧《演艺船》,其中的歌(音乐)、舞(舞蹈)、剧(戏剧)三者的融合,为后来的音乐剧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创作模式,即要求对白、音乐、舞蹈与戏剧表演融为一体。由此可见,音乐虽然是音乐剧的最重要的表现方式,却并不是主导因素。音乐剧是一门高度综合的舞台艺术形式,其本质终究是以歌舞讲故事,一部音乐剧除了要有生动的歌舞,最为重要的是有一个打动人心的故事。国际上至今成功的音乐剧,至少在故事层面上,亦可以大致总结出一个规定性:首先是要有一个优秀的剧本,要有一个合理的戏剧结构,符合戏剧发展原则,如此才能“讲好”故事,这甚至决定一部音乐剧的成败。音乐剧在具备一个合理的戏剧框架后,通过音乐、舞蹈、对白,以及舞美、灯光等多种艺术表现方式呈现出这个故事,合理安排人物以及戏剧冲突,以多种形式表现人物的情感世界。
二十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音乐界人士在轻歌剧、音乐剧、歌舞剧、戏曲音乐剧等等诸多称谓中无所适从,很大程度是由于音乐剧与歌剧确有很多共通之处。在实际的音乐创作中,很多歌剧导演同时也作为音乐剧的导演,一些歌剧演员同时也作为音乐剧演员。但是,音乐剧与歌剧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又是有目共睹的。它们产生的年代相差300余年。因为它们是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背景与艺术思潮的产物,所以它们的艺术风格、结构特征、表现方式及审美诉求等各个方面均有着巨大的差异。
在艺术风格方面,歌剧与音乐剧的差异,可以看成是“神圣化”与“大众化”的差异。歌剧诞生在十六世纪的佛罗伦萨,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群文化艺术界名人热衷恢复古希腊戏剧,力图创造出一种诗歌与音乐相结合的生动艺术,实验的结果是产生了歌剧。歌剧发展了近400年,在其成形之初,就已形成了音乐与歌唱叙事的质的规定性。纵观歌剧的发展历史,它一直是宫廷化、古典化、精英化、舞台呈现追求程式美的艺术体裁。从选材上看,歌剧艺术更为倾向于表达历史神话或经典故事,其文本要善于表现歌唱性,如表现才子佳人爱情主题的歌剧《茶花女》。音乐剧则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百老汇,它较多受爵士乐、踢踏舞、话剧和含有歌唱的喜剧等通俗艺术形式的影响,这些成为音乐剧广受大众喜爱的重要原因,也造成了音乐剧通俗性、娱乐性等特点。音乐剧天然地具备“草根”特性,是大众文化的产物。
在结构方式上,歌剧与音乐剧的差异,可以看成是音乐主导与戏剧主导的差异。歌剧的主体就是音乐,“作曲家就是戏剧家”。音乐是歌剧的绝对主导因素,以音乐推动戏剧的发展,歌剧中人物性格、人物关系、戏剧冲突等均是通过音乐来表现。歌剧的结构方式可分为分曲结构和四幕结构两种,前者中是由一系列自成段落的分曲组成歌剧结构,由十几个至几十个分曲组成,每一个分曲都是一个有头有尾的、结构完整的独立分曲,即为独唱曲、重唱曲和独唱与合唱相结合的歌曲;四幕结构则是十九世纪后由瓦格纳创造的歌剧结构方式,即是由独立分曲扩大到整个一幕。瓦格纳认为:“被称为歌剧的那个艺术样式最大的错误,就在于表现手段(音乐)变成了目的,而目的(戏剧)则变成了手段。”尽管瓦格纳无比强调歌剧中的戏剧性,但是,歌剧的美学依然是音乐叙事、歌唱叙事,以音乐和歌唱为审美的绝对标准。
音乐剧与话剧结构相同,基本是两幕结构。整体布局上,歌与舞的比例没有程式化限制,同时表现出较大的即兴表达空间,比如可以把一段歌唱转换成一段台词表述出来,这种方式在歌剧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音乐剧以戏剧冲突为推动剧情的主要手段。音乐剧剧本要有对生活场景及戏剧细节的具体描写,避免像歌剧强调歌唱感受、舞剧强调肢体感受,它要给观众的是一个故事的整体感受。音乐剧强调戏剧的整体性,在以音乐与舞蹈为主要叙事手段的同时,并不刻意强调与夸张音乐与舞蹈的呈现,而是通过日常语言的对话、抒情叙事兼具的音乐与舞蹈融合协调的推动剧情发展。因此,音乐剧的美学是由戏剧性、音乐性及其舞蹈性共同建构的。
而在表演方式上,歌剧程式规定性与音乐剧的大众化、个性化则有着明显的差异。无论是西方歌剧还是中国歌剧,演唱者均需经过多年声乐技术训练,娴熟掌握歌剧唱法。歌剧唱法不依靠扩音设备,以追求人声的完美、挑战人声歌唱的极限能力为技术衡量标准,使用交响乐队伴奏是传统的美学要求,具有鲜明的程式性规范和成熟的美学原则;中国歌剧自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以西方歌剧美学为基础,虽然在演唱风格、表演风格、舞美风格方面与西方歌剧有很大区别,其质的规定性是一致的。歌剧的演唱强调音色统一,往往沿用一个固定的唱法,其演唱形式包括宣叙调、咏叹调、重唱、对唱、合唱,其演唱方法、声区划分已形成几百年之久。本质上,欣赏歌剧就是为了欣赏歌唱家的演唱,大段的咏叹调与华美的声音的炫技是吸引观众的重要看点。
音乐剧的表演美学是贴近生活的,在大众化中追求个性化。音乐剧不以音乐风格的统一为追求,可根据剧中的人物造型、戏剧环境的改变而调整演唱者的声音状态。音乐剧的演唱虽然以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为主,但并不排斥西方歌剧唱法或中国民族唱法,也惯常使用RAP、摇滚、爵士等多种演唱方法,在音乐创作与编曲的手法上,増加大量电声乐队的比重。由于音乐剧音乐注重流行性和娱乐性,因此很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爱好者也可以自如演唱,甚至可以使用方言演唱。西方许多音乐剧中的唱段广泛流传,登上流行音乐排行榜高位的作品不胜枚举。
一件事物转移到另一环境中生长发展,会面临着调整本身内在与外在条件的问题。对音乐剧来说,当它传至中国的时候,它必然面对着如何适应浸淫于中国戏曲文化中的观众的问题,它的调整和适应过程,即是它的本土化过程。在音乐剧的中国本土化过程中,有学者认为,“音乐剧本土化”就是“中国戏曲的现代化”。这种带着强烈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色彩的观点,虽然强调了音乐剧在本土化过程中与中国戏曲的密不可分,但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既取消了音乐剧的独特性,又取消了中国戏曲的独特性。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音乐剧的中国本土化确实离不开它对中国戏曲艺术的吸收。音乐剧与中国戏曲在美学原则上的相通之处,为这种吸收提供了便利,从而也为它的本土化提供了通道。中国戏曲作为传统的戏剧样式,它植根于民间,它的观众群体要远远大于音乐剧在全世界的观众群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吸收了音乐、舞蹈、文学、诗歌、杂技、武术等不同的民间艺术。其中,作为防身健体手段的武术被纳入戏曲的范畴,最具有说服力,它不仅成为塑造英雄的手段,还进而发展出了武生、武旦等角色类型。中国戏曲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在世界戏剧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构成了它的综合性的美学特征。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中国戏曲最重要的叙事方式就是歌舞,正如清末学者王国维所说,“戏曲者,以歌舞演故事也”。这一点,与作为歌、舞、剧三者合一的音乐剧是相通的:既相通于它的综合性,也相通于它的歌舞叙事。也就是说,这是音乐剧与中国戏曲进行有机融合的美学基础。
但是无论如何,正如歌剧和音乐剧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一样,音乐剧和戏曲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中国音乐剧的本土化,并不能看成是中国戏曲的现代化。音乐剧的本土化解决的“因地制宜”的问题,通过“因地制宜”而“落地生根”,中国戏曲要解决的“与时俱进”的问题,通过“与时俱进”而让人再次“喜闻乐见”。事实上,只有理解并尊重它们的差异性,它们才可能在发展的同时互相借鉴、相互促进,并进而有效地解决各自所面临的“因地制宜”和“与时倶进”的问题。
音乐剧与中国戏曲在美学形态上的不同之处,突出也表现为音乐剧的写实性与中国戏曲的虚拟性的差异。传统的中国戏曲,重“写意”而轻“写实”,重“神似”而轻“形似”;扬马鞭,便是骑马跃进;一撑竹篙,便是乘风破浪;走一个圆场就意味着已经越过了千山万水。而西方音乐剧则是高度写实的,《猫》中垃圾场便是由铁桶、轮胎等废弃物真正堆积起来的垃圾场,只是根据“猫”的形体的大小在比例上做了些调整,它在舞台上再现了一个“物”的世界。在《西贡小姐》中,在表现美军乘坐直升飞机从西贡撤退的场景时,一架直升飞机从观众头上缓缓降落到舞台上空,它巨大的噪音将混乱与绝望直接有力地传达给观众。但这种高度写实性在东方的中国舞台上是不可复制的。中国戏曲的表现方式带有强烈的程式性特征。它把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人物表演的各种动作,都规范化了,也就是程式化了。但在程式化的同时,演员的表演又有相当的自由度。程式化的表演可以使有经验的观众直截了当地进入剧情,或者说,观众的兴趣不再局限于剧情,而在于集中的观赏演员在程式化表演的背后所呈现出来的演技和风格,观赏演员如何通过自己的演技和风格来抒发剧中人物的情感。由此,演员的重要性甚至凌驾于所有戏剧因素之上,一个著名演员跳出剧情的一段清唱也能使观众如痴如醉。演员自身的表演成为戏曲的审美核心,明星自身的表演特点甚至成为一个戏曲的表演流派。了解这些不同,正是为了给音乐剧的本土化寻找方案。中国的本土音乐剧,完全有可能从中国戏曲中吸取充足的营养,给音乐剧打上中国戏曲的美学色彩。举例来说,当中国音乐剧在表现直升飞机从天而降的场景时,通过舞美设计、音乐、布景和演员的配合表演,完全可以让观众深临身其境,完全可以达到西方音乐剧的舞台效果,完全可以表现人物在类似情景中的情感的细微变化。
所有的外来艺术形式,走入中国的文化土壤,与千年积淀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相融合,都面临着一个民族化的问题。“民族化,实际上应当是指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吸取外来文化的先进成果,以丰富、补充中国文化,在此基础上建设新文化的过程。”一种不同于西方歌剧、不同于中国传统戏曲,也不同于西方传统音乐剧的中国本土音乐剧,出现在中国当代的艺术舞台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
用音乐剧讲述中国的故事,不仅是中国当代的都市生活,也包括中国的历史故事、民间传奇、文学经典,这自然是音乐剧本土化在剧情方面的要求。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穿着民族服装、跳着民族舞蹈、讲述中国民间故事的音乐剧,并不意味着音乐剧的本土化的成功。
一部充分“本土化”的音乐剧,必须是一部在西方戏剧美学与中国戏曲美学的结合部穿越而过的音乐剧。“本土化”不等同于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方现代音乐剧的简单相加,要有效规避与区别戏曲中“形体动作程式化”、“人物造型脸谱化”、“演员形象模式化”等传统风格。“本土化”也不等同于民族歌舞加故事的“民族化音乐剧”。中国音乐剧的表演艺术既应是内部与外部的统一体,也应是理智与情感互相交替的统一体。我们既追求“神似”,又要追求“形似”,要做到“形神兼备”,“情动于衷而形于外”。优秀的表演艺术应该是体验与体现、心灵与形体、感情与理智完美结合的统一体,中国音乐剧应该能够准确而艺术地表现人物形象的外部形体动作,更应该艺术而准确地表现人物的精神生活,既符合音乐剧的现代审美原则,又符合当代中国观众的审美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