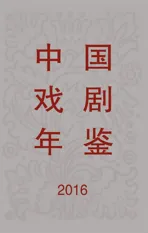天地大舞台上的生命综合体
——藏戏的生态学价值笔记
2016-11-20廖全京
廖全京
雨后,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瞬间跳出的彩虹,把视线牵往神秘的时空邃道深处……
所有后现代主义的娱乐至上、消解意义以及为文化消费主义所裹挟的种种时尚,都连同城市的雾霾一起,被若尔盖上空无以计数的负氧离子抛到了遥远的天边之外。
我陷入了关于藏戏的生态学价值的沉思。
生态哲学认为,世界的存在是一个由人、人类社会、自然界组成的有机整体,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只要人类存在,人与自然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与其他万物之间始终存在这种普遍的联系,并由此而达到共生互补,相依相存。人类并不是宇宙的核心,也不是万物的主宰,人与万物是互为主体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和谐的。
如果用这种观念来考察藏戏,也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若干年前,在川西北高原上第一次接触到藏戏,那是嘉绒藏族同胞在山谷中的一块平地上演出的。具体内容已不记得了,但那种以山和天为背景的奇特场景,那幅高高挂起的莫尔多山神的唐卡画,尤其是头戴面具的演员在开场时念诵、表演的仪式感,至今留有深刻印象。不远处,梭磨河静静流淌,如同一条长长的磁带,把这高原天堂里的美妙乐音,永久地记录了下来。
藏戏作为一个大的生命系统,是一个活泼的多元艺术的综合体。在四川藏戏与西藏藏戏、甘肃藏戏、青海藏戏之间,在四川藏戏内部的康巴藏戏、嘉绒藏戏、德格藏戏、安多藏戏之间,无疑有这样那样的区别,有各各不同的秉性,但从根本上说,所有藏戏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表现出了藏民族的精神生态,都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有机环节。从这个角度看去,在全世界的各类戏剧形式中,藏戏至少是最具生态意识和生态学价值的戏剧之一。
在“戏剧与环境”这个课题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所重视,并越来越紧迫地成为一个带有世界性的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课题时,藏戏理所当然地应当作为关乎人类发展的独特戏剧样式纳入中国戏剧研究的视野。值得注意的是,藏戏绝对不同于谢克纳所倡导的“环境戏剧”。准确地说,古老的藏戏为我们演示的,是一种充满鲜活生命力的生命常态。因此,它是区别于通常所说的“环境戏剧”的“新环境戏剧”,我们不妨称之为生态戏剧。
所谓生态戏剧,即在哲学上将古老的“天人合一”或“自然用对立的东西制造出和谐”(赫拉克利特语)作为基本理念的戏剧。在人类正不断地攫取自然、压榨自然、破坏自然、毁灭自然同时毁灭人类自己的当今,发掘生态戏剧、保护生态戏剧、创新生态戏剧、发展生态戏剧,是确定无疑的当务之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在认知层面上准确把握生态戏剧的血脉中枢和神经中枢——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方面,眼下有两件事可做:一是了解古今中外学者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论述;二是考察已然存活和正在产生的生态戏剧的舞台呈现或文本呈现。通过比较、研究,寻觅生态戏剧的生态学特征、生态学价值,从而抵达创新、发展生态戏剧的始发站。
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藏戏这个天地大舞台上的生命综合体,视为原始的生态戏剧的典范。
在我看来,藏戏生态学价值有三:
一、藏戏的核心精神传达出了藏族民众对大自然的敬畏
从戏剧生态学的角度看,世界上的许多戏剧样式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某一类或某几类原始宗教的影响。藏族地区(包括西藏、西康、安多等)自公元7世纪以来为印度佛教思想波及,此前的藏族自有他们的原始信仰。这一原始信仰就是被称为苯教(又称黑教)的本土宗教。据出版于1801年的《教派明镜》(衮隆嘉巴凌活佛著)记载,出生于古老的香雄(一作象雄)国的辛饶大师创立了苯教。传说,当人们陷入轮回的愁苦大海之中时,由于无知,做了不知多少错事。顿巴辛饶(即苯教创始人)对他们起了慈悲念头,就由天上的宫殿放出五种颜色的光,普照大地,然后把自己变成蓝颜色的布谷鸟,蓝得与蓝宝石一样,唱的歌与琴声一样。他以这种形象落在一个天王的头上,扇了三下翅膀,闪出带红色的白光,然后投入到他母亲的头里。当他最后降生时,立刻就能发出有音节的语言,并有旁的幸福的象征。①请注意,上述记载表明,与传说共生的藏族原始宗教信仰在诞生之初,就与大自然有密切的关系。传说中,普照大地的五彩阳光、华丽的布谷鸟,正是大自然的象征。更重要的是,这些阳光和鸟,都与神性相通——它们能降福祉于人间。这正是原初的藏民相信万物有灵论的反映。在苯教看来,万物皆有神灵,山是神山,水为圣水,石头亦有灵性。在藏族庞大的神山系统中,从念青唐古拉到嘉木莫尔多,几多神迹,几多仙境,几多生命。无论在苯教(黑苯)传统观念中,还是在佛教传入后经过改良的苯教(白苯)理念中,生命神圣、大地神圣、天空神圣、万物有灵,乃绝对真理。对于人类普遍关注的生命死亡现象,藏族自古有自己到的看法:死并不是生命的终止,而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得到解脱的人,死即是免于“轮回”,而不是脱生。作为解脱者来说,死是值得庆幸的事,是生的另一种成功。他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看待生死。面对生死,如同面对自然(包括对遗体的处理过程也显示出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人与大自然一样在无尽的时空永存)。这是一种藏族特色的生命观,藏族特色的泛神论。这种理念的精髓,就在于人与大自然的融合,人与大自然是完整的生命统一体。其中,人对神的崇拜和敬畏,实质上是人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敬畏。
深入考察藏戏,你会发觉,人对大自然的敬畏,表现在诸多藏戏的文本和演出中,并且成为了藏戏的基本的、核心的精神。这正是原始的万物有灵论长期浸润于藏族原始宗教乃至于藏传佛教之中,进而广泛影响于藏戏的结果。
曾经在清晨或傍晚走过川西北的高山、峡谷、草原。这些地方,即阿坝州的马尔康、大金县、小金县、红原、壤塘、若尔盖,以及甘孜州的丹巴、色达等地,保存或流行着嘉绒藏戏或安多藏戏。在原始苯教的影响下,这里的人们以天地日月、山川树石为神,把生命之源的高山、草地等尊为神山、圣地。比如,位于丹巴一带的莫尔多(又译墨尔都)山就是藏民心中会显示神迹、满足人们的愿望的东方神山。嘉绒藏戏和安多藏戏就和这些神山、圣地、净土净水密切相关。嘉绒藏戏(或称“陆呷尔”)中有一个乍看并不起眼的小戏《吉祥颂》(也叫“木茸”),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满鲜活的生态意识,充满人们对大自然的崇拜、敬畏。演出中,演员们唱道:白雪环绕的藩夏尔嘉莫查洼戎地区,是吉祥的圣地;佛慧灌顶的人民,是英雄墨尔都的后裔;威震四方的雄狮,是雪山冰峰的山主;勇猛无畏的山虎,是林海雪原的威风;体大膘壮的野牛,是辽阔草原的幸福。这个戏告诉我们,对山神的敬畏,是对英雄(战神)的敬畏,也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大自然孕育了英雄(指战神墨尔都),大自然化身英雄为人们造福。这个小戏之所以不小,是因为它几乎出现在所有嘉绒藏戏演出时的开场,用以向观众表达衷心的祝福之意。《吉祥颂》在反复告诉人们,野牛、狮子、老虎等等,是伟大的山神赐给嘉绒人的幸福源泉。在另一个名为《幸福的源泉》的嘉绒藏戏中,更是集中、突出地赞颂了野牛:大自然养育的野牛,是大山神赐给山民的幸福源泉。奶供山人食,毛供山人穿,耕犁驮运离不开它……日落西山,红霞万道,幸福野牛扬起四蹄,从远山肥沃的草场归来停在圈坝,等待主人挤奶。年轻的主人熟练地挤下一桶洁白如玉的乳汁后,为感谢野牛的施舍,盛满一杯杯香奶,第一杯敬天,求大山神大慈大悲;第二杯敬地,愿大地五谷丰收;第三杯敬在场的朋友,祝大家的生活像奶一样的甘甜。这浑然就是一幅“天人合一”的藏地风情画。
大多取材于人物传记的安多藏戏(或称“南塔”“南塔羌姆”),在一些剧目的具体情节中,也透露出了敬畏大自然的生态意识信息。《贡波夺尔基》这个戏据说是由拉卜楞寺三世贡唐活佛丹贝卓美根据道歌《米拉日巴传》中的同名故事改编的,后来传入四川安多方言区。剧中的猎人贡波夺尔基在山中放犬追捕野鹿,经过苦行僧米拉日巴修行的山洞,米拉日巴要他听一首道歌,才能放他走。贡波夺尔基很生气,他挖苦讽刺米拉日巴一番之后,继续追捕野鹿。正当他举起猎枪要射杀野鹿时,远处传来一阵阵如泣如诉的歌声——米拉日巴为救野鹿唱起了悲凉的道歌。充满仁慈和怜惜的歌声让凶残的猎狗也放弃了追逐,跑到了歌者身边;野鹿则朝着歌声传来的方向飞奔而去。贡波夺尔基被打动了,开始忏悔并拜倒在米拉日巴脚下,请求宽恕。他决心跟米拉日巴修行,成为他忠实的弟子。这个戏的内容显示出鲜明的藏传佛教色彩。尽管戏是围绕西藏噶举教派第二代祖师、全藏最著名的瑜珈大修士米拉日巴以道歌形式宣传教义、广收门徒的事迹展开的,但其中蕴含着浓烈的敬畏生命、敬畏大自然的生命伦理观念。这正是藏族民众普遍虔诚地敬畏大自然的社会心理的表现,也正好向我们显示了藏戏的核心精神。②
二、藏戏中有着非人类中心意识的可贵表现
在宇宙之间,人类究竟居于一个怎样的位置?人类是不是处在与“客观世界”(或者说大自然)相对立的中心?这是一个问题,一个至今未达成明确共识的问题。
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学者就逐渐从形而上学、形式逻辑、科学分类等领域将自然界与人类的理念世界“一分为二”地分离并对立起来,形成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大力提倡人的理性与自然的对立、抗争,在“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声中推行机械论世界观,反对有机论世界观,并以此为思想基础和意识动力,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当莎士比亚高声赞叹人为万物之灵长而将人推举到至高至尊的地位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百年之后,人越来越成为自然的主宰,越来越对自然拥有生死予夺的绝对权力,从而导致人对大自然贪得无厌的征战掠夺和人自身精神生态的日益沦落衰败。对此,恩格斯有所预料并提出过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③人类征服了,自然界报复了。于是,人类开始反思。这时,一些清醒的学者从世界各民族和历史各阶段寻找各类思想资源和文化参照系,开始重新考量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确定人在宇宙间的位置。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东方,投向了中国。有材料证明,他们努力从中国汉族的古代思想家如老子、庄子那里寻找脉络、肌理和思想的碎片,以期获得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深刻理解和启迪。④
我孤陋寡闻,不知他们在向中国古代汉族的圣哲表达由衷的敬意时,是否注意到了中国藏族古老的文明,是否注意到了古老的藏戏?
仔细考察藏戏,你会感到从中透出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股股暖意。藏族民众时时生活在大自然中,大自然赐予他们明媚的阳光、碧蓝的天空、辽阔的草原、连绵的群山、奔腾的江河、明净的湖水、纯美的奶和蜜……他们在大自然面前,永远保持一种虔敬和谦恭,从不企图征服大自然,甚至不愿打扰大自然,尽量让它保持自己的那一份宁静、那一份优雅、那一份端庄。藏戏中的人物,并不处于世界的中心,人与所有的动植物都是融入高山大川的生命体。
藏戏从它诞生那日起,就与自然处于相互依托、相互支撑的关系。藏戏一词,在藏语中称“阿吉拉姆”,意思是“仙女姐妹”。这“阿吉拉姆”之中,就透露出了藏族人与自然关系的若干信息。传说在十四世纪,噶举派(白教)的高僧唐东杰布在云游途中,遇到了湍急的雅鲁藏布江的阻拦。江中激流常常将渡江的牛皮船掀翻卷走。为了民众的便利、安全,在唐东杰布的主持下,开始在江上修建铁索桥。在修桥的过程中,唐东杰布发现民工中有七姐妹能歌善舞。他就把她们组织起来,指导她们为行善修桥募集资金而表演节目——最初的藏戏随之诞生。上述传说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这些演出的节目内容和形式是什么?据后人的调查研究,它是在西藏原始苯教巫师祭祀自然神仪式基础上,吸收了民间土风舞成分的宗教仪式舞蹈,加上佛经中的传说和民间传说中带有戏剧因素的内容等等,由唐东杰布编排而成的。其中,还含有原始的白面具戏的成分和民间说唱艺术的成分。二是唐东杰布编排这样的演出,目的是为了以最适当的方式——修桥来处理、调适河流、洪水与自然生命体、人类生命体之间的关系。他面对江流,他并非征服更非镇压,而是顺势而为,并不干扰、改变河流本身的水势和走向。似乎应当这样来理解唐东杰布当年修桥的深意。正是这一顺应自然、遵从自然的善举,催促了藏戏的呱呱坠地。
我注意到藏戏中流露出来的不同于其他戏剧样式的时空观念。藏戏中的物理时空是阔大浩渺的,藏戏中的心理时空更是浩瀚无穷。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戏剧或中国汉族传统戏曲的时空观念来理解或框范藏戏。首先,它的舞台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舞台与山谷、草地融为一体——藏戏的编排者只是把自己作为大自然的一个生命个体,而不是主宰大自然的挥斥方遒的中心或核心。这样,雪山、草地、江河、湖泊都是背景,月光下的峡谷也是背景。而且,戏一演就是好几天。因为,在藏族民众心目中,生命与天地一样久长。他们对生命的未来充满信心,观演过程上时间的流逝,藏戏故事中时间的流逝,不过是白驹过隙,倏忽而已。正如将己身置于宇宙中的李贺所谓“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梦天》)看来,藏人的先辈与汉人的先辈早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藏戏的这种独特的时空观受藏传佛教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藏传佛教经典中贯穿着这样一种思想:人类在六道轮回中受苦遭罪,当一千零八尊佛(又称千佛)全部降临人世之后,人类将得到最后的解脱。到那时,世界将是一片净土,不再有六道轮回,人们将永远脱离变畜牲、成饿鬼、下地狱之类的不幸命运。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人们现在信奉的佛祖释迦牟尼只是那一千零八尊佛中的第四位佛。到第五尊佛——慈尊弥勒佛,即现世的人们所向往、呼唤的未来之佛出现,还要等待五亿七千万年。至于最后那一千零八尊佛——遍照佛(又名燃灯佛)降临人世,那将是亿万亿万斯年之后了。这就是藏传佛教的时间概念——长长的流水,几乎没有尽头。在如此浩渺的时空之中,人当然不可能是主宰一切的中心,而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有灵性的一员。藏族民众面对如此漫长的时光隧道,绝无半点惊诧,只是以平常心静穆地、虔诚地、执着地往前走,往前走。他们相信,神(即大自然)会始终陪伴在自己身边,有神(即大自然)的护佑,路上遇到的所有艰险、邪恶都无法阻挡一往直向前的踏实而沉稳的脚步。
这种精神状态,在几乎所有的藏戏剧目中都有所表现。康巴藏戏的代表性剧目《卓瓦桑姆》中,主人公卓瓦桑姆便是神的女儿,她降临人间,受到魔妃的迫害。是天神通过屠夫、大猎人等这些时时与自然打交道的普通人救了她,她变成老鹰救了自己的儿子。在戏中,大自然化身为神,人依靠神(大自然)、求助于神(大自然),甚至化身为大自然的一部分(鹰)。在嘉绒藏戏里,《格冬特青》颇具代表性。这是一个关于慈祥的天王为解除嘉绒部落的苦难而派来战神降伏魔首恰巴拉让的故事。戏里的战神转世为一对年过五旬的老夫妇的儿子,取名格冬。在嘉绒人的心目中,格冬就是山神莫尔多的化身。藏地的山神,大多为战神。可见,人们依然是在山神(大自然)的帮助下,战胜了邪恶,走出了灾难。藏人明白,没有大自然的依托和支撑,人无法在地球上生存。人类当然不能是也不应该是世界的中心。
三、藏戏中鲜明的善恶观是大自然中光明与黑暗强烈对比的折射
我在藏戏中寻找一种感觉。
我在藏区的高山河谷、草原湿地上寻找一种感觉。
我蓦然悟到,这二者之间似有相通之处——大自然中形成强烈反差的白天与黑夜,被古老的藏戏演绎为天地大舞台上善良与邪恶的鲜明对比。
人猿相揖别的时段在藏区成为历史不久,那一片雪域高原就进入了善良与邪恶长期相持、不断冲突的人类社会。作为人和人类社会、自然界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藏人与藏族社会不可避免地被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善恶冲突所浸染。在中华各民族不同的戏剧样式中,几乎都有善恶冲突的思想痕迹,但论其反差强烈和对比鲜明的程度,藏戏确实独树一帜。也就是说,善恶分明是藏戏通过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表现出来的突出特色。
佛教是讲善恶有报的。藏传佛教以一种革新的姿态讲善恶有报。在通往灵性的智慧、纯洁的净土的道路上,善良不断地遭受邪恶的侵扰和迫害,不得不勇敢地、光明磊落地接受邪恶的挑战。这一基本的历史现象,在藏戏尤其是17世纪以后成熟起来的藏戏中得到了大量的反映和表现。藏戏的传统剧目相传有“十三大本”,其中经常上演的《文成公主》、《诺桑法王》、《朗萨雯波》、《卓瓦桑姆》、《苏吉尼玛》、《白玛文巴》、《顿月顿珠》、《智美更登》被称为“八大藏戏”。这最具代表性的八个剧目的内容几乎无一不涉及善与恶的冲突。最要紧的是,各个剧目的编、导、演无不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惩恶扬善,是非分明。在演出现场,你常常能看到代表邪恶势力的魔鬼在漆黑的夜里出来活动,顿时,妖风四起,鬼哭狼嚎。这时,战神降世,英雄登场,驱邪灭妖,环宇澄清。待到天色大亮,太阳升起,天地变得那么高朗、明净、敞亮!
“八大藏戏”之外,许多传统的或新编的藏戏剧目也充分体现着善恶分明、对比强烈的特色。最近,阿坝州壤塘县壤巴拉藏戏团推出了由俄旺旦真活佛编导的藏戏《赤松德赞》,歌颂弘法利众的救主文殊菩萨的化身——藏王赤松德赞。他于公元762年进行策划并动工开建宫殿,妖魔却在夜里前来阻挠。舞台上出现了善恶搏斗、驱妖镇邪的场面。这无疑是藏戏传统的一次精彩再现。
我感觉,藏戏这种善恶分明的特色不仅是藏族社会生活现象和道德观念的折射,还是包括四川藏区、青海藏区、甘肃藏区和西藏地区在内的藏族地区大自然现象的折射。
无论你走上巴颜喀拉,绕过冈底斯山,还是沿大渡河溯流而行,你都明显地感到它与川西平原的巨大差异。其中最大的差异在哪里?也许各人感觉不一样。对我来说,最强烈处在天空的色彩。这里的海拔很高,空气透明。这里的天空有在成都很难见到的那种碧蓝,那蓝色可穿透你的肌肤沁到你的心里去。一朵朵飘浮着的云,在那种蓝色的映衬下,白到了极致,净到了极致。整个天宇里,大海一般流动着、汹涌着、奔泻着的都是阳光,阳光,还是阳光。俗世常用的“明亮”、“明媚”、“明丽”之类的词汇,根本无法传达此时此地人对白昼、阳光的强烈感受。然而,火烧云燃过之后,黑夜降临。一切都几乎是在瞬间发生变化——气温骤降,星斗骤亮,万籁骤寂。无论有月无月,四野的花草树木、山川河流都在宁静中悄悄散发着朦胧与神秘。夜的时空任由你用各种想象去填充。总之,我感觉,仿佛整个川西北藏区就是那么简单又复杂地被白与黑的巨大反差所塞满。不知怎的,它让我想起一位藏族作家年轻时的诗句:“若尔盖草原哪,你由墨曲与嘎曲,白天与黑夜所环绕。”看来,我的感觉明显是一种后觉。在我之前,藏人和他们的祖先早就有如此的感觉,而且远比愚笨的我辈生动、丰富、奇幻。对于藏戏来说,这种黑与白的对比是一种大自然的先在,一种先于藏戏的存在。早在藏戏形成之前,鲜明而强烈的黑白分明便进入了藏人的生活、藏人的宗教、藏人的语境。于是,我们从许许多多的藏戏中见到了与自然界的黑白绝对分明相对应的社会生活中的善恶判然有别。这不仅体现在藏戏的内容中,还体现在藏戏的形式上。比如面具,在戴面具表演的藏戏中,白色代表纯洁,是善者面具的颜色。巫女或魔女的面具则是半黑半白,表现她的伪善,两面三刀。
需要稍作补充的是,从藏族的宗教思想中可以察觉到,他们常常站在天堂与地狱之间与死神对话,常常将从神秘莫测的大自然中感悟到的哲思表达出来。藏地的圣徒能从人类的角度看到大自然的两面,残酷无情的恶魔的一面和欢乐美好的天使的一面。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泾渭分明,所有僧众对此了然于心,并持鲜明的爱憎。这种精神的养料,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寺院和僧人的演出渗透到藏戏中去。
在亿万斯年以来,藏族生存及藏族生存之前就精神抖擞地蓬勃着、茁壮着的这片土地上,孕育着一个生命综合体——藏戏,他不仅在物质上对藏族的民间歌舞、说唱艺术、宗教仪式和宗教艺术等等进行了综合,它更对人的生命意识、生态意识、宗教意识等进行了精神的综合。在当今这个地球的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的精神生态系统都饱经沧桑并不断遭受重创的情势下,重新认识藏族文化,认真探讨作为天地大舞台上的生命综合体的藏戏的生态学价值,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
(《四川戏剧》2015年第9期)
注释:
①参见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4页。
②此节所提及的藏戏剧目内容,参见严福昌主编:《四川少数民族戏剧》,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19页。
④关于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论述,参见鲁枢元主编《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料库》下册,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