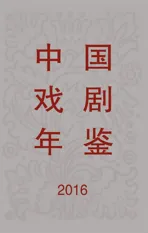小剧场戏曲:观念和能力的相互掣肘
2016-11-20张之薇
张之薇
“小剧场”本是个西方戏剧运动的概念,缘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戏剧导演安德烈·安托万创建了小得有些寒酸的“自由剧场”。他的初衷是为了挑战欧洲当时极为繁盛的商业戏剧,旨在反叛固有而僵化的戏剧形式,并让人对自身所处现代社会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可以看出,“小剧场”这种戏剧形式在它诞生之初不仅仅止步于“小”,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涵上都被注入了革新的基因,因此,“小剧场”在西方被称为“ExperimentalTheatre”,意即“实验戏剧”,但是随着它在西方的方兴未艾,发展至今这个又被称为“黑匣子”的戏剧空间内发生的事情也在悄悄地变化着,实验与先锋不再是它唯一的面孔,细腻的情感表达与心理化的表演也可以成为“小剧场”的另一种表情,也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拥有独特观演关系的空间场域内,探索戏剧的无限可能成为“小剧场”的标签。
今天的“小剧场”也许不一定是小众而非主流的,也许不一定是先锋而实验性质的,也许它也不一定与商业化、与通俗化格格不入,但一定的是,基于它开放的空间决定了它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也基于它的“小”,决定了大剧场所没有的观演之间的化学反应。这两点,可以说在2000年一部叫《马前泼水》的小剧场京剧突然亮相之时,就被证明了。传统戏曲历来被认为与现代生活扯不上关系,也被年轻人视为陈年古董,可没想到一出取自明代传奇《烂柯山》的小戏在“小剧场”的奇妙作用之下,不仅放大了戏曲表演的无限魅力,而且还让年轻人对理解其中的崔氏和朱买臣无丝毫障碍,这正是它的成功之处。不可否认,《马前泼水》作为小剧场京剧的发端之作,创新的步子与之后的一些作品比其实并不算大,这主要基于导演张曼君创作的观念,她认为:“彻底颠覆剧作主旨,刷新人物形象,形式上为先锋而先锋的做法,不太适应京剧传统艺术的风采展现,反而可能造成晦涩或疏离”,因此,“退一步海阔天空,对艺术传统的尊重不是抱残守缺,食古不化,而是实践我们潜心研究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文化环境中人的生存状貌,同时也为张扬京剧(戏曲)的独有表现形式给现代观众腾出一块欣赏、认识的空间。”这个现在看起来相对保守的创作理念或许正是《马前泼水》赢得年轻观众的原因,之后两三年陆续上演的小剧场戏曲,如《阎惜姣》、《偶人记》大约都秉承着这样的理念。
实验观念再好戏曲表演本位也不能失
如今,又一个15年过去了,小剧场戏曲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鲜事物了,但实验和创新却成为它存在的最鲜明理由,那么如今,小剧场戏曲究竟发展得如何呢?2015年的夏天,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这个33年前曾经诞生过中国第一部小剧场话剧《绝对信号》的地方,北京市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戏曲展演单元正在进行,这无疑可以看作一次阶段性的检阅。
这次参演的7部作品均是近五年来的作品,既然能被选送参加这个展演单元,应该都算上乘之作,它们是民营韩非子剧社的《灯官油流鬼》,中国戏曲学院的《程妻》《赶尸记》,北京京剧院的《碾玉观音》,天津京剧院、元声京戏坊的《琼林宴》,北方昆曲剧院的《一旦三梦》,北京天艺同歌国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倾国》,这些作品可谓形态各异,各有特色,从其中也可以看出每一个创作者自己的小剧场戏曲创作观念。但是,看罢之后才发现原来十几年前的《马前泼水》《阎惜姣》《偶人记》起点之高,想超越它们远没有那么容易。
在这几个戏中,《灯官油流鬼》《程妻》《琼林宴》《一旦三梦》应该说不同程度上都有传统戏曲厚实的基础支撑,《灯官油流鬼》的故事取自传统老戏《探阴山》(也叫《铡判官》),《程妻》的故事改编自元杂剧《赵氏孤儿》,而《琼林宴》本来就是经典余派老生戏,《一旦三梦》呢,则是撷取《牡丹亭》《烂柯山》《长生殿》中三位女性的梦境。看来小剧场戏曲借助传统的积淀还是创作者们的一个共识,尤其是在原创剧作能力羸弱的今天,有古典老戏的基础打底或许不仅能在戏剧的文学性上保驾护航,也可以保持戏曲表演的原有精髓。但是究竟该如何取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老戏原样,还是改头换面重新改编?是重探索,还是重经典表现?这一切都在摸索中。
《灯官油流鬼》在其中值得关注,至少在“小剧场”这一层面上,它的创作观念值得借鉴。首先,从文本上来说,原剧《探阴山》本是以包公为主角的裘派名剧,故事以柳金蝉和颜查散爱情的阳间线和判官徇私舞弊小鬼维持正义的阴间线组成,昼断阳间夜断阴的包公在此戏中是绝对主角。而《灯官油流鬼》在文本上却进行了大胆调整,将《探阴山》中的一个正义小鬼改为了主角,这既符合现代剧作以小人物为视角的创作方法,也可以将传统鬼戏中精彩绝伦的武丑应工尽情发挥,符合初涉戏曲的观众审美。剧中的油流鬼不仅起到了串场的作用,而且还参与剧情,通过他的目光发现了判官的徇私枉法,所谓“人间地狱,走个来回,当一天灯官,就不让这天下黑”,一个小人物的心理逻辑、情感逻辑以这个善良正义的小鬼为依托逐渐充实丰满。另外,鬼戏的表演是传统戏曲中很是出彩的一个类别,但平常人们都是将目光集中在女鬼或判官身上,小鬼作为龙套常常被忽视,而《灯官油流鬼》却与众不同,将扮相同样好看、台词通俗、还有不俗技法表演的小鬼推至台心,可谓别出心裁,有创造性。
但这部戏最引人注目的原因还是中国皮影的介入。“小剧场”的魅力就在于它的边界探索,此戏不仅与戏曲结合,还与皮影混搭,据说是法国青年导演的想法。戏中,柳金禅和颜查散的爱情线直至柳金禅被害的情节全部用皮影来呈现,并配以演员幕后的配唱,皮影白色的幕布由三块组成,根据场景变幻而移动并没有打破戏曲舞台的连贯性,相反幕布上的皮影与幕布前的真人表演相对应,共同构成了舞台上下场的自由流转,舞台空间也更为丰富。可以说,该戏的创作理念很具有实验精神,既将戏曲的传统发挥又有跨界的创造。可惜的是,如果此中的皮影演绎可用精湛来形容的话,真人表演却只能用业余来界定,观念是有了,可戏曲特有的舞台表现却大打折扣,戏中男旦、女花脸以及小鬼的表演功底薄弱极大地折损了整场演出的魅力,让闪转腾挪、活灵活现的皮影艺术抢尽风头。所以,对于小剧场戏曲来说,戏曲的属性还是根本,无论实验的观念多么令人点赞,戏曲表演的本位也绝不能缺失,更何况在如此近距离的观演空间内,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表演的粗糙反而被无限放大。
不能低估现代观众对美的判断力
与《灯官油流鬼》相比,《琼林宴》《一旦三梦》却正好相反,它们的创作精神是以尽量保留戏曲传统文本和表演的原貌为主,但又有些小的加工。《琼林宴》是在传统老戏的基础上加了一个老人给小孩讲故事的引子,《一旦三梦》是在女人的三个梦境之间加了非京白、非苏白、而是用普通话插科打诨的串场人。不知道创作者的思路是什么?是为了迎合所谓“小剧场”的概念吗?觉得将一个传统老戏原封不动地放到小剧场里,有些不合适?还是怕观众不理解剧情,想用现代化的语言给观众解释一下剧情?无论哪个,创作者都犯了可笑的错误,前者是过于狭隘地理解小剧场戏曲,后者是过于低估观众的能力。
其实,小剧场戏曲发展到今天,多种面孔是不可避免的,与西方小剧场戏剧的发展路径一样,实验和先锋不一定是它唯一的表情,如果真能够在这样一个近距离的观演空间内欣赏一出唱念做打俱佳的传统老戏,又何尝不可以呢?别忘了,传统戏曲本来就是在厅堂、戏园里的小氍毹上演的。原汁原味的戏曲表演在现代小剧场的空间内亮相,让观众清晰地看到了大剧场中看不到的细微表情、汗珠,以及眼神、髯口等技巧,这种观演距离拉近自然有种与以往不同的非凡感受。作为目前新生代老生演员的凌珂在《琼林宴》中也算是唱做俱佳,唯有那画蛇添足的引子让人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一旦三梦》显然也是想尽量保留昆曲细腻而极致的表演美,昆旦演员顾卫英一人分饰三角,《牡丹亭》中杜丽娘、《烂柯山》中的崔氏、《长生殿》中的杨贵妃,此三人性格各异,在旦行的表演上也有差异,如果说杜丽娘和杨贵妃在昆曲中属于闺门旦的话,那么崔氏属于正旦,其中在塑造人物上不仅阶层不同、性格不同、身份感的表达也不尽相同,所以,一人分饰三角很考验功力。但是,可以说除去顾卫英所展示的昆曲传统的东西之外,该戏极力表现小剧场创新的地方都很让人遗憾。首先,是串场人。他用类似说相声的语气来衔接剧情,其中大多是现代语言,调侃逗趣的话,显得与整个昆曲的雅致氛围极其不符,对整场演出的风格有所破坏。如果是借用传统戏曲中“副末开场”,让整台戏浑然一体或许会是更好的选择,这其实暴露了编剧创造力的不足。其次,就是该戏为了迎合“小剧场”的概念而在舞美上的所谓创新。舞台由一张白色的纱幕隔开,纱幕左后则是一套欧式古典风格的桌椅,桌上一面类似风格的梳妆镜,演员几乎全部的换装都在这里进行,而纱幕前是演员的演区,传统戏台上一桌二椅也变成了欧式古典风格,一出昆曲却被舞台氛围烘托得不中不洋,仿佛中国古典园林孕育下的昆曲愣是被挪到了欧洲小镇。最后,龙套演员的不匹配也是问题。由于是小剧场演出,不能照搬大剧场的龙套演法,但是此部戏的龙套无论是在表演上还是在道具上都显得极为粗糙。在此,我想表达的是,虽然“小剧场”诞生之初,革新是它最初的特点,但是面临小剧场戏曲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课题时,我们却不能为了小剧场的革新而丧失传统戏曲的古典美感,也不能为了迎合现代观众而破坏戏曲传统的法则,更不能低估现代观众对美的判断力,在这样一个独特的场域内,对的东西会被放大,不对的自然也会被放大。
戏曲欣赏的还是技巧与程式下活脱脱的人
戏剧的生命力究竟如何,据说是要看原创剧作的水平,那么小剧场戏曲的生命力如何,大抵也是需要考量一下原创的实力。这次小剧场戏曲优秀剧目的展演,《碾玉观音》《赶尸记》和《倾国》基本可以归类为原创作品,平心而论,从中能够看出年轻创作者们活跃的创作观念,但有时观念的混乱也制约着原创作品的水准。
《赶尸记》和《倾国》的创作者显然都热爱戏曲,是常年浸染在戏曲氛围中的年轻人,如何让戏曲被更多年轻人接受也是他们思考的问题,所以,《赶尸记》被定位为京剧丑角玩笑戏,将湘西民俗赶尸与京剧中最具乡土气息的玩笑戏结合在一起;《倾国》的创作定位为话剧与戏曲结合,创作者有意于重新思索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这两个早已被历史定义的失败者和成功者的个体生命状态。两部作品的创作者显然都有着一颗充满活力的探索之心。但是探索小剧场戏曲,最为不能轻视的恰恰应该是戏曲的本体,如果没有敬畏传统的心,呈现出来之后可能会有“四不像”的嫌疑。
《赶尸记》中如果能把玩笑戏中“三小”的表演特色淋漓尽致地发挥出,将京剧玩笑戏中形象生动、语言机趣的喜剧特色,甚至是世俗特色发挥地恰到好处,凸显戏曲大俗即大雅的审美特点,或许会与现在看到的不同。如何能够将现世风土民俗与古典程式融合,而不是毫无创造力地上演赶尸闹剧,如何通过戏曲移步换景、抒情写人的优势展现湘西特色和人物性格,这其实都是需要功力的,同时创作者需要对戏曲传统深入了解和熟知。而这正是《赶尸记》最为欠缺的。
《倾国》的文本还是可以看出编剧的人文思考的,关于西施浣纱、夫差亡国、勾践卧薪尝胆的古老传说在不同的朝代早已被不同人书写过,说明它本身蕴藏着经典性。《倾国》当然要重新解读,而吴王夫差这个因红颜误国的君王就是编剧的新视角。解读有美人相伴、曾经金戈铁马的夫差如何沉沦,解读贡献美人、卧薪尝胆的勾践如何谄媚而卑贱地活着,解读女人爱情滋长的多种理由。作者力图挖掘每一个人作为“人”的心理发展轨迹,因为结果只是属于历史的,唯有过程塑造了人,却往往被人们忘却。《倾国》的文本渗透出作者的哲理性的思考,如果作为纯粹的小剧场话剧,我认为依循着此路径可以继续深挖下去,可惜的是,它是小剧场戏曲。我始终认为戏曲最大的优势不是哲理叙事,而是抒情叙事,所以,演什么重要,怎么演更重要,过于复杂的人文思考对戏曲表演的发挥又有多少优势可言呢?所以,目前《倾国》的呈现方式有些杂乱,其中有话剧讲述的一条线索,也有人偶的运用,还有戏曲的表现,但是给我的感觉是没有哪一门类的表现让我折服,点子有了,亮点不足,离完美距离尚远。这其实暴露了创作人观念混乱的问题,或者说是对小剧场戏曲的创作没有建立正确的本位意识。还是那句话,小剧场戏曲,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为了实验而实验,对传统的敬畏之心还是要有的。
这一点《碾玉观音》做得要比前两者好,好的原因就在于编创者们是在戏曲的规律下创作的,没有旁逸斜出,这绝对是小剧场戏曲的重点。此戏的编剧兼导演是年轻女孩李卓群,恐怕是长期在戏曲环境中浸染,对戏曲的熟知程度显然在一般年轻人之上,她还曾以一部小剧场戏曲《惜·姣》获得好评。这个《碾玉观音》,取材于宋话本,话本原本就具备了丰富的情节和戏剧冲突,这对于戏曲创作来说是利,因为人物构架都已具备,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弊。众所周知,戏曲历来讲究“以歌舞演故事”,这个故事并非等同于情节,也就是说,其实戏剧、小说或电视剧中所追求的跌宕起伏的情节要素在戏曲创作中反倒是个大忌。过于复杂的情节无助于“无动不舞,无声不歌”的戏曲表演原则。为什么呢?人物们都在忙着交代叙事呢,自然会削弱抒情、描景、写人的写意能力。而留白这种传统美学原则对于戏曲创作来说太重要了,尤其是今天。不要说小剧场戏曲因为是面向年轻人的,所以一定要讲一个圆满丰富的故事,真要听故事观众可以看电影、电视了,但凡进入小剧场戏曲的空间内欣赏戏曲,欣赏戏曲的技巧与程式下活脱脱的人还是最重要的。而《碾玉观音》其实缺的恰恰是这些,故事下的唱段、表演没太多亮点,至于故事本身在内涵上也没有太明显的突破,无非是私定终身、隐姓埋名、女鬼回到阳间找自己的情郎。所以,《碾玉观音》作为小剧场戏曲,实际上在改编上还应该继续做减法,而在表演上则应该精细打磨,这当然考验的是创作者的原创能力,原创肯定比脱胎于传统老戏的小剧场戏曲难度要大。
在中国,如果从1982年发生在北京人艺的那部《绝对信号》算起,小剧场戏剧已经走过33年光阴。从推倒“第四堵墙”的初衷到把“小剧场”看作是一张能够将年轻观众拉入剧场的王牌,“小剧场”区别于大剧场的自由度和包容度始终是被创作者们津津乐道的,否则不会有15年前的那场古典与现代的邂逅。可是,谁又能说它不是隔世的相逢呢?戏曲产生的那一刻就是在小的、开放的空间内纵横捭阖,几百年后,终于又回到了它原本似曾相识的空间内,所以,小剧场戏曲,也许它是现代的,但其实它更是古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