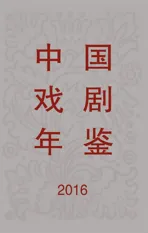现代语境下中国戏曲的传承困境
2016-11-20李红艳
李红艳
目前,全球化、现代化已成为浩浩汤汤的天下大势,在这样的潮流语境中,中国戏曲要图谋发展,必须保持与与潮流共涌、与时代同行的锐气和鲜活;与此同时,尊重文化的多元化、民族化、个性化也正成为全世界人们越来越一致认同和自觉践行的“共同纲领”。特别是近几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先后问世及生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为包括中国戏曲在内的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提供了契约和法律意义上的道德遵循和行为规范。作为最具民族个性、中华特色的中国戏曲,在这样的生存语境中,如何在传承与创新、守护与发展,维护稳定性与尊重变异性这个既相互龃龉,又相克相生的两难悖论中找到一条稳妥、有效的发展之路,确实是个难题。其中既有分寸把握和掌控上的艰难,更有观念认知和实践操作偏差上的或左或右。而对戏曲传承发展构成致命打击的,最关键的恐怕还是认识和观念上的误区。
一、现代化语境中“嗜新症”对中国戏曲造成的传承困境
“艺术贵在创新”是被无数实践证明了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古老的戏曲艺术从历史的深处一路走来,到今天积淀成为最具中国元素、中国个性、中国特色的艺术品类,正是历代艺术家革故鼎新的结果。但是,时下的一些戏曲“创新”,却误入歧途,成为备受诟病的“耍泼、纵欲”行为,一些专家、观众几乎到了谈“新”色变的程度。“创新”有那么可怕吗?说实话,那些“嗜新癖”们的盲目“创新”,的确能给戏曲的传承带来灭顶之灾!
先来说说什么是“嗜新症”!
1973年,奥地利诺贝尔医学和心理学奖项获得者、“习性学之父”康德拉·洛伦茨出版了一本书《人类文明的八大罪孽》,他希望藉此搜寻人类进化过程中由于侵犯行为而造成的骇人听闻的严重后果。这八大罪孽中,有一条就是“抛弃传统”。在这个话题的阐释中,康德拉提出了“生理性嗜新症”的概念。他认为,人在青春期阶段,开始有了叛逆心理,开始离开父母,脱离传统。那些传统事物看起来都很无聊,而所有的新鲜事物则富有魅力,“他们环顾四周,寻求新的观点、想法,寻找可以加入的新团体……人们可以称之为是‘生理嗜新症’。”①康氏认为,“生理嗜新症”有着很高的物种保持价值,它赋予那些过于僵化呆板的传统文化行为准则一些适应能力。“要实现结构的转换,就必须拆除旧框架。”②
康氏转而又指出,“生理嗜新症”是青年人人生特殊时期的阶段性生理反应,跨过了这个阶段的青涩和冲动,便是“传统之爱的复活期”。在“传统之爱的复活期”,他会对父辈、对传统进行回望、审视、重新评价、重新回归,珍视并传承其有价值的成分。他举例说,一个人在60岁时对父亲许多观点的评价一定比18岁时的评价要高得多!但是,“生理嗜新期”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在除旧建新的过程中必定会有一个动荡的、毫无防卫能力的时期。”当这个系统功能受到外部、内部各种因素的影响时,这种“嗜新状态”就可能变成固执的、非生理性的,那么,其导致的结果就可能是:青年人对父辈仇恨的加深,对传统的无视与断裂。
回到当前戏曲“创新”的主题上来。这里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戏曲革新”展开话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戏曲遭遇了令人恐慌的“戏曲危机”,在各种外来文化和各种新的戏剧观念的冲击下,戏曲几乎是无所适从,陷入史无前例的阵地和观众“沦陷”。那一时期,“戏曲过时论”、“戏曲夕阳论”、“戏曲危机论”的口号震耳欲聋,彼此起伏的呼喊让大家感到中国戏曲“来日无多”。戏曲界的广大同仁于心不甘,开始了企图重获新生的戏曲变革。从那时候起,“改革”、“创新”就成为伴随戏曲艰难复苏、崛起的“励志箴言”和行动准则。戏曲变革,已远远突破了循序渐进的正常逻辑规律,各种创新、实验蜂拥而起,改革创新的幅度也远远超过人们的接受力。这场变革确实极大推动了戏曲现代化的进程,既有创作观念的重大突破,也有表现形式的巨大创新,确也创作演出了不少被广大观众认可,足以载入史册的优秀作品,有收获,有经验,更有教训。这场发轫于“拯救戏曲危机”的变革,算得上是谋求戏曲新生的“生理性嗜新”。但是,正如康氏所担心的,“生理性嗜新期”也是危险期。那种超常规的革新幅度,新观念、新手段、新元素短期内的迅速集聚,确实也让一些人眼花缭乱,不能自持。改革中的急切、盲从、轻率、甚至对传统的大杀大伐现象普遍存在。但是,在大家对这些教训还来不及思索,来不及回望,来不及反思的时候,全球化、现代化的浪潮已经越来越呈现出席卷之势,“创新”已经从先前“拯救危机”的探索实验变成了顺势而为的时代主旋律,大家或是追逐着潮流走,或是被潮流裹挟着往前走,于是,那些盲从者、急切者、轻率者遂被被轻易裹卷,不能自持,在“创新”的路上渐渐迷失。如果说,80年代那场改革中的盲从、轻率还是出于“求生”的急切和“摸石头过河”的茫然,还是有志于戏曲未来发展的激情探索和理性思考;那么,后来一些改革者的轻狂和冒进,则完全是顽固“嗜新症”下对传统的睥睨、无视和抛却,是对“创新”的狂热迷恋和曲意逢迎。从主观意识上,他们已不愿驻足,不愿回望,不愿反思,对传统完全没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也就再也回不到“传统之爱的复活期”。此时的“创新”,已经完全变了“味道”。
综观这些年的戏曲创作,越来越多的人已有切肤之痛,“嗜新症”,已经成为不少戏曲创作人员的病态心理。博大精深的中国戏曲,在他们眼里已经不再神圣,不再珍贵,而成了任意宰割、任意糟蹋的“纵欲”试验田。于是,我们看到了太多以“创新”之名,行破坏之实的戏曲创新;看到了太多把戏曲搞得面目全非的“创新”:写意、虚拟、程式化的戏曲本质丢失了,剧种没有剧种味道了,人物没有行当归属了,表演不讲程式章法了……创新,已经不是艺术发展从偶然到必然的内在需求,而是癖好恣意下的狂野撒欢;已不是一种天赋、能力的体现,而是一种无知者无畏的胡言乱语;已经不是除旧布新、推陈出新的艺术探索,而是将婴儿连洗澡水一块泼掉的轻贱传统;已经不是引领潮流之先的开拓之举,而是贴着标签自我标榜的虚张声势……那些遭到观众、专家诟病、谩骂的“创新”戏,大抵都是“顽固性嗜新症”病态下的“创新”成果。这种病,对戏曲的危害,远比戏曲危机来得厉害,它从根本上削弱、消解、阉割了戏曲最本质、最有价值的东西,对中国戏曲的传承造成了灾难性破坏。
数年前,看到戏曲教育家、理论家傅瑾质疑戏曲创新的文章,觉得有失偏颇。今天回头再看,却有某种掷地有声的认同感。他在《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自言自语》中写道:“创新本该是对艺术一个极高的标准,现在它却成了一批蹩脚的末流艺术的托辞;创新原本应该是经历了大量的学习与模仿之后,对传统艰难的超越,它是在无数一般的、普通的艺术家大量模仿和重复之作基础上偶尔出现的惊鸿一瞥,现在却成了无知小儿式的涂鸦。”他那看似偏激的观点,某种程度上是对这些“创新”虑之深、恨之切的“矫枉过正”。放眼望去,能够看到,当下中国大量的“嗜新症”患者,前赴后继为中国戏曲园地制造的景观,大多是惨不忍睹的“满目疮痍”。这些盲目的创新,归根结底,都是对传统缺乏认知,缺乏自信,长期患虚妄症的结果。
窃以为,康德拉·洛伦茨提出的由“生理嗜新期”和“传统之爱的复归期”(迟到的顺从)构成的这个体系,对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创新来讲是一个健康的内部生态循环体系,它为传统艺术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和思路。“生理嗜新期”是生理性的、短暂的、汲取激情和勇气的变异期,它“将传统文化中那些明显过时的、陈旧不堪的、不利于新发展的因素淘汰掉”;“传统之爱的复归期”是价值认知上的、渐进的、长期的,是对传统价值本质的再认识、再评价、巩固强化期,它“将那些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织结构继续保存下去”,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戏曲内在结构的相对稳定。待积累有年,会再次产生一个意识上的“嗜新”期,而这时候的“创新”,则是立足传统的,有根基的,有底气的,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变异——稳定——再变异——再稳定,中国戏曲就是在这样的循环往复和对自身的再认识、再突破中一步步前进的。所谓的推陈出新、返本开新、固本求新、传统戏曲的现代回归,都是这种良性体系内的良性循环、上升、发展。
对传统的轻贱,还体现在对科技的过度迷恋上。康德拉在对“抛弃传统”的罪孽陈述中,还特别指出科技发展对“抛弃传统”罪恶行为的重要影响。他说,“科技的进步促进着文化的发展,这种由工艺强加于当代文化上的发展速度也产生了这样一个后果,它使得每个时代所拥有的传统财富中都有相当大的部分都是有理由被青年人批评为陈腐过时的。”③科技发展对文化传统影响的后果在中国的传统手工业艺术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中国戏曲的发展中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应验。如今,科技发展已经为戏曲舞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能和景观,先进的舞台科技在带给人们幻觉般的真实感、视觉的震撼感、审美的愉悦感的同时,恰恰也掣肘、削弱了中国戏曲表演艺术言说功能的诸多潜在可能。因此,年轻人对中国戏曲艺术以虚代实、以无代有、以有限表无限的强大写意功能和优势没有了敬畏感,没有了自豪感,没有了认同感,当他不以拥有这样的艺术而自豪、而骄傲、而珍惜的时候,他不可能认同这门传统艺术的价值,所谓的“传统之爱的复活期”就不会到来,抛弃传统大概就是必然的结果。
“嗜新症”导致的戏曲创新“泛滥”已经对戏曲的传承保护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大量的资金都投注在了这些所谓的创新剧目中,有意味的是,舞台上常演、观众爱看的,依然是那些流淌着中国戏曲诗情、韵味、程式、情趣等传统之美的剧目。人们已经厌倦了“嗜新症”下的妄行呓语,且对它所带来的危害已有深刻“警觉”。今天对“戏曲继承传统”的深切呼唤,其实正源于此。不少专家也已经对这种“创新”提出了质疑、批评和反思。“只要一种危机的起因被充分认识,那么其危害性也就会被大大削弱。”④认识危害、分析原因、总结得失,应该是走出误区的第一步。这些年,灾难性戏曲“创新”的泛滥,评论界的失语、缺位和太过轻率随意的“点赞”、“叫好”,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总结长短得失,指导创作实践,引领创作导向,唤起反思意识,应该是戏曲评论界应有的担当。对真正的艺术创新,我们要不吝赞美;对有价值的艺术传承,更要高歌点赞;对打着“创新”旗帜的胡言乱语,一定要慎重说“好”,更要敢大胆批评。建立良性的戏曲创作生态,重振戏曲传统的自尊、自信,保护中国戏曲的有效传承,戏曲评论界不可缺席,任重道远。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中的传承困境
说完了创新中的“传承”困境,再来说保护中的“传承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方兴未艾,在全球蓬勃开展,且有“宣言”、“公约”、“法律”作遵循、后盾、支撑的全球性文化保护活动。目前,在中国,“非遗”保护已基本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联动的保护体系,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传统戏曲项目已经达162项,传统戏曲国家级传承人达600余人。入选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和传承人则更多。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保护的行为已经普及。但是,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入开展而出现的,也有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其中,“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保护中的“去艺术化”、“近人情化”、“近行政化”、“趋福利化”,还有对“保护”认识的顽固僵化”,都使得“保护传承”的初衷变得复杂艰难,甚至使传承保护行动陷入尴尬的困境。
1.狭隘的地方主义、功利主义对某些剧种造成的“肢解性”破坏
以我所熟悉的豫剧为例。我想作为中国分布最广的地方戏剧种,她的现实境况有一定的代表性。
豫剧,是流于面广、观众群体庞大的一个地方戏剧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其发展的兴盛期,全国近20个省份都有专业的豫剧团。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戏曲艺术的整体式微,豫剧的分布区域虽有所减少,但仍然是分布区域最广、观众最多的地方戏剧种。2010年,我所在的河南省艺术研究院对全国所有的专业豫剧表演团体进行了地毯式的实地调查,共走访了13省份的专业豫剧团156个。仅仅过了两年,到2012年,原来的13个省份就变成了11个,剧团少了数十个,而且目前仍在减少。大概谁也不曾想到,造成剧种分布区域缩小和剧团数额急剧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却是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众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对独特性、创造性、区域认同感的尊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精神。但是,一些地方文化主管部门,将区域性狭隘地理解为地方性,将独特性理解为唯一性,更忽视了非遗保护中对某一艺术形式“群众持续认同感”的要求,对多元性的尊重,将分布在本省、广大人民喜欢、但诞生在外地的剧种视为“外来剧种”,对之采取排斥、挤压、拒绝的野蛮态度。强行使其“变节招安”,改变性质,然后,将其作为本地的遗产加以保护。于是,我们看到,豫剧在江苏,变成了江苏梆子;在安徽,变成了淮北梆子;在山东,变成了山东梆子;在湖北,变成了花鼓戏、二棚子戏……
狭隘功利的地方主义已经够可笑,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游走于全国戏剧界的权威专家,却颠倒黑白,心安理得地干着“指鹿为马”的荒唐事,为这种狭隘自私的文化保护主义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例如,山东聊城市豫剧团、济宁市豫剧团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豫剧团,章兰、李新花作为这两个团的主演,分别以豫剧的剧种身份获得了“二度梅”和“梅花奖”。但是,某些权威专家在配合当地政府宣传的学术文章中,均以“山东梆子”的身份总结介绍上述剧团、演员,试图生硬地割断他们与豫剧的历史关系。近些年,豫剧,就是在这样的“保护”名义下被残酷“肢解”。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些改了名换了姓的剧团,下基层演出,往往还要挂上“某某某豫剧团”的牌子,因为他们数十年来得以安身立命的、在观众那儿获得的“认同”是豫剧的身份。非遗保护伞下的“苟且偷生”,让本来名正言顺的艺术行为在面对市场时变得“豫”说还羞,在进行正常的艺术交流时变得心态“暧昧”。这,就是它们目前的真实状态。
不太知道,全国跨地域的剧种还有没有类似豫剧的尴尬和困境?但我觉得豫剧绝不是剧种家族里的个案!如果所有跨地域的剧种都面临着相同的遭遇,那所有的地方戏,最终都要退缩到最初的本源地去寻求庇护和生存,越剧要回归浙江,秦腔要回归陕西,评剧要回归河北,淮剧要回归苏北……与其这样阉割式地保护,还不如让它在多元的文化格局中接受优胜略汰的残酷考验,或在风雨飘摇中历练得自信强壮,或在无情的竞争中被自然淘汰。如此,也远比“以保护之名,行破坏之实”的人为破坏来得自在、鲜活和任性。
剧种的分布,本身就是优胜劣汰、不同时代观众审美筛选的结果。逆观众认同感的任何外在强加和干预,未必能达到预期目的。相反,这种功利狭隘的保护思想,无异于画地为牢,不管对原来的剧种,还是对试图想要作为本地遗产保护而改名的新剧种,都造成了艺术传承、发展的巨大困境,最终也造成了对剧种生态的极大破坏。就像当今自然界的生态破坏一样,以拙劣的人造景观代替永远不可再生的自然景观。
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独具特色的地方剧种,都有各自独特的文化密码和遗传基因。但是,一些地方无视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为了获取保护资金,可谓绞尽脑汁、用尽心机。除了上面提到的强行改变剧种的“移花接木”,还有强行“复活”剧种和“创造”剧种。“复活”就是把当地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或流行过、但已经灭亡多年的剧种重新找回来,企图以保护资金的注入让它获得重生;“创造”就是捕风捉影地创造一个新剧种。这两类剧种,一般流行地域很小,存在历史也不长,或仅有零星的资料遗存,或仅有个别民间艺人的碎片记忆,不太为人所知,容易制造“履历”和辉煌历史。它们没有根基,少有传统,缺乏人员,没有演出实体,不用说开展活态的传承保护,就是基本的资料记录挖掘抢救,恐怕也是一种空谈!因为没有能力开展有效的传承保护项目,那些绞尽脑汁争取来的保护经费,只能挪作他用、购买设备,甚至以劳务费的形式装到个人腰包……目前,大家普遍意识到非遗传承保护中存在的“重申报轻保护”、“重投入轻效果”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无传承可能、无保护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义下的“保护传承”,有些其实只是一句冠冕堂皇的套钱空话!
2.“非遗”传承人评定的“去艺术化”、“近人情化”、近行政化”、“趋福利化”,导致保护结果和初衷的较大落差
作为当前既有政策支持,又有法律保障,还有经费投入、大势所趋的全球性保护行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包括传统戏曲在内的传统艺术的传承保护确实是有力的促进和推动。就传统戏曲而言,除了对剧种的整体保护,还有一项重要的传承保护手段,就是对“传承人”的评选和认定。戏曲是一项技艺性非常强的艺术形式,特别是作为核心元素的表演艺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一个成功的流派传承人,其艺术大多是经历了千锤百炼的实践锻造和苦心孤诣的艺术探索,绝活和本事都附着在演员身上。他们要把这些“绝活”或融合了人生感悟的艺术创造成果传递给下一代,“口传心授”是很重要的传承方式。所以,“非遗”传承人的评选和认定,对剧种和流派的传承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当选为剧种和流派的“传承人”,不单是一种荣誉,更是一份责任和担当。至今为止,仅传统戏曲的国家级的传承人就达到600余人,省级、市、县级的传承人则更多。如果这些不同级别的传承人都能发挥“传、帮、带”的作用,那他们汇成的滚滚洪流,对传统戏曲的传承保护将是非常强大的一股力量。但毋庸讳言,在这些传承人中,确有一些非实至名归。特别是近几年,评选当中的“去艺术化”、“近人情化”、“近行政化”、“趋福利化”倾向十分严重,行政干预、亲信优先、打压异己、不择手段,把当选传承人作为凌弱手段、恃强资本、福利待遇……传承人的评选已经裹挟了太多的非艺术因素。而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是显而易见。且不说有些享受着传承人荣誉、待遇的“传承人”不去传承、无力传承,仅是他们的当选,已经对那些真正在为剧种奉献担当的艺术家又造成了待遇和精神上的不公。毕竟,“非遗传承人”相对于各个剧种人才济济、名家众多的现实,名额少之又少,一定程度上是这个剧种的形象符号。因此,非遗传承人评选当中的“四化”倾向,对剧种传承保护产生的负面效应不可低估。在现实操作中,这种负面影响已然显现,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传承困境。
“非遗”保护是一项新事物,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做好准备、做好筹划的时候,它已经以不可阻挡之势来了。因而,在行进当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始料未及的问题。如何在行进当中不断反思、不断调整、不断完善项目评选和传承人评定的机制,如何对保护项目的实施和传承人的传承状况进行有效的监管、评价、考核、验收,如何加强对保护经费的管理,做到钱尽其用……恐怕都是亟待完善和解决的问题。否则,非遗保护中结果和初衷的适得其反,大概会成为常令我们扼腕长叹的遗憾。目前,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以经典剧目传承、以流派传承、以剧种行当人才培养为依托的支持方式,就实现了剧种传承力量的跨地域有效联合,值得借鉴。
3.对“保护传承”的认识误区,造成保护传承的僵化、板滞
和前面“丢弃传统的创新”一样,在传统戏曲的保护中,同样存在对“保护传承”的偏执化、极端化认识误区,将“保护传承”和“发展创新”完全对立起来,强调传承的“亦步亦趋”、保护的“原汁原味”。认为曾经的、传统的都是有价值的,应该保护的,值得继承的;当下的、创新的都是没价值的、不值一提的。于是,在传统保护中,又开始一窝蜂似地走“回头”路,向历史致敬,向传统致敬,以“原汁原味”为保护传承的最高境界,一切以旧为贵、以“原封不动”而马首是瞻。将保护传承带入了僵化、板滞的另一个误区,显然是走入了另一个极端。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同时踏进同一条里”,因为当人第二次踏入这条河时,河里的水已经不是昔日的水了。一切皆流,无物常驻。“传统”本身就是一条流动的河。目前所认同、所强调的那个“传统”,其实也就是当下人们视野所及的那个传统,而不是该剧种最原始的那个传统,甚至也不是该剧种最本质、最精髓、最核心的那些东西。艺术在流动中发展,也在发展中流动。所谓的稳定,也只是某一历史阶段的相对稳定,历史的车轮还是在去芜存菁的吐故纳新中滚滚向前。保护,说到底还是为了传承,为了发展。王骥德在《曲律》中曾说:“世之腔调,凡三十年一变”。每个历史阶段的艺术创造,都有它可贵的创造,也有它难免的局限。比如梆子体系剧种的男声唱腔,都是在对不同时期声腔局限的一步步突破中走到今天的。追求“原汁原味”,能回到那个让男声提高八度、和女声同腔同调的年代去吗?能把曾经的局限、遗憾当宝贝继承吗?“保护”是保护传统中最本质、最核心、最精粹的东西,不是原封不动地搬来为今人所用,不加选择地全盘继承,如此,保护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应该是保护传统的应有姿态和最终目的。
中国戏曲艺术的生存境遇,从没有像今天这么复杂。做好多元中的坚守、创新中的继承和继承中的创新,何其难也。但中国戏曲,也许就会就是在这种克服困难的披荆斩棘中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康庄大道。让我们为此一路同行!
注:①②③④⑤:《人类文明的八大罪孽》,康德拉·洛伦茨著,徐筱春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