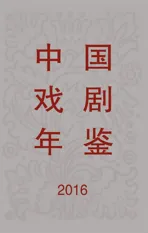舞台美术新思维三题
2016-11-20刘杏林
刘杏林
进入新世纪以来,舞台美术连同整个戏剧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关注和探究这些现象及其背后的观念,对于舞台美术专业教学和创作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适逢上海戏剧学院召开“2014舞台美术新思维研讨会”,我在梳理自己有限的相关知识的过程中,发掘出一些国际上给人印象或感触较深的,与舞台美术新思维有关的现象或者说法。以下这些具体说法和现象大多是介绍性的,而不都是我个人的结论,所归纳的也不尽全面,旨在给大家提供参考,或者引发更深入的思考。
一、舞台美术设计者作为演出作者而存在
“2011布拉格国际舞台美术四年展”将名称中的“舞台美术”(scenography)改为“演出设计”(performancedesign)。在这届四年展上,克罗地亚国家展的主题是“作者舞台设计”(StageDesignerasanAuthor)。这说明,舞台美术设计领域已形成了一个引人注意的发展趋势:舞台美术设计者已具有作者的特征,或者说舞台美术设计者是作为演出作者而存在的。这与舞台美术设计者工作重心的转移、观念方法的转变是分不开的。传统的舞台美术设计,无论是布景服装还是其他设计,大多依据剧本表面的提示,从剧本的人物规定、剧本的场景规定,特别是时代地域规定进行创作。如此一来,舞台美术设计者与导演有统一的出发点或参照物,最后的创作成果,即视觉样式自然不会相差太远。但是最近几十年来,这种工作方法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在当代舞台设计中,舞台美术设计者越来越强调对特定剧作的阐释,而不仅仅根据剧本中关于场景的表面提示进行设计。正是这种创作立场的确立,使人们过去熟知的剧目耳目一新。以俄罗斯舞台上契诃夫的《樱桃园》之演出为例,“樱桃园”一直是这一剧作中的关键形象,把它作为大自然景色的一部分呈现出来,是从契诃夫时代到1950年代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中所要把握的重点。然而这一把握重点并非一成不变。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樱桃园”成为一去不复返的生活方式的隐喻,也成为其基础与形态遭残酷毁灭的隐喻。在2003年至2006年的莫斯科的三台演出中,“樱桃园”则象征着剧院(代表民族文化遗产)和每个艺术家自身。在这里,“樱桃园”的自然属性变得不再重要。对于舞台美术设计者斯坦尼斯拉夫·贝涅迪克托夫(StanislavBenediktov)来说,樱桃园就是曾号称为“第二个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俄罗斯青年话剧院。在他2004年的设计中,剧院空旷的观众厅被处理成演出空间的一部分,与舞台贯通,观众则坐在舞台上面,对着演区的一侧。观众厅作为一个反常处理的空间和另一个世界的局部,被白布覆盖和遮挡着,人们似乎是通过透明的百页窗来看景象,到演出最后淹没在黑暗中。贝涅迪克托夫和导演鲍罗丁(AlekseyBorodin)在樱桃园的毁灭中,看到了这个剧院本身的衰落,看到上一辈杰出演员和导演所创造的精神世界正慢慢消失。2006年,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戏剧学校,德米特里·克里莫夫(DmitryKrymov)及其学生根据包括《樱桃园》在内的契诃夫的四个剧作,改编、整合成功《拍卖》一剧,其舞台美术设计概念是,将瓦西里耶夫戏剧学院剧场作为将要拍卖的樱桃园。他们认为瓦西里耶夫剧场是独特的俄罗斯文化载体,既是他们的母校,也是他们首次演出的地方。这座建筑及其环境实际上已被莫斯科当局从瓦西里耶夫手中收回,在剧中,它被按比例缩小为河沙制成的复制模型,在演出中堆放在铺着黑胶皮的地板上,成为舞台设计者眼中的具有象征性的樱桃园。2003年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的《樱桃园》中,舞台美术设计者鲍罗夫斯基(DavidBorovsky)和导演沙庇罗(AdolphShapiro)用樱桃园的毁灭来隐喻这一剧院的真实命运。绣有海鸥图形的剧场大幕成为布景和演出意义的传达者。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时代到今天艺术剧院的观众,都目睹它一次次开合之间所展示的戏剧景象。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一次,大幕不像一百年来那样,习惯性地向舞台两侧打开,而是往舞台空间纵深处滑动。如此意外和反常的布景运动,暗示了不可逆转的灾变,标志性的大幕几乎是这次演出中舞台上主要的舞美视觉因素。它代表着几代艺术家顶礼膜拜的舞台,反映了这个伟大剧院和伟大文化的悲剧命运,表达了契诃夫剧作中的深刻思想。[1]当舞台设计把剧本提示或规定情境中原先的人与景的关系,也就是环境与角色的关系打破,使原先规定的场景或支点“缺失”后,舞台设计就不得不建立新的人与景或人与空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舞台美术设计者无法回避从导演的角度去考虑对演员的处理,如此才能对文本有更深入的把握。概言之,当今的舞台美术设计者是以演出作者的身份参与戏剧演出的。具体地说,以往作为舞台布景设计,主要是提供一个剧本所描述的环境和一个剧情发生的地点,对演员动作的考虑相对有限,可是当你带着自己对剧本独特的理解,提供一个跟剧作者的预期完全不同的舞台空间或者舞台布景时,你就不得不给导演或演员提供一个新的解决办法,以代替原先那个缺席了的支点。也就是说,要能够指明在这样一个环境或空间里面,演员该怎么行动。比如,原来剧本的提示中有一扇门,现在把它取消了,那么演员该怎样上下场?本来剧本规定有桌椅,现在没有了,或成了别的东西,那么演员怎么与之产生联系?原剧本中规定的景物缺席以后,舞台美术设计者就不得不从演员的行动角度去考虑变通方案。这就如同你设计一座房子的时候要规划它的功能一样。如果在这方面不深入考虑,没有足够的预期,没有足够的思路提供给导演和演员,那么这个设计注定会不完整或不成立,甚至是短命的。我们不光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而且在教学中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学生开始时往往容易根据自己的理解提供一个超越剧本规定的场景,其中具有学生自己主观的视像或空间,但他很少能够像导演一样,想象演员在这个空间里怎么演戏,这是特别大的缺失。而在国际上,那些越是有特点的,或者越是别具一格的舞美设计,就越是很大程度地介入了导演思维,也就是说舞美设计要从一个导演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总体上说,舞美设计要从概念上对整个剧本有所把握,在这点上,前辈老师也提出过,强调舞美设计的“形象的种子”的同时,着眼点应该远远不止于“形象”,而是要更多地放在空间上,也就是要设置人能够活动的空间和支点,想办法让演员在其中行动起来,并且以行动赋予设计丰富的意义。记得胡妙胜先生在多年前就把当代舞台美术的特征之一称作“动作设计”,其实“动作设计”就包含了上述意思,即强调舞台美术设计要考虑到演员行动。舞台美术设计对剧本表面所规定的场景的超越,还在于对剧场表现和接受规律的更深入的认识。当代德国舞台美术设计师约翰尼斯·舒茨(JohannesSchutz)就是一位借喻和虚拟方面的高手,他在场景提供方面充分借助剧场性的表现原则,重视演员表演的发挥和观众的想象力的价值。他的舞台布景是一种知性的空间,是思想和智慧的演练场,而不是幻觉主义图像的滋生地。从他的舞台美术设计中,可以梳理出一份剧本规定景物缺失的清单:在克莱斯特的《海尔布隆的凯西》中,没有了城堡或木炭作坊;在《洪堡王子》中,没有了花园、监狱或者战场;在高尔基的《夏日来客》中,没有了庄园里的陈设、茶炊和白桦林……他认为,当某些东西缺失时,演员(包括观众)会释放能量来补偿正在失去的东西。他指出,人们会喜欢共同探寻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表演情境,如果可能,无需来自外部的额外因素。这意味着舒茨的舞台美术设计基本上是一种空间,在那里,演员和观众双方能够一起思考和想象。他认为与现实相关细节的排除有助于提高观众的主动性,视觉阐述所展现的它自身的逻辑,要胜过从属于文本的规定。[2]对演员行动功能的设计和舞台视觉样式的耳目一新,两者之间如果能做到相辅相成,则使戏剧具有了无限的可能,因为戏剧演出的剧场性或虚拟性本质是其强大的支撑,戏剧演出所需要的是对这一规律的领会和灵活运用。另一方面,在传统的分工下,戏剧学院有了专业的划分,这使我们往往过多地着眼于视觉造型因素而忽视了演员。而上述设计途径的转变则直接考验着我们既定的工作方法、教学模式和专业知识结构。其实,从根本上说,舞台美术设计更大程度地介入演出,是由于戏剧演出的综合性特点或本质的合理发展。戏剧本是综合艺术,专业分工不过是阶段性产物。随着人们对此认识的发展和深入,各专业彼此的进一步融合是必然趋势。在此情况下,国际上许多有影响的舞台美术家涉足导演艺术,或是许多有成就的导演身兼舞台美术师就毫不奇怪了。例如英国的帕梅拉·霍华德(PamelaHoward),德国的阿契·弗雷耶(AchimFreyer),俄罗斯的德米特里·克里莫夫(DmitryKrymov),意大利的罗密欧·卡斯特鲁奇(RomeoCastellucci)等等。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所有专业之间需要互相转行或取代,而是说明了一种规律性的、必然的关联。
二、戏剧可以在任何地点发生
这些年,国内各地纷纷在建造大型的常规剧场,即使是一些县级市,也在建造规格差不多的大剧场。与此不同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由于既要保留历史文脉,又要满足演出形式和实验需要,因此,因地制宜地将旧有建筑改造为剧场或综合性文化设施,正成为更普遍的现象。有着强大的空间改造传统的法国,过去四十年里就有彼得·布鲁克的北方布夫剧院(BouffesduNord)和姆努什金的太阳剧院作为古旧建筑改建和重新利用的典范。法国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改建项目,包括鲁贝市利用百年前经营纺织品的工商业建筑改建的“公共环境”(LaConditionPublique),勒芒市在铸造厂旧址改造的“木筏剧院”(TheRafttheatreRadeau),以及圣纳泽尔市利用前德国潜艇基地改造的“生命”(LeLife)等。这些方案促使了建筑界和政府决策部门进行思考,以充分挖掘这类可以进行功能转换的空间改造项目的价值。[3]德国的类似项目大多与现代主义时期的工业建筑和剧场有关。例如,把鲁尔地区建于20世纪初的大型工业建筑和德绍市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包豪斯风格的舞台改建为前卫表演艺术的实验场所。鲁尔艺术节(Ruhrtriennale)的主要场地波鸿“百年厅”(Jahrhunderthalle)本身就是一个对建筑进行功能性改造的优秀典范,这座既像工厂又像教堂的建筑原本是为1902年杜塞尔多夫贸易和工业展所建的展厅,之后曾长期被当作厂房和仓库使用。直到2003年,设计师皮兹辛卡·平克(PetzinkaPink)看上了“百年厅”卓越的钢架结构,将其从杜塞尔多夫移建至波鸿,使得重新建造的“百年厅”在鲁尔艺术节活动中焕发新的生机。捷克在近年来的戏剧活动中加大了对非戏剧空间的利用——将戏剧演出、美术展、音乐会等艺术演出活动转移到老工业区举行,让废弃的工厂成为固定的舞台。设计师们不再把工厂空间改造成传统的镜框式舞台剧场,他们更喜欢利用这种场地本来的优势(甚至局限性),发掘舞台演出非常特殊的美学价值——质朴、粗砺和未经加工的美。艺术家在其中进行创作,所用的一些材料由于技术和安全原因,几乎不可能在传统舞台上使用。西班牙把同样的空间加以利用,开发出不同的功用,近年来实施了多个相关项目。人们把废弃的钢铁厂厂房、粮库、屠宰场、部队营房、纺织厂车间等老建筑改造为剧场或文化中心。此外,波兰、斯洛伐克、新西兰、挪威、匈牙利、瑞典等国也都在进行类似的旧建筑改造。虽然这些项目的形式和规模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是把历史遗迹和当地居民个人记忆中的老建筑改建为表演空间,让“旧”与“新”相互交织,让过去与未来彼此联结,为城市的文化和戏剧生活增添了新的活力。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在过去十年中将一些建于19世纪的废弃工业建筑更新改造成文化场所,与此同时,还实施了两个将陈旧的公共设施改造为剧院的项目——“戏剧列车”与“戏剧渡轮”。后两个项目赋予了上世纪两种重要的传统交通设施以新的价值。其中,《戏剧东方快车》(OrientExpress),是土耳其与德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合作的项目。在两个多月里,火车从安卡拉出发,途经参与此项目国家的多个城市后到达斯图加特。列车在沿线各国停靠时,都会有当地剧团登上列车。剧团以侧面打开的车厢为舞台,向站台上的观众演出,所演的戏剧作品是专为这一项目编写和排练的。值得注意的是,改造老建筑并不是获得独特演出空间的唯一手段。许多国家以更为灵活生动的方式,临时性地利用特定场所进行社会性表演。墨西哥的“眼睛剧院”(TeatroOjo)以《在一个失败的国家中》(WithinaFailingState)为题,通过“拆除”这一行为,对野蛮的“现代化”和“城市化”,以及虚假的繁荣进行了批判,隐含了“失败的发展政策就是‘在废墟上建造废墟’”这一主题。巴西的“眩晕剧院”(TeatrodaVertigen)的《BR-3》的演出中,观众们泛舟于圣保罗的铁特河,沿途的河堤被创造性地利用为表演空间。在长达5公里的行进路线中,观众们同时看到了河岸上光鲜亮丽的都市景象和船下肮脏不堪的铁特河水,听到的是讲话声、枪声与沿河高速路上的噪声相混杂的声音,闻到的则是河里泛出的刺鼻气味。此作品揭示了快速城市化与环境污染之间的辩证关系,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景象,营造了一个反思空间。观众们所乘坐的驳船更成为了一种可悲的象征:人们被迫陷入“现代化”进程中,无处逃避,只能随波逐流。[4]“眩晕剧院”一向善于利用非常规空间批判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中心都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创作者们认为,公共建筑、自然景观或具有历史意义的场地可以成为有冲击力的表演空间,甚至比为演出特意设计的那些布景更具表现力。戏剧研究者、纽约城市大学教授马尔文·卡尔森(MarvinCarlson)论及剧场与城市的关系时说:“剧场作为一种稳定性因素,并不意味着它在城市中的角色一成不变,相反,它能使自身不断适应城市功能的多样性。”[5]这种以逢“场”作“戏”为特点的特殊地点演出(site-specific)正方兴未艾。在最近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一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重要的潮流。与把历史建筑改造成新的剧场不同,“特殊地点演出”几乎是一次性地利用一个特殊地点作为戏剧演出场所。这也就是把原本的非戏剧演出场所,不加改造地用于戏剧演出。这种特殊场地演出,与我们国家这些年兴起的所谓的“实景演出”相比,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很大不同。且不论内容的新颖独特和对当下社会的关注程度,我们的实景演出大多在原有的自然环境中制作和添加大量的布景,而特殊场地演出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于重视和利用这个场地原有的景物,挖掘其原汁原味的价值。从最纯粹的意义上说,任何一个地点,任何一个场所,如果跟某一个特定演出的内容相符,就有可能作为其演出场地,就可以临时产生剧场的属性。将实景作为特殊场地用于戏剧演出,也是一种借景或虚拟。在此情况下,重要的不是景的表面形式及其既有的属性,而是其背后的戏剧原则和艺术家对它的态度。正是这种对特定演出条件的利用,使得原有的景物产生了神奇的转换。如波兰艺术家所说,我们对剧场建筑的理解受到城市空间戏剧化的影响。我们不把剧场当一种建筑看待,而是作为一种空间看待——人们在其中共存,并建立彼此的联系。带有文化印记或信息的场所,其美学价值正日益受到重视。2014年4月,我参加了“2015布拉格国际舞美展策展会议”,会议场所就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布拉格的克罗莱多·曼斯菲尔德宫。这个陈旧的王宫几乎不加修复,走廊里面斑驳的石头地面和房间中褪色的墙饰尽显岁月之沧桑。但是,在这样的椭圆形大厅里面开会,会感到宗教题材的天顶画(包括屋里的巴洛克的装饰)是与会议相呼应的,能传达出某种信息,或形成某种符号。有了这种信息以后,人们会感到,在这样的环境里开会议,场地本身也变得有了新的意义。而“2015布拉格国际舞台美术展”整体上的“共享空间”主题和展览场地的设置概念,恰恰跟特殊场地有关。“2015布拉格四年展”中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展览场馆,它们完全不像我们熟悉的上海展览馆或者某个大的展览中心那样具备超大的空间,相反,它们是布拉格老城中心的一批不同建筑风格的老房子,包括废弃的教堂、修道院地下室、名人故居、画廊等等。把这些大小不等、面积有限甚至狭小的老房子,作为国际舞台美术展览场地加以利用,这样的策展理念所看重的,显然是其中所含有的文化价值。
三、舞台的去物质化
如今,新媒体技术越来越多地进入戏剧领域,虚拟技术涌到了活生生的戏剧艺术的面前。如何认识诸如“投影”一类的技术手段的剧场特性,对它持什么态度,“技术的新”是否等于“创造的新”,对这些问题,我们仍缺乏足够的思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戏剧学教授阿诺德·阿隆森(ArnoldAronson)近年来关于“舞台的去物质化”(TheDematerializationoftheStage)的论述,颇为深入独到。所谓“舞台的去物质化”,是指以新媒体手段消解舞台本身的物质存在,但并不否认戏剧演出的现场性本质。在此前提下,要重新面对舞台空间的有限与表现可能的无限,要重新面对表象与本体,感性与理性,以及理性认识与超验、不可知的问题。阿诺德·阿隆森认为,舞台美术作为一种物质实体的存在(无论是二维的还是三维的),总是短暂的,它是一个只能随演出过程本身存在和被解读的符号系统。而戏剧的基本定义,一直在于演员是面对观众而存在的。这种共享的真实在场,也意味着它只存在于此时此地——一个活的演员与观众一样,是在真实时间和同样真实的物理环境中行动的。但是,当新媒体进入戏剧现场时,由于它分裂了时间与空间,因而开始了去物质化的过程。预先录制的图像、电影、视频等媒介,将另一种时间和空间引入了现场。例如,从后台输送的现场视频虽然同步,但却打乱了空间。舞台上演出的现场视频将观众的视线分散到两个方向——现场和媒介,这与人们在使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同时又能接触到周围“真实世界”的环境(也许是通过其他媒介)没什么不同,让人们获得了现场和媒介、在场与缺席、真实存在和转瞬即逝相结合的多重感知和体验。在这类现象中,舞台美术不再受制于剧场建筑,也不再受制于传统的观演关系或演员与舞台美术设计的关系。具体分析起来,首先是由于投影手段造成的效果已经不受上述条件的限制,在这些
演出中,舞台仍然存在,表演被包容于其中,然而形象又变得不可思议起来。观众已经难以确定舞台的界限和物理属性。即便是舞台地板、阶梯,甚至活生生的演员等这些往常不言而喻的真实因素,也不再是测定尺度和进行理解的可靠手段。[6](P.88~89)阿诺德·阿隆森指出,对这种“去物质化”产生影响的主要技术——投影和视频,事实上并非新事物。投影在剧场的使用至少可追溯到18世纪,从理论上说,它甚至可联系到更久远的“柏拉图洞穴原则”。柏拉图把人们形容为锁在山洞里被迫面对墙壁的囚徒: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其活动被身后的火堆映在墙上形成投影,这些被人们误以为是现实。而视频显示器从1980年就开始出现在舞台上了。几年或是几十年来,一直有关于新媒体、数字技术和投影技术将代表未来舞台布景的宣称和预言。但这些预测和宣言常常遭到嘲弄或断然否定,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这些技术往往成了舞台尴尬的介入者,或成为了噱头,或成为了传统舞台美术形式的可怜的替代品,或者,人们使用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媒介的语汇,也不懂得如何将它们与舞台表达相结合。[6]在阿诺德·阿隆森看来,约瑟夫·斯沃博达的开创性作品,特别是1950至1970年代,他创造的新的灯光和投影设备,以及此后越来越先进的用于戏剧的灯光和投影技术戏剧,促进了对投影方式的更深理解,使得动态和静态的投影与现场演出达到更大程度的整合。[6]最近的例子是南非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Kentridge)和加泰罗尼亚的投影和视频设计师弗兰斯·艾留(FrancAleu)的演出实践。前者在电影和投影演出《魔笛》中创造了一种在演员与投影之间的审美对话。在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鼻子》中,投影与舞台现场的交替处理使得观众时而难辨表演者和布景,陷入肯特里奇的超现实的图像世界中,时而随物质布景的显现,将注意力转到演员身上。拉夫拉前卫剧团(LaFuradelsBaus)的作品,也模糊了真实与投影的差异,不断变化的影像投在不同层次的事物的表面上,包括演员身上也被投了影,由此创造了一个动态的世界。表演者和景物似乎是从投影中浮现出的,又消失在飘渺的画面中。阿诺德·阿隆森试图以这些例子从图像的角度具体说明“舞台的去物质化”的特点。演员、观众、现场景物与投影图像的时空关系的衔接、错位或延伸,是另一种舞台去物质化的体现。阿诺德·阿
隆森例举的最近的演出中,包括了由杰伊·沙伊布(JayScheib)根据法斯宾德的电影《世界旦夕之间》(WeltamDraht)改编和导演的《电路世界》(WorldofWires)。在演出过程中,观众面对着两个现实——从舞台上看到的现场表演和视频里呈现的按照不同的方式编排和制作的影像,而且影像呈现的,大多是观众的视线所不能达到的画面。一种现实情况是,摄影师是一个非常主动的(并可能是核心的)角色——尽管表演者在很大程度上看不到摄影师,但他常常是观众的焦点,就像日本能剧中的身着黑衣的辅佐员。而另一种现实是,摄影师不在现场,但他所拍摄的画面是观众注意的焦点。在这个世界中,随着电子信号序列的不断变换,图像在一直变化;而在另一个世界中,舞台具体的真实性和临时性,通过表演过程中一些细节性的物件得到了强化,比如,覆盖舞台地面的废弃的道具和服装、溢出的饮料、纸片、记录了九十分钟时长的表演的摄影机等。[6]这类演出中,摄影图像和现场演出之间的张力被以多种方式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如在罗伯特·勒帕吉(RobertLepage)和机器神剧团(ExMachina)所创作的《众声喧哗》(Lipsynch)中,舞台上似乎随意设置了些木块,但通过摄像机和投影设备,舞台后区屏幕上呈现了一个实体的桌子和钢琴的形象。在威廉·弗希斯(WilliamForsythe)的《金属匣》(Kammer/Kammer)中,部分舞台被一些可移动的墙体装置均匀地分割,演员就藏在它们的后面。观众虽然可以通过舞台上方和两侧设置的摄影机看到墙后面的动作,但他们只能看到被拍摄的那部分空间(只有二层包厢内观众的视线可以越过顶部到达墙后)。“舞台的物质性”在多方面遇到最大挑战的,是英国和德国艺术家组成的戈博·斯奎德(GobSquad)剧团所演出的《戈博·斯奎德的厨房》(GobSquad'sKitchen),这个戏的舞台从技术角度来看并不复杂,一块投影幕覆盖着大部分舞台前区,从观众席上看不到投影幕后面的舞台。不过,观众在进入剧场时会被邀请参观“后台”,他们会看到三件小规模的粗糙的布景,以及三个固定位置的摄像机,他们还可能会遇到演员。但是一旦演出开始,观众便只能通过投影幕观看三个同步的画面——“厨房”布景中的大部分动作和对话出现在投影幕的中间部分。观众难以确定表演是在投影幕后面的哪个空间完成的,也难以确定他们看到的是当下的图像,还是至少有一部分是事先录制的。演员的表演常常通过摄像机的拍摄被放映出来,而不是当场面对观众讲话。这意味着某种直接的和潜在的不安。但是,与观众讲话的大幅图像拉近了观演关系。而当观众不得不接受这样一部“彻底”的影像作品时,四位演员意外地从投影幕后面走出来,开始到观众席中找一些人出来,与他们互换位置。也就是说,这部戏剧既让观众进入影像中,又让影像中的演员从投影幕后面出来,步入到真实世界。对于戈博·斯奎德剧团来说,尽管投影幕后的空间与观众所处的空间仍是同一空间,但是,一旦演员走到幕前并站在大幅的投影形象前,他们就会显得非常小。这时,图像就显得非常重要,而演员本身似乎又显得“毫无意义”了。同时,在大部分剧场中(除了环境戏剧或特殊场域的演出形式),尽管演出的现场性和空间的共享性创造了一种亲密感,但观众还是无法体验舞台上的空间。但在《戈博·斯奎德的厨房》中,观众实际上能够亲自体验舞台空间并能接触到布景,尽管这种体验是有距离感的,也是影像化的。在上述例子中,舞台的概念受到了质疑。视频显示器在舞台上的功能几乎就像科幻小说中穿越时空的虫洞,它展现了舞台之外的另一种真实,站在另一种地理位置上,以现场行动的不同视角,把预先录制的影像,包括经典电影、电视节目以及历史事件的片段呈现给观众。演员可以在现场与他人形成互动,也可以与预先拍摄的影像(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影像)互动,甚至可以同已逝去的人的图像进行互动,形成新的交往关系。结语:交错与外延如阿诺德·阿隆森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电子屏幕包围并且不断与之互动的世界里,其中有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脑和电子阅读器这样的私人屏幕,也有体育场、机场、城市繁华地段的广告牌等大型公共屏幕。这些大大小小的屏幕,打乱了我们与周围真实世界的互动。我们可能在上街时也会在屏幕上与周围世界的人交流,原本稳定的城市景观被运动变形的图像肢解,在其中,时间和空间失去了它们的历史意义……”[6]在此背景下,既有的戏剧形式已不能充分反映当代人对世界的体验和感受,戏剧和舞台美术不可避免地要应对必然的变化。最近十几年以来,国际戏剧或舞台美术领域中出现了各种文字表述,其中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越界(crossboundary)、混杂(hybridization)、互动(interaction)等,是一些频繁出现的关键词。无论是让戏剧这一大行业内部的各专业之间彼此介入和融合,还是以新的文化态度和戏剧观看待原有的生活环境,或者通过舞台新媒介开辟新的时空关系,都是戏剧或舞台美术原有方式、概念和界限的外延,也是与其他相关因素之间界限的交错。这无疑代表着舞台美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和特点。
1.ViktorBeriozkin:“RussianNationalExpositions”“P Q07RussiaCatalogue”,PublishedbyTheatreUnionoft heRussianFederation,RussianCentreofOISTAT,2007.
2.“PragueQuadrennial2011”EditedandPublishedbyA rtsInstitute–TheatreInstitute,Prague,2011
3.“BrazilPQ2011”,PublishedbyRiodeJaneiro,Funar te,2011
4.ArnoldAronson:TheDematerializationoftheStage“TheDisappearingStage:Reflectionsonthe2011Pr agueQuadrennial”,PublishedbyArtsInstitute–TheatreInstitute,Prague,2011.
注释:
1.ViktorBeriozkin:“RussianNationalExpositions”“P Q07RussiaCatalogue”,PublishedbyTheatreUnionoft heRussianFederation,RussianCentreofOISTAT,2007.)
2. 〈JohannesSchutzstage2000-2008〉VerlagFurModern eKunstNurnberg,2008,P129.
3.“PragueQuadrennial2011”EditedandPublishedbyA rtsInstitute–TheatreInstitute,Prague,2011.
4.“BrazilPQ2011”,PublishedbyRiodeJaneiro,Funar te,2011.
5.转引自〈The1stvolumeofthePragueQuadrennial2011 Catalogue〉publishedbyPragueArtsAndTheatreInstitu te,2011, 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