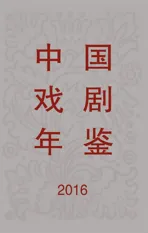移步换形不散神
——谈谈戏曲的扬弃继承与转化创新
2016-11-20罗怀臻
罗怀臻
传统戏曲生存艰难,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即是戏曲自身没有及时完成向现代审美的转化。现在有些人以为传统戏曲就是夸张的脸谱,就是小嗓子演唱的声腔,就是杂耍,完全忽略了戏曲形式之内的生活内容和精神内涵,忽略了戏曲首先是用来与人沟通与人交流的文学艺术形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戏曲曾经在一种共识之下积极发展,那就是“传统戏曲的现代化”与“地方戏曲的都市化”。现代化不是要颠覆传统藐视经典,都市化更不是要阳春白雪脱离大众,而是正视戏曲所面对的生存时代,提倡戏曲自觉实现自身的价值更新与审美转化。
缺失方向感的戏曲艺术
今天,戏曲有必要提出“重返城市”的理念。重返城市是说曾经拥有城市,而后逐渐疏离了城市;疏离了城市说明已经不能与城市审美同步同行,因而不得不淡出城市;淡出城市的结果则意味着戏曲越来越丧失了在城市文明中的竞争力与影响力。中国戏曲最繁荣的时期是在与城市文明相融洽的时期。元杂剧繁荣是因为它占据了当时的京城大都,明清传奇兴盛是因为它依托着江南一带经济富庶的商业都会,京剧兴起是因为四大徽班涌进了京城。黄梅戏从湖北黄梅县流入安徽当时最大的码头城市安庆,而后唱进上海,在上海华东戏曲研究院的京昆和话剧专家的帮助下,从黄梅调转化为了黄梅戏。越剧,原来也不叫越剧,进入上海时,有的称绍兴文戏、四明文戏,有的称绍兴女班、的笃班、小歌班,最后才由上海《申报》统称之为越剧。就连京剧也是在当时“远东第一大都会”的上海被叫出名的。此外,诸如淮剧、扬剧、锡剧、甬剧也都是在上海都市的繁华商演中逐渐成形并被确定了剧种的名称,这些都是戏曲进城的结果。应该说,全国各地方剧种的成长成熟经历也都大致相仿,没有进城之前,它的舞台可能是庙会,可能是广场,可能是草台,但都是简易的;进入城市尤其是进入大城市后,戏曲逐步登上了20世纪的镜框式舞台,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程度很高的剧场艺术,由此迈进了中国戏曲的新时期。
回望历史,我们不能忽视戏曲的每一个繁荣时期,都是以城市为标志的,不仅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古希腊、古罗马的戏剧,莎士比亚的戏剧、印度的梵剧和古歌舞剧都是在当时那个国家的首都或商业大都会完成,然后形成了一个时期的戏剧形态,再向周边中小城市和乡村的市场辐射,同时享受在城里形成的戏剧成果。现在我们一说下乡,就是简单的为农民服务,就是大篷车或简易的土台演出,好像下乡就等同于轻装简从,等同于老戏老演、老演老戏,等同于将就而不是讲究,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中把农村演出当成了广场艺术的演出,把送戏下乡与艺术简陋简单地画上了等号,这是一种将戏曲演出市场与艺术发展方向相对立的简单思维。
进入新世纪的这十几年,由于理论上模糊了方向,因而戏曲艺术的整体发展缺少了方位感与方向感,本体上进步不大,收获有限,因而寄望于戏曲人自身首先是戏曲理论评论工作者跟上步伐,作出判断,给出戏曲发展的理论方略。
扬弃平庸才有希望
在中国戏曲的发展历史中,2015年7月17号发表公布的《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和7月29日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座谈会必将载入中国戏曲史册,且会对中国戏曲艺术今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召开的全国性戏曲工作会议,应该是第一次。在此之前,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关注戏曲艺术的发展,参加提出过“三并举”的方针,这个方针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戏曲发展的进程。而这一次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专门针对中国戏曲艺术传承发展所召开的会议和制定的方针政策。如同中国社会所面对的整体性转型一样,戏曲工作座谈会也是一次带有转折性的、历史性的重要会议。
“扬弃继承,转化创新”这个新的理论用语,回答了几十年来我们反复争论的问题,即对传统的继承是哲学概念的继承,是有扬弃意识的继承,对传统中具有活力的那一部分要传承好、发展好,而传统中与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不相适应甚至格格不入的部分则必须要剔除它、放弃它,不是把传统看作是固态的东西被动地、不加选择地继承下来。对于创新,也不能看作是一枝一叶的创新,有时候是一种形态的转化,犹如唐诗转化为宋词,宋词转化为元曲,一个时代应该催生属于那个时代的戏曲,而不是要求新的时代一成不变地沿袭过去时期业已成型的作品。
进入新世纪的十数年间,文化最受诟病的就是缺少独创性和甘于平庸。作家王蒙先生于2013年在中国剧协全国青年戏曲音乐家研修班的讲座中说:“平庸固然无罪,如果只剩下平庸文化就没有希望了”。作家冯骥才先生在2014年全国两会上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艺没有出现真正优秀的人才。如果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中国文艺的确没有出现卓有建树的、具有引导风气的杰出人才,十数年间我们仍然享用着的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才成果与观念成果,无论是作家还是艺术家,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
联合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翻译过来就是四个字:“保护”和“利用”,保护的目的正是为了利用,是要让历史成为现实生活的一个活的部分。就如我们去意大利,漫步罗马大浴场,在那一片废墟上,可以无拘无束地行走拍照,到了晚上还可以坐在废墟上听一场露天交响音乐会。在这里,历史不是负担,不是阻隔,而是延伸出来的有意味的独特风景。保护非遗不是私人藏宝,生怕被人窥见,要用一道一道门深锁起来。藏书也是,不是为藏而藏,藏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有,而是为着用,为着使之发挥现世的作用。
戏曲界经常引用梅兰芳先生的一句话“移步不换形”,其实梅兰芳先生就是“移步换形”的典型,他的表演艺术已经不是他曾经继承的王瑶卿的表演艺术,梅兰芳先生的表演艺术是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前人的超越。年轻时代的四大名旦都是当时的文化先锋,是当时致力于创新的“另类”。移步是量的积累,不断的积累必然带来质的变化和形态的转变。我们推崇梅兰芳,就是因为他的创新意识,因为他留下的不同于他的前人的新的创造成果,包括他经过“移步换形”之后所留给后人的既源于传统,又别于传统,最终自成一家独具一格的京剧梅派表演艺术。
汉赋到唐诗,唐诗到宋词,宋词到元曲,其间经历了多少移步过渡,抑或经历多少争议探索,我们如今均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却最终看到了各种移步之后的进步成果,看到了新的形式的崭新建立,而新的形式并没有抛弃旧的传统,唐诗之中依然流淌着汉赋的血液,宋词之中依然延续着唐诗的神韵,元曲之中依然传承者宋词的基因……尽管一代有一代的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一代有一代的形式变异,但是一种内在的神韵并没有因之消散,更没有转变基因,而文学艺术的递进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扬弃转化过程中保持着活力,并且证明着各个时代的杰出创造。唐诗的辉煌不能证明宋朝,宋词的成就也不能证明元朝,因此我们不能身在宋代整天高喊振兴唐诗,也不能为了繁荣元代的文学艺术整天研究着如何发展宋词。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评价口吻,说某某作品不够传统,其实这里所称的传统并不是指古典戏曲的元明清时期,甚至不是指上世纪京昆的二三十年代或地方戏的五六十年代之前,有时候我们容易将“传统”限定在某一个过去的时间段内,乃至将这个时间段内形成的经验奉作永恒的规范,不敢越雷池半步。其实任何阶段的经验都只是构成传统的一截而非源流,戏曲艺术自它萌发、塑形、生长到成熟、变异、创新的全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移步,不断换形的循环递进,也是一个不断扬弃继承、转化创新的过程,只是在这个不断重塑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戏曲应该始终谨守住戏曲之所以为戏曲的本体特征与创造特性,守住戏曲艺术的自在精神,正所谓“移步换形不散神”。
更新观念才能创新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戏曲艺术越来越被边缘化?主流媒体倒是一直没有停止过呼吁“振兴戏曲”,送戏下乡、送戏出国是为了“振兴”,转变体制、变换身份是为了“振兴”,评奖泛滥、廉价吹捧也是为了“振兴”,可就是在这一片“振兴”声里,剧种越来越减少,演出越来越边缘,处境越来越艰难,待遇越来越寒碜,到头来人人痛心疾首,人人又都不承担责任。在新的戏曲发展机遇面前,作为戏曲人尤其是戏曲理论工作者,是不是首先应该更新自己的戏曲观念,包括更新戏曲的价值评判观念和审美观念,实事求是地思考一番传统戏曲与当下社会的各种关系。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传统戏曲与当代都市的关系。尽管戏曲的繁盛是在各个朝代的首都或是商业中心城市形成发展和繁荣的,但那个时候的城市是农耕时代的城市,它是以农业文明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为标志的。当我们乘坐在纵横交错的城际高铁上,巡视窗外,无论从东到西、由南向北,沿途已经很难看到记忆中的乡村,映入眼帘的都是城镇化了新农村景象,小楼、别墅、标准化的田园和集体化的住宅,住宅的顶上安着太阳能装置、竖着电视接收天线,即便是绿地也是城市化了的美化了的绿茵。整个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娱乐方式以及审美趣味都在快速的城镇化、城市化、都市化的进程中。以农耕时代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交流方式为依托的戏曲艺术是不是因为我们重视了它,它就一定能够如我们所愿,自然而然地融入现代社会中来,它是不是也同样需要实施由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的时代转型和审美转化?事实上,传统戏曲的生存危机主要是在城市剧场演出的危机,我们在鼓励“送戏下乡”的同时,首先应该鼓励“站稳城市”。
其次是传统戏曲与当代剧场的关系。我们今天所称的传统戏曲主要是在过去的戏园、茶楼、庙台、广场等简陋的民间演出场景中形成的表演艺术形态,而今天传统戏曲的演出场所已经转移到了城市化规范化的现代演艺空间。表面上看,演出场所与表演形态似乎没有关系,其实关系很大,有什么样的演出空间就有什么样的演艺形态,有什么样的演艺形态就有什么样的演出场所。时至今日,中国舞台艺术的主体形式仍然还是戏曲,然而全国各地正在热火朝天建造的大剧院、歌剧院仿佛又都与戏曲演出无关。是让变化的剧场适应不变的戏曲,还是让戏曲在变化中适应不同的剧场,我想戏曲既要在相适应的场所展示自己,也要自觉登上包括大剧院在内的各种新兴的演出场所与传播平台,以适应现代演艺环境的变化。戏曲进入大剧院演出,并不意味着大制作或人海战术,而是要有足够的气场与能量足以支撑起庞大的空间。为此,戏曲的创作必须跟上,简单地把戏曲传统戏放置在大剧院的环境中演出,不但显示不出传统戏曲艺术的精妙,反而会显得单调简陋,与现代剧场演出环境格格不入。二十一世纪大剧院建筑在中国的兴建,是对中华传统戏曲的刁难,也是挑战,更是机遇,它倒逼戏曲在“扬弃继承”基础上的“移步”,加快实施“转化创新”意义中的“换形”,从而创作出与当代社会、当代剧场、当代审美相适应的新的一代戏曲。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层关系,即传统戏曲与当代观众的关系。戏曲一统天下的时候是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的,也很少看到电影,国外的交响乐、芭蕾舞、音乐剧更是少有接触,现在的人们视觉听觉里储存着丰富的非戏曲表演的记忆,戏曲要进入现代人的审美选择,就不能完全无视审美风尚的变化,无视包括影视、网络、自媒体等新兴审美传播介质的存在,尤其是在接受人类社会普遍文明、尊重现代人的价值取向与审美风尚的基础上,自觉地融入时代,保持独特,如此才是戏曲艺术走出低迷、重焕生机的方略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