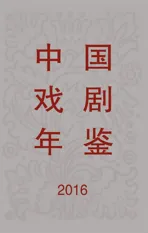麒派三思
2016-11-20刘连群
刘连群
1994年以来,我曾经三次到上海参加纪念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诞辰的学术研讨活动。前两次是纪念梅兰芳、周信芳两位大师的百年和110周年诞辰,又一个10年过去,在周信芳诞辰120周年之际,再次出席研讨会,正如我过去所感受到的,每次都是更深一步地走近大师的演剧思想,获取新的启示和认知。
作为京剧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周信芳演剧思想博大精深,极为丰富和深刻,我把新的感受归纳为三组数字,或许更为集中和易于表达。
一、“600——30——10”
“600”,指的是周信芳生前创演的剧目总数(还有一个说法是590多个)。如此数量浩繁的创演剧目,在京剧史乃至戏剧史上的表演艺术家中间都是罕见的,是大师紧随时代,面向大众,终其一生,致力于京剧艺术继承、创造的心血和才智的结晶。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他就提出演剧要反映“世事潮流,合乎观众的心理”,这原本是他赞许前辈谭鑫培的两句话,随之也成为了他的演剧观的两个重要支点。他处于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基于艺术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与时代紧密结合,在反帝反封建的大潮中,编演了大量配合时事,呼唤觉醒、进步和斗争的戏;当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又不顾自身安危,排演一部部反思历史的沉痛教训、高扬爱国主义思想的新编剧目,鼓舞和激励民族精神。与此同时,在数十年的舞台实践中,适应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的变化,撷选传统老戏进行加工和改编,从思想内容、情节结构和人物塑造上加以提升,注重雅与俗的结合,向大众靠拢,使之在保持戏曲的通俗特性的基础上更具鲜明的传奇色彩,强烈的爱憎情感和道德观念,通过他的刚劲、质朴、真切而炽烈的精湛技艺,与观众声息相通,赢得了社会共鸣。
这些创演剧目,是周信芳演剧思想的直接体现,记录着他在创立麒派艺术历程中的足迹,也是留给后人学习和研究的文化财富。
那么“30”和“10”呢?是指周信芳长期演剧生活逐渐筛选出的保留或代表剧目。据资深的专家估计,这些剧目“再宽一些,可到30个以上,再紧一些不会少于10个。”[见《梅韵麒风》一书第291—292页。]这两个数字,和前面的600或590相比,似乎显得落差太大,是否属于对大师创演剧目的过于苛求或轻易抹煞?实际上,大师本人的估算比上面两个数字还要精减,另有专家文章记述,“周信芳晚年他自称常演的传统剧目为‘七出半’:《萧何月下追韩信》《四进士》《赵五娘》《清风亭》《乌龙院》《群英会带华容道》《打严嵩》,是为七出,《徐策跑城》若不加薛刚发兵,则只有20分钟,故算半出。这‘七出半’,多数是与老生其它流派共有的剧目,当然演法各有不同,而麒派独有的剧目只有《萧何月下追韩信》《赵五娘》《徐策跑城》这两出半。”[见《梅韵麒风》一书第522页。]按这样的算法,加上新编剧目,虽然晚年由于年龄、体力和各种因素的制约,常演剧目并不等同于保留或代表剧目,但还是说明后者约在10到30出之间是有一定根据的。
从创演剧目到保留或代表剧目的大幅缩减,并非个别现象,与周信芳同时代的大师们,早年剧目颇丰,后期同样有“×出戏”之说。其中,既有时代环境变化,艺术家年事和自我从严从高的要求的因素,也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起时伏的“左”的文艺思想的桎梏和影响,使得一些具有很高的艺术保留价值的剧目,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能在舞台上保留下来,这是要用历史的眼光具体分析的,不能简单地视为大多数剧目的贬值。
不过,除去主、客观的有关因素,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剧目由多而繁到少而精,又是符合在数量基础上求质量的艺术规律的,在某种意义上,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就麒派而言,没有数十年600出戏的雄厚积累,也不会有今天30出或10出、7出半的传世经典。这是关于大师创演剧目的一组数字最具现实意义的地方。强调数量,不是主张粗制滥造,而是“高原”需要一砖一土的勤奋堆积,一级一级地精心砌筑通向“高峰”的阶梯。当前,京剧舞台演出的剧目还不够多,题材和样式还不够丰富多彩,剧目创作一度片面强调“原创”,忽视了传统剧目包括大师遗留作品的继续整理加工,而新剧目的舞台呈现又存在着趋同化,制作投入普遍较大,制约着更多的条件不同的院团进行经常性的剧目创作,不利于普及基础上的提高,也难以满足大众和市场的欣赏需求。
而且,剧目建设又和人才培养密切相关,新人的成长离不开对经典的学习和传承,也离不开对新的创作的体验和锻炼,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经验证明,这是新人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当京剧舞台更加多姿多彩,进一步实现题材、类型和样式的多样化,剧目和艺术风格极大地丰富起来,老戏精演,新剧迭出,才能使“高原”广阔,“高峰”竞起,锤炼出更多的真正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久的传世之作和堪当传承重任的栋梁之才。
二、“六说”
戏剧家吴石坚先生,在担任上海京剧院副院长期间,曾经与周信芳“同桌共事”十年,晚年在《戏曲研究漫说》[ 见《吴石坚戏曲论文集》第147—157页。]一文中回忆,“周信芳循规蹈矩,下午二时准时上班,我尽可能不下排练场,陪他吃茶谈心。”他所忆及的谈心内容,以问答的方式,追记了周信芳关于艺术传承和创造的多方面的真知灼见,可以归纳为“六说”:人物说、定型说、创派说、读书说、传留说、“主义”说。
“人物说”,是对“怎样塑造那么多人物形象”的解答。周信芳一贯重视塑造人物,这显然是他乐于谈的话题,“他笑一笑说:‘塑造人物形象,听起来是个新词,挺唬人的,其实我们唱戏人,早就说得不要再说了,扮相扮相,扮上就像嘛!话剧叫造型,京剧叫扮相。”接下来,他从扮得像,历数了“像”的一系列环节:“出了台走得像、做得像、念得像、唱得像、亮得像,都像了,就算像了。定了相观众认定了;若是走了相,观众就会说你错。”又说:“每学会一出戏,就将这出戏中的主人公形象印入心中;学一百出戏,我心中就有一百个主人公的形象。”这番话,强调了塑造人物历来就是演戏的核心任务,从扮戏开始,到上台以后的一动一静、一念一唱都围绕着那个人物,“像”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不能有一点疏离,“都像了”,观众才会承认,而且每戏如此,都把不同的人物“印入心中”。对于实现“像”的途径和方法,他首先谈到了表演的“成规”:“戏的成规,由历代艺人总结形式,吃戏饭的就得守‘成戏’之规,发展‘成戏’之规。墨守成规失之于迂,数典忘祖失之于倚,唱戏的也要懂得。”所谓“成戏”之规,应是指历经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创造、积累而形成的剧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由基本特征而生发的艺术手段,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在塑造人物过程中要守护传统规范,不能把路子走偏,也就是近年来普遍在讲的坚守京剧本体。同时,也不能“墨守成规失之于迂”,要在运用中根据人物的需要“发展‘成戏’之规”,他说:“《打严嵩》是北派戏,邹应龙的形象不是我开创的,但到了我手,就成麒派了……戏是我弄的,当然像我,我和别人不一样,就独树一帜了。”这里讲的就是在守成基础上的创造,守中还要有“我”,我有所创,就能够在舞台上树立别具一格、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体现出了流派的特色。综合上述说法,套用现在理论文章的表述方式,塑造人物关键词是:人物,像,成规,独创,还涉及到人物形象与流派风格的关系,今天读来仍然具有鲜活而深刻的指导意义。
“定型说”“创派说”均与流派有关。京剧史上存在“南欧北梅”的提法,“南欧”指欧阳予倩,“北梅”即梅兰芳,两位大师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相媲并美”。对于后来为什么“欧戏不传,梅戏大传”?曾与欧阳予倩合作多年,又和梅兰芳在富连成同班并于后来多次同台的周信芳,认为“梅欧走两个路子,梅派艺术体系早年形成,定型较早,有较为稳定的梅词、梅腔、梅调、梅步、梅指、梅形、梅韵。定型的东西好学……观众印象深刻,学者遂众,梅戏遂传。欧阳先生聪明绝顶,临场发挥,奇峰迭出,当场红,场场红……他怎么唱都好听,怎么演都好看……但细细品量,他是一场一个样,不定型、不定格、不定品”,“后学者捉不牢,很难学”,“无格不成范,无范则无徒,所以欧派戏不传。”
周信芳的解析,在一般关于流派传留的说法中见解独到,更为深入和具体,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近二百年的京剧舞台,不乏才情天纵的艺术家,生前红遍大江南北,艺术特色为同行和观众所承认,有的已被称“派”,但艺术风格未能传留下来,突出的是近年来倡导传承流派,后人也只是学演了某位艺术家的拿手剧目,舞台的实际呈现则相去甚远,不足以传前人风貌、神髓,其中有些是天赋、功力的局限,也有的与流派在艺术形态和方法上是否“定型”有关。这让我想起一代武生大家厉慧良,早年看他的戏,每场都有变化,上个世纪80年代初,应《剧坛》杂志之约评介他的代表作《艳阳楼》,先后看了七场,也是必有“临场发挥,奇峰迭出”。但到1986年,在参加了纪念天津京剧团(院)成立30周年的庆典演出之后,他对学生说:“咱们的戏,这么些年一直在变、在改,到今天就算是定型了,以后再加工也是小修小动了。”这一“定型”,为时隔二十多年后,中国戏曲学院在天津开办武生流派班,请他的学生出来教戏,几出厉派风格的名剧得以重现舞台埋下了伏笔。厉慧良的舞台生涯起步于江南,在上海曾经深受南派包括周信芳的熏陶影响,晚年的“定型”之举,可谓与前辈大师一脉相通了。
“创派说”,从余派、麒派创建过程的异同谈起。周信芳、余叔岩从小结识,都学谭派,变声后嗓音条件不同,按周的说法,开始“各走各路,他走京路子,我走海路子,他是学谭出‘余’,我是学谭出‘麒’。”余叔岩的出‘余’是“停演专研,他停演在家,躺在烟床上,一面偷学谭戏,一面细嚼慢咽,品字品味,十年磨一剑,嗓音练好了,成套的余派艺术体系出来了,一朝登台,一鸣惊人。”周说:“我不是这样琢磨的。我靠几个朋友帮我琢磨,靠我的剧团成我之志。我靠唱戏,边琢磨边唱,边唱边琢磨。台下台上灵气来了,就有新的东西出来,并将它抓住不放,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样子出。”所谓“样子出”,就是麒派艺术风格的逐渐形成了。同样学谭,因从艺环境和自身条件、选择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走向“独树一帜”的方式,一个“停演专研”,一个“边唱边琢磨”,最终造就了各自风格鲜明、影响深远的两大艺术流派。他们经历的过程,都离不开一个“磨”字,“磨”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条件和实践体验继续深钻细研,执着追求,直至创造“新的东西出来”。周信芳强调“千看千学千演,不如一琢磨”,这个“一琢磨”实际上是“十年磨一剑”,又何止“十年”,而是伴随了大师的终身,他的戏和余叔岩的唱法,不是到晚年还在“磨”么!
“读书说”是由吴石坚称赞周信芳“家藏万卷,学富五车,所以你的戏也多、也好”引起的,爱读书也会读书的周信芳,一上来就介绍了他的读书方法:“闲中读史书,忙中读小说,在小说中找戏……看了小说,再读文章,再看史书,收获更多。”确属演员读书的经验之谈,“三国戏”“水浒戏”“封神戏”等大量剧目主要出自于演义小说,再读相关的文章和史书,有助于对戏和人物的认识、丰富与深化。他同时认为读书是“戏外之功”,“光读书不行,要多学戏,多演戏,戏多了,才是学问。”这就是要处理好戏内与戏外之功的关系,读书当然也是学问,但对于演员是学戏、演戏的“副课”,不能颠倒以至影响主业,这对于当前戏曲教育的课程设置应是有所启示的。
“传留说”谈的是剧目的保留和失传。周信芳的看法集中在两点:一是“文戏是有戏无曲不传。武戏是有武艺无人物不传。靠情节取胜只能眼前景,剧情平淡无奇,但唱段可取,台上唱,台下学,唱入人心,其戏必传。”并以自己为例:“我弄的戏多了,灯光布景、机关布景,就尽心机追求上座率……我演《文素臣》后,人们称之为‘文素臣年’ ……可现在呢?我连一个折子戏也没留下来,怎么唱的,我自己也忘了。”二是“戏是好是坏,戏传与不传,不由你个人做主”,“谁做主,观众做主。”前者属于创作方法,后者指服务对象,都是新剧目创作至今仍然面临的重要课题。
“主义说”最为简短。吴石坚问周信芳:“有人说你是‘现实主义表演艺术家’,你以为如何?”他的回答只有4个字:“我不理解。”再无它言。4个字也列为一“说”,是因为它反映出原本侃侃而谈的有思想的表演艺术家,对于所谓“主义”的一种态度。应该承认,周信芳简单、干脆的回答是带有某种情绪的,他一向反感二、三十年代的某些文人用“洋说法”吓人,在谈心时曾经提到鲁迅先生说的“假洋鬼子们”,“老是在我面前吓唬我,他们欺人太甚。假洋鬼子挂着鲁迅的面具,偷梁换柱,欺世盗名!”谈到这些就“生气了”。但他并非只是意气用事,作为一位紧跟时代、乐于接受新思想的艺术家,也不会对“现实主义”毫无了解,问题在于仅凭演剧注重结合现实、贴近生活和人物,就把从事民族传统的以写意、虚拟为基本艺术特征的戏曲演员,简单地冠名为“现实主义表演艺术家”,又是不准确和不全面的,难免有“‘洋说法’吓人”之嫌,这应是他拒绝的真正原因。“主义”虽好,在“不理解”的情况下,绝不盲目地领受虚名。民族传统艺术领域,多年来不乏引入外来的、新的概念、提法,扩展原有的学术研究和理论表述,在这一过程中,周信芳的严谨务实,坚持独立思考的求真精神,是十分可贵和值得后人尊敬的。
三、三思
最后,是由纪念活动引发的三点思考:
其一,大师的艺术精神、思想和经验,像他在舞台上创造的不朽成就一样,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富矿”,我们远远还没有全面认识和把握,而它的超越时代的强烈而鲜活的现实性,正是今天把回顾和研究继续深入下去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其二,传承是当前面临的紧迫课题。大师是高峰,需要高水平的传承。实现高水平传承,一方面要扎扎实实地学,为传人提供更多的学戏、实践和创造的机会,同时要把修养和见识这一课摆上位置,后者作为“学问”,也是高峰耸立云霄的厚重基石。
其三,我一直觉得,京剧史上有三位创造了奇迹的艺术家:周信芳、程砚秋和侯喜瑞。他们行当不同,却都在嗓音条件不符合剧种传统标准的境遇中,以一种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精神,上下求索,顽强进取,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以勤补短直至化短为长,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创立了前无古人、魅力无穷的新流派。当时,不排除有生存压力的因素,用周信芳的话说“为了活命没办法”。时代不同了,但是,大师们的精神没有过时。传统艺术面临着新的挑战,攀登高峰永远是长期的、艰辛的历程,仍然需要那样一种向高、向上的艺术精神,让前人开创的事业在新的时代保持生命的活力。这,将是对大师们的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