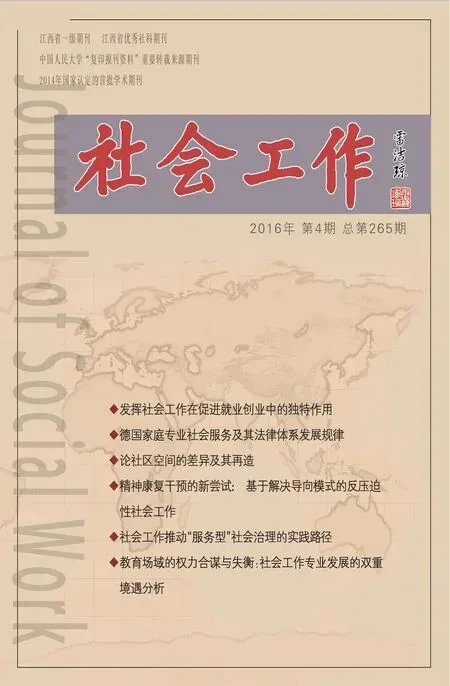精神康复干预的新尝试:基于解决导向模式的反压迫性社会工作
2016-11-14文哲民
文哲民
精神康复干预的新尝试:基于解决导向模式的反压迫性社会工作
文哲民
反压迫性社会工作,在个体层面上,是解决当前精神康复实践困境的一种有益的回答。基于反压迫性理论导向的批判性反思(社会建构及充权视角),此文旨在明晰如下方面:第一,阐明中国精神康复的制度性设计现状与社会工作的内在逻辑以及反压迫性实践原理;第二,理清反压迫性社会工作的复杂性,探讨为何反压迫性实践应被视为专业人员所忽略的重要内容;第三,整合焦点解决模式与反压迫性实践框架,建构新的精神康复干预策略。
精神康复反压迫性实践社会建构充权解决导向
文哲民,深圳市南山区惠民综合服务社,MSW(深圳518000)。
目前,中国精神疾病患者数量在逐年攀升,按照精神病流行病率为17.5%的估计,中国的精神病患者为1.73亿人。而近年来精神疾病患病率的追踪数据显示,患病情况都有明显的增长。深圳综合患病率达13.35%,广州各类精神疾病的终生患病率为15.764%,而北京居民情况则是11.30%(张毅宏,2006;赵振环,2009;陈曦,2010)。在庞大的患病人数面前,精神康复专业人员所面对的挑战一方面是治愈的漫长周期和易复发因素,使得精神疾病成为威胁社会良性运行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社会文化认为精神疾病是源于前世今生所做坏事的报应,以及对精神病病理的偏见,致使康复者遭受来自社区及其他子系统的歧视,邻里互动和社会参与受阻隔(Pearson and Phillips,1994;Yip,2007)。相关的社会污名化和对疾病认识缺乏,亦影响到康复者后续的复原。
鉴于此,社会工作领域的精神康复采用反压迫性实践(Anti-Oppressive Practice)取向,通过改变固化的社会文化对康复者影响,实现社会正义和权利平等。一方面,学者和专业人员注意到,在应对康复者提出的需求方面,传统的心理减压和活动不能达到康复的理想状态。但是,由于缺乏有益的补充,反压迫性实践依旧停留在抽象层面,社会工作在此具体实践中被边缘化。另一方面,精神康复干预不仅采用传统的心理动力治疗方法,也包含后现代疗法(Postmodern Therapy),例如叙述治疗(Narrative Therapy)、优势视角(Strength-based Approach)、短期焦点解决疗法(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通过挖掘精神康复者的能力,重新理解过去和现在,重塑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其目的则在于回归康复者自我,遵循人本理念,提高抗逆力,顺利实现在子系统环境的良性互动。
对此,文章框架围绕几个重要议题展开:第一,当前中国精神康复事业的制度性设计与社会工作运用的内在逻辑及反压迫性实践原理;第二,理清反压迫性实践理论框架的复杂性,旨在理解为什么反压迫性实践是实践者一直所忽略的重要内容;第三,焦点解决模式何以突破反压迫性社会工作在精神康复实践策略的不足。通过对这三点探究,此文有助于探讨焦点解决在其他领域的运用以及为反压迫性实践提供具体化策略。
一、精神康复与反压迫性实践
2012年颁布的《中国精神卫生法》明确提到地方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从事精神障碍诊断和治疗的医疗机构和精神患者康复机构。同样,社会力量的角色也在《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报告中被特别强调,需要配合建立健全的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制度,显著减少患者重大肇事祸案(事)件发生,积极营造理解,接纳关爱精神病患者的社会氛围,提高全社会对精神卫生重要性的认识(中国社会工作,2015)。
这些对社会力量的呼吁折射出精神康复制度落实的严峻现状。首先,中国精神康复工作的挑战是精神卫生法案没有提供对精神疾病与精神健康认识的具体阐释,清晰辨明精神疾病与精神康复的不同概念和范畴。卫生法主要基于机能疾病对于健康状况的受损严重程度以及诊断和治疗难度进行分类。而论及精神疾病,则不得不谈及精神健康。精神卫生法内容不仅须提供精神卫生工作的管理规定,同时也应该提供精神健康工作具体工作和方向指南。精神健康体现的是每一个体意识到其各自的潜能,并能处理生活中的正常压力,有效工作并对他人和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9)。精神健康的理念有别于精神疾病的管理规范,强调不同的思考范式,注重患者和康复者的优势而非疾病本身(Caplan,2010)。其次,在精神卫生制度落实的方面,精神患者遭受到服务机构不恰当的态度,而这些不友好的回馈反映出社会对于病人的行为态度依旧嵌入在中国传统文化习惯里(Shao et al.,2012;Shao et al.,2014)。再次,新型精神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存在严重的不足。这体现在政府在此领域的公共投资滞后及人才培育的匮乏。然而,从目前来看,我国780多万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有90%生活在社区,以及社会转型下的失序诱发的精神病,共同迫切在服务模式上要求以人性化为引导,群体化为目标,多专业协作,以转变目前精神卫生工作被边缘化的困境(黄悦勤,2011)。基于此,尝试运用反压迫性社会工作在精神康复领域有助于突破问题瓶颈。
反压迫性社会工作着眼于实现康复者充权、自我效能与社会融入的能力,打破社会公众对于精神疾病的刻板印象,帮助精神康复者顺利融入环境的子系统解决社会排斥,摆脱嵌入性孤立的关系格局,实现“个人——环境”的协调发展。反压迫性实践强调以社会工作的实践形式,实现社会正义与挑战非社会正义的社会关系(Martin,2003)。而其中,拥有权力的群体(例如专业人员)对于弱势对象(案主与病人)的反压迫实践有重要意义(Martin and Younger,2000)。其中,权力是社会工作领域中社会正义的重要议题。践行反压迫性社会工作主要是聚焦在权力的不平衡,着力于提升变化(changing)①提升变化在反压迫性社会工作领域里,侧重于后现代实践逻辑,强调从传统实践模式的初次改变(First-order Change)向次级改变(Second-order Change)的转向。和处理权力不平等的风险(Dalrumple and Burke,1995)。具体来看,反压迫性社会工作基于社会工作伦理守则,例如服务(service)、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个体尊严和价值(dignity and worth of the person)、人类关系的重要性(importance of human relationships)以及能力(competence)。社会工作伦理(NASW,2008)强调,服务提供需要基于社会正义原则,提高对于压迫及文化伦理的多样性,帮助服务使用者找到需要的信息资源,并同时鼓励积极的决策参与;其次,这种社会正义也应该是体现服务使用者的尊严和价值,在自主决定原则基础上强化改变现状和处理需求的能力和机会;再次,这完整的实践过程要注重人类关系的重要性,对于关系促进改变,使案主成为治疗联盟一员,通过强化关系,提升维持个体健康的能力。因此,在遵循社会工作伦理基础之上,笔者提出个体层面实践的基本原理。其基本原理的动机取向和重要性则在“反压迫性实践的复杂性”部分中详细论述。

表1 精神康复的反压迫性社会工作的实践原理(个体层面)
二、反压迫性实践的复杂性
在上述讨论中,反压迫性精神康复社会工作注重精神康复者的社会关系(“治疗师—案主”关系,案主与家庭等其他系统的关系)所实现的社会正义,强调关系的平等和康复者自主决定的理念。然而在实务中,精神康复工作存在诸多与反压迫性社会工作实践不同的地方。为此,笔者结合反压迫性实践主要理论基础(社会建构主义以及充权),与中国精神康复工作的不足做归纳对比,总结迄今为止所存在的两大困境。
(一)唯实论(realism)与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
阿伯特(Abbott and Alexander,2004)认为,唯实论对社会问题的解读体现在一批明确的团体(专家,律师,政治家等)对具体环境的理解和认识,并认为社会现实是稳定的。而社会建构则是强调社会进程是人们在互动中产生,脱离了互动关系,则解释没有任何意义。就前者而言,明确的团体指富有知识和威望的群体,并对社会公众及专业人员如何认识精神疾病有支配性权威性的意义。唯实论取向的精神疾病病理的理解更多的是体现在传统的精神康复治疗及研究,倾向于探寻案主的问题脉络性,将症结归因于人生历程不同时期的问题经历和病理。
从唯实论角度审视,当前中国精神康复治疗占支配地位的依旧是采用问题聚焦(problem-focused)取向,并根据精神疾病诊断标准(DSM-5)加以辨别,采取药物治疗的办法。传统治疗手段及后续的康复工作倾向于药物维持的疗效为最主要内容。例如一些学者强调,精神分裂症目前无法彻底根除,主要靠药物维持治疗,因此服药依从成了最关键的因素,而抗精神病药物的持续、巩固治疗是防治精神分裂症复发的最重要因素,提高患者对维持治疗的依从性是改善精神分裂症预后的关键(牛亚杰等,2010)。这种占支配性地位的精神康复话语在中国精神卫生工作成为了主流,并使得心理咨询和社会工作的实践范围深深嵌入在这种主流意志的范畴里。另外,标签化行为强化了社会公众对于康复者的偏见,固化精神疾病康复者的“缺陷”和“病态”的刻板印象。因此,这些传统治疗论断与社会区隔阻碍康复者与其他群体的经验分享,使他们对于自我概念的形成和对社会真实(social reality)的认识不能得到有效形塑。
自我概念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并通过社会建构形成。米德强调,在交谈的过程中个体在成为自我的之前是具有他人特征,并在实践中自我的形成通过他人化的角色进行处理(Mead,1926)。米德的自我理论与社会建构主义观点相呼应,将自我的建构归结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Mead,1925;Berger and Luckmann,1967)。他同时也提出“泛化的他人”(generalized other)概念,以深化对自我身份形成的阐释。在米德看来,“泛化的他人”代表社会价值、规则与社会道德,并内化为自我身份。因此,这些社会文化在米德看来有助于个体理解他人会是如何看待自己(Priscilla,2014)。但在精神康复实践中,专业人员忽视康复者自我身份的建立对于后续治疗成效的积极意义。康复者对自我的认识在泛他人化过程中受到源自支配性的社会文化,致使在合作型治疗关系中呈现消极状态。因此,不平等的治疗关系让康复者更多地促成了类似于多米内利所强调的压迫性关系,即通过特殊的属性和社会位置的文化价值,运用权力关系促成身份的形成,并以运用二分法将群体分为优势支配群体与附属群体个体(Dominelli,pp:39)。
而社会建构视角则落脚于康复者之社会互动建构出的集体经验,批判所谓客观科学的精神诊断,鼓励案主自身文化或特定故事脉络下的主观观点。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看来,传统精神康复治疗师倾向于强调治愈对象为案主、病人、受害者、犯人,并将其标签化“反社会”、“边缘人”、“抑郁”、“侵略性”、“精神分裂”,以此判定这些标签可以准确全面的描述病人状况(Lee et al.,2003)。但是,在社会工作价值观里案主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患病者及需要先对其疾病进行分类,而应从功能角度试图聚焦案主潜能优势(Taft,1944)。在社会建构主义认识中,这些源自刻板印象的压迫(oppression)通过人们互动的形式作用于对方进行社会建构(Dominelli,2001)凸显出传统治疗模式的不足与局限。后现代心理治疗学派里,优势视角的观点认为康复者有其优势和成功经历,并可以加以复制到当下问题。因此,后现代疗法遵循社会建构主义的逻辑,拒绝承认现实主义所关注问题的不可变性以及康复的“被决定”假设,通过建立专业互动模式,重新建构对问题新的理解以及帮助康复者认识到问题具有可变性。
(二)丧权(dis-empowerment)与充权(empowerment)
充权指的是增加个人、人际,政治相干的权力,使得个人家庭社区有能力采取行动改善处境,因而侧重于探讨权利剥夺和无权感的过程中,个人能力如何培育(Cheryl and Julian,2010)。实现充权,包含三方面内容(Jacobson and Greenley,2001):自主性(autonomy)、意愿(willingness)及责任(responsibility),即充权在康复者内心建立新的“我”,能自主做出选择,通过与专业人员共同参与计划制定和目标发展,实现自我照料之责任。如何实现充权,其具体操作在第三部分的解决导向实践内容详细论述。但是,在精神康复议题里,对丧权有充分认识有助于理解充权的价值及其如何实践。
自我身份(self-identity)与权力控制(power over)两个维度凸显充权至丧权变换的可能性。在权力控制(power over)维度,压迫性的治疗关系造成的丧权体现在社会排斥与服务质量。目前,中国精神康复工作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局面折射出社会工作实践中所出现的社会排斥。当前精神康复所面对的社会排斥,不单指涉社会学意义上的资源获取和社会流动,更是指权力控制色彩的治疗关系。皮特亚伯拉罕认为,从状态看社会排斥是指缺乏运用权利的能力,而从原因看是由于参与社会整合机制时受到了歧视或者被拒绝(丁开杰,2009)。
压迫性的精神康复以两种社会排斥形式存在:自愿性排斥与非自愿性排斥。自愿性排斥虽然不构成显现的压迫,但是却归因于自我身份的阻隔。权力控制下的不平等治疗关系,造成治疗师与案主互动过程里,阻碍对方形塑有效的自我身份。在许多康复者看来,一方面自我身份的无效体现在不能正视自己在机构中心参与服务的主人翁精神;另一方面则是服务提供的传统模式中价值文化层面的制约,“病理”、“缺陷”等刻板印象在社会建构中有/无意识地内化。康复者在参与商议问题如何解决上,倾向于表现害怕怯懦等消极负面的回馈。因此,对于服务使用者,其真正意义上的参与不仅仅在于增加新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是要减少害怕,减低这些不利的社会排斥边界及改变权力关系对其消极影响(Viola and Paul,2009)。
而非自愿性的社会排斥围绕着权力控制涉及的服务质量议题。目前多数机构所提供的精神康复服务仅围绕康复者需求层次的基础级别。例如,承接康复工作的服务机构聚焦在康复者日常休闲的健康娱乐以及提供稳定的场所让精神康复群体活动。然而,实践的空间无法延伸至康复者社会能动的提升,推动职业规划等社会功能。其中,他们的服务质量折射出服务机构本身的权力控制。在福柯所著的《疯癫与文明》里,他指出精神病院的诞生并不是现代医学史上的一个进步,对精神病人的压迫和控制只不过是改变了方式(厉以宗,2007)。基于这种逻辑,当下精神病医院等一系列禁闭功能的机构并不能有效地发挥人们所期待的作用,虽然吸纳了精神康复者,但只是起到了掩盖的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助精神病患者摆脱问题。因此,禁闭意义的机构在理性、科学知识、权力等各种制度共同作用下会致使“治疗师—康复者”的关系以及建构出来的话语及实践变得更加不平等。
例如,提供精神康复的社会服务机构在康复者危机事件的介入调查,对事件发生经过的责任认定及记录,专业人员对康复者行为的评估,都体现对康复者禁闭场所色彩的控制权。也就是说,无论是事件评估还是心理介入评估,专业人员遵循以理性和机构规范为导向的会谈。因而,这不但不利于与康复者建立治疗联盟,同时丧失激发其优势和建立希望①希望(hope)是后现代治疗法(优势视角和焦点解决)的基本要素。它有别于传统治疗模式所强调的“问题聚焦”视角,侧重于建立合作型治疗关系、发掘案主过往成功的经历也有重要意义。梦的问题对于希望建议有正向意义。其具体论述,请参看本文第三部分“解决导向模式”。的反压迫性实践。
三、解决导向模式下的反压迫性实践
在前部分的论述中,笔者已经详细阐述了反压迫性社会工作的实践原理以及在精神康复领域所遇到的瓶颈。解决导向模式则有助于实现反压迫性社会工作的操作化。解决导向(Solution-oriented)模式有别于传统的短期焦点解决治疗(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不仅体现焦点解决疗法的核心概念,同时亦整合其他后现代疗法的模式:优势视角,叙述治疗(Greene and Lee,2011)。介于此,笔者借鉴解决导向模式,提炼各治疗方法的核心要素,整合个体层面反压迫性实践的原理框架(见表2)。

表2 解决导向模式的反压迫性精神康复实践的技术要素
关系建构层面:精神康复领域的对象在病理层面上存在差异性,但从康复定义层面上存在共性因素:希望、处理问题的技巧、充权及可支持性社会网(Greene,et al.,2011),而实现共性因素有效处理的前提基础则是建立合作型治疗关系。合作型关系建立要求专业人员坚持社会建构的互动成效(interactive outcomes)原则:第一,在会谈初期阶段,贯彻言语表露所体现的平等主义色彩,并遵守社会工作伦理的自主决定价值。第二,合作型治疗关系强调合作的具体化行为,即要求专业人员秉持人本中心理念,给予康复者充分的机会试图去解释其目前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第三,在叙说充分表达的过程中,专业人员需要探知案主的个人优势和品质,以及解决问题的可能资源,并铭记合作型治疗关系所强调康复者对于其自身的所处经历的诠释要优于专业人员对其的评估。例如,我们可以采用以下问题践行合作性关系建立:
1.“今天,你想要去处理所关切问题的哪些方面呢?”(自主决定)
2.“我们能够一起合作去做些什么去达到你的期望呢?”(平等主义的合作)
3.“你觉得咱们之间的合作方式应该怎么样才能让你觉得放松无压迫感?”(非权力控制的尊重)
4.“我很好奇一点,对于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理解认识的呢?”(案主中心原则;假设康复者是问题解决的专家;以及专业人员秉持好奇心,从康复者的语言和视角探究问题,而非规范性的诊断标准和专业知识。)
问题建构与解构层面:在非权力控制的治疗关系中,专业人员需要通过人在情境中的评估模式并结合初次转变技巧,探知康复者是如何在个人文化价值层面上解释问题故事。这种反压迫性实践的尝试,有助于帮助专业人员了解其丧权因素,以及所涉及的评估内容与自我身份塑造的相关性。例如患有焦虑症的康复者特别重视自我身份塑造的互动背景。这类康复者对于他人回馈的反应是十分敏锐,对于来自他人的异议以及对自己行为的负面评估的早期暗示会变得十分警觉(Fraser and Solovey,2007)。这些负面的论断会导致焦虑症在认知、行为及生理层面的症状,其最终会消极促成在自我身份展现的偏见以及加剧焦虑症病况的周期延长(Turk,et al.,2001)。因此,自我身份的形塑对于精神类康复者而言深深嵌入在社会建构中。其次,较为准确捕捉康复者自我身份形塑的缘由还需要了解解决问题的初次改变。初次改变强调康复者运用以往既有的方法和假设处理当下问题。在康复者看来,一直沿用固有的规则方法处理问题是因为相信促成的改变是正当的。因而,当问题再次出现恶化,若康复者若坚持采取相似方法,则会造成“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的局面,即问题本身不仅得到强化,同时也促使相关的其他问题对于原问题的影响。
康复者充权的自主性发挥、意愿和责任意识得益于文化多样性和复原力的培育。在反压迫性社会工作实践中,利用康复者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在于规避精神病理诊断分类的支配性知识框架,重新拾个人独特性的优势视角,防止陷入被支配的压迫关系。在了解康复者是如何将问题框架化的基础上,专业人员可以使用问题外在化技巧帮助康复者把问题陈述方式客体化和拟人化(White,1988)。这种技巧有助于帮助康复者理性看待与问题之间的关系。同时,从不同的位置审视问题,康复者可以摆脱失常的认识,实现问题“去中心化”,创造更多空间发挥由内而外的优势,促进自主性能力。另外,这亦有助于了解问题暂时消失或程度减轻时,何种处理方法是案主可以接受的(de Shazer,1985)。在共同拾回过去故事中成功经历时运用例外问题、可能性问题及评价性问题,专业人员有机会解构医疗模式,将关注点投射在复原力。例如,专业人员可采取如下问题介入:
1.“你觉得自己在目前的环境状况下能否顺利去尝试性地解决当下问题吗?”
“你觉得目前你所处的康复环境让你觉得有种安全感吗?”
“还是说这个康复环境对你来说是不稳定的,存在变化,因而不利于你康复”(旨在了解康复者与所处的康复机构之间是否是和谐一致的关系的。当康复者表示否定态度,专业人员可试图去探究是否与压迫性的环境因素有关。)
2.“你能用一个东西去代表或描述当下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吗?”
“你觉得当下问题的是怎样影响你的能力和想法?”
“你是怎样解释目前的问题变成现在这个情形?”
(这些解构性的问题外在化技巧有利于帮助康复者认识问题是可解释及可改变的,以及有助于通过自我对问题的审视,规避医疗模式所造成的问题内在化,实现探究其可能的优势能力和资源。)
3.“通过你的描述,我肯定你在这段经历中经历许多挫折。但是你也成功度过了这些危
机。那么我很想知道,当精神状态良好或者发病程度轻的时候,你是如何成功处理
好类似的问题呢?”(评价性问题与例外问题共同使用有助于放大康复者的自身
优势并建构更广的问题解决视角)
“在这些不同的精神状态时期中,你在处理相似的问题上是不同的吗?若是不同,你是采取什么不同的方法做的呢?(可能性问题提出旨在保证康复者能够充分思考曾经成功处理问题的成功经历。)
重构故事框架、身份意识和行动:此阶段采用“会谈间任务”(between-session task)贯彻执行个人计划。前期关系建立和问题解构,实现了与康复者共建的合作型治疗联盟,并保证“自主决定”原则与平等主义的权力分享理念,共同去探知康复者为本的对问题的认识和内在优势。在这些相关权力意识的塑造下,康复者可从中摆脱支配性权力(power over)影响,转向达致性权力(power to)及集体性权力(power of)的充权意识形成。精神康复下的支配性权力体现在专业人员诊断的知识,强调治愈工作围绕病理与症状。这种先验性假设和诊断标准将个体自主决定和康复者独特性文化特征置于次要地位。然而,解决导向型的反压迫性实践将压迫性权力类型转变为了达致性权力及促成集体性权力的实现。达致性权力强调康复者可以运用潜在资源实现权力目的和权力转型。集体性权力则是关于个体为实现目标与他人结合起来,构造集体性合作行为。这三种权力之间的成功转变就在于重构对原有故事的新的陈述(restorying),建立目标和希望,践行二次转变。
在此阶段,目标的建立依靠前期案主自主决定和权力转变。目标设置要遵循四个原则(Lee,2003),即实用性、人际关系、新颖以及规律性实践。行动的目标要依循案主发展和个人意义(personally meaningful),在解构问题维持模式基础上共同制定“二次转变”(second-order change)的策略。二次转变的介入超越案主的问题架构(framing)和一次转变,旨在打破问题维持模式,寻找与当下问题对立的尝试。然而,被压迫性的康复者倾向于将问题内在化,而对于“二次转变”的行为并无太大动机和信心。因此,目标制定环节需要坚持系统理论所强调的小的改变促使大改变的发生,以及协助康复者对目前的情况进行和期望的程度进行刻度化(scaling)。正如Berg和de Shzer(1993)所强调,刻度化问题具有目的性,并充分阐释目标内容以及与康复者相关的其他问题。
1.“接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可以给自己的能力打多少分(0-10分)呢?”
“你觉得自己需要怎么做才能往上提高1分呢?”
“当你成功提高1分后,你觉得你会去做些什么而这时候却没有做过的?”(Berg and Miller,1992)
其次,个人计划强调细化目标的诸多小的改变,在践行目标过程中遵循“阶梯化”逻辑。另一方面,个人计划的制定及执行,有利于专业人员与康复者共同审视行动方案和成果。因为,在践行二次转变的过程中,精神疾病的症状依然存在或者制约康复者实现某些转变。这些问题都会致使康复者误认为不存在任何的变化与进步。因此,上述策略与接下来的技巧(梦的问题、希望问题、处理问题)的结合,有助于协助康复者顺利完成个人化计划。
梦的问题(dream question),有助于辅助希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梦的问题比奇迹问题(miracle question)更贴切康复者的意识流,发挥更有效的优势视角。梦是康复者所共同拥有的一种优势资源,并与他们的需求相关,其所蕴含的个体自我生命的意义可以转变为一种积极能量。弗洛伊德认为梦具有极大的记忆力,并有别于清醒状态所围绕的以意念形式为显著特点,而侧重于强调视觉形象。他同时还认为,在精神分析工作过程中,沉思着的人与正在观察自身精神过程中的人具有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在沉思中比在最集中注意力的自我观察中付出的精神活动还大(佛洛伊德,2007)。通过梦的形式所做出的沉思,康复者运用个体的观念和生活联系共同建构对未来的认识,则可促进自我生命的意义积极探寻。
希望(hope)体现在康复者的行为动机和执行力,属于优势视角的重要技术。在个体层面上,希望被视为个体所认为具有价值和积极意义的目标、成效或者状态(Schrank,2008)。同时,希望作为个体在多维层面的建构,是基于认知和受情感促成的一般现实评价以及对美好未来的理解(McCann,2002)。换句换说,希望绝非简单意义上的愿望和目标,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建构出有符合康复者自我生命意义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框架。它所促成的精神状态,作为康复的重要部分,旨在帮助康复者意识到通过问题外在化技巧和二次改变的策略,可以积极去摆脱与问题所构成的压迫性关系。例如,科博克等学者的前后侧研究发现,对于具有情感障碍及行为问题患者而言,希望问题(hope question)作为影响治疗效果的自变量,在第一期及最后一期会谈后具有显著性(Coppock,et al.,2010)。因此,在前期充分的关系建构基础之上,实践者在中期任务中结合希望问题,可以达到更有效的治疗目的。
2.“假设今晚当你正在熟睡的时候,你突然做了一个特殊的梦,在梦中你找到了从未发现解决现在问题的方法和资源。当你明日醒来,你也许不记得梦的内容了。但是,你却注意到自己和以前完全不同。然后你醒来并开始一天的生活。你觉得自己所发现的方法是什么呢?”(在多数情况下,康复者会有一种丧权感,表现出沮丧和憔悴。他们并不有太大的热情对未来有一种展望。因此,奇迹问题有些时候不太适用。专业人员此时需要通过柔和贴切的梦的指引,帮助康复者平缓情绪,进而激发他们的希望。)
3.“那当你发现梦醒后,自己所关切的问题消失,那你最希望某一个看到你改变的人谁呢?你最希望他/她看到你改变的东西是什么?”(梦的问题与希望问题结合起来可以促进个人计划的具体化。另外,梦的问题可以引导康复者把焦点聚焦在处理问题上。康复者在处理问题上的反思是基于个体自我生命意义的希望。)
四、结语
首先,反压迫性实践具有反思性、批判性,并对于实现康复者康复宗旨具有积极意义。其次,此项研究主要关注个体层面的反压迫性社会工作在精神康复领域的可能性,并非涵盖反压迫性实践理论的其他层面的议题,例如社区、制度等系统相关的反压迫社会工作。然而,从目前的国内外研究情况看,反压迫性社会工作在个体层面上的实践缺乏具体的、系统的可操作化框架。基于此,本文运用解决导向型理论框架,与精神康复领域的反压迫性实践相结合,提供在个体精神康复模式的新思维。
这种在个体层面上的反压迫性社会工作,遵循以建构“治疗师——案主”的合作型治疗关系为前提,明晰问题建构并实现对其解构,最终达致重构故事框架及身份意识和行动。因此,针对不同的阶段性目的,解决导向型模式为反压迫性实践提供了必要的实践支持。虽然解决导向型技术要素在反压迫性实践的阶段中有特殊意义,但是对于所涉及的问题技巧,在会谈期间任务的计划执行中,这些均可灵活使用。例如,对于康复者而言,普遍存在的一种共性是对于重度精神疾病患者,无论是问题解构还是践行个人计划,他们会认为康复实践不存在任何的积极改变以及任何正确的行动。因此,例外问题和可能性问题,甚至是梦的问题对于保持案主对关系和实践的希望均有正向功能。
[1]陈曦,2011,《北京市常见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现况调查》,北京大学博士生学位论文。
[2]丁开杰,2009,《社会排斥概念:语义考察和话语转换》,《晋阳学刊》第1期。
[3]佛洛依德、张燕云译,2007,《梦的释义》,新世界出版社。
[4]黄悦勤,2011,《我国精神卫生的现状和挑战》,《中国卫生政策研究》第4期。
[5]厉以宗,2007,福柯:《疯癫与文明》(1965年),收录于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6]牛亚杰、杨少杰、周锦、徐征、罗群、南振国,2010,《出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状况调查及康复工作方案的制定》,《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第4期。
[7]王国强,2015,《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解读》,《中国社会工作》第7期。
[8]张毅宏、胡纪泽、胡赤怡等,2006,《深圳市神经症流行病学调查》,《中国公共卫生》第7期。
[9]赵振环、黄悦勤、李洁等,2009,《广州地区常住人口精神障碍的患病率调查》,《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第9期。[10]Abbott A.,Alexander J.C.,2004,Methods of discovery:heuristic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USA:W.W.Norton& Company.
[11]Benard B.,Truebridge S.,2013,A Shift in Thinking:Influencing Social Workers’Beliefs about Individual and Family Resilience in an Effort to Enhance Well-Being and Success for All,in Saleebey D.(ed.),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6th,USA:Pearson.
[12]Berger P.,Luckmann T.,1967,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UK:Allen Lane.
[13]Berg I.K.,Miller S.D.,1992,Working with the Problem Drinker:A Solution-focused Approach.New York:Norton.
[14]Berg I.K.,de Shazer S.,1993,Making numbers talk:Language in Therapy.In Friedman S.,(Ed.),The Language of Change,New York:Guilford Press.
[15]Caplan M.A.,2010,Social Investment and Mental Health:the Role of Social Enterprise.In Midgley J.,Conley A.(Eds.),Social Work and Social Development:Theories and Skills for 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USA: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Cheryl H.M.,Julia B.,2010,Advocacy and Empowerment in Parent Consultation: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Practice,Journal of Counseling&Development,88,259-268.
[17]Coppock T.E.,Owen J.J.,Zagarskas E.,Schmidt M.,2010,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rapist and client Hope with Therapy Outcomes,Psychotherapy Research,20(06),619-626.
[18]Dalrumple,J.,&Burke,B,1995,Anti-Oppressive Practice:Social Care and the Law.UK:Open University Press.
de Shzer,1985,Keys to Solutions in Brief Therap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Dominelli L.,2001,Anti-Oppressive Social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UK:Palgrave Macmillan.
[20]Fraser J.S.,Solovey A.D.,2007,Second-Order Change in Psychotherapy:The Golden Thread That Unifies Effective Treatments.DC: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1]French M.,1985,The Power of Women.Harmondsworth:Penguin.
[22]Greene G.J.,Lee M.Y.,2011,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Working with Client Strengths:Solution-oriented Social Work Practice.USA: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3]Greene G.J.,Kondrat D.,Lee M.Y.,2011,Working with Persons with a Severe Mental Illness,in Greene G.J.,Lee M.Y.,(ed.,),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Working with Client Strengths:Solution-oriented Social Work Practice.USA: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4]Jacobson N.,Greenley D.,2001,What is Recovery?A Conceptual Model and Explication,Psychiatric Services,52,482-485.
[25]Lee M.Y.,John Sebold,Adriana Uken,2003,Solution-Focused Treatment of Domestic Violence Offenders:Accountability for Change.USA: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6]Martin,G.W.,&Younger,D.2000.Anti-oppressive Practice:A Route to the Empowerment of People with Dementia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Choice.Journal of Psychiatric and Mental Health Nursing,7,59-67.
[27]Martin J.,2003,Mental Health:Rethinking Practices with Women.In J.Allan,B.Peace,&L.Briskman(Eds.),Critical Social Work: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and practices.Crows Nest,NSW,AU:Allen&Unwin.
[28]McCann,T.,2002,Uncovering Hope with Clients Who Have Psychotic Illness,Journal of Holistic Nursing,20(1),81-99.
[29]Mead G.,1925,The Genesis of the Self and Social Control,in F.C.Da Silva(ed.),G.H.Mead:A Reader,Abingdon:Routledge,pp.70-85.
[30]Mead G.,1926,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Perspective,in F.C.Da Silva(ed.),G.H.Mead:A Reader,Abingdon:Routledge,pp.195-203.
[31]NASW Code of Ethics,Website,available at https://socialworkers.org/pubs/code/code.asp(Accessed June 7,2016)
[32]Pearson V.,and Phillips M.,1994,Psychiatric Social Work and Socialism:Problems and Potential in China.Social Work,39,280-287.
[33]Peter D.J.,Miller S.D.,1995,How to Interview for Client Strengths,Social Work,40,729-736.
[34]Pransky J.,Mcmillen D.P.,2013,Exploring the True Nature of Internal Resilience:a View from the Inside-out,in Saleebey D.(ed.),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6th,USA:Pearson.
[35]Priscilla D.W.,2014,Social Work Identity,Power and Selfhood:a Reimagining,in Christine C.,Trish H.L.(ed.),Rethinking Anti-Discriminatory and Anti-Oppressive Theorie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UK:Palgrave Macmillan.
[36]Richmond M.E.,1917,Social Diagnosis,NY:Russell Sage Foundation.
[37]Saleebey D.,2013,The Strengths Approach to Practice Beginnings,in Saleebey D.(ed.),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6th,USA:Pearson.
[38]Shao Y.,Xie,B.,Wu,Z.,2012,Psychiatrists’Attitudes towards the Procedure of Involuntary Admission to Mental Hospitals in China.Int.J.Soc.Psychiatry,58,440-447.
[39]Shao Y.,Jijun Wang.,Bin Xie,2014,The first mental health law of China,As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13:72 -74.
[40]Schrank,B.,Stanghellini,G.&Slade,M.,2008.Hope in Psychiatry: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118:421-433.
[41]Sullivan W.P.,Floyd D.F.,2013,Animating Hope:an Essential Ingredient of Strengths-Based Practice,in Dennis Saleebey(Eds.)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6th,USA:Pearson.
[42]Taft Jessie,1944,Afunctional approach to family case work.Philadelphia,P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43]Thompson,Neil,2009,Practicing social work:meeting the professional challenge.UK:Palgrave MacMillan.
[44]Turk C.L.,Heimberg R.G.,Hope D.A.,2001,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In D.H.Barlow(Ed.),Clinical Handbook of Psychological disorder:AStep-by-step Treatment Manual(pp.114-153).New York:Guilford Press.
[45]Viola N.,Paul W.,2009,Anti-Oppressive Practice in Health and Social Care.UK:Sage.
[46]White M.,1988,The Externalizing of the Problem and the Reauthoring of Lives and Relationships.Dulwich Centre Newsletter,Summer,3-20.
[47]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ebsite,available at http://www.who.int/mental_health/en/(Accessed April 17,2009).
[48]Yip,K.S.,2007,Chapter 9:Futur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Mental Health,Mental Health Service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pp.173-185,New York:Nova Science Publishers.
编辑/杨恪鉴
C916
A
1672-4828(2016)04-0051-11
10.3969/j.issn.1672-4828.2016.0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