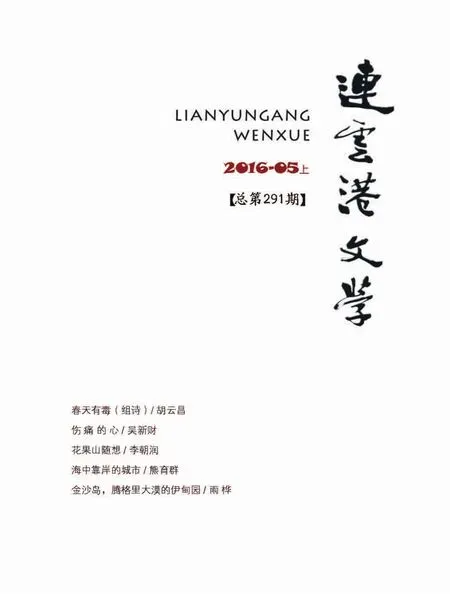剃头
2016-11-14华杉湖北
华杉/湖北
剃头
华杉/湖北
村子里的老年人死了几茬,数来数去,最戳眼珠子的要数九老爷了。
九老爷还活着,无论冬夏,弓着犁弯腰,抬头看人,一脸弥勒佛般的笑。九十年代了,他还穿着传统的中式扁腰裤子。为这扁腰裤,九老爷也丢过丑。那还是八十年代初,九老爷去食品店买猪肉。你拥我挤,推推搡搡。那时他还壮实,手一按人肩膀,竟然从空档里挤了上去。不料你扯他拽,大扁腰裤子不争气地掉了下来。那年月,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为吃哪怕羞。
不过事后左右思量,九老爷也想用一条皮带布绳什么的绕一圈子,然而试过几次,总不如这一扯一掖来得便当。于是乎,九老爷还是九老爷,扁腰裤还是扁腰裤。春日载阳,田野里热气升腾。九老爷脱去黑油油的狗打洞帽,靠墙根下晒太阳,露出一个又圆又亮的光脑袋。孩子们围住他笑,却没有谁敢上前摸一摸。因为,在这个村子里的大宗族里,九老爷是辈分最长年纪最大的人。
九老爷的光头出众,多亏了剃头师傅游千户。剃户头,是老游家的祖业。方圆十里八村的老少爷们,哪一个的脑袋瓜子不是从他游家人手下过的?可是到游千户这一代,生意却不那么顺当,三天两头有小青年宣布,不剃户头了,要进城理发。更有心灵手巧的,竟花钱买了推子长剪,相互理了起来。
小青年的这些做法最使老游伤心。他们从不当面议论老游的手艺,可是背后说长道短总会传到老游耳里。他们认为,剃光头,老游是光着身子睡觉——没盖的,可要是剃一边倒两边分运动头一类的青年式发型,老游就是累花了眼,累弯了筋,剃出的头还是像水瓢扣在脑壳上。老游岂有不想跟潮流暗暗提高改进之理,可是弯腰的老树,哪有拉直的回天力,心时而怨恨,嘴上却说不出道道来。
青年人纷纷叛离,九老爷却立场坚定。他搬出那个重得吓人的枣木独凳,往大门外的阳光下一摆,吹吹灰,落座,脖子上立刻挂上游千户那灰不溜秋黏糊糊的围布。那嚓嚓的剃刀声,九老爷听也听不够。随着游千户手指的拨弄,他的头不时转动,脸上的神情更加得意。等到游千户拿出绝招,掏耳朵,九老爷的享受也进入高潮。他歪着头,眯缝着眼,满脸的皱纹都尽量往那抬高的眼角旁边凑,来尽情体验这轻微的刺痒和巨大的幸福相互杂糅的混合感觉。每逢这样的时刻,游千户总是高挽袖口,将那把古旧的剃刀熟练地扬起,在那块明晃晃的荡刀布上来回摩擦十几下,严肃认真老练快当。别人的光头仅光一遍,九老爷的头至少要光两遍,所以与人相比,九老爷的头光净亮。久而久之,游千户对九老爷无限敬重,九老爷对游千户无限信赖。
每次剃完头,九老爷便下保证,老游,咱们是世交。往后随便哪个毛蛋孩子把头往城里送,我家蔫茄子是认准了你这把刀。说完,便向院内喊,看你那蔫样,你游叔公等你呢!快来剃头,我去烧水。只要蔫茄子笑吟吟地迈出门槛,九老爷和游千户就不约而同地得意起来。
蔫茄子是九老爷的细儿子。九老爷的大儿子在县城里工作,自然从城里的女人堆里找了一个,安了家,算是城里人。不到万不得已,九老爷是不进城的。他偏爱细儿子。细儿子小时候蜷蜷巴巴的,像晒干了的茄子。凡事退后三步,让人三分。要是蚊子叮来了,急性人听见声音便开始轰打,他却不动声色。听到嗡嗡声,看到蚊子落在自己手臂上,稍等片刻,有感觉了,他这才伸出巴掌,啪一下,溅出一星半点血来。村子上有人喊他老蔫。久而久之,来个巧妙的合并,于是喊开了蔫茄子来。
九老爷逢人便夸蔫茄子,说他诚实厚道孝顺听话,最像自己的骨血。蔫茄子没读完小学,自认是麻袋片做裙子,不是那块料。他没读过二十四孝,压根儿不知道郭巨埋儿王强卧冰的故事。前几年,九老爷得了一场大病,想喝一碗鱼汤,当时吃药的钱都拿不出,哪还有钱吃鱼?蔫茄子不吭不响,下到村前那冰冷的水库里,摸了满满一碗小鱼。九老爷和着泪喝完鱼汤,下决心将自己这把老骨头都托付给细儿子。
蔫茄子娶了个像样的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一家人有老有少和睦相处。可谁能料到,不久前为剃头的事,父子俩竟大闹一场。
据说老实人发怒更难劝,因为老实人的气都是从肝脏深处生发出来的。来劝架的邻居一跨进九老爷的大门,就觉察出一种不同常日的气氛。九老爷刚剃完头,手拄一截乌黑的顶门棍,两片青黑的嘴唇在不停地抖动,昏花的老眼也是泪汪汪的,说话都像是结巴了,好你个蔫茄子,反了,反了,你也想进城剃头。
蔫茄子二十好几的人了,竟笔挺挺地跪在九老爷面前。据推测,风暴初起时,他那屁股上曾挨过一顶门棍,不然跪时两手不会老搓揉屁股。游千户忙着调和,一会去拽顶门棍,一会去拉蔫茄子,可是拄着的仍然拄着,跪着的仍然跪着。看见有人涌进来,游千户像遇难人碰到了菩萨,赔着笑说,都是我游千户的错。我这剃头担也该砸了,我这老骨头也该收了。说着竟放悲声,大有用剃刀自刎的趋势。众人忙来相劝,游千户才慢慢道出事情的缘由。
其实事情再简单不过了。那天,九老爷还像往日一样悠然自得地剃完光头,照例去喊蔫茄子。左喊不来,右喊不到,九老爷为细儿子烧的两瓢洗头水已经开了,游千户双手抱膀,坐在枣木凳上迎着太阳打哈欠。九老爷默默起身,走进堂屋,正见儿子与媳妇叽叽咕咕。要是仅这点小事和这个场面,就算是拿蒲扇也扇不出九老爷的火来。
九老爷向媳妇头上望去,不望则已,一望就气。媳妇进了一趟城,头上就落个雀窝,哪个缺德的把她那头发一根根弯来绕去,摆弄出一些花样来。这工夫钱怕也要贴上好几斤谷。不止头变,脚下也变,添了双皮鞋,后跟儿还高出一截,媳妇穿着噔噔噔地走出走进,胸脯挺着,那样子好神气!蔫茄子一双眼滴溜溜跟着媳妇转,涎水都流了出来。
九老爷先是背地里交代儿子要防止媳妇变,后来又在全家吃饭时讲过一个乡干部看见自己女儿穿高跟皮鞋,要拿刀去砍的故事。灵巧的媳妇听后,当晚脱下高跟鞋。蔫茄子夜晚上得床来,脸贴着媳妇的脸,翻来翻去,左看左俊,右看右美。他知道媳妇还是自己的媳妇。早上起床,媳妇对着小圆镜,把个头三抓两挠就搞得服帖入眼,再不像当初绕麻花似地辫辫子。蔫茄子看在眼里,品出滋味,一摸自己还是光头一个,往镜子前一站,比媳妇逊色不少,恨不得头上也生出个雀窝,心中渐渐对老父生出怨恨。
打从记事以来,蔫茄子的头就交给了游千户,除了光头还是光头,记忆中绝没有第二个式样。放学后,九老爷一再提醒,种田的人家,没有比光头再好的了,下田藏不住汗,扬场不沾灰。就这样,一年二十四刀,刀刀是光头。那次去对象,刚巧剃过头,蔫茄子对着镜子看这青溜溜的圆东西,横竖不顺眼,怕对不上相,大热天自己去集上买顶帽子套在头上。今儿一见媳妇的波浪式,更加心痒,便把心事说给媳妇听。媳妇向院内努努嘴,九老爷恰从眼前走过。蔫茄子手抚光头,说出两句有气慨的话来,我的头我当家。我头长在我头上。媳妇听后顺手摸了一下他那光头,会心一笑,蔫茄子在房间里表的决心也就暂时没有张扬开去。
几天来,父子俩心里早就憋着气,这问题决不单是头上文章。
俗话说,日子好过,户门难搪。蔫茄子在这个家庭中渐渐当家,正是符合传统的农村习惯,儿大自立,父老让位。再加上媳妇进门,那经济大权,对九老爷来说,便更无时机执掌了。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乡下逐步富裕起来了,死不尽的老人,娶不完的媳妇,如一树春花,这朵谢那朵开。而婚丧嫁娶,老百姓都要吹喇叭放鞭炮,热热闹闹。每到这时,九老爷总是成为最忙碌的人。他在村里倚老卖老,作联络,送礼费。方圆十里八村,几乎无人不晓九老爷这脾性。每次赴宴前,他伸手向儿子要钱,总不免一场口角。宴罢归来,九老爷兴致勃勃,谈菜论酒,儿子在一旁就放冷腔,有钱自家不会吃喝。九老爷几次想发作,一想自己酒足饭饱,还能说甚,也只好忍气吞声。
就在媳妇从城里烫头回来的第二天,九老爷告诉细儿子,隔壁张家塆你姨表姑昨晚老了。蔫茄子知道他又要干什么了,哼哧好一会,掏出十块面值的三张票子,交给九老爷。九老爷把三十块钱移到左手,右手又伸过去。蔫茄子无奈,又摸出一张十块。九老爷接过翻一下眼,蔫茄子心疼地拿出最后一张十块钱。九老爷抖抖五张票子,咳一声,开了腔,五十块钱,如今还抵屁的用。不料儿子竟顶了起来,谁有钱谁给,谁认识这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
你个蔫茄子,你说什么?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我这是在替你们铺路,将来我死了……九老爷火气渐渐上升了。
蔫茄子接的却不是蔫话,该嫁的嫁,该死的死,尽搞铺张浪费,将来你死了,我节俭办……
你节俭办什么?蔫茄子还未吐出下文,九老爷已明白大半了,他大吼一声,你敢从你老子头上节俭?战火眼看要蔓延下去,门外去奔丧的人来喊九老爷,这才制止住了。
出了门来,九老爷掏出自己那个常年不见水的深色手帕,城里大儿子逢时过节给的几个烟酒钱都裹在那里面。一看一数,刚巧还剩五十块,凑上蔫茄子给的五十块,足了一百块。在九老爷看来,这才能拿得出手,不损老面子。九老爷常常这样,几百块的零用钱,不出一个月,就能贴干用尽。
九老爷坐在上席上,往日扑鼻香的稻花香酒,今儿个左品右尝,苦味腌心。看到眼前哭声动地喇叭齐鸣的场面,想想自己辛辛苦苦的一生,死后不能排排场场请人,不能鸣炮奏乐,可能被蔫茄子无声无息草草掩埋,他酒过三巡就晕晕乎乎地转回家来。真是树老败,牛老宰,人老该活埋。日子一天比一天富,他却觉得在家中一天比一天别扭。他想瞅个空再给细儿子谈一番为人立身治家处世的道理,不然,他死时也咽不下这口气。
可巧,蔫茄子在给小麦上肥。
九老爷的责任田是自己动手拈阄拈来的,一块全村谁也不愿意要的地。地的土质薄且不说,被两条路一夹,成为一个斜三角,一条路通县城,一条路通集镇。地高路低,阴天下雨,人们从地里走,那损失,一时也就难以计算了。眼前这块地,九老爷觉得正是谈话的好借口。
九老爷所在的生产小组实际上就是同姓的大家族。亲近的还没有出过五服,可是土地第二轮承包分田地的那当口,也到了寸土必争动辄面红耳赤的地步。
作为宗族中的年长者,九老爷自觉得威严在身,有举足轻重之势。他先是在家里向儿子媳妇讲一通这个家族诚实待人和睦相处不计得失世代相传的优良传统,接着又挨门逐户将这传统兜售一遍。晚辈们九爷爷长九爹爹短地齐声乱叫,他脸上挂着满足自信的笑。
终于,划田分产的一天到了。这样的会让蔫茄子参加,九老爷照例是不放心的。为了公平,还是做了阄。大家听了九老爷的传统宣传,不争不吵,一个个脸上涂了大红油彩似地红光泛亮。那个刚过门不久就被誉为炮筒子的侄孙媳妇,端过一个破葫芦瓢,里面横七竖八地放着搓好的纸条儿。她恭恭敬敬地喊一声,大家都说九老爷年高,那就让九老爷先拈一个。
九老爷顿时感到说不出的荣耀。在小字辈的一再劝说下,九老爷伸出两个粗裂的手指,战战兢兢地拈了一个,打开一看,正是这块斜三角地。他的心不由咯噔一颤。真是巧了,这块斜三角地第一轮承包时就分给他了,在他手里摆弄过二十几年,他还真说不出它有多少优点,真是苦命一辈子。九老爷的侄儿侄女们停止了拈阄,纷纷议论开来。
嗐,怎么恁巧,一块最孬的地让老长辈给拈去了。有人惋惜。
不算,重拈!有人半和稀泥半讨好地说。
这是老天爷长眼,怕你们这些年轻人种不好那地。有人奉承中夹杂揶揄。
九老爷顺水推舟地接过话茬,乖乖,还是这孩子说得对,那薄地只认我九老爷一个人。他一时也不知是啥滋味,又担心儿子媳妇会闹,就急匆匆回家给儿子报信去了。
这都是过去了的事,回忆中虽然苦涩多于甜美,但在九老爷看来,能用十分耕耘和汗水换来一分尊严和荣誉,那也是值得的。
你看,茄子,九老爷开始启发闷坐在地头抽烟的细儿子,就拿这块地来说,当初我要不领下来,还不知要闹到猴年马月呢。
蔫茄子没有搭话,站起身去撒化肥。一个来回趟了,九老爷还在絮叨,庄户人,勤劳为本。地孬,多累点,少收点。吃亏人常在,总比大集体的时候强。
蔫茄子真蔫,似听不听的,又撒开了。第二个来回了,九老爷站起身,说话也带上了感情,茄子,我也是黄土埋到脖子上的人了,只巴望你们好。为人要厚道,人情世故怎能不要?我死后,你可千万不能太节俭……蔫茄子咳了一声,九老爷以为他明白,又扯上别的了,你媳妇那头……
媳妇那头怎么啦?蔫茄子闷闷地开了腔。
还是辫子好。
你真是个老糊涂!蔫茄子用力踹了踹脚下的土块,说,往后再按你说的,一天也过不好。你还不知道人家怎么糊弄你的,这地就是炮筒子她们串通好来糊弄你的。
……
九老爷老眼乱挤,一时摸不着头脑。
你拈的那个瓢里的阄全写的是这个三角地,他们拈的是另做的一副阄。
你听谁说的?九老爷万分惊愕,好像那年他第一次见到火车一样。
没有不透风的墙。蔫茄子成竹在胸,又显出宽宏大量。反正多累点少收点呗,省得一个个抓破了脸。
你怎么不早说。九老爷像公安人员听到大案迟报一样气急。
早说迟说,反正你都是不信。蔫茄子说完又低头撒化肥去了。
不会的,不会有这事。我九老爷还能是一天的九老爷?九老爷一边走一边想,一边点头又摇头。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家中走去,只觉得身子像手中的空化肥袋子一样虚空轻飘。
这些曲曲折折,游千户哪里晓得,他所看到的听到的不过只是那么一星半点。
九老爷走进堂屋,威严地干咳几声,叫道,蔫茄子,快出来剃头。
蔫茄子勇敢地跨了出来,不剃!
你也想进城剃头?九老爷一猜就中似的。
我的头我当家,我头长在我头上!这决心终于清清楚楚地送到了九老爷和游千户的耳朵里。
不知是什么力量,什么情感,九老爷拿起了顶门棍,他要打出这一棍!是要打去自己一世的苦心晚来的哀伤?是要打醒儿子从自己身上所承袭的敦厚与仁义?还是要打碎自己与儿子也许到死都难以填平的鸿沟?这些他似乎都想不到说不清楚。他只觉得尊严——人生最宝贵却被儿子无意伤害的尊严,让他举起棍。
九老爷这个家族的晚辈们几乎都挤进了小院。各种脸谱各种语言各种举动都一齐呈现在九老爷面前。他看见他们拉起了蔫茄子,没有人敢上来夺他的棍。他像一头斗败的公牛,猛然间以凄厉的声音怒叫起来,都给我滚!你们统统不是好东西!
比阵头雨还快,人流涌出了小院。游千户又告别了一个老头,开始转移阵地。外号炮筒子的侄孙媳妇迈出门槛就手指院内,做着鬼脸,这老头疯了,真是该死!
傍晚时分,九老爷手拎小包袱悄悄离家,奔上去县城的大道。他想到大儿子那里去住。夕阳西下,暮鸟归巢。四野黄土时有埋人意,夹道杨柳却无留客之情。九老爷不禁感到阵阵心寒。抬眼朝县城方向望去,大道上,一男一女在等候。走近一看,原来是细儿子蔫茄子和他的媳妇,他俩是抄近路才赶到前面的。蔫茄子不由分说,接过九老爷小包袱。媳妇将公公扶转身,小夫妻俩一边一个搀住他往回走。儿媳妇说话甜甜的,软软地,爸,到大哥那里,你不是更过不惯吗?往后,我不惹您老人家生气,您老人家不能也变变吗?
九老爷机器人似地迈动两腿,一声不响,听着儿媳妇那低声细语的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