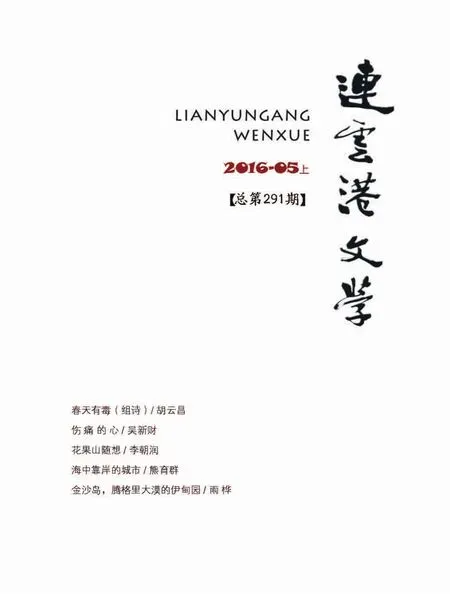表叔
2016-11-14周益龙江苏
周益龙/江苏
表叔
周益龙/江苏
一
许多年来,我怀着负疚的心情穿梭于茫茫人海中,试图寻找记忆中的冷峻面孔。
二
寒潮将逝、万物复苏,应该是1977年的初春,冰雪消融、柳枝泛绿。
我躺在用于拉砖的木板车上,刚出蒸笼般滚烫的身子却捂不热一颗冰冷的心,在四处漏风几近于无的破被褥里,瑟瑟蜷缩成一个典型的乞丐模样,双手紧紧地捂住阵阵发作的腹疼。收工时分,窑工们粗鲁的玩笑声渐渐在吧唧吧唧的足音地消逝,可恁是不见父亲的身影。
我知道,身子瘦弱的父亲,打疲劳战才是他唯一的强项。他想象不到的是,在麻木自己意志的时候也在培养女儿的耐心。可这样的耐心一旦深陷、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不能应验的泥潭,会变成无法复燃的死灰。
“这是谁家的孩子?”不无责怪的语气扯出一张冷峻的面孔,他俯下身子后说,“烧成蒸馍了,还不送医院?父母是怎么做的?”
他,见我陷入如此窘境,却能即兴评论几句,比起那些见了我绕道走的人可强多了。可这样的风毕竟料峭,我宁肯关闭所有的窗户,只为免遭更不堪的伤害。意外的是他再次出现时,便不由分说地拉起板车飞奔起来,到医院的时候,他也被蒸熟了。我正想对他说上一句感激的话,医生们已经把枪口一致对准了他,“不是阿姨嘴臭,你以为孩子的肺是铁打的?铁在炉火里搁久了也要化的!”一会儿,诊断结果就出来了,急性阑尾炎,医生催促他签字时,他一脸焦急、四顾茫然,医生看出端倪后对他说,“难道你不是女孩的父亲?”“我是她的表叔!”他在回答医生的问话时还故意挺了挺胸膛。
那年,我毛十岁。
三
谁料,母亲不仅不领表叔的情,还为诊所与医院之间的那点诊疗差价与父亲打起了口水仗,“一个破阑尾炎,犯得着杀鸡用牛刀吗?一个臭代课的,凭什么作我们家的主?让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他在医院出的垫资,我们一分钱都不给。”
父亲嗫嚅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生计,是他们夫妻大战的导火索。母亲的撒手锏是把我送人。自母亲送走姐姐后,脾气愈发暴躁。面对母亲的狂轰滥炸,父亲从来不作任何抵抗,好像唯有隐匿方能负隅苟活。每次硝烟散尽,我都能坐收渔利,父亲塞给我几颗糖块或一小把炒熟的花生,劝我千万千万不要生妈妈的气,说这个家沦落到这个地步,要怪只能怪当爸爸的无能。而母亲呢?她会挤出时间,带我逛街,扯上一段花布,缝制一件鲜亮的小棉袄,还趁机开导我,“别恋窠了,去舅舅家吧,爸爸妈妈给不了你的,舅舅那儿都有。”
有一天,母亲让我晚上跟她睡,钻进被窝,母亲怀抱温暖、体香扑鼻,在母亲暖融融的怀里,我像一只归巢的倦鸟一般,很快恬然入睡,起床时却不见了母亲的踪影,我四处翻找,盛放母亲衣物的木箱是空的,好闻的樟脑味都变得寡淡,连母亲用于梳头的木梳子都长了翅膀。我走出屋子,一阵风刮过,我支棱起耳朵、鼓动鼻翼,徒劳地捕捉母亲留下的丝丝气息。就这样,母亲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母亲离我远去如同她将我带到这个世界上一样,无须征求我的意见。
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摆脱母亲曾经给予我的温柔,我亦因此对母亲产生了恨意,恨母亲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然后又抛弃。恨不起来的时候又替母亲开脱,如果不是家里揭不开锅,如果不是奶奶长年卧床不起,如果父亲不被学校辞退,如果……每一种假设都在奋力泄洪,改变流向,使我莫名地恨奶奶、恨父亲、甚至恨连长成什么样子都想不起来的姐姐。
而令我切齿是多管闲事的表叔。
四
表叔是上海知青,他任课的学校在村口,近得捂紧了耳朵都能听得见铃声。自母亲离家后,父亲也辞去了窑上的工作,侍弄承包田,农闲时节便做些小买卖,赚点零花钱以补贴家用。父亲外出时便把我托付给表叔照顾。
记得父亲第一次携我去找表叔时,腼腆得姑娘似的,低头不语。在这所村办学校,表叔是初中部教师,而我则是个小学生,两股道上跑车,不搭界。好在表叔一眼看出了父亲的心思,说:“李师傅,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是想让我替您照顾几天可可的吧。”父亲听了后,终获特赦一般,头点得鸡啄米似的,“对,就两天。没办法,手头太紧了,这不,您垫的医药费我还欠着呐。”表叔说:“李师傅,这点事还记着,我可早忘了。”
每天三餐,他从学校的食堂里打来寡淡的饭菜,都要在我家的土灶上加工一下,掺一点虾米和肉糜之类,饭菜就变得美味可口。没过几天,多少只手从胃子里争先恐后地伸出来,抢夺适时到来的美食。渐渐地,奶奶两颊蛛网密布的皱褶里也泛起了霞红。晚上,他收拾完碗筷便放下脚盆,调试好水温让我洗澡,他却口叼烟卷去了室外,重新回归他的局外人身份。尽管如此,我依然不肯把衣裤悉数褪去,在这寂寥的夜晚,竟有如临深渊般的恐惧。
对于他的关怀,我常表现出一种漫不经心的样子,甚至破罐子破摔地耍赖,把所有家务活推到他一个人身上。我就这样,在提防他的同时又理直气壮地享受起他的照顾来;即便如此,他依然忙得不亦乐乎,根本不去顾及手里捂着的是块生铁。我记得他在开学典礼上发言时说过的一句话:石头捂久了也会烫手。我暗中与他较劲,就是想教训一下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他检查完我的作业,像父亲那样,以命令的口吻对我说:“你先睡,我还有几本作文要改。”
其实,父亲所说的“两天”,绝不是一个具体的时间概念,而是指一段时间,有时候是个把星期、有时候更长。父母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日子比抹布还要无趣和暗淡,羞以启齿的落寞如影随形。在学校里,我也只能独自玩耍,实在感到无趣时便去看男生捏泥人,班上有个被称为促狭佬的掉鼻涕男生,捏了一大一小的两个泥人,说小的是我,大的是表叔,说完后又打碎了重捏。我似乎明白这个促狭佬的用意,所有的屈辱从心底里泛起,汇成滔天巨浪,瞬间冲溃了理智的河床,表叔赶到时,我仍然死死地揪拽着促狭佬的衣角不放。当表叔问及争端起因时,我有意隐瞒了真相。夜里,他为我缝补被撕破的衣衫,细语叮咛:“你是一个有教养的孩子,远离这些泼皮,要学会隐忍和保护自己。”
一天傍晚,我被四合的暮色压得窒息,思念像荒草一样疯长,当我走上村路时,泪水模糊了眼睛。
在这儿,我经常把辛苦了一天的父亲接回家里,那竟然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从桥头坠落的一刹那,我享受着无比曼妙的飘飞感觉,我甚至渴望自己的生命能定格在这样的空灵状态里。当我落地后才发现,我只是摔倒在并不陡峭的河滩上,河水在我前方二米远的地方泛着幽绿的波光,想到自己倘若坠河、纵然溺死都没人知道,不禁悲从中来,泪水瞬间模糊了眼睛。我仰面躺着,任泪水冲刷面颊,感觉又冷又饿。想到那些同龄的孩子此时正蜷缩在妈妈的怀里酣睡,眼泪如决堤的河水泛滥。后来我隐约听见表叔的呼喊声,心中的柏林墙轰然倒塌,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认定,他就是我的至亲。
可我不能接受他发现我坠落河滩的真相,待他走远后我才爬起来,瘫坐于路边树下,果然在他折回时被发现,他蹲下身子,以不无自责的口吻说:“我真够粗心的,来回两遍了竟然都发现不了。当他听说我扭了脚要伸手扶我时,我却生硬地对他大吼一声:“我自己能走。”他扯了下嘴角,板结的脸有了松动。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
在他眼中,我只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偶尔的任性倒是个不错的催化剂,能激活他天生中的父性,他的付出,意在践行一个父亲的责任。
我记得,即便是在父亲回来以后,我仍然摆脱不了他的“掌控”。在被各大卫视频道视为黄金时间的那个时段里,我被他安排在他的办公室里做功课,几乎所有的晚上,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费在对我功课的辅导上。他辅导我作文的写法,怎样开头、怎样展开故事又怎样结尾。操作时,首先对我的习作作精心的批改,划出错别字,有眉批和总批,然后拿出他原创的范文供我借鉴。每当父亲当着他的面问及我的学习情况时,他总是以鼓励的口吻说:“有进步,有进步。”
五
难头过后,母亲回来了,不久,母亲又把姐姐从舅舅家里接了回来。
原来,父亲只是因爷爷的历史问题受株连、下放农村接受改造。父亲返乡后因不谙农事而家境窘迫,母亲迫于生计,在离舅舅家不远的街头摆小摊,以赚取小钱给奶奶买药。在家境渐渐好起来之后,特别是在父亲恢复工作并当上校长以后,表叔与我们这一家人的关系且行且远。
如果有人问起,表叔是我的什么人?我只能借用某个样板戏里的经典唱词来回答: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这里的奥妙你也能猜出几分——
一家五口,其乐融融。我和姐姐都在父亲任职的完中读书,母亲因读过几年书农转非后被塞进了学校的档案室,奶奶已经能下地走路。苦尽甘来的庆幸令我们全家人振奋不已,表叔这个称谓以及它所指的那个特定的人早已从我们的生活中淡出,谁也没有提起过;在我们这个家的生活史上,他代表着一段曾经的坎坷,有谁愿重蹈覆辙和自寻烦恼呢?说白了他就是我们这个家庭躯体里那截可有可无的盲肠,留之患、去之快。
如何来形容我们这一家人大难过后的幸福生活呢?何尝不可以把它比作一列从穷山恶水中穿越过来的列车,沿途的风景美不胜收,姐姐初中毕业后插入我就读的班级复读一年后,与我同时考取了小中专,这意味着我们一家子人都捧上了铁饭碗。毕业后不久,姐姐调入县委组织部,然后经人介绍与组织部长的公子恋爱、结婚,使我的父母无悬念地晋升为外公外婆;而我呢,当然也不甘示弱,凭借在市党报副刊上登载了两篇散文被该报社录用,成了一名新闻记者,正在与市委书记的秘书热恋。
我的初恋男友,堪称白马王子,可他就像一支不适合我咏唱的曲子,总给我以勒嗓子的不适感。很长时间我找不到症结,因而将此归咎于己。后来因为一件完全可以疏忽的小事,让我彻底看清,我与他不是一路人。
电影院的门口,一位双腿高位截肢的女孩坐在地上乞讨,我从她前面经过时把随身携带的所有钱都给了这位还不到十岁的女孩。回家后,白马王子用复杂的眼神打量着我说:“你是在拯救她还是在拯救你自己?”我恍然大悟,看似愈合得浑然天成的伤口,完全可以被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揭开。我运用表叔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回敬了我的白马王子,“不爱一人,何以爱世界?!”一段在局外人看来似乎牛头不对马嘴的对白,却是对各自阵营的坚守。
说完那句话后我放声大哭,白马王子跪在我面前请求我原谅他的造次,我们疯狂地拥吻,我一遍又一遍地对他说:“我给不了你,真给不了你所想要的那个我。”
六
我与第一任男友的分手,拉开了母女大战的序幕。她把涂了指甲油的右手食指抵到了我的鼻子上:“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了皇帝的女儿?王帅,他哪一点比不上你?”
之后,她便三天两头给我安排相亲会。放眼望去,茫茫人海,千人一面、千人一念,无法分辨拣与不拣的区别。我对母亲说:“反正都是男人,生物学方面又都能凑合,您说谁就是谁好了。”母亲拍着桌子:“我害你啦?你这么对我说话?”我说:“我要找也得找个表叔那样的人。”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母亲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气急败坏地嚷:“一个穷酸不堪的老男人也值得你去糟践自己?你真是鬼迷心窍了。”须臾,她又双手捂脸放声恸哭,好像挨耳光的不是我而是她自己。父亲把我拽进房间后对我说:“爸爸明白你的心思,你是想找一个像表叔那样具有慈悲情怀的男人共度一生。”“这辈子,我还就非表叔不嫁了!”我说出这句话时,看见父亲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然后又徐徐绽放,他拍着我的肩头说:“孩子,不管你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做爸爸都会支持你。”稍作停顿后他又说:“妈妈是因为太爱你了,才这么急躁的。”我想说:妈妈伤害的不仅仅是我,还有社会的正义和良心。话到嘴边却变成了:“爸爸!我想静一下,好吗?”其实,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让我清静,一会儿,姐姐进来了,姐姐的眼睛里闪动着泪花,她抓住我的手说:“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债,都不是问题,都是能够偿还的,唯独感情这笔债,不是你想偿还就能偿还得了的。小时候,我心安理得地接受父母的庇护,享受父母的宠爱,因为我以为长大后可以报答他们;可是,长大后我才发现,我根本就报答不了,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缺。”姐姐望着我,我努力地扯了一下嘴角,以示回应。姐姐像得到鼓励似的,搂紧了我的肩头:“可可,你可能不知道吧,刘老师,也就是表叔,在你们认识之前,他就与爸爸共过事。如果去舅舅家的是你,在当时的情况下,爸爸也肯定会把我交给表叔来照顾的,如果是这样,我也愿意给他家的温暖,可是我们都给不了,因为他快要结婚了。”姐姐走后,奶奶又来了,她颤颤巍巍的样子令我心碎:“我的可爱的乖孙女,这一切,都是奶奶不争气的身子骨造成的。可是我要告诉你,你妈妈是爱你的。你还可能不知道吧,你姐姐玲玲被你舅舅抱走时是签下领养协议的,光景好了以后你妈妈才以死相逼把你姐姐从舅舅家抢回来的,为这事舅舅都不理妈妈了。”
我如雷轰顶,被若干年前的这一真相所击中,沉积多年的对母亲的感恩和爱,仿佛突然被唤醒,我跑进母亲的房间,看到坐在床沿上的母亲双手抱头,哽咽难禁。刹那间,理智的城垣轰然倒塌,我乖乖地举手缴械:“如果婚姻注定要被亲情绑架,我认命。”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妈妈!我知道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我也爱您!”母亲缓缓地抬起头来,说出一句令我肝胆俱裂又无地自容的话:“可可,如果你不理妈妈了,妈妈都不想活了。”说完就抱住我,半晌,她又小心翼翼地询问:“难道你真的爱上了他?”我已经不是小孩了,爱情不以婚姻为唯一载体,它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或终成眷属或梦不能圆,有情人非此即彼,皆因造化弄人。我非常平静地对母亲说:“表叔,他马上就要结婚了。”
七
若干年后的一天,新闻组长给我提供了一条新闻线索:一个爱心大使因为无力偿还贷款被银行起诉。新闻组长说:“你不是已经很长时间没跟家里人聚了吗?据初步调查,爱心大使就出生在你的家乡,羁押地就是当地的看守所。”新闻组长的话还没说完,我已拨通了在省电视台工作的丈夫的电话,打算把家乡的爱心大使从监狱里捞出来后交给丈夫,做一期别开生面的访谈节目。
为了尽快见到爱心大使,我自驾驱车二百五十公里,当天出发,于下午三点便赶到了那里,我向监狱领导陈述来意后,监狱领导便取出了案宗。
当我看到刘一守三个字时,我眼前一片漆黑,脑子里一片空白,差点栽倒,要不是身傍有人及时拽住了我的膀子,我极有可能从椅子上滑落。
虽然我早有预感,但依然出乎我的预料,他的亏空金额竟然高达五十多万,他的两任妻子都先后离他而去,因为他收留了很多孩子。
与他相见的那一刻,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胡子拉沙,头发像乱草,人又瘦又老又黑,他的眼对我忽闪了一下,然后转身消失在门外。我突然冲着大门喊了声:“刘老师!”
为了掩饰失控的情绪,我匆匆离开了看守所,出门后我把车泊在离看守所不远的路边,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预想不到的是,我曾经的那段生活,竟然就是一则无比神奇的广告,在那流浪儿中间产生了那么大的效应,使众多寻求保护的儿童趋之若鹜。
回到家后,父亲、母亲围着我。父亲大概已经猜出我突然回家的原因,说:“爱心大使因拖贷代款遭投诉、省党报名记者即日光临县看守所这件事,我是下班时听说的。他的情况你已经摸清了吧?”“总数五十二万八千六百七十一,其中银行贷款本金为二十万,其余为民间借贷。”父亲接口说:“抛开具体背景,它也就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纠纷案,我们怎么可能知悉?却便因风起涟漪,也是拜你这位省报的名记者所赐。”我瞅了父亲一眼,他什么时候对自己的女儿赔上了小心。欠账还息,自古是王道,尤其是感情债。看到父亲为表叔而内疚,我的心软了,“爸爸,我没有责怪过您,从来没有;您也不容易,吃过很多苦。”父亲叹了一口气,看着我,嘟哝道:“我能帮刘老师做些什么吗?”我说:“我让公明给表叔做一期电视访谈,动员全社会的人来帮他。”父亲又叹了口气,说:“这个小刘啊,过于单纯。”单纯?我对父亲睁大了眼睛,可以算得上怒目向相了,单纯又什么不好?难道让每个人的灵魂都沾上铜臭味,才叫成熟。当初您将我交给他照顾,也是在利用他的单纯吗?我怒不可遏,以致忽略了我所指责的对象是父亲,“别人怎么说,我不管;可您不可以这样说他,我们这个家里的所有成员都不可以这样说。”看着在我的唾沫星子里一点一点地矮下去的父亲,理智僵蛇一样地苏醒,父亲的本意或许是惋惜或许在代言。我正想对父亲说声对不起时,奶奶闻声过来,瞪了父亲一眼后转向我:“乖孙女,谁欺侮你了,把眼睛哭成了烂桃,告诉奶奶,奶奶替你作主,好不好。”奶奶的话像一个火团,把我这块冰坨瞬间烤化了,我哭诉道:“奶奶,表叔被关起来了。”奶奶说:“好人遭罪,坏人得势,还有没有天理了?不是多亏了刘老师,我这把老骨头早烂成了泥。”母亲插话道:“小可,你妈妈就是那种不知好歹的人,把刘一守戏说成‘留一手’,把刘老师对你的爱误解为黄鼠狼给鸡年,我买后悔药找不到店儿。”奶奶接口道:“刘一守,这个名字还真起得好。现在不是有‘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这些新鲜词儿吗?我看刘老师就是个‘留守天使’。”母亲立即给奶奶一个点赞,说奶奶说的话有水平。我说奶奶的觉悟也高。
八
一切似乎尽在意料中。
表叔的事迹以及我与表叔的故事被小人利用,被冠以非虚构文本的名义得以出版,赚了个盆满钵满。为了表叔的清白,我开始了一次艰难而漫长的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