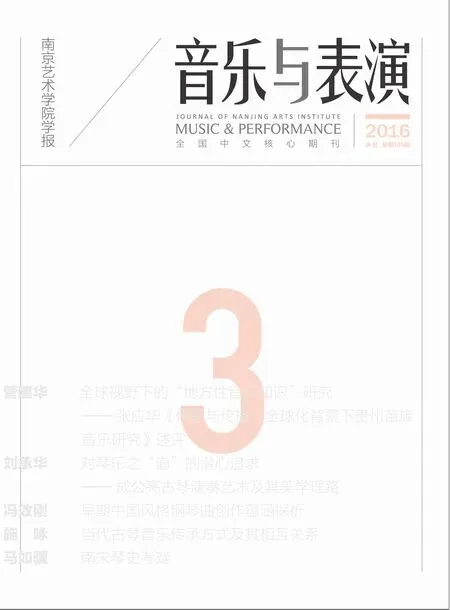罗忠镕《第二弦乐四重奏》的音高组织分析
2016-11-10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牛 林(安徽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罗忠镕《第二弦乐四重奏》的音高组织分析
牛 林(安徽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作为当代中国杰出的音乐创作大家,罗忠镕先生在其《第二弦乐四重奏》中,以一个原始的十二音序列为基础,在保持作品整体音响同质性的同时,对原型序列进行了多种变化处理,使其成为一部音乐表现力极其丰富的十二音作品。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述作品的音高组织逻辑:其一,该作品采用的各种序列再派生的方式;其二,五声性四音组即音级集合[4—23]在作品中的作用。
第二弦乐四重奏;五声性序列[1];音级集合[4—23];截段;严格序列;序列派生体
引 言
作为我国五声性十二音创作领域的开路人和创新者,罗忠镕先生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他通过不断地探索和实践,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五声性十二音作品,在如何将十二音技法与我国传统的五声调式相结合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代表作有:歌曲《涉江采芙蓉》,此曲也是罗忠镕先生创作的第一首五声性十二音作品,之后又陆续创作了《暗香》、《琴韵》以及晚期的《第二弦乐四重奏》、《第三弦乐四重奏》等。
《第二弦乐四重奏》创作于1985年,此曲的独特之处在于作曲家成功地将西方的十二音序列作曲法与中国的传统吹打乐种“十番锣鼓”中的等差数列节奏模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该曲在原型序列的设计方面与早期的作品也有所不同,其音调虽具五声性特征,但又明显地规避完整的五声音阶,即整个序列中没有在任意连续的五个音上形成完整的五声音阶,因此被认为是一部非调性五声十二音作品。
作品自首演以来,国内已先后有多位学者对其进行分析,每篇文章的分析角度略有不同,其中几篇侧重分析作品的十二音序列特点及其用法的论文对笔者撰写此文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如郑英烈先生(1988)从“形态”的角度对作品的序列原型进行了多种可能性的解释,从而指出该部作品的原型序列同时兼有“调性”、“对称”、“五声”、“可组合性”等多种特点,这为笔者更好的理解作品中的序列特点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该文也是国内第一篇研究此部作品的论文,对后人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韩焱(2004)同样对该部作品的序列特点、序列在作品中的使用情况以及作品的结构进行了分析,除此之外还关注了作品中所使用的复调技法、节奏特点等问题;[2]19-24薛谨(2004)的文章虽然不是一篇专门分析《第二弦乐四重奏》的论文,但是在文章中,将该部作品放在作曲家创作的五声性十二音作品的系列作品中进行分析,同时对该作品的序列特点、如何规避完整的五声音阶以及序列在作品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单一序列的结构、组合性重叠序列的结构以及非组合性序列重叠的结构。[3]该文有助于笔者清楚地了解罗忠镕先生运用五声性十二音序列技法进行创作的发展和演变过程。
此外,有些文章虽然不是以作品中的十二音序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如王瑞(2003)以作品中的“时序控制”作为研究对象。该文研究了作品中使用的等差数列节奏逻辑以及节奏、节拍等微观方面的设计,从而对如何控制全曲的紧张度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该文章从多个角度阐释问题的研究方式给予笔者很大的启发。[4]
除上述几篇论文外,郑英列先生编著的《序列作曲教程》(2006)(以下简称为《教程》)中提出了六种序列再派生方式,分别是“原型基础上的重新排列”、“互插式变体”、“拼接式变体”、“轮转式变体”、“循环式变体”以及“动机贯穿式变体”,该书中还提出:“序列的变体当然远不只上述这六种”。[5]165-171《教程》中的这部分内容为本文第一部分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和基础。
综合上述研究文献,总体来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针对序列本身进行分析,包括序列的特点以及在作品中的使用情况等;另一方面则关注作品中使用的等差数列节奏模式以及其他节奏问题。在本文中,笔者将重点分析该作品的音高组织,其中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作品中使用的各种序列再派生技术;第二、五声性四音组即音级集合[4—23]在作品的不同层次所发挥的作用。在整部作品中,作曲家并非自始至终严格地使用序列的四种形式,而是根据音乐发展的需要,对原型序列进行了各种变化处理,这些独特的处理方式仍值得深入研究。笔者将试图通过以上研究来填补对此作品中的音高组织进行侧重分析研究的空白。
一、序列再派生的技术手段
罗忠镕先生的《第二弦乐四重奏》是一部采用五声性十二音进行创作的序列音乐作品,但该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没有严格遵循序列音乐写作原则进行创作,而是在十二音写作思维的控制下,通过使用序列的四种形式以及各种序列再派生的手段生成作品的旋律、和声以及各种对位化的线条,有时对原始序列的改变已经到了相当自由的程度,但总体音响仍在十二音的控制范围内。此时,十二音是保证全曲音响统一性的重要原则。
尽管前人已经对作品的序列原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为了后文阐述上的需要,此处仍有必要对作品的原型序列进行简要地分析。
谱例1.原始序列及其四种形式①注:本文中所用序列均采用原型为P-0的形式。如作品中的原型序列从#F音开始,即文中的P-0.而没有记写成P-6。

如谱例1所示,逆行倒影是序列原型的t5移位,同样,倒影是逆行的t5移位。因此,十二音序列的四种形式实际上只有两种不同的形态,[2]19这一点早在韩琰(2004)以及王瑞(2004)[6]的文章中就已经被提出。基于此种情况,在本文中,除作品中的第Ⅰ和第Ⅷ部分外,对其他各部分的分析仅采用原型和逆行两种形式表示。
谱例2a中,将序列分成三个音级集合相同的五声性四音组。众所周知,五声调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宫—角”之间形成唯一的大三度,并以此作为确定调式的基础。谱例2中的3个四音组均具有很强的五声性特征,但由于缺少大三度,每个四音组可分别属于3个不同的五声调式,如第1个四音组可以属于E宫、A宫、D宫三个五声调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调式模糊的感觉,这也是作曲家在晚期的五声性十二音作品中有意规避出现完整的五声调式的结果。
谱例2.对原型序列进行的各种可能性的划分
谱例2a.

谱例2b.4个三音组或2个互为倒影逆行的六音组

谱例2c.

谱例2c清楚地表明了该序列内包含的又一调式因素,即序列内部包含了两个完整的自然大调音阶或称七声音阶。
谱例2中的a、b、c分别展示了四种划分十二音序列的可能性(2b包括两种)。这一特点为作曲家在创作过程中对于序列进行各种变化的处理供了有利条件,该序列的这些特点也为笔者在后文中将序列分成各种截段提供了可行性的依据。

表1.各部分主要写作特点一览表
如表1所示,该作品中对于序列形式的使用及其应用的各种变化处理方式往往和某一结构位置相对应,从而使各种序列的使用在作品中具有整体的结构布局意义。如表1所示,除第Ⅰ和第Ⅷ两个部分,其他各部分都对序列做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处理。由于每个部分在作品中所处的结构位置不同,写作手法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序列进行再派生的方式也有所相同,大体上可分如下三种形式:“序列局部的音级重组”、“截段式变体”以及“混合式变体”。[5]
(一)序列局部的音级重组
其实,序列局部的音级重组也属于郑英烈先所提到的“原型基础上的重新排列”一类。不同的是,本文所提到的序列局部的音级重组总是以序列内部的某一音组为单位,而不是以整个序列为单位。因此,笔者以“序列局部的音级重组”将其单独提出,这和该作品序列本身的特点有密切联系,又因所处结构位置的不同其重组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谱例3.

在第Ⅵ部分中,序列在使用过程这中,很明显被划分为3个四音组。序列P-7各音出现的顺序是1、2、3、4,5、6、7、8,12、11、10、9(见谱例3中方框中内各音,关于序列中每个音出现的先后顺序可对照附录中的矩阵图)。此时,作曲家把序列分成了3个独立的四音组,在使用过程中,前2个四音组中每个音的先后顺序保持不变,这保证了序列P-7呈示时的清晰性,而第3个四音组中各音则以逆行的形式出现,形成了序列局部的音级重组。
同样是改变某一音组内部的音序,其方式也有所不同。
第Ⅶ部分的主体部分(采用数列节奏模式“蛇脱壳”的部分)采用了序列P-11及其四次减缩变奏,每次序列的完整呈示其总时值呈逐渐递减趋势,从而序列的使用和该部分使用的等差递减数列节奏模式保持一直。如表2所示,序列P-11从最开始的16拍(以四分音符为一拍)经过4次变奏后,减缩至4拍,在这个过程中,第一次(7)和最后两次(1)所用的序列各中每个音的顺序不变,其他几次均以4个三音组为单位,在其内部进行了音级重组。
表2的“序列各音序“一栏中清楚地展示出了序列P-11在几次变奏中其内部各音在顺序上的调整,其中对应节奏序列“5”和“3”的两次序列的变奏是序列各音整体顺序变化较多的,但正如笔者所说,这两次可看成是序列P-11的两次变奏,加之在其前后分别使用了严格的序列P-11,因此,并不会因为局部各音顺序的改变而影响该序列的表达。

表2.
谱例4是另一个序列局部音级重组的例子。
谱例4.

谱例4中的第248—249小节是序列P-2以2个六音组为单位其内部进行重组的例子,其各音出现的顺序在谱例中以数字标出,此例已经是对序列进行比较自由的处理了。
(二)截段式变体①所谓截段式变体是笔者根据此部作品的写作特点而提出的,之所以称为是截段而不是减缩,是因为纵向仍然在12音的控制范围内,此时是选取序列中的一部分作为该序列的代表而出现在织体中的某个层次,主要是在旋律层。
作曲家除了以某个音组为单位将其内部的各个音进行重新排列,还将12音序列划分成各种长度不等的截段,使序列以截段的形式形成某一声部的旋律,而纵向音响仍在12音控制范围内。此时,序列中截段以外的其他音已经融入到其他声部或作为和声层、或作为对位化的线条出现。此种变体被广泛引用于作品的第Ⅱ部分。
表3是第Ⅱ部分的节奏与所用序列的部分对照表(由于受空间的限制,节奏模式“四和二”两个部分未包括在内)。作品的第Ⅱ部分是以“7531”递减的等差数列模式为基础,在每一“节”[7]中以“3”或“1”同基本的节奏数列相加而形成的数列节奏模式。该部分是典型的旋律+伴奏的主调式写法,分别用表中的和声层和旋律层表示,各“节”的旋律分别由两个完整的序列(在“十”的位置)以及不同序列的各种截段构成(如表3中的“八”、“六”两个部分)。采用此种方式一方面和原始的序列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则大大加强了创作上的灵活性。
除表3中所列的各种截段外,在作品的其他部分尚有不同长度的截段的使用。
四音截段:以原型序列中的第一个音至第九个音中的任何一音作为开始音,按照序列音顺序不变的原则,依次可以构成9个四音截段(见谱例6),同理,逆行序列也可构成9个四音截段,其中除了三对互为逆行或者倒影的五声性四音截段(原型及其逆行)外,其他各四音截段因其内部均在不相邻音之间含有半音关系而破坏了五声性音调的风格,因此,没有纳入作曲家的使用范畴,而仅以谱例2a中所列的三个四音组作为主要的四音截段应用,从而保持了全曲五声性音调风格的统一性。(见谱例2a中有关四音组的划分)见谱例5和谱例6。
谱例5中的方框内是序列R-6中的第5—8音,序列中的其他的音已经融入到了和声层。
七音截段:之所以划分出七音截段,同样是由于序列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见谱例2c)
谱例7中的第1小节矩形框内是序列P-11中的第5—11音,此处是完整的D自然大调音阶;而第2小节矩形框所表示的是序列R-4中的第2—8音,形成了完整的G自然大调音阶,此处具有很强的调性感,而且形成了类似四、五度关系的转调,第3小节的D音(用黑色圆圈标注)起到了连接两个调的中介作用。

表3.
谱例5.

谱例6.原型序列中可以划分的9个四音截段

谱例7.

八音截段:可以将八音截段看成是2个四音截段的结合,因此对八音截段的划分方式同其它截段相同,即没有打断各种音组划分的特点。因此,在作品中,仅以两个四音组为基础,使用由序列中的前2个四音组相结合或者后2个四音组相结合而产生的八音截段形式(见谱例8)。
谱例9中的两小节是八音截段的例子,分别是序列P-11中的第1—8音(谱例9第1小节中的方框)以及序列R-3中的第1—8音(谱例9第2小节中的方框)。
(三)混合式变体
上例中(见谱例10)小提琴声部的旋律从表面上看很难和任何一个序列形式相联系,但似乎在听觉上并未产生太多的陌生感。探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在这个旋律片段中,各相邻音之间的音程关系均来自原型序列,包括小三度、大二度和纯四度,其纵向在十二音的整体音响控制下,在某一声部形成了新的旋律;其二,如谱例10所示,所选小提琴声部的旋律正好形成一个完整的B大调音阶,由此也可以说这一部分是由某一原型序列中第2—8音或者是第5—11音两个七音截段中各音的重组而成。因此可以看成是采用 “截段式变体”和“音级重组”两种序列再派生两种方式相结合的结果,因此笔者称之为混合式变体,此例也代表了该部作品中变化使用原型序列的最大自由度。

谱例9.

谱例10.

(四)其他变化处理方式
除上述三种变体外,作品中还对序列进行了其他变化的形式,见谱例11。
谱例11的第一小节中采用的是序列P-5,如谱例中所示,序列中的第四个音并未出现在第3和第5音之间 ,我们可以认为是省略了第四音,也可认为是改变了第4个音出现的位置,而将其与其他音构成四音和弦出现在小节内的第四拍,此外,小方框内的音表示两个音的重复。此种方式与上述三种均不相同,再一次体现了作曲家创作上的灵活性。
综上所述,全曲从一个原始的十二音序列出发,通过将其划分成具有不同特点的各个音组(三个五声性的四音组、两个互为倒影逆行的六音组等,同时内容还包含两个完整的自然大调音阶),并以此为基础,采用各种变化的方式对其进行再创造,整体作品在十二音写作思维的控制下,极大丰富了乐曲的表现力,达到了严格序列音乐写作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罗忠镕先生的这种创作思维与早于勋伯格首创十二音技法的奥地利作曲家豪尔 (Josef Matthias Hauer)的将十二音序列不作为一个整体、平分为若干个音组的十二音音乐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谓是一种传承与创新。
二、音级集合[4—23]的使用情况及其作用
在整部作品中,五声性四音组即音级集合[4—23]在作品各个层次的音高组织方面发挥了最为核心的结构力的作用。首先,作为序列的重要组成作用(见谱例2a);其次,作为重要的旋律动机;再次,作为形成纵向四音和弦的主要形式出现;最后,音级集合[4—23]控制了该曲第Ⅳ部分(有学者认为该部分是整部作品的展开部[1])的序列布局,称为控制音高组织的深层结构力,此处重点论述后两点。
首先,音级集合[4—23]的使用情况。
谱例12是作品中使用的所有四音和弦,其中和弦a在作品中出现次数最多,在第Ⅱ、Ⅳ、Ⅵ、Ⅶ四个部分均有使用。很显然,和弦a、b、c、d四个和弦均属于同一音级集[4—23],后两个和弦虽然稍有不同,但同样是具有五声性音调特征的四音组,仍保持了风格上的统一。
谱例8.
谱例11.

谱例12.


表4.
谱例13.

其次,音级集合[4—23]在宏观上对作品音高组织的深层结构起到了控制作用,具体分析如下:
如表4所示,此部分以两个节奏模式A+B构成一个乐句,前两段全部使用序列原型的各种移位形式,而后两段使用逆行的各种移位的形式,形成了更大规模的对称性。各段在序列的布局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特征。如第I部分中的4个乐句所使用的序列采用连续上四度(或下五度)循环的方式进行安排(谱例13),这似乎与这部分大提琴声部在乐段开始处所强调的五度叠置的四音和弦(谱例12中的和弦a)相吻合,更重要的是这一组序列的开始音和序列中的四音组属于同一音级集合,是一组具有五声性特征的四音组;后面两次反复也同样遵循着这样的原则,即每段中使用的序列,其开始音结合起来是一个具有五声性特征的四音组。
由此可见,作品的五声性不仅仅是体现在原型序列的设计上,音级集合[4—23]还在作品的更深层次起到重要结构力的作用。
如果把序列开始的音级比作传统调性的主音,那么上述序列布局就好比是传统作品中的调性布局。传统作品中的调性布局往往和作品中的主要动机音调或者是核心音程有关,第IV部分作为全曲的中心,其序列的布局明显和序列原型中的四音组有着密切联系,从这个层面上考虑的话,它是和传统奏鸣曲式中的展开部有几分相似。
结 语
综上所述,这部五声性十二音作品中,作曲家从一个原始的五声性序列出发,通过采用各种序列再派生的方式,如以序列中不同的音组为单位对其内部进行音级重组、从完整的序列中划分出各种长度不等的截段即序列截断的多重处理以及二者结合等方式对其进行各种变化的处理,从而使作品在整体上受十二音思维控制的同时,产生了严格的序列音乐写作所无法达到的音乐效果,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音乐表现力。
此外,具有五声性特征的四音组即音级集合[4—23]在作品的各个层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作品的第Ⅳ部分,[4—23]成为了控制该部分序列布局的主要原则,音级集合[4—23]无论在作品的表层以及深层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作品中控制全曲横向与纵向音响最为重要的音高组织结构力。这部具有创造性的作品,为十二音技法与我国传统的五声调式相结合之技法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1]郑英烈.《罗忠镕第二弦乐四重奏》试析[J].音乐艺术,1988(4):55-58.
[2]韩焱.《罗忠镕第二弦乐四重奏》的分析[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4(2):19-24.
[3]薛谨.罗忠镕的五声性十二音及其运用,上篇[J].天籁(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4(4):22-47.
[4]王瑞.罗忠镕《第二弦乐四重奏》的时控逻辑[J].音乐研究,季刊,2003.9(3):66-81.
[5]郑英烈,编著.序列音乐写作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165-171.
[6]王瑞.罗忠镕十二音作品技法研究[D].上海音乐学院学位论文,2004:22-23.
[7]袁静芳.民间锣鼓乐结构探微——对《十番锣鼓》中锣鼓乐的分析研究[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3(2):15-24.
[8]樊祖荫.论《十番锣鼓》中的节奏、音色序列与当代音乐创作的关系[J].音乐研究,1987(4):12-25.
(责任编辑:王晓俊)

附录1.罗忠镕《第二弦乐四重奏》矩阵图
J614.3
A
1008-9667(2016)03-0103-08
2016-01-18
牛 林(1983—),男,安徽芜湖人,硕士,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小提琴演奏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