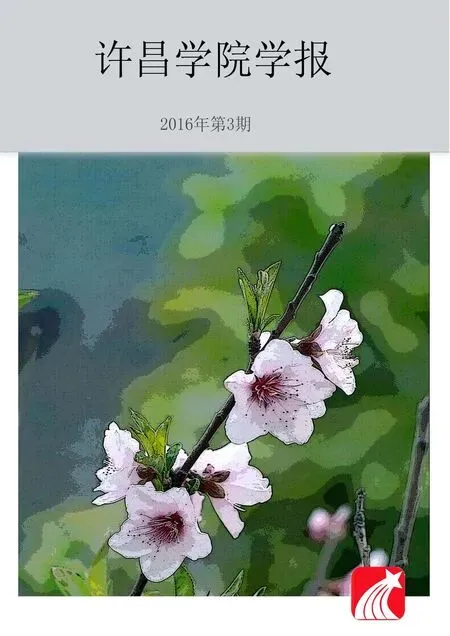庄子“无待”逍遥与主体间性审美内涵
2016-10-28刘思梦
刘 思 梦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庄子“无待”逍遥与主体间性审美内涵
刘 思 梦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在“有待”的世界中,个体受到来自外在条件和内在思想观念的双重束缚,与世界之间是主客对立的关系。“无待”逍遥突破了来自以上两方面的限制,实现了个体的绝对自由,是个体在身体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双重自由。在“无待”的世界中,个体物我两忘,与世界混同为一,没有主客对立,是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的和谐共在,正体现出主体间性走向审美领域的意义。揭示庄子“无待”逍遥与本体论领域的主体间性之间的联系,对于庄子的哲学与美学思想在更广泛的世界领域传播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庄子;有待;无待;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概念随着主体间性理论的发展和演变,在不同的领域中有着不同的含义,已经不再是最初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统一性内涵了。杨春时将主体间性的内涵概括为三个领域:社会学的主体间性、认识论的主体间性和本体论(存在论、解释学)的主体间性。而在以上三个领域中,只有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才能够走向审美,成为美学构建的基础。[1]
一、本体论的主体间性
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源自海德格尔,后期他提出的“诗意地安居”、“天地神人”和谐共在的思想,共同建立了本体论的主体间性。[1]不论是“诗意地安居”的本真存在思想还是“天地神人”四重世界整体存在与相互转化的思想,都旨在言明人与世界之间是一种理解和交往的和谐平等关系,是个体与世界的本真共在。当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之间不再是一种对立与利用关系时,个体便能以本真的存在于世界中进行审美活动,最终实现个体的自由。“只有在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的四重世界里审美才作为最高的境界,作为自由的生存方式,诗意地安居在大地上,进入本真的共在。”[2]44个体主体不将个体的意志强加给世界主体,不侵凌自然,不将个体的地位凌驾于自然之上,个体与世界就能从相互的利用关系中解放,实现双方彼此间的自由。个体主体在与世界主体的交往过程中,不刻意拔高自己,也不有意贬低自己,而是在世界主体面前本真地显现自我,平等地与世界主体进行对话和交往,由此进入二者自由与和谐的本真共在。
庄子所谓的“无待”逍遥旨在追求个体摆脱外在限制与内在思想约束的自由,是个体在身体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双重自由。这种“无待”逍遥的自由境界体现出了个体之于世界是平等、和谐的关系。这种关系正体现了主体间性的审美内涵所在。而《庄子·逍遥游》并无直接提及“无待”二字,而是以列子御风而行的“犹有所待”,相对地提出“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的无待逍遥之境。因此,“无待”逍遥的意义与其所彰显出的主体间性审美内涵只有在与“有待”之境的联系和对比中方可显现。
二、释“有待”
庄子《逍遥游》一文旨在肯定“无待”逍遥的精神自由。这种肯定和赞扬是以否定多个“有待” 的事例予以显现的,因而揭示“无待”之旨必须建立在对“有待”的分析之上。“有待”指有所依凭、有所限制,从而导致精神不能自主,不得自由。庄子阐明有待之境是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个体有所拘束而不得精神自由的,即外在条件的限制和内在心态、观念的束缚。
(一)外在条件限制下的“有待”
首先,大鹏图南和水之负舟的事例说明了外在物质条件对个体的约束和限制。在天地大境之中,大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其翼若垂天之云”,大鹏徙于南冥,势态宏大有力,羽翼击水形成的水波可达“三千里”,之后“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然而此种境界仍然凭借着“六月息者”,大鹏背负青天,上天九万里是“风斯在下”的结果,必定承负着一定的物质条件。水之负舟的事例说明水浅则不能负大舟,体现出水这种外在的物质条件对浮舟的约束和限制。大鹏图南和水之负舟的事例均体现出个体凭借外在物质条件而有所拘束,因而不得逍遥的道理。
其次,蜩与学鸠止于榆枋、行者聚粮的事例体现了空间对个体的限制。蜩与学鸠因其止于榆枋,活动空间狭小,不曾体会大鹏高飞南海的壮阔与乐趣,仅仅看到了大鹏背负青天的劳苦,因而导致其视野与心态上的局限,发出“奚以九万里而南为?”的鄙言。行者根据路程的长短而准备相应的干粮,体现了个体依据空间条件的限制而调整个体行为。以上二者均为空间条件限制下的“有待”之境。
再次,与空间相伴而来是时间对个体的限制。“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是“小年”的有待。朝菌暮死故不知晦朔,夏蝉秋死故不知春秋,时间的局限令其生命短促不得见到更为广阔的世界。与之相比,楚南灵龟以二千岁为一年,上古大椿以三万二千岁为一年,灵龟与大椿的生命与朝菌、蟪蛄相比足够长久了,而如此“大年”仍旧受到时间的限制,终有一死。郭象云:“苟有乎死生,则虽大椿之与蟪蛄,彭祖之于朝菌,均于短折耳。”[3]11在时间长河面前,以三万二千岁为一岁的大椿与朝生暮死的朝菌,其生命同样短促,仍旧受到时间条件的限制而不得永久。
最后,外在条件制约下的“有待”之境还体现为自然规律对个体的限制。列子御风而行,犹有所待,其所依凭的正是“天机之动”*天机之动:成玄英疏云:“御风而行,犹待天机之动焉。郭象云:‘自然御风行,非数数然求之。’误。”在成玄英看来,郭象所认为列子御风而行出于自然,并非汲汲以求的说法是错误的。列子并非自然乘风,而是有所依凭和借待的,凭借的就是“天机之动”,是一种自然规律。详见(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2010年重印),第19页。。列子之所以能免于步行,泠然而善,是因为对风的凭借和利用。而这里的风是有所指的,并非任何风都能够令列子泠然善乎。列子所乘之风必然受到“天机之动”的统御,是符合自然规律之风,或者说代表着自然规律。在《齐物论》中庄子借子綦之口论述风的本质:“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成玄英疏“大块者,造物之名,亦自然之称也”[3]68,“大块”即为“自然”,自然呼气,此气为风。可见,在庄子看来,“风”在本体上是由大块而生,是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本是一体。因而,列子乘风而行,依凭着“天机之动”统御之风,受到的是自然规律的限制,仍旧无法达到“无待”逍遥的自由之境。
在外在条件限制下的“有待”之境中,个体之于世界是工具性的利用关系,世界之于个体则是不同程度的约束与限制。此种关系下的自我主体始终不能与世界主体和谐共在,更不能实现自我的自由和审美意义。
(二)内在心态、观念束缚下的“有待”
在庄子看来,外在条件对个体的束缚并非个体无法达到“无待”逍遥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在阻碍个体实现“无待”逍遥的因素中,来自个体内在思想观念和心态的约束,更甚于外在条件对个体的限制。内在思想观念和心态对个体的束缚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三是内外有分、荣辱有境的观念。针对为世俗之名所累而犹有所待之人,宋荣子笑之,他能够超出世俗之名的限制,“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世人的赞誉或诽谤都不能入于心,不为之奋勉或沮丧。陈鼓应认为宋荣子把握住了真实的自我,肯定自己内在的才德,外在的赞誉或诽谤都由他人,不在己身。[5]204而庄子说:“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犹有未树也。”宋荣子虽不为世俗之名所累,却认为内外有分、荣辱有境。在这种观念的限制下使得“他的境界仍然是‘内外之分’还需‘定’,‘荣辱之境’还需‘辩’”[6],在他看来,自己与外在世界存在有内外之分、荣辱之境,并没有实现精神与思想上的真正自由,因而仍旧处于“有待”之境。
相对于受到外在客观条件限制的“有待”,以上源自内在观念束缚的“有待”之境更是从根本上遏制了个体以本真的存在与世界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往。个体内在心态与观念是内在世界的体现,是个体与外在世界相处状况于内心的投射。本质上讲,“匹”的心态、名誉、荣辱等观念之于个体是限制与约束,个体之于以上诸多思想观念仍旧是工具性的利用关系。个体无意识地遵从此类观念行事,与内在世界之间形成既利用又被其限制的关系,不能以本真的存在于世界中进行审美活动,无从实现个体的自由。
三、“无待”逍遥与主体间性审美内涵
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指向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指存在中的人与世界的共在关系,不是主客的对立关系,而是作为个体的主体与作为世界(包括人和自然)的主体之间的交往与理解关系。简而言之,是人与世界的同一。在同一性的共在关系中,主体间性走向了审美领域,而个体走向了自由。庄子“无待”逍遥正是同一性的共在关系中的绝对自由。
从“有待”中看“无待”,无待逍遥即指个体不凭借任何外在的条件,不被任何物质或观念所制约,顺应万物之变,与自然合而为一的精神自由。庄子列举了种种“有待”的事例之后,提出了如何才能达到“无待”逍遥,即“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郭象注云:“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万物必以自然为正……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御六气之辩者,即是游变化之途也。”[3]20欲要摆脱各种限制与束缚,达到自由与逍遥,必须顺应世间万物之性,顺应自然变化之径。个体顺从万物,与自然合而为一,则万物亦将与个体同游于“无何有之乡”。无处而不通,明彻于无穷之境,则无物可阻碍个体通向逍遥自由之境。庄子又言“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个体忘却自身形体的物质性存在和独特性,忘却形体与天地间他物的区别,在此基础上,进而忘却功绩和名誉,万物不伤于身,功名不留乎心,和光同尘,与万物为一。林希逸说:“‘无己’、‘无功’、‘无名’,皆言无迹也。特下三句,赞美之,又赞美之也。”[4]7“无迹”即言个体忘己、忘功、忘名,个体融于自然,与天地万物混同合一,故谓无迹。此“无”不是否定与消除,而是与自然同化之后的“无”。庄子再次赞美了个体顺应自然,忘却功名,融于自然,无作为、无痕迹、无拘束的“无待”逍遥。
“无待”逍遥中的个体不仅不受外在事物的限制,而且更进一步摆脱了内在思想观念的约束。自我主体将世界视为与自身同样具有生命力与感悟力的主体进行交流和感应,物我两忘,世界与我自身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世界之于自我如同左手之于右手,同属一体。个体和世界之间无所凭借,并非主客对立,而是和谐共在。个体对世界并不征服,世界对个体也不屈从,因而也无所约束,各得自由。
中华美学也体现出主体间性,这源自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与物我合一的哲学思想。一个民族的传统神话体现了该民族对世界的认识。一方面,中国上古神话所独有的“以己观物、以己感物”[7]41的思维特征显现出原始先民在思维中没有将自身同自然界截然分开,认为人和天(自然和社会)是浑然一体的,不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和区分,即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人与神并非对立的关系。另一方面,“以己感物”的思维特征也决定了中华美学在审美本质观上属于感兴论,即审美活动是通过世界与个体之间相互感发和感应而完成的。在个体看来,世界(自然和社会)并不是作为死寂沉沉的客体存在,它同自身一样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感悟力,与个体自身一样可以进行平等和谐的交往和理解。在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的交流和感应中,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中华传统美学中并不存在主体性,也就是说主体没有得到独立。“这种前主体性就蕴涵着古典的主体间性,即把自然和社会当作主体而不是客体(自然被人性化),注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8]中华美学的主体间性正体现于此。
庄子“无待”逍遥的哲学思想置于中华美学的范畴之内,是中国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重要根基,因而也体现出主体间性审美内涵。不论是“有待”还是“无待”,解决的都是个体的存在方式问题,即个体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有待”是个体在世界中有所依凭、受到限制、不得逍遥的存在方式。个体与世界之间是对立的关系。个体对外在事物有所依凭,体现出自我主体对外在客体的一种工具性的利用关系。自我与世界之间并不是平等的理解和交往,而是双方之间的利用与限制。处于“有待”之境中的个体,并没有将外在世界视为与自身平等的主体进行交往,而是将其视为客体并加以利用和征服。因而在主客对立中,主体终究受到限制和约束,没有自由可言。与之相反,在“无待”逍遥中,通过个体的自然化和世界的主体化,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相互理解、相互感发,混同为一。个体达到物我两忘,在与世界的和谐共在中实现各自的逍遥,体现出主体间性的审美内涵。
[1] 杨春时.本体论的主体间性与美学建构[J].厦门大学学报,2006(2):5-10.
[2] 张文通.海德格尔的主体间性美学思想[D].厦门大学,2006.
[3]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 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庄子鬳斋口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 陈鼓应.老庄新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8.
[6] 王英娜.在“有待”中实现“无待”的追求——庄子《逍遥游》解析[J].理论界,2012(2):123-125.
[7]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8] 杨春时.中华美学的古典主体间性[J]社会科学战线,2004(1):76-81.
责任编辑:石长平
2014-09-22
刘思梦(1991—),女,河南许昌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文学。
I206
A
1671-9824(2016)03-005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