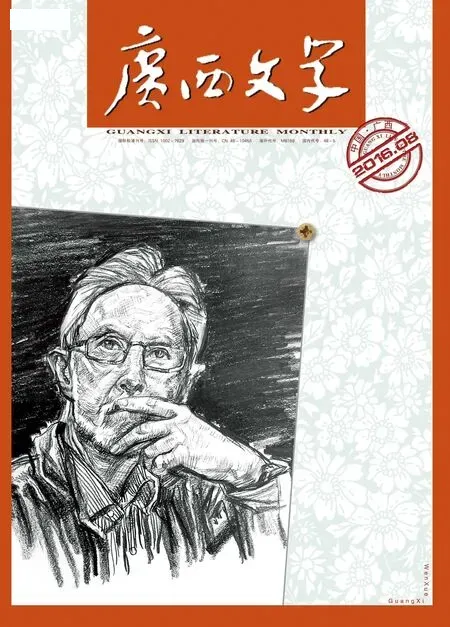故乡:默认的连接
2016-10-23黄咏梅
黄咏梅/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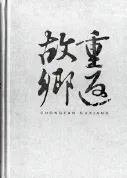
十七岁读书就离开故乡出门求学,之后扎根异乡,我再也没能看到过故乡完整的四季。这么多年来,每每与他人谈起故乡,多半是在说记忆里的那个小城。
位于广西东部的梧州市,与广东接壤,据说在历史上有“百年商埠”之称,而到我出生的2 0世纪7 0年代之后,人们不见得再这么提,他们骄傲地称自己生活的地方为“小香港”,又因它的地理环境特征,更多的人称它为“山城”“水都”。除了龟苓膏、纸包鸡、冰泉豆浆等特产之外,梧州闻名于世的是它的“水浸街”。
我在跟外地人说起故乡梧州这个地名,他们几乎第一反应都是——啊,你们那里每年都被水淹。我总是哭笑不得。“水浸街”这个“传统”使梧州的房屋以骑楼为主,高高的楼脚可以避免整栋房子被洪水淹没。在骑楼的“脚”上,固定着一个铁环,那是用来系小船的,水浸街的时候,小船是交通工具,那铁环等同于现在的车锁。近年,梧州建了防洪堤,“水浸街”的现象很少发生,骑楼被装饰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每次走在河东旧城区的骑楼城,找找那些锈迹斑斑的铁环,我会想起那个背着大书包,走在一路不见天的骑楼底下,即使下雨也不用打伞的学生妹。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有个花花世界叫香港。从西江码头上船,可以一直开到香港,当然,仅限于集装箱里的货物,人要跑到香港,那就叫偷渡了。隔壁那个整天想着发财的叔叔总是说,游水去香港发财,听大人说,他还真的行动过一次,不是游水,是划着自己家的一条小木船,不过并没能走多远,好像到肇庆就上岸了。大概因为我们这个小城处于交通要道上,还没改革开放,这里的人早早就开始做发财梦了。过新年,大街小巷都在放香港歌星许冠杰那首《财神到》,即使在一间破破烂烂的居民房里,那喜洋洋、催人奋发的歌声也能穿过幽暗的花窗——“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
离开故乡多年,我与故乡总是在记忆中相逢,在情感中缔结,在写作中重返。
老 屋
我们家不是梧州市本地人。父亲是广东潮汕人,母亲是贺县(今贺州市)人。上世纪6 0年代初,父亲在暨南大学毕业后,因为华侨成分的“不良”出身,被支边分配到广西地质队。母亲和父亲相识于在贺县今贺州市搞“四清”的那段日子,结婚后定居梧州市。即使如此,我们家也是梧州市的“边缘人”。现在回想起来,在我有记忆开始的那间老屋,是很有象征意味的。
父亲在梧州的第一份工作是梧州地委矿产局,梧州地委大院远离梧州市中心地区,单位分配给父亲的一间房子,位于连接地委大院石鼓冲的一座山上,我父亲回忆当时的房子,写过一篇文章《挂在半山腰的老屋》。这个“挂”,其实是很能形容当时我们家的情形的——父亲母亲就是“挂”在梧州户口里的外来人。听起来有点世外桃源的浪漫,但事实上那段日子的确相当艰难。母亲告诉我,我出生五十六天之后就搬进了这个老屋。

这是我们最早的一张彩色全家福。摄于1980年,我念小学一年级。从表情看,我们是在看电视,那是我们家最早的一台电视机,十四寸黑白,在身后那个还没涂漆的柜子里,还能看到装电视机的空盒子。
老屋是平房,只有两间居室,水泥地,门口搭个简易的厨房。这在当时条件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并不算特别窘迫,但艰苦的是,这间老屋左右无邻——背后是上山顶的路,左边是农业局的一个大实验室,下班后空荡荡的,各种躺在架子上的玻璃试管、瓶罐,散发出刺鼻的药味;右边是空旷的山野,要走十多分钟才有一个废弃的“独立营”,偶尔能看到有士兵在那里训练,鬼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我猜父亲也没指望他们来保护我们。所幸,在老屋的脚下,有几家居民,夜晚,母亲看到脚下星星点点的灯火,才不至于害怕。
每天,父亲母亲要爬山上下班。那时候我们家很少有访客,大概是山路吓怕了父母的同事,再加上,那个年月,似乎人人都很忙,除非邻居,很少有人串门扯闲篇。
在这间“挂在半山腰的老屋”,我和哥哥姐姐孤独地度过了童年。姐姐是老大,比我大六岁,哥哥是老二,大三岁,因为没有长得足够大,所以我被禁止跟随哥哥姐姐偷溜到山野里疯玩。实际上,他们疯玩的主要动力是吃——采各种他们能认识的野果。他们也会带些回家给我,味道不是酸就是甜,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期,酸和甜已经足够撑起幸福的童年生活。现在,我们三个孩子坐在一起回想老屋的生活,就是好玩两个字,谁知道,在父母来说,那是多么不堪回首的艰苦岁月。
父亲是一介书生,大学读的是历史系,而他干的工作却跟历史专业没多大关系,他在地质队挖过栊道,点过开山炮,风餐露宿,要是看到过他一贯瘦弱的身板,会觉得他能在那么重的劳力工作中活下来是个奇迹。可是,那个年月,到处都是这样的“奇迹”,因为他们怀抱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活下去。活下去就是胜利,而不是成功什么的。
父亲母亲总是有很多方法让我们活下去,并且活得相对体面。在老屋的前前后后,父亲开垦了荒地,种蔬菜、瓜果,他自嘲为“潮汕老农”。各个季节,我们都有自种的蔬菜吃,吃不完还带到单位送人,我猜当时父亲最希望的是地里能种出肉来。当然,父亲还养了鸡、鸭、鹅甚至兔子,这些家禽缓解了我们几个孩子长身体阶段对蛋白质和脂肪的本能需求,不过也仅仅是缓解罢了。胆子一贯小的父亲还跟农业局的职工进山捕过蛇,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吃到肉——不拘什么肉。
母亲的手一贯很巧,只要有一寸布,她似乎都能将它做成有用的物品。那时候,我们所有的衣服都是母亲缝制,穿得也不比别人差。记忆最深的是,隔壁农业局时常有用完的化肥布袋,母亲跟职工搞好关系,讨了些来,拆洗后,裁剪缝制成内衣短裤,要不是那种月白色的土布做成外衣实在难看,我母亲会把这些土布变成时装。后来我们兄弟姐妹过年回梧州团聚,年夜饭围在桌子前忆苦思甜,常常会想起那些白色的土布衣裤,说起我哥哥当时有一条睡裤,屁股上印着两个字——“尿素”。我们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文 学
如果说,自给自足是父母对抗贫穷的武器,那么,文学就是父亲教会我们对抗孤独的法宝。既非本土人,又仅仅在梧州只有着十七年的完整生活,我不能说对这个故乡有多么了解和理解,但是,梧州的确是我的文学故乡,不仅是这个小城自身的历史文化底蕴,更多的来自成长期家庭给予我的文学滋养。
住在那个半山腰的老屋,话还不会说全,父亲就教我背诵唐诗。我对老屋生活第一个记忆的画面,是父亲趴在地面的凉席上,给我们三个孩子当马骑。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灯光昏黄,父亲跟我们玩得高兴,他高兴的原因是,我们把他教会的唐诗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正值学校放暑假的姐姐和哥哥,也在外边疯玩一天之后,赶在父亲下班前将唐诗背好了。而四岁小小年纪的我,竟然也背得很好。这是父亲最开心的一幕。事实上,作为文学青年的父亲,这一辈子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到子女走在通往文学圣殿的道路上。
一个四岁的孩子,哪里懂得唐诗的美好?只是出于本能的趋利避害。唐诗就像是幼时的一个诱饵,只要背完唐诗,就有“马”骑,就有水果和糖粒奖励,就有父亲母亲夸奖的虚荣感,反之,则会受到责怪,而即使是声量稍大一点的责怪,也会让我委屈地哭上好一阵子。母亲说,在文学上,我从小就要强。父亲则解释说,那是因为我对文学有特别的天赋。谁知道呢?现在我时常想,要不是因为这间孤独的老屋以及父亲一开始“填鸭式”的唐诗背诵,我今天是否会成为一个作家?
童年就这样,三个孩子在无聊的老屋,比赛背唐诗、看小人书中度过。通常是,一家人围坐在席子上,背唐诗,听父亲讲老虎的故事,母亲举着扇子为我们赶蚊子。这个场景,是我人生中最初的记忆。
十多年前,我从广州回梧州过年,姐姐提议去老屋看看。一家人气喘吁吁爬上山,那老屋居然还孤零零地“挂”在那里,荒芜、破朽,像个风烛残年的受辱老人。我们一家人看得唏嘘。走进去,发现褪剩一点淡绿色的门板上,竟然还有我歪歪扭扭的几个粉笔字。父亲说,六岁多一点,我就吵着要上小学,因为年龄不足,托关系找了人,参加入学前考试,父亲在门板上教我识了很多字,终于让我考过了。我比同龄的孩子提前一年入学。
就在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搬下了山,搬离了老屋,矿产局在石鼓冲的宿舍楼给父亲分了两房一厅。我们住进了四楼的家,有左邻有右舍,有楼上有楼下,从阳台往底下的街道看,母亲说,楼没有山高,但看下去却更可怕似的。
那次重回老屋看过之后没多久,老屋就被拆了,事实上,那座山的整个大半都被夷平了,成为房地产开发的一块肥肉。
浅绿色门板上的那几个粉笔字,一笔一画,开始构成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之旅,同时也开启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建构之旅。
正如父亲所预料,我的作文比同龄人优秀,每每成为贴堂的范文。十岁那年暑假,我写出了第一首分行的诗,经父亲鉴定,推荐到《梧州日报》副刊发表。大概是那些背诵过的唐诗成长发酵,加上一些早熟的情绪抒发而成。后来我听到有人说,少年写诗,青年写小说,中年后写散文。在我看来至少前两个阶段是有道理的。少年浪漫,青年务实,中年深沉。我最浪漫的时代,是在梧州写诗度过的。

穿越骑楼上学放学,是我童年的深刻记忆。图片右下角两只铁环,是水浸街时用来扎系船只的,每次经过都会去拉一下,像跟好朋友拉拉手

中学时代,十四岁,出第一本诗集需要个人照,于是有了这张摆拍的照片。
黄金时代
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复苏,文学也获得了解放,相比今天文学的境遇,的确称得上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借由文学而改变的命运,在国内比比皆是。父亲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父亲在大学时代就喜欢写作,经常串到中文系蹭课、听讲座,由此结识了广东的一些作家诗人,秦牧、张永枚、郭光豹、韩笑等,在他们的鼓励下,他写诗也写杂文。在矿产局工作的时候,不时有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羊城晚报》《广西日报》等,在当时的梧州,这种层次的发表并不多见。于是,他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得以脱离那个不对口的矿产局工作,调入《梧州日报》副刊部。文学改变了父亲的命运,同时也注定了我的命运。父亲视写作为最有价值的事,只不过,他们是被时代所耽误的一代,那些未能实现的文学抱负,希望能在下一代人身上实现。他的愿望如此强烈。我们家三个孩子中,多少都受到过父亲有目的的引导,但是最终走上文学道路的,是姐姐和我,而坚持到最后的只有我。
整个中学阶段,我几乎都沉浸在写作的乐趣中。父亲时常带我到鸳鸯江边散步,在那个黄绿河水交接的界线处,时常暗涌着急流,如同我青春期一起萌动的写作激情。我已经想不起来当时怎么应付其他科目的,学习虽然严重偏科,但整体也并不算差。那时候,全国的校园文学是很热闹的,关注并培养文学新苗似乎是全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比较典型的是各个学校的文学社,开展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比如诗文比赛、名师讲座、文学夏令营,等等。我中学读的是梧州一中,当时的文学社叫萌芽文学社,在梧州属于很活跃的一个。1988年,梧州举办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年会,可以说是当年的一大盛事。全国各地的中学生文学社代表集中在诗意盎然的鸳鸯江畔,畅谈文学,大有恰同学少年的意气风发,这对当时的校园文学影响很大,也大大增强了我写作的动力。
那个年代,因为通信很不发达,所以写信交笔友很流行。我时常在国内报纸杂志发表诗歌,小有名气,经常收到全国各地文学爱好者的信。我记得在梧州师范念书的时候,是住校的,每周回家一次,每次回家我都会带回厚厚一沓信。最高兴的就是父亲,他每封都读得很认真。这些信现在一直保存在梧州的老家,偶尔回去帮母亲收拾屋子,会翻出一两封来看。近三十年前的信纸已经发黄,那些不认识的陌生人的笔迹,向我倾吐着自己的文学情怀和理想,现在读来,还能感到那一颗颗颤动的心跳,同时,满纸洋溢的对写作这项伟大事业的崇拜感,总是让我唏嘘不已。
学校的文学小环境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文学氛围造成的。我很清楚地记得,1988年我第一本诗集出版的时候,当时的梧州市副市长李培鑫接见了我,并请我上茶楼喝了一次早茶,他说自己花钱买了五十本赠送给梧州的文学青少年,可以想见,文学在当时是很红的。由于政府重视文学,梧州文联举行的活动层出不穷,每年定期召开青创会,不定期请著名作家秦牧、紫风、陈残云、张永枚等来举行文学讲座,开展诗文比赛还请到了著名诗人贺敬之、柯岩来颁奖并讲授诗歌……这些都为整个梧州市的文学创作营造了很好的氛围。
已经调入《梧州日报》副刊部的父亲,固然成为梧州文学活动的一个活跃分子。我们家隔三岔五就高朋满座,都是父亲的文友。那个时候,我们家虽然还说不上富裕,但也算得上脱贫了。父亲的文友们时常来我们家,他们畅谈文学的兴致很高,一坐就是一天,母亲还要给他们管饭。因此,母亲的厨艺在当时梧州文学圈是出了名的,她能用很普通的食材烹出美味,酿豆腐、酿南瓜花、酱油鸭……这些家常小菜通常是文友们来家聚会的一大诱惑。当然,他们最主要还是来谈文学的,有时候恰逢母亲没有准备,就着萝卜干喝光一大锅白粥,他们也欢畅无比。说句夸张一点的话,这些文友们似乎可以把文学当菜吃。
那个时候不兴下馆子,客人来家里吃饭大概是最高的礼遇了。秦牧、张永枚等著名作家,在我们家吃过母亲烧的菜。后来,我跟姐姐放暑假,父亲带我们去广州玩,就住在广州军区达道路诗人张永枚的家。有一次,父亲破例从寄宿的学校把我接回家,原来是香港的诗人傅天虹,广西作家杨克、彭洋三位老师要来我们家,父亲希望能借此机会让我得到点拨。类似这样的机会有不少,我得益于父亲的那些文人朋友,获得了书本之外的创作指点。
这种文友家访、聚会,在那个年月特别常见。那时候没有高铁,坐飞机更是少数人才能实现,万水千山,相见不易,但是,穿省过界只为相见畅谈文学,激情燃烧的人不乏。听父亲说,有的诗人在国内游历,每到一个地方,就算素不相识,两手空空上门拜访,主人都会热情款待,因为诗歌是他们唯一的“接头暗号”,是他们敞开心扉的钥匙。进入21世纪的今天,以文学的名义聚会不计其数,各种研讨会、座谈会、采风……然而,同行相见,真正谈文学的居然稀少了。“我们谈谈文学吧……”“谈什么文学,喝酒,喝酒……”我时常被这样的拒绝弄得意兴阑珊。
我们家有一套年代久远的功夫茶具,是父亲潮州老乡送的,它在文友聚会的时候是主角。广西人对工夫茶并不熟悉,所以,父亲每次都给文友示范茶道,“关公巡城”“韩信点兵”……而一切关于文学、写作的话题便由那一只只盛着铁观音的小瓷杯传递着开始了。文学的芳香和温暖,在我的记忆中,总是离不开父亲那套虽古旧却精致的工夫茶具。

大学时代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喜欢拍这些很文艺的黑白照片
写作中的故乡
父亲经由文学而被改变的命运在我身上得以延续。在梧州师范毕业后,我因为公开出版了两本诗集(那时候没有自费出书,能公开出版是一种荣誉和认可)而被保送到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年后,同样因为写作被保送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又是因为写作的特长而分配到《羊城晚报》副刊部。2012年,我调到浙江文学院,干着一份更为纯粹的文学工作。
从桂林到广州到杭州,离梧州一次比一次远,回家的次数也随着距离的改变而减少。
2002年,我转向小说写作,有评论家明确指出我的写作是一种“岭南写作”。从1998年到2012年,我的生活在广州。刚开始,我一直以为我的小说是以广州为根据地。我写出的《骑楼》《多宝路的风》《达人》《少爷威威》等小说,就连街道名也都用广州的。然而,写着写着,我发现自己笔下的广州跟我每天所呼吸到的广州气息并不那么吻合,小说里的广州更多的是过去的广州,无论风物特点、人物气质都与当下难以对应。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才找到答案——那个借由广州地名呈现在小说里的,无非是我记忆中的梧州,是潜意识里通过小说返回故乡的种种途径。

大学时代,父亲带着我去广州、北京等地拜访文友老师,坐那种慢吞吞的绿皮火车
梧州跟广州一衣带水,无论是气候、食物、建筑、方言还是人情、风俗,都与广州一脉相承。在历史记载中,梧州曾归属于广东,后来才被划到广西,所以, 梧州对于广东既有地理也有人文的亲近。梧州的流行元素都来自对广州的模仿,梧州人谋生、找财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落广州。我在广州工作期间,回家探望父母,每遇到熟人,他们都认为我在广州是“捞世界”,是最好的归宿,听到他们最多的话就是——几时返落去?那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回广州?过去国道还没有开通,梧州人去广州只能坐船,一夜到天明就抵埠,是顺流而下的。因此,梧州人去广州不是“上”,而是“下”。这种地理位置和心理归宿感,构成了梧州人的复杂心理。梧州人对广州比对首府南宁的亲近感似乎更为强烈,然而相比其他城市,梧州的经济并不见得很有优势,发展的步伐相对也慢些,所以,这里的人有点自卑又有点自尊,既务实又不势利,虽有梦想却缺少野心,虽有想法却容易被吃喝玩乐耽搁。他们更喜欢跟自己人扎堆。我虽身处广州,在感情中却活在故乡,这些感受特别敏锐,不自觉地渗透到我的写作里来了。
写故乡,对于像我这样离家在外的人来说,其实就是写记忆,是写童年记忆。童年记忆就是一张无边无沿的页面,任他无数次敲打回车键,将自己发送回去的每一次都能获取一个新的开头。苏童曾经说过:“作家一生的写作都是为了找寻第一记忆,并让其复原。而第一记忆,注定是丢失的。”作家每一次对“第一记忆”的寻找,都会创造出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往往令人恍若隔世。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出发点就是源自一种恍若隔世的惊诧。
这些年来,梧州的变化很大,过去我们居住的河东市中心,如今已经变成了老城区,市政府搬到了河西,那一带高楼林立,成为新的城区中心。我们家依然住在河东的马皇巷梧州日报社旧宿舍,也就是那个时代不少文学爱好者摸上门来谈文学的家。我很庆幸河东片没有太多改变,这样,每次回去我不至于有太多的失落感。是的,失落感,因为每一次回家,我其实都在下意识地印证记忆,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我找到故乡的感觉:骑楼底下的大排档、巷口的河粉、牛杂店、珠山隧道里的服装小摊、北山脚的酸菜铺、中山路口的凉茶铺……当然,还有母校的校门、西江里的游泳场以及江上的清风……这些进入过我写作中的信物,依然像证据一般向我证实着光阴的流逝。
前一段日子,我请探亲假回梧州看望父母。一打开门,我的口袋里就叮叮咚咚此起彼伏地响了。手机、Ipad、电子阅读器中,那些一直在等待登录的端口,纷纷默认连接上了宽带网。这些声音吓了我一跳,就好像踩中了某个机关,某些断了线的机器自动开启。这是上一次回家的时候,我设置连接过家里的宽带,只要在一定范围内,网址缺省、密码缺省,一切的连接都是默认、自然而然。这些网络连接一直沉默着,游子归家的那一瞬间,这些连接统统复活,并奏响了动人的乐曲。
我与故乡之间,从我出生的那一天,就设置了默认的连接方式,那些隐而不见的情感,就是我重返故乡的缺省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