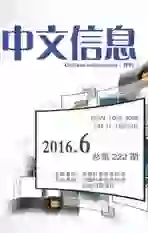文人与文人画超越物象回归心性的气息
2016-10-21钟云龙
摘 要: 梅兰竹石是文人庭居中必不可少的雅物,微风过竹响清音,寒梅傲骨独暄妍,空谷素兰有幽香,总是唤起人的归欤之情。当一个人放弃了通过外在的功名来确立自己生命的价值时,他必定要转向自己的心灵寻找生命的价值。文人所向往的“归”,就是心灵性的,是一种由外在世界向心灵世界的回归,是文人隐士们对自我真本生命之呼唤。
关键词:文人 文人画 归隐 心性化 内在精神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6-0396-01
陶渊明赋《归来兮辞》,他脱去的不仅仅是樊笼,还有伪装和面具;他载欣载奔所归向的,亦不仅仅是那个“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家,还有他的心灵。那个家是他的真心呈现的一个场所。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苏轼身上,苏轼定灵烂漫的灵性,也是在他被放逐到广州、广东、南海,过着不问世事的生活时,才有充分的展现。人释手只有从人群中分离出来独处时,才能对自己的生命有深切而强烈的体认和感悟。
一、文人“明心见性,即佛即心”的心境
中国文人对地有着深刻的体会,所以中国文人对孤独情有独钟,总讲隐居,离群,脱俗。表面上看,这是消极的退避,而实际上,隐藏着他们积极的寻求——寻找自己的灵魂,体会自己的生命。因此,归隐它不仅仅属回避政治问题。在现在看来更是一个哲学问题,其中隐含着中国文人对心灵和生命极深刻,极动人的关怀。
“归”的深层表现是“反求诸心”,中国儒家文化中,讲“仁”与“礼”,“仁”强调人的内在心性方面,“礼”则强调人的外在行为(形式)的方面。孔子还提“礼”与“乐”,那么“礼”与“乐”并不仅仅是在这外在的形式,它们更有内在的,属于心灵中的东西[1]。后期的儒家越来越强调人的内在心性,从孟子大讲心性,到宋明理学家拈出“敬”和“诚”,心学家则突出涵养,这此种种无不表现出向心世界的追求[2]。道家也强调内在心性的修养保持,庄子所谓“得意忘形”,既得心之以即可,至于形,是可以弃置而不顾的。中国化的佛教更是如此了,也是一种向往内心的追求本心的开悟。唐王维便是以佛理禅趣入画,悟禅即悟画,得其妙境,色空观道出:“真道出画中之白,即画中之画,即画外之画也。”画外之画——自然得其中之,闲、静、淡、空、远之深意,这正是禅境所示,在回归心性这一普通的文化倾向下,中国画很自然就走上了重视内心的表达转而轻视外形的描绘之路,以文人意识主体的文人画的根本精神正在于此。
就“内在心性的追求”这一点来,以画家而论,顾恺之已经以名士身份作画,而且以名士的风神为描写的对象;以画论而论,《古画名录》已经提出“若拘以体物,未见精萃,若取之象外,方见膏腴”。那么在《历代名画记》一方面把“气韵生动”置于核心地位,提出“绘画中所表现出来的所有独特的意境之味”。还提出了“以形似之外求其画”的追求,这里既有提高绘画地位之意,还把绘画看成了衣冠贵胄、逸士高人的风雅之事。这两方面的结合,便有了文人画理论的发生。苏轼等人的文人画理论,是在张彦远思想的基础之上加入了一些新的因素(所指为禅学为主),进而促成了文人画的新阶段。文人画的基本精神;即心性化追求,自六朝始一以贯之。
二、“画”乃心之产物
心性化的追求,形而上的心灵意味,决定了中国艺术不求以外在的形色给感官以强烈的刺激和震撼,而欲以内在深长的意蕴给心灵启示。落实到绘画上,具体表现为物象形式的弱化,即所谓“离形得似”离外在之形式,得内在之神似。
画是“心性之学”、“画者,心画”。中国文人画,是为写心中一点灵明,而不是为赞叹物象的鲜妍。中国文人的画,它所表现的是指向心灵的象征。诸如“从于心者也”、“高雅之情,寄于画”、“专以意求,不在形似”、“得其性情为妙”等等。所以有徐渭、石涛、齐白石等强调“似与不似”,以“不似之似”为真似。再如水墨山水中点苔,它把山石上的苔衣简化成墨点,这些浓浓淡淡或聚或散的墨点作为苔衣的象征符号,有特殊的意义。
顾恺之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四体妍媸说的就是一种外形之美,但顾恺之认为这并不是人物(画)的妙处,人(画)之妙应在于眼睛所在传达出神(人的心灵)。张彦远还说道:“夫画物特忌形貌采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漏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3]。
三、艺术形式上的“平淡”
无论是诗还是画。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冲淡”:“脱有形似握手已违”。便是说表面上纵然相近,精神却已经离远,也就是说形似抓不住内心深处那幽邈的意味,所以对于文人与文人画者来说,一味的去追求“穷形极貌”,粘著于事物表象,着意去寻求外形的肖似,其结果可能会是貌合而神离。元代四家倪瓒也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4]。三国魏嵇康《养生论》则提到:“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在一般情况下,形(身体)是依赖于神(精神)而挺立的,神(精神)则赋形(身体)而存在,两者形表影附,内在精神在文人心中占了重要地位。
艺术的动人之处,恰恰是形之外的那一种深情远趣。张彦远说:“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可与俗人道也”[5]。便是这深情远趣的表现,所以,文人之所以對墨的偏爱,它也是有原因的,即是借助于水墨技法的应用,为人的灵和画的内蕴的开拓,提供一个开阔的空间;人文对色的排斥,也有这样一个深层的理由,即感官要给心灵让路。
绘事的“心性化的趋向,对中国文人及绘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由此而产生了文人情怀和文人画家追求平淡含蓄的绘画风格。中国绘画的心性化趋向,原本就是文人与绘画互相影响的结果,它必然与文人情结联系在一起,中国文人的向内(心性)的回归必须摆脱奢豪艳丽的物欲,才能回归到自己,直接面对一己的真实生命。可以说:“艺术上追求平淡,是思想上回归心灵这一文化底蕴的象征”。
参考文献
[1][2]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知三联书屋, 2009年
[3]傅慧敏著.中国古代绘画理论解读[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29页
[4] (元代)倪瓒.清閟阁全集卷十 尺牍篇之倪瓒《答张藻仲书》
[5]潘运告著.《唐五代画论》 唐代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论六法卷> [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1997年第166页
作者简介:钟云龙,(1992—),男,汉族。广西北海城人,现就读于广西艺术学院2015级美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画花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