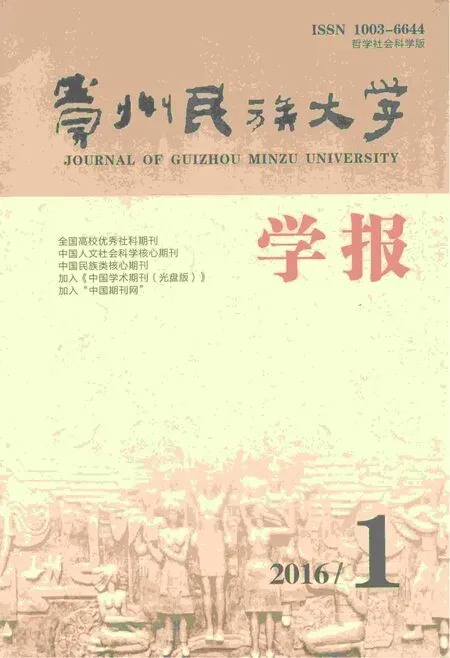跨文化视野中的“看图讲故事”研究——梅维恒《绘画与表演》读后记及其论题意义
2016-10-20孟令法
孟 令 法
跨文化视野中的“看图讲故事”研究——梅维恒《绘画与表演》读后记及其论题意义
孟 令 法
美国汉学家梅维恒的《绘画与表演》是一部关于中国变文起源与传播的重要著作。该著充分利用印度、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故事画”资料,以中亚为中介构拟出“看图讲故事”的基本传播路线和分布走向,旨在展呈中国“看图讲故事”的印度起源图景。本文基于对该著的立论和论证过程的系统梳理,结合学界对民俗学的“流传学派”和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的相关讨论,评析该著的研究模式及其结论之于当下的学术价值;而“看图讲故事”这一新论题的提出,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内探查故事讲述的民俗实践路径及其活形态表达的文化多样性。
流传学;梅维恒;《绘画与表演》;故事讲述;看图讲故事
作者孟令法,男,汉族,江苏沛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5级民俗学博士研究生(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 房山 102488)。
《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下称《绘画与表演》)*[美]梅维恒著.王邦维、荣新江、钱文忠译.季羡林审定.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此书在2011年由上海中西书局再版,将书名副标题更定为“中国绘画叙述及其起源研究”,其内容也做了些许调整,并于书前增加了梅维恒作、季羡林翻译的《〈绘画与表演〉中译本前言》,书后则添加了王邦维所写的《重印后记》,全书正文(不含书前插图)也由第一版的297页,增加到303页。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原著副标题的理论关注正是围绕“看图讲故事”这一新论题的提出而展开,本文依然选用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阅读与叙写对象。除特别说明外,本文对该著的引用仅于引文后用括号标注页码。此外,就书名正题的翻译而言,笔者认为更切近的译法当为“绘画与演述”,由此可呼应该著的中心论题“看图讲故事”;就performance一词的汉译,民俗学界已形成过多次讨论,本文不作展开。简而言之,该术语来自语言学概念中的“语言运用”,而非“表演艺术”(performing arts)。是美国著名汉学家、敦煌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系教授、考古及人类学博物馆顾问梅维恒(Victor H. Mair,1943~)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该著于1988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专门讨论有关中国俗文学之变文的印度起源及其传播路径。
据欧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网介绍,梅维恒早年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1965年加入美国和平队(US Peace Corps),在尼泊尔服役两年。1967年秋,他进入华盛顿大学学习印度佛经、中印佛教、藏文及梵文。翌年,他留学英国伦敦学院亚非学院,学习梵文。后来,他入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深造,于1976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79年起,他转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直至今日。其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包括中国语言文学、中古史、敦煌学等,被誉为“北美敦煌学第一人”。[1]除《绘画与表演》外,其《敦煌俗文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敦煌通俗叙事文学作品》(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诸多著作都在中西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尽管季羡林在读过《绘画与表演》后表示:“并不能说,我完全同意他所有的新观点和新提法”,但他依然给予了很高评价,“是书中新观点和提法之多,却是很少有书能望其项背的。在学者平常不注意的地方,他能提出崭新的解释。在学者平常不能联系的地方,他能联系起来,而且似乎是天衣无缝。有的联系简直近于石破天惊的程度,不由得你不点头称是”[2]P1,故而他在督促弟子翻译此书时曾言:“他(梅维恒)的眼光开阔,看得远一些。我们不注意的一些东西,他注意到了。我们也要眼界开阔一些,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从全世界文化交流,来看敦煌文化、敦煌文学。”[3]由此可见,作为我国首屈一指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在耄耋之年依然在思考我国学术研究的国际视野,而《绘画与表演》的翻译者之一、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则认为:“梅维恒的这三部著作,尤其是《绘画与表演》应该能给中国学界许多启迪,用更广阔、更深刻的眼光来看待俗文学·民间文艺·文化交流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恐怕就是许多启迪中最重要的一个”[4]P111。那么,《绘画与表演》在论述变文之印度起源与传播路径时展现了哪些内容,而这些融为一体的阐释又以哪些理论作支撑,以怎样的方法来呈现,则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对象。
一、从印度到中国:“看图讲故事”的起源及其传播路径
《绘画与表演》的正文部分由包括导论在内的六章组成,其中导论为全书的引子,其重点在于提出变文的产生与发展并非源自中国本土,而是有着印度佛教传播的基础;而自第一章到第五章,则分别论证了印度作为“看图讲故事”的起源地,在这门口头表达艺术的传播中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相似艺术形式得以产生与发展的本质性影响,并于文末再次强调了中国变文的印度渊源。
具体说来,“导论”从变文的概念、使用群体及其在中国的重要性出发,在概述变文发展脉络的同时,将论述主体落在变文与“看图讲故事”的关系上,并在历时与共时的双向勘察中得出,中国的变文实是源自印度的一种宣讲活动。在梅维恒看来,“变文始于唐代(618~906),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的小说史和戏剧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长篇白话叙事文学”,而“最早用‘变’的形式讲故事的人与其说是僧人,不如说是一些世俗的表演者,而且其中有些是妇女”(页1),尽管“变的表演本身看来在宋代(960~1277)就逐渐消亡了,但是看图讲故事仍然用其它的名字坚持流传了下来”(页3),如自元代兴起并延传至今的评话、宝卷、全相,以及明清时代才出现的善书、戏曲、西洋景,甚至丧葬中的祭台布景和诵经表演等,均有变文的遗韵。虽然“在变文和同时的历史著作中,都有些细微的迹象表明,这种文学形式是从一种被简称为‘转变’的口头的看图讲故事的形式发展而来的”,但“由于配合‘变’的图画讲唱在中国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民间的传统,在史书——它们自然是上层社会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一点有关的细节可寻”(页1~2),不过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分别在敦煌发现的图卷P5511、P4398和P4524则在民间层面弥补了这一缺憾,进而为中国变文的“印度起源说”提供了基础证据。
第一章“古代印度的看图讲故事”对印度“看图讲故事”的起源进行了探查。其中述及早有古印度文法学家波你尼在其《波你尼经》中提到过一些物品或图像;英国学者托马斯也曾提出在孔雀王朝的日常生活中看图讲故事早已成为大众的娱乐形式,而“提到在古代印度讲故事时要用图画,最重要的或许是在波颠阇利(Patajali)的《大疏》(Mahābhāsya)中的资料”(页22~23)。对此,梅维恒从古印度saubhika(“魔术师”)的词源以及它在其他语言中的同源词开始,将一系列古籍经典,如梵文《大事》中的演艺人员“名”,巴利文《梵网经》中的娱乐“名”,以及佛经《学处论集》中的表演类别“名”等与之对照,而更多的历史文献,如曷立沙《璎珞传》、毗舍佉达多《指环印》、耆那教经典《博伽梵经》、霍恩雷《十居士支》、薄婆菩提《罗摩后传》等都为“看图讲故事”的印度起源提供了有力证据。另外,“在古代印度——从saubhika的时代不久以后——就有了影戏,也有了傀儡戏”,而这类大概兴起于公元前1世纪的艺术类型(页31),也可在巴利文《长老尼偈》或梵文《摩诃婆罗多》中得到印证。不过,在看图讲故事的发展中,如考底利耶的《政事论》便指出saubhika可以被雇佣为间谍(页34),但“看图讲故事与不受尊重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之间的这种联系并不使人觉得奇怪”(页41),而这与中国唐代寺院外进行表演的民间艺人如出一辙。故而,梅维恒于本章开头便强调“转变是一种看图讲故事,他们所具有的韵散结合的形式和从本体上所作的假定,都说明它们来自印度,它们与其说是由僧人们来表演,不如说一般是由世俗的艺人来表演”(页22)。

除此之外,中亚的文化结构也成为梅维恒讨论变文产生于中亚文化间关系的重点,而由出身帕提亚王室的摩尼在公元三世纪创立并在西亚巴比伦逐渐壮大的摩尼教,则成为其探查中国变文的印度起源之关键。因为摩尼教曾于唐宋时期与佛教发生密切关联,而中亚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混合体,其语言也相当复杂——曾经的佛国于阗也通用过伊朗语和波斯语。因此,梅维恒认为“中亚的佛教吸收了伊朗的因素,而中亚的摩尼教则吸收了印度的成分”,而“配有图画而散韵相兼地说唱故事的技法是在印度出生的,由佛教化的伊朗族‘伯父’和突厥族的‘伯母’培养长大,最后由中国‘双亲’收养”(页72)。虽然在成吉思汗时代摩尼教既已绝迹于中亚,但“直到14世纪末叶,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仍分散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在东南沿海福建地区的穷乡僻壤)。另外,摩尼教的一些要素还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保留到17世纪的某些秘密会社中”(页70)。不过,在南宋时既已广泛存在的“禁摩”活动中已有禁止“图画妖像及传写刊印明教等妖妄经文”(陆游《条对状》)的规定。因此,梅维恒认为变文演唱的兴起和衰落,“部分地与摩尼教的命运相联系”(页72)。总之,梅维恒的论述是力图证实中亚在中国变文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桥梁”地位。
二、从中国到东南亚再回到印度:中亚作为传播的“中介”
为了进一步论证中国变文的印度起源,梅维恒在中亚找到了作为中介的有力证据,而类似于“变文”的看图讲故事,不仅存在于中国广袤的大地,而在印度尼西亚也有“相似的东西”(第三章),这就是类型多样的“瓦扬(wayang)”。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讲,瓦扬“变自意思是‘影子’的字根”,而这种理解“与其说它指的是从后面放出光来把影子投在幕上的技巧,还不如说它是呈现在观众眼前的幻觉效应”,因此“画卷、傀儡、皮影和舞蹈演员都可以被合理地称作‘瓦扬’”(页80)。在梅维恒看来,“至少从公元一世纪起,南亚影响就开始进入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其他地区。公元三四世纪缅甸、暹罗、印度尼西亚与不久之后跟上来的印度支那海岸的广泛印度话,在四五世纪达到了巅峰”(页81),而印度作为佛教(也包括婆罗门教)的发源地,看图讲故事在这里的应用具有不可争议的宗教属性,因此受佛教影响的区域在演绎各类“影戏”或“曲艺”时都会带有这种特征——中国的变文和印度尼西亚的“瓦扬”自然也不例外,并且这种“宗教母题不仅在一场成功的皮影戏表演中起作用,它们在特定的情况下还是催请演员的根本基础”(页91),故而“瓦扬”的表演者如“达郎”等会认为自己具有异乎寻常的“神力”,因而在梅维恒看来,这类印尼表演具有显著的萨满特征。

作为中国、东南亚及中亚诸国看图讲故事发源地的印度,在千百年的发展中,并未因历史潮流而泯灭曾经的传统。第四章详细论述了“近现代印度的看图讲故事”。早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期里,有关印度看图讲故事的人类学研究就已经展开,数量可观,且质量不错。从这些学术文本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看图讲故事在近、现代印度世界里可谓无处不在,并且得到很好的发展。例如,在印度迈索尔邦的吉勒吉阿塔人(Killekyāta)中就有被称为“木偶舞蹈者”或“图片表演者”的艺人,他们既以操纵木偶或将木偶与画片结合起来演绎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和《往世书》的故事,而“从属类的观点上来看,木偶戏、皮影戏和看图讲故事(使用画卷、帘幕或者其它种类的绘画场景和人物)之间没有绝对清楚的区别。再者,使用人工照明的方法应该加以注意,这意味着,用发展的观点来看,皮影戏的人物本来就是从叙事画卷上剪下来的”(页126)。而通过《孟买管辖区地名辞典》,梅维恒不仅发现了吉勒吉阿塔人中的看图讲故事者,还于这一文献中看到卡特布(Katbu)、奇多罗卡提(Chitrakāthi)、哈尔德(Harda)、奇多罗卡尔(Citrakar或Citrakār)等人中同样存在演述“图画”的群体,尽管他们处在不同的种姓中,但对于看图讲故事的演述者而言却都属于“流浪的乞丐”。
三、从东亚到欧美:从传播路线到分布走向的构合

在欧洲的意大利南部,曾经存在一种名为“狂喜画卷”(exultet rolls)的看图讲故事行为,而后发展成朗诵praeconium paschale的实践活动,其直接源流则上溯自6世纪前半叶的以cantambanco(“长凳歌手”)见长的盲人或伪装成盲人的表演,由此成为欧洲看图讲故事的重要中介。“亚洲看图讲故事在德国的翻版叫做Bänkelsänger(‘长凳歌手’)、Marktsänger(‘市场歌手’)、Strassensänger(‘街头歌手’)、Zeitungssänger(‘新闻歌手’)、Ständilsänger(‘站立歌手’)和Schildersänger(‘图片歌手’)”(页185),这些歌手虽在演述内容或形式上有所不同,但他们均以巡回各地的模式于街头巷尾、广场集市表演简单易懂的民间故事,因而也被称为“街头表演者”或“游吟诗人”。而法国的此类表演者则以“圣歌歌手”、“集市歌手”、“罪恶或悲剧商人”、“买报小贩”以及其他类似的名字为人所知(页191);他们不仅将演述民族史诗《罗兰之歌》、《武功歌》视为最高资本,同时也以售卖相关图片为生。在西班牙,至迟从17世纪开始,巡回商人就在出售并由游吟诗人口头解说的名为auques或“[pliego de] aleluyas”的对折图片;而一种可被视为汉语“变相”的“retablo de las maravillas(奇异画面)”在西班牙也很流行,并在塞万提斯《奇异画面》与加西亚·洛尔迦《鞋匠的美妙妻子》中都可找到证据。
此外,在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地区、英格兰地区、荷兰、瑞典、瑞士、佛兰德地区都可以发现看图讲故事的影子,但“由于它低下的社会地位,看图讲故事没有被系统地记载在历史书里。结果是,对许多国家来讲,要得到这个题目的可靠材料是非常困难的”(页194)。综上所述,梅维恒推演出一个“肯定的结论”:这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看图讲故事形式,虽已发生根本性变异,但最终源头滥觞于印度。
四、“流传学派”与“印度中心论”:溯源研究的瓶颈
施爱东在简评《绘画与表演》一书时指出:“德国语言学家本菲在对比世界各民族故事之后,认为许多流行于欧洲的故事并非源自欧洲本土,而是源自印度。印度故事先是传向穆斯林,然后通过回教徒传遍世界”,从而开启了以民间故事为本体对象的民俗学的“流传学派”[5]封二。通观全书,我们不难发现,梅维恒对变文的中国生成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相似艺术表现形式的延传同样沿用了“流传学派”的理论模式*刘魁立在《欧洲民间文学研究的流传学派》一文中对“流传学派”的理论方法作出了全面的学术史梳理。文中指出“19世纪中叶,在德国,在格林兄弟所创立的神话学派的故乡,逐渐形成了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的流派——流传学派。在我国,这个学派及其学说,在不同时期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名称:传播学派、播化学派、因袭说、迁徙说、外借说等等,但其内容是同一的。”参见刘魁立:《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流传学派》,刘魁立:《刘魁立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69页。,同时利用早已成熟的词源分析法、文献疏证法和比较研究法对印度“看图讲故事”的文化表达形式及其艺术发生学的核心地位作出了充分的肯定。这种研究模式与民俗学的流传学派和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有着极其相似之处。不过,与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把世界文化的原点得以形成的中心定位在埃及有所不同,流传学派(特别是其后继者芬兰学派)的故事传播学*芬兰学派是在20世纪初承续“神话学派”和“流传学派”的“历史比较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个以“研究故事情节、确定这些情节产生的最初发祥地和在世界各地分布的情况、以及这些情节传播的地理途径”的学派,又被称为“历史—地理学派”,而其研究方法则被称为“历史地理比较研究法”,这一学派在民间故事的研究中同样认为欧洲的民间故事有着印度发源的特征。参见刘魁立:《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流传学派》,刘魁立:《刘魁立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93-294页。人类学的文化传播论学派是19世纪末21世纪初在欧洲形成的一个继文化进化论学派后的第二个流派。该流派所创立的“传播论”“将人类社会文化的变化归因于物质文化和习得行为从一个起源社会散播到其他社会。换句话说,传播论认为文化变迁(cultural change)的过程主要是文化采借(cultural borrowing)的结果”,而在传播论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两个变体,即英国的埃及中心论和德奥的文化圈理论。参见庄孔韶主编:《人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页。由此可见,虽然芬兰学派与人类学的文化传播论学派所关注的对象有所不同,研究的路径也有所差异,但二者对文化因素及其变迁的探索都呈现出追本溯源的一致性。结论则同梅维恒的“印度起源说”不谋而合。
对梅维恒来说,《绘画与表演》能够得出“看图讲故事”的“印度起源说”,似乎带有一定的偶然因素,而这或许也非其本意。在此书的最后一段梅维恒写到:“我在为本书收集材料时,目的不是要想论证看图讲故事只有一个单一的印度来源。我原来唯一的目的,是想弄清出自敦煌的一个谜一般的故事画卷(P4524)的意义和作用,它表现了舍利佛与六师外道之间的神变较量。在比我曾设想的要长出许多年的探索与比年代更长得多的旅行之后,我和任何人一样感到惊奇:印度显然是看图讲故事的显而易见的源头。本书的副标题于是可以被当作一个有待于证实的假设”(页195)。由此可见,对“看图讲故事”的起源地探究来自一幅与唐代变文相配套的伯希和敦煌画卷(P4524),现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而正是为了弄清画卷与变文之间的关系,梅维恒顺着变文的宗教源头,从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中国西藏、伊朗、土耳其,以及西欧诸国的材料中搜集相关文本,并由过去很少注意的材料,如明清文书、绣像小说、文人散曲、宫观壁画、河西宝卷,乃至通书、弹词、拉洋片等艺术形式中寻找可资佐证的线索,最终为曾经广泛流行的“看图讲故事传统”的假说找到一连串证据,并确定这种传统的源头出自印度,于隋唐之时途经中亚传入中国,进而于中国的在地化实践中衍生出其他种类的表演(说唱)艺术。
其实,单从变文的角度来看,梅维恒的“流传学”研究似乎无懈可击,而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看图讲故事”均带有显著宗教属性的事实以及相似的表演模式都为“印度中心论”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但是,文化发生的“一元论”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作为人类文化多样性表征的“看图讲故事”或许存在多种发生的可能,而非只有一个来源。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变文的溯源中,梅维恒并未对美洲做出相应的证据链梳理,尽管他曾表示:“我之所以没有追踪这个艺术类型向美洲的传播,是因为在新世界里它实际上是一个现代现象,而我意在研究看图讲故事的传统表现形式”(页194)。那么,我们或许会产生以下的疑问:从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到北极地区的爱斯基摩人(因纽特人)都拥有漫长的文明史,难道他们的“传统表现形式”中就没有生长出这类“看图讲故事”的演述艺术吗?而就文化人类学的英国传播论学派所认为的世界文化均出自埃及的论断而言,印度的“看图讲故事”是否也有来自埃及的可能?再有,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或其他拥有久远历史的岛屿部落是否也会存在类似的表演艺术,因此,如果按照“流传学派”的推论,这些地方的“看图讲故事”是来自印度还是埃及,抑或为本土生本土长的?另外,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其变文艺术是否也有可能是反向“西进”而为印度所接纳并于在地化实践中成为印度的民族艺术?或者说,发源于印度的佛教为适应中国实际而不得不借助一定的本地化形式而加以传播,进而在中国民众中得到接受并传承?
虽然我们都知道,以一已之力要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做出竭泽而渔的全面钩沉非常困难,但该著的相关推论及其证据链还是存在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例如有关“在古代印度——从saubhika的时代不久以后——就有了影戏,也有了傀儡戏。影戏大概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经有了,因为在巴利文的《长老尼偈》有一处提到rupparūpakam”,以及“相似的发展进程(即幻像→皮影戏)可能在中国宋代早期已经出现”(页31)的论述尚欠稳妥。因为在《史记·孝武本纪》中记载:武帝时有“齐人(李)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后世做“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术盖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6]P458而在《汉书·外戚传》对同一事件作了更为详细的记述:“上(汉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李)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科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7]P3952对此,宋代文士高承于《事物纪原》中写到:“故老相承,言影戏之原,出于汉武帝李夫人之亡,齐人少翁,言能致其魂,上念夫人无已,迺使致之,少翁夜为方帷,张灯烛,帝坐他帐,自帷之望见之,仿佛夫人像也,盖不得就视之,由是世间有影戏”[8]P495。由此可见,早在公元前1世纪的武帝时(前141~前87年)影戏既已在中国出现,这与印度影戏的产生时间大体相当,而结合先秦两汉时的丧葬礼仪、墓葬画像石与陶俑等陪葬品,以及乐府伶人等更能确认影戏的中国自发性[9]P59-62。因此,后世的印度影响很可能只是作为我国皮影戏走向成熟的催化剂,而非源头。
我们不能否认,从流传学派(传播学派)到芬兰历史—地理学派,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及其理论和方法论贡献为我们呈现了追溯人类文化发生的可能性。不过,之所以会出现结论的“不确定性”,或仅是作为一种“假说”而提出的推考,归根结底在于此类“溯源性研究”太过重视文字资料与历史实物,而忽略了民间口头传统的运作机理及其重要的传播—接受作用,此其一;其二,这类研究需要大量实证性材料作支撑,而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可谓遍布全球,文化传承世代赓续又有所变异,并于代际之间不断被再创造,难于以一种研究向度去盖棺定论;再者,将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文献材料搜罗齐整,从而真正做到竭泽而渔,也是这类比较研究往往遭致诟病的主要挑战,更何况又有多少文字材料由于自然或人为原因淹没于时间的长河。
刘魁立对“流传学派”的理论方法论来源、贡献和局限性等问题作出了公允的评价。他指出:“流传学派的研究家们始终没有摆脱掉实证主义哲学和方法论对他们的严重影响”,而“正像神话学派把他们的雅利安神话起源论绝对化一样,流传学派也把自己的印度起源说和情节流传说绝对化,套用于一切民族的一切作品。他们不仅贬低了除个别民族以外的其他所有民族的艺术才能和创造精神,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学作品的民族特色,忽视了作品本身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该民族的历史实际对于作品所产生的种种影响。”[10]P294庄孔韶认为:“文化研究者必须考虑文化自身的主体和能动性,即承认社会文化有选择、拒斥及整合文化外来要素的能力。相比之下,传播论那种以分散特质及其机械组合来解释文化或建构文化史的做法就显得不科学和不可取。”[11]P48孟慧英则评论道:“流传学派大都主张文化中心论,从而侧重历史溯源的探讨。在传播论看来,就是那种来自中心的古代文化传遍了世界各国,把埃及文化、印度文化的作用片面夸大,设置加以绝对化。……传播学派贬低了非古代中心文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化创造精神,同时也忽视了各个民族对外来文化现象或吸收或排斥的选择事实”,而“芬兰学派否定了民间叙事的创造性。故事文本是变化的,它总是处在被读或被表演之中。文本、语境或环境交织在一个表演过程中。讲故事为一个社会戏剧过程,文本知识为那个语境或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12]P110-111,131应当说,以上批评当是中肯的。故而,对文化发生作“一元论”的溯源推考实难以令人彻底信服。
五、由“静”至“动”的研究:“看图讲故事”的论题意义
通过以上描述,我们对梅维恒的《绘画与表演》一著的立论当已形成基本的认识。虽然从整体上看,该著的重点在于追溯中国俗文学之变文的来源,但正是对其源头的追寻,让作者有了新发现——其所考察的各种类型的看图讲故事——均有印度看图讲故事的影子,甚至也包括皮影戏、傀儡戏、戏剧和曲艺等,从而形成一种假说性结论——印度是世界范围内看图讲故事的源发地。而正是由于这项研究成果的出现,让原本只重“文本”不重“变相”的定式发生转变,也就是说学者们的研究已经从静态的文本转向动态的演述,从而为中国俗文学的研究打开了新纪元。

另一方面,我在调研重庆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双槐善书”时也曾发现,这种口头表达与看图讲故事,尤其是变文(宝卷),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梅维恒在《绘画与表演》中也曾提到一种流传于甘肃武威地区的善书表演艺术,而这种以佛教经典故事图卷作辅助的韵散结合的说唱形式重在教导那些信奉佛教的善男信女(页10~11)。然而,与梅维恒所介绍的“武威善书”不同,流传于川东渝北的“双槐善书”却没有使用画卷的传统,而于2006年已忝列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名录的湖北“汉川善书”同样如此。尽管刘守华认为:善书“是中国文学史上‘宝卷’的支系,乃至可以说就是‘宝卷’的别名或俗称。而‘宝卷’又是从唐代的‘变文’、‘俗讲’演化而来”[13]P81,但车锡伦则表示:即便“民间宣讲(善书)和清及近现代民间宣卷(宝卷),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它们在历史发展中既没有‘源’与‘流’的关系,在演唱形态和文本形式上也有明显的差别”[14]P134-135。目前,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善书与开启于明初的“宣讲圣谕”存在着密切关联,而流传于渝鄂地区的此类民间说唱艺术多被考证为成型于乾隆时期*可参见游子安:《从宣讲圣谕到说善书——近代劝善方式之传承》,《文化遗产》,2008年第2期,第49-58页,贾平:《论汉川善书的传播》,《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234-237页,张祎琛:《清代圣谕宣讲类善书的刊刻与传播》,《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34-140页。。正如“双槐善书”传承人黄华清所言:“善书劝人向善,老辈子用勒个讲圣谕……善书不全在庙子里唱,在坝坝里也可以唱,我们不只是唱佛经,还有民间传说,像孟姜女、白蛇传、杨家将、宋蒙战争啥子的。还在婚礼上唱骂媒的都有,现在都用到宣传国家政策上喽。所以善书和佛教没得多大关系。”*被调查者:黄华清(1941-),男,初中文化,“双槐善书”重庆市级非遗传承人,农民;调查者:孟令法(1988-),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参与者:李凤琴(1985-),女,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教师,民俗学硕士;调查时间:2015年7月4日周六下午;调查地点:重庆市合川区双槐镇宏新村四社被调查者家中。由此可见,善书作为一种民间说唱艺术,是否源自佛教影响而产生的变文及其变异品——宝卷,依然是一个值得追索的话题。
那么,从中国本土探查“看图讲故事”这类传统文化表达形式的广泛流布,我们依然能在国内其他民族中找到一些鲜活的例证。例如,凉山彝族世代存续的毕摩宗教绘画——神图与鬼板——同样具有表现民族起源或神鬼信仰的仪式注解功能;贵州彝族的那史绘画传统同样是毕摩诗画合璧的故事讲述形式之流存;而纳西族的“东巴经”、景颇族的“目瑙柱”、水族的“水书”、苗族的“刻道”及壮族的“坡芽歌书”等多种多样的本土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着“看图讲故事”的传统性表征。倘若沿着《绘画与表演》的推论去考察,难道我们就能够进行如下联系——上述诸民族的“看图讲故事”也源自印度?诚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化发生学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思路,但不是唯一的进路,而答案应当始终是朝向开放性的探解,以包容各种可能性的求证。
综上所述,梅维恒的《绘画与表演》一著在结论上虽有可商榷之处,但在研究变文这种俗文学题材的论述过程中,围绕“看图讲故事”这一核心命题所提供的丰富材料,已然让我们看到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另一面——人类文化的共通性。从整体上讲,该著的重要价值正是在于以“看图讲故事”这一新论题的提出,在“看”和“讲”之间以一种动态模式的勾连和演绎,打破了只重“文本”而忽略“变相”的静态思考,从而为变文之变的进一步探讨开启了新的格局,也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内探查故事讲述的民俗实践路径及其活形态表达的文化多样性。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认为,“看图讲故事”作为研究论题的提出,其意义大于“溯源性研究”的推论过程。
[1]Maxiaohe.《梅维恒》[EB/OL].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f02/128.html,2004-05-14/2015-07-17.
[2]季羡林.序[A].[美]梅维恒著.王邦维、荣新江、钱文忠译.季羡林审定.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3]易华.梅维恒与汉学研究的不解情缘“新疆每一寸土地都很亲切”[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8-06(630).
[4]钱文忠.俗文学·民间文艺·文化交流——读美国梅维恒教授的三部近著[J].读书,1990,(8).
[5]施爱东.梅维恒的《绘画与表演》[J].民俗研究,2009,(1).
[6][汉]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宋]裴骃集解.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8][宋]高承撰.[明]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M].北京:中华书局,1989.
[9]刘得腾.皮影戏“西汉起源说”新证[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3).
[10]刘魁立.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流传学派[A].刘魁立.刘魁立民俗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11]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12]孟慧英.西方民俗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3]刘守华.从宝卷到善书——湖北汉川善书的特质与魅力[J].文化遗产,2007,(1).
[14]车锡伦.读清末蒋玉真编〈醒心宝卷〉——兼谈“宣讲”(圣谕、善书)与“宣卷”(宝卷)[J].文学遗产,2010,(2).
责任编辑:杨 兰
Studyon“Story-tellingthroughPictures”fromCross-culturalPerspectives:ReadingAmericanSinologistVictorH.Mair’s“PaintingandPerforming”andGraspingitsTheme
MENG Lingfa
“Painting and Performing” by American sinologist Victor H. Mair is an important work regarding Chinese Bianwen (a popular form of narrative literature flourishing in the Tang Dynasty) in terms of origin and transmission. The work makes full use of Indian, Chinese and other countries’ documents of “story pictures” available, draws a transmission route and distribution directions with Central Asia as medium, and illustrates the Indian origin for Chinese “story-telling through pictur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rguments, combines the discussions of “Transmission School” of folklore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comments on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e work. It is argued that the new topic of “story-telling through pictures” is helpful for exploring the practice routes of story-telling and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living forms.
transmission; Victor H. Mair; “Painting and Performing”; story-telling; story-telling through pictures
K890
A
1003-6644(2016)01-01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