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坪的诗
2016-10-17
墓 畔
妈妈,在你落气的那一个秋夜,
是否真的需要我们把你扶起来。
是否真有一位天使在用器具,
把你吐出来的那一口气容纳。
在太阳和生命之间难道
就没有一场告别的仪式。
在我们的目光意想不到的地方,
是什么在安慰你离去时的悲伤。
看看先辈们组成的大家族,
如何接受一个早归的孩子。
兄 弟
一生下来我们就是失散
的兄弟被亲人各自领走。
分手的路口我们看见十字架,
看见太阳把黑夜驱散。
离开后我们是两个小黑点。
彼此进入我们的眼睛,
你看我为何从不相识。
读的天书,现在合上。
我们把衣服穿旧,
我们把头发剪短。
为什么你要指着胸膛发誓,
开口的同时还紧闭着嘴唇。
失踪的孩子
就是两只眼也不够用,
谁看见失踪的孩子?
就是翻开书,也得合眼,
就是不看,也在想,看什么。
房屋已拆迁,只剩门。
门没有框,只剩一瞬间的倾斜。
就是睁眼,也看不见什么在倒塌,
只听见轰鸣,在听到之前停息。
只知道寻找孩子的父母失踪了。
孩子早已归来。
孩子就是贪玩,玩一个自由的游戏,
现在归来,他讲述另外的世界。
就是两只耳朵也听不够呀,
他说出的距离过于遥远,
两张嘴分头呼叫,父母怎能听见?
失踪的孩子,回到自己想象的家,
把窗户开成两只眼的形状,
白天装得下太阳,
晚上装得下月亮,
就是睡着也睁开眼。
寻找孩子的父母看见——那是两口水井,
他们喝着双手捧起的水,
眼泪流下来,盐一样,
他们坚定无比,就是要寻找到失踪的孩子。
否则,永不回家。
小狗和三弟
我的腿曾狠狠地踢过一只小狗,
当它休克时我心里充满了内疚。
我想起小狗在追着我疯狂吼叫,
我的恐惧感一下子得到了释放。
我的手曾狠狠地打过三弟的后背,
三弟被击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我们在一起是玩追人的游戏,
最后暴力显露出了它的原型。
我的腿和我的手告诫我,
我曾经是一个野蛮的人。
我把这野蛮写进了诗中,
希望能得到诗神的规训。
我的腿变成了一只小狗,
手也从三弟的后背缩回。
当我被生活狠狠地踢打,
小狗和三弟却给我安慰。
柔 软
我如今怎样去探望被拆迁的房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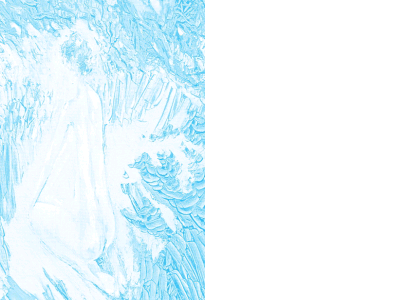
窗户停留在空中,像月亮已经消失,
土墙化作泥,密密麻麻地长满杂草。
依然有歌声,从某一个房间里传出,
可感受到房间里原有的陈设?
散居的亲人又聚集在了一起,
弟弟在房屋边上种下一棵杏树,
春天在它的枝头上开出了花朵,
夏天的叶子一直到秋天才掉落。
冬天,我们离开了房屋与果树,
有一些东西,并未被及时带走,
似乎再也不会失而复得。
一排晾在屋外的青菜,会发酸,
燕子北方飞来没了扎窝的屋檐,
炊烟若返回将听到鞭炮的响声。
亲爱的妻子我带你回家,
不是要来看这一片废墟,
它不美,不是我的描述。
雨下个不停,我们不可久留,
回到车上,万物连成了一片。
小时候我赤着脚上学,
摔脏了衣裳回家换洗。
为什么我会放声哭泣?
刚刚来还是永久离开?
请听我无法说出的原由,
并理解我一路上的沉默。
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站在这一片空地上,
人类的迁徙故事是不是太过明了?
房屋虽然不是最坚固的建筑,
而人的心,已是无比的柔软。
李白论天才
我们时代的天才病污染了空气。
他没有配剑,但有想象的剑术,
有见识,知识与个性的双重偏见。
他以为自己进入了伟大者的行列,
其实早已远离人性最基本的生长,
他因自居时代之上而远离了时代,
像一个守财奴,有数不尽的横财。
他是绰号和帽子的制造者批发商,
有商人的精明,和政客的计算器,
他很有一套,一环一环纠缠不清。
现实对他来说是一笔糊涂账,
谁离他最近他反对谁,
远方是文明的同义词,
古典让他腰缠万贯,本质上
他是乞丐、疯子、孤独者和暴君。
他的洁癖,使这个世界无比肮脏。
一个不爱但丁的女人
一个男人最爱
一个爱不上的女人。
他为她感到羞怯而窥视自己
对于生活的愿望,对此她
轻轻地回头,含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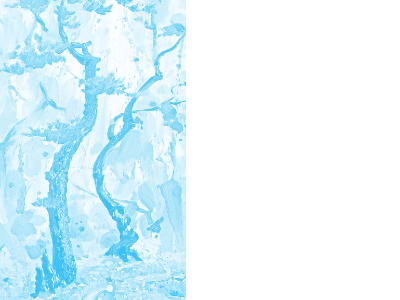
他以为,这就是全部,
一种漫不经心的拥有。
于是写作像一个人临近中年,
长年流浪,开始白头。
梦见先知和圣灵,
思想深刻得穿越了地狱,
终结并迎来了一个时代。
作为一个人,他说出了
“动太阳而移群星”的爱。
回忆少年时期的梦想,
年轻、无知,热血燃烧,
爱着一个不存在的女人,
为她倾其所有,
调整自我言行,
风尘仆仆地,结束女人的一生,
领会痛切而永久的喜剧。
街 灯
暮色在雕刻街灯,经过上一个世纪的美食街,
那时,饥饿还闪着太阳的光。
我仍在乡村彷徨,倾听远方的召唤,
幻想的未来是人的倒影。
今天,车辆绕着大街奔跑,
在落日与地平线之间,人们闭上了眼睛,
我知道,有一个真理在沉睡中把我模仿,
当我醒来,只有黎明在微笑。
我经过的,仿佛是一场遗忘,
在你的叫声中获取了从前的名字。
我突然想哭,像早已记不清第一次那样,
肯定世界在我离开以后会回过头来打量。
而此刻,繁星已布满苍穹,
再也无法置身旷野的宁静,
永不能理解时代对于一个人的安排,
因为我的生活并不是一个人的生活。
广场僵尸舞
早晨,我的爱人睡在床上
窗外的歌声将她吵醒,
夜里,我们散步穿过所有小区的广场,
我们走呀走,有的人走进了长长的人群,
他们抬腿举步,双手摇摆,
幕色中只见黑色的人影,在大地上晃动。
这是我们生活中带有歌声的河流,
小贩的吆喝声,房屋的倒塌声如同波涛,
小孩子也在这旋窝中玩耍成长,
警车刺耳的尖叫声麻痹了所有人的神经。
我对爱人说,咱们离开这儿去别的地方吧,
我们去开垦一片荒地,挖一囗水塘,
爱人问那儿有虫子吗?它们肆意飞舞,
把人从梦中惊醒,不知身处何方!
每天,我们都无可奈何地看着人们跳舞,
他们排着长队,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他们真的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僵尸吗?
他们在这儿始终练习起步,但从未出发。
给王东东
早晨,仅有的一滴水走向街道,
阳光离开路人又重新回到天空。
但是早晨,光是没睡醒的病人,
大地上,找不到属于它的病床。
黄昏,人们纷纷涌向夜晚深处,
睡眠让沉睡者获得短暂的尊严。
可是黄昏,一个老人整夜不眠,
儿孙们追讨他握在掌心的硬币。
明天朋友远行欲找回诗性正义,
因为饭桌上发生出埃及的争执。
那么分吧,新鲜的杏每人一份,
穿过腐朽的街灯又见一个黎明。
钢铁轨道架到城市繁华的高空,
流浪汉身上的血摊成一面旗帜。
儿童们哼哼大人唱过的赞美歌,
死者记起了胸膛开放过的白花。
一面镜子凸出挂在牢门上的锁,
瞬间一队人流穿过囚服的扣眼。
阴沟沉没的客轮唤起一江春水,
远方手艺人从古代消失到如今。
厌 倦
生活已经厌倦了我,因为不变的口音和善变的诺言,
一不小心我把一张白纸捏成纸团请原谅!
为什么我会看见一个奔跑的女孩?
当我买了一杯豆浆忘了领取吸管,
我望着一个老人牵着孙子的手远去,
花瓣落在地上不在空中是有道理的,
尽管厌倦,而我一如既往地热爱着。
像一只小麻雀在地面上蹦跳,行走,
一个披肩少妇是那么优雅像一段往事回放,
我的厌倦由来己久像存心撕碎的彩色照片,
因为厌倦,我无比地厌倦,话说不出口,
每一件事都会结束我想起卡夫卡的咳嗽,
不要以为他喜欢全部而我只偏向唯一。
红色的连衣裙当然是好看的,
一勺饭喂进那个婴儿的嘴里,
想起妈妈领我去赶集一个劲地问我想吃什么,
我的弟妹们离我的生活很遥远,
我父亲在电话的一头安度晚年,
多么丰富,我的口音不能改变。
我不伦不类的话语有时抽象有时具体,
我的手断过在我还不能够去把握什么的时候,
我一生的渴望远未形成,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像一个中国式的鲁滨逊,
我知道孤独的是海洋而不是岛屿。
我已经有了一个陈旧的过往,
不在前世而在于此刻的厌倦。
病的原理
我感冒了躺在床上,
风也感冒了药也感冒了躺在我的身上。
秋天的病春天也会犯,
它们躺在湿润的大地上。
我呼吸,命运像一张纸巾,
我努力去习惯生活,
在健康中停止创造,
在事物的运动中咳嗽。
白天堆积了一大堆杂事,
它们涉及到记忆、民俗和历史。
它们随日暮分布在天空,
夜色里有一盏点亮的灯。
那些天上的星星,
在眼睛闭上的一刻消失。
它们是远方的终点,
它们是自我的一部分。
我应该疯狂,
我的宁静由来已久。
太多的力量把床扔出了窗外,
我的病将飘在空中。
牙 缝
一股无名火穿上了衣裳,
在地面打转,不知道疼痛是响亮的。
系上扣子,这世界夜深如水。
轻声咳嗽,戴着满手臂金表,
时针指向白日。
念头穷尽把一棵树移植,摔碎,
什么东西在反面吞吐泉水,
流向晚霞,对纯洁一无所知,
借黑暗和另一只手数星星。
恍惚一瞬间,路的起点;
一艘巨轮停靠岸边,被火点燃,
远方在终点起伏的大陆,褶皱的痛苦;
雪里皴露红色小径,
那是一万张嘴紧咬着牙,
那是舌头被咬断的牙缝。
咳 嗽
田野放牧的牛有一个吃的形状。
可咳嗽使人多么痛苦,
一万吨铁钉在喉咙里挤着,
一片细小的鹅毛钻进鼻孔。
咳嗽痛苦地围绕着地铁弯曲,
疯子歇斯底里地紧闭起双唇。
春雷把阳光击成星月,
花斑贴满教堂的窗户,
双手祈祷,痛诉罪人。
咳嗽让男人分开女人,
女人分开小孩,小孩分开空气,
空气的另一面眼神在四处闪烁。
死神在活人中间潜伏,
把手夹进法律的字眼。
可灵魂是一枚别致的书签。
咳嗽改变人体的器官终身服役,
把生命教化成知冷知热的木头。
咳嗽是愤怒的扁担,疾病的冲锋号,
没人会安心躺在床上等待黑夜降临。
婴儿喝完毒奶粉红润的心变黑,
烧完垃圾在家里喝农药,死神,
咳嗽时手碰额头,商人活见鬼。
政治犯遇大赦,咳嗽从肚子里
重新冒出一颗人头,孩子错了,
长长的舌头刮起一阵历史飓风,
咳嗽,咳嗽,它让人唠叨不止。
自 然
我们是朋友,但一定要克服对手,
即便对于公正并没有准备好言论,
但不必用过多的体恤,面对没有
忏悔意识的宽恕,就像一个傻子。
抗辩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意味着
必须放弃道德感进行政治友爱博弈,
如同回到深海打捞太阳让它高悬于
人心,跟大地具有同等厚度的天空。
他们在否定的逻辑中建立起一套
与事实相悖的法则,唯一的事实
总是有各不相同的讲法,分责任
为主次、轻重,他们好各处躲藏。
当我们在言语的转换处停顿时,
他们扮演着正义的化身,
我在这样的屋子里陷入我的彷徨。
【作者简介】陈家坪,诗人,纪录片导演。1970年出生于重庆。曾任北大在线新青年网站学术频道编辑、中国学术论坛网主编。参与编辑民刊《知识分子》,参与采访整理《沉沦的圣殿》。出版诗集《吊水浒》,拍摄教育纪录片《快乐的哆嗦》。近年与友人发起北京青年诗会,主编《桥与门:北京青年诗会诗人访谈》。现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