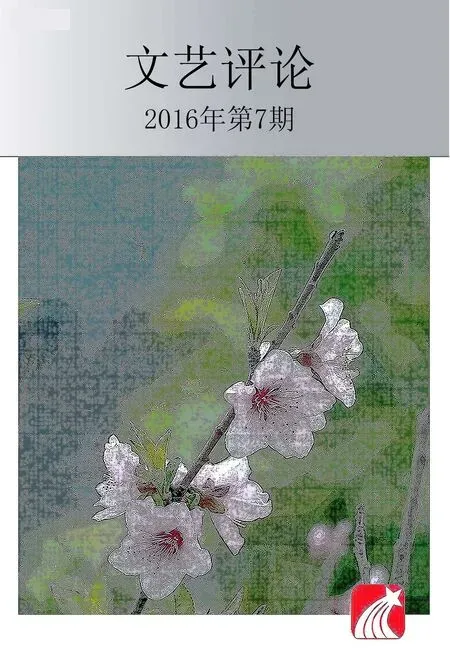汉魏六朝志人小说对唐小说创作的影响
2016-09-29何亮
○何亮
汉魏六朝志人小说对唐小说创作的影响
○何亮
志人小说,顾名思义,即记载人物言行事迹的小说。汉魏六朝时期,小说编撰者以“补史之阙”精神搜集、编撰小说作品,其中涉及的人物、事件,很多以真人真事为素材,近乎“实录”。上至地位显赫的帝王,如曹操、曹丕、晋武帝、晋明帝,盛极一时的名士,如陈仲举、周子居、郭林宗,驰骋沙场、扬名后世的大将军,如桓温、王敦、刘裕、祖狄、檀道济等,史书中都有真实记载。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最先提出志人、志怪小说概念,并对两者加以区分,志人小说最大的特征是“尚实”:“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①不仅如此,志人小说语言受清谈之风影响,讲究言简义丰,寥寥数笔勾勒出人物的风雅神韵;事件的叙述也以简略达意为胜,注重给接受者带来精神上的审美愉悦。汉魏六朝志人小说在记事、写人方面的经验,对唐小说创作影响深远,是唐小说取之不尽的宝库。唐小说在继承汉魏六朝志人小说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对促进小说文体成熟、独立有重要意义。
一、取材真实
志人小说之翘楚,当之无愧者应为刘义庆《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作为主要记载魏晋时期上层社会某些人物传闻轶事的小说作品,其人、其事史书中大都有真实记载,是窥知历史的另一面镜子。
如《任诞》二十四,载刘伶喜好喝酒之逸事:“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②为从夫人处骗取喝酒,竟想出于神前盟誓的主意,不禁让人捧腹大笑。刘伶好酒,《晋书》的记载与《世说新语》大同小异:“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尝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兒之言,慎不可听。’仍引酒御肉,隗然复醉。”③阮籍为魏晋名士,其事迹《世说新语》多有记录。如“任诞”,“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④。此事与《晋书》所载基本相同:“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⑤《世说新语》所记人、事与历史书籍的高度重合,反映时人编撰小说以真实性为标准的自觉追求。裴启《语林》本盛行一时,但因所载谢安之事与实际不符,顿销声匿迹,就说明真实性对小说的重要。因此,汉魏六朝志人小说注重所述事件的真实,尽可能以真人、真事为题材进行创作,还原事件的本来面貌。
以真人、真事结撰小说,影响了唐小说的创作。唐小说家也喜欢以现实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为故事的题材,如皇甫枚《玉匣记》,王敬之将刻有铭文的玉匣献给魏帅乐彦真后,彦真广集人才,却无人洞悉铭文蕴涵的深意。故事行将结束之际,铭文所暗示乐彦真兵败被杀之事得到应验。经学者考证,乐彦真历史上实有其人,真实姓名应为乐彦祯,“中和三年至文德元年(883—888)任魏博节度使(《唐方镇年表》卷四),丙午岁乃光启二年(886)。魏博乃河朔三镇之一,自田承嗣以来屡衅逆乱,朝廷不能制。乐彦祯镇魏骄满不轨,终军乱被杀”⑥。《玉匣记》故事人物、结局与历史记载完全一致,但富有神秘色彩的铭文,增添了作品的虚幻性,作品的主题也因此而得以提升:不仅仅是为了还原历史,而是通过乐颜真兵败如古铭谶语所预言,表达对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和唐末动乱的无奈。又如李复言《续玄怪·韦令公皋》,韦令公依附岳父,屡遭岳父轻视侮辱,过着“忍愧强安”的生活:
他日,其妻尤甚悯之,曰:“男儿固有四方志,大丈夫何处不安,今厌贱如此而不知,欢然度日,奇哉!推鼓舞人,岂公之乐。妾辞家事君子,荒隅一间茅屋,亦君之居;炊菽羹藜,箪食瓢饮,亦君之食。何必忍愧强安,为有血气者所笑。”⑦
韦令公皋,为德宗朝封疆大吏韦皋。《新唐书》记载:“韦皋字城武,京兆万年人。六代祖范,有勋力周、隋间。皋始仕为建陵挽郎,诸帅府更辟,擢监察御史。张镒节度凤翔,署营田判官。以殿中侍御史知陇州行营留事。”⑧他出身于名门望族,家世显赫,为唐朝的安定曾立下汗马功劳。《新唐书》卷二十二详细记载了他在平定南诏过程中的丰功伟绩。《续玄怪录·韦令公皋》对韦皋离开相府后人生经历的描述,与史书大体相符:“是日韦行,月余日到歧……奏大理评事……俄而朱泚窥神器,驾幸奉天,兵戈乱起……乃除御史中丞、行在军粮史……乃授兵部尚书、西川节度使。”⑨韦皋虽历史上实有其人其事,但妻子鼓励他奋发图强的一段话,显然为作者的有意编造。其目的是想通过韦皋人生发迹的事例警戒世人,人生的名誉、财富、地位,需个人竭尽所能争取。
佚名《邺侯外传》、沈汾《续仙传·司马承祯》、尉迟枢《中朝故事·李德裕广识》、何延之《兰亭记》、陈鸿《长恨歌传》《开元升平源》等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在史书中也可见其踪迹。唐小说家取材之时,虽很多源自史书,但他们所追求的真实,不是汉魏六朝志人小说的为真实而真实。历史素材只是影射现实,表达主题的一种手段。唐小说的这种特性,使陈寅恪、汪国垣、卞孝萱等老一辈大家,运用“文史互证”方法“以小说证史”,从小说中探究所隐藏事件的真相。卞孝萱《唐传奇新探》由新旧《唐书》《资治通鉴》所记元载、杨炎、刘宴之死事,推断沈既济创作《任氏传》的真正用意:“沈既济感到在实录中替杨炎辩解,还是有限度的,不如写小说自由,可以虚构、幻设,尽情渲染,而又不要负文责、担风险,于是《任氏传》与《枕中记》同时问世了。”⑩“《建中实录》一方面诬蔑刘晏‘动摇储宫’,另一方面歌颂元载‘独保护上(指德宗)’,沈既济偏袒元载、攻击刘晏的观点也是明显的。他描写雌狐变化为‘丽人’任二十娘,对郑六忠贞不二,以讽刺刘晏背叛元载,人不如‘妖’,正是他亲元载、杨炎而敌视刘晏的立场观点的表现。”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把《长恨歌传》中事件与《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对照,对《长恨歌传》进行全面的探讨。如考证《长恨歌传》中杨太真入宫始末,杨太真度为女道士入宫,杨太真册封为贵妃等事件。可见,唐小说以真人真事为素材,只不过借其外壳寄寓现实的寓意。
汉魏六朝志人小说要求对人物、事件进行复写,不容许出现偏差,但不少志人小说有很多荒诞不实的内容,与所述事实有较大出入。这绝非作者本意,否则裴启就不会因谢安的指责而不安了。汉魏六朝志人小说的真实,只能是一种“真实的荒诞”。唐小说继承此传统,以“实录”相标榜,不少篇目以真人、真事命名。有时作者对内容加以处理、加工,作品的形式看似虚诞,内容却很真实。因为对唐小说家和接受者来说,他们关注的不是故事内容、人物是否真实,而是意识到虚构故事可以作为一种表达真实的手段。唐代小说的真实是一种“荒诞的真实”。
二、以情节展现人物性格
汉魏六朝志人小说不以情节的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取胜。它最大的特点是截取人物瞬间的神情举止,用只言片语描绘人物的性格特征,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中国小说在六朝时期刻画人物只是素描速写,勾勒人物最有表现力的形象特征和神态,遂形成以形写神的志人小说审美规范。”汉魏六朝志人小说,描绘了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如《世说新语·忿狷》,王蓝田食鸡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蹑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以筋刺、举以掷地、以屐齿蹑、取纳口中、啮破吐之等一系列动作的勾画,生动展现王蓝田急躁的性格;“德行”,管宁、华歆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两相对比,作者无一言予以评判,但管宁、华歆之品行立现;“雅量”,谢太傅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危难之际,孙王诸人神色俱变,谢太傅则安之若素。谢安临危不惧的精神品质,在众人中独树一帜。
刻画人物虽是汉魏六朝志人小说的重心,但它往往只捕捉人物某一瞬间的性格特征,未能动态显示人物的情感、性格的发展。受六朝志人小说的影响,唐小说也塑造了许多惟妙惟肖的人物形象,但作者摒弃了静态式地勾勒人物的神貌、言语、动作。高尔基说过,情节是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是叙事性作品的第一要素。作品要表现人物性格,塑造立体的人物形象,必须设计好相关情节。“情节的发展、推进、展开,是否自然、真切、合理,是否紧凑、起伏而有迭宕,不在于故事编得多么玄妙离奇,也不在于情节的发展多么惊险怪诞,而在于情节的发展是否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是否按照人物自身性格的发展轨迹去组织情节、设计场面、推进矛盾、展开冲突。”唐小说在继承志人小说重人物形象塑造及塑造人物形象方法的基础上,注重故事的情节性,以其独运匠心的情节设置及人物言行展现人物性格,塑造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
第一,选取展现人物性格的典型情节刻画人物。如《达悉盈盈传》(节文),作品为完成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选取盈盈与同官之子幽会数月而不被人知晓,知晓后又将过错转嫁给虢国夫人这两件互有勾连的情节,塑造了集美貌与聪慧于一身的贵族少妇形象。对比同官之子,在明皇颁布诏令搜寻自己的危急时刻,不仅想不出应对的良策,反而自怨自艾、后悔不迭的无能,盈盈巾帼不让须眉的智慧不言自明。《余媚娘叙录》同样选择能彰显故事女主人公余媚娘性格的两段情节:媚娘丧夫后,毅然与心爱男子结婚,以及新丈夫移情别恋,手刃与丈夫相好的女子。唐代的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寡妇再嫁也得到律令的首肯。唐太宗曾颁布《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凡是鳏夫、寡妇丧期已过的,“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因此,自上而下,除民间女子之外,就连唐朝公主再嫁者,也不乏其人。据《新唐书·公主传》载,唐代公主再嫁者达24人,其中三次嫁人的就有5人。但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再婚在世人看来普遍认为失节,丧偶再婚需要勇气。媚娘不顾世俗非议,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展现了其性格勇敢、大胆的一面。丈夫婚后朝三暮四,她竟将过错归于与丈夫相好的女子,手刃杀之,又体现了她敢爱敢恨,残酷的另一面。人物性格的复杂、多面,在余媚娘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第二,把人物置于情节的矛盾冲突,通过紧张、激烈的故事冲突展现人物性格。这种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多用于以爱情为主线的小说,《任氏传》《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都属于这一类。如《李娃传》,情节有三次矛盾冲突,人物性格及形象也相应发生三次转变:荥阳生与出身娼门的李娃相遇,因涉世未深而倾情投入这段难以有结果的恋情。当荥阳生忘情于与李娃的两人世界时,所有资财都已耗尽,以谋财为目的的鸨母见无利可图,欲将荥阳生骗走。面对荥阳生的情深意重,李娃内心焦灼,有许多不舍,是继续与荥阳生长相厮守还是离开?这是第一次冲突。李娃敌不过鸨母的劝说,充当了赶走荥阳生的帮凶。荥阳生被骗后,穷困潦倒,沦落到乞讨度日。荥阳生的悲惨境遇,让心地本善的李娃内心五味杂陈。是帮助荥阳生还是视而不见?这是第二次冲突。经过抉择,李娃供养荥阳生,扶助他考取功名。荥阳生中举后,世人争相奉承,就连对他弃之不顾的父亲,也重新与之相认。做荥阳生的妻子还是独自开始新的生活?这是第三次冲突。从这一系列矛盾冲突中,一位嗜财而深情,美丽温柔而不失果敢坚毅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
汉魏六朝志人小说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往往用简短的语言抓住某一瞬间最契合人物性格的言行。人物性格的变化是无法看到的,唐小说吸取了汉魏六朝志人小说以言行刻画人物的方法,也有发展和创新。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再局限于只言片语。小说围绕情节,除讲述在一定时间流中发生的有首有尾的完整故事,还通过情节展现人物形象。对人物的刻画,既重视内在的神韵,又不忽视外在形体特征的描绘,并且在故事流中,可以感受到故事人物性格的变化。唐小说刻画了更为生动的人物形象,讲述了更为曲折、动人的故事。
三、娱乐的审美主旨
汉魏六朝志人小说的盛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人们消遣、娱乐的审美需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陈书》卷三六《始兴王叔陵传》载:“叔陵……夜常不卧,烧烛达晓,呼召宾客,说民间细事,戏谑无所不为。”《魏书》卷九一《蒋少游传》载:“高祖时,青州刺史侯文和……滑稽多智,辞说无端,尤善浅俗委巷之语,至可玩笑。”
《笑林》是记魏晋时期人物言行的笑话类作品。“它是第一次以消闲的态度写人间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实为志人小说之滥觞。”《笑林》作者邯郸淳初见曹植,植洗完澡后,“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曹植提及的“俳优小说”就是笑话。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中的东方朔、优孟、淳于髡、优旃等是说笑话的行家,司马迁说他们“谈言微中,亦可解纷”,肯定了笑话在言谈中调节气氛的意义。
《世说新语》注重载录上层贵族、名士们的轶闻逸事。这些轶闻逸事展现了他们超脱、尔雅有韵致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带给接受者不一样的审美愉悦。书中特列“排调”一类,专记人与人之间的玩笑。《任诞》所述刘伶纵酒、诸阮与猪同饮事: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刘伶好酒,酩酊大醉后竟赤身裸体,其旷达、放任形骸,不禁令人莞尔。众阮更是放诞不羁,狂喝滥饮到与畜无别的境界,着实让人惊叹、诧异。鲁迅先生认为,“自《德行》至《仇隙》,以类相从,事起后汉,止于东晋,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志人小说在资谈笑的同时,并没有让接受者一笑而过。诸名士狂放不羁的言行,是在当时黑暗、恐怖的政治环境下,寻求的精神超越和解脱。
唐文人驿馆官舍“征奇话异”,唐小说也带有游戏娱乐的成分。如《东阳夜怪录》和《任氏传》,作者在文末交代故事来源的时候,就表明了娱乐意图:
前进士王洙,字学源,其先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尝居邹鲁间名山习业。
洙自云,前四年时,因随籍入贡。暮次荥阳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虚者,以家事不得就举,言旋故里,遇洙,因话辛勤往复之意。
建中二年,沈既济自左拾遗于金吴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户部郎中崔需,右拾遗陆淳,皆谪居东南,自秦徂吴,水陆同道。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而随焉。浮颍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
《东阳夜怪录》和《任氏传》,都是文人士子在驿馆官舍“昼晏夜话”之作。《东阳夜怪录》是前进士王洙投宿荥阳旅馆之时,与秀才成自虚谈论的有关往返于科考路途上的事。而《任氏传》则是沈既济等一行人,从秦地到吴地的途中,晚上说话时记载下来的奇异故事。文人士子在驿馆官舍“昼晏夜话,各征其异说”之“说”和“话”,正透露出小说创作的消遣、娱乐性质。
出自《广古今五行记》的《纥干狐尾》,讲述了一个令人捧腹的故事:
并州有人姓纥干,好剧。承闻在外有狐魅,遂得一狐尾,缀着衣后。至妻旁,侧坐露之。其妻私心疑是狐魅,遂密持斧欲斫之。其人叩头云:“我不是魅。”妻不信。走遂至邻家,邻家又以刀杖逐之。其人惶惧告言:“我戏剧,不意专欲杀我。”此亦妖由人兴矣。
并州人纥干喜欢开玩笑。当村人正苦于狐媚为祟之时,他伪装成狐狸,戏弄妻子。他果真被当成了狐狸,遭到妻子、邻居的追逐、打杀。这个故事,作者用诙谐的笔墨,将故事写得兴味盎然。纥干伪装成狐狸的得意,纥干被当成狐狸遭到妻子砍斫的磕头求饶,纥干被邻居追打后的惶遽,作者都描绘得趣味横生。在嬉笑声中,故事情节达到高潮。
唐人小说观念和理论有了较大发展。唐前的志人小说,虽有娱乐的成分,人们却以真实的标准来要求志人小说。到了唐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小说的虚构特性,并不以绝对的真实来要求小说作品。唐小说家所认为的真实,不是所述事件的真实,而是小说反映的人情物理的真实。因此,唐代小说“用让人们感到有趣的奇人奇事以反映世俗人情,认识到了小说应有娱乐性,思想性寓于娱乐性之中,而且愈加明确”。柳宗元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亦肯定“俳”有益于世:“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就连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书事》亦云:“《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刘知几充分认识到小说娱乐性的巨大影响力,以至于“斯风一扇,国史多同”,小说的娱乐性质还影响到了史书的撰写。唐小说中的不少作品,很多是赏心而作,有“远实用而近娱乐”“足为谈助”等特点。这也符合小说消遣和娱乐的基本功能。
汉魏六朝志人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结构简单,只粗陈故事梗概。语言受清谈之风影响,言简义丰,通过人物的片言只语,生动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在题材的选择上,讲究“实录”,以达到“补史之阙”的目的;事件的叙述以简略达意为胜,注重给接受者带来精神上的审美愉悦。汉魏六朝小说家搜集、编撰志人小说的标准和原则,是唐小说取自不尽的宝库。受其影响,唐小说在题材的选择上,秉着真实的精神选取素材。但唐小说家选取真人真事为素材,也对其进行虚构、加工。作品的形式看似虚诞,内容却很真实。唐小说家追求的真实,是一种人情物理的真实;在创作宗旨上,追求娱乐的审美效应。但也不纯粹为了娱乐受众,思想性寓于娱乐性之中;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再局限于只言片语。通过情节的矛盾冲突,展现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人物形象更真实,更贴近生活的本来面目。唐小说在继承中发展了志人小说。小说在生动曲折的情节中,展开人物形象的刻画,在自娱、娱人的同时,赋予小说深刻的社会蕴意。与此前的小说相比,唐小说文体的独立性更强,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言小说走向成熟,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天地。宋以后,文言小说创作在唐小说的影响下,续有发展。同时,唐小说对宋元明清的通俗小说戏曲也产生巨大影响,其中的承续、嬗变更为直接、多见。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③⑤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76页,第1361页。
⑥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38页。
⑧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33页。
2014年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公牍文与唐小说相互关系研究》(编号:2014PY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