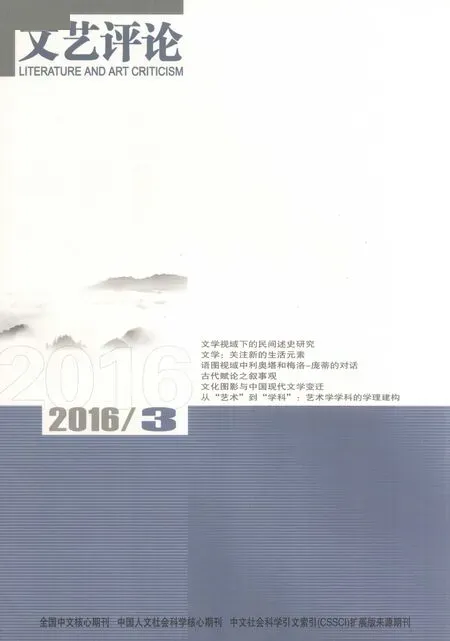“将身份放入话语中”:从话语维度谈当前身份研究的现状及趋势
2016-09-28○程毅
○程 毅
理论视野
“将身份放入话语中”:从话语维度谈当前身份研究的现状及趋势
○程毅
人们生活在世界上必然要以某种身份(identity)示人,进而对自己及他人进行定位,这样才能促使交往行为继续进行下去,从这个角度讲,思考身份问题也是思考“我是谁”以及自己在社会或群体中的角色与归属的问题。①同时,身份还是一个跨越社会学、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人类学等众多领域的学科,是极具“高度理论性和生活经验性”的问题,是“生命政治的核心”②。如今恐怖袭击、民族冲突、性别和种族歧视、贫富差距、多元文化等社会现象使人们面临越来越多的身份问题,身份俨然已成为学界热衷讨论的话题。本文首先将对身份研究的理论发展进行简单梳理,继而讨论身份研究领域的话语转向问题,之后在身份话语转向的基础上指出身份的转换并不是面具式非此即彼的替代,实际话语交往行为中的身份是混杂模糊难以界定的,是擦抹式的,身份并不存在一个稳定的核心,是众多隐性身份相互指涉的产物。
一、身份研究的理论梳理
要理解本质主义的身份概念首先需从身份最早的涵义着手。从词源学上讲,“身份”(idnetity)源自中世纪的法语identité,是相同,同一的意思,identité源于拉丁语(公元5世纪)identitatem,identitatem则源自古拉丁语idem,与梵文表示相同、同一的idam意思相似。海德格尔曾指出idem在希腊文中是“自身、本身、同一”,翻译为德语则为“同一者”③。可见,本质主义身份观显然与其词源学意义中的同一性有密切关系,并在后来衍生为身份研究中不可忽视的“认同”问题。因此,identity除翻译为“身份”外,在某些语境下也被译作“认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将这种同一性引申为“承认”(recognition),并指出身份“是由他者的承认或者说是由这种承认的缺席造成的”④,阿甘本也认为“被他人承认(recognized)的欲望与作为人的存在密不可分”⑤。也就是说,所谓身份最初便是同一性基础上的认同或承认。
早期identity作“同一性”的意思出现于“同一性法则”(law of identity)的提法中,是指一件事情或一种观念需要与其自身同一,即A=A。它源于古希腊哲学家对固定本源的追寻,在他们看来同一性是世界得以顺利运行的内在法则,是封闭、绝对、“自给自足”⑥的,是“逻辑学的基础”,没有同一性,事物之间的差异便很难区分。⑦换句话讲,同一性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基础,也是二元论思维模式的基础。
古希腊哲学家在探讨同一性时便开始将它与自我(self)以及个人(individual)这两个概念被放在一起加以讨论。到中世纪,天主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通过追问罪的来源进一步深入思考人的自由意志。他认为上帝造人时便赋予了人自由意志,使他们拥有自由决断的权利。圣奥古斯丁进而指出“没有自由意志,人便不能正当的行动”⑧。因此有学者认为正是圣奥古斯丁使“现代理论中的独立自我开始浮出水面”⑨,它使人们开始考量自身,而所谓自我认同便是这种“反思后的自我认知”⑩。
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人被放置在宇宙中心成为理性原则的代言人。个人作为“单独、独特、唯一”的统一体成为世界的主导,身份概念此时也开始与主体密切相关。在公元17世纪后,identity才真正脱离纯哲学研究的范畴,开始被从主体的角度用作“对个人尊重”的含义成为我们如今通常所说的身份。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从主体角度对身份的探讨比较具有代表性,在《文化身份问题》中他以主体为轴,将身份的发展史分为启蒙主体,社会学主体以及后现代主体三个阶段。
首先是启蒙主体。启蒙主体的核心是人,它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指导,将人视作理性的主宰者,具备判断、意识和行为能力,是先验性的主体,并且“与其自身保持连续性或同一性……这个自我的本质性中心就是一个人的身份。此后洛克进一步将个体视作“理性存在的同一”,将身份与主体的同一性、连续性紧密结合起来。他们在高扬理性的同时将个人主体意识推至核心地位。启蒙主体中的身份注重独立个体内在同一性的主体性认同,主体对外部世界拥有自主权,外部世界依自我主体意志的变化而变化。
如果说启蒙主体的身份秉承了古希腊哲学中对本质、同一性的追寻,实现了以自我为核心的内在身份认同的话,那么此后的社会学主体则完成了身份由内向外的转向,它既是现代世界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我们如今日常使用的身份概念的雏形。在产业革命影响下,个人身份更多地依赖与他者的交往关系,成为“自我与社会交互影响的产物”。于是,社会交往便成为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这种由社会关系构筑起来的身份认同则动摇了此前启蒙主体的同一性和稳定性,并使身份认同遭遇到第一次危机,也正是这次危机使人们开始认真思考自身在社会中的身份问题。
以英国为例,圈地运动和产业革命解除了此前英国劳动者与土地之间相对紧密的联系,破坏了过去稳定自足的生活方式。大量失去土地的人口涌入城市并与企业结成契约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便成为人与人交往的核心,并威胁着“过去自以为独立的人们的独立性”。同时,个人的内在同一性与这种不稳定的社会关系难免会产生认同上的鸿沟,身份则成为沟通“内在”个体与“外在”世界之间的“桥梁”,承担将主体缝合到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任务。于是,人必须以某种身份示人并努力归附于该身份的话语模式,才能得到某种社会关系的认同,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加固内在主体与外在社会联系的基础上使二者“更加对等统一”。可以说社会学主体的身份观是身份研究承前启后的阶段,它秉承此前人们对同一性身份的追寻,同时开启了一个以社会关系为身份存在前提的崭新时代。但即便如此,这种身份观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仍以追求身份同一性及内在自我为目的。
进入20世纪后,受后结构主义哲学影响,作为身份核心的主体遭到消解,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将后结构主义哲学称作“消失的哲学”,充斥着“人类的消除,意识形态的消除。缺席的结构,主体的死亡,匮乏,性欲缺损”。在主体消亡的基础上,此前的本质主义身份观受到挑战,这便是霍尔所谓的后现代主体,它不再强调身份的稳定整一,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身份的碎片化和多元性上。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对主体消解引起的身份变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身份,在日常生活中已然遭到破坏和解构。”显然,主体的消解导致人已经不再是身份的核心,在国家机器与现代社会制度的宰制下,身份化约为数字符号,识别它的关键不再是人而是作为数字幻象被储存于数据库中的信息代码,现代人的身份在数字时代也被降格为“生命体”或“纯粹的生物数据”,传统意义上的身份认同被网络、机器等现代科技下的数字认同所代替,人的面目日益模糊,并转化为一种平面化、与社群或他人无直接联系的“无人格身份”。正是在此基础上,身份研究发生了由内向外的话语转向。
二、身份研究的话语转向
如果说此前身份研究一直延续对本质主体的追问,那么身份研究的话语转向则将研究重心移至主体外部的社会交往行为。社会学家克里斯·巴克曾指出,身份“是一种语言的描述”,“是话语的构形,根据时间、地点和使用改变它们的含义”。社会心理语言学家安德鲁·麦克金利(Andrew McKinlay)则认为,由于人们每天都要面对内部自我与外部世界,身份及身份问题必然出现在人们的日常话语中,因此话语研究是身份研究的新方法,从话语入手可以考察“人们是怎样从他们自己的视角出发,用他们自己的话语为自己的身份赋予意义”。可以说,身份是对一个人的客观存在不可化约的话语描述,它建构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在这个视野中人不仅作为独立个体存在,还处在与他人共同建构的话语网络中。
目前学界较有影响的话语批评理论分别是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和福柯式话语分析(Foucauldian discourse analysis)。前者强调话语是如何影响权力和意识形态的,重在考察社会和政治不平等如何被嵌入我们的话语当中,研究被视作具备改变和挑战这些意识形态权力的话语元素,并通过话语塑造人们的日常生活。后者则吸取了福柯话语理论的养分,并深刻影响了之后针对身份问题的研究理路。
法国哲学家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将话语视作脱离了抽象文字和语言符号的“系统化组织人们言说之物的运作”。也就是说,话语是“实际应用而不是作为抽象体系的语言”,是被还原到具体语境中的言语行为,是人们进行交流、沟通和理解、认知的单位,被某种社会目的所决定的交际行为。在此基础上福柯进一步扩展了话语的内涵,认为整个世界都处在交织错杂的话语网络中, 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被话语标记、交织的世界”,并将话语的性质重新界定为“陈述的独立集合”和“用于解释某些陈述的规则化运作”。也就是说,一方面,福柯在并未放弃话语独特性的前提下将所有得以言说于现实世界的陈述都称作话语,强调正是话语的独特性使一种话语能够与其他话语区分开来。另一方面,福柯认为话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规训本质,通过探讨话语是通过怎样的运作方式将人们纳入到自己的法则之中,指出一种话语就是一套系统性的行为规范或思维方式。
在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下,一大批语言学家开始摈弃传统抽象僵化的研究模式,转而从具体话语语境入手来探讨身份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社会结构主义分析(social constructionism)。这种分析方法因受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而具有稍许权力批判的意味,持该方法的学者认为身份既不是先验给定的,也不是建构行为的产物,而是一个过程。他们借鉴语言学中的话语分析方法,摈弃早期对先验生物学意义上本体论身份的追逐,将注意力集中在探讨身份在社会交往行为中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思考更加“私人化,碎片化”的身份问题。社会结构主义身份研究以霍尔为代表,他将众多当代学者对身份的思考归纳为“去中心的主体观”,指出身份是意识形态、他者/镜像、语言、权力话语以及表演行为建构的产物,并最终指出“后现代身份不再是本质、永恒的,而是流动的盛宴”,是不同权力话语共同打造出来的,由于后现代主体丧失了连续性,身份于是也不再是变动不居的,以往统一、完整、稳固的身份“只是一个幻象”。
二,归类与成员界定进程分析(the analysis of processes of categorization and membership definition)。这种方法受社会学家哈维·萨克斯(Harvey Sack)的影响,尽管萨克斯不是语言学家,但他却是最早研究人们日常交往语言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对话交往行为中的相邻语对理论(adjacency pairs),将交往行为进一步细化分类,指出交往行为中的话语往往是成对出现的,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的对话行为是有选择性的,而不是完全随意的。受萨克斯启发,归类与成员界定进程分析认为身份的建构与自我和他者交往中对行为分类和界定的接纳或排斥有关,当自我认为与他者的交往行为有利于身份建构时,他便会主动选择与其交流,反之则拒斥该交流行为。于是身份不仅仅被视作话语的再现,而且被视作各种语言或非语言行为展开的“操演、表演和具象”,身份也不再是由话语单向生产出来的,而是二者相互选择的结果。这种方法在具体研究中基本以考察交往行为中话语对个人身份塑造以及个人身份对话语的选择为主,如安娜·德·芬娜(Anna De Fina)等语言学家主张从具体语境入手考察身份问题,指出身份并不是言说者的附属品,而是通过交往实践在具体语境中运用语言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此外,还有学者通过研究工作谈话中的趣闻轶事对个人与集体身份的具象化,指出个人身份的表演方式受他所处的群体行为的改变而不断调整,工作环境中的群体话语制造出一套规则体系,主导甚至塑造了在该话语体系下的个人身份。
第三、“自我”的反本质视域分析(anti-essentialist vision of the“self”)。这种方法多用于性别身份和话语心理身份研究中,其核心在于用反本质主义的方式思考自我身份。以性别研究为例,这种方法认为性别身份既不是生来就有的,也不单纯是社会建构的,它一反此前女性主义理论对女性主体的强调,通过消解性别二元论来消解性别身份,其代表人物是朱迪斯·巴特勒。在她看来,传统女性主义对女性身份的诉求依然寓于二元性别秩序之中,她指出身份是一种压制形式,语言习惯和社会话语控制着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个人通过将男性或女性应有的性别规则理想化并对这种性别身份进行模仿,因此,我们的性别表演实则是一种复制、模仿下的话语塑形,性别身份只是针对“某个幻想的幻想”,性别只是“一种行动”,在性别表现的背后“没有性别身份”。
除性别研究外,这种“自我”的反本质视域还被运用于话语心理分析。与巴特勒不同,语言学家班维尔(Bethan Benwell)并未彻底消解身份,而是通过结合多种不同的话语语境——如电话交谈、采访、故事讲述等——从最宽泛的意义上对身份进行考察,展示身份在言说和书写中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在其主编的《话语与身份》中,研究者突破了以往对身份单一的研究模式,甚至将研究领域延伸至赛博空间,指出赛博空间取消了传统主体间性交流方式,将以往言说基础上的身份建构取代为赛博空间中的书写建构。
三、作为话语踪迹的擦抹式身份
在身份话语转向的基础上,我们基本上可将身份视作交往行为的产物,是人们在不同语境中通过话语运作的结果。由于话语的运作过程并不是前后更替的过程,因此很难找到话语的起源,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或标志性事件意味着某种话语的形成。以社会对疯癫的界定为例,从最初被视作神的眷顾到18世纪被视作非常态的存在直到19世纪后成为病理学意义上的症候,疯癫的界定其实是一个话语不断变化的过程,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变化并未完全抹去之前的界定,而是选择性地将之前对疯颠的界定包容其中,比如在今天依然有许多人会将疯癫视作某种神灵附体的产物,即便他们也不排除将之视作病态。可见,话语的存在并不是由一套话语替换另一套话语,而是不断从已有话语系统中抹去某些元素,同时纳入新元素,形成新话语,也就是说,话语所容纳的不仅是在场的共时性话语,它还包括缺席的历时性话语踪迹,每一套话语体系都与其他话语体系相互交织关联。
因此,建基于话语之上的身份才被后现代理论家视作多元流动的,然而这并非意味着身份是人们社会交往中的面具,身份的转变也不是一副面具简单替换另一副面具。面具的更替不存在任何踪迹,面具的摘除与佩戴意味着身份的绝对转换,在该转换过程中,身份的在场与缺席都是绝对的,而这显然与话语中实际的身份运作并不一致。打个比方,一个人既可以是一名女性,也可以是一名美国公民,同时她可以出生在中国,在大学拥有教职,是一名基督徒,业余摇滚乐手,素食主义者,她同时拥有众多身份,这些身份因她所在的不同话语环境各不相同,但这些身份并不是以面具的形式交替转换,当她以教授的身份站在讲台时,她的其他身份将被隐去,然而这些身份并未全然消失,在该过程中她将受自己女性、素食主义者等身份的影响对授课内容做出调整,甚至将主宰她对讲授内容的选择。在这一系列身份操演(perform)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稳定的核心身份,身份转换并非面具式的取而代之,而是混杂模糊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必然生活于众多不同社会话语中,身份是对人的存在这个客观事实不可化约的话语描述。身份不仅基于与他人互动交往之上,而且也是诸多身份相互影响的结果,当面对某种状况或情境时,这些由不同话语塑造出来的身份便会参与到他们的交往行为里共同而不是单独发挥作用,所以,以多元与流动为身份划界,以面具隐喻为身份定性的做法,只能将身份简单化和模式化,在此我们不妨将这种身份转换的方式视作擦抹行为,身份转换的外在表现便是这个擦抹的过程。
此处的擦抹类似于书写文字然后将其划掉并同时保留二者,德里达曾将之视作“对自我以及自我在场(presence)的抹消”,它意味着“没有终结、没有出现、也没有被遗忘”,将它书写出来意味着它确实存在,抹去则因为它或许并不准确,但由于这种存在是难以取消的,于是才用擦抹的形式保留下来。也就是说,擦抹的身份令身份的在场与缺席同时存在,既不会威胁在场也不会完全取代缺席,是“在场缺席的标志”和“始终缺席的在场”,从而为身份制造出一个在场的幽灵。身份的这种擦抹特性一方面拒绝了所有以非此即彼二元模式对身份的粗暴界定,并有效防止身份内部产生一个稳定的核心,另一方面也形象地展示了在实际交往行为中身份亦此亦彼的存在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的身份视作显性身份,受到擦抹的身份隐于显性身份之后,我们将其视作隐性身份,它以显性身份的“他者”或“增补”的形式与其相互指涉彼此影响,显性身份是多重隐性身份的在场投射,因此并不存在一个终极意义上的身份,任何一种身份只是无尽身份链条上的一环,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中。于是以往学者为身份定义的努力经常无疾而终,甚至使身份的涵义愈发模糊。正是身份的擦抹特性使理论界无法对其加以明确定性,它以身份自身意指的不确定和身份之间的相互指涉使任何对其进行界定的企图均无功而返。也正因为此,身份本身往往是矛盾甚至自反的,由于身份的擦抹特性使得显性身份同时集合了因擦抹行为而缺席的身份幽灵,这些缺席的身份幽灵与显性身份之间并非同一吻合关系,隐性身份作为显性身份的补充,为它提供参考坐标,甚至会以完全相反的形式阻碍显性身份在社会交往中的表演性行为,这便构成了身份的矛盾甚至断裂,从而也使身份得以避开任何中心性的界定和二元论的简单划分。
以身份的认同与差异为例,后结构主义理论认为由于后现代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稳固、有序的,而是多元、游动、错位的,于是,身份实则是差异性而不是认同性的,也就是说身份认同这个提法在后现代理论中是一个伪命题。比如美国社会学家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便将身份与认同割裂开来,认为“身份”更强调差异性,而“认同”则强调同一性,从而完全剔除了身份中蕴含的同一性原则。霍尔曾表示,即便相同民族的民族身份也不可能是认同性的。他以法兰西民族为例,通过历史考证指出法国人其实是凯尔特人、伊比利亚人以及德国人的混血,因此今天法国人的民族身份其实是由各种不同民族身份缝合的产物,于是建立在同一性基础上的民族身份认同便是虚假而不可靠的。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却指出,即便是差异性的身份仍无法摆脱对同一性的归附。他考察了英国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文化,并以英国中产阶级青年运动为例,指出青年运动摈弃传统绅士观念与道德束缚,在言谈中加入脏字,抛弃西装等服饰,取而代之以牛仔或紧身皮衣,以标新立异的装扮挑战了英国传统价值观世界观,凸显青年差异性和多样性的身份和强烈的自我意识。但霍布斯鲍姆强调,即便如此青年们依然“摆脱不了同辈及时尚的压力,众人的一致性反而不比以往低”,也就是说,这种强调差异性的身份实则只是针对特定身份而不是所有身份的差异,它依然是以对某种身份的认同为基础,其参照仍然是那个隐性的同一性身份,正是在认同基础上,他们的差异性才得以体现。
可见,由于当今身份研究的方式已然从传统的内部主体研究转为外部话语研究,研究重心也转移到挖掘不同话语语境中身份的不同生产方式,展示不同层面身份相互指涉后的身份表现,甚至通过将身份“行为化”来消解身份概念,那种仅将着眼点放在身份的显性层面并屏蔽其隐性层面而将身份问题平面化的做法必将忽视由众多话语共同建构起来的身份内部的矛盾性与独特性。显然,身份既不会永远趋同也不可能永远趋异,任何对身份问题的定论都将有失偏颇,就身份的探讨还应从具体话语入手,不仅考察显性身份的特点,还要挖掘显性身份背后缺席的身份幽灵,只有这样才能把握身份本身所蕴含的独特性与矛盾性,从而推动身份问题在文学及文化领域的深入研究。
①查尔斯·泰勒在他的《承认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中曾指出,“身份表示一个人对他是谁以及他作为人在本质上的界定性特征的理解”。see Taylor,Charles.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from Charles Taylor(eds.),Multiculturalism: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4,p.25.
③马丁·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8-29页。
④Taylor,Charles.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M],from Charles Taylor(eds.),Multiculturalism: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25.
⑤19○Agamben,Giorgio.Nudities[M].trans.David Kishik and Stefan Pedatell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46,p.52.
⑥Fumaroli,Marc.“I is an Other”:Delusions of identity. Diogenes[J],March 1997,vol.45,177:p.111.
⑦Craig,Edward.(eds).The Shorter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435.
⑧奥古斯丁《独语录》[M],成官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⑨Lemert,Charles.“A History of Identity”[C],from Anthony Elliot,(ed.).Routledge Handbook of Identity Studies.London:Routledge,2011,p.7.
⑩Giddens,A,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p.53.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