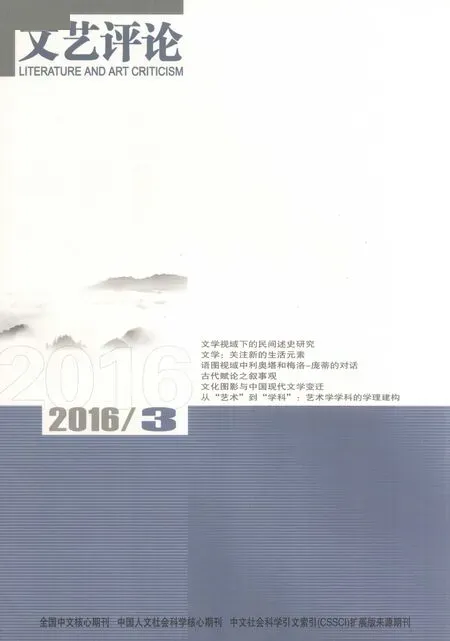梁鸿非虚构写作的乡土关怀
2016-09-28由婧涵
○由婧涵
梁鸿非虚构写作的乡土关怀
○由婧涵
在非虚构作品中,学者梁鸿的《中国在梁庄》(2010年出版)与《出梁庄记》(2013年出版)是两部重磅力作。作者怀着对农村那片土地强烈的爱与责任,以对乡村、农民的理解与关怀为出发点,通过口述实录、现场调查等方式讲述了一个个具有典型性的农民的人生故事,以及他们在村庄中与走出村庄后的生存、情感及所面临的问题,真实地展现了农民的生存状态与中国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危机。在看似客观的笔触之中,凝聚的是作者浓浓的乡土情怀。
一、生存关怀
《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是梁鸿对自己的故乡进行的纪实性乡村调查后写成的,记录了当下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体现了梁鸿对农民深切的生存关怀。梁鸿曾说,“在《中国在梁庄》中,既有原生态的人物自述,也有我的观点表达,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呈现乡村原有的生存状态。”①“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能使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村庄所承受的悲伤,慢慢浮出历史地表。由此,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的关系。”②梁鸿做到了这一点。她让梁庄走进了受众的视线之中,让农民的生存问题受到了关注。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最为关注的是留守老人、留守妇女与留守儿童三代人的生存问题。五奶奶、芝婶等这些经历了战乱、贫困的老女人,依然不能享受现在的温饱生活,而是要为在外打工的子女照顾孩子,她们要忍着自身的病痛种地、做饭,还要每天往返几次去接送孩子上学。劳累还在其次,她们还要承担巨大的责任,如五奶奶的孙子溺水身亡,她的悲伤与自责是别人无法感受到的,但她还要承受儿子、儿媳的埋怨与指责。书中还写到了留守女性的情感压抑,服毒自杀的春梅、被打工的丈夫染上性病而上吊的小媳妇等等,这些悲欢离合令人心痛,五奶奶、春梅的形象是无数乡村留守老人和妇女的真实写照,谁能来安抚他们的绝望、伤痛与无奈呢?
在《出梁庄记》中,梁鸿把目光投向了农民工。书中共记录了51位农民工的打工故事。为了生存,梁庄的农民背井离乡,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新疆、云南、广州、内蒙,甚至到国外打工。他们有的当保安、做传销,做小生意,更多的是出苦力,当油漆工、搬运工,收废品,卸煤,翻沙,总是干最脏最累的活。然而他们虽然来到了城里,却无法与城市融为一体,只是城市的寄居者。他们不愿意再回到农村,但又无法被城市真正地接纳,处于一种尴尬的两难的生存处境。农民工的生活漂泊、艰辛,但他们不愿放弃。与其说他们的生命是多么顽强,不如说他们是别无选择。那些最后回乡的打工者往往都是因受伤、患病,或照顾孩子等不得不回。在书中,有受访者提到,只有在生病的时候他们会想到回梁庄治病,因为在城里他们没有医保。其实在城里,他们缺失的不仅是医保,还有购房权利、孩子的受教育环境、升学权利等,这些缺失使他们总觉得低人一等。生存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停地奔波劳作。即便工厂污染超标,即便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正遭受威胁,他们仍不放弃在城里的生活。他们寄居在城里最狭小肮脏的角落,顶着没有教养、扰乱治安等多重罪名,没有尊严地顽强地生活着。
梁鸿虽然也是从梁庄走出来的农民中的一份子,但她毕竟在首都生活得久了,重新回到故乡,她感到陌生和隔膜。她尽量让自己能够与村民们平等对话,尊重他们,关怀他们,取得他们的信任。正是由于有这种诚挚的态度,村民们才能向梁鸿吐露心声,我们也才能在梁鸿笔下看到中国真实的村庄,看到城里真实的农民工。这种诚挚的态度也是我们社会对待农民应有的态度。
梁鸿写这两部作品的目的不是要同情农民的遭遇,或者谴责他们的陋习,她的目的是要引发社会关注农民,关注乡村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生存问题。梁鸿对乡村的一切忧虑与反思都是以爱与关怀为前提的。
二、心灵关怀
在梁鸿的两部非虚构作品中,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她不仅关注农民的生存问题,更关注农民的心灵问题。“梁鸿的写作在这方面做出了出色的示范。她的精神诊断既是整体性的,也是个体性的。”③“几百个活生生的精神个案,勾勒出中国的精神状况。迷茫的,低沉的,冷漠的,孤独的,算命的,信教的,迷信的,各种精神现象都有典型性。这两本书中提到很多人的精神状态,都是麻木和孤独的,除了发财之外,很少有其他的价值指引。”④
在《中国在梁庄》中,作者用一章的篇幅来写乡村的留守儿童,写梁庄的小学。青少年是农村的希望,梁鸿把目光投向他们,自有深意。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令人堪忧的农村青少年的生存现状。基础教育令人堪忧,昔日的小学已经被废弃,甚至变为养猪场。在书中,梁鸿道出了自己的忧思,“让一所学校消失很容易,也很正常,因为有许多实际的理由,人口减少、费用增多、家长嫌差等等。但是,如果从一个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它又不仅是一所小学去留的问题。对于梁庄而言,随着小学的破败,一种颓废、失落与涣散也慢慢弥漫在人们心中。在许多时候,它是无形的,但最终却以有形的东西向我们展示它强大的破坏力”⑤。梁鸿的担忧颇有道理,学校是文化的象征,小学的消亡导致村庄的文化氛围缺失,村民的精神生活枯竭。梁庄小学办得好时,村民的精气神也足,他们对孩子的未来充满了期盼,希望他们受到更好的教育。可是现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与文化氛围的缺失导致孩子们都不愿意上学,更何况还有上了大学的孩子也找不到工作,孩子们逃学、逃课,只想着去打工。这种厌学情绪弥漫在乡村,它使人们对教育失去了希望,对孩子的未来失去了寄托。梁鸿对此非常痛心,她在书中写道,“如果一所小学的消失是一种必然,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重新把这已经涣散的村庄精神再凝聚起来?能够重新找回那激动人心的对教育、文化的崇高感与求知的信心?”梁鸿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农村学校教育的缺失,受伤害的不仅仅是农村的孩子,受伤害的是农村的未来和国家、民族的未来。因此,农村孩子的精神成长应该是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
《中国在梁庄》中还写到了王家少年,由于看了黄色碟片,引起了青春期性的冲动,把82岁的刘老太杀害后强奸,他也为此被判处死刑。村民们大多对王家少年恨之入骨,他们认为王家少年手段残忍,道德败坏,应该被判处死刑。而梁鸿关注的却是孩子的心灵健康,“没有人提到父母的缺失、爱的缺失、寂寞的生活对王家少年的潜在影响,这些原因在乡村,是极其幼稚且站不住脚的。而乡村,又有多少处于这种状态中的少年啊!谁能保证他们的心灵健康呢?”“谁能弄清楚,那一个个寂寞的夜晚在少年心里郁结下怎样的阴暗?谁又能明白,那一天天没有爱的日子汇集成怎样的呐喊?而又有谁去关注一个少年最初的性冲动?”⑥的确,我们对乡村少年的心灵关怀确实太少,尤其是日渐增多的留守儿童,他们成长中的精神困惑被长期忽略。“梁鸿在坦诚、冷静地记录客观事实的同时,也加入了自己的追问与呼号,体现出强烈的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彰显了其高度的忧患意识与悲悯情怀。”⑦
令梁鸿痛心的还不止于此,《出梁庄记》中还写到了被强暴的9岁小女孩黑妮,这样一个小孩子却要用一生去承受这样大的伤害,这件事令梁鸿愤怒,也令她深感无力。她不知该如何让孩子的心灵走出这个阴霾,不知如何抚慰她受伤的心灵。在贫瘠落后的农村,很少有人关心孩子的精神世界,这是比贫穷更为可怕的缺失。包括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村人也是如此,《出梁庄记》中的正林是一名专科生,后又到名牌大学进修,毕业后成了服装设计师,但白天奢华的工作条件与下班后蜗居的生存条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落差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物质上的贫穷使他们找不到精神的归宿,他们带着没有灵魂的躯壳在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奔波劳碌。这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应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三、生态关怀
梁鸿在这两部作品中对农民生存的环境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因为生态与生存是息息相关的两方面,生态的优劣决定了农民的生存质量。在梁庄城镇化过程中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生态问题,当然,这不是梁庄一个村庄的问题,它是中国所有乡村都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当下中国乡村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提到乡村,我们脑海中就会呈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风光,然而在《中国在梁庄》中,我们看到的却是“黑色淤流”,曾有小鸭小鹅惬意嬉戏的坑塘,曾经清澈得可以洗衣、洗菜的坑塘,曾经长满荷花,风吹过,清香满村的坑塘,曾经有许多青蛙欢叫的坑塘,不仅变成了散发着臭味的垃圾场,里面注满了乌黑发亮的工业废水,上面漂着一层绿藻和密密麻麻的苍蝇,而且已经随着房屋的建造被挤占得所剩无几。曾经盛产蔬菜、粮食的肥沃的黑土地,现在因砖厂烧砖而再也无法生长任何植物。童年时在其下玩耍的桑葚树也不复存在,甚至连小学校也变成了养猪场。梁庄的生态环境变得令人绝望。“绕着砖厂的是无数不均匀的大坑,它们或在树林旁边或在房屋后面,或紧靠河坡。因为挖土时太靠近树,有些树已经有些歪斜了,盘曲的根部裸露着。而高高的河坡,它曾经像城墙一样挡住了汹涌而来的河水,如今已经被削得几乎和地平线一样了。”“但是,我又能指责谁呢?如此破坏环境,如此不注重生态平衡,如此不重视自己的生存质量?”⑧连番发问,梁鸿对乡村的生态之痛可见一斑。这不是梁鸿一个人的痛,它是所有乡村的痛,所有农民的痛,整个中国的痛。
在《中国在梁庄》“河的终结”这节,作者写到了河淹死人的事件。为什么每年都有人在这条河里淹死?原来是好多挖沙厂在这一河段挖沙,在河底留下了很多很深的沙窝,人一下水就会被漩涡卷走。和河水相关的还有上游的造纸厂、化肥厂排放污水问题。面对这一切生态灾难,梁鸿说出了自己的忧虑,“河流,一个国家的生态命脉,一个民族未来的保障,但是在过去十几年中,我们却把它提前终结了。我们生活在干涸、散发着臭味、充满诡异气息的河岸两旁,怀着一种绝望、暗淡和说不出的恐惧。如果这一切再不改变,大灾难要来了,或者,其实已经来了”⑨。梁鸿毫不讳言自己的绝望与恐惧,在她眼里,河水死了,村庄也就死了,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就是在断绝自己的生路。
梁鸿的忧虑应引起我们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在中国,有无数个生态遭到破坏的乡村,有无数条被污染的河流,有无数村民失去了绿色的家园。作为一个学者,梁鸿这种敢于直面现实的精神与勇气是可敬可佩的。她深入面临生态灾难的乡村,把不被世人关注的乡村生态困窘揭示出来,这种诚挚的生态情怀令人感动,启人深思。
梁鸿的梁庄系列非虚构作品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梁庄这一个村庄的生存状态,而是整个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虽然这种呈现还不是非常全面、深入,但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这是一个学者“接地气”的写作,它使文学逃离书斋,走近生活,贴近现实。这也是一位来自乡村的学者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体现,她要为乡村代言,要为农民代言,让他们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关怀。
①梁鸿、张丽军《梁庄:乡土中国的现在与未来——梁鸿访谈录》[J],《百家评论》,2015年第2期。
②靳晓燕《归乡,找寻精神家园——〈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访谈》[N],《光明日报》,2011年1月18日13版。
③④师力斌《打开一座村庄呈现中国——读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J],《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6期,第137页。
⑤⑥⑧⑨梁鸿《中国在梁庄》[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第70页,第42页,第52页。
⑦任雅玲《文学视域下的民间述史研究》[J],《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6期,第21页。
[基金项目: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文学视域下的民间述史研究”(编号:14YJA751019)]
作者单位:(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