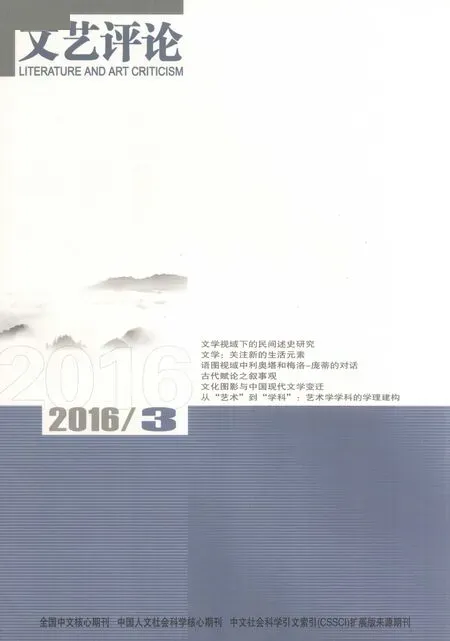回归诗性与真实性的非虚构书写
——以张郎郎的作品为例
2016-09-28王向荣
○王向荣
回归诗性与真实性的非虚构书写
——以张郎郎的作品为例
○王向荣
1943年出生的张郎郎曾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文革”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师,现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张郎郎写有两部非虚构作品,即《大雅宝旧事》(2004年8月由文汇出版社出版,2012年1月由中华书局再出修订版)与《宁静的地平线》(2013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大雅宝旧事》记叙了上世纪50年代,作者孩童时期随父母居住在北京东城区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中央美院宿舍时期的生活片段和见闻。《宁静的地平线》主要讲述的是“文革”给作者留下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张郎郎说:“我相信每个写历史的人都有自己的单镜头,像纪录片一样,以后的历史研究者把这些充满真实细节的单镜头综合起来,那个更有价值。”①其实,非虚构作品不仅具有史学价值,也同样具有文学价值。张郎郎的两部作品形成对比式单镜头非虚构书写模式,《大雅宝旧事》中张郎郎建构了一个理想主义的童话世界,运用儿童视角和“童话”语言展现唯美纯净的童年及童趣,而《宁静的地平线》中则选用成人视角和旁观者讲故事的口吻对文革苦难娓娓道来,同时引发对人性善伪的拷问。
一、童年温情回眸的唯美表达
张郎郎的《大雅宝旧事》来自一个孩子的纯真记忆,文学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并存,且能从中获得一种奇特的审美愉悦和历史沉思。张郎郎说:“《大雅宝旧事》和我过去写的文字不太一样,是我在文字尝试方面,走出新的一步,可能和自己心态的变化也有关系。在这本书里,讲了许多童年时代的朋友,我们有共同的回忆,共同的故事,共同的梦。”②“我的大雅宝逸闻,您大可以完全当童话听。”③于是,张郎郎的“床头故事”中有动人的诗篇和美丽的童话,他运用儿童视角带我们熟悉了住在大雅宝甲二号的那些可爱的大人和孩子,鲜活生动地描述了美术大师们作为平凡人的生活化的一面,但是这一切的欢快、高兴、热闹的理想时代在1957年就煞住了车,真正成了一个永不复返的孤本“童话”,让人读来泪中带笑,诙谐中见沧桑。
1.以童心感受世界
北京“大雅宝”胡同甲二号是上世纪50年代中央美院宿舍所在地,国宝级美术大师聚集于此。因为张郎郎的父亲张仃是我国著名美术设计家、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之一,所以张郎郎也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乌托邦式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书中以儿童视角切入,描绘了“大雅宝”那一圈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和故事,如那些暑假前后的玩乐日子,院子里的葡萄架,那些可爱的教授先生们的趣事,不知所踪的民间艺人等。《大雅宝旧事》中的很多故事都是围绕张郎郎的家庭展开的,这种以自己家庭为线索展开并带起其它故事的非全景式单镜头描写,符合非全知全能儿童视角的叙述要求。
《大雅宝旧事》首先描述搬家的线路,沿途以吃为线索进行撰述,每搬到一个地方,给作者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吃到了不同的特产,其中包括白城子的白菜粉条豆腐汤,蒙古的酸奶干,哈尔滨的咖啡糖,佳木斯的高丽糖,沈阳的花生米、口香糖、牛肉干、柠檬水等。大人们沿途艰苦的颠沛奔波映射到儿童的视角中成了美食游历过程,尤其是描述穿过草原到了蒙古的沙漠遇到了骑马持枪的人,作者以一个儿童旁观者的角度认为是一场好莱坞的电影镜头:“我老想顺着轱辘多看点镜头,可大人老按住我的脑袋,等让我爬起来看的时候,电影早完了。那些有枪的人和一些骑马的人已经打完了,玩了个不亦乐乎。为了热闹,那些人临走还不时扔点手榴弹什么的。”④作者选择儿童视角,运用举重若轻的笔法,以调侃的语气进行叙述,以童心感悟世界,以童趣观察生活。大雅宝的那段童年经历在张郎郎看来至今仍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回忆中充满了人性的美好善良,故事中的童心和童趣带给人的是精神上的愉悦,那段美好的回忆也成了永远一去不复返的孤本童话。所以在《大雅宝旧事》中叙事的情感基调是甜蜜而感伤的,也为那段特殊岁月写下了不同寻常的文学证词。
《大雅宝旧事》中除了运用儿童视角审视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周围人们的生活外,还详细记录了在大雅宝的那段时期孩子们玩的各种至今已经消失了的游戏,在叙述中为我们营造了乌托邦式的童话世界,同时也建构了丰富多彩且不可复制的童趣空间。在书中张先生运用大量的篇幅为我们建构了大雅宝孩子们天堂式的乐园,其中详细介绍的各种玩具和游戏也成了上世纪50年代儿童游戏史的活化石,今天看也是比较珍贵的资料。“小蘑菇”的“模子”玩具、面人汤的面人以及暑假前后玩的拍洋画、弹玻璃球、逮蜻蜓、招蝴蝶、粘知了、挖知了猴、斗蛐蛐、抓蝙蝠等今天已经少有人玩的游戏。其中尤其详细介绍了蛐蛐儿、蜻蜓、知了的种类以及斗蛐蛐和捉知了的过程:“黑蝈蝈叫驴驹子,多么形象!和小型的叫驴一样,也那么黑,嗓门也那么大,也那么欢蹦乱跳,不叫它大尾巴驴驹,就真委屈了。”⑤张先生说当时的孩子都到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年纪,每个人都是“面茶锅里煮鸡子——犯浑的混蛋”,幽默的说自己和同龄的小朋友“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儿”⑥,用白描的手法详细介绍逮蝙蝠的过程:“成群的孩子,每个人都脱下一只鞋,光着一只脚,抬着小头,紧盯着夜空中呼啸而过的蝙蝠群。当那群黑色闪电向孩子们俯冲过来的时候,只听大生子一声喊‘燕巴虎,钻鞋喽’,其他孩子跟着同声呐喊,同时手中的鞋都抛向天空,形成一个飞鞋阵。”⑦这种游戏只能凭借作者的描述,我们运用想象还原一下,在今天已经完全看不到了,当时的孩子是多么快乐,多么无忧无虑,这种童趣在经历了人生的大劫难及异乡漂泊后更有“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几多风雨”的感慨。
张郎郎说自己一直都很怀念大雅宝,并且把它看作是多年劫难和漂泊中一份不可多得的温馨,是因为大雅宝大院中人与人之间的那份真诚、那份善良,每个孩子不仅是自己家的,也属于其他家,属于这个大杂院,众多像李苦禅、李可染、董希文、黄永玉这样的国宝级艺术大师不但有学识,且谦虚有爱心。张先生描述中秋节黄永玉请大家吃葡萄的场景:“细心的人会看到这些葡萄和藤子之间都有细细的红线绑着。原来这又是黄叔叔的一个花招儿,这些葡萄都是他自己买的,为的是请全院的小孩儿都来参加中院的中秋葡萄月饼晚会。”⑧张郎郎用诗一般的温情语言为我们描述的童趣空间是带有理想主义的大雅宝,既给生活注入艺术情趣,也享受了融洽的人情之美,是一个童话世界和人间乐园。
张郎郎把童稚时的每一件逗事儿都描写得淋漓尽致,并尽最大的努力去发掘其中的乐趣所在。但这一切的美好,在“文革”时都被挤成碎片,所有乌托邦式的美好理想一夜之间被磨成齑粉。但也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温馨童话作心理铺垫,所以在经历了十年牢狱折磨之后,张郎郎仍然能以旷达释然的心态去描写一部这样的孤本童话。张郎郎并不刻意去营造一个理想主义的乐土,他希望用自己儿童视角的单镜头去记录上世纪50年代在大雅宝的艺术家和孩子们的童话般的生活,我们透过大雅宝的童年或者可以些许管窥到我们国家的青涩童年。
2.以童言书写生活
在《大雅宝旧事》中张郎郎是这样定位自己的:“我从小就糊里糊涂掉进一个童话王国里,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糊涂人,人家都不看童话了,我还在童话中生活。”“我的童话底子伴我度过多少长夜漫漫,好处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坏处是心理年龄严重滞后。”⑨这里的童话指的就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生活方式,张郎郎的《大雅宝旧事》中除了运用儿童视角审视建国初期的中国社会状况以及大雅宝胡同的生活外,还在书中运用细节描写建构了众多的儿童游戏以及无忧无虑的理想国式的童趣空间。而这一切都是运用儿童“童话”般的语言来表述的,这样既符合儿童视角的叙事策略,也显示出张先生高超的语言功底。
《大雅宝旧事》以童言书写生活,语言率真自然、天真活泼。张先生形容董希文家孩子董沙贝哥俩的衣服“要样有样,相当威风,同时还非常实用,无论和大洋宜宾胡同的孩子土坷垃大战,还是到豁子外去逮蛐蛐儿,这身行头再合适不过。无论跌打滚爬,还是上房揭瓦;无论钻铁丝网,还是扯喇喇秧,别的服装绝对不灵。”⑩语言押韵流畅,富于节奏性音乐美。小伙伴们要到大雅宝以外的地方逮住最厉害的巴厘蛐蛐儿,大家信誓旦旦的说:“咱们人穷志不短,马瘦毛不长,远征豁子外,踏平鬼子坟地,一定逮回来真正的好蛐蛐儿,不能让小蛮子和春英那么得意。”语言不但京味儿方言化且口语化,短句节奏明快,运用纯粹北京胡同的京味儿语言来叙述更显得真实亲切。简单的短句结构,致使叙事节奏比较明快、活泼,朗朗上口,这种童趣语言具有成人语言所不具备的特殊美感。张先生也是希望通过孩子般不受世俗和社会熏染的纯净心灵,把当时最原始、最真实的情况记录下来,不做文学加工,希望对将来历史研究者有所帮助。这也是史学家们宏大的历史叙事中的一种真实的微观展示,这些散落在民间的历史记忆对正史是一种细节真实、个体生命感极强的补充。
张郎郎也用童言为我们重现了一个质朴、温暖的大院,他常常把成人视角中极为严肃的事件用比较调侃的语气,诙谐平和地呈现出来。例如叙述著名的热带病学专家李宗恩、油画家李宗津曾拒绝胡适等人去台湾的邀请、诚心留在国内奉献,后来被打成右派,李宗恩被迫害致死。这件历史性的悲剧张郎郎用调侃的语气说北平的地下党为留下不可多得的人才而高兴,但是“八年之后,这兄弟俩双双被打成右派。从此入了另册。历史老人开起玩笑来真是不含糊,让一个艺术精湛的医学专家,一个有天赋的油画家,这么兄弟俩,就因为相信了一个童话,都成了八大山人——哭笑不得”。语言机智、犀利、幽默。张先生以儿童视角、儿童语言把沉重的历史灾难以诙谐平和的笔法举重若轻地展现出来了,文字接近化境,近似于平静地娓娓道来,不带一丝不平之气,于从容宁静之中显示出超凡的语言功力。
二、文革人道灾难的个体见证
张郎郎的《宁静的地平线》主要讲述在1957年童话般的美好生活戛然而止之后的生活,尤其是“文革”期间,张先生经历了十年的牢狱磨难,被无辜判处死刑,甚至曾经被押上刑场,亲眼目睹了无数像遇罗克、孙维世、金豆等无辜生命的被揪斗、游街、示众,折磨,直至被处决。张郎郎用近乎碎片式的记忆模式见证了那个特殊时期人们对自由和尊严的美好向往,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卑琐、邪恶,以及面对正义被无情践踏时的冷漠与无情。张郎郎并没有以愤怒甚至控诉的笔调来叙事这一切灾难,而是用闲聊八卦的鼓书艺人的写作方式,津津有味地打捞着自己的苦难记忆。他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似乎事不关己的鼓书艺人,仿佛在那乐呵呵地扯着前朝的闲篇,心态平静、自然、逍遥,似乎言语间还有些自得其乐,沉醉于讲书的乐趣之中。
1.平静再现个体伤痕
在《宁静的地平线》中金豆等众多无辜人的死去,个体命运在强大的历史环境与政治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脆弱、无力、悲哀,是整个时代的个体伤痕。而张郎郎却以似乎旁观者的“鼓书艺人”说书侃大山的口吻,为我们再现那个特殊年代的个体伤痕。张郎郎力求平静地叙述自己真实的经历,既不是声色俱厉的控诉,也不是唯美的不动生色的抒情,而且还时不时地揶揄一下荒诞的岁月中那些荒诞的人和事。
同是文革记忆,张郎郎的《宁静的地平线》和巴金的《随想录》、季羡林的《牛棚杂记》以及陈凯歌的《少年凯歌》不同,巴金、季羡林、陈凯歌等“见证文学”基本描述“文革”给个体和整个社会带来的灾难,叙述的笔调带有控诉、痛苦等情感基调。张郎郎曾感受过人生中最真挚的温暖,后来命运又让他感受了最深刻的绝望,所以不仅张郎郎的故事与众不同,他讲述故事的语调也耐人寻味。在《宁静的地平线》序言中直言自己在书中讲的故事是自己“‘看到的’或‘以为的’,都是单镜头的管窥之见;要么就是道听途说,觉得是那么回事儿,就这么组成了故事。我这么一说,你那么一听。千万别指望在我故事里找历史,找哲学,找教益,顶多就是有点意思”。他把自己定位为事不关己的鼓书艺人,似乎在那乐呵呵地扯着别人的闲篇。这种宣言和定位让读者以为是“荒唐言”,但字字都透着作者的“辛酸泪”,用轻松、调侃的笔调去描述那段黑暗残酷的经历是劫后余生的看破,也是大智若愚的表现。
张郎郎像一个说书艺人一样,以臻入化境、富有幽默性的调侃文字,为我们讲说了他那一代中国人的残酷青春。文革时期批斗是既残忍又常见的运动,对被批斗者是身心双重摧残。但是这样的苦难张郎郎似乎在讲述别人的故事,语气中既没有不平也没有怨气,更不想以此来控诉那个时代,情感平和且宁静,还略带几分黑色幽默的调侃。《宁静的地平线》用白描的手法描述作者和金豆一起被批斗的情景。
那是在“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公社”批斗的当儿,我俩正好安排在同一场唱主角。毕竟是从市局提来的要犯,气宇凡不凡不敢说,至少行头地道:几十斤重的上下件,傻大黑粗,落墨浓重——原始美,另勒上焦黄新麻绳,交交错错织出图案意思。甚至更有别致的戏扮:为弘扬民族传统,为使农民兄弟喜闻乐见——每人插一根一丈长四寸宽的木板,官称“亡命牌”。
基本用旁观者看客的口吻细节生动地描述被批斗的场景,仿佛是一个鼓书艺人兴致勃勃地讲述着前朝别人的故事,在记述这些亲历的日常往事时,作者像旁观者去回望曾经的个人经历,不诉求任何主观评价,越是不诉求任何主观判断的文字,越能折射记录者的真实心态。
2.深度拷问人性善伪
“文革”是一个人道与自由彻底沦丧的时代,无数无辜的个体生命以“革命”的名义冠上合法与崇高的帽子被迫害,甚至惨死。那是一场生命与暴政、自由与暴政的残酷较量,在较量的过程中既呈现出人性的残暴、脆弱、卑琐与邪恶,尤其是人性中热衷于内斗和看客的冷漠,也透露出人性中难能可贵的正气与尊严,以及人与人之间亲情和爱情的深厚和美好,更有对自由的坚持和对真理的维护。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对自由与美的追求是一种罪。张郎郎从小就在浓郁的艺术氛围中长大,一度认为只有艺术家才是真正的无冕之王。这种理想主义思想,为他在文革“红色暴政”时期的灾难埋下了种子。当时北京最为活跃的两个地下文艺沙龙,一个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组建的“X社”,另一个是张仃之子张郎郎组建的“太阳纵队”。1967年25岁的郭世英背着捆绑着的椅子跳楼身亡,张郎郎也被捕入狱,在看守所被关押了将近十年,经过了几十次的提审,最后作为未决犯,被送进了死刑号,经历了十年的牢狱浩劫。张郎郎把那个时候最热门的词汇“游街”“示众”“批斗大会”“陪绑”“检举”“揭发”“抄家”,甚至“枪决”等等荒唐惨烈的“人间喜剧”都体会到了,因而对人性的善伪也有了深度的体察。
但张郎郎始终坚信人性的美好,认为“要抵抗暴力、抵抗丑恶,而不是比它更厉害,否则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变得暴力、变得丑恶”。所以对抗丑恶和暴力最有利的武器是善良、是真诚。在死刑号里因为想着明天就要上刑场了,在前一天晚上所有的犯人开了一个小型的晚会,他们唱着向往自由的苏联歌曲,以此来抵抗这场暴力浩劫,并且挑选了最有希望活下来的孩子——金豆儿,希望他能把晚会最后的情况转告给家人,不要让家人觉得自己很惨,自己是微笑、优美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步的。这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乐观,是对人性自由和本真的彰显,虽然大家指望捎信的金豆儿也被带走了。
文革的灾难不仅仅波及张郎郎一个人,父亲张仃是最早受到批斗的,张仃的画被定义为黑画,他也就成了黑画家,每天都要挂牌批斗,不停地折磨,让他交代自己莫须有的罪行,交代不存在的幕后指使,那是一个疯狂到失去是非辨别能力的人性异化的时代。“所以文革一开始,我父母就让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每个人兜里都揣一份揭发我父亲的材料。这个材料的内容必须是事实,但不是要害,是人人都知道的。比如说我爸爸喜欢毕加索,毕加索是资产阶级反动画家,而且他推崇齐白石,齐白石是封建主义的代表,大家就觉得你说得非常对。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我们这些孩子是过不了关的。张郎郎在接受采访时不无感慨地说:“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白鼠,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什么都不知道就被牺牲掉了。
张郎郎在《宁静的地平线》中冷静地叙述了自己以及整个那一代人所遭受的磨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波及整个中国大地上的所有阶层,尤其是针对文化艺术领域人士的残酷迫害,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作品让我们在官方历史记录之外,更真实地从单个个体的角度重新审视了那段历史以及在暴力斗争中显露出的人性。
张郎郎的《大雅宝旧事》《宁静的地平线》以个人碎片式记忆拼接还原历史,从亲历者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一种“活化”的历史。其价值体现在“它是个人史与国家、民族史的有机融合,是国家、民族史的生动细化与鲜活补充。”张郎郎不但为他那无限珍贵的童年存档,同时,也是为时代和历史存档。这种非虚构写作既具有历史细节的真实性,又具有虚构写作的诗性内涵,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并存。张郎郎的非虚构书写正是胡适所鼓励的一种传记:“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①张郎郎《不辜负这辈子的故事》[N],《深圳商报》,2012年3 月28日。
[基金项目: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文学视域下的民间述史研究”(编号:14YJA751019)]
作者单位:(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