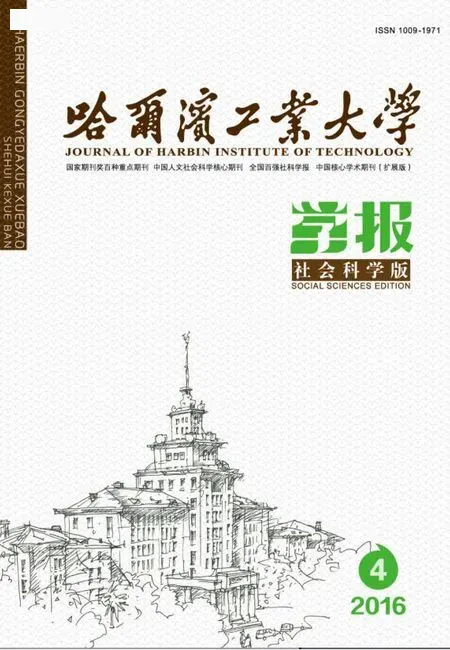主客观社会地位对社会信任心态的影响
2016-09-24谭旭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谭旭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社会理论与社会建设·
主客观社会地位对社会信任心态的影响
谭旭运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采用对北京、上海、广州、郑州、重庆、西安、武汉七个地区城市居民信任状况调查数据,从个体微观层面探究个体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及其维度之一人际信任的关系。研究发现,(1)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不存在相关,与主观社会地位存在显著正相关。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月收入和文化程度两个指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此外,男生和女生的主观社会地位和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均不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和女生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显著高于女性。另外,年龄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呈显著正相关,与社会普遍信任水平不存在相关关系。(2)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均与人际信任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就主客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的关系而言,与客观社会地位相比,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的关系更敏感。主客观社会地位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不同于社会信任水平,这表明更为细致地探究主客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不同维度的关系有其必要性。
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社会信任;人际信任
社会信任通常是指个体对所在社会的大多数人的信任[1]。一直以来,社会信任对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个体的行为具有重要且广泛的影响,例如,社会信任会促进金融市场的繁荣[2][3],推动创业环境不断完善[4],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质量的提升[5],提高个体对社会活动的参与水平[6],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进[7]等。由此可知,社会信任非常重要。因此,为更好地发挥社会信任在社会和个人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探讨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是重要课题。
一、文献回顾
目前,影响社会信任的因素主要存在三种解释,分别关注个人层面、社会层面和社区层面[8]。其中,个人微观层面的解释认为,社会信任是个体进行的完全个人化的主观性的评价,个体自身所具备的客观和主观特点是影响个体社会信任水平的因素。本文主要从个体微观层面,研究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因素,即性别、年龄等人口学特征,包括家庭月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在内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主观社会地位。
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是指个体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和教育水平等[9],参照前人研究[10],本研究将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操纵为个体的家庭月收入水平和最高受教育水平两个指标。社会经济地位是决定个体健康和心境易感性的重要因素[11],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个体对社会的态度[12]。Alesina和Ferrara[13]通过分析美国1974—1994年间的纵向数据发现,个体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与社会信任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具体表现为:收入水平越高,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信任水平越高。他们认为个体的客观经济水平越高,越能承受由社会信任所产生的决策失误上的损失[14][15]。Delhey和Newton[16]发现,个人占有的资源和财富越多,会越容易信任他人,社会信任水平越高。据此,我们认为个体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与其所持有的社会信任呈正相关。
尽管有研究发现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信任呈正相关关系,但是作为社会地位类型之一的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的关系并没受到足够重视。主观社会地位是指个体对自己处于社会阶层中某一位置的信念和主观的认知[17]。主观社会地位通过询问个体对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阶层位置的觉知,来测量在社会中个体的相对地位。有研究表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客观地位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8],主观社会地位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有可能呈正相关,也可能呈负相关[19]。Wilkin⁃son[20]和Goodman[21]提出,主观社会地位作为社会地位的一个类别,其提供的评定信息比客观社会地位这一客观指标更优越,其能更为准确地捕捉到个体在社会地位中更为敏感的方面。因此,我们认为个体的主观社会地位作为个体自身对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一种主观感知,其对社会信任的关系或预测作用可能更强。另外,也有研究发现主观社会地位与个体对现在和未来的一些具体感知指标更相关,如控制感、主观幸福感等[22][23]。而Delhey和Newton[24]的研究发现,居民的控制感和主观幸福感等会提高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根据以上分析,相对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而言,引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探究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因素是值得关注的。我们认为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呈正相关。
此外,关系是中国社会信任的最大特点[25],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亲密度和信任呈正相关[26]。中国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熟人社会”,人际信任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状态。根据费孝通差序格局的观点,中国社会“好像是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以‘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27],个体主要依赖于关系中的熟悉程度来构建信任模式和信任水平。虽然,有研究指出现代社会信任可划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两个维度[28],但基于中国社会信任的独特性,我们主要从人际信任这一维度,考察人际信任及其各维度上的水平如何,我们认为亲属信任的水平最高,熟人信任水平其次,陌生人信任水平最低。此外,本研究初探主客观社会地位对社会信任维度之一——人际信任的影响,考察主客观社会地位与人际信任的关系是否与社会信任完全一致。
综上分析,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相比,作为社会地位另一种研究路径的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的关系可能更敏感。另外,基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有必要将作为社会信任维度之一的人际信任进行更深入地分析。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与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合作,对北京、上海、广州、郑州、重庆、西安、武汉七个地区的城市居民信任状况进行的调查,我们分析了个人微观层面上客观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的关系。我们预期,与客观经济地位相比,主观社会地位更能预测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与社会信任的关系更敏感。同时,我们初探在个人微观层面上主客观社会地位与人际信任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结构
本研究共调查1943人,根据是否报告家庭月收入状况,最终确定有效数据1907人。其中,城市分布上,共选取北京(15.9%)、上海(15.6%)、广州(15.6%)、郑州(13.0%)、重庆(13.2%)、西安(13.3%)、武汉(13.4%)七个城市。年龄在18岁~6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9.56±11.62岁。
此外,还统计了性别、家庭月收入、受教育水平、就业状况、职业和宗教信仰上的人数分布状况。性别上,男性和女性分别占50.1%和49.9%;家庭月收入水平上,1000元及以下占0.8%,1001元~1999元占1.8%,2000元~2999元占8.3%,3000元~3999元占13.3%,4000元~4999元占13.3%,5000元~5999元占16.6%,6000元~6999元占8.4%,7000元~7999元占7.8%,8000元~8999元占7.3%,9000元~9999元占2.8%,10000元~11999元占 10.4%,12000元~13999元占2.6%,14000元~15999元占 2.1%,16000元~17999元占0.8%,18000元~19999元占0.9%,20000元及以上占2.4%;受教育水平上,小学及以下占2.6%,初中占18.8%,高中/职高占40.8%,大学/大专占36.0%,硕士及以上占1.8%;就业状况上,全日制学生占3.3%,无工作的占2.8%,在职工作的占73.0,离退在家的占11.4%,离退后重新应聘的占1.6%,离职、内退或下岗的占4.0%,失业占3.4%,其他占0.5%;职业上,农民占0.7%,专业技术人员占14.1%,公务员占2.4%,商业服务业人员占 30.4%,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占9.9%,工人占 28.3%,会计占 93.9%,其他占8.1%,缺失占6.1%。
(二)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主要包括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社会普遍信任水平、人际信任水平四部分,均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进行测量。
1.客观社会经济地位
指标为个体的家庭月收入水平和最高文化程度(见表1)[12]。这些变量分别赋值数字为1到16和1到5,数字越高表明对象的家庭月收入水平越高,文化程度越高。赋值后,进行标准化转化,然后将个案的标准化分数相加作为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因变量指标。
2.主观社会地位
要求被试报告“就您自身而言,您觉得在这个社会中您所处的阶层位置是?”采用1到5点等级评定,1表示下层,5表示上层,数值越大表明个体的主观社会地位越高。
3.社会普遍信任水平
测量项目共3项,为“请问您认为在与人交往时,大多数人是可信的还是要非常小心?”“请问您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一有机会就占你便宜,还是他们尽量按规则公平办事?”“请问您认为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乐于助人还是只关心自己?”,均采用Likert式5点等级评定,计分方式为正向。所有项目的平均分作为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分数越高表示社会普遍信任水平越高。
4.人际信任水平
测量题目为“请问您对以下人际关系的信任程度如何?”,人际关系共划分为9项,分别为“家庭成员,一般熟人,一般朋友,亲密朋友,亲密朋友,单位同事,单位领导,邻居,陌生人,网友”,包括亲属信任、熟人信任和陌生人信任三个维度[28]。所有项目均采用Likert式5点等级评定,1表示非常不信任,5表示非常信任,分数越高表示对某一人际关系的信任程度越高。参照前人研究[28],所有项目的平均分为人际信任总体水平;家庭成员的评定分数为亲属信任水平;一般熟人、一般朋友、亲密朋友、一般朋友、单位同事和单位领导的平均分为熟人信任水平;邻居、陌生人和网友的平均分为陌生人信任水平。以上均为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信任水平越高。
三、数据分析
(一)主客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人际信任及其各维度间的相关关系
对各变量及其指标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1 各变量及其指标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结果
就社会普遍信任水平而言,如表1所示,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普遍信任水平不存在相关(r =.01,p=.714),与主观社会地位存在显著正相关(r=.27,p<.001)。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r=.20,p<.001)。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月收入和文化程度两个指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rs=.83,ps<.001)。在人口统计学上,各变量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男生和女生的主观社会地位(t=-1.72,p=0.09)和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均不存在显著差异(t=-0.72,p=0.48);男生和女生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显著差异(t=2.14,p=0.03),男性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M=0.08,SD=1.66)显著高于女性(M=-0.08,SD=1.64)。另外,年龄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呈显著正相关(rs>.29,ps<.001),与社会普遍信任水平不存在相关关系(r=-.01,p=.53)。
就人际信任及其各维度而言,如表1所示,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人际信任水平、亲属信任、熟人信任和陌生人信任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主观社会地位与人际信任水平、亲属信任和熟人信任呈显著正相关,与陌生人信任不存在相关。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中的文化程度与人际信任各维度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但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中的家庭月收入只与人际信任总水平、熟人信任和陌生人信任存在显著正相关,与亲属信任不存在显著相关。在人口统计学上,各变量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男生和女生在人际信任水平(t=0.80,p=0.42)、亲属信任(t=-0.51,p=0.61)、熟人信任(t=0.27,p =0.79)和陌生人信任(t=1.56,p=0.12)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年龄与人际信任水平、亲属信任和熟人信任均呈显著负相关(rs<-0.49,ps<0.05),与陌生人信任不存在相关(r=-0.01,p=0.54)。此外,对人际信任总水平及其各维度进行与中间值3相比较的单样本t检验发现,人际信任总水平、亲属信任和熟人信任水平都显著高于随机水平,陌生人信任水平显著低于随机水平,ps<0. 001;并且,通过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亲属信任的水平最高,熟人信任水平其次,陌生人信任水平最低,F(2,3812)=8969.36,p<0.001。
(二)个体微观层面,社会信任和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
以社会信任水平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别检验个体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模型1),个体主客观社会地位、所在城市、宗教信仰、就业状况和职业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模型2),以及个体所在城市、宗教信仰、就业状况和职业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主观社会地位正向预测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个体所感知的自身主观社会地位越高,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没有预测作用,个体的宗教信仰、就业状况和职业也不存在预测作用。采样城市在社会信任上具有预测作用,为进一步发现不同采样城市的社会信任水平,以主客观社会地位为协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城市的社会信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F(8,1896)=23.54,p<.01。多重比较发现,北京(M=2.91,SD=.04)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低于上海(M=3.07,SD= .04)、广州(M=3.46,SD=.04)、郑州(M=3.42,SD =.044)、重庆(M=3.32,SD=.05)、西安(M=3.38,SD=.04)和武汉(M=3.36,SD=.04);上海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低于广州、郑州、重庆、西安和武汉;广州的社会信任水平与郑州、西安和武汉不存在显著差异,显著高于重庆,ps<.05。

表2 个体微观层面,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鉴于人际信任水平与各维度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仅以人际信任水平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别检验个体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模型1),个体主客观社会地位、所在城市、宗教信仰、就业状况和职业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模型2),以及个体所在城市、宗教信仰、就业状况和职业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个体微观层面,人际信任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由表3可知,主观社会地位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个体所感知的自身主观社会地位越高,人际信任水平越高;个体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人际信任水平越高。个体的宗教信仰、就业状况和职业对人际信任水平均有预测作用。这表明个体的主观社会地位、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宗教信仰、就业状况和职业都会影响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
四、讨 论
基于个体微观层面,通过分析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发现,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是社会地位的两个研究路径,相较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而言,主观社会地位更能预测社会信任,其与社会信任的关系更敏感。具体表现为: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呈显著正相关,主观社会地位对社会信任具有预测作用;客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不存在相关关系。性别、就业状况、职业和宗教信仰对社会信任均没有预测作用。此外,不同城市的社会信任水平不同,北京和上海的社会信任水平最低。通过分析人际信任及其各维度的水平和个体微观层面上的影响因素发现,主客观社会地位都会影响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人际信任总体水平上较高,尤其亲属信任最高,熟人信任居中,陌生人信任水平最低,且低于正常的信任水平。
(一)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
分析发现,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呈正相关,主观社会地位能够正向预测社会信任。这表明,个体的主观社会地位越高,所持有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这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根据主观社会地位与一些与自我相关的具体感知指标间的关系[22][23],以及相同的感知指标,如控制感、幸福感与社会信任的关系,主观社会地位之所以能正向预测社会信任水平,是因为它可能通过控制感、幸福感等实现[29]。个体的主观社会地位越高,可能控制感和幸福感越强,对自身决策的风险性知觉更低,对未来的安全性感知更强,从而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社会信任。但事实上,主观社会地位是否通过以上机制作用于社会信任,以及二者的关系是否在另一种方向上也成立,仍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予以证明。
(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信任
与主观社会地位不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信任不相关,对社会信任不具有预测作用。这与 Alesina和 Ferrara[13]、Brehm等人[14]以及Guiso等人[15]所发现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该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与社会信任无关。一方面,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只探究了个人微观层面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因此社会层面和社区层面等因素的影响,或许能够用于解释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另一方面,正如前人所提出的观点[8][10],尽管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均是社会地位的研究途径,但是二者关系的方向性并不是始终一致的,并且,就用于更准确、更敏感地捕捉个体的知觉感受而言,主观社会地位可能更有利。
就个人微观层面而言,结果发现性别、就业状况、职业和宗教信仰对社会信任都不具有预测作用。这与李涛等人[8]、Alesina和Ferrara[13]、Bre⁃hm等人[14]以及Guiso等人[15]所发现的研究结果都不一致,但与Delhey和Newton[24]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性别因素、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对社会信任均不存在显著影响。结合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信任的关系,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相对于主观社会地位而言,个体的性别、职业、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等的客观社会地位的确不对社会信任水平构成影响。
除此之外,不同城市的社会信任水平不同。结果发现,在控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之后,北京和上海地区城市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最低。根据采用的测量项目“请问您认为在与人交往时,大多数人是可信的还是要非常小心?”“请问您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一有机会就占你便宜,还是他们尽量按规则公平办事?”“请问您认为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乐于助人还是只关心自己?”,该研究的社会信任主要源于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的地区可能在熟人圈破裂程度、对社会信任的期望水平、社会信任相关经历、维权途径和意识等方面有所不同。有学者主张,作为社会表征的总体信任程度与市场化程度呈负相关[30]。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究东中西部地区不同城市的社会信任水平,更为细致地分析影响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社会信任水平的因素。
(三)主客观社会地位与人际信任
结果发现,城市居民的人际信任水平整体高于随机水平,其中,亲属信任水平最高,熟人信任水平次之,陌生人信任水平最低,且低于随机水平。这与费孝通的观点相一致[27],中国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熟人社会”,人际信任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状态,个体主要依赖于关系中的熟悉程度来构建人际信任。此外,研究还发现,个体的主观社会地位、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均能正向预测人际信任水平,宗教信仰、就业状况和职业也会影响人际信任水平。这表明,虽然人际信任是社会信任的一个维度,但其受到主客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在未来研究中,一方面可以更深入地分析宗教信仰、就业状况和职业等客观社会地位如何影响人际信任;另一方面,社会信任不仅包括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也是现代社会所产生的一种社会信任形式,鉴于主客观社会地位对社会信任和人际信任的作用不完全相同,因此有必要探讨主客观社会地位对制度信任的影响。
结 论
经过分析发现如下结论:(1)主观社会地位对社会信任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主观社会地位越高,社会信任越高;(2)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信任没有影响;(3)相较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而言,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的关系更敏感;(4)性别、就业状况、职业和宗教信仰都不影响社会信任,不同城市的社会信任水平存在差别;(5)人际信任整体水平较高,其中,亲属信任水平最高,熟人信任水平次之,陌生人信任水平最低,且低于一般随机水平;(6)主客观社会地位均对人际信任产生影响。
[1]DURLAUF S N,FAFCHAMPS M.“Social Capital,”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J].Volume IB,Edited by Aghion,P.,and Durlauf,SN,2005:1639-1699.
[2]GUISO L,SAPIENZA P,ZINGALES L.Trusting the Stock Market[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8,63(6):2557 -2600.
[3]GUISO L,SAPIENZA P,ZINGALES L.Rebuilding Trust after the Crisis.Implications for Financial Markets[J]. Politics,Economics and Global Governance:The Euro⁃pean Dimensions,2010.
[4]GUISO L,SAPIENZA P,ZINGALES L.Does Culture Af⁃fect Economic Outcomes[J].Cepr Discussion Papers,2006,20(2):23-48.
[5]PUTNAM R D,LEONARDI R,NONETTI R Y.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6]蔡起华,朱玉春.社会信任、收入水平与农村公共产品农户参与供给[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1-50.
[7]HELLIWELL J F.How's Life?Combining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Variables to Explain Subjective Well-being [J].Economic Modelling,2002,20(2):331-360.
[8]李涛,黄纯纯,何兴强,周开国.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8,(1):137-152.
[9]OAKES J M,ROSSI P H.The Measurement of Ses in Health Research:Current Practice and Steps Toward a New Approach[J].Social Science&Medicine,2003,56(4):769-784.
[10]ADLER N E,EPEL E S,CASTELLAZZO G,ICKOVICS J R.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wit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ing:Preliminary Data in Healthy white Women[J].Health Psychology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Division of Health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0,19(6):586-592.
[11]LINK B G,DOHRENWEND B P.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Depression:The Role of Occupations Involving Di⁃rection,Control,and Planning[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3,98(6):1351-1387.
[12]KRAUS M W,KELTNER D.Sign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A Thin-slicing Approach[J].Psychological Sci⁃ence,2009,20(1):99-106.
[13]ALESINA A,FERRARA E L.Who Trusts Other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2,85(1):207-234.
[14]BREHM,JOHN,RAHN,WENDY.Individual-level Evidence fo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apital[J].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7,41(3):999-1023.
[15]GUISO L,SAPIENZA P,ZINGALES L.People's Opi⁃um?Religion and Economic Attitudes[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3,50(1):225-282.
[16]DELHEY J,NEWTON K.Predicting Cross-national Levels of Social Trust:Global Pattern or Nordic Excep⁃tionalism?[J].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5,21(4):769-771.
[17]SINGH-MANOUX A,Adler N E,MARMOT M G.Sub⁃jective Social Status:Its Determinant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Measures of Ill-health in the Whitehall ii Study[J].Social Science&Medicine,2003,56(6):1321-1333.
[18]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J].社会,2008,28(2):1-19.
[19]ADLER N,STEWART J.The MacArthur Scale of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J].Summary Prepar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sychosocial Working Group,2007,Re⁃trieved 23.06.08,from.http://www.Macses.ucsf. edu/Research/Psychosocial/notebook/subjective.html.
[20]WILKINSON R G.Health,Hierarchy,and Social Anxi⁃ety[J].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1999,896(1):48-63.
[21]GOODMAN E,ADLER N E,DANIELS S R,MORRI⁃SON J A,SLAP G B,DOLAN L M.Impact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on Obesity in A Biracial Cohort of Adolescents[J].Obesity Research,2003,11 (8):1018-1026.
[22]DESTIN M,RICHMAN S,VARNER F,MANDARA J. “Feeling”Hierarchy:The Pathway from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to Achievement[J].Journal of Adolescence,2012,35(6):1571-1579.
[23]SAKURAI K,KAWAKAMI N K,ISHIKAWA H,HASH⁃IMOTO H.The Impact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Men and Women in Japan[J].Social Science&Medicine,2010,70(11):1832-1839.
[24]DELHEY J,NEWTON K.Who Trusts?:The Origins of Social Trust in Seven Societies[J].European Societies,2003,5(2):93-137.
[25]吴江龙,刘伶俐.关于当下中国社会信任状况的实证分析——基于八个省市的数据 [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6):75-83.
[26]杨宜音.“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 [J].社会学研究,1999,(2).
[2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8]李志,邱萍,张皓.城市居民社会信任现状及提升途径——以重庆市为例[J].城市问题,2014,(1):2-8.
[29]陈艳红,程刚,关雨生,张大均.大学生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自尊:主观社会地位的中介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4,30(6):594-600.
[30]饶印莎,周江,田兆斌,等.城市居民社会信任状况调查报告[J].民主与科学,2013,(3):47-52.
The Effect of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on Social Trust
TAN Xu⁃yun
(Institute of Soci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732)
This paper adopted seven regional urban residents'trust survey data,Shanghai,Guangzhou,Zhengzhou,Beijing,Chongqing,Xi'an,and Wuhan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socioeco⁃nomic status,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nd social trust on the individual level.It was found that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was not correlated with social trust level,but there wa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nd social trust level.Two indexes,monthly family income and educational level,show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ocioeconomic status.In addition,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oth on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nd so⁃cial trust level in male and female,but exis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ocioeconomic status,presenting that mal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emale.Besides,age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but was not related to social trust.This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nd social trust is more sensitive.
O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Subjective social status;Social trust
C913
A
1009-1971(2016)04-0064-07
[责任编辑:唐魁玉]
2016-04-23
谭旭运(1986—),男,山东滕州人,博士,从事社会心态、社会信任和社会公正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