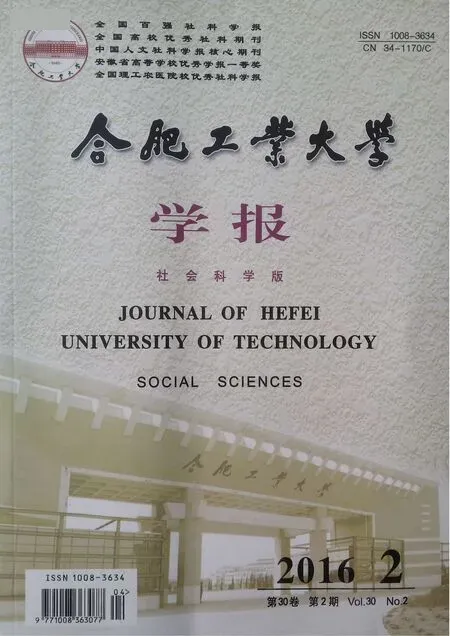贫困地区城乡夫妻权力模式对比研究
——以甘肃省定西市T县为例
2016-09-23唐永霞罗卫国
唐永霞, 罗卫国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政史系,甘肃 定西 743000)
贫困地区城乡夫妻权力模式对比研究
——以甘肃省定西市T县为例
唐永霞,罗卫国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政史系,甘肃 定西743000)
中国贫困地区城镇和乡村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存在着不均衡性,在夫妻权力模式方面也表现出明显差异。文章认为,贫困地区城乡间夫妻权力模式存在共性也有着差异,城乡家庭中妻子均居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城镇趋于夫妻平权,农村依然男权盛行,而且贫困地区城乡夫妻权力模式较之于全国其他地区差距更加明显。究其原因有传统性别观念的普遍存在;农村妻子文化程度偏低、经济独立缺失;区域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等因素。
贫困地区;城镇;农村;夫妻权力模式;对比研究
和谐家庭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石,夫妻权力模式是影响家庭和谐的决定性因素。当前中国贫困地区城镇和乡村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已然存在着不均衡性,在夫妻权力模式方面是否也表现出明显差异?笔者为此曾做过相关调查,结果表明:在贫困地区的农村家庭,夫妻权力模式依然是“夫主妻从”型,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值差距悬殊,丈夫是家庭权力的绝对拥有者,家务劳动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现象普遍存在[1]。本文以妻子在城乡家庭权力结构中的相对位置为考查点,以甘肃市T县为样本,观察并分析贫困地区城镇和乡村夫妻权力模式的差异与变化,旨在为贫困地区家庭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实证依据。
一、研究背景
(1) 相关概念界定自1960年布拉德等在《丈夫与妻子:动态的婚姻生活》一文中提出婚姻关系中夫妻权力的概念起,国内外有很多学者相继对夫妻权力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关于“权力”,韦伯认为“权力是处于特定位置的某一社会成员排除阻力实现自己意愿的可能性”[2]。依据韦伯对权力的界定,罗斯·埃什尔曼认为夫妻权力是“夫妇各自能力的相互影响,衡量权力一般以谁来做决定和谁来执行决定为尺度。”[3]445奥尔森和克伦威尔也据此将夫妻权力划分为“权力形成的基础、权力的过程和权力的结果”三个层次。其中,权力的基础主要是指个人所拥有的资源,权力的实施过程体现了夫妻之间的相互影响,权力的结果指谁做决策和谁取胜[3]445-449。国内多数学者对于夫妻权力的界定遵循西方相关理论,如学者郑桂珍的研究认为,“当一个家庭遇到事情时谁说了算、谁拍板,说了算的那个人就是家庭权力的拥有者。”[4]
关于夫妻权力模式的测量指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在共性中存在着分歧。大多数学者均将预设好的家庭事务决策项目作为夫妻权力的衡量指标。如:布拉德把家庭事务决策权细化为八方面(即:丈夫的职业选择、妻子是否外出工作、买房子、买车子、是否买人寿保险、到什么地方度假等)来研究夫妻权力模式;森斯特等人在布拉德的基础上把家庭事务决策权进一步细化到家庭日常生活事务的决策权,增加了家庭应酬、房间装饰、买衣服、选广播电视节目等六个测量指标。国内大多数研究者亦是将女性是否拥有家庭事务决定权作为衡量妻子权力大小的主要变量或指标之一[5-7]。家庭权力,有学者将其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家庭事务决定权,二是个人事务自主权[8]。陶春芳、蒋永萍提出了“重大家庭事务决定权”概念,即从事何种生产、住房的选择或盖房、购买高档商品或大型生产工具、投资或贷款等家庭重大事务的决策权才是家庭实权的象征和真正体现[9]。但也有学者对夫妻权力模式的研究由静态的分配偏向了动态的分配过程,通过对家庭中夫妻互动具体过程的考察来透视夫妻权力模式[10];学者徐安琪根据以往的研究,总结归纳出夫妻权力测量的几种主要模式: 重大家庭事务决定说、经常性管理权重说、受访者客观认同说、多元指标综合说、家庭实权测量说等测量指标[11],但她认为:多维测量存在诸多缺陷,以“家庭实权”这一单项指标来描述和分析婚姻权力的现实模式更具可操作性、更为有效[8]。对于城乡夫妻权力模式的对比研究,国内大多数学者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学者徐安琪通过实证比较分析,认为中国城镇的家庭更加民主、平等,甚至“阴盛阳衰”,但农村家庭丈夫拥有实权的最多,妻子的地位和生活质量都较低[12]。
那么,对于贫困地区的城镇、乡村而言,夫妻权力模式是否符合上述研究结论?事实上,虽然在国家城乡一体化政策的推动下,城乡之间的交往和融合逐步成为主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二元分割体制的烙印在现代城乡之间依然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想文化观念的差异必然折射到家庭中来,直接影响着城乡夫妻权力的呈现模式。本研究拟从主观和客观角度来测量城乡夫妻权力模式。主观角度采用一个概括性的测量指标,即选取“家庭实权”,从家庭权力的主观认同方面来测量夫妻权力模式;客观角度则主要以“家庭事务决策权”、“个人事务自主权”、“家务劳动分工”三方面作为城乡家庭夫妻权力模式对比的参考变量。
(2) 研究设计本次调查样本T县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本次调查研究对象:甘肃省T县居住在家庭户内、年龄在20至60周岁已婚女性;样本的抽取:在城镇主要以T县城的“双职工”家庭为调查点,在农村则按照T县各乡镇经济发展水平高、中、低层次,选取P、L、S三个乡为调查点。然后随机抽取若干村及城镇家庭,抽中行政村及城镇家庭的所有符合条件的已婚女性均进入样本框,由于研究的主题为夫妻权力,故排除了未婚、离婚、丧偶的个案。计划采用等距抽样,由于实际操作的困难,在调查中则实行了滚雪球的调查方法,利用关系网展开调查。资料收集采用结构式问卷调查与入户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完成,当面访问,当场回收。共发放3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98份,有效回收率99.3%。其中,农村已婚女性149人(占50.0%),城镇已婚女性149人(占50.0%);20至30岁的占25.5%,31至40岁占24.8%,41至50岁的占25.2%,51至60岁的占24.5%。
二、贫困地区城乡夫妻权力模式的现状分析
(1) 家庭事务决策权关于家庭事务决策权,有研究者将其分为:家庭日常事务和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并认为对夫妻权力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拥有这种权力就意味着对家庭资源的控制和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13]。学者认为,城镇夫妻共同决策极为普遍,如将夫妻进行比较,妻子对家庭收入的管理权、支配权及决策权均略大于丈夫[14]。对于贫困地区的城镇与农村家庭而言,在家庭事务决策权方面是否与上述结论一致?从表1数据得知:首先,在“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方面,城乡存在着明显差异。“丈夫决策型”家庭,在农村比重明显偏高,而在城镇的比重则明显偏低。如在“购买大件商品/大型农机具”、“买房/盖房”、“投资或贷款”等方面,农村家庭表示“由丈夫决定”者均在77%以上,而城镇家庭表示“由丈夫决定”者仅占18-28%;农村家庭中表示“夫妻商量”者仅有11-19%,城镇家庭则均在65%以上。也就是说,与城镇家庭相比,农村家庭中夫权特色仍然比较明显,夫妻协商型家庭相对于城镇来说大大偏少;其次,总体而言,城乡丈夫在“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上都拥有显著的优势,但“家庭日常事务”方面,妻子较之于丈夫则掌握更多的决策权。如在“购买大件商品/大型农机具”、“买房/盖房”、“投资或贷款”等方面,城镇与农村虽然在“夫妻共同商量”方面数据有很大差异,但是仅从丈夫与妻子的对比来看,丈夫决策权力仍占有相对优势,而以妻子决策为主的仅限于“家庭日常开支”一项。这说明:在贫困地区即便是城镇家庭,妻子在家庭日常事务中的决策权高于丈夫,而在家庭重大事务的决策上,其权力的天平则更多地倾斜于丈夫一方。

表1 家庭事务夫妻决策权力城乡对比分析(%)
(2) 个人事务自主权韦伯认为权力是“在特定社会关系中个人即使遭到对方反对也能行使自己意愿的能力”。但由于家庭事务决策大多是为了整个家庭的利益,故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矛盾和冲突。因此,有学者认为个人事务自主权是衡量夫妻权力的一个更合适的指标,因为自主权标志着个人独立意志和自由度的大小,准确地反映了权力的内涵[15]。本研究主要从“妻子外出学习/工作”和“妻子个人收入的支配”两方面来考量城乡妻子的“个人事务自主权”。首先,在“妻子外出学习或打工”方面,贫困地区的城镇和农村已婚女性表示自己能做主的比例都相应较低(城镇32.2%,农村5.3%),且在此方面,城镇已婚女性的自主权仍然高于农村已婚女性,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个人自主权相对来说还是偏低。“妻子外出学习或打工”不像“购买高档消费品”和“资助自己的父母”那么简单,妻子的决策会影响到整个家庭。因此,需要更多的夫妻双方的协商。如表2数据显示,城镇家庭在妻子“外出学习或工作”时,有49.7%的已婚女性表示由“夫妻共同决定”;然而,在贫困地区的农村,丈夫是妻子是否“外出学习或工作”的主要决定者。从表2数据可知,67.8%的农村已婚女性表示由丈夫决定妻子是否外出学习或工作。其次,在“妻子个人收入的支配”方面,在贫困地区的农村,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妻子个人收入十分有限,即便有微薄的个人收入,其支配权也会大打折扣。如表2显示:仅有7.4%的农村已婚女性表示“个人收入的支配”“由妻子决定”;与之相较,城镇已婚女性在“个人收入”方面则拥有更多的支配权。如表2数据显示,有59.1%的城镇已婚女性表示“由妻子决定”。即便如此,贫困地区的城镇已婚女性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较而言,妻子的个人收入支配权仍然严重缺失。贫困地区的城乡夫妻权力模式与全国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异。

表2 妻子个人事务自主权力城乡对比分析(%)
(3) 家务劳动分工调查分析表明:在“家务劳动分工”方面,贫困地区的城镇和乡村夫妻权力模式中,既存在共性也有差异。首先,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家庭,妻子依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调查数据显示:除“家庭生活用品采购”、“大的力气活”等几项外,其它家务劳动由“夫妻共同承担”的家庭均在35%以下,而“主要由妻子承担”者城乡均在35%以上。其次,在贫困地区的农村家庭中,家务劳动性别分工倾向依然严重,“男主外,女主内”现象普遍存在。调查显示,丈夫承担的家务劳动主要是“家庭生活用品采购”、“大的力气活”等(分别占65.4%、59.2%);妻子承担的则主要是“洗碗”、“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等(均在76.5%以上);另外,在城镇家庭中,丈夫承担家务劳动的比重及夫妻双方承担家务劳动的比重都明显高于农村家庭。除“家庭生活用品采购”、“大的力气活”等几项外,其它家务劳动由“丈夫承担”者,城镇家庭在19.5-28.2%之间,农村家庭在4.0-10.7%之间;由“夫妻共同承担”者,城镇家庭在25.5-53.0%之间,农村家庭在2.7-12.8%之间。然而,贫困地区的城镇家庭,丈夫承担及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务的比重较之于全国其他城镇,仍然差距明显(全国数据表明:“做饭、洗衣服、做卫生、照料孩子生活”等家务由妻子完成的比例高于72.0%,男性均低于16.0%;在“照料老人”分工上,全国数据显示:由妻子承担者为39.7%[16])。
(4) 家庭实权学者认为,家庭实权是对夫妻权力结构的总体测量,在描述和分析夫妻权力的现实模式中更具可操作性、更为有效[8]。表3数据呈现了城乡家庭夫妻双方掌握家庭实权的状况。首先,整体而言,城乡家庭中的丈夫,在家庭权力模式中仍占有相对优势。家庭实权在丈夫一方者,城镇占35.5%,农村占65.8%;家庭实权在妻子一方者,城镇占33.6%,农村仅占14.8%;其次,从城乡对比来看,城镇家庭中夫妻权力更偏向权力共享型(表示“夫妻双方差不多”者占30.9%),但农村家庭中夫妻权力仍以丈夫主导型为主(表示“夫妻双方差不多”者仅占19.5%)。而且,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在贫困地区的城乡家庭中,妻子掌握的实权大多是家庭经济的管理权,然而这种“管理权”往往更多地是一种责任而非权力。由此可见,城乡家庭在夫妻权力模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家庭中丈夫仍是绝对实权的拥有者,城镇家庭权力模式则趋于表面的平权型或夫妻共享型。但是,却并未达到研究者所认为的中国城镇的家庭更加民主、平等,甚至“阴盛阳衰”这一状态(徐安琪,2000)。
表3城乡家庭夫妻谁拥有更多的家庭实权(%)

城乡家庭实权总体城镇农村丈夫151(50.7)53(35.5)98(65.8)妻子72(24.2)50(33.6)22(14.7)差不多75(25.1)46(30.9)29(19.5)
三、影响城乡夫妻权力模式差异的主要因素
贫困地区的城乡间夫妻权力模式依然存在着诸多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传统性别观念的存在是导致贫困地区城乡妻子居于相对弱势地位的重要因素。由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外界先进的性别文化对其冲击相对较弱,“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观念依然存在。规范潜在地成为人们行动的依据,左右着具体的家庭互动,塑造着特定的夫妻权力模式。这种状况在贫困地区的农村尤为严重。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思想观念更为滞后,且又在婚姻家庭中缺乏经济独立,故而很难打破传统的“夫主妻从”局面;贫困地区城镇已婚女性,虽然相较于农村妻子而言,经济上相对独立,文化程度也更高,她们大多有着自己的社会工作。然而,这种经济的独立和文化程度的提高并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男权文化的根基,所以,夫妻双方的观念和权力模式也就不会因此而发生彻底改变,妻子只能在家庭权力模式中居于弱势地位。
第二,文化程度偏低、经济独立缺失致使贫困地区农村妻子在夫妻权力模式中与城镇妻子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者认为,夫妻文化程度越高,夫妻权力关系越平等,且随着妻子文化程度的提高,夫妻共同拥有决定权的比例明显增加,而以丈夫为主作决定的比例明显递减[13]。然而,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贫困不仅使得她们物质匮乏,也剥夺了她们应有的教育权利和学习机会。在本次调查样本中农村已婚女性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以下”者合计占96.6%(城镇为14.1%);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者仅为0.7%(城镇为60.4%),文化程度“男高女低”者占66.4%(城镇为51.7%)。所以相较于城镇已婚女性,农村妻子获得信息的能力极其有限,对丈夫的依赖性也更严重,在家庭中的主动权也随之丧失,夫妻权力模式只能处于“夫主妻从”型;同时,大多数农村已婚女性的收入远远低于丈夫。本次调查样本中“妻子年收入占家庭年收入百分比”在40%以下者,农村占91.3%,城镇占27.5%;夫妻收入对比“男高女低”者,农村占69.1%,城镇为36.9%。农村已婚女性由于未获得独立的职业身份,在经济上只能依附于自己的丈夫,经济独立相对缺失;而城镇已婚女性往往通过高等教育的获得和外出工作的增加,提升了其自身的社会经济资源。虽然说受传统性别意识的影响,城乡家庭中妻子均处于弱势地位,但由于她们间存在的文化和经济差异,故仅就贫困地区的城乡对比而言,城镇家庭权力模式趋于夫妻共享型,农村家庭中丈夫仍占绝对优势地位。
第三,区域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区域间性别意识的差异,这是贫困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夫妻权力模式存在差距的主要因素。性别意识是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往往影响着当地的性别意识。截至目前,我国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仍存在不平衡性,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间二元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依然存在。贫困地区虽也受现代化和工业化影响,但经济产业仍以农业为主,传统社会结构和家庭权力模式的留存较多,“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等男权意识的留存也较为浓厚。在这种男权性别意识的影响下,妻子个人所拥有的资源与其在夫妻权力模式中的位置并无显著的相关性。因为,夫妻双方在家庭中权力的差别主要源于当地性别意识环境对女性的歧视,而非取决于妻子个人拥有的绝对资源或相对资源优势。这种传统的性别意识赋予丈夫在家庭权力模式中的优势地位,而妻子往往居于家庭权力结构的从属地位。正如埃弗克·考姆特在《婚姻中被遮掩权力》一文中所述,丈夫和妻子都是根据长期以来形成的性别角色习俗来描述自己和对方。丈夫一方面由社会所推崇的性格特征而受到尊重,另外一方面,由于在价值上暗含的等级影响,使得女人依附于男人,增强了男人在婚姻中的权力[17]。
四、研究结论
第一,贫困地区城乡夫妻权力模式共同之处:妻子居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贫困地区家庭夫妻权力模式中,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丈夫权力仍占相对优势,而妻子往往居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主观家庭实权和客观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个人事务自主权、家务劳动分工等方面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数据结果显示,丈夫在家庭中有实权的仍然要高于妻子,家庭事务决策中,除了“家庭日常开支”这一项日常事务决策以“妻权”为主外,在“购买大件商品/大型农机具”、“买房/盖房”、“投资或贷款”、“孩子升学/择校”等家庭重大事务中丈夫的决策权力相对于妻子来说占有明显优势。而且,在贫困地区的城乡家庭中,妻子掌握的实权大多是家庭经济的管理权,然而这种“管理权”往往更多是一种责任而非权力;个人事务自主权方面,贫困地区的城镇和农村已婚女性表示自己能决定“外出学习或打工”的比例都相应较低(城镇32.2%,农村5.3%);家务劳动承担方面,虽然在贫困地区越来越多的已婚女性外出工作,丈夫逐渐与妻子分担家务劳动,但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善,且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家庭,妻子依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除“家庭生活用品采购”、“大的力气活”等几项外,其它家务劳动由“夫妻共同承担”或“丈夫承担”的家庭在35%以下,而“主要由妻子承担”者城乡均在35%以上,这显示出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对家庭权力模式的持续影响。
由此可见,妻子整体而言在夫妻权力模式中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家庭权力模式中也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父权制社会规范赋予丈夫在家庭权力中的优势地位依然存在。由于男性作为男权文化的“受益者”,其在夫妻权力模式中的优势地位本就根深蒂固,女性的家庭权力必然要通过其他方式来挣得,比如性别观念的更新、教育程度的提升、相对于丈夫的收入优势,等等。这对于贫困地区的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来说任重而道远。
第二,贫困地区城乡夫妻权力模式存在差异显著:城镇趋于夫妻平权,农村依然男权盛行。仅从城乡对比来看, 城镇家庭趋于夫妻平权,农村依然以丈夫主导型家庭为主。城镇家庭中,有35.5%的妻子表示家庭实权掌握在丈夫手中,表示家庭实权在妻子一方者占33.6%,夫妻共享权力者占30.9%。城镇家庭基本趋于夫妻平权;农村家庭中,65.8%的农村已婚女性表示家庭实权掌握在丈夫手中,表示家庭实权在妻子一方者仅占14.8%,夫妻共享权力者占也仅为19.5%。农村家庭丈夫已然是家庭权力的主宰者;家庭事务决策权、个人事务自主权和家务劳动分工也呈现出同样的城乡对比趋势。家庭日常事务决策中,城镇妻子的权力要明显高于农村妻子;家庭重大事务决策中,与城镇家庭相比,农村家庭中夫权特色仍然比较明显,夫妻协商型家庭相对于城镇来说大大偏少;个人事务自主权方面,农村家庭中,67.8%的妻子表示由丈夫决定其是否外出学习或工作;“个人收入的支配”方面,仅有7.4%的农村妻子表示由自己支配,然有59.1%的城镇已婚女性表示“由妻子决定”;家务劳动承担方面,城镇家庭中丈夫承担家务劳动的比重及夫妻双方承担家务劳动的比重都明显高于农村家庭。表明城镇家庭中丈夫比农村家庭中的丈夫承担更多的家务,更愿意与妻子共同承担家务劳动,也在一定程度体现出在城镇家庭中,夫妻权力模式更加趋向于平等。
显然,贫困地区城乡妻子相对于丈夫而言,虽然均处于弱势地位。但仅从城乡夫妻权力模式对比而言,城镇夫妻权力模式趋于夫妻共享型,农村家庭中丈夫仍占绝对优势地位。可见即便在全国经济、文化大发展的现阶段,贫困地区城乡家庭中的夫妻权力模式在顺应全国大趋势的同时,仍然未实现根本性的变迁,且农村家庭中丈夫依然是家庭权力的主宰者。
第三,贫困地区城乡夫妻权力模式较之于全国其他地区差距依然存在。对于贫困地区的城镇、农村已婚女性来说,在个人事务自主权、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以及家务劳动的承担等方面,均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有着明显差距。
首先,在个人事务自主权方面。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在“购买自己用的贵重物品”和“资助自己父母”方面,分别有92.9%和94.5%的女性表示,能“基本可以”或“完全可以”以自己的意见为主[16],说明92%以上的已婚女性拥有个人收入的支配权。然而,在贫困地区仅有7.4%的农村妻子和59.1%的城镇妻子表示个人收入由自己支配;在“妻子外出学习/工作”的问题上,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女性88.8%的人认为“基本可以”或“完全可以”以自己的意见为主,比从未外出过的女性高4.1个百分点[16]。但是,在贫困地区仅有32.2%的城镇已婚女性和5.3%的农村已婚女性表示以自己的意见为主。显然,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贫困地区已婚女性仍然缺乏充足的“个人事务的自主权”。其次,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方面,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在“家庭投资或贷款”的决策上,贫困地区城乡家庭中由妻子决定者仅有3.4%,夫妻共同商量者占41.3%,但全国调查数据显示,由夫妻共同商量及主要由妻子决定的比例达74.7%[16],在“买房、盖房”的决策上,贫困地区城乡家庭中由“妻子决定”或“夫妻共同决定”的比例分别为5.4%、40.9%(全国数据中妻子参与决策者为74.4%),差距依然明显。再次,家务劳动的承担方面。全国数据表明:“做饭、洗碗、洗衣服、做卫生、照料孩子生活”等家务由妻子完成的比例高于72.0%,男性均低于16.0%。贫困地区城乡家庭中平均由妻子完成的比例高于56.7%,丈夫则均低于20.5%(见表3)[16];另外,贫困地区城镇夫妻权力模式与学者的研究结论也大相径庭。如学者徐安琪认为,中国城镇的家庭权力模式是“阴盛阳衰”(徐安琪,2000),且城镇夫妻共同决策极为普遍,如将夫妻进行比较,妻子对家庭收入的管理权、支配权及决策权均略大于丈夫[18]。妻子更具实权的家庭也多于丈夫更有实权的家庭,中国城镇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普遍较平等,女性地位与世界公认的两性平等国家瑞典相比毫不逊色[19]。显然,在贫困地区城乡夫妻权力模式在目前还尚未达到这一状态。
综上所述,贫困地区城乡间夫妻权力模式存在共性也有着差异:城乡家庭中妻子均居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城镇趋于夫妻平权,农村依然男权盛行;另外,贫困地区城乡夫妻权力模式较之于全国其他地区而言,差距依然十分明显。究其原因有:传统性别观念的普遍存在;农村妻子文化程度偏低、经济独立缺失;区域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等因素。贫困地区若要改善目前夫妻权力模式现状,必须直面以上影响因素的存在。
[1]唐永霞,罗卫国.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调查研究[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4):46-49.
[2]Bell R,Edwards D V,Wagner R H. Political Power:A Reader in Theory and Research [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9:80.
[3](美) J.罗斯.埃什尔曼.家庭导论[M].潘允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郑桂珍.女性与家庭[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06.
[5]刘启明. 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研究的理论框架及指标建构[J].中国人口科学,1994,(6):1-9.
[6]沙吉才.当代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7]单艺斌.妇女婚姻家庭地位的综合评价法研究[J].大连大学学报,2001,(5):15-19.
[8]左际平.从多元视角分析中国城市的夫妻不平等[J].妇女研究论丛,2002,(1):12-17.
[9]蒋永萍.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10]郑丹丹,杨善华.夫妻关系“定势”与权力策略[J].社会学研究,2003,(4):96-105.
[11]徐安琪.夫妻权力和妇女家庭地位的评价指标:反思与检讨[J].社会学研究,2005,(4):134-245.
[12]徐安琪.中国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生活质量──来自实证研究的报告[J]. 妇女研究论丛,2000,(3):29-30.
[13]陶春芳,蒋永萍.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
[14]沙吉才.当代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15]左际平.从多元视角分析中国城市的夫妻不平等[J].妇女研究论丛,2002,(1):12-17.
[16]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J].妇女研究论丛,2011,(6):5-15.
[17]郑丹丹.中国城镇家庭夫妻权力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4-59.
[18]杨善华、沈崇麟. 改革以来我国大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格局的变化[J].中国社会科学,1996,(3):52-65.
[19]徐安琪.夫妻伙伴关系:中国城乡的异同及其原因[J].中国人口科学,1998,(4):32-39.
(责任编辑蒋涛涌)
Comparative Study of Urban and Rural Marital Power Patterns in Poverty Areas:A Case Study of T County in Dingxi City, Gansu Province
TANG Yong-xia,LUO Wei-guo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 Dingxi Teachers College, Dingxi 743000, China)
There is imbalance in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s poverty areas, and the patterns of marital power are also different. The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ree 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marital power patterns in poverty areas. Wives in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s are in a relatively weak position, but there is a tendency towards couples' equal rights in urban areas, and the patriarchy is still dominating in rural areas. Moreover,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areas in China, the urban and rural marital power patterns in poverty areas still lag far behind. 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s: the universal existence of traditional gender concept, the lowe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deficiency in economic independence of wives in rural areas,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culture and other factors.
poverty area; urban area; rural area; pattern of marital power; comparative study
2015-09-23
定西师范高待专科学校校级科研项目(项目编号1326)
唐永霞(1973-),女,甘肃会宁人,副教授。
F067.4
A
1008-3634(2016)02-004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