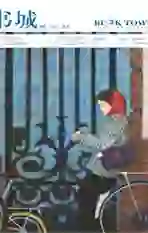奈斯毕特的真实身份
2016-09-22游伟
游伟
一
“文学即人学”。这句话我们现在经常听到,可能都不太觉得其中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可言—文学确实不应该是别的什么,用各种各样的故事以及讲故事的方式,从每一个角度去挖掘、展示人性的各种可能,一直都是文学最大的魅惑所在。
如此,研究文学也应顺理成章地成为研究人学,好的典范如陈思和先生的《人格的发展—巴金传》。在这本名声远不及陈思和其他作品的传记体研究著作中,陈思和将巴金的生活史与创作史交融在一起,彼此对照,用巴金的生活变动来揭示作品的情感思想来源,用作品中的思想来反证当时巴金的生活心态,清晰地描绘出作为作家与普通人的巴金的人格发展道路。要知道,陈思和写这本书的时候,巴金先生尚在人世,如果巴金先生不认可陈思和的说法,完全可以阻止这本书的出版。而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当初阅读这本书时给我带来的情感冲击,以及因为这本书理解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的满足。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相信这种若有所悟的满足与若有所感的冲动,既是阅读的意义,也是我们能继续阅读下去的动力。但是类似的作品确实太少,我们绝大多数的文学研究著作几乎都很难从“人”的角度来打动读者,甚至那些空虚无人的理论词汇与书写研究对象时的冰冷文字,都透着将普通读者隔绝在外的漠然。据说美国经济学界“对用小说阐述经济学极为重视,二○○三年初美国经济学会年会还以‘经济学小说作为教材召开了一次研讨会”(梁小民《想读》),且不说这种方式是否得当,是否取得了良好效果,单是这种俯身迁就初学者、普通人的态度,就值得点十万个赞。遗憾的是,种种原因,中国的文学研究作为一种人学研究,却似乎很少有这种充满人情味的思路与文路。
大概也是出于这种感受,当看到韩少功推荐刘禾的《六个字母的解法》,称其用侦探小说的写法来做思想理论文学研究,你应该能理解我那种欣喜与迫切。
二
刘禾自承创作这部作品的起点,在于自己对纳博科夫和纳博科夫的小说《塞·纳特的人生真相》的喜爱。在这篇远不如《洛丽塔》那样为中文读者熟知的小说中,纳博科夫塑造了一个“只能在幻想之中安身立命”并最终客死他乡的流亡者塞·纳特。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个结局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异之处。然而对于纳博科夫的粉丝刘禾来说,它与纳博科夫的真实命运产生的契合,透出某种神秘的吸引力,让她觉得这本小说“不同寻常”,甚至促生出要从纳博科夫的人生踪迹中找出某种心理逻辑的探索欲。
包括我在内,可能很多人没有读过《塞·纳特的人生真相》(王家湘、席亚兵译为《塞·奈特的真实生活》,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但是对这种真实可感的、吃了好吃的鸡蛋还想见见那只母鸡的窥探欲望却并不陌生。从叙述的角度,用共通的情感吸引读者,也是百用百灵的技巧。正是出于对这种代入的情感的接受,刘禾从瑞士的一场学术会议神游到一九一九年纳博科夫到底在干吗,以及纳博科夫自传中的奈斯毕特(NESBIT)到底是谁,其中的突兀感倒可以理解成意识流动的必然,“剑桥大学”四个字确实也是合理的触发点。一九一九年纳博科夫正在剑桥大学读书,他在自传中说这位化名“奈斯毕特”的同学在讲话时烟斗不离手,而且磕烟斗、放烟丝、点火和抽烟的姿势总有点与众不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引人入胜的是,因为这位奈斯毕特后来成为令人瞩目的公众人物,纳博科夫拒绝透露他的真实姓名,反而激发了大家想搞清楚奈斯毕特到底是谁的欲望。这确实是一部侦探小说的美妙起点。
不过,让人不能理解的是,按照通常的逻辑,疑问已起,接下来就应该是解答或者为解答做铺垫,刘禾却在描述几笔自己曾试图通过解字找寻答案,最终不了了之之后,将笔墨绕开。直到在剑桥探访一番之后,才提起纳博科夫的传记作者博伊德早就对奈斯毕特的身份作出过猜测,点出了巴特勒(R.A.Butler)的名字,并表示纳博科夫也曾“透露”过此言不虚。任何侦探小说都会告诉大家,第一个给出的答案、第一个被指认出来的嫌疑人肯定是错的,刘禾也完全有理由不接受博伊德的猜测和纳博科夫并不可靠的“透露”。但是任何侦探小说同样不应该在故事的开头就对读者隐瞒如此重要的线索—推理小说黄金时代代表作家之一—范·达因(Willard Huntington Wright,1888-1939)曾定下推理小说创作应该遵守的二十条准则,头两条便是:“一、必须让读者拥有和侦探平等的机会解谜,所有线索都必须交代清楚;二、除凶手对侦探所玩弄的必要犯罪技巧之外,不该刻意欺骗或以不正当的诡计愚弄读者”。范·达因的二十条准则或许有争议,然而由于作者在叙述上原本就对读者占有优势,如果在线索的把握上都不与读者站在同一水准上,全然以上帝视角压倒读者,侦探游戏就将毫无公平可言,一个对玩家不公平的游戏如何让人玩下去?如果刘禾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在这个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中,叙述者“刘禾”也即书中的那个“我”确实此前并不知晓博伊德的这个猜测,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责怪她材料掌握得太少?一个侦探尚未好好调查现场,就开始缉拿凶手,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位侦探的推理水平。
当然,这是阅读到后面我们才能产生的疑惑。不论如何,当刘禾踏上前往瑞士的火车之后,故事已经停不下来。甚至,迅速走向最让人惊叹的一幕。
三
那辆火车在阿尔卑斯山秀丽的风景里穿行,而疑惑的种子已经种在读者的心中。看山是山,看山却又不只是山。刘禾描述从缆车上看到五只色彩各异的滑翔伞点缀在白皑皑山脉之间的这段文字,不论作为随笔,还是作为小说中引人入胜的闲笔,都堪称妙极,胜似一部美国大片的开端,情景交融。当她在黄昏时再次踏上返程的火车,一个主动搭腔的陌生人将故事带入最心跳的时刻:他居然也叫奈斯毕特!
刘禾说自己并不能确定写的到底是随笔还是小说。到这个点上,我们已经不能相信她。这不是小说是什么?刘禾如果在遇到他之后不继续追踪纳博科夫笔下的另一位奈斯毕特,简直就是反人类—没有人能抵挡得住这种冥冥中的暗示所带来的巨大诱惑。而且,更神奇的是,这位奈斯毕特甚至给刘禾提供了一条线索,一个名叫Gwei-Djen Lu,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工作,后来去了剑桥大学的中国女人。
遗憾的是,在这个美妙的开头之后,整个故事的逻辑开始陷入随意。且不提“Gwei-Djen Lu,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工作,后来去了剑桥大学的中国女人”,明明已经只差喊出“鲁桂珍”三个字,而书中的那个“我”却茫然不知,让人再度怀疑到底是作者的小说笔法,还是确实知识敏感性较弱。不管怎样,此后这段查询奈斯毕特真实身份的过程已经等同于自说自话。书中的“我”再次捡起了拆字游戏,开始对当时的剑桥风云人物一番走马灯式的审验,逐个否定,万般无奈之下,最终居然在别人的启发之下,改变了刚开始拆字时定下的规则—在六个字母中寻找当时与纳博科夫有交集,同时满足姓名中有这个字母、抽烟斗等条件的人中进行甄别—转而为心中已有的猜测寻找依据,通过将NESBIT六个字母中两个元音字母套在普利斯特利(J.B.Priestley)身上,略加辨析,便得出了奈斯毕特就是普利斯特利的结论—我是怎么都没看出来这中间的推理何在,推理的合理之处何在。如果这是一本学术研究著作,我们几乎可以毫不犹豫地认定其犯了结论在先的错误,这似乎不该是刘禾这样的学术大家会犯的错误。更让人觉得可惜的是,当作者在书中说出“文本分析是思想的侦探仪,而思想和罪犯一样,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时,曾引发读者对缉拿某种思想的期待,然而全书读罢,却并未见她在探寻的过程中揭示出“思想”所在,以及这些“思想”和纳博科夫到底有什么关系。至此,韩少功在序言中所期许的“把思想理论写成侦探小说”,几乎全盘落空。
如果再挑剔一点,我们甚至可以指责“我”既然是长期生活在西方世界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将没有获得邀请函而被剑桥大学英国海外圣经公会档案馆拒之门外,与上世纪女权尚未明确时女作家伍尔夫被剑桥大学图书馆拒之门外相提并论。后者确实是社会有待进步的一例,而前者只能说是自己不守规矩,怎么就怪到了别人头上?
这已经不能不说是一次失败,甚至都谈不上是一次深刻的失败,但是我却依然从这份失败中感觉到了希望。刘禾这本(在我眼中的)失败之作,冒犯地说,就如我老家农村鸡窝里放的乒乓球或破蛋壳,本身也许没有太大的价值,却足以被称为“引宝”,有着催促母鸡生蛋的神奇能力。“引宝”不需要自己就是好鸡蛋,它只需要有个鸡蛋的形状。《六个字母的解法》可远不止有了形状,“文本分析是思想的侦探仪,而思想和罪犯一样,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所以完全有可能“把思想理论写成侦探小说”,刘禾已经证明了理论上的可能。她甚至还实践出一个值得珍惜的开头,解放了一种不再用论文专著的呆板语调约束自己的自由心态。只是太可惜,侦探毕竟也是一门专业,刘禾未必掌握了其中的奥秘。好在时代风气变了,读者对趣味的追捧已经开始倒逼作者创作时的心态。这本书的销售数据显示读者买账的不少,使得这本书俨然成为最好的“引宝”,而我这样的痴汉已经开始守在鸡窝边上。万事俱备,接下来,只差一只既懂“思想理论”,又懂“侦探小说”的母鸡在“引宝”的催动下,诞下那只美味的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