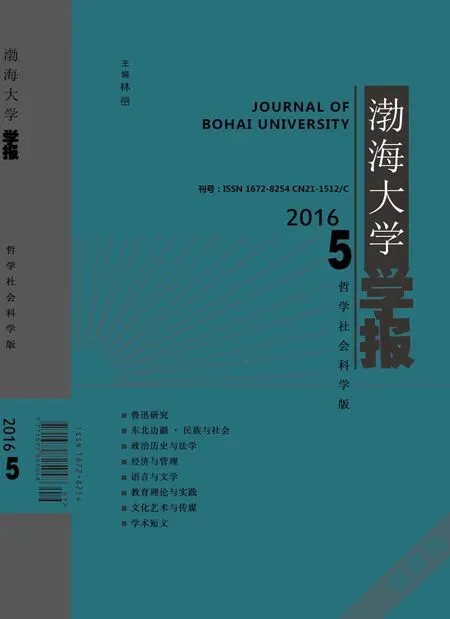荻生徂徕《训译示蒙》的古汉语虚词研究
2016-09-21王雪波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北京100083
王雪波(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北京100083)
荻生徂徕《训译示蒙》的古汉语虚词研究
王雪波(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北京100083)
荻生徂徕所著《训译示蒙》,是关于古汉语虚词意义、用法的注释书。此书首先阐释汉语从字义到句子的构成,划分汉语词类;进而多从词语搭配、句法位置等方面描述古汉语虚词的使用特点。既结合日语和训、翻译来解释古汉语虚词的意义,又能从语法功能的层面说解虚词用法,是江户时代古汉语虚词研究的重要著作。
荻生徂徕;《训译示蒙》;古汉语虚词;江户时代
荻生徂徕(1666~1728),名双松,字茂卿,是日本江户时代古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他关注汉语词义,逐类探讨汉语动词、形容词、虚词的意义用法,并将注释内容整理成教科书《译文筌蹄》,[2]向门下弟子传授讲解。后来,《译文筌蹄》写本得到分卷刊行,虚词部分刊作单行本《训译示蒙》。《训译示蒙》全书由总论和虚词释义两部分构成,体现了荻生徂徕的语言观和对古汉语虚词的认识。他在虚词注解中所运用的方法,也已出现语法分析意识。
一、《训译示蒙》的成书由来
江户初期的庆长到元和年间(1596~1623),船载赴日的书籍中携有一套《格致丛书》,元代卢以纬《助语辞》收于其中。[3]宽永十八年(1641)十一月,风月宗智翻刻刊行《新刻助语辞》,此后直到江户元禄(1688~1703)年间,《新刻助语辞》受到修习汉学人士的关注,成为汉籍经典阅读、汉文写作时的辅导用书。[4]
汉籍在古代日本是学习各种学问的途径,学习汉语自然成为治学的重要前提。[5]在汉语各词类中,虚词有活跃的语法功能,占重要地位,但意义抽象,难以把握。正因如此,卢以纬的这本虚词专著一经传入便受到关注。据考,当时的名儒大家,如毛利贞斋、三好似山、荻生徂徕、伊藤东涯等人,纷纷参与到汉语虚词的研究中,产生多部汉语虚词专著。[4]
荻生徂徕的汉语虚词研究正是在《助语辞》的影响下产生,最初同动词、形容词研究同时进行,并以《译文筌蹄》写本的方式流传。后来,动词、形容词部分单独刊作《译文筌蹄初编》(1714~1715年出版),[6]总论和虚词释义部分单独刊作《训译示蒙》。
《训译示蒙》于明和三年(1766)出版,到了明治年间,又出版了《校订训译示蒙》。[7]校订本是本文研究中采用的底本,此本五卷,明治十四年十二月刊行,东京高桥平三郎刊本,中二册,荻生徂徕撰,筱田正作校。
二、虚词研究的理论基础
《训译示蒙》前两卷主要阐述:汉籍经典的修习门径,翻译要领和朱子注解定法。徂徕先生认为学习汉文始自明辨文字义理,强调词义的重要性;朱子注解定法是对朱熹训诂术语的总结整理;翻译要领着力分析汉、日语的差异,汉日语间的翻译方法,汉语构成及词类划分。这是徂徕先生语言观的集中体现,同时成为其虚词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关于汉语构成
徂徕先生提出“字义”“文理”“句法”“文势”的概念,探讨汉语从字义、短语,到句子、文章的构成。原文论述到:
探讨译文问题,包括“字义”“文理”“句法”“文势”四个方面。“字义”指单字之意,积字成句,积句成文,故“字义”为本。其次,须知“文理”,此为字的先后放置之法。即使相同文字,若先后位置不同,则会带来意义变化。“句法”是在一句之上论巧拙,至于“文势”,则是全体文章之风格。[7]
字义即单字之义;文理指词语出现的先后规律,即词序;句法在文理之上,为组词成句之规律;文势指文章整体风格。尽管分析尚不精细,但徂徕先生已对字、词、句的构成有自觉的分析意识。他从对汉语的整体把握入手,继而展开词义研究,这一点尤为可贵。
(二)关于词类划分
在此基础上,又深入到词义内部,进行词类的下位划分,原文论述到:
“字义”的大纲即“字品”“字势”。“字品”是“字”之原本属性,“字势”是字之构成情形。“字品”包括:虚字、实字、助字。“虚字”如“大、小”,“飞、走”之类。“虚字”又分动字和静字,静虚字是指,“大、小”,“清、浊”等;动虚字指,“喜、怒”,“飞、走”等。“实字”指“天”“地”“草”“木”“手”“足”“枝”“叶”等字。“实字”又分“体字”和“用字”。“体字”指“天”“地”“草”“木”等字,“用字”指“手”“足”“枝”“叶”等字。虚字、实字统称“正字”,“助”是“助语”,“之乎者也矣焉哉”之类。“正”是语之实质,“助”如同日语“てにをは”之类,辅助正语,是成文关键,作引导实语之用。[7]
徂徕先生在词类划分中运用的名称与现代语法学的术语并不相同,但两者划分实质基本一致。“字品”即指“词类”,“字品”下位分“正字”和“助字”,即现代语法学中的“实词”和“虚词”。“正字”下位分“实字”和“虚字”,即“实词”下位的“体词”和“谓词”。“虚字”下位分“静虚字”和“动虚字”,即“谓词”下位的“形容词”和“动词”。
如下表所示:
这种划分是基于意义标准,是否有具体形象可以表达,是其划分正、助词类的依据。徂徕先生尚未认识到词类划分中关键的功能标准,小类划分也未深入,但在理论探索的早期,如不作苛求,他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已属难得。
三、《训译示蒙》的收词与体例
(一)收词
全书列出105个条目,收单音虚词452个、双音虚词44个,其中包括重出词条。文言虚词为主,辅以个别俗语虚词。以现代语法学的观点来看,收词以副词、介词、助词居多。其中也含有非虚词的词条,如卷五的“明”“宜”“必也”三条。原文释“明”“宜”意为“清楚、显然”,应属形容词;“必也”非词,徂徕先生没有解释为何将其视作虚词。此外还收有表被动、意志、应该、可能的助动词,如:“见、被、所、遭”;“肯、敢”;“当、应、合、须、宜、可、容、消”等词。以及三组动词:“为、作、成、做”;“在、有”;“云、曰、谓、言、道”。“助动词”专用于修饰动词,它和副词有相类似之处,是介于副词和动词之间的一类词。三组动词没有明显的动作性,徂徕先生在释义中强调它们在主语、宾语间起到的联系作用。因此,整体来看,徂徕先生对汉语虚词的判断较为准确的。
(二)体例
编写上依循“同用同条、义近相接”的体例。如“也、矣、焉、兮”;“乎、邪、耶、欤、与、夫、哉”;“以、将、庸、用、式、须、消”等,各依相近的用法而归为一组。
前后词条之间也体现了“义近相接”的特点。如语气词“也、矣、焉、兮”,“耳、尔、已、而已”,“乎、邪、耶、欤、与、夫、哉”相继排列,连词“或、若、如、设、傥、倘、乍、脱”,“虽”,“假使、假令、设若、设使、纵、虽、就、饶使、任、譬、喻、况”,“况、矧”紧接排列,在释义时便于比较。
注意到一个虚词的多个用法,同一虚词因用法不同会再次列出。如“尔”字前后出现三次,在“其、厥、夫、那、尔、彼、某”词条释作代词用法;在“然、尔”词条释作句末助词用法,“那样、似的”意;在“耳、尔、已、已而”词条释作句末语气助词用法,“限止”意。
四、《训译示蒙》的虚词研究内容
《训译示蒙》的卷三到卷五注释虚词的意义、用法。每一词条下先列出虚词对应的日语和训、翻译,其后说解用法。以具体词条为例加以说明。
如“之”字词条释义:
“之”读作“的”“这、这个”是助语;读作“去往”,不是助语。如“大学之书”,指《大学》这本书,举出区别,即“指示”意。此“之”上字重读。若“之”下字重读,则强调并非大学之“道”、大学之“学校”,而是大学之“书”。
又“之”字和“其”字相似,“其”字重,是指辞。比较“大学之书”和“大学其书”,“大学其书”强调“书”,缺少“像这样的”意。
又“之”字同“而”字,连接文字,但“而”字置于上下二事中间,连接前后,为“语折”。“之”字置于上下二事间,或上名下物,为“语直”。如云“仁义”,并指“仁”“义”两事。云“仁之义”,指“仁”中之“义”。
又“之”下字必为“死字”、必为“物”。所谓“物”,可以是“理”“事”“实物”“时”“处”。例如“气质之禀”的“禀”,若读作“领受”则非死字;“三代之隆”的“隆”,若读作“旺盛”则非死字。又“之”下字数较多,难以出现死字时,则“之”下置“所”字,或句末置“者”“也”字。
又《诗经》有“子之荡兮”“扬之水兮”,此“荡”“扬”为形容字,形容字皆死字,故“之”字在下,《诗经》此等语,皆依句法,与平常文法意思不同。为“一正”“一助”之句法,“子”“荡”为正,“之”“兮”为助。[7]
以上释文表现出:
(1)徂徕先生认识到“之”兼有助词、代词、动词用法,前两者为“助语”,将“之”字的虚词、实词义项作出了区分。
(2)标明作虚词用的“之”有“指示”义,指出“之”用在词组中,前后语义必有所侧重。以“大学之书”为例,“之”在其中,则必为偏正关系,或强调书的内容为“大学”,或强调是《大学》这本“书”。
(3)比较虚词“之”和“其”,“之”和“而”间的细微差别。“大学之书”义为“《大学》这样的书”;“大学其书”则强调《大学》一书。“而”为转折关系;“之”为顺接关系。
(4)从词语配合规律的角度对“之”字加以解释,指明“之”下字必为“死字”,即“名词”与活用作“名词”者。所指可具体、可抽象,可以是“理”“事”“物”“时”“处”。例如“气质之禀”的“禀”不读作“领受”,“三代之隆”的“隆”不读作“旺盛”,因为这些读法均为“活字”,不合“之”下为“死字”这一规律。
(5)指出理解虚词时,诗、文句法有别。如“子之荡兮”为一正一助之句法,与平常文法意思不同,应区别对待。
又如“其、厥、夫、那、尔、彼、某”词条释义:
○“其”“此”“彼”同为指物之辞,和训分别指眼前、身边和对面之物。“彼”“此”,可置于句中任何位置;“其”较“彼”“此”字轻,不能置于句末。若用在词语之前,“夫”字作发语辞,“其”和“夫”不同。“其”读作“那~”,以“那”“物”连下;读作“那个”,下为“那个”做什么。读作“那~”,置于死字之上;读作“那个”,置于活字之上。又“其”字置下时,同句末的“夫”字。○“厥”是古字。读作“那~”,同“其”,但比“其”字音塞,有“大概”义。○“那”是俗语的“其”。○“尔”是“尔后”“百尔君子”,指物之辞,应参见古人用例。○“彼”与“此”相对。○“某”译作“ナニガシ”。○“夫”字读作“这~”。“其”字迫切,“夫”字悠缓,故“其”字训作“ソノ”(那~),“夫”字训作“ソレ”(那個)。“彼”“此”二字相对指意。“夫”“其”,均可置於“彼”“此”之上指意。故,“其”字可与“彼”“此”二字叠用,又“夫”字比“其”字悠缓,故可与“彼”“此”“其”三字之意叠用。[7]
以上释文表现出:
(1)释义中以和语对译,参考和训。释“其”“此”“彼”作“それ”“その”,分别指眼前之物、耳边之物、对面之物。
(2)通过在句中所处位置说明虛词用法。如说明“其”字一般不出现在句末,“彼”“此”则较随意。又如说明“夫”字置于篇头,用作发语辞;出现在篇中,为更换词端用语;出现在句末,同句末“其”字用法。
(3)从词语配合规律上,解释虚词用法特点。如释“其”用作连体词“その”時,置于死字之上,构成词组“那~”;“其”用作代词“それ”時,置于活字之上,构成句子主语,表“那个”做什么。
徂徕先生认识到词语配合都有一定的规律,但对规律的把握还带有日语的印记。在日语中,“その”是连体词,须加名词构成词组才可使用;“それ”是代词,可以独立作句子成分。“その”后续名詞,与单用“それ”,有相同的指代功能。如“その本”和“それ”,都可指代“那本书”。“その”“それ”之別,用在解释“其”字的不同意项上过于牵强。如《诗经·周南·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此“其”字用在名词上;《三国志·魏志·贾诩传》:“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此“其”字用在动词上,两例似乎正合荻生氏的解释,前者相当于“その”,后者相当于“それ”。但实际上,两例中的“其”均为第三人称代詞,前者表“领属关系”,后者表“指代性”关系。
(4)同义、反义互训。如以“其”释“厥”“那”“夫”,以“彼”“此”互训等。
(5)从发音的不同来区分近义虚词。如“夫”“其”两字义同,但“其”字迫切,“夫”字悠缓,故“其”字可与“彼”“此”二字叠用,“夫”字比“其”字悠缓,故可与“彼”“此”“其”三字之意叠用。这种释义方法在我国虚词专书中也较常见,但过于主观。
再如“坐、立、默、动”词条释义:
“坐”读作“自然地”,《文选》:“惊沙坐飞”,注作“无故而飞”。未经察觉就呈现那样子。
“立”表动作十分迅速,“立刻”“忽然”意。
“默”在“默契”“默仪”“默运”等词中,应译作“自然而然地”“不知不觉地”。
“动”有“动辄”意。[7]
以上释文表现出:
(1)“坐、立、默、动”行为性明显,用作动词比用作副词常见。徂徕先生认识到“坐”有“自然地”“漠不关心”意,“立”有“立刻”意,“默”有“私下”意,“动”有“动辄”意,对词语虚、实之别的判断已较为纯熟。
(2)释义中继承前人古注。“坐”释作“自然地”,是从《文选》注继承而来。《文选》:“惊沙坐飞”,注作“无故而飞”。
(3)收在卷五“仅、才、乍、忽、倏、怳”词条的“乍、忽、倏、怳”训作“立刻”意。“立”同样训作“立刻”意,却归在本条内。大概是由于徂徕先生认识到“立”有副词义项,但不同于“仅、才、乍、忽、倏、怳”这样纯粹的副词,而“坐”“立”“默”“动”都兼有动词、副词的义项,在词类特点上有更广泛的共性,因此归为一组。
《训译示蒙》以“助语”(即虚词)为注释对象,列出其对应的日语和训、译文,又从语法功能等方面描述其用法,以此教示汉文初学者。此书的虚词研究有三大突出特点:(1)重视汉语中普遍存在的一词多义现象;将既可用作虚词、又可用作实词的词语加以说明,强调区分词类问题。(2)注意到用法相近的虚词间的细微差别,善于通过比较进行释义。(3)重视虚词的语法功能,通过描述词与词的配合规律、虚词在句中的位置等,来解释虚词用法。
但也存在不足,释义中有部分主观描述,如释“其”字迫切、“夫”字悠缓,故“其”字可与“彼”“此”二字叠用,“夫”字可与“彼”“此”“其”三字叠用。另外,一些释义中也带有日语的特点,如释“其”有“那~”和“那个”意,这在日语中属连体词和代词之别,但在汉语中不能算作意义差别。不过瑕不掩瑜,《训译示蒙》一书的内容早在18世纪初期就以《译文筌蹄》写本的方式问世,在300多年以前,徂徕先生已在理论探索的基础上研究汉语词义问题,并能从语法功能的层面描述汉语虚词的使用规律,这在当时,可以说极具进步意义。
[1]田尻佑一郎.日本思想家15荻生徂徕[M].东京:明德出版社,2008:133.
[2]吉川幸次郎,小岛宪之,户川芳郎.汉语文典丛书·译文筌蹄[M].东京:汲古书院,1980:225-358.
[3]王宝平.清代中日学术交流的研究[M].东京:汲古书院,2005:475-476.
[4]牛岛德次.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3:19-20.
[5]陈景彦,王玉强.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儒学的吸收与改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9.
[6]吉川幸次郎,小岛宪之,户川芳郎.汉语文典丛书·译文筌蹄初编[M].东京:汲古书院,1980:3-157.
[7]吉川幸次郎,小岛宪之,户川芳郎.汉语文典丛书·训译示蒙[M].东京:汲古书院,1980:7,7-8,22,26,44.
(责任编辑陈方方)
H131
A
1672-8254(2016)05-0078-04
2016-03-15
王雪波(1985—),女,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博士研究生,从事古代语言学文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