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反腐困境
2016-09-20李永忠
李永忠
1982-2011年30年中,因违犯党纪政纪受到处分的党员、公职人员达420余万人,其中省部级官员465人;因贪腐被追究司法责任的省部级官员90余人,其中从2000-2007年,有5名省部级和1名副国级高官被判处死刑(不含军队数据)。
截至2015年11月11日,全国各省(市、区)均有省部级高官落马。2016年4月1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载文指出:“天涯无净土,各地区各部门只有问题多与少的区别,没有没问题的。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是政治,也是警讯。”(《把握运用“五条体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之五》)
十八大以来3年多落马的163名高官中,地方副省部级以上110人;军队副军级以上53名(其中3名上将、6名中将、39名少将,还有5名大校)。163人中:包括副国级以上5人,本届中央委员8人,候补委员12人,中央纪委委员2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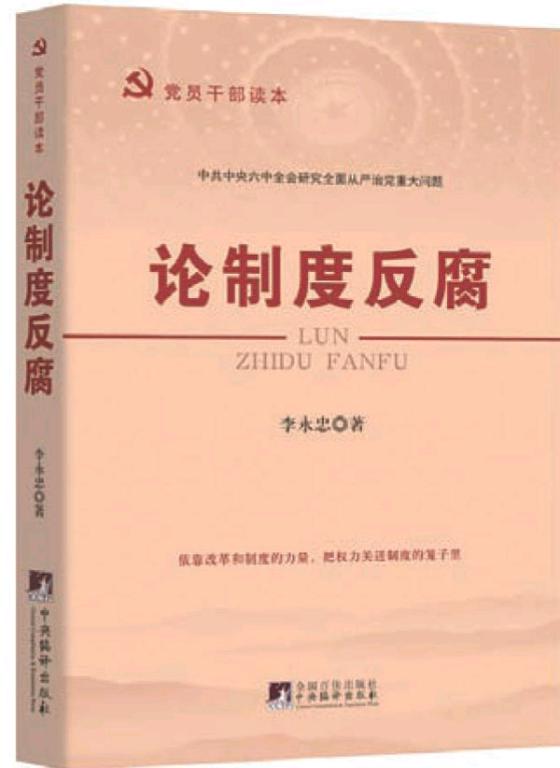
十八大以前,只要不搞运动,全国年平均处分率通常在1.5‰-1.7‰徘徊。2013年突破2.1‰,2014年突破2.6‰,2015年突破3.9‰。3年来全国共处分党员、公职人员75万人,移送司法机关3.6万人,占75万人中的4.67%。
3年来,中央管理干部立案189人,移送司法机关80人,占189人中的42.3%,接近一半。
3年来,本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委、中央纪委委员落马22人,占两委委员总数5.5%,年均1.8%,而且几乎都要进监狱面临重刑。
十七届政治局委员25人加书记处5人,减去既是政治局委员又是书记处成员3人,实为27人,已有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薄熙来、令计划5人落马,占上届中央领导成员总数的18.5%。除了徐才厚已死,其余均为无期徒刑。
上述数据折射出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越是位高权重,越容易犯错误,越容易落马,越容易受重处分,越容易被判重刑?
其实,在常人看来难以理解的问题,无不同我们沿用至今的苏联模式有关——不科学的权力结构和不合理的选人用人体制,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两大根本性原因!
苏联在成为全球第二个超级大国的过程中,也曾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也满满地自信过……但他们既忽视了自身权力结构的先天不足,又忽略了选人用人体制的后天不良!苏联模式的这两大根本性弊端,无法支持其长期执政的愿望!苏联共产党每10年翻一番查处腐败案件,证明其反腐并非不坚决;苏联共产党各级党委、组织部每年都从少数人中挑选少数人,证明其选人并非不认真!然而,一个偶然的“8·19”事件,让拥有近2000万党员(亡党前有420万党员退党)的执政党,在几天内便结束其执政生命;让拥有200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苏联,在几个月内便分崩离析、悄然瓦解……
对这样一个结局,不仅苏联党内外无人料到,各社会主义国家莫名惊诧,乃至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世界都难以预料……
然而,苏联亡党亡国的前后,采用苏联模式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传来一片多米诺骨牌的倒塌声……
四分之一世纪来,研究分析苏联亡党亡国的文章著作成千上万,有说错选接班人,有说“两杆子”失控,有说石油价下滑,有说民族矛盾激化,有说西方势力操纵……却少有人分析其长期治标的权力反腐之殇,也鲜有人研究其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的深层次弊端……
其实,邓小平在36年前的“8·18”讲话中就找到了“权力过分集中”这一“总病根”,30年前从“苏联模式”中查找总根源……
受其启示,30多年前,我开始了对制度研究,特别是对权力结构研究的兴趣。1984年撰写了《略论我国封建社会监察制度》,1985年撰写了《改革党内监督制度》和《改革党委“议行合一”领导制度》,1986年撰写了《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当时没有报刊刊登我这篇文章。直到1994年11月20日才登载在《人民日报》内刊《理论参考》上。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把党的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之中”;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相并列;2012年十八大报告中,第一次把制度建设放到党的五大建设的最后,作为前四大建设的托底。
这些研究的点滴积累,使我明白,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时,同样采用苏联模式的中国却能一枝独秀,其奥秘就在于当时中国1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主要是民营企业)大多摒弃了苏联模式的两大根本性弊端,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是市场经济用脚投票“选举”出来的,而非各级组织部培养考察选拔并按等级授职的方式任命。正是这快速做大的“蛋糕”,支撑了中国在苏东剧变中的一枝独秀。
但是,经改的快速做大蛋糕,与政改的严重滞后,也造成了两极分化加速,党群关系疏离,干群关系紧张,腐败愈演愈烈……
3年多的高压反腐,既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的坚定决心和明显成效,也折射出30多年权力反腐留下的巨大腐败存量和呆账,同时反映出我们还要从政治领域摒弃苏联模式的决绝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尖锐地指出:“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我以为,苏联在亡党亡国前,一是没有形成我们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二是没有经历过我国十年“文革”的浩劫;三是还有相当多的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宗教信仰。因此,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制度反腐,走出多年的反腐困境,不能恢复和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一旦亡党亡国,将可能是人类史上最血腥、最惨烈的浩劫……
正是清醒地认识到可能的危险,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为了国家、民族、政党的明天,党十八大以来积极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既是对此前主要失误的纠偏,也是他40多年治国理政的深思熟虑。而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其主题就是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既要解决严厉问题,更要解决严密问题。在我党的历史中,先后经历过战争反腐、运动反腐、权力反腐三个阶段。
以战争为载体的反腐,与血与火的年代是适应的。以运动为载体的反腐,与计划经济的建设时期也基本相适应。但是,尽管依靠隔三岔五的群众运动,遏制了腐败的滋生蔓延,却严重干扰了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同时还造成了党内关系的人人自危。
30多年的改革开放,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以权力为载体的反腐,与市场经济却严重的不相适应——致使腐败“越演越烈”(习近平语)。
2013年1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习总书记下定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反腐决心;2014年1月,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习总书记明确了“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反腐或政改目标;2015年1月,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习总书记作出了“制度治党”“重构政治生态”的战略规划。制度反腐开始发韧。
如果说战争、运动、权力三大载体,在反腐中主要是解决严厉的问题;那么以制度为载体的反腐,则主要解决严密的问题。
制度一词有两层含义:一为浅层含义上的规章、守则,即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表现为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条条款款;一为深层含义上的组织体系(其核心为权力结构)。即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衡的“专门机构”,以保证上述规章、守则(即那些嘴上、纸上、墙上的条条款款)制定公正、实施有效、监督到位。
判断好制度有三要素:第一,客观性。不能脱离和超越其产生的那个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第二,代表性。必须体现大多数人的整体意志和利益。第三,可操作性。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取决于构成其权力结构的决策机关是否公平,执行机关是否高效,监督机关是否有力。也即这三个子系统的设置是否科学、结构是否合理,操作时能否有效地相互制衡并相互促进。
30多年前,我在潜心于制度建党、制度监督、制度反腐的自选课题研究中,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防止腐败(我将腐败称之为权力事故),制度比人更重要。
其一,制度虽然是由人制定的,但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制度,人们却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制定。因而,能被称之为好的制度,必然是人们对客观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反映。
其二,好的制度一旦制定出来,包括制定者都无法随心所欲去违反。因而好的制度,必然以强制性为后盾,而非仅以自觉性为前提;必然以科学分权的“专门机构”有效权力制衡为保障,而非只以颁布若干规章、守则为目的;必然体现客观发展规律,成为一种客观存在,而非仅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所以也不是人的主观愿望所能轻易改变。
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大多数人包括相当数量的领导干部,对于制度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制度浅层含义上的条条款款,而忽略制度深层含义上的组织体系(核心是权力结构),对于习总书记“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这一重要论断严重缺乏认识和理解。
我在多年前,对制度反腐做过如下定义:通过对沿用于苏联模式的现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的、科学的权力结构来防治腐败。
领导制度的核心,是权力结构;组织制度的核心,是选人用人体制。
权力结构则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排列组合方式。
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权力结构)和组织制度(选人用人体制)采用的都是苏联模式。因此,1980年8月18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标题就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是《邓小平文选》中含金量最高的论著,时隔36年,仍然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30多年反复研读邓小平“8·18”讲话,并不断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我懂得了:制度反腐,必须以权力结构改革为前提,必须以设立政改特区为条件,必须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为取向。而权力结构改革,则必须以摒弃苏联模式为前提,必须以合理分解权力为条件,必须以“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为目标。
实践证明:问题的复杂性,通常不是来自于问题本身;而是因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远离原点的缘故。
如果只满足于权力反腐的思维定式,无论纠多少风,查多少案,抓多少人,判多少刑,只要腐败的病根不除,一旦反腐高压无法继续,所有努力,都会瞬间归零。
反腐的压力当然在案中,功夫却必须在案外,成功则只能靠改革。
对于恶化多年的政治生态,靠什么来净化,靠什么来重构?
从战术而言——靠查案。但是,查处一案只能净化一时,案又滋生则污染一片。
从战役而言——靠用人。但是,用一君子虽然所属皆净,用一小人则此地全污,何况靠什么阻挡君子变小人?
从战略而言——靠制度。因为,制度好则坏人难成坏事,制度坏则好人易变坏人。
再好的权力反腐,也只能治标;通过政改,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制度反腐,才能治本。
有鉴于此,我将这30年来我发表于各类报刊中有关制度反腐的文章集结成书,以此说明什么是制度反腐,制度反腐有哪些要素,并以此求教于各位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