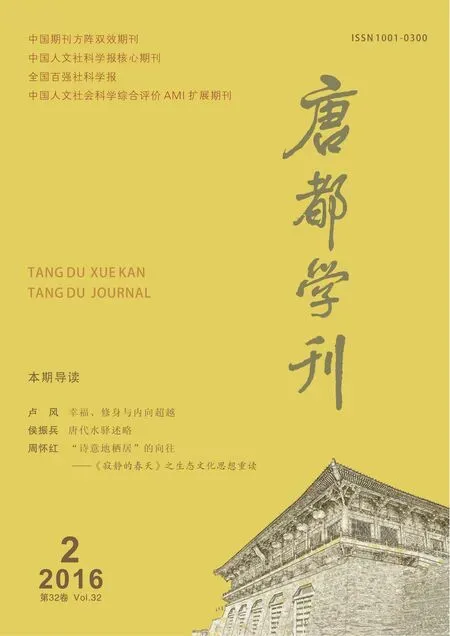从先秦文献命名方式看《离骚》篇题及其内涵
2016-09-20张世磊
张世磊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济南 250199)
【博士论坛】
从先秦文献命名方式看《离骚》篇题及其内涵
张世磊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济南250199)
有关《离骚》篇题的内涵,从古至今有许多种解说。最早司马迁解为“离忧”,班固解为“遭忧”,王逸解为“别愁”。到当代又有学者从一些新的学术视角解为古乐曲之名等等,皆言之有据。然而“离骚”首先是作为篇名存在的,探究先秦尤其是战国时期文献篇章的命名原则及其相关文化背景,无疑是首先要做的。通过对先秦文献篇题命名方式的探析,可得出《离骚》篇题的命名方式是依文本主旨内容而定,通过对《离骚》文本内容分析,应解为因是否离开(楚国)而愁苦。
屈原;《离骚》;篇题命名;篇题内涵
从汉初至今两千余年,“离骚”二字似乎已没有了什么“秘密”,甚至我们还透视了它的“秘密”。但对这首长诗,若让我们详细说出它的原委,理清它的内容脉络,恐怕谁都不能如数家珍。而作为篇题的“离骚”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涵,它与诗篇内容存在怎样的关系,却因《离骚》艺术样式的神幻性、原古性,似乎也不容易弄清楚。以往我们对于《离骚》的认识,是较为宏观的,即它是屈原在遭谗被疏后所作的抒情诗,但从微观上看,包括《离骚》篇题在内的很多问题还不能得到定论,一些研究多数还在讨论之中。这也表明限于各种条件,我们还不能完全把握《离骚》。新时期以来,出土战国楚地的文献资料是十分丰富的,我们试图通过对这些文献篇题的考察,结合现有传世先秦文献的篇题命名现象,把《离骚》篇题的命名切实还原到战国中期那个时代背景当中,力求能通过把握其命名方式进而揭示其篇题内涵。
一、《离骚》篇题解读简述与先秦文献命名方式
关于《离骚》篇题的解读,如今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大约有以下几种: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说“离骚者,尤离忧也”[1]3010,他把“骚”字训为“忧”,对于“离”字,没有做出解释,但结合《列传》上下文,司马迁所认为的“离”应通“罹”,是“遭遇”之义。“离骚”即“罹忧”。
班固在《离骚赞序》中说“离,犹遭也。骚,忧也”[2]51,明确将“离”训为“遭”,“骚”训为“忧”,“离骚”即是“遭忧”,班固此说实则与司马迁说相同。
王逸在《离骚序》中说“离,别也。骚,愁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2]2,王逸将“离”训作“别”,“骚”训作“愁”,“离骚”即是“别愁”。根据他说“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别愁”应存在一种因果关系。其中将“离”训为“别”,与马、班有异,将“骚”训为“愁”,与马、班训作“忧”无区别,因为我们至今还在使用“忧愁”一词。
近现代以来,游国恩有“牢骚”说,他说“我以为《离骚》可能本是楚国一种歌曲的名称,其意义则与‘牢骚’二字相同”[3]。
萧兵从民俗学入手,认为“离”即是《山海经》中的“离朱”,是楚人崇拜的太阳鸟,而“骚”他倾向于认为是“歌”,由此他认为《离骚》的最古义便可能是“太阳鸟的悲歌”[4]。
黄灵庚则认为“‘离骚’即‘离箫’也”,“离箫,咏颂大舜的功德之乐,是歌咏有虞氏的图腾之歌,是属于有虞氏的凤鸟文化”[5],也是从古曲角度来阐发。
姚小鸥认为“离,别也,即远逝;骚,懮也,即悸动”,并说“‘离骚’描述了屈原决计远逝自疏、即将离别故国时的心灵悸痛,简言则为‘离别之痛’”[6]。
以上所举诸家对于“离骚”的题解,或从训诂入手,或从古乐曲名称视角入手,或从文本内容入手,都言之有据,富于启发性。然而随着《离骚》离我们渐愈久远,加之其文本内容包含了多种原古性、巫术性的艺术样式,人们更愿意相信“离骚”应包含有某些宗教般神秘性的内涵。事实也是,自汉末以后“离骚”似乎成了一个意象,成了屈原文化现象的一个代名词。我们以为,这种历史传承中堆垒起来的带有文化性的认识,并非就是《离骚》篇题的本初内涵,要解析“离骚”的篇题内涵,首先要有一个前提性的认识,即它首先是作为一篇诗歌的名称存在。因此考察先秦文献典籍命名的方式、原则及相关文化背景,对于释解《离骚》的篇题无疑是应该首先要做的。
有关先秦文献篇题命名的情况,我们不妨先从考察传世文献典籍的篇名入手,先来看《诗经》。《诗经》305篇,不论是风诗、雅诗还是颂诗,对照其篇题和诗篇文本来看,明显可以看出其篇名都是源于撮取篇章首句几字,首句字数较少者则径直以首句为名,如《麟之趾》《殷其雷》《野有死麕》《南有嘉鱼》等等。基于这样的一种事实,《诗经》各篇的篇名,可以说均没有什么深刻内涵。因为《诗经》中诗篇的首句大多是起兴的,其中一些诗文的首句甚至与诗文内容没有什么关系。
《论语》篇名取定的原则也是如此。《论语》共20篇,篇名分别为《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结合篇章文本看,篇名也是取相应篇章首段首句的前几字而得来,多以二字为名,三字者皆是人名,想必是没有办法强为二字。如《学而》篇,首段首句为“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7]3《公冶长》篇首段首句为“子谓公冶长:‘可妻也’。”[7]109《子罕》篇首段首句为“子罕言利”[7]220,其余篇章的命名形式也是如此,没有例外。这些篇名,也均无什么独立性的含义,一些甚至还不具备基本名词的规范性,如《子罕》分明是强取“子罕言利”前二字,这些篇题所起到的只是标记篇章的作用。
楚地文献《庄子》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通过比对内、外、杂篇中各篇篇名与相对应的文本内容,我们发现《内篇》各篇名,皆为依文章内容主旨而定,篇名所反映的内容基本就是文本所论述的主题。《外篇》《杂篇》则无一例外地都是撮取文章首句几字为名,与《诗经》《论语》各篇章名称的取定原则相同。
再看《荀子》32篇,同样对照其各篇文名与相应文本内容,《荀子》各篇题之名以总括所论内容为名者居多,只有《不苟》《仲尼》《儒教》《哀公》《议兵》《性恶》《成相》《大略》是撮取篇章前几字为名的。
我们通过对这四部文献篇题的考察,能得到以下认识。首先,可以把这些文献篇章的命名原则归纳为两种:一是撮取篇章首句几字为篇题,二是以所论篇章内容主题为篇题。其次,我们还发现时间越早的文献,其命名方式越是简单,往往是撮取篇章首句几字为题,如《诗经》《论语》无一例外地是以篇章首句几字为名。到了《庄子》,就开始有以篇章所论主要内容为篇名的现象了,但仅限于内篇。到《荀子》,这种命名形式便多起来,而以简单撮取篇章首句几字为篇名的现象却很少了。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中说:“其有古人手著之书,为记一事或明一义为起讫者,则以事与义题篇,如《书》之《尧典》《舜典》……。其有杂记言行,积章为篇,出于后人编次,首尾初无一定者,则摘其首简之数字以题篇,《论语》之《学而》《为政》,《孟子》之《梁惠王》《公孙丑》是也。”[8]所说的也是这两种命题形式。
这里就考察传世文献命名而言,其实也存在一个问题,即起初很多文献是没有篇名的,甚至连作者的名字也没有,一些文献资料篇章的篇名可能为后人整理时所加。对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相关出土文献的篇题命名方式来进行补充。
近几十年来,我国出土文献资料是十分丰富的,而恰恰又以先秦楚地文献资料为盛。出土文献的优势在于,一是时间上早,二是它没有经过后人整理,保持了下葬之前的原貌。新时期以来出土文献资料规模较大者,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郭店楚简以及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回的上博楚简,还有自香港抢救回归由清华大学校友向清华大学捐赠的清华楚简。巧合的是,经专家的鉴定以及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测定,这三批楚简的时代相近,都为战国中后期,与屈原活动期相贴合。其中上博楚简和清华简又都是典型的古代书籍,上博简全名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由其名即可得知;清华简全名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李学勤先生在其文《初识清华简》中说:“通过清理间的大致浏览,以下三点是可以确定的”。其中第一点即是“这批简的性质是书籍”[9],既然二者都是书籍,那么考察它们的篇章命名方式、原则,是能够映射出那个历史阶段有关诗文篇题命名的相关原则的。
首先来看《上博简》,上博简的编者在《上博简(一)》中的《凡例》中对这批简的篇题情况,有一个简要的说明,“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中,共发现二十余名时人书写的篇题,这些篇题一律按原名刊出。凡篇题缺损者,由注释者按文义内容题名。”[10]1从这则说明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信息:一是这批楚竹书有些是有篇题的,有些是没有篇题的,而且没有篇题的文献数量要更多;二是整理者在给没有篇题的文献命名时,遵循的一个原则是“按文义内容题名”。下面就结合《上博简》中的具体篇章名称来看。
据整理者说,《上博简》(一)中的《孔子诗论》篇和《上博简》(二)中的《子羔》《鲁邦大旱》这三篇文献的“字形、简之长度、两端形状,都是一致的,一个可以选择的整理方案是列为同一卷”[10]121,其中在《子羔》篇第三支简的背面有卷名《子羔》,整理者根据这三篇文献内容的差异,提出了两种可能性,即“同一卷内有三篇或三篇以上的内容;也可能用形制相同的简,为同一人所书,属于不同卷别”。这里不论是哪种可能,可资确定的是,现已出版的《孔子诗论》篇与《鲁邦大旱》篇是没有篇名的,都是整理者根据文义内容所加。《子羔》篇原有篇题,从《子羔》篇的第一支简来看,有“子羔曰”,其篇题即据此而来,这毫无疑问是撮取首句几字为篇题。
《上博简(五)》中的前两篇文献《竞建内之》和《鲍叔牙与隰朋之谏》都是有原篇题的,并且篇题都与它们的文本内容紧密相关,如《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就是讲的鲍叔牙和隰朋向齐桓公进谏的事。
《上博简(八)》中有几篇文学色彩很强的文献,《李颂》《兰赋》《有皇将起》《鹠》,在原简中这四篇文献均无篇题,其中《有皇将起》是整理者取该篇章首句前四字作为篇题,其他三篇篇题均为整理者依据文献内容定名。综观现已出版的《上博简》,关于其篇题的情况是:大量的文献并没有篇题,有篇题者,多以撮取篇章首句几字为名,也有以文义内容为篇名者。而对于没有篇题的文献,整理者基本也是遵循以上这两种命名形式给其定名。
我们再看清华简,编者在《清华简(壹)》的《凡例》中也有关于这批简篇题及其定名情况的说明,即“竹简各篇,凡原有篇题者以原篇题为名,无篇题者由整理者拟定。原篇题字数较多者,括注简称或传世文献中相应的篇题,如《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祭公之顾命》(《祭公》),并在引文及字形表中使用简称”[11]。相较于《上博简》的介绍,清华简编者的介绍要简单一些,但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清华简一些文献有篇题,但也有许多没有篇题的文献,没有篇题的同样由整理者拟定。下面也结合清华简的具体篇章来看。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有一篇题为《系年》的文献,整理者在其说明中说“原无篇题,因篇中多有纪年,文字体例与若干内容又近似西晋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故拟题为《系年》”[1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整理者是依文义内容来为其定名。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中的《说命》,在关于其说明中整理者说:“《说命》简长四十五厘米,共有三篇,由同一书手写成。每一篇最后一支简简背都有篇题《傅说之命》,现据内容次第分别题为《说命上》《说命中》和《说命下》”[13]121。而结合文献内容看,原篇题《傅说之命》是依文本内容定的。《芮良夫毖》也无篇题,整理者也是“据简文内容另批篇题为‘芮良夫毖’”[13]144。“《良臣》与下篇《祝辞》,原由同一书手写在一编相连的竹简上,共十六支简,简长三十二·八厘米,无篇题。鉴于两者内容性质截然不同,今分别拟题为“良臣”、“祝辞”,作为两篇处理。”[13]156显然这两篇简文也没有篇题,整理者依据文义内容给其定名。《赤咎之集汤之屋》篇,是有篇题的,“第十五支简简背下端有篇题‘赤咎之集汤之屋’”,而结合简文首句“曰故有赤咎,集于汤之屋”[13]166看,这一篇名当是依据首句几字而来。据此,就已出版的清华简的篇题情况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认识:清华简中,有许多没有篇题的文献;而有篇题者,其篇题名称的制定,也遵循或依篇章内容而定,或是取篇章首句几字为题这样两条原则。对于没有篇题的文献,整理者多是以文献内容为据定其篇名。
二、屈辞篇章命名方式及《离骚》篇题命名原则
就文献篇题的命名情况,我们不妨再从屈原作品自身看一下,除去我们所论的《离骚》,屈原作品还有《九歌》之《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国殇》《礼魂》,《九章》中的《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以及《天问》《远游》《渔父》《卜居》《招魂》《大招》。
其中《九歌》属于固有乐曲之名,《山海经》与屈原《离骚》《天问》中都曾提及这一曲名,《山海经》中载“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雨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14]。《离骚》中载“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2]21,“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娱乐”[2]46。《天问》中载“启棘宾商,《九辩》《九歌》”[2]98,这三处所提及的《九歌》都是古夏启《九歌》,不论其性质是巫乐还是祭祀之乐,可确定的是“九歌”是乐曲名。就屈原之《九歌》看,可以肯定地说它是祀神乐歌,其中各篇目之名皆以所祀之神的名字而定,最后总以已有的乐曲名《九歌》。屈原与《九歌》的关系,是重作,是改作,还是独创,学界尚存有不同认识,但可以达成共识的是《九歌》是祀神之歌,是乐歌,因此《九歌》之名不是屈原的创造,与原有《九歌》必然存在一定的关系。就《九歌》言,我们可以概括是延用原有古乐曲之名。
《九章》中的《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橘颂》,根据篇题与文本内容间的关系,可总结为以文本所述主旨内容定名。《天问》《远游》《招魂》《大招》《卜居》《渔父》也属于此类命名形式。《九章》剩余篇章,《惜诵》《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则以诗文首句几字为篇名,如《惜诵》首句为“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思美人》首句是“思美人兮,揽涕而伫眙”,《惜往日》首句是“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悲回风》首句则为“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这与《诗经》中篇章命名的方式是相同的。
通过上文对屈原作品篇题命名情况的分析,可把除《离骚》之外的其余所有屈原作品的篇题命名方式概括为三类:一是篇题之名沿用原有古曲乐歌之名,具体篇目之名以所祀之神的名号为之;二是以总诗文所述主旨内容为名;三是撮取诗文首句几字为名。准此,我们看,除《九歌》之外,屈原其它作品的命名方式与上文我们所举的传世文献的命名方式及出土文献的命名方式并没有任何的不同。屈原《九歌》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是一组祭歌,篇目之名皆以所祀神之名为之。若是硬要归类,似也可以归为以诗文所述主旨内容为名的行列。
既然现有屈原作品与我国先秦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的命名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么上文我们所列举的除《离骚》之外的屈原其余所有篇章命名之方式总有一种会适于《离骚》。也即是说,在屈原全部作品中,就篇题命名上看,《离骚》不会是一个特殊,即使它对于屈原其他作品的命名方式是一个特殊,对于整个先秦文献的命名形式来说也绝不会是一个特殊。
反观以上我们对先秦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命名方式的考察,包括除《离骚》外的屈原其余作品篇题的命名形式,其样式基本可概括为:撮取篇章首句几字为篇名;以概括文本所述主旨内容为篇名;延用原有古乐曲名为篇名,这三种形式。由此我们认为《离骚》篇题的命名原则应该合乎这三种命名方式中的一种,不妨拿《离骚》与之一一对照。
从现存所有的文献来看,屈原《离骚》之前,还没有发现作为古乐曲的《离骚》存在。甚至同名的其他文献也没有,也就是说,《离骚》不可能是延用原有篇题名称。从《离骚》文本内容看,其中有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的“朕”、“余”、“吾”,结合相关诗句来看,显然为抒情之作,而且《离骚》也不可能是神名,由此可以判定《离骚》篇名的制定不会同于《九歌》及其诸篇之名。
《离骚》首句为“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不包含“离骚”二字,所以《离骚》篇题的名称也不会是撮取文本首句几字而来。
那么《离骚》之名,就只能是总括诗文主旨内容而来了,我们以为是这样。
上文所举诸家对于《离骚》篇题的解释,不论是司马迁的“离忧”说、班固的“遭忧”说,还是王逸的“别愁”说,他们的这些解说或多或少都有着眼于《离骚》的内容来训解的一面,而姚小鸥先生则主要依靠《离骚》文本内容来解析“离骚”,根据上文我们所论,这种解释的路子无疑是正确的。
我们在探究先秦传世文献篇名时,已经得出时代越早的文献,其命名方式越是简单,《诗经》《论语》的篇名无一例外都是由文本首句前几字而来。而到与屈原作品相近的《庄子》以及出土的上博简、清华简中的文献都有许多以总括文义内容为篇题的现象了,这表明屈原作品所处的时代根据文本内容敲定篇题是可行的、是流行的。且屈原作品本身的命名现象也已能证明这一点。既然《离骚》篇题之名依文本内容而定,我们就要对其内容主旨作一番考察。
三、《离骚》文本内容及其篇题内涵
正如人们所说,《离骚》是一篇抒情性非常强的作品,但同样它的叙事色彩也很明显,据此,可把这首长诗以“女媭之詈”为界,分成两个主要部分。“女媭之詈”之前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实写的,主人公交代了其出身正统,又有合天地之正的“内美”,且又“好修以为常”,他希望能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但现实是“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以齌怒”,“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2]8-15。即使不看司马迁《屈原列传》和刘向《新序·节士》的有关记载,仅凭此我们也可推断出,屈原本是正直向善一心为国的,无奈遭到小人谗毁,而君王又不分青红皂白,不但不能给他公正,而且还将其疏远,自己是非常无辜的,因此作者内心非常哀伤,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这是“女媭之詈”之前的第一部分给我们呈现出的主要内容。
如果翻阅《国语》和《战国策》,屈原的这种遭遇在春秋战国士人中还是有一定普遍性的,不同的是士子们在一国遭遇谗毁,而君王又不能给以公道,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去另外一国,那么屈原是否会这么做呢?结合屈原的生命结局来看,他最终沉身汨罗江,显然他没有离开楚国;但若结合《离骚》的下半部分内容看,屈原确实是有离开楚国想法的,并且为此纠结、痛苦。其实《离骚》下半部分“神游求女”、“灵氛占卜”、“巫咸夕降”等情节的描写,就是在纠结是否要离开,以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
“神游求女”的描写,虽然被学者们坐实为多种解说,如“求君”说、“求贤臣”说、“求志同道合者”说等等,但可以肯定的是,主人公的这种求索,是在寻求一种“两美相合”,映射到现实中,即是寻求一种理想的政治环境,一种能实现美政的政治环境,这足以证明屈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2]34,显然楚国的现实状况不能给他一个实现政治理想的环境。于是他请灵氛占卜,灵氛说:“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2]35,主人公“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于是又请巫咸来确证,结果是“皇剡剡其扬灵兮,告余以吉故”,印证了灵氛之占,于是主人公“历吉日乎吾将行”,他是想离开楚国去寻求这种政治理想的。但诗篇最后结果是“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2]47,在他终将离开的那一刻,是“旧乡”让他“蜷局顾而不行”,陷入了一种矛盾和纠结当中。使屈原纠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主要的无疑是“旧乡”因素,这正好与《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的身份相照应,这是一种宗族根性意识的表现。因此《离骚》下半部分内容,可总结为屈原为实现两美相合的美政,决计离开楚国,但在将要离开时,却又陷入一种纠结之中,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即是对宗族根性的认同。因为从本质上讲,他若离开楚国去实现其政治理想,不论去哪一国,终将会与楚为敌。
而把《离骚》这两部分内容串联在一起的,正是夹在它们中间的“女媭之詈”这一节。如果说《离骚》这两部分内容的核心是屈原离不离开楚国的问题,那么“女媭之詈”这一节则是描写对于“中正”与“姱节”,屈原坚持不坚持的问题。我们看其内容:
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

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2]19-20。
女媭这番话的核心在于拿鲧之例作比让屈原放弃“中正”与“姱节”,这对于屈原来讲,实际上就等于让他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这时他有两种选择:要么坚持,要么放弃。若屈原选择放弃,留在楚国随波逐流,那么自然不会再纠结,《离骚》也便不会有下半部分内容;但屈原选择的是坚持,坚持“中正”、坚持“姱节”、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同样是艰难的,紧接着“女媭之詈”的是“重华陈词”一节,此一节在屈原进行选择的心路历程上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该节列举“启”、“羿”、“夏桀”、“后辛”、“汤禹”之例,就是要证明君王的正直、贤明、德性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而楚国上下显然是不分是非、嫉贤妒能的,依据历史的经验,这样的国家必将会消亡。由此屈原得出“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揽余初其犹未悔”[2]24,毅然坚持本初的理想信念。于是也就有了下半部分纠结是否离开楚国,去追寻自己政治理想的描写。
而从屈原所述“重华陈词”这一节,也让我们看到,一位不淫奢、不骄靡、贤明有德性的君王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恰好在《国语·楚语上》的《伍举论台美而楚殆》篇中,楚大夫伍举对楚灵王为满足一己之私欲而建造章华台的行为表达了不满,其中有说到“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其中对于“骚离”的解释,徐元诰撰《国语集解》的注释为“骚,愁也。离,叛也”[15],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的《国语》中,对“骚离”的解释也是“骚,愁也。离,叛也”[16]。若准此,伍举的这句话则可以解释为:如果君王不推行德与义,那么国内的贤士就会忧愁叛离,其他国家就会抗拒违命。事实也是如此,楚灵王为满足一己私欲,大肆收刮民财,建造章华台,想邀其他诸侯王一起登台,而结果是“诸侯皆拒无有至者”。
而对于迩者之“骚离”,主要还是因为在楚国遭遇愁苦不幸而叛离,这种叛离往往是被迫的,对此伍举是深有体会的。在《国语·楚语上》的《蔡声子论楚才晋用》篇中,伍举就因楚康王是非不分的误解而被迫离开楚国,但他又非常想回到楚国,如他所说:“若得归骨于楚,死且不朽”[17]592。蔡声子为伍举之事向楚国令尹子木进谏,其所举王孙启、析公臣、雍子三人之例是非常具有典型性的。其说辞如下:
昔令尹子元之难,或谮王孙启于成王,王弗是,王孙启奔晋,晋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晋将遁矣,王孙启与于军事,谓先轸曰:“是师也,唯子玉欲之,与王心违,故唯东宫与西广实来。诸侯之从者,叛者半矣,若敖氏离矣,楚师必败,何故去之!”先轸从之,大败楚师,则王孙启之为也[17]593。
昔庄王方弱,申公子仪父为师,王子燮又为傅,使师崇、子孔帅师以伐舒。燮及仪父施二帅而分其室。师还至,则以王如庐戢黎杀二子而复王。或谮析公臣于王,王弗是,析公奔晋,晋人用之。实谗败楚,使不规东夏,则析公之为也[17]594。
昔雍子之父兄谮雍子于恭王,王弗是,雍子奔晋,晋人用之。及鄢之役,晋将遁矣,雍子与于军事,谓栾书曰:“楚师可料也,在中军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若合而臽吾中,吾上下必败其左右,则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败之。”栾书从之,大败楚师,王亲面伤,则雍子之为也[17]596。
由以上三则材料我们可以看出,王孙启、析公臣、雍子原都是不同时期的楚国大夫,在楚国三人都曾遭遇到了小人的谗谮,而君王则“王弗是”,不能给他们以公正待遇,于是被迫离开楚国,结果又都帮助其他国家战败过楚国。从结果看,说他们是叛离楚国是不为过的,但前提是他们在楚国都遭遇谗谮,而君王又是非不分。伍举因为有切身的体会,所以到楚灵王时,面对他的骄奢淫欲、不施德义,说出“迩者骚离”,是有根据的,也是有警示意义的。
而通过上文我们对《离骚》两部分内容的分析,可以明显感受到屈原的遭遇与他们是非常相似的,屈原也遭遇谗谮,也遇到了是非不分的君王,但他不想放弃“中正”、“姱节”及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只能有一条路,即离开楚国。屈原的身份也是政治家、楚国的核心臣子,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1]3009,可以说他知晓楚国的一切,他很清楚他一旦选择离开楚国,投奔他国,对楚国意味着什么。最终宗教般的民族认同感、强烈的根性意识,还是使他在决计离开时,“蜷局顾而不行”。
如果伍举所说“骚离”可以解释为“因遭遇忧患而叛离”,那么根据我们对《离骚》内容的阐释,屈原“离骚”则可解释为“因是否离开(楚国)而忧愁、痛苦”,这是符合文本内容主旨的。而且将“离”解为“离别”、“离开”在屈原作品中也是有内证的,在此将“离”理解成动词的意动用法也是可以的;将“骚”解为“忧愁”、“愁苦”,伍举所说“骚离”也已有前例。
由此看来,王逸“别愁”说和今人姚小鸥先生“离别之痛”说,对于《离骚》篇题的解释是接近其本初内涵的。“遭忧”说,虽也有从内容着眼的一面,但毕竟不够全面,就《离骚》文本的第一部分讲是合适的;就《离骚》整个文本来讲,并没有体现出屈原在遭忧的前提下想离开又不能离开的那种纠结与痛苦。
纵观以上所论,通过对先秦文献篇题命名原则的考察,我们得出《离骚》的篇题命名形式是依文本内容定的。而通过对《离骚》整篇内容的考察,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辅证,我们得出《离骚》篇题的内涵应为:因是否离开(楚国)而忧愁。结合《九章》来看,屈原的生命可以说就是政治生命,但楚国的现实是没有圣君,谗臣当道,没有人赏识他的才华,这使屈原陷入一种尴尬的窘境,简单来说,即不离开楚国,其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离开楚国,又必将会以楚国为敌,而又与其宗族意识相背。因此他忧愁于是否离开,陷入了生命的两难,这委实是一种痛苦。我们以为对《离骚》的篇题做这样的解释,是符合其文本内容主旨的,应是《离骚》篇题的实际内涵。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游国恩.游国恩学术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213.
[4]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185.
[5]黄灵庚.楚辞与简帛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71.
[6]姚小鸥.离别之痛:《离骚》的意旨与篇题[J].文史哲,2007(4):120-126.
[7]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8]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M].北京:中华书局,2007:34.
[9]李学勤.初识清华简[M].上海:中西书局,2013:2.
[10]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1]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M].上海:中西书局,2010:1.
[12]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M].上海:中西书局,2011:135.
[13]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M].上海:中西书局,2012.
[14]袁珂.山海经校注[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349.
[15]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495.
[16]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544.
[17]陈桐生.国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3.
[责任编辑贾马燕]
Analysis of the Title and Connotation of Li Sao fromthe Literature Naming Method in Pre-Qin Period
ZHANG Shi-le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99, China)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up to now, there were many kinds of interpretations about the title of Li Sao.First, Sima Qian interpreted as “leaving sorrow”, Ban Gu interpreted as “suffering sorrow”, Wang Yi interpreted as “parting from sorrow”.Today, scholars interpret as the name of ancient music from some new academic angles, they all made some sense.However, first of all, Li Sao is a poem title, it is the first thing to study the literature naming method and its related cultur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iterature naming method in the Pre-Qin Period,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naming of Li Sao comes from the main content, therefore, Li Sao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sorrow because of leaving Chu State or not.
Qu Yuan; Li Sao; title naming; title connotation
I109.2
A
1001-0300(2016)02-0067-07
2015-12-03
张世磊,男,山东梁山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