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后现代女权主义视野下的“苔丝”悲剧
2016-09-18余珊
余 珊
(安康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生态后现代女权主义视野下的“苔丝”悲剧
余珊
(安康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通过对一个农村姑娘悲惨一生的描述,控诉了维多利亚时代虚伪的社会道德。在生态后现代女权主义的视野中,女性与自然具有同一性,在力量——理性——逻辑建构起来的文化氛围中,女性被置于弱者地位,被动性生存方式最终使得苔丝的悲剧命运无可逆转。
生态后现代女权主义;苔丝;自然;同一性;悲剧
所谓生态后现代女权主义是建立在后现代女权主义和生态主义理论基础之上、旨在揭示整个人类的社会组织结构及思想文化领域中作为被统治的妇女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处境的相通性,反对任何形式的暴虐、压迫与统治,进而实现解决生态危机及妇女解放问题的现代文化理论。这一理论,不仅可运用于解析人类社会工业生产及社会组织结构的性状,同时也可用于对文化及文学文本的解读。经由这一视角的解读,人类文化及文学的一系列文本都可呈示出新的意义。
一、生态后现代女权主义与文学
女权主义认为,男性建立的文化模型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男性与女性间展开的,这一主体意义上的人只指男人。这一文化模型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模式,人类在面对社会、他人的关系中,始终遵循着人对自然征服的关系模式,尤其对于女性及社会低级阶层而言是如此。这种压迫和奴役在以力量为基本表征的人类演进历史中始终以隐或显的方式积淀在人类文明结构的底部,甚至决定着文明的基本走向,这在工业化及后工业化社会达到了顶峰。表面看来,随着工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作中解放了出来,在教育、就业、公民身份、学术文化活动、政治活动等方面也赢得了制度层面的基本权益,但在社会从业、政治活动、公众话语、社会权益、思想、学术活动、人身、婚恋等方面,女性并未获得真正的解放,甚至被置身于较之于以前更为严密的牢笼中。女权主义最初的诉求是结束这一状况,解除性歧视与性压迫,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实现全面的男女平等。在文学方面,女权主义以“反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为口号,还原男性文学中被歪曲的女性形象,探讨文本中的女性意识,探索女性独有的写作与生存方式。
后现代女权主义是要寻求社会有序发展的新力量,解构二元对立逻辑,消除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对女性的消极规约,摧毁男性中心主义,建构以多元差异为本的秩序世界。
生态女权主义理论一方面与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一样——接受差异、倡导多样性、解构二元对立思想等;另一方面又继承了生态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尊重生命、反对压迫、追求和谐共存。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男性是自然唯一的压迫者,男性统治女性与自然。它同时指出,女性在尊重自然与理解生命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更擅长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依此思路,生态女权主义理论能够最终实现女性与自然、女性与男性、女性与文明之间的生态和谐。
生态后现代女权主义不满意以男性的力量与理性所组建的社会秩序和自然秩序以及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这种关系模式,竭力要捍卫女性与男性同样的主体地位,要打破男性为女性所设置的女性与自然同一的这种规范,重新以女性的感知来重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时,她们主张为了生态的协调性,重新建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伙伴式关系,以此来重组破碎不堪的世界秩序。
二、哈代笔下的苔丝命运
苔丝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①文中所引小说原文均出自托马斯·哈代著,孙致礼、唐慧心译的《德伯家的苔丝》,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中的女主人公,小说展示的是苔丝的悲剧命运。故事的发端是苔丝不得不替醉酒的父亲架着马车去集市卖蜂箱,却被迎面而来的邮车撞上,马被撞死,如此,家里就断了经济来源。万分自责的苔丝不得不听从父母的意见,去近郊找那个非常富有的德贝维尔夫人“认亲”。在德贝维尔家做佣工期间,苔丝被德贝维尔夫人的儿子亚雷诱奸,她被迫生下小孩,小孩却因为营养不良,最终夭折。遭遇不幸的苔丝并没有得到周围人的同情,对于这样一种未婚先孕的行为,她遭到了村里人的一致唾弃,于是不得不离家去奶牛场打工。在奶牛场,苔丝遇见了克莱尔。几经波折之后,苔丝终于和克莱尔结婚。在新婚当夜,当克莱尔向她坦述了自己以前的荒唐后,她也向克莱尔坦白了自己曾经被诱奸的事实,但克莱尔不能原谅她的过去,远走巴西。被抛弃的苔丝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去更远更艰苦的高原农场打工。身心饱受煎熬的她抗争徒劳之后,被迫再次投入亚雷的怀抱。美洲的经历使克莱尔身心疲惫,他重新回到了苔丝身边,他的归来重新燃起了苔丝对生活的热望。由于这希望压抑的时间太长,于是当它再次燃烧的时候,就变成了欲望的熊熊之火,这一把火杀死了亚雷,也毁灭了苔丝。
苔丝的一生虽然历经各种坎坷,但每一坎坷都是生存的被动处境导致的,她每一次生活的改变都是被迫无奈之举。她一生的举动中,只有两次是主动的,一次的结果是被遗弃,一次是自我毁灭。新婚当晚,苔丝以为生活迎来了新的契机,主动将自己的过往告知了克莱尔,并且也终于发出了男女平等的呼声,但获得的是被克莱尔遗弃。苔丝最终杀死亚雷,似乎是一种生的主动,但这一主动建立在毁灭自己的基础上。她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抗议——“我是一个纯洁的女人,我错在没有任何过错”。苔丝抗议的是什么?没有过错,那是什么酿造了她生存的悲剧?
三、女性与自然的同一性规定了苔丝的命运
女性生存命运首先源于女性与自然的同一。在这同一中,女性如同自然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意志更没有能动,只是默默无言、没有感知的自然本身,是文明精神征服的对象。这一对女性的物化过程,是随着人类文明史的展开而展开的。所谓物化,是把女性当成物来对待,就是说女性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在西方文化中意味着原始、低下、粗野、直接,人类文明就建立在这种对自然的征服之上。在理性特征鲜明的古希腊文化中,人的概念是不包括女性和奴隶的,女性处于人和自然外的第三种状态中。在基督教文化中,亚当意味着人,而夏娃只是孕育生命的容器,夏娃代表水与生命。甚至在中世纪基督教中,关于女性是否具有灵魂问题曾展开过长达几个世纪的争论。父权制文化其实就是用一种霸权的方式来诠释奴役自然与奴隶女性的合理性。在西方文化体系中,女性被当作物质的组成部分,可以用来交换和买卖,其价值明显要低于人以及人的精神领域。在这个逻辑下,男性彻底凌驾于女性、自然之上,成为绝对的主宰,而女性不断被物化。在苔丝被诱奸的晚上,原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样一个美貌女子,像游丝一样敏感,像白雪一样纯洁,为什么偏要在她身上绘上粗野的图案,就像她命中注定那样,为什么粗野的往往把高雅的人据为己有……”这段话看似是作者在替苔丝鸣不平,可实际上,苔丝活生生的身体被看成没有生命力的丝织品,即便作者用“白雪”来形容,那也依旧是一个质地比较好的丝织品罢了。在作者看来,苔丝的不幸在于粗鄙占有了精美,用作者的话说,就是“被不匹配的男人所占有”。换句话说,如果该占有这个女人的男人占有了这个女人,那么苔丝就可以幸福。在幸与不幸之间,作为当事人的女性,自己并不能做出选择,永远处在自在物状态,她们只能等待和被挑选。
四、力量——理性——逻辑建构的文化置女性于弱者的地位
男性统治世界,首先借助于理性,这种理性建立在力量与规则的基础上。在原始阶段,力量不仅体现为身体的强壮有力,同时体现为人类智力的规范化确立。这种智力是以线性逻辑为基础的建构框架。男性在这种理性建构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优势首先是以身强力壮为代表的力量优势,同时伴以狩猎活动中所形成的以因果律为特定的逻辑思维优势。这就是男性征服世界、展现自我的力量所在。女性相对柔弱,在以生育、采集及养殖、种植农业活动中所形成的生命及心理的自然节律,使女性与自然之间具有更强的亲和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男性展开了对自然和女性的征服与统治。在后世文化中,这种以理性为基本表征的文化成为文化主流及人类展开自己历史的基本动力,文化也就日益成为男性力量及生存的确证,女性就被置身于文化边缘状态。这种文化认定凡属自然的都还没有上升到意识状态,即仅仅生存着或存在着,它无力反思自己的存在,只是自在者无法成为自为者,因而,没有自身存在的独立性与自由性。男性统治女性、男性统治自然的理论基础反映了典型的二元对立思想,这种二元对立把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女性与社会、理性与情感等等方面都隔离开来。人与自然完全分割,男性与女性截然不同,理性与情感也不能共存。事物之间的差别,被演绎成了一种等级关系。所谓等级,是指中心与边缘化,统治与被统治。于是,在传统文化中,女性、自然界、物质、情感等等范畴被作为排斥和贬抑的对象,而男性、力量、理性则成为了讴歌的对象。男性其实就是理性的同义转换,男性就是社会,就是世界。苔丝在被诱奸之后,回到了马洛特村,恢复了一段时间之后,苔丝才敢在礼拜天的时候去教堂,即便如此,“她总是赶在还没敲钟的时候,就动身往教堂里去,在楼下后排靠近存放废旧杂物的地方找个座位。除了老头儿和老婆儿,别人是不到这里来的,因为在那些挖坑刨坟的工具之中,还竖着一副棺材架子”。苔丝的小心翼翼,只是为了避免他人的注意,诱奸的事实、失身的结果,让她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只有被忽视和遗忘,她才有可能融入到周遭的环境当中,被大家所接受。而这个就是男权制规约下的社会现实。克莱尔是苔丝心中的完美先生,但当克莱尔向苔丝求婚时,苔丝却一再地闪躲和拒绝。苔丝的犹豫与徘徊,并不是成熟女性的爱情策略,也并非是不明确自己的感情,而是在她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有罪的,是配不上克莱尔的。苔丝的自我否定充分反映了男权准则的根深蒂固。即便是作为受害者的女性,也是身体力行的维护着、践行着践踏她们的准则,在无形之中成为了造成伤害同类的帮凶。
男性统治世界的方式首先是通过为社会、为自然立法,女性也同样被纳入这种规则所统辖的范畴。因而,女性就成为这种规则的遵从者,女性的命运也就被这种规则规范。苔丝的父亲可以是酒鬼,但是苔丝一定不能是酒鬼。苔丝的父亲理所应当的成为了不受约束的酒鬼,苔丝替父亲驾车就成为了必然,苔丝的悲剧也就开始。亚雷之所以敢于诱奸苔丝,是因为他知道即便是发生强奸这样的行为,他也不会遭受到惩罚。克莱尔之所以选择向苔丝坦白,是因为他明白是否被原谅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当苔丝以为坦白意味着平等,于是用同样的坦白去换取克莱尔的理解时,却不知她与克莱尔之间根本不存在平等,规则的制定者永远是克莱尔,于是她被抛弃的命运也就无法避免。
在男权文化背景下,女性仅仅是生命力展开的论域之一。爱情和婚姻是女性生活的全部内容或核心内容。于是爱情和婚姻对于女性的要求也就比男性更为严格。男性展开生命力的空间是广阔无垠的,他们除了爱情和婚姻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女性的全部世界就是家庭。家对女性来说,是生活的核心和全部,对男性来说,仅仅是生命的一站。男性通过家庭来传宗接代、来获得情欲的满足及生存的保障。男性力量的体现是指向外部世界,女性只有通过对家庭的依赖才获得自身身份的确证。当苔丝从冒牌本家回来之后,苔丝的几个小学同学和朋友一起来看望她。按道理,都是同村的乡亲,又是从小一起长大,这样的看望本不用“兴师动众”,她们却“把自己最好的衣服浆洗熨平之后,穿着跑来了”,因为在她们看来,苔丝是一个“卓越征服者”。所谓“卓越”,是因为在她们看来,苔丝恋爱的对象是一个绅士。也就是说,绅士的身份增加了苔丝的附加值,使得周围的人对苔丝刮目相看。苔丝作为一个悲剧的人物,她对于自己悲剧命运的认识,只是归结于美貌。因为美丽,所以会被诱奸;因为美丽,获得了克莱尔的爱;为了维护对克莱尔的感情,自毁容貌。苔丝甚至认为,自己最美丽的时候是在16岁,之所以是在16岁,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失去贞洁。尽管苔丝最后和克莱尔在一起了,可是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克莱尔决定原谅苔丝。换句话说,在克莱尔的心里,苔丝是有罪的,只不过克莱尔决定不再计较。苔丝被抛弃,是罪有应得。那是什么样的罪过?罪在被诱奸,让身体、让自身贬值。
五、被动性生存方式酿造了苔丝悲剧
历代论者在探讨苔丝悲剧的成因时,都强调社会历史成因,即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冲突的矛盾,也强调男女不平等处境导致的矛盾,而没有从更深刻的文化层面,即生态学角度来探讨这一悲剧的成因。苔丝的悲剧首先在于文化视苔丝为自然的构成部分,是受动性生存者。作为受动性生存,女性自然被置于被动性的处境中,而在这一处境中,人的独立性和自由性无法呈现出来。苔丝的生存不是在选择中展现出来的,而是在被动规定中被规定着。她赶马车、认亲、遭诱奸、外出打工、被遗弃等等,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一种远远大于个体的不可控制的力量。苔丝只有最终杀死亚雷的行为,基源于她的自由选择,而这一选择却导致了她的毁灭。
人与自然之间、男性与女性本应处于和谐的关系中,应该达成一种契约式关系。但在男权主义文化背景中,这一关系却被处理成服从与被服从这种律法式关系。于是,自然、女性成了服从的对象,他们的自由意志就被扼杀在这种服从关系中。自然和人之间的抗争、女性与男性之间的抗争就演绎成一种持续不断的冲突关系。当甜蜜的新婚生活在苔丝的坦白中戛然而止,克莱尔远走他乡,来到了巴西时,“在巴西库里蒂巴附近的黏土地带得了热病,卧床不起”。克莱尔与其说遭遇了巴西突然的气候而病倒,还不如说是遭遇了与苔丝突然的变故而倒下。表面上看,克莱尔是在与巴西自然环境相较量,实际上,克莱尔是在与他想象中的苔丝和实际生活中的苔丝之间的“反差”相较量,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较量其实就是与苔丝之间的拉锯。根据生态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巴西的自然环境就是苔丝本人的象征,克莱尔在巴西的各种不适应、他与巴西自然环境相抗争的过程其实就是对苔丝由憧憬、失望、排斥到逐渐接受的过程。充斥着《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大量的自然描写并不是烘托人物形象的陪衬,而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自然描写并不是为了渲染和烘托苔丝的心境,而正是苔丝境遇的写照。被迫与爱人分开的苔丝,来到了高原农场。这个农场又冷又干燥,目光所及之处,一片荒凉。没有丁点的绿色,没有丝毫的生机,即便是在树篱中间生长了几棵树,也早就被那些种田的佃户们无情地砍倒了。“整块地里显出一片凄凉的黄褐色,好像一副没有眉毛口鼻的脸,从下巴到额头,只是一大块皮肤”。苔丝将自我放逐在这极其广袤寂寥的地方,即便是在这儿生活的鸟,也都“骨瘦如柴”“长着悲伤的眼睛”。苔丝在遭遇了人生的第二次变故之后,来到了棱窟槐。这个阶段是苔丝人生的低谷,没有克莱尔的每一天都是那么的煎熬,漫长、冰冷、了无生趣,就像棱窟槐漫长而寒冷的冬季,乏味、绝望,没有一丝生机。克莱尔的离去使苔丝抽离了灵魂,空剩下了一副皮囊。但即便只剩下皮囊,苔丝也不放过,依旧要自我惩罚。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满口脏话的残暴老板,极其简陋、恶劣的生存环境就是苔丝自我的折磨。尽管分手后的两个人都陷入了痛苦的境地,但这样的痛苦也是有所不同的。克莱尔的痛苦和折磨,是因为他自己选择了巴西,倘若他从巴西回国,那么他的痛苦也就解脱。换句话说,巴西环境给予克莱尔的痛苦,是克莱尔自我纠结的结果。倘若他能够释怀并且回归,那么这种痛苦也就无疾而终了。但是,苔丝的痛苦并不仅仅是她自我的选择,在更大程度讲,这是外界给予她的折磨。苔丝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自我选择,她只能是被选择和被挑选的对象。她的生活环境是无法逃避的,她的痛苦,也就不可避免。
六、苔丝悲剧对现代理论的启示
苔丝的悲剧不仅是女性的,更是人类的。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是依靠相互之间的合作、照料和彼此的爱来维持,唯有这样,人类才能真正做到尊重并且保护所有生命体的多样性。苔丝悲剧对现代理论的启示之一,是重组人类文明,更新人类的生态关系。这一生态关系不仅仅是人与自然之间,同时存在人类社会之间。人依存于自然存在,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家,不再是被奴役和被征服的对象。同时,人类社会生态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建的。男女两性是一种共生性关系,女性不再是被奴役和被欺凌的对象,也不是自然的化身,而是男性的合作伙伴,是男性印证自己存在的基本前提。同时,重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然是文化的,不是自然所具有的原始性、野蛮性、粗野性和直接性。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完成了人对自然的人化,环境已是属于人的。因此,它不再是陌生的、异己的力量,而是经文化陶冶和修正的人的自然。自然成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成为了文明的元素。最后,以理性和力量为特征的人类文化需要由人类的智慧来进行改造,重新确立男性与女性的伙伴式关系。女性不再呈现为生存的被动者,而是和男性一样,以主动的形态来参与并创造人类的文化。这既是文明的使命,也是人类扭转现代危机的契机所在,当然这更是生态女权主义应该追求的目标。
[1]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M].孙致礼,唐慧心,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2]莫里斯.男人和女人的自然史[M].蒋超,孙庆,杜景珍,译.北京:华龄出版社,2002.
[3]张广利,杨明光.后现代女权理论与女性发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4]马昌仪,刘锡诚.石与石神[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
[5]伊丽莎白·赖特.拉康与后女性主义[M].王文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朱迪斯·巴特勒.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M].李钧鹏,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7]凯瑟琳·巴里.被奴役的性[M].晓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校朱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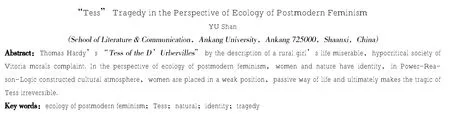
I106.4
A
1674-0092(2016)04-0054-05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4.012
2016-03-16
余珊,女,陕西汉中人,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助教,硕士,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