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虞“二冯”“比兴”说的内涵及影响
2016-09-18李亚峰
李亚峰,王 兵
(1.常熟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2.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新加坡 637616)
论海虞“二冯”“比兴”说的内涵及影响
李亚峰1,王兵2
(1.常熟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常熟 215500;2.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新加坡 637616)
作为“虞山诗派”“疑丞”的海虞“二冯”,其诗学理论虽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系统地研究,但其中最核心、最富有创新性的“比兴”说,却未被突显出来,甚至其基本含义,至今都混沌不清。“二冯”创造性地阐释“比兴”之义,并将其与“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融为一体,概括了诗歌“以比兴寄美刺”的体用本质。其“比兴”说虽有狭隘之嫌,却也深合我国古代的论诗传统,对清代诗词的创作和理论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只有真正理解“二冯”“比兴”说的内涵及影响,才能正确认识其诗学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合理评价“虞山诗派”在清初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虞山诗派;二冯;比兴;诗教
“虞山诗派”是“明末清初转移一代风会者”,作为“疑丞”[1]的海虞“二冯”,自然也颇受学界重视。虽然有不少学者对他们的诗学进行了系统地研究,但是“二冯”诗学中最核心、最富有创新性的“比兴”说,却没有被突显出来,甚至其具体内涵至今仍混沌不清。这不仅影响了学界对“二冯”诗学价值和意义的评判,也遮蔽了人们对“虞山诗派”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值得深入研究。
一、“比兴”说的内涵
“二冯”诗学的“比兴”说之所以没有被学界重点发挖,那是因为“比兴”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老话题,似乎没有多少新意,但是,古人的创新多半蕴含于旧命题的阐释之中。“二冯”论诗极为重视“比兴”,冯舒说:“诗无比兴,非诗也。读诗者不知比兴所存,非知诗也”,可见,他将“比兴”视为诗与非诗的标准。其弟冯班也指出“比兴乃诗中第一要事”[2]51,其《钝吟文稿·古今乐府论》又说:“文无比兴,非诗之体也”[3],也将“比兴”上升到了诗歌本质层面。“二冯”对“比兴”的这种空前重视和推崇,使我们不得不关注其“比兴”说的真正内涵与意义。
其实关于“比兴”的内涵,冯班有过具体的阐述,他说:“晝公云: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义,此语直接分晓。”冯班借用了唐代诗僧皎然阐释比喻与用事区别的一段话来解释“比兴”,认为“取象曰比,取义曰兴”,那么“象”就是“比”,“义”就是“兴”。又说“义即象下之义”,那么“象”和“义”、“比”和“兴”之间的关系,又变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是一种表现方式与表现内容的关系。所以,冯班说,兴“本是意兴之兴”[2]64。可见,他所谓的“兴”属于名词性范畴,是表现对象或内容。这样,冯班所谓的“比兴”,就不再是“比”和“兴”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它变成了一个动宾词组,是指一种“立象尽意、托物言志”表现方式。这显然与历代儒学经师所传承的“比兴”之义有很大差别,郑众、郑玄、王逸等历代儒学经师向来都是把“赋、比、兴”视作《诗经》中三种并列而且不同的表现方式。而冯班却将“比兴”视为一体,它们之间表现方式与表现内容的关系,这是他的创造性阐释。
那么,这样解读冯班的“比兴”是否符合其原意呢?我们可以通过其父冯复京对“赋、比、兴”的解释来作以参考。实际上,“二冯”关于“比兴”的理解,与其父是一脉相承的。这一点,学界尚未有人注意到。冯复京曰:“诗有赋、比、兴三义。赋者,布也。兴者,感也。布义感情,情理一揆。比者,喻也,托物见志,浅深殊趣”[4]。我们可以看出,冯复京对“赋、比、兴”解释也非常奇特,他将“赋兴”合释为“布义感情,情理一揆”,类似于“说理言情”。而将“比”单独阐释为“喻”,成为一种“托物见志”的表现方法。可见,冯班将“兴”作为表现内容,而把“比”视为表现方式的思路,其父冯复京已开其端。只是冯班论诗不讲“赋”,因而,他用“兴”取代了其父的“赋兴”。而关于“比”的含义,父子二人的理解基本相同,“取象曰比”,“取象”就是“喻”,也就是“托物见志”。可见,冯氏父子关于“比兴”的理解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也可以印证我们对冯班“比兴”的解读是符合冯氏家学之义的。这一点,我们还可以通过吴乔对“比兴”的阐释加以印证。吴乔论诗极力推崇“二冯”,对其诗学也独具会心。他不仅在诗论中大量引用了冯班之言,且称冯班《钝吟杂录》、贺裳《载洒园诗话》与自己《围炉诗话》是“谈诗者之三绝”[5]。因而,他关于“比兴”的理解应该与冯氏比较接近,他说:“感物而动则为兴,托物而陈则为比”,那么,“兴”就是作者在特定环境中产生的“情志”的过程,而“比”就是以“托物而陈”方式表达这些“情志”的方法。这与我们对“二冯”“比兴”的解读非常相似,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我们阐释的合理性。
不过,“二冯”关于“比兴”的这种创造性阐释,并非所有人都能认可。何焯对此就提出了批评,他说:“千古区分比兴二字,莫善于刘彦和……定翁不是之采,而意断比兴之说,吾所不取”[2]64。那么,既然冯氏的“比兴”阐释颇遭非议,它为何还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这是因为,“二冯”还将“比兴”与传统“诗教”观紧密地融合为一体。
冯班说:“又比兴是诗中作用,诗人不以比兴分章,朱子谬甚”[2]64,可见,冯班认为“比兴”不仅是“托物寓意”的表现方法,它还指诗歌的作用。那么诗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儒家传统的“美刺教化”的诗教功能。中国古代向来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他们认为诗歌在社会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统治者既可以通过诗歌教化民众,也可以通过采诗观风的方式了解民情。而诗人既可以通过诗歌吟咏情性,又可以通过献诗诵诗的方式发表政见。而政见的内容既包括颂美,也包括怨刺。这就是自孔子“兴、观、群、怨”说至《毛诗序》以来形成的儒家“美刺”的诗教传统。“二冯”论诗继承了这一传统,冯班曰“诗以讽刺为本,寻常嘲风弄月虽美,而不关教化,只是下品”[6],可见,冯班认为诗歌的作用在于“美刺教化”。而且,冯氏把诗歌的“美刺”功用也上升到了诗歌的本质层面,他说:“有美焉,有刺焉,所谓诗也。不如此则非诗”[2]56,认为诗歌如果不具备“美刺”功能,也就丧失了诗之为诗的价值。
那么,“比兴”又和“诗教”有什么关系呢?这一点,冯舒有过明确的阐述,他说:“大抵诗言志,志者,心所之也。心有在所,未可直陈,则托为虚无惝恍之词,以寄幽忧骚屑之意。昔人立意比兴,其凡若此。自古及今,未之或改。故诗无比兴非诗也。读诗者不知比兴所存,非知诗也。余兄弟于此颇自谓得古人意,故能以连类比物者区分美刺”[7]37。可见,冯舒认为诗歌是言志缘情之物,但作者的“情志”产生以后,并不是直接就可以发而为诗,而是要“托为虚无惝恍之词,以寄幽忧骚屑之意”,通过“比兴”的方法来表现。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用“比兴”方式来表现呢。这就与“二冯”倡导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有关了。他们认为,诗歌虽然具有“美刺”功用,但要使其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保证“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因而,就需要采用合理的形式,要“主文而谲谏”[8]18。只有这样,诗歌才能“发乎情,止于礼义”[8]19,符合“温柔敦厚”之旨。所以,诗歌需要运用“比兴”手法,“托为虚无惝恍之词”,使其内容变得隐秘婉曲,从而激切不平的棱角自然磨掉,情感也就归于中正和平了。这样,“比兴”就成为实现“美刺”的手段,而“美刺”就是运用“比兴”的目的。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体用”关系。所以,“二冯”“比兴”说的真正涵义就是“以比兴之体,寄美刺之用”。陆贻典评冯班诗歌曰:“其为诗敦厚温柔,秾丽深穏,乐不淫,哀不伤,美刺有体,比兴不坠”[9],其“美刺有体,比兴不坠”的概括是深得“二冯”“比兴”之义的。
其实,从“诗教”方面解释“比兴”并非“二冯”首创,东汉经师郑玄就曾说:“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10]。但郑氏“比刺”“兴美”的观点对“比兴”进行了生硬的区分,并不符合《诗经》“比兴”的使用实际,因而多为后来学者所质疑。所以,它未能在“比兴”与“诗教”之间建立明确、有效的联系。而“二冯”含混地将“比兴”合释为“托物言志”的表现方式,弥合了这种缺陷,从而清晰地沟通了“比兴”与温柔敦厚“诗教”之间的体式与功用的关系,这是其“比兴”说的一个重要创新。在此基础上,“二冯”对诗歌的本质从体、用两方面作了明确规定,认为诗的本质就是“以比兴之体寄美刺之用”,这也是前人未发之论。“二冯”的这种概括虽不免狭隘之嫌,却也深合于古代儒家论诗的传统,所以冯舒不无骄傲地说:“故诗无比兴非诗也。读诗者不知比兴所存,非知诗也。余兄弟于此颇自谓得古人意,故能以连类比物者区分美刺”[7]37。当然,“二冯”“比兴”说也存在含混比兴的问题,这违背了传统经师并列、对比阐释“比兴”的惯例。所以,何焯批评冯班不采用刘勰之论。当然,以“二冯”之学,不可能不熟悉刘勰之言。冯舒曾多次校对、题跋《文心雕龙》,冯班也曾手抄其书,今有存本藏于常熟图书馆。不过,学者的偏执之见,往往恰是其理论的创新之处。冯班之所以不取刘勰之论,是因为刘勰对“比”“兴”作对比性地区别,认为“比显而兴隐”,比是“蓄愤以斥言”[11]。而这种“比”的解释,和冯氏所倡导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是凿枘不合的。所以,何焯的批评并未能真正理解冯氏竭力沟通“比兴”与“诗教”关系的良苦用心,及其为统一、概括诗体特征所做的努力。
总之,“比兴”不是新概念,但冯氏对其内涵进行了创新性的阐释,它就具有了新的意义。“诗教”也是老传统,以“诗教”言“比兴”,汉儒也已发其端,但清晰地沟通了“比兴”与“诗教”的关系,并将“以比兴寄美刺”视为诗歌的本质特征,这都是前所未有的创新之论。我们不能因为“二冯”的“比兴”说没有提出“新概念”“新名词”,就否定其创新意义和价值。相反,正为“二冯”采用了这些旧话头、老传统,才使其诗学显得句句引经据典、渊源有自,从而能使人信服,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如果“二冯”“比兴”说,真地仅是传统理论的简单引述,不具有创新与独到之处,那么,那位心高气傲的清代著名诗人赵执信,对“先达名公诸论”都不屑一顾,怎么可能会对一位“乡先生”“村夫子”顶礼膜拜、铸金呼佛,并亲至其坟前焚刺而自认私淑呢?
二、“比兴”说的影响
“二冯”对“比兴”的创造性阐释,对清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首先,“二冯”的“比兴”说深化、更新了人们对“比兴”的认识。“二冯”论诗高度推崇“比兴”,将其视为“诗中第一要事”[2]51。他们的这种观点,必然会引起人们对诗中“比兴”的关注和重视。其“比兴”说对贺裳、吴乔、赵执信、何焯,甚至纪昀等清代诗论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吴乔,他论诗重“意”和“词”。而其所谓“词”就指“比兴”手法。他从赋、比、兴的角度描述诗歌发展源流说:“大抵文章实做则有尽,虚做则无穷。雅、颂多賦,是实做;风、骚多比兴,是虚做。唐诗宗风、骚,所以灵妙。”[12]10认为“比兴”是风骚传统,唐诗多继承这一传统。进而,他又以“比兴”视角论述了唐诗、宋诗之异,“唐诗有意,而托比兴以杂出之,其词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诗亦有意,惟赋而少比兴,其词径以直,如人而赤体。”[12]2唐诗、宋诗之异就在于有无“比兴”。他论诗文之别又说:“问曰:诗文之界如何?答曰:意岂有二?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是以诗文体制有异耳。文之词达,诗之词婉。书以道致事,故宜词达;诗以道性情,故宜词婉。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词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噉之则饱也。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变尽米形,饮之则醉也。”[12]8可见,他认为诗文之“意”同,其差别主要在于体制表现,其所谓的“词婉”,就是指运用“比兴”手法。这些显然都是“二冯”“文无比兴,非诗之体也”观点的合理发展。
“比兴”认识的深化不仅表现在诗学理论方面,而且表现在诗歌的解读方面。既然“比兴”是诗歌特有的表现方式,那么,诗歌也应该以“比兴”方式来解读。这种诗歌阐释方法的变化,极为突出的表现在对李商隐诗歌的态度上。自宋初反对“西昆”诗风以来,李商隐诗歌总体上是被贬斥的。但明末清初,这种情况开始变化。李商隐诗歌逐渐被人重视起来,并产生了笺注李商隐诗歌的热潮。明清之际,先有释道源为李商隐诗集作注,后来钱龙惕也加入其中。其后朱鹤龄有《笺注李义山诗集》、吴乔有《西昆发微》、何焯有《李义山诗集笺记》等。他们都是从“比兴寄托”的角度对李商隐诗歌进行了新的解读,其中释道源指出:“义山当南北水火,中外箝结,不得不纡曲其指,诞谩其辞,此风人小雅言之遗。推原其志义,可以鼓吹少陵”[13],他将李商隐和杜甫相提并论,认为二人“志义”相同,只是李诗多“比兴寄托”而已。李商隐诗歌阐释方法的转变,充分显示了人们对诗中“比兴”认识的深化。而“二冯”论诗极力倡导“比兴”,对这种变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其次,“二冯”“比兴”说重新平衡了中国诗学中“文与质”“情与礼”的矛盾,对清代诗歌乃至词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与质”“情与礼”的平衡和协调一直是中国诗学乃至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永恒主题。由于传统文化尚实用的特性,中国文学一直存在着“重道轻文”“以礼抑情”的倾向。因而,齐梁、晚唐至宋初西昆的诗歌传统,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直是被批判、受压抑的一脉,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浮靡的内容和华丽的辞采与中国以“教化”为中心的文化体系相矛盾。而“二冯”的“美刺有体”的“比兴”说,重新平衡和协调了这种矛盾,在新层面上重新界定了“情采”与“教化”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尚采重情”诗风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二冯”认为诗歌应该以“比兴”之体来实现“美刺”之用。这样,华丽的辞采和浮靡的内容就变成了并非实指的“寄托之物”,只要其最终喻义合于“礼乐教化”,也就无所谓“淫邪”了。这就大大提升了诗歌“尚采重情”的空间。不仅如此,面对别人的指责,冯班还进一步从“礼乐”文化层面对“尚采重情”的诗风进行了理论辩护,他说:“韩吏部,唐之孟子,言诗称鲍、谢,南北朝红紫倾仄之体,盖出于明远。西山真文忠公云:诗不必颛言性命而后为义理。则儒者之论诗可知也。人生而有情,制礼以节之,而诗则导之使言,然后归之于礼,一弛一张,先王之教也。”[14]可见,冯班认为,诗之旨与“礼”不同,与“乐”相合。“礼”是对人们的情感进行规范,而“诗”则是通过对人情感的合理疏导而使之归于“礼”。这样,诗歌的“尚情重采”就不再与“礼”相违,而具有了合理性,所以他说“光焰万丈李太白,岂以酒色为讳耶?”而且,冯班认为“礼”自“情”出,“礼者,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生乎人情者也。”[2]105强行压抑人性,并非“礼”之旨义,“先王因人心而制礼,岂以其违性者强之乎?”[2]61进而,他提出了“咏情欲以喻礼义”的主张,这都是相当前卫的,是对晚明以来“情、理之辩”的继承和发展,为“重情尚采”诗风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正是在“二冯”“比兴”说理论的影响下,向来被人指为“浮艳”的晚唐诗风才在明末清初兴盛起来,并形成了一股以虞山诗派为中心的宗法晚唐的诗歌热潮。虞山诗派虽然以钱谦益为魁首,但其诗学宗趣却是以“二冯”倡导的“温李”诗风为主导。王应奎《海虞诗苑》称:“是时邑中诗人,率以冯氏为质的”[15],可见,当时海虞诗歌的主要风气。钱良择也说:“吾虞从事斯道者,奉定远为金科玉律。此固诗家正法眼,学者指南车也”[16]。所以赵永纪先生认为“一般所谓虞山诗派,主要是指二冯及其追随者中提倡晚唐,学西昆体的那一部分诗人”[17]。据《海虞诗苑》记载,除“二冯”外,冯行贤、冯行贞、冯武、钱曾、陆贻典、陈玉齐、孙江、瞿周、陈帆等人的诗歌都有宗法晚唐的倾向。当然,清初诗宗晚唐的风气并不仅局限于虞山一隅。据《渔洋山人年谱》载,顺治十六年(1659),王士禄、王士祯兄弟曾与彭孙遁在京城倡和香奁体,并有《彭王倡和集》行世。可见顺治年间,晚唐诗风在京城也有影响。而据汪瑶《二冯批才调集·跋》称:“近日诗家尚韦縠《才调集》,争购海虞二冯先生阅本为学者指南,转相模写,往往以不得致为憾。”[6]该版本《二冯批才调集》刊于康熙四十三年,可以看出,这股晚唐诗风一直到康熙后期还很盛行。不仅如此,与之相适应,晚唐诗歌的文献整理和编选也流行起来,如《中晚唐诗纪》《晚唐诗抄》 《中晚唐诗》 《中晚唐诗叩弹集》等都在这一时期刊刻。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明末清初晚唐诗风的盛行。
“二冯”“比兴”说对“重情尚采”文风的影响并不仅限于诗歌领域,对词学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启发性影响。清代词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完成了词的“尊体”运动。词向来被认为是“艳科”“小道”,为浅斟低唱、娱宾佐欢之具,不登大雅之堂。而清人使词体不断向诗体靠近,从而使其最终获得了同“诗”一样可言志载道的地位。但毕竟“诗”庄“词”媚,词“别是一家”[18],它又不能完全等同于诗。那么,如何才能使词体保持自身的绮靡风格,而又能通于诗教之道呢?显然,“二冯”的“比兴”说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因而,“比兴”说在清代词学中大放异彩。无论是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的“夫作者非有《国风》美人、《离骚》香草之志意,以优柔而涵濡之,则其入也不微,而其出也不厚”[19],还是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的“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20],还是常州派领袖张惠言在《词选序》中提出的“比兴寄托”“意内而言外”[21]的主张,都和“二冯”的“比兴寄美刺”之论颇为相似。诗、词之间这种理论的互动和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二冯”的“比兴”说,通过创造性地阐释“比兴”之义,完成了“比兴”与“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的无缝沟通,进而从体制和功用两个方面对诗歌的本质作了“以比兴寄美刺”的明确规定,虽有狭隘之嫌,却也深合我国古代的论诗传统。它在传统“诗教”范围内,为诗歌的“情”“文”要素开拓了最大的理论空间,对清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只有真正理解“二冯”“比兴”说的内涵和理论价值,我们才能正确认识和评估“虞山诗派”在清初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1]钱仲联.钱遵王诗集笺校序[M]//谢正光.钱遵王诗集笺校.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0:1.
[2]冯班.钝吟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冯班.古今乐府论[M]//王夫之.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9.
[4]冯复京.冯复京诗话[M]//吴文治.明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7179.
[5]阎若璩.潜邱札记[M]//清代诗文汇编:第14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27.
[6]韦縠.二冯批才调集[M].康熙四十三年汪瑶刊本.
[7]冯舒.家定远游仙诗序[M]//清代诗文汇编: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8]孔颖达.毛诗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9]陆贻典.冯班诗集序[M]//清代诗文汇编: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
[10]郑玄.周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55.
[11]刘勰.文心雕龙校注[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240.
[12]吴乔.围炉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753.
[14]冯班.陆敕先玄要斋稿序[M]//清代诗文汇编: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5.
[15]王应奎,瞿绍基.海虞诗苑海虞诗苑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88.
[16]王应奎.柳南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1983:184.
[17]赵永纪.论清初坛的虞山诗派[J].文学遗产,1986(4):91.
[18]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95.
[19]陈维崧.词选序[M]//湖海楼全集:卷五.清康熙二十八年刻本.
[20]朱彝尊.陈纬云红盐词序[M]//曝书亭集:卷四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5:1617.
【责任编校杨明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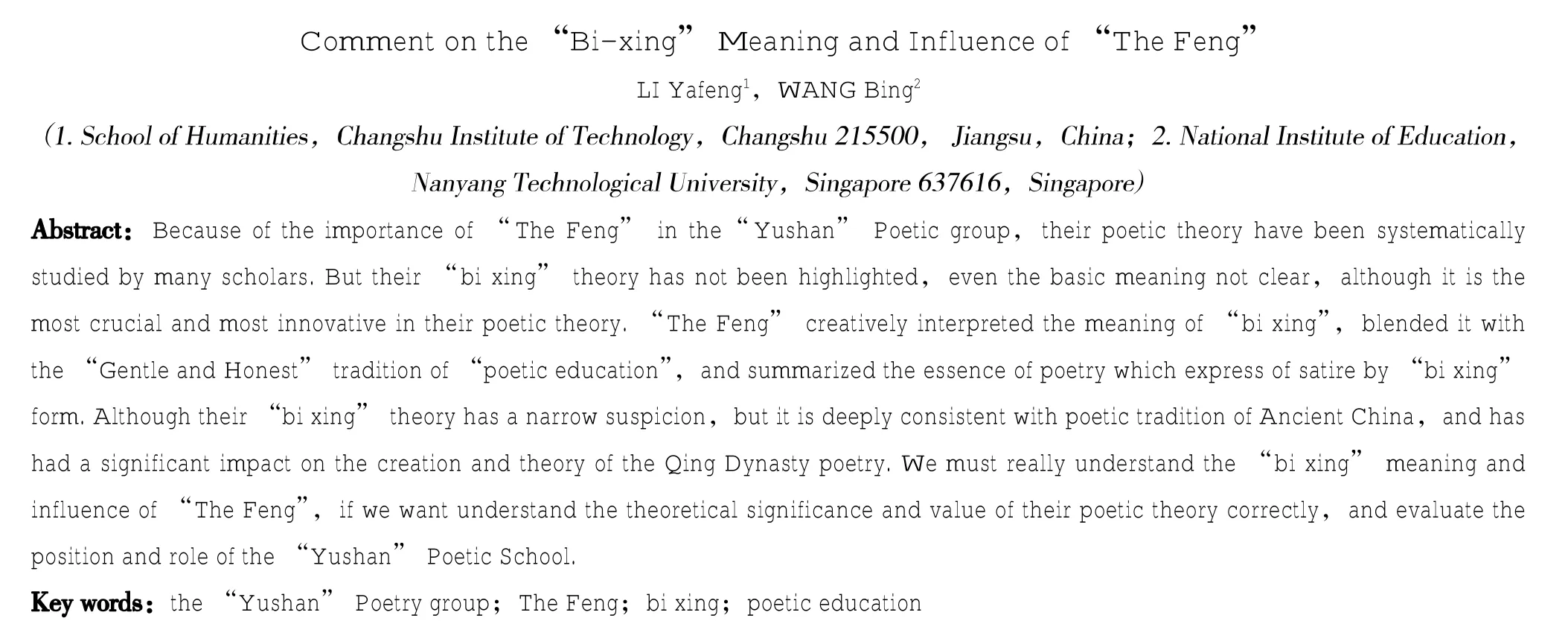
I206.2
A
1674-0092(2016)04-0024-05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4.006
2016-03-07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清初虞山诗人群体研究”(2013SJB750001);常熟理工学院社科项目“虞山诗派文献整理与研究”(QS1301);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资助项目
李亚峰,男,江苏沛县人,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诗文研究;王兵,男,安徽合肥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助理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