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力士》里的成长探索
2016-09-18邹军
邹 军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英格力士》里的成长探索
邹军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英格力士》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本文对小说主人公刘爱的成长进行了探索。首先将他的成长论述为在王亚军的理性启蒙下的“正导”型成长,接着对这种看法进行反拨,说明王亚军形象有较大的虚幻性,强调在刘爱的潜意识里隐藏着众人给他的精神哺育,最后分析了众人精神哺育的有限性,刘爱的真正成长需要一股超越性力量,小说中的超越性力量正是王亚军形象里蕴含的启蒙信念,从而将刘爱的成长确定为启蒙信念导引下的“自导”型成长。
《英格力士》;成长;正导;潜意识;自导
《成长小说概论》里将成长小说定义为:“成长小说是一种着力表现稚嫩的年轻主人公历经各种挫折、磨难的心路历程的一种小说样式。成长主人公或受到导引,得以顿悟,如期长大成人;或若有所悟,有长大成人的可能性;或迷茫依旧,拒绝成长,成长夭折。”[1]22成长引路人是成长小说中一类重要的人物形象,他们引导主人公成长,在主人公的成长之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长引路人被分为“正导”“反导”“误导”“互导”“自导”五种类型。其中,“正导,即从正面导引的引路人”[1]27;“自导,即成长者在成长路上的自我教育,无缘借助他者之力长大成人,因卓越的悟性和超强的自省能力而自助成长”[1]31。
许多作家的“文革”童年叙事作品,比如毕飞宇的《白夜》、艾伟的《田园童话》、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 《在细雨中呼喊》、苏童的《刺青时代》《城北地带》,都可归为成长小说。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点——主人公的成长未能如期完成。同为有关“文革”的童年叙事,王刚的《英格力士》是一个例外,作品里的成长主人公刘爱如期地长大成人。那么,按照《成长小说概论》对成长引路人类型的划分,刘爱的成长可以看成哪种类型?
黑格尔所讲的“否定性”,是黑格尔辩证法里的精髓。张世英在《精神现象学》的“总序”里说:“黑格尔认为克服对立统一以达到统一即自由之境的动力是‘否定性’。这种‘否定性’不是简单抛弃、消灭对立面和旧事物,而是保持又超越对立面和旧事物,他称之为‘思辨的否定’或‘辩证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是精神性自我‘前进的灵魂’。”[2]下面,我们将运用黑格尔的这种“否定性”辩证思维,探讨成长小说《英格力士》中主人公刘爱的成长之旅。
一、理性启蒙下的“正导”型成长
“正导”,即“从正面导引的引路人”“他们睿智、果敢,具有卓越的精神美和道德美,浑身散发出令人着迷的人性光辉。他们或潜移默化,或直截了当,为成长者指明前进的方向,为成长者传道、授业、解惑,为成长者扫清成长之旅中必然或可能遇见的各种痛苦和迷惘”[1]27。王亚军就属于这类成长引路人,成长主人公刘爱似乎是在他的正面导引下获得成长经验,经历精神领悟,从而长大成人的。
《教育漫话》是十七世纪英国伟大的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所写的一部教育名著,它的主题是所谓的“绅士教育”,即如何将儿童培养成有理性、有德性、有实际才干的绅士。洛克非常看重儿童早期所受的教育,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所以千差万别,都是出于教育的不同。我们幼小的时候得到的印象,哪怕极其微小、几乎觉察不到,都会对一生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3]3洛克认为儿童早期的时候基本上是一张白纸,尚未形成自己的理性,这时他的精神处于“最柔软、最易于支配的时候”,需要遵从成人的戒律,服从成人的理性,随着其理性的逐渐形成,严格的管教也可以渐渐放松,直到他们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理性。通过洛克的教育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在儿童的成长中有一个正面导引的成长引路人何其重要。
在大多数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的“文革”童年叙事里,往往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缺少一个类似王亚军的成长引路人。在主人公们成长的那个特殊岁月里,基本的人伦价值体系崩溃,人心失去了应有的约束,整个社会陷入了某种无序与疯狂。“在充斥着‘揭、批、斗’的政治话语的滔天浊浪中,成长期的孩子们经受着这种大浪的冲刷并为之吸引。这种从上到下的全民性话语以其无可置疑的强势,绝对地排斥了其他真正美好的思想源流,从而也就断绝了孩子们向其他方向成长的可能。”[4]由于没有一个内心坚定的正面引路人,在似乎一无所有的时代的精神荒原里,成长主人公们面对着那个充斥着暴力与疯狂的时代,要么在外部环境的不良影响下成长夭折,要么拒绝外面的世界而无法如期长大成人。《十八岁出门远行》里,“我”最终从虚伪冷酷的成人世界退回内心,觉得那里才温暖安全;《刺青时代》里,男孩小拐只能感受到世界的暴力与血腥,受其影响,最终也被其吞噬;《耳光响亮》里,缺少了精神导引的心灵破碎、混乱,不仅是牛氏姐弟的受难,也是六十年代出生一代人的受难。苏童说:“共同的特点是以毁坏作结局,所有的小说都以毁坏收场,没有一个完美的阳光式结尾。我所有成长小说没有一个以完成成长告终,成长总是未完待续”[5]。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英格力士》中的知识分子群体处于异常狼狈、促狭与悲惨的境地,被人批斗,朝不保夕。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比如“我”父母、校长、范主任、郭培清等人,都基本上放弃了内心的全部信念。英语老师王亚军被描述为这群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另类,他依然恪守启蒙的信念。王亚军像是“殉道士”,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为那帮不幸的孩子流下了悲悯的泪水,“他的眼泪在不停地流着,就好像那是一条河,是我们乌鲁木齐河”“我们这些乌鲁木齐出生的孩子就是喝着王亚军的泪水长大的”。他教育刘爱、黄旭升等学生,充满热诚地关怀学生的成长,但是刘爱的母亲“只是害怕他这种人给她的孩子,以及她的家庭带来危险”,也许在家长们的眼里他只是一个书呆子和可怜虫。不过,王亚军是一个承载了西方启蒙理念的人,他有着坚实的人道主义理念。作为正面导引的引路人,王亚军对人道主义理念的信仰自始自终从未动摇过。在“破四旧”“打到牛鬼蛇神”“狠批封资修”等“文革”话语泛滥的恶劣环境里,王亚军依然相信人与人之间要有“爱”,要“仁慈”,依然坚持教“最纯正的林格风英语”,依然要求班里的同学做“绅士”。
王亚军注重仪表,他用香水,不留胡子,衣着整洁,“总是干净,典雅”,他的微笑“谦和”而“含蓄”。刘爱因此偷用母亲的香水,买平光眼镜,在刘爱后来成为英语老师后,他也和王亚军一样衣着讲究,往身上洒香水。
在刘爱因青春期的自慰行为而忧伤、恐惧时,王亚军告诉他“你要学会自慰”,这拯救了当时的刘爱,“让我意识到每当黎明想念女人,浑身燥热是无罪的”。在青少年的成长中,性的成长是很重要的部分,这方面的引导不当可能使主人公的成长陷入危险的境地。王亚军没有将其视为禁忌,也没有任其发展,教会刘爱正确地面对它,引导刘爱顺利地渡过了人的成长中这个必不可少的阶段。
王亚军告诉刘爱,“绅士是有教养的男人”“一个绅士在挨了女人耳光之后,绝不能想到还手”“他首先应该想想是不是自己真的错了,如果没有错,那他就应该自嘲地笑笑”。王亚军注重理性对自我的约束,尽力反对人与人之间的暴力行为,这使得刘爱没有选择去当基干民兵等,从而避免了遭遇与同龄人黄旭升、李垃圾类似的成长之殇。
王亚军热爱英语,告诉刘爱以后“要去周游世界”“天山挡住了你的眼睛”。他的热情激起了刘爱对英语的热情,使得刘爱最终也成了一名英语老师,拥有了宽广的视野,“在英语的世界里,看到了美国,看到了欧洲”。
在整部作品中,王亚军一直在尽力地引导着刘爱,他的形象、语言与行动等各方面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刘爱。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传统的儿童教育被毁坏,已经不可能对儿童的成长实行良好的导引,在这种境况下,王亚军这一人物形象被作家赋予了西方启蒙的理念。王亚军用西方绅士的要求尽力地约束着刘爱,引导着刘爱,这里寄托了作家对成长主人公刘爱的美好祝愿。我们可以把王亚军看成“正导”类型的成长引路人,正是有了他的正面导引,刘爱克服了外界的重重阻扰,避开了青春期成长的陷阱,初步具备了自己的理性思考能力,最终长大成人。
二、众人对刘爱的精神哺育
洛克认为好的儿童导师需要两方面的素质,一方面他要有良好的教养,“懂得对于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地方应该有什么样的举止与礼貌”,另一方面要熟悉世态人情,“懂得他那个时代人们的行径、脾性、罪恶、骗术和缺点,尤其是他本国的”[3]75-77。前一方面的素质王亚军无疑是具备的,他有着良好的教养;后一方面,他对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灵完全懂得吗?刘爱和黄旭升的母亲打他耳光,学生家长不敢让他给学生太多的影响,似乎他并不是一个当时家长心目中的好老师。那么,王亚军是否缺了什么?质朴美丽的新疆女孩阿吉泰为什么就不能接纳王亚军,在她的眼里王亚军是否缺了什么?
荣格曾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有一幢老房子,其顶层里的家具陈设气派,下面一层里的则要陈旧得多,是中世纪的,最底层即地下室里有原始文化的遗迹,有破碎的陶器和两个原始人类头骨。在荣格看来,那幢房子是他精神的一个意象。顶层房间代表他的意识人格,下面一层代表其个人潜意识,最底层代表其集体潜意识。其中,集体潜意识里有我们的祖先一代代传承给我们的共同的精神遗产,荣格称为“原型”,人的意识与行为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原型”[6]。
《英格力士》中的两个人物形象阿吉泰、老张可以看成两个经典的“原型”,其中,阿吉泰是母爱“原型”,老张是父爱“原型”。阿吉泰是新疆本地的维吾尔族姑娘,她质朴、美丽而善良,是大地里带着民间气息的精灵。从“原型”意义上讲,她的身上承载着在中华大地上生存的各个族群里那源远流长的普通而伟大的母亲形象。在岁月的长河里,多少普通的女性默默地承受着各种天灾人祸、兵荒马乱而顽强地养育着子女,呵护着家庭,让族群能够繁衍至今。很多文学作品里都有这样的母亲形象,《丰乳肥臀》里承受重重苦难把子孙们拉扯大的母亲,《黑骏马》里勤劳质朴的索米娅,还有《为奴隶的母亲》里受着屈辱而始终念念不忘自己孩子的阿秀。实际上,这样的女性形象不仅有母亲,还有姐姐。歌手张楚在《姐姐》里唱道:“这个冬天雪还不下,站在路上眼睛不眨,我的心跳还很温柔,你该表扬我说今天还很听话……”,一个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怀念着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替他遮挡了外面风霜雨雪的姐姐,“姐姐带给我们的亲情以及长姊若母的那种温柔感动,永远地留在了那段相濡以沫的时光里”[7]191。
刘爱离家出走遇到阿吉泰,在领刘爱到她宿舍的途中,她教刘爱唱维吾尔民歌,“小路在延伸,就好像那是没有尽头的理想,温柔,淡泊,苍凉”,民歌里往往蕴涵着一个族群心灵深处、流传久远的情感和记忆,是一个人的精神原乡。刘爱离家出走时学唱民歌的经历,可以说是在回溯人的精神原乡,重新体验先辈人的思想与情感。王亚军的形象里没有体现出这些事物,这也许是阿吉泰不能接受王亚军的原因。
老张是从内地来新疆的“盲流”“是一路要着饭来的”“盲流在我们这些孩子的心目中是骂人的话,是小偷,杂种,流氓,强盗的另一种称呼”。刘爱离家出走后偶遇老张,和他一起住在倒塌的破屋里,跟着他去偷东西,艰难地生活了一个多月。主人公的这段艰难的生活,让人想起王刚的其他作品里“我”和哥哥的生活。王刚在西北大学读书时,曾写过一篇回忆性文章《湖南坟园散记》,里面回忆了他“文革”时期的童年时光,爸妈被改造,只有妈妈周六回来一趟,几岁的他和哥哥一起相依为命[8]55-62。后来,他在一篇小说《博格达童话》里,对这段童年时光进行了艺术再现。“我”和哥哥缺衣少食,无人管教,目睹外界的癫狂,心灵荒芜地生长。小说中,兄弟俩尽管被饥饿折磨,但还喂养鸽子,哥哥向熟人讨要吃的,带着“我”去偷瓜,和同伴一起偷废铁[8]203-247。长兄如父,哥哥和“我”一起,艰难地求生,竭力地填饱肚子,竭力地维护虚弱的心灵。
儿童文学理论家刘绪源认为,与“母爱型”作品相比,“父爱型”作品更加强调人要直面人生,往往具备“撄人心”的力量。它更追求一种迫近人生现实的深刻性,更倾向于让孩子去经受生存的艰辛、世事的艰难,去体会生活那强悍而残酷的一面[9]89。作家在写作《英格力士》时用笔是很节制的,那段岁月里生活的苦难与残酷在文中很少显露,但是主人公“我”要实现足够的成长,必须要经受残酷生活的洗礼。全书里老张所占的篇幅很短,但老张这个人物形象的设置是必要的,某种意义上他象征着深沉的父爱,领着“我”经受那段艰难岁月的洗礼。王亚军可能正是缺少了阿吉泰和老张身上带着的那种来自大地的气息,这些气息来自于族群以往岁月的观念和情感,是一个人的集体潜意识里流传久远的“原型”。潜意识里充满了生命本能的运动,实际上是一个人寻求人格意识发展的力量源泉,也是人的理性发展的源泉。
考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我们可以发现“父亲”“母亲”等人物形象是“圆形”人物,血肉丰满,形象生动,而王亚军的人物形象是“扁形”人物,性格比较单一、平面,更多的是一种理念的象征。作家为了张扬理性启蒙的理念,把很大的一部分笔墨用来塑造王亚军这个人物形象,同时使得作品里有一种审父的倾向。实际上,在六十年代作家的“文革”叙事作品里,这是一个通病。王刚在写《英格力士》时已经四十多岁,他下笔时相对节制一点,试图以一种更加悲悯、同情的视角来进行创作,但是他作品里的审父倾向依然是较严重的。所以,在创作中作家可能无意识地把一些本应属于父亲、母亲的品质转移到了老张和阿吉泰的身上。在恶劣的生存环境里,父母的人格素质也许只能比较地“平庸”和“低下”,他们对主人公的成长有很大的消极作用。不过,也许父母这些人格素质可以更好地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得以在那个环境里生存下来。在一些境况下,父母这些“平庸”“低下”的人格素质也给予了刘爱精神上的哺育,适度地引导了他的成长。下面的两个场景就是如此。
第一个场景:刘爱离家出走,跟着“盲流”老张艰难地生活了一个多月,为了填饱肚子而偷窃。在老张不幸死亡后,他回到了家附近,正在犹豫是否该回家时,听到了父母寻他的呼喊,“我就是在那时看到了父亲的背影,和朱自清爸爸的背影一样,它让我温暖而心酸。母亲站在他的身边,扶着他。他们像是相依为命的两个孩子”。面对着父母,他有了不同的目光,实在是因为他有了不同的心灵。“我突然出现在他们身边,吓得他们猛地转过身来,爸爸先是朝后边退了两步,惊恐使他张开了嘴,妈妈也下意识地拉上了他的手。当意识到站在这儿的人不是鬼,而是他们的儿子时,爸爸的脸上露出了从恐惧到欢乐的表情。”父母与儿子,目光与背影,离别与守候,呼喊与相逢,这样的场景在有人类以来的岁月里一直在上演着,蕴含着一种来自土地深处的气息。
第二个场景:在公审王亚军时刘爱拒绝揭发他,回家后,“我坐下来吃饭,他们两个人竟都坐在我的身边,看着我吃”。也许,父母挨在他身边坐时是一边一个,已近年迈的父亲对儿子的爱、期望甚至试图的倚靠,一切尽在不言中。在父亲斥责王亚军时,刘爱说“我觉得你也挺不要脸的”,父亲“给了我一巴掌”,“我”抬起脚狠狠踢向他的肚子,“竟把可怜的父亲当场踢到了”“在母亲的哭叫声中,我愣在那儿”。父与子的关系,永远值得探索。苍茫的天地间,永远是子与父一同地、保持适度距离地前行的剪影。生活对每个人都是艰难的旅程,托克维尔曾说:“我把生活在世上的人比作一个在十分寒冷的地区漫无止境地艰难跋涉的旅行者。”[10]只是一味地指责父辈已经形成的物质与精神,是否有利于子辈形成自己更好一点的物质与精神?而父子相向中“母亲的哭叫声”,也许更具有“原型”的普遍意味,蕴藏在很多人的成长记忆里。
还有同龄人之间相互的些许温暖和帮助,也是刘爱得到的精神哺育。他和儿时女伴黄旭升一起呆在树上,寒冷中他把自己的衣服给她穿并把她抱住,不经意间刘爱感受到她的胸部:“我更加清晰地闻到了她身上的薄荷香味,而且,我感到她的胸脯上很软,而且有两处地方显然高起来。就说:‘你们女生都这样吗?’她说:‘我比她们都高,别看我别的地方廋。’”这是少男少女美好的纯真情怀。那个特殊岁月里对性的禁锢,并不能完全阻止少年男女彼此的相互温暖和他们性意识的健康、自然地萌发。即使在比较混蛋的同龄人李垃圾身上,也看到了人性的微光,黄旭升的父亲自杀后,李垃圾去食堂打了米饭和肉菜端给她吃。
人容易因为太渴望得到一个事物而忽视了一直在他身边的也很重要的另一个事物。也许,作家在创作时,渴望让成长主人公刘爱得到西方的理性启蒙,而相对忽视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刘爱实际上更可能得到的、对他的成长也有帮助的精神哺育——周围的众人给予他的精神哺育。
三、有着启蒙信念的“自导”型成长
由第一部分的描述,可以看出主人公刘爱在王亚军的正面导引下,最终长大成人。但是,根据第二部分的反拨,王亚军这个人物形象更多的是一种理念的象征,带有较大的虚幻性,刘爱的成长实际上得到了周围众人的精神哺育。那么,主人公刘爱的成长到底是什么类型呢?
张国龙对成长引路人“自导”类型的理解,是“成长者在成长路上的自我教育,无缘借助他者之力长大成人,因卓越的悟性和超强的自省能力而自助成长。这样的成长者凤毛麟角,其成长经历非常另类”[1]31。张国龙接着以《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中的成长主人公哈克为例阐述这一成长类型,哈克为了“逃脱恶魔般的父亲”而离家出走,踏上漫长而艰难的成长旅程,尽管在途中黑人吉姆时不时地与他相逢,但在他的成长之旅中吉姆基本上处于缺席状态,哈克靠着自己的体悟慢慢长大成人[1]31。令人意味深长的是,《月亮河》这首歌正是讲诉哈克和吉姆这两个漂流者的。这首歌在《英格力士》里出现了三次:王亚军将这首歌教给刘爱,离家出走中刘爱唱给“盲流”老张听,父亲在逝世前向刘爱解释了它。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刘爱处于迷茫之中,王亚军教给了他;在离家出走期间,刘爱顿悟了父母的“可怜”和环境的某种“可怕”,他唱给“盲流”老张听;父亲逝世前,向刘爱解释了歌的意义。在这首歌里,父亲、老张和王亚军三人的形象合而为一了,他们似乎都是哈克的朋友黑人吉姆,而刘爱正是哈克。这明确地暗示了尽管王亚军正面引导了刘爱,但他只是刘爱成长之旅中的见证人,主人公的成长是和哈克一样的“自导”型成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家长们疲于应付各种运动而自顾不暇。“在那种人人自危的社会关系里,他们要么忙于大生产,为生计奔波,要么出入各种政治学习的会场,参加各种层出不穷的批斗会,根本无暇去关心这些孩子的成长。”[11]34处于这种境况下,孩子的成长必须依靠他自己,主人公刘爱正是在主动的离家出走中独自实现了精神的顿悟。
实现精神顿悟是欧美经典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在成长之旅中经历的标志性事件,在主人公经历精神顿悟后,他的主体性得以生成,从而在精神上真正地长大成人。“‘顿悟’一词原是宗教术语,乔伊斯对这个术语作了新的阐释:顿悟是一种突发的精神现象;通过顿悟,对自己或者对某种事物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12]《英格力士》全书中,主人公的精神顿悟出现在刘爱遇到阿吉泰,领悟到父母“可怜”的标志性事件中。刘爱离家后遇见了阿吉泰,当晚在她家窗外看到了范主任的非礼行为,刘爱去砸门而让她有机会跑出来。范主任叫她再进去,阿吉泰犹豫着,“她的眼神有些可怜,就好像她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她无辜,无奈,无所适从”,然后,“奇迹发生了,阿吉泰竟然听话地进去了”,当然最终刘爱“挽救了阿吉泰”。这时,父母呼喊他名字的声音从湖南坟园里传来。“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爸爸妈妈的可怜,他们跟阿吉泰一样的可怜”。
阿吉泰在本书里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刘爱成长的经历中,如果说王亚军给了刘爱来自西方的理性启蒙,那么,她给了刘爱孕育于大地里的情感启蒙。她质朴、美丽、健康而善良,是大地里带着民间气息的精灵,是那个混乱岁月里刘爱、李垃圾等一帮懵懂少年梦中的女神和心灵的慰藉。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女子,在范主任的无赖举动下,是那样地可怜——这个画面对他太震撼了。就在这时,刘爱听到了父母的呼喊。这些大人真可怜!主人公刘爱便在这个时刻实现了精神顿悟,主体性得以生成。刘爱在此时有一种类似存在主义的个人意识,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孤独的存在。他觉悟到了父母照料他的不易,他们的可怜和周围环境的某种“可怕”,他像野兽一样独自地躲在暗处“观察”他们。这种存在主义意识在《“六十年代”气质》一书里也有描述:“这代人有着天生的、永恒的距离感。他成了历史的观看者。所谓观看者,就是历史上演的一切都跟他若即若离。‘文革’他经历过……但他却并不是个参与者”“实利社会来临了……(与他们的)幼年根茎相悖,也产生了一种疏离”[7]83。不过,在这种观看中,其中会有人形成清醒的存在主义的个体主体意识,勇敢地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刘爱正是如此。他在觉悟了父母的“可怜”和周围环境的某种“可怕”后,选择了离家流浪,和老张艰难地生活,在英语老师王亚军被公审时拒绝揭发自己的导师,他扔向空中的纷纷扬扬的纸张在某种意义上是向外界宣告其独立主体意识,是一种经历重重考验后的成人式的正式完成。
《英格力士》中,王亚军这个人物形象不是可有可无的。在那个苦难的岁月里,众人的精神哺育可以给予主人公刘爱一定的心灵温暖和慰藉,但是单凭这些,并不足以让主人公跳出那个时代的局限,实现真正的成长。在其它作家的“文革”童年叙事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即使有了周围众人的精神哺育,主人公也很难如期长大成人。《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光林、国庆和苏宇等人的父亲要么是个无赖,要么不在场,使得他们在无序成长中遭遇了集体式的受难;《刺青时代》和《城北地带》中的王小拐、红旗和李达生等人只能寻找所谓江湖高人的指引,只能任凭青春期的本能力量四处奔突,在香椿树街上洒下少年血。从这些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出,有一个优秀的人生导师,一个能够给你指示正确方向的人生导师,是多么重要。在那个丧失理性的年代里,拥有启蒙信念的英语老师王亚军正是这样的人生导师。在《英格力士》里,王刚通过设置王亚军这个人物形象,让主人公刘爱认清时代的荒谬,找到成长的正确方向,实现了对他所处现实的某种超越。
“儿童是永远弱小的,但他们总是在想象中将自己描绘得无比强大。这是因为儿童同成人一样爱体面,爱成功,而不喜欢遭受狼狈的挫败。这种自小形成的对于体面和成功的自觉与不自觉的追求,正是整个人类得以向前发展的一种精神的推力。”[9]165实际上,何止儿童,每个人在面对现实世界时,他又何尝不是永远弱小的,他永远受制于现实的种种束缚,永远在不断地面临挫败。这样,一个人在回首自己的成长时,他看到的常常是在种种困难和打击中狼狈不堪的自己,顺利的成长是偶然,挫折与失败是常态。那么,他应该怎样看待自己以往的成长,从而更好地在未来前行?面对以往的成长之旅,他是应该更强调现实世界的永远强大对人的永久束缚,还是应该强调在永远强大的现实世界里,人的精神点点滴滴的积极努力?可能应该选择后者,想象正可以给人插上翅膀,使得人不用永久地匍匐于现实的尘土,而自由地翱翔于精神的天空。阿尔贝特·史怀泽面对物质发展过分超越了精神发展的当今人类世界时说:“决定文化命运的是信念保持对事实的影响”[13]。实际上,一个人回首自己的人生时,面对众多已经发生的所谓客观事实,他也需要让自己积极的信念保持对这些事实的影响。一个六十年代出生的成人回首他糟糕的童年现实时,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作家在《英格力士》中创造王亚军这样一个比较虚幻的人物形象,会更有意义。
“在六十年代出生人的成长记忆里,最突出的是理性启蒙的缺席。它意味着科学和人性的缺席,使他们无法明白作为一个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当他们成年后,站在科学理性的价值观中来反省这种状态,便会发现这种成长与健康意义上的成长有着太多的差距。”[11]40作家王刚的成长记忆正是如此,他在回首自己的童年时说:“我的童年只有暴力。我看见了很多大人在打……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孩子在教室里老师的批斗会上,当灯关上时,也会忍不住地冲到老师的身边,在黑暗中,拼命踢她的肚子。”[14]9然而,一个人儿时如果只是在暴力的阴影下成长,那是可悲的,童年里一定有一些其他更好的东西。值得作家庆幸的是,他找到了少年时吹长笛的经历,“它的声音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动情精神,我吹过巴赫、柴可夫斯基、莫扎特、鲍罗丁等许多人的作品”[14]9。这些作品属于西方古典音乐,古典音乐讲究节制、和谐、匀称。那么,在那个文明被放逐的年代里,一个少年学习和迷恋这些作品,是他努力地通过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部分来引导自己成长的艰苦探索。王刚在构思《英格力士》时已经四十多岁,有了很多的人生经历,有了一种更加平和的人生态度,更加意识到这些古典音乐作品所蕴含的精神的可贵。在英语老师王亚军这个比较虚幻的人物形象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精神的影子。在那个时代的暗夜里,主人公刘爱正是在王亚军的启蒙下,依靠自己的不懈探索,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性思考能力,穿越了重重迷障而最终长大成人。考察到这里,我们可以确定王亚军这个人物形象的重要性,它实是小说《英格力士》的灵魂。
四、结语
《英格力士》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成长主人公刘爱有幸遇到了王亚军,在他的启蒙信念的引导下,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悟性,顽强、艰难地长大成人。六十年代出生的学人单世联说:“我觉得德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保存了深厚的精神传统的同时迅速致力于经济技术的现代化,失落了现代启蒙的环节并把浪漫主义的反抗现代性推向公共政治领域,为后来的历史悲剧埋下了伏笔。”[7]274和德国相比,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精神传统不是保存过多,而是破坏过多。不过,现代化进程中欠缺理性启蒙,这一点中国与德国似乎有相似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那个放逐了文明的特殊年代里,代表着启蒙信念的王亚军形象是值得肯定的。
[1]张国龙.成长小说概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
[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
[3]约翰·洛克.教育漫话[M].徐诚,杨汉麟,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4]谈凤霞.喧哗与骚动中的成长危机——论“文革”童年叙事的人文反思[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105-109.
[5]苏童,王宏图.南方的诗学[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75.
[6]史蒂文斯.简析荣格[M].杨韶刚,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223-226.
[7]许晖.“六十年代”气质[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8]王刚.秋天的男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刘绪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M].上海:华东大学出版社,2009.
[10]塞缪尔·斯迈尔斯.自己拯救自己[M].刘曙光,宋景堂,李柏光,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26.
[11]洪治纲.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12]ABRAMS M H.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8.
[13]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45.
[14]王刚.在怀旧中叛逆成长[J].语文教学与研究(读写天地),2012(11).
【责任编校朱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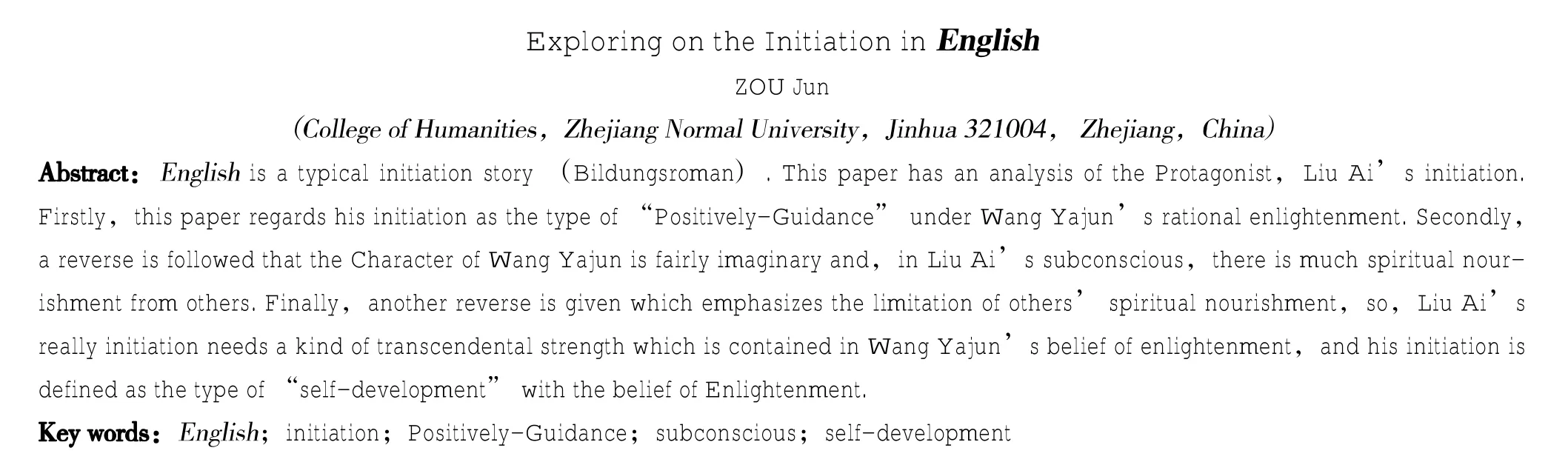
I207.42
A
1674-0092(2016)04-0048-06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4.011
2016-01-10
邹军,男,湖北仙桃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