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强权的选择:小说的思考
2016-09-18陈利娟
陈利娟
(广东金融学院 财经传媒系,广东 广州 510521)
面对强权的选择:小说的思考
陈利娟
(广东金融学院 财经传媒系,广东广州 510521)
强权现象在中国小说中一直存在,多以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欺压和打击为主要方式,体现了中国人固有的官/民、贫/富的二元对立心理模式;直到明代中期以后,在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等中,出现了各种各样、多角度的强权现象。这种种描述使我们认识到强权产生的深刻性与复杂性,认识到若不加以规范,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施暴者。小说世界的暧昧性和复杂性,使得小说与现实的极权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
强权;世情小说;道德;相对性
道德没有对错,只有选择,任何关于道德的判断总是以某种特定的选择作为标准,是比较的结果,而不是所谓客观的真理。只能以道德作为阿基米德的支点来撬动道德,这是所有道德话语的悖论。这点实际上意味着人类生活中“最高审判官的缺席”“人类事件具有本质上的相对性”。烛照那些暧昧、相对的世界,发现我们的存在密码,是如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智慧”[1]。
一
在中国古代,小说往往掷地有声、义正辞严,在小说的序言、跋、行文之始、上下文中间以及小说结尾处鲜明地表明某种观点,阐明微言大义,清晰地作出不容置疑的道德判断,评点人物,结构故事。从六朝时期的《搜神记》至新文化运动以前,基本都把教化民众、劝善惩恶作为评判世事人生的终极真理,以正视听。在《搜神记·自序》中,干宝就提出自己作《搜神记》的主旨:“……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栽。亦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2]20直接将小说当做阐释其学说、思想的工具。刘知己在《史通·杂述》篇说:“在昔三坟五典,《春秋》 《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纪,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来尚矣。”[3]将小说当做历史的辅助资料,读之亦有价值。瞿佑在《剪灯新话·序》中道:“今余此编,虽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客以余言有理,故书之卷首。”[4]教化目的十分明确。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传统诗教的影响由很大关系。儒家诗教“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5]自汉代成为主流思想后,一直左右着文人的创作,使得他们自觉遵循创作要有益于世代人心、要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启发民智的倾向。在主流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小说的功能亦偏重教化至上。小说家和评论家都很重视小说的社会教育作用,认为小说须“有补于世,无害于时。”[2]147要“表其乐以酬善”“彰其丑以惩恶”[6]。“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而怵惕,以成风化之美。”[2]264甚至认为:“小说家千态万状,竞秀争奇,何止汗牛充栋?然必有关惩劝,扶植纲常者方可刊而行之。”[7]突出强调的正是小说的教化和劝解作用,即鲜明的道德意识。在作者自以为是的善恶判断下,小说的主旨和叙述呈现并行不悖的契合。这种叙述方式一方面造成小说陈腐抽象的说教比较多,使小说沦为善恶果报的图解,破坏了小说的艺术完整性;另一方面造成小说人物形象单薄空洞,类型化而非典型化,面目相似,性格固化,人物缺乏个性,忠奸分明、黑白立现,对比反差过大,正面人物无一处缺点,永远伟大、光荣、正确,而反面人物则獐头鼠目、浑身猥琐,呈现脸谱化的恶俗特点。
实际上,只有在道德审判被悬置的境况下,小说才能成为小说。在作者的笔下,一个个人物形象并不能作为客观规律的影像,或者按照某种善或恶的样板来设定和构思,只能按照他们自己的生存面貌、他们自己的规律法则,他们自己的道德体系来构建,这样小说人物才能茁壮成长。而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小说观念,要到《金瓶梅》 《红楼梦》以及受这些小说影响的后世小说出现后,才真正体现出来。具体在描述强权现象上,这些小说写出了人类事件具有本质上的相对性,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峙的世界,呈现了小说独有的智慧。
在一个畸形的、混乱的社会中,强权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关于这一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金瓶梅》与《红楼梦》两部世情小说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探索。在此之前,中国文学对强权的书写一向是单向度的,皆是自上而下的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强势阶层对弱势阶层的欺侮和压迫。如《窦娥冤》之类社会剧中官府对良民的迫害和屈杀,《西厢记》之类爱情剧中父母对子女爱情婚姻的强行干涉,《包公案》之类公案小说中有钱有势者通过贿赂官员导致案情错判的黑暗现象,《碾玉观音》等宋元话本社会小说中职位高贵者对身份低贱者的任意虐杀……在强权肆行的社会中,民众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和被同情者,而上层统治阶级、身居高位者、辈分居长者、财富亨通者成了施虐者、施暴者,是迫害事件中惟一的肇事者,不值得任何同情和理解。实际上,这种将强权的施行者/被施行者按照阶级、阶层二元划分、直接对立的写法影响深远,直到现当代小说中,仍然可见清晰的痕迹,如巴金的《家》、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莫言的《丰乳肥臀》等等,都是将身居强者的群体或个人当做是施暴于弱者的恶人或恶势力。只有在描写善恶边界模糊、暧昧的世情小说《金瓶梅》 《红楼梦》等小说中,强权才呈现出相对性、多元性。
二
在《金瓶梅》 《红楼梦》等多部小说中,作者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对强权进行了审视,体现了大慈悲者的悲天悯人与生存智慧。实际上,置身于权力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对他者施加强权,而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专利。上至高官下至奴仆皆可能成为施暴者,他们凭借手中小小的权力去要挟、干涉、欺辱他者,通过碾压他人获得存在感和利益。当然,社会地位的不同必然造成人们的力量差异。高位者拥有更多的权力,也就有了更多施以强权的条件。富压穷,官压民,大官压小官,这在《金瓶梅》中远不止百起事件。高官如山东御史曾孝序,遭遇太师蔡京,却也在强权面前被碰了个头破血流。小说写曾公本为御史,考核清河县理刑正、副两千户的政绩,发现两人玩忽职守、大肆搜刮民财,于是行使职权,“振扬法纪”,上本参劾。结果由于夏延龄和西门庆上京打点,蔡京暗示部下只批了个“该部知道”,将此掩盖。曾孝序不甘心这种不公正的回应,觐见朝廷时再次上奏表章,批判蔡京所行政事。怎奈蔡京拍好了皇帝的马屁,先是把他“黜为陕西庆州知州”,后又使人“劾其私事,逮其家人,煅炼成狱,将孝序除名,窜于岭表”,像俗语说的“官大一级压死人”①文中《金瓶梅》引文均出自秦修容整理的《金瓶梅(会校会评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又如主人公西门庆从依附于权力的无赖到成为权力圈中的官吏,强权之棒舞得更加猛烈了。在未握实际权力时,西门庆仅敢胡作非为,敛财、猎色尚且畏手畏脚。揽财说事,获取好处,必须先交通官吏;追逐女性,至少你情我愿,不敢明目张胆、强取豪夺,迎娶潘金莲只能偷偷摸摸天黑时从偏门接进。杀害武大也并非本意,是在潘金莲和王婆的挑唆与指引下,一步一步走向深渊。在听说武松为其兄伸冤将自己告发后,他急忙上下打点、卖力经营,才将武松“充配孟州道”。他的恶行恶迹,都以手中的银子为工具,以买通官吏的庇护得以成行,自己尚没有能力摆平一切,尚不能为所欲为地欺压他人。待到贿赂过蔡京、得其赏识,做了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后,西门庆才彻底放开胆子,依仗官职,施行强权,肆无忌惮,直接将官府赋予他的权力变为最直接的施暴工具。他公开索贿,以一千两银子的所得换取了杀人犯苗青的生命;为情妇出气,竟随意动用官刑“夹打二捣鬼”。他威胁别人的口头禅竟是“好不好,也拶他一拶子”,官府的人员、刑具都沦为其行使私利的工具。北岛的诗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居高位者所拥有的统治权力正是强权的通行证。《红楼梦》亦复如是。第四十八回写贾赦看上了石呆子家里的扇子,但是石呆子不肯卖,结果贾雨村就胡乱按了个“拖欠官银”的罪名把他家的扇子全部抄来送给贾赦,而且把石呆子惩治的不知死活。第十五回写王熙凤弄权铁槛寺,只为三千两银子,便强行拆散了一对夫妻①文中《红楼梦》引文均出自曹雪芹著、高鹗续《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在位高权重、财大气粗者的世界里,是没有规则、公平而言的。
然而,身处社会底层的人,那些为强权所欺侮的人,也会施行强权,只要有机会也会挥舞起手中偶尔得之的大棒,毫不犹豫地挥向更为弱势者,展示自己的力量,侵占别人的利益。如《红楼梦》中怡红院的丫鬟秋纹,因早几年跟在宝玉身边,成为贴身丫鬟,比别的小丫鬟与宝玉的关系亲密,就似乎得了权势,经常防范和压制其他的丫头接近宝玉。当有一天秋纹等贴身丫鬟因忙别的活不在宝玉身边时,后进园子的小红及时出现在宝玉面前,待其欲趁递茶机会想多表现自己的才貌时,便得到了秋纹的打击和嘲弄:“没脸面的下流东西!正经叫你催水去,你说有事,倒叫我们去,你可抢这个巧宗儿。一里一里的,这不上来了吗?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么?你也拿镜子照照,配递茶递水不配。”断绝了她跟宝玉见面的机会。秋纹声声口口骂小红下流,骂她不配递茶倒水,将自己看成了主子,无奈在外人眼里她也只是个下人,其强权行为遇到机会便不遗余力地发泄出来。又如宝玉的贴身男仆茗烟,因是“宝玉第一个得用且又年轻不谙事的”“无故就要欺压人的”,听说主人在学堂里被他人欺负,顿时不顾身份高低,直接找地位比宝玉低的肇事者报仇,将学堂弄了个天翻地覆。在《金瓶梅》中,这样的例子更多。西门庆的家仆玳安,仅仅因为是西门庆的贴身奴仆,没有任何官职和社会地位,但其和主子西门庆一样,在嬉游妓院蝴蝶巷时,恶意霸占妓女,随意打骂客人,并威胁他们“好不好,拿到衙门里去,且交他试试新夹棍着”,仿佛官吏。再有西门庆家仆来旺妻宋惠莲,就因为与西门庆通奸,依仗主子的宠爱,“把家中大小都看不到眼里”,不仅推卸本职工作,且随意打击其他家奴。在《金瓶梅》浑浑噩噩的纷乱尘世里,在《红楼梦》大观园内外人来人往的交接中,有头有脸的丫头随意指使新来的或粗笨的丫头,得势的奴才仗着主子的权势,为虎作伥,无不与他们依仗的势力有关。下与上,低与高,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实质上大多相像。膨胀自大,欺负弱者,自以为是,以凌辱他人来获得身份感与存在感同样存在于底层人物的内心深处。
三
换个角度说,强权不仅存在于个人、群体、阶层对外的关系之中,也存在于其私密的内部的关系之中,如家庭内部的生活、朋友交往也总是为强权所左右,甚至爱情、亲情、友情往往靠强权来维系。强权得力,风风火火;强权弥失,树倒猢狲散。对西门庆来说,其一妻五妾,女儿、女婿,生存发展都得仰仗于他,都需要他施与怜悯和救助,理所当然也必须听从他的指挥和强治。妻子吴月娘空有正妻名号,既不敢阻止西门庆节欲守家,又不能奉劝他遵行正道,只能顺着他的心意小心行事。其余妾婢,更是其泄欲的对象,“稍不中意,就令媒人卖了。”妻妾的地位完全取决于西门庆的好恶。孙雪娥虽尊为三房,持羹做汤,辛苦劳累,但遇西门庆不高兴,就被打得鼻青脸肿;潘金莲虽貌美如花、风情万种,因家境贫寒,无出子嗣,内心充满了危机感。为讨好西门庆,巩固自己的地位,她宁愿忍受剧烈的疼痛来迎合西门庆变态的嗜欲,结果使自己“头目森森然,莫知所之矣”,险些丧命。李瓶儿对西门庆一片真心,将万贯家财交付于他,就因曾招赘蒋竹山一事,被西门庆记恨于心,在新嫁西门庆之际,被“汉子一连三夜不进他房”,饱受冷暴力折磨,直至绝望地“悬梁自缢”。被解救下来,西门庆不仅不去安慰,还要马鞭子伺候,大骂一顿,抽了几鞭,待其告饶后方才罢休。强权深深地渗透在西门庆与其妾婢的关系之中,在争宠的过程中,西门府中的女性无不伤痕累累。《红楼梦》中,王熙凤依仗贾母宠爱和丰厚的经济财富,常常凌驾于贾琏之上,阻止其娶妾生子,生分了夫妻之情。除了夫妇之间,带有血缘关系的父女之间也存在强权。西门庆的女儿、女婿寄居其家,待遇却几同奴仆。女婿常年为其免费打工,吃饭却只能与奴仆伙计一起;女儿处境更是寒酸可怜,每次制作新衣,都与“灶下婢”孙雪娥一般。强权以理所当然的男权控制了夫妻关系,以冷酷僵硬的父权淹没了亲子关系,将最私密的亲人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夫妻关系、血缘关系,都不是可以护身的屏障。为攀附权势,《金瓶梅》中韩道国、王六儿夫妇,心甘情愿把十五岁的女儿嫁给了年近四十的蔡府管家翟谦做二房。为偿还债务,《红楼梦》中贾赦、邢夫人将女儿嫁给“中山狼”式的人物孙绍祖。在强权面前,牺牲家人、亲人的利益以取得丰厚的物质利益,实在是普普通通的一件事。所谓朋友之义亦不过如此。《金瓶梅》首回即“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一冷一热对比之下,可见西门庆的朋友之情实在滑稽可悲。众人“热结”西门庆,无非“见西门庆有些钱钞”可以蹭吃蹭喝,见其结交官府可以仗势欺人;待其纵欲身亡,势去权倾,其余人等纷纷变脸背叛。应伯爵排行老二,是西门庆最亲密的朋友,待其死去,应伯爵即刻投靠张二官,并唆使他娶西门庆二房李娇儿、五房潘金莲为妾。三弟吴典恩既不感激西门庆对他的提拔,还在西门庆死后,企图霸占西门庆正妻吴月娘、吞并其家产。西门庆本人更是“朋友妻,不可欺”道义之情的反面典型,不仅吞并了其四弟花子虚的家产,更抢走了他的妻子,将人们心理愿望中的朋友之义彻底解构。所谓“十兄弟”,实际是“见他家豪富,希图衣食,便竭力奉承,称功颂德”,一旦门庭冷落,“就是平日深恩,视同陌路”的最佳讽刺。又如杨大郎与陈经济之间几度分合,也莫不与强权有关。蒲松龄在《镜听》中曾借异史氏之口曰“贫穷则父母不子”[8],鲁迅先生感叹,在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9],就是对彼时家庭、民族中强权左右人际关系的最沉痛的反思。成功就是王道,任何人都没有原罪,不计过程只看结果。一切的人际关系都在强权中“正名”“定分”,攀附强者,欺压弱者,由此构成了生活的常态。
在遭遇强权凌辱时,各阶层的表现亦不相同。在《金瓶梅》与《红楼梦》描绘的世界中,可以发现唯有拥有权力者才能反抗强权。《金瓶梅》中的曾御史本为行使御史职责,弹劾贪官污吏,“振扬法纪”,但遭遇上司阻止;曾公“心中忿怒”,见朝覆命时又上奏表章,批判蔡京所推行的政事。曾公之所以如此,一是出于道义,更重要是其御史之职所致。《红楼梦》中唯一敢为受害者说几句公道话的是贾琏,他身为荣国府长子贾赦之子,在看到贾雨村为讨好父亲任意欺凌石头呆子的行为后,实在看不过眼,向父亲抱怨了贾雨村的恶行。因为是荣国府的核心成员,又是贾府嫡系继承者,他才敢指出贾雨村的恶行。可在更高职位者的再次施压后,他们再也无法抗拒,只能接受不公正的处罚。作为底层者,在面对强权施暴时,少数反抗者一律得到残酷的报复,多数选择了接受、屈服,乃至主动迎合。《金瓶梅》中武大的妻子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给武大戴了“绿帽子”,为挽回尊严,武大前去捉奸,但结果被打伤甚至被毒死。仆人来旺因妻子宋惠莲与西门庆通奸,心中愤怒,酒后骂了几句主子的气话,结果被西门庆设计陷害,被官府发配至徐州。为活下去,大多数被施以暴行的受害者多选择了接受、主动投靠。落魄的韩道国受西门庆提携做掌柜,得知其妻王六儿与西门庆通奸后不仅不愤怒,反而即刻嘱咐老婆:“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承他些儿。如今好容易赚钱?怎么赶的这个道路?”以后凡是得知西门庆要与其妻私通,他自觉地躲出去。这番机灵和配合,使得西门庆便格外看顾他们,为其买房,为其提供更多发财的机会。而被西门庆抢了其弟家产又夺了弟妹的花子由,在弟妹李瓶儿新婚之际不仅不回避,还以亲戚身份与西门庆家走动,其乐融融,不能不说权势的力量真的可以磨灭人性与伦常。《红楼梦》中鸳鸯的哥嫂得知贾赦看上了妹妹,一口应承下来,主动请缨来做鸳鸯的思想工作,见到鸳鸯就道喜,并说这“可是天大的喜事”,期望“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没有权势者,在强权压境时自觉放弃了抵抗,放弃了人格与尊严,以屈辱的姿态迎合着强权者的施暴,并通过种种献媚与配合成为了一个个冷酷的施暴者。这个人群的扩大,直接导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10]
四
鲜活的人生有太多的晦暗、复杂与暧昧,非黑即白、大奸大恶、至善至美只能存在人类天真的臆想中。尽管司马迁认为历史的目的在“究天人之际”,明白告诉世人,我们的成就也许有“天理”可循,但“天”并没有道德,也没有公理,否则司马迁不会发出这样的喟叹:“至若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11]《金瓶梅》与《红楼梦》就是用这种生死相对、明暗对比的方式告诉我们,道德与感情是非常脆弱的,最伟大的情操面对苦难也会显示出它的晦暗与不堪,而沉沦与堕落有时候竟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必然选择。
这两部小说触及了人类生活的重要现象:强权和如何面对强权的凌辱。作者没有洞若神明般地暗示与指点,更没有高高在上地批评与审判,只是以平静地口吻和精妙的文字向我们展示了相同境遇下不同人物的不同选择和反应,即活着或是死去,让我们在道德与苦难的两重困境中警醒与反思,探究该如何面对世间的种种偏狭;让我们在充满暧昧性、模糊性的表述中,找寻到真正的生存智慧。
[1]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8.
[2]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3]刘知己.史通(卷十)[M].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瞿佑.剪灯新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
[5]李学勤.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 [6]佚名.海游记·序[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7]佚名.说呼全传·序[M].鲍方,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8]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09.
[9]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2.
[1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4:116.
[11]司马迁.史记(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657-1658.
【责任编校杨明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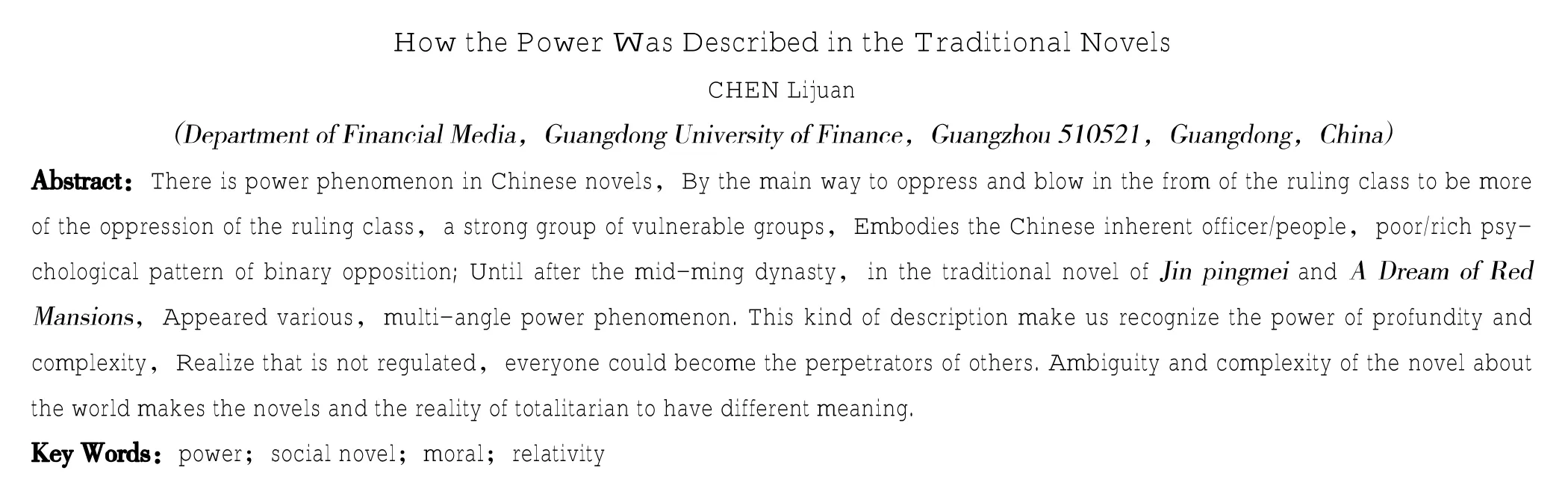
I207.4
A
1674-0092(2016)04-0034-05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4.008
2016-04-01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面对强权的选择——中国明清世情小说的现实性思考”(GD13XZW02)
陈利娟,女,河南民权人,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典小说与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