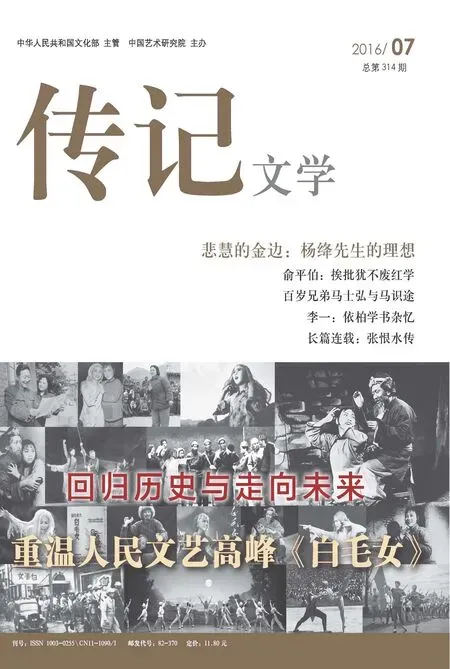张恨水传选章一
2016-09-16解玺璋
文 解玺璋
张恨水传选章一
文解玺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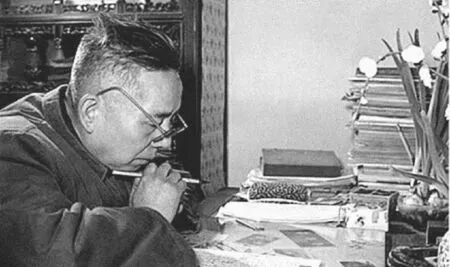
求学
1906年的到来,似乎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9月1日,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整个中国都激荡着一种求新求变的气息,在张恨水的家乡,新式学校已很少要求学生读经,重外而轻内,成为一时的风气,课本则多用东洋。但张恨水显然还没有脱离昔日的轨道,尽管已经没有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可能,但他所读之书仍在传统的范围之内。不过他后来承认,那时,他“真正感到有味的,还是家藏的两部残本小说。一部是大字《三国演义》,一部是《希夷梦》(又名《海国春秋》)”。书中的故事深深地吸引着他,使他欲罢不能。后来,他又找到一本残缺的《七国演义》,可惜只剩下“孙庞斗智”那一节了。这些书他都看得津津有味,从这些书中,他看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神奇的世界。这时,他已经能读懂《左传》了,他把《左传》也当作故事来读。家里还有一部《西厢记》,对此书,就像父亲桌上那部《红楼梦》一样,当时还不能引起他的兴趣。
张恨水喜欢小说到痴迷的程度,他曾说过,“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喜欢的程度,至于晚上让大人们睡了,偷着起来点着灯”,也要看。这自然引起了父亲的不满。在他的眼里,小说属于闲书,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之物。读书人所读之书,不敢说一定要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有关,总是要读那些有用的书,沉迷于小说,毕竟不是个好兆头,说轻了是“玩物丧志”,不求上进;说重了,也许会变成一个有文化、无操守的无赖流氓。他在心里早就为儿子规划好了人生道路,是想等他长大后送他到日本留学的,所以,见他迷上了小说传奇一类的“闲书”,不能不着急。张恨水因此受到了父亲的严厉批评。他本是个孝顺孩子,对父母从来都是恭顺听话的,然而,在这件事上,他却表现得很固执,把父亲的批评当成了耳边风。既然白天不能看,他就晚上偷着看。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全家人都沉睡进了梦乡,他便“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拿出藏好的小说,再爬上床,放下帐子,在枕头旁边放只小板凳,放上点好的蜡烛,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常常是天光大亮,才小睡片刻”。这种行为当然瞒不过父母。父亲就很为他的这种做法担忧。一是怕他长此以往把身体搞垮,二是担心水火无情,万一失了火,就麻烦了。父亲和母亲商量之后做出了让步,可以读小说,但不能影响“正经功课”,而且必须在十二点钟以前入睡,他每晚亲自查夜。对于所读之书也做了规定,凡是不能看的小说,一律没收。
张恨水一直说,他很不幸,从6岁入塾启蒙,直到12岁,就没遇到过一位好老师。然而,对广大内陆地区的学子而言,这样的求学经历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在家乡潜山住了一年有余,1907年初,因父亲再次奉调江西新淦县(今新干县)任职,他也随全家来到了该县的三湖镇。这里是南昌通往吉安的交通要道,赣江由南向北,在水流切割而成的峡谷与险滩中穿行,至吴城入鄱阳湖。流经这里时,江面变得开阔起来,水也深了,从赣州放下来的木筏,到这里要重新编扎,卖到各地去,清政府便在这里设了厘卡,抽取木税。张恨水的父亲就是厘卡上的一位师爷。多年后,张恨水在长篇小说《北雁南飞》和《八十一梦·退回去廿年》中,都借用了这段生活经历。
在三湖,父亲把张恨水送到一家半经半蒙的学馆里读书。科举时代,学馆是有蒙馆、经馆之分的,前者主要负责识字,后者则除了讲解经义,还要教学生作八股文。一般学生,六七岁进蒙馆识字读书,不间断地学到十六七岁,也就是十年之后,把《四书》《五经》都读熟了,再读一定数量的八股名文,掌握了八股文与试帖诗的作法,就可以考秀才了。张恨水进的这家学馆,学生年龄大小不一,程度深浅亦不同,事实上兼有经馆、蒙馆的双重性质,对外则称经馆。教书先生姓萧,大名萧廷栋,是个廪生(廪生,本名廪膳生,是考中秀才,入县学读书,由国家供给膳费。廪生是秀才中学问较为优秀者,其社会地位比秀才高。廪生教书,每年束脩也比秀才高一些)。因所设经馆系借用三湖镇老屋饶家的祠堂,于是又称“饶家经馆”。这里环境很好,四面橘林环绕,虽是严冬,那树叶子依然是绿油油的,如果是深秋,绿叶丛中结满橙红的果实,还会散发出一种甜香。院子里一棵大树,参天入云,庞大的树荫笼罩下来,显出十分的幽静。这可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他在这里是寄宿的,和三个同学同住一室,另有一间屋供他们读夜书。
萧先生有学问,人也相当开通,对学生采取“放任主义”,并不过多地干涉学生读什么书;对张恨水尤为赏识,潜山的乡人都称张恨水为“神童”,萧先生也是听说了的,一试,果然是名不虚传。张恨水在《北雁南飞》(小说《北雁南飞》作于1934年,先在上海《晨报》连载,1946年、1947年在山城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书中的姚廷栋就以萧廷栋为原型,李小秋就以张恨水为原型)中曾这样描述姚廷栋考查李小秋时的情形:“姚廷栋便叫小秋到师位前去,随便地在书架上抽了一本《古文辞类纂》来。掀开第一页,乃是贾谊的《过秦论》。姚廷栋道:‘我不知道你汉文的根底究竟如何。你可以把这篇文章,先念后讲一遍,我知道你的深浅了,再订定你的日课。’小秋回头一看,许多同学,都向自己望着。心下这就想着,我应当把一些本领给人家看看,不要让大家小视了我。于是将那篇《过秦论》抑扬顿挫念了一遍。姚廷栋听完了,点点头道:‘不用讲了,我已经明白你的根底。今天你初来,不必上什么新功课,可以自己随意理一理旧书,把心事安定了。明天我出一个题目你作,试试你的笔路。’”
上述虽是小说家言,却并非空穴来风。萧先生安排的功课,他都完成得很不错,夜课也只是念念古文,没有更多的要求,这让他感到十分的悠闲,使得他有更多的精力去读小说。同室有位管君,家里的小说很多,他不断带到学堂来给张恨水看。两个月之内,张恨水就读完了《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五虎平西南》。家里原有的半部《红楼梦》和一部《野叟曝言》,也被他一股脑儿全看完了。在他看来,读小说并非无益,至少,“使我作文减少了错别字,并把虚字用得更灵活”了。
六七月间,萧先生要到省里考拔贡。临行前,出了十道论文题目给张恨水回家去作,学校就算是“放暑假”了。按照清代制度,由各府州县的廪生秀才中选拔文章道德最优者,贡于京师,名曰拔贡。每十二年选拔一次,一等优秀者可以做七品小京官,或分发各省做知县。从前管这件事情叫做平地一声雷,形容其升官速度迅捷,是各种贡生中最出风头的。不过,清政府既已在1906年废除了科举制度,何以还有考拔贡一说呢?原来,朝廷考虑到停罢科举,改兴学校,中间还应该有个过渡期,才能实现新旧之间的平稳转型。因此,作为善后举措的一种,特别安排以前选拔出来的举贡生员参加优贡、拔贡考试,以及考职。其中考优只限三科,考拔只限一次,考职每三年举行一次,也限三年考尽,只是取录名额比以前略有增加。具体安排是,生员补考优贡于1907年和1909年各举行一次,补考拔贡和考职于1909年举行一次,举、贡考职于1907年和1909年各举行一次。由此可知,萧廷栋此时要考的,不可能是拔贡,而应该是优贡或考职,因为,拔贡考试要等到两年后才举行。
离开了饶家经馆,张恨水回家自学。当时,父亲办事的地方是万寿宫,他白天不回家,就在万寿宫戏台的侧面,要了一段看楼,摆上一张书桌,布置成一间书房。上得楼去,他叫人拔去梯子,又用小铜炉焚好一炉香,白天就在那里读书作文。他说:“那时,我桌上就有一本残本《聊斋》,是套色木版精印的,批注很多,我在这些批注上,懂了许多典故,又懂了许多形容笔法,例如形容一个很健美的女子,我知道‘荷粉露垂,杏花烟润’,是绝好的笔法。我那书桌上,除了这部残本《聊斋》外,还有《唐诗别裁》《袁王纲鉴》《东莱博议》。上两部是我自选的,下两部是父亲要我看的。这几部书,看起来很简单,现在我仔细一想,简直就代表了我所取的文学路径。”
有一种说法,要了解一个人,最便捷的方式,是看他读过哪些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就是书塑造的。也许,从这些书里,真的可以发现打开张恨水心灵之锁的钥匙。《聊斋》就不必多说了,全名《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小说集,作者是清代大才子蒲松龄。《唐诗别裁》是一部唐诗选集,选家是清康乾时期拟古诗派的代表人物沈德潜,“别裁”一词取自杜甫诗“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他选诗的标准,是“取其宏博”,又不失“诗教之本源”,所以主张“微而婉,和而庄”;而又欲纠王士禛“神韵说”之偏,使人知道,唐诗中不仅有“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还有“杜少陵所云鲸鱼碧海,韩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至于诗教之尊,是“可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的。这两部书,是他的自选动作,由此可以慢慢品他的趣味;后面这两部书,一部《袁王纲鉴》,一部《东莱博议》,是父亲给他规定的“功课”。后者见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列在“史评弟十四”,南宋理学大家吕祖谦,人称东莱先生者所撰,是一部“为诸生课试之作”,张之洞称之为“词意显豁,段落反正分明,有波澜,有断制。学之可期理明词达”。然而也有真知灼见,譬如其中对管仲的议论,就对张恨水不无启发。再看前者《袁王纲鉴》,袁是袁了凡,王是王世贞,号凤洲,他们二人都是明代大学问家,一在思想道德领域,他的《了凡四训》,被誉为“东方第一励志奇书”;一个独领文坛二十年,是明“后七子”的精神领袖。然而,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考证,这部简明纲目体通史应是书商牟利之作,托名于袁、王二人而已。这且不去管他,我们所看到的,是他父亲为他作出的选择,包含着对他的怎样的期许;同时,我们对他的知识结构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万寿宫的“书房”里,张恨水把自己“关”了大约两个月。同学很少来找他,父亲也不加干涉,他乐得自由自在地读书写作。他模仿《聊斋》和《东莱博议》的笔法,将萧先生走时留下的十个题目都作成了文章。幼稚是很自然的,因为用字求其简练,甚至有些不通,但其中有一篇《管仲论》,交卷的时候,先生竟做了批改,而且,让父亲的朋友们传看。对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能得此殊荣,是十分不易的。因此,张恨水说,这“引起了我的自满”,并以“小才子”自居。后来到重庆,他在《王猛与管仲》一文中还提到了这件事:“儿时作《管仲论》,窃有所发挥。曾云:‘若欲图王,则有周在,若欲图伯,则列国尤多。何必低首下心,降于其仇之庭乎?’塾师见之,密为圈点。童子何知,自鸣得意,常以语人。”可见留给他的印象之深。
这一年的冬天,他们回到了南昌。父母因事回潜山老家去了,将他和弟妹托付给在南昌的亲戚照料。没有人管,张恨水更加胆大“妄为”起来。“我收拾了一间书房,把所有的钱,全买了小说读。第一件事,我就是把《红楼梦》读完。此外,我什么小说都读,不但读本文,而且读批注。这个习惯,倒是良好的。我在小说里,领悟了许多作文之法。”从前不大能看得进去的《西厢记》,现在也慢慢看出些门道来了。他说:“我看到金圣叹批的西厢,这时,把我读小说的眼光,全副变换了,除了对故事生着兴趣外,我便慢慢注意到文章结构上去,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的。”多年后他写过一篇短文,承认他曾得益于“三位古人先生”,这三个人,“一个是金圣叹,一个是袁才子,一个是纳兰性德”。袁才子就是写过《随园诗话》的袁枚,从他那里,他学会了“口所欲言笔述之,不用那些陈陈相因的话”;纳兰性德的《饮水词》也是合他口味的东西,读起来没有格格不入的感觉;“最有益于我的,要算金圣叹了”,他说:“我十岁的时候,就看了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那些小说,那不过当故事看罢了。十三岁时,我同时读西厢水浒,看到金圣叹的外书和批评,我才知道这也是好文章,得了许多作文的法子,后来再看石头记儒林外史,我就自己能找出书里的好处来。而且我读小说的兴趣,也格外增加。”为了感谢金圣叹送他写小说这个“金饭碗”,他甚至想过要改名“圣叹后人”。
转过年来,张恨水的父亲为了更好地教育子女,自立家馆,课子读书,请了徐孺子的后人做先生。徐孺子,名稺,南昌本地人,东汉时的贤人高士,他的家风是不作官,以“淡泊明志”为处世之道。相传,豫章(今南昌)太守陈蕃非常敬重徐的人品,特为其专设一榻,去则悬之,唐代诗人王勃作《滕王阁序》,便有了“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的不朽名句。这位徐孺子的后人没有教会张恨水什么,但他那鄙视做官的名士作风,却给张恨水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后来回忆道:“我这时本已打进小说圈,专爱风流才子高人隐士的行为,先生又是个布衣,作了活榜样,因之我对于传统的读书作官说法,完全加以鄙笑,一直种下我终生潦倒的根苗。”
这一年,张恨水14岁了。秋天到来的时候,他提出要进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父亲同意了。由于国文底子不错,他被插入南昌大同小学三年级。这是一所新式学堂,学制四年。校长周六平是江西著名的维新人物,晚清举人,学堂是他在1904年创办的,校舍就设在省城南湖湖心的水观音亭内。他在讲课的时候喜欢讥讽守旧分子,时常慷慨激昂地批评清政府腐败无能,介绍国际形势和新的科学知识。张恨水自幼接受的是旧学教育,又喜欢模仿名士的作派,在别人眼里很容易被看成是个守旧青年。因此,周校长有时也把他当作讥笑的对象。张恨水因此受到很大的刺激,但他没有气馁,反而促使他“极力向新的路上走”。这时,他“除了买小说,也买新书看。但这个时候的新书,能到内地去的,也无非是《经世文篇》《新议论策选》之类”。他只能从上海的报纸中汲取一点新的知识和思想,明白了现在这世界已经不是“四书五经”上的世界,而旧小说中常见的那种风流才子,似乎也不再适宜于眼前的社会。于是,“我一跃而变为维新的少年了”。不过,那时的张恨水对新文化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他的思想或许受到一些影响,但总是一些表面的东西,不会很深刻。而且,他在文学上的嗜好并没有改变,还是爱读小说,爱读风花雪月式的词章。这期间,他从金圣叹那里知道了《西厢记》和《庄子》都是文采飞扬的“才子书”。然而他说,“对于《庄子》,我只领略了较浅的《盗跖》《说剑》两篇”,而《西厢》却让他得到了“文学上莫大的启发,在那上面,学会了许多腾挪闪跌的文法”。
1910年暑假,张恨水考入了位于南昌敬贤门外的甲种农业学校,那一年他15岁。这是当时南昌仅有的两所洋学堂之一,按照规定,像他这个年纪是不能报考这所学校的,但他虚报年岁为19岁,竟也被录取了。在学校里,他看到同学都是二十多岁的人,心里便有一点自傲,看自己真像个少年才俊。但他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毕竟“除了英文,勉强可以跟得上而外,其余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没有一项不赶得头脑发昏”。因为这些课程对他来说都是从未接触过的,学起来自然觉得不甚容易。由于学业紧张,他已无暇顾及文学。只有到了放假的时候,他才能暂时回到小说的世界中去。这期间,他相继读了讽刺小说的经典之作《儒林外史》,以及当时流行甚广的《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以揭露清末官场腐败和社会黑暗的谴责小说。作者笔下婉而多讽、嬉笑怒骂的叙事风格,给他以全新的感受,不同于看惯了的风花雪月、才子佳人。这时,另有一部词章小说也引起了他的兴趣,就是咸丰年间魏秀仁所作《花月痕》。这部小说的特点,不在于写了什么,而在于写法别致,他的朋友符兆纶评价这种是:“词赋名家,却非说部当行,其淋漓尽致处,亦是从词赋中发泄出来,哀感顽艳。”这种写法之于小说,或有“文饰既繁,情致转晦”的种种缺陷,但其中的诗词小品,以至于精巧工整的小说回目,却让张恨水陶醉了。后来他作《春明外史》,在词章方面,分明便有《花月痕》的影子。由于这样的趣味深深地影响着他,他便更进一步地读了《桃花扇》《燕子笺》《牡丹亭》《长生殿》等明清传奇,以及四六体的《燕山外史》和古体文的《唐人说荟》。

少年时期的张恨水
张恨水接触外国文学,大约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起因是他很偶然地买了一本创刊不久的《小说月报》。在这本刊物中,他第一次看到外国作家写的短篇小说,便有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是以前从未体验到的。他很惊奇,于是,又找来许多翻译作品,主要是林纾翻译的小说,他说:“在这些译品上,我知道了许多的描写手法,尤其心理方面,这是中国小说所寡有的。”这一年,他剪了辫子。这是一个新旧交替、动荡不安的时代,新的事物层出不穷,旧的生活又何曾远去?张恨水在新式学校里读了些新书,感受着周边洋溢的新的生活气息,各种新的思潮冲击着他,影响着他。他毕竟是个青年,有着一般青年意气风发、跃跃欲试的特点。入学第二年的10月10日,武昌发生兵变,并引发各省在短时间内纷纷宣告独立,清王朝随之垮台。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张恨水剪了辫子,要做革命青年了。二十四年后的“双十节”,他还作诗忆及当时的情景,其中一首写道:
剪发高呼喜欲狂,白旗一夜遍南昌,
回思廿四年前事,雨泊风飘梦一场。
尽管如此,他始终未能脱离固有的生活轨道。看起来,他不是一个主动选择人生道路的人,他只是在惯性的驱使下,遵从着个人的兴趣往前走。多年来所读的小说和词章,塑造了他的品性和气质。在革命激情退去之后,他仍然是那个“才子的崇拜者”。他很清醒地看到了在新旧之间游移的自己,他说:“这两种人格的溶化,可说是民国初年礼拜六派文人的典型,不过那时礼拜六派没有发生,我也没有写作。后来二十多岁到三十岁的时候,我的思想,不会脱离这个范畴,那完全是我自己拴的牛鼻子。虽然我没有正式作过礼拜六派的文章,也没有赶上那个集团,可是后来人家说我是礼拜六派文人,也并不算十分冤枉。因为我没有开始写作以前,我已造成了这样一个胚子。”
“礼拜六派”这个名称源自1914年6月在上海创刊的《礼拜六》周刊。它的编者最初为王钝根、孙剑秋,后又加入周瘦鹃,他们的宗旨可见于王钝根写的《出版赘言》:
或问:“子为小说周刊,何以不名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而必名礼拜六也?”余曰:“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人皆从事于职业,惟礼拜六与礼拜日,乃得休暇而读小说也。”“然则何以不名礼拜日而必名礼拜六也?”余曰:“礼拜日多停止交易,故以礼拜六下午发行之,使人先睹为快也。”或又曰:“礼拜六下午之乐事多矣,人岂不欲往戏园顾曲,往酒楼觅醉,往平康买笑,而宁寂寞寡欢,踽踽然来购读汝之小说耶?”余曰:“不然!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且买笑觅醉顾曲,其为乐转瞬即逝,不能继续以至明日也。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故人有不爱买笑、不爱觅醉、不爱顾曲,而未有不爱读小说者。况小说之轻便有趣如《礼拜六》者乎?《礼拜六》名作如林,皆承诸小说家之惠。诸小说家夙负盛名于社会,《礼拜六》之风行,可操券也。
由此可知,这是一本典型的都市消闲刊物,其中多是供给读者在劳累一周之后放松身心、消磨时光的游戏之作,体裁则兼收并蓄,以哀情及社会性质者居多数。大部分是文言,也有用白话的。译作以长篇或中篇为多,作者有周瘦鹃、天虚我生(陈蝶仙)、李常觉、陈小蝶、叶圣陶、许指严、姜杏痴、包天白、罗韦士、程华魂、吴双热、吴绮缘、包柚斧、俞天愤等。当时,这一类刊物数量相当多,即鲁迅所说的“鸳鸯胡蝶式文学的极盛时期”,除了《礼拜六》,还有王蕴章、恽铁樵编的《小说月报》,徐枕亚编的《小说丛报》,李定夷编的《小说新报》,包天笑编的《小说大观》《小说画报》,以及他与陈景韩合编的《小说时报》,再加上高剑华编的《眉语》,王钝根与天虚我生编的《游戏杂志》,胡寄尘编的《香艳小品》之类,据范伯群统计,大概有三十七种之多,真可谓洋洋大观。这种消费性期刊的盛行,其社会基础是近代以来大都市崛起、发展所形成的正当需求,也是人性的自然需求之一。满足这种需求,则是文学应尽的职责。而且,清末剧烈的社会动荡,使传统读书人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科举时代,读书人纵然有万般想法,走的仍是同一条仕途,然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这些人来说,却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件。随着清王朝的被颠覆,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也因此终结,天下精英从此解除了与固有体制的契约关系。以前是学好文武艺,售与帝王家的,现在买方不在了,这些被原有轨道抛离出来的读书人只能另寻出路。其中一部分鲁迅所谓的“才子”,恰逢清末民初报刊业繁荣发展的大好时机,这些报刊就成为他们展露才华的舞台,他们也因此为自己的才学找到了用武之地。
但是,很久以来,新文学界总是以改造社会、反抗现实为理由,谴责这些以休闲、娱乐、消愁、解闷为宗旨的读物,“给人们的情感导向是庸人的消遣、生意经的媚俗和迷惘的感伤”,指控他们的趣味和追求,“是置于买笑、觅醉、顾曲的替代品的平庸的世俗文化和精神层面的”。有意思的是,在新文学界对他们的讨伐中,《礼拜六》一直首当其冲,并被冠以“派”的雅号。直到20世纪70年代,陈蝶衣在香港撰文,还称“对于‘礼拜六派’的鞭尸工作,多年来其实并没有终止”。或是因为它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刊物。它曾在1916年4月出满一百期后停刊,五年后,到了1921年3月复刊,出满第二个一百期后,于1923年2月再度停刊。在这期间,张恨水确实如他自己所言,没有和礼拜六派发生过文字上的往来,也没有作过礼拜六派的文章,但他认为,像他这种亦新亦旧,既向往革命又崇拜才子的“两重人格”,正是民国初年礼拜六派文人的典型人格,所以,后来有人说他是礼拜六派文人,他也并不觉得十分冤枉,因为那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
这也许可以看作是张恨水的人格底色。以他所受教育而言,固然属于旧学的范畴,但又处在一个新旧转型的时代。他是在传统文化的染缸里浸泡过的,有很深的传统文化素养,然而他并不拒绝近现代以来所发生的新文化,他也曾受到新文化的某些影响。不过,他骨子里还是传统文人,而且是他从小就崇拜的才子型文人,有时也被称作旧文人。鲁迅对此曾有个说法,他把那时的文人,分为两种,即“君子和才子”。这两种人各有自己的特点,“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做八股,非常规矩的。而才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还要做考试上用不着的古今体诗之类”。不知鲁迅把自己归入哪一类,也许哪一类都不是,因为他毕竟属于新文化中的一员,是知识阶级的一分子。不过,就文人而言,绝非像他说的那样简单。文人最初称士,秦汉以后,有了做官的机会,成为官僚,遂称士大夫。但是,又不甘心做皇帝的雇工或食客(帮忙或帮闲),还有做帝师的一点野心。他们固然不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但他们要用自己的知识,即道统来规范、驾驭或影响实际的政治权力,也就是皇权、政统,孔夫子的万世师表就是这么来的。所以,那个时候的读书人——文人、儒生,要做的事一定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古人已有“经天纬地谓之文”的说法,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有经天纬地之才、之德的人,才有资格称作文人。说到底,文人骨子里都有那么一点忧国忧民、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或者叫情怀。他们以经营天下为己任,关心社会现实,人间冷暖,表现出积极的入世精神,人们常说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都是这种文人情怀的形象写照。尤其是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们的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就表现得更加突出。
士要介入最高政治权力只有两条道,一是天,一是孝。事实上,这两条道都未能走通。董仲舒抬出天来压制皇权,只是消解了皇权的绝对性,给改朝换代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并不能使道统居于政统之上,为此,他甚至付出了几乎被杀头的代价,最后以教书先生终了此生;孝是强调伦理秩序,要约束皇权,除了敬天,还有法祖,对皇帝来说,孝就是法祖。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要开懋勤殿,目的是想打破原有的权力格局,只能把祖宗抬出来做依据;而慈禧政变,拘禁光绪,也打着祖制家法的旗号。可见,法祖也未必就能被道统用来约束或防止皇权的滥用。在宋代,士阶层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要在政治上表现出主动性的自觉,神往于皇帝与士大夫“共定国是”,而且找到了以往“士贱君肆”的根本原因,“正以在下者急于爵禄,而上之人持此以为真足以骄天下之士故也”。就是这位张栻,曾说出千古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一个士人的最高理想,今日读之,犹有泰山岩岩,壁立万仞之气象。宋之后,元、明、清之士人,已不复此想。
士是知识的拥有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知识,因此敢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也说明了一个现象,士的知识如果不能用于治理国家,就只能闲置,等待时机,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知识的单一性给士人造成的困境,所以,唐宋以前多隐者,他们除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没有别的事可做。那些玩世或出世的,看上去与世无争,其实往往是由于对君的失望和恐惧,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采取的逃避策略。宋代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市井文化的繁荣,刺激了都市文化消费的膨胀,事实上也为士人开辟了一条实现自身价值的新路,而不必拥挤在求仕(求隐只是求仕的另一种方式)这一条道上。皇帝要柳永“且去填词”,未必不是放他一条生路。这种情形到晚明就更加普遍了,才子型的士人从传统士人,即士大夫中分离出来,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隐者,尽管他们也崇尚陶渊明;他们的知识除了卖给帝王家——如果帝王家想买的话,也可以拿到文化市场上去销售。而清末民初,由于整个知识阶层都成了一定意义上的“自由人”,都要重新确定自身的位置,于是,一些有政治情怀,立志要治国平天下的人,也许就走上了职业革命家或政治家的道路,一些有学术理想的人就走进了书斋,成为学者,还有一些士人,既有才学,又有情趣,人很善良,又很敏感,就可能选择去当作家,当然是与旧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作家。
然而,无论是在旧文化,还是在新文化的评价体系中,这种才子型文人的身份都显得有点暧昧和尴尬。瞿秋白曾引顾炎武的话,“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来说明他这个人作为“文人”的无所用之;清代诗人黄景仁(字仲则)也曾说过“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话,把文人看作无用的废物。他们所指,大约就是这种才子型文人。但这种评价体系对这些文人的看法显然是带有偏见而极不公正的。他们自然不是传统意义上追求“内圣外王”、经世致用的文人士大夫,严格来说,他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知识分子。但他们仍是中国文化传统养育的文人,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感知世界的方式,基本上还是在传统文化的范畴之内,他的文人情怀和气质秉赋,则主要表现为他的善良、仁慈、平和、忠厚、耐劳、雅致,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以及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对权势和丑恶的社会现实的不满。他们是很讲究生活趣味的,有时还表现得有一点清高。在20世纪中国以启蒙、革命和追求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并不像新文化人或左翼文人那样,热烈拥抱新时代的到来,而是心平气和、心静如水地走在既定的轨道上。他们不热衷于政治,也很少参加任何党派,并不以党派之见作为评判事物的准则。但他们对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并非没有感受,没有认识。他们也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对民众生存现状的改善有一种期待,甚至表现出深深的忧患意识,但他们很少想到为了改变现状自己身负怎样的历史使命,更不会参与现实中的革命运动。他们可以为人间的不平而奋笔疾书,为人生的艰辛和苦难抛洒同情之泪,写下一行行感情饱满的文字,但他们不会与激进主义同行,而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落落寡合地固守着旧有的文化传统与道德伦常。他们的作品仍然表现出与卖文为生的旧式文人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他们对现实生活中种种丑陋现象的揭露、讽刺、鞭笞和批判,也折射出一个传统文人出于道义良知的精神风骨。
不管这种才子型文人在别人眼里是怎样的一些人,对于正处在“志于学”年纪的张恨水来说,他们的才情却是他所向往的。他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成为像他们那样能写书的才子,尽管他现在还只是才子的胚子,但大的环境已经为他准备了胚子生长所需的土壤、阳光和水,也许未来还有许多难以预料的事情会发生,但一株幼苗的破土而出,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