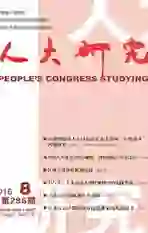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机制重构与程序设计
2016-09-14辛一科
辛一科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经典《孟子·离娄章句上》有言:“徒法不足以自行。”时空流转不能阻碍思想的互通。无独有偶,成名于20世纪的著名法学家、社会学家罗斯科·庞德在其名著《社会学和法学的范围》一书中同样提出“法律的生命在于其实施”。面对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周年重要讲话”中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宪法作为法律的最高形态,同普通法律一样也面临着如何适用、如何更好地适用的问题。但目前我国宪法解释机制和解释程序层面已难以回应宪法解释实践的需要,更遑论与宪法学研究保持应有的理论契合。以上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我国宪法适用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一、当前我国宪法面临的主要挑战
自我国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以来,经过四次局部修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适应时代发展步伐。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与尚待完善、制定的宪法解释机制与程序在应对社会多元利益失衡、私权利与公权力冲突、行政合法性与宪法信仰危机等社会问题时,并非通过宪法修正案单一方式即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一)社会多元利益失衡
自改革开放后,因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与世界各国交流互通的不断深化,多元利益主体主导下的价值追求呈现多元化趋向。我国尚需进一步完善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与受到重大冲击的本国文化等客观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价值诉求“单级结构”向“多级结构”的转变。正因如此,才出现了诸多重大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等社会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上述现象是我国多元利益失衡的外在表征。“行政法调整方法是以当事人不平等为前提,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的意志加于另一方当事人,使另一方当事人的意志服从自己的意志。”[1]因不合时宜的传统行政法理念表现出的行政权“乏力”的窘境已经显现。行政法理念的更新、具体原则、规范的制定均难以脱离宪法解释。随着时代发展,如何使宪法解释适应社会治理的客观需求,并且以宪法解释理论与实践回应行政治理的当代命题,以平衡多元利益诉求等目标将是摆在我们法学研究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二)私权利与公权力冲突
各国宪法对私权利的保护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已然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的共识。例如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第十七条规定: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我国现行宪法也沿用不受侵犯的法律条文表述模式,其中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分别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等公民基本权利。诚然,公民上述基本权利受宪法限制,无论是事实论意义上的限制,抑或是规范意义上的限制,首先,由于事实论意义上的宪法限制条件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主观性,在实务中难以产生足够说服力,这就为解释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带来巨大挑战。其次,在规范意义层面由于宪法规范的原则性、高度概括性特点,在一定程度增加了解释难度。例如,现行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在现实社会生活形态如此多元的今天,对上述条文的解释就存在多种可能性。例如,什么是“住宅”?“宾馆”属“住宅”吗?学生宿舍属“住宅”吗?如何理解“侵犯”?等等。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解释会造成公民私权利与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冲突。如果尚不能很好地寻得一条科学合理的宪法解释机制与程序路径,加之行政管理的复杂性、繁杂性造成管理难度日益增加,行政自由裁量权日渐扩大的今天,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利冲突的局面必会日渐强化。
(三)行政合法性危机
宪法规定了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在“依法行政”的法治构想下行使宪法赋予的行政职权。可以说,宪法赋予了行政机关行政行为正当性与合法性。在现有“代议制”政治体制之下,人大代表成为表达民意、反映民愿的重要途径。但现实情况是,一方面,作为宪法具体化的行政法,由于宪法解释力的缺失,使得行政法律法规的解释缺乏应有的原则性规范,从而扩大了行政机关在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等行政法律法规的解释张力;另一方面,在缺少宪法解释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打着“为人民服务”“为民众谋福祉”“公共利益”的旗号,恣意解释行政法律法规(包括所谓的“红头文件”),公民私权利与国家公权力关系一度紧张无序,由此造成“政府官员严重的、结构性腐败现象,都使得政府的行政活动合法性受到人民的普遍怀疑”[2]。由于对政府不信任,行政相对方为了维护自身合法利益放弃正当、合法途径而代之以采用群体性、极端化的方式宣泄不满,寄希望于“捅破窗户纸”以引发社会关注,面对激烈的抗争方式行政权合法性危机与政府形象的贬损程度日趋严重,而行政机关在应对上述情况之时更加力不从心、捉襟见肘。
(四)宪法信仰危机
法律的威慑力来源于其规范力,宪法同样如是。宪法作为一国根本大法,其规范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宪法是组织规范。我国现行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绳。”上述规定“明示了宪法作为根本法规范和最高法规范的旨趣”[3]。另一方面,宪法还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规范,我国现行宪法以24条的较大篇幅涵盖了绝大部分的权利规范。24条权利规范构成了我国宪法的核心内容,具有根本性、原旨性。总体而论,不论是组织规范还是权利规范在法规范的逻辑构成层面很大程度上包含着“法效果”,即宪法强制力。有些规范关于法效果的表述较为明显,如“国家应该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法效果是“应予保障”或“有义务保障”。此外,有的宪法规范法效果不甚明显,但可通过表述转换和条文解释揭示其应有的法效果或者通过行政法等部门法的规定,以进一步明确宪法规范法效果。但现实情况是,由于解释理论的匮乏和解释实践的缺失,丧失了宪法应有的规范力,造成人们普遍认为宪法就是“闲法”,是“纸老虎”。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形成“风险社会”的可能性在增加,如果不能树立对宪法的信仰,实现宪法与其他部门法的有效衔接以更好地抵御潜在风险,代价必然是牺牲社会秩序。
二、目前我国宪法解释的机制与程序
西语“宪法”一词源自拉丁文Constitution,法语la Constitution与德语Verfassung。从词源学观之,“宪法”一词的“基本含义是组织、结构、确立、批准、整理、体制安排、命令、指示、设置等”[4]。但从学理角度讲,Constitution含“宪制”之意蕴,“机制”与“程序”即是“宪制”的两项基本要素。所谓“机制”是指行使权力的机关组织体系,涉及权力的建构方式、模式、体系等;“程序”则是指如何行使宪法所授之权,涉及行使权力的方式、过程、手段等。
(一)宪法解释机制
1.宪法与法律解释统一体制。我国现行宪法第六十七条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具有解释宪法和法律的权利。首先,依据“‘明示其一,排斥其他的法律解释规则”[5],全国人大常委会独享宪法解释权且具有最终解释效力。其次,根据本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宪法解释权之外还拥有普通法律解释权。但不可因同一解释主体而忽略了宪法解释与普通法律解释之间的差异,不论从宪法的制定与修改主体还是从法的效力等层面讲,宪法解释程序都应当与普通法律解释程序迥然相异。从1982年对宪法进行全面修改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未针对具体个案以宪法名义作出过有权解释,代之以普通法律解释吸纳宪法解释的方式,使得宪法解释在宪政中难以充分彰显。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宪法解释在解释体制和程序方面的不完善。
2.宪法解释与宪法监督混合体制。早在1954年我国宪法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第三十一条第六、七项规定了全国人大享有宪法监督权。现行宪法第六十七条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这一宪法规范实际上表明了两层含义:其一,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之权;其二,宪法同样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监督之权。从宪法监督制度演进过程可以看出,宪法监督权的行使主体由全国人大逐渐演变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文义解释视角观之,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是为了凸显宪法解释对宪法监督的作用和彰显解释与监督的一致性而作出的制度性安排。但就宪法解释的出发点而论在个案适用之时需将原则性、概括性的宪法规范予以一定的具体化、明确化,因此就宪法解释的特征而言,其必然是规范性、被动性、中立性、适应性的有效集合。因此,宪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宪法“活起来”的必然手段,是实现宪法续造的重要环节。宪法监督则不同,在遵循法定程序的前提下以“合宪性推定”方式监督宪法贯彻实施状况的一种宪法实施制度,其具有“刹车阀”与一部分司法功能。因此,从功能上讲宪法监督与宪法解释是截然相反的两个宪政制度,将两者统摄于同一宪法规范中显失科学性、规范性。
3.多重解释程序与目标的混合体制。从世界各国解释模式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往往强调个案与法律之间的高度契合以突出解释个案效力。在维护法制统一层面,司法解释者可依据宪法精神、原则和规则认定行为人的行为(作为与不作为)违反下位法或者下位法不适用该案件。域外国家坚持议会至上理念,法解释者是以宪法的抽象解释为前提。与域外国家解释体制不同的是,尽管我国无宪法解释文本规范,但可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发现我国宪法解释提请程序坚持提案制。换言之,欲启动宪法解释程序须经相关提案机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解释议案申请方可进入宪法解释程序。从这一规定可发现我国宪法解释机关与提案判断机关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面行使解释与是否接受宪法解释提案的双重职权。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第十二条的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委会提出属于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通过分析就会发现,不同的解释提请机关会产生截然相异的解释程序和动力。首先,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国务院在提请宪法解释之时会出于经济社会变迁的需要,在宪法层面寻求施政的合理性。国务院会更多的将管理国家科教文卫事业相关的行政权力行使宪法解释问题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宪法解释案的效力也随之导向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在这种情形下国务院提请宪法解释的目标是引起适当的宪法变迁,以便更好地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寻求合法性依据。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宪法解释导向行政法规、地方性规章、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抽象解释的程序与功能,势必会造成行政权与宪法解释权合二为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国务院的职权,弱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独立判断与解释的可能性,造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权与解释权威的克减。其次,作为最高审判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检察机关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我国最高司法解释机关,“两高”在解决个案时必然会将解释诉求导向宪法解释层面,致使司法权与宪法解释权合二为一。同样,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作出宪法解释与否、如何解释等重大决策之时同样受“两高”影响,从而也会影响解释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再次,就专门委员会而言,出于其维护宪法权威、法制统一与专门监督的权责,其必然以“法秩序”维护者的面目示人。恰恰由于专门委员会高度专业化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我国立法,致使立法权与宪法解释之权合二为一。最后,由于多元解释提请机关和相异解释诉求的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目标模式也会呈现出多元化特色:形成性的解释目标与防御性的解释目标[6]。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宪法解释奉行解释的程序与目标、抽象解释与具体解释、形成性解释与防御性解释的多重混合体制。
(二)宪法解释程序
由于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以下亟待完善之处。
1.宪法解释程序规范的缺失。不论我国采用何种宪法解释体制,宪法解释主体、内容、原则、方式、步骤、时限等基本问题都需明确。操作性强弱程度是宪法能否焕发生命活力的前提和条件。我国现行宪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具有高度的原则性、概括性,难以形成具有操作性的程序规范。在具体宪法解释实践中宪法解释主体很难将国家意志转化为法律规范,从而致使该条规定尚停留在纸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