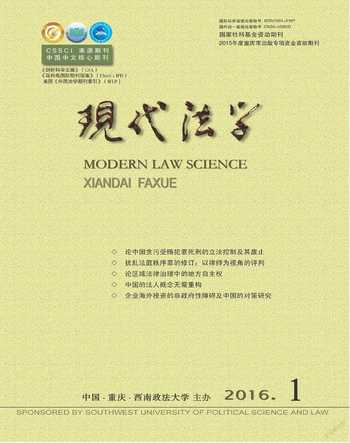论《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恐怖犯罪的规定
2016-09-10张明楷
摘要:《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恐怖犯罪的规定,在总体上具有法益保护早期化、处罚范围扩大化与处罚程度严厉化的特点。从构成要件的角度来说,则存在帮助犯的正犯化、预备犯的既遂化与构成要件的交叉化三个特点。帮助犯的正犯化与对帮助犯单纯设置量刑规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规定;《刑法修正案(九)》所增加的第120条之一第2款以及被修正的第1款,对帮助犯实行了正犯化;对于实施上述两款行为的,应当作为正犯处理;教唆、帮助他人实施该两款行为的,应认定为两款犯罪的教唆犯与帮助犯。《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第120条之二第1款,对预备犯实行了既遂化(独立预备罪);该款规定的行为属于实行行为,而不再是预备行为;教唆、帮助他人实施本款规定行为的,成立准备恐怖活动罪的教唆犯、帮助犯;为他人实施恐怖活动进行准备的行为,也可能成立准备恐怖活动罪;按独立预备罪论处导致处罚程度轻于从属预备罪时,应按从属预备罪论处。《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恐怖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存在大量交叉现象,但不能将这种交叉关系解释为法条竞合,而应认定为想象竞合,从而发挥想象竞合的明示机能,实现预防恐怖犯罪的目的。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九)》;恐怖犯罪;帮助犯的正犯化;预备犯的既遂化;构成要件的交叉化
中图分类号:
DF62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6.01.03
《刑法修正案(九)》第5条至第7条是关于恐怖犯罪的规定,其中不仅修改了《刑法》第120条与第120条之一,而且在《刑法》第120条之一后增设了5个条文。
总的来说,《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恐怖犯罪的修改内容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一般来说,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主要表现为增加危险犯(尤其是抽象危险犯)、预备罪的规定,使刑法对危险犯、预备罪的处罚由例外变成常态。《刑法修正案(九)》对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主要表现为,在恐怖组织或者相关人员的行为仅对公共安全产生抽象危险时,就作为犯罪处理。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第120条之六规定:“明知是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而非法持有,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的物品的行为,对公共安全仅具有抽象危险,而没有产生具体危险与实害,将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是法益保护早期化的典型表现。第二是处罚范围的扩大化。处罚范围的扩大化与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不是等同含义,但又有密切联系。虽然法益保护的早期化意味着处罚范围的扩大化,但处罚范围的扩大化并不意味着法益保护的早期化。至为明显的是,刑法增设某种实害犯时,虽然是处罚范围的扩大化但不是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第120条之四将“利用极端主义煽动、胁迫群众破坏国家法律确立的婚姻、司法、教育、社会管理等制度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这一行为实际上是实害犯(至少是具体危险犯)。《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其他恐怖犯罪,都可谓处罚范围的扩大化。第三是处罚程度的严厉化。处罚程度的严厉化主要表现在,对新增设的犯罪,不管是实害犯还是危险犯,都规定了较重的法定刑。另一方面,对帮助犯与预备犯直接规定法定刑,也导致处罚更为严厉。因为按照刑法总则的规定,帮助犯与预备犯都可能减轻处罚乃至免除处罚,但《刑法修正案(九)》对帮助犯与预备犯直接规定法定刑后,使得部分恐怖犯罪的帮助行为与预备行为不可能被免除处罚。此外,《刑法修正案(九)》还扩大了财产刑的适用。例如,《刑法》第120条对组织、领导、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行为仅规定了主刑,而没有规定附加刑,对其他参加者在规定主刑的同时,仅规定了可以单处剥夺政治权利。《刑法修正案(九)》则对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增加了没收财产与罚金的附加刑,并对新增加的恐怖犯罪都规定了财产刑。这是因为,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的恐怖活动往往需要大量资金,增加财产刑有利于预防恐怖犯罪分子再次犯罪。
从构成要件层面来说,《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恐怖犯罪的规定,有三个值得研究的立法现象(特点):一是帮助犯的正犯化,二是预备罪的既遂化,三是构成要件的交叉化。前两个立法现象不仅直接加重了帮助恐怖活动、准备恐怖活动行为的处罚,而且间接扩大了恐怖犯罪的处罚范围;后一个立法现象涉及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分。
本文拟对帮助犯的正犯化、预备罪的既遂化与构成要件行为的交叉化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因为这三个问题并不限于恐怖犯罪,而是涉及刑法分则规定的其他犯罪。研究这三个问题,不仅有利于对恐怖犯罪的定罪量刑,而且有助于解决其他犯罪的相关问题。
一、帮助犯的正犯化
刑法典一般在总则中规定共犯(教唆犯与帮助犯),分则所规定的构成要件行为通常是正犯行为,对于教唆、帮助正犯的行为则适用总则的规定,以共犯论处。所谓帮助犯的正犯化,则是指刑法分则条文直接将某种帮助行为规定为正犯行为,并且设置独立的法定刑。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分则条文对帮助犯设置了独立法定刑,就是帮助犯的正犯化。总的来说,分则条文对帮助犯设置独立法定刑时,存在两种情形:一是帮助犯的正犯化;二是单纯的量刑规则
关于量刑规则的含义,参见:张明楷.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J].清华法学,2011(1).。在后一种情形下,分则条文并没有将帮助犯提升为正犯,帮助犯依然是帮助犯,只是因为分则条文对其规定了独立的法定刑,而不再适用刑法总则关于帮助犯(从犯)的处罚规定。
首先,帮助犯被正犯化后,不再按照刑法总则规定的从犯处理,因而不得适用《刑法》第27条关于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而必须直接按分则条文规定的法定刑处罚,这便没有免除处罚的可能性
当然另具有免除处罚情节的除外,但该“帮助”行为本身不可能成为免除处罚的情节。。同样,对帮助犯单纯设置量刑规则后,也是直接适用分则规定的法定刑,而不再适用总则关于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就此而言,区分帮助犯的正犯化与单纯对帮助犯设置量刑规则没有实际意义。
其次,帮助犯被正犯化后,不再以正犯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为前提。众所周知,根据共犯从属性说的原理以及作为通说的限制从属性说,只有当正犯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时,才能将教唆犯、帮助犯作为共犯处罚
当然,由于我国刑法处罚预备犯,所以,在正犯实施了预备行为时,教唆者、帮助者也可能成立预备犯。这一结论同样符合共犯从属性说的原理。。例如,甲认识到乙将要杀害丙,而将丙的行踪提供给乙。然而,乙并没有实施杀害丙的任何行为。根据共犯从属性说的原理,对甲不能以帮助犯论处。但是,在帮助行为被正犯化之后,就不需要以其他正犯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为前提。这并不意味着帮助犯的正犯化采取了共犯独立性说,而是原本的帮助行为已经被提升为正犯行为,故不需要存在另外的正犯即可成立犯罪(而且成立的是正犯)。但是,倘若对帮助犯设置独立的法定刑只是一种量刑规则,那么,该帮助犯的成立仍然应以正犯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为前提。显然,就此而言,必须区分帮助犯的正犯化与帮助犯的量刑规则。
最后,帮助犯被正犯化后,由于原本的帮助行为提升为正犯行为,于是对该正犯行为的教唆、帮助行为又能成立共犯(教唆犯与帮助犯)。众所周知,教唆犯是指唆使他人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教唆他人实施帮助行为的,并不是按教唆犯处罚,而是按帮助犯处理
参见: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M].东京:成文堂,201:440;山中敬一.刑法总论[M].东京:成文堂,2008:899.例如,A得知B要杀害甲,于是教唆C将杀人凶器提供给B,B使用该凶器杀害了甲。A并没有唆使他人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只是唆使他人实施帮助行为,故只能认定为帮助犯。;帮助犯是指帮助正犯者
例如,日本《刑法》第62条第1项规定:“帮助正犯的,是从犯。”其中的从犯就是指帮助犯。,所以,单纯对帮助犯进行帮助,而没有对正犯起帮助作用的,并不成立帮助犯,因而不得处罚
国外刑法理论对此存在争议。例如,日本《刑法》第61条规定,教唆教唆犯的(即间接教唆)按教唆犯处罚,但没有规定对帮助帮助犯的(即间接帮助)按帮助犯处罚。于是,对帮助帮助犯的能否处罚,就存在争议。肯定说与否定说可谓势均力敌。持肯定说的有平野龙一、前田雅英、山中敬一、山口厚等教授;持否定说的有团藤重光、福田平、大塚仁、西原春夫、川端博等教授。肯定说的理由是,帮助犯的处罚根据在于使正犯行为更为容易,因此,使正犯行为更为容易的间接帮助,也成立帮助犯。否定说则认为,刑法没有规定处罚间接帮助,如果帮助行为使正犯行为更为容易,就要认定为对正犯的帮助,而非认定为对帮助犯的帮助。(参见: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M].4版.东京:
成文堂,2012:447-448.)但在本文看来,肯定说与否定说所争议的并不是对帮助犯进行帮助的行为能否成立帮助犯,而是对帮助犯的帮助是否均能对正犯起帮助作用。。但是,一旦对帮助犯实行正犯化,就意味着原本的帮助行为成为刑法分则规定的正犯行为,故教唆他人实施该正犯行为的,就成立对正犯的教唆犯(而非帮助犯),帮助他人实施该正犯行为的,也会成立对正犯的帮助犯(而非不处罚)。但是,对帮助犯规定单纯的量刑规则时,帮助犯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所以对帮助犯的教唆依然仅成立帮助犯,单纯对帮助犯的帮助,就不成立帮助犯。就此而言,帮助犯的正犯化与帮助犯的量刑规则的区分,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例如,《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刑法》第120条之一,所增加的第2款规定:“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倘若认为本款规定属于帮助犯的正犯化,那么,首先,对于实施本款行为的人不得依照《刑法》总则第27条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只能直接按照第120条之一第1款的法定刑处罚。其次,招募、运送行为本身就是正犯行为,不以他人(正犯)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恐怖活动、恐怖活动培训为前提。最后,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上述招募、运送行为的,成立第120条之一第2款犯罪的教唆犯与帮助犯。但是,倘若认为本款规定只是对招募、运送这类帮助犯设置了量刑规则(适用独立的法定刑),那么,招募、运送行为本身仍然是帮助行为,其成立犯罪以正犯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恐怖活动、恐怖活动培训为前提;教唆他人实施招募、运送行为的,就不成立教唆犯,仅成立帮助犯;单纯帮助他人实施招募、运送行为,而没有对正犯行为起作用的,就不受处罚。
显然,对帮助犯的正犯化与帮助犯的量刑规则不可能进行法律形式上的判断(因为二者的法律标志完全相同,都是规定了独立的法定刑),只能进行实质判断。在进行实质判断时,要根据共犯从属性的原理、相关犯罪的保护法益,以及相关行为是否侵犯法益及其侵犯程度得出合理结论。
例如,《刑法》第244条第1款规定了强迫劳动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第2款规定:“明知他人实施前款行为,为其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强迫他人劳动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要区分本款规定是帮助犯的正犯化,还是对帮助犯的量刑规则,必须进行如下实质判断。
首先要判断的是,在A明知B将要或者正在强迫他人劳动,便采取发微信的方式为B招募人员到B的工场,B接收A所招募的人员并强迫他们参加劳动时,A的行为是否侵犯了法益以及侵犯法益的程度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强迫劳动罪的保护法益是公民是否参加劳动的权利或者公民是否参加劳动的意志决定自由。不言而喻,由于B的行为直接造成了侵害他人人身权利的结果,而A的行为与该结果之间具有物理的因果性,所以,对A的行为应以犯罪论处。
其次要判断的是,在甲明知乙将要或者正在实施强迫他人劳动的行为,便采取发微信的方式为乙招募人员到乙的工场,但乙并没有接收甲所招募的人员,或者虽然接收了甲招募的人员,但根本没有强迫他们参加劳动时,甲的行为是否侵犯了法益以及侵犯法益的程度如何?显而易见,在上述情况下,乙对甲所招募的人员的行为既缺乏强迫劳动罪的构成要件符合性,也缺乏违法性即没有侵犯甲所招募的人员是否参加劳动的权利。甲的行为既没有作为正犯直接侵犯他人是否参加劳动的权利,也没有作为共犯间接侵犯他人是否参加劳动的权利。既然如此,对甲的行为就不应以强迫劳动罪论处。
不难看出,《刑法》第244条第2款虽然对强迫劳动的帮助行为规定了独立的法定刑,但该帮助行为成立犯罪以正犯实施了符合强迫劳动罪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为前提,故该款规定并不是帮助犯的正犯化,只是单纯的量刑规则而已。
再如,《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第284条之一第1款规定了组织考试作弊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第2款规定:“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那么,倘若甲为乙组织考试作弊提供了作弊器材,但乙没有实施组织考试作弊罪的任何行为时,对甲应如何处理?由于甲的行为既没有直接也没有间接侵犯任何法益,故对甲的行为也不可能以犯罪论处。所以,《刑法》第284条之一第2款的规定也属于量刑规则。
那么,《刑法修正案(九)》所增加的第120条之一第2款的规定,是帮助犯的正犯化还是帮助犯的量刑规则呢?可以肯定的是,第2款规定的“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并非限于为本人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
倘若为了本人实施恐怖活动招募、运送人员,则同时属于预备犯的既遂化。,而是包括为他人组织、领导的恐怖活动组织以及他人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那么,在后一种情形下,如何判断招募、运送人员行为的可罚性呢?
可以肯定的是,当A招募、运送的人员已经成为恐怖活动组织成员,或者正在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正在接受恐怖活动培训时,就意味着正犯已经实施了符合相关恐怖犯罪的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而且A的行为与正犯结果之间具有物理的因果性,A的行为具备可罚性。但对此得出肯定结论,还不意味着第120条之一第2款对帮助行为实行了正犯化。需要讨论的是,甲明知乙要组建恐怖活动组织、组织他人实施恐怖活动或者组织他人进行恐怖活动培训时,为乙招募、运送了人员,乙接收了甲所招募、运送的人员,但还没有着手实施相关恐怖活动、培训活动时,即作为真正正犯的乙还没有着手实施符合恐怖犯罪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时,甲的行为是否侵犯了法益以及侵犯程度如何?对此,可以联系相关法条规定的犯罪进行判断。
根据《刑法》第120条的规定,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本身就是正犯行为。这种行为对公共安全虽然只有抽象的危险,但由于恐怖活动组织实施的犯罪具有极大的法益侵害性,恐怖活动组织本身具有实施恐怖犯罪的极大危险性,一般预防与特别预防的必要性大,所以,将这种抽象的危险行为规定为犯罪具有正当性。当今各国刑法也都对恐怖组织及其活动采取严厉打击的态度,因而针对恐怖犯罪设置了大量的抽象危险犯。既然上述甲招募、运送的人员被恐怖组织或者人员接收,就表明甲的行为增加了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犯罪的危险性,当然应当作为犯罪处理。换言之,“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的行为对公共安全法益的侵犯程度,并不一定轻于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行为。因此,将这种行为作为正犯处理即承认帮助犯的正犯化,能够使法条之间保持协调关系。
一般来说,在甲与恐怖犯罪分子乙具有通谋的情况下,乙通常都会接收甲所招募、运送的人员。如果乙接收了甲所招募的人员,使恐怖组织成员增加,即使乙还没有组织他们实施恐怖活动,对甲也应适用第120条之一的规定定罪量刑。问题是,在甲与恐怖犯罪分子乙没有通谋的情况下,甲为乙实施恐怖活动招募、运送人员,但乙没有接收的,应当如何处理?在本文看来,由于乙的行为产生了扩大恐怖组织及其恐怖活动的危险,对此完全有可能认定为未遂犯,因而能够肯定《刑法》第120条之一第2款的规定属于帮助犯的正犯化。倘若A误以为他人会实施恐怖活动而为他人招募、运送人员,但他人根本不实施恐怖活动的,可以认为A的行为属于不能犯,故不应以犯罪论处。显然,即使对A的这种行为不以犯罪论处,也只是因为该行为没有侵害法益的抽象危险,因而不能否认《刑法》第120条之一第2款的规定属于帮助犯的正犯化。
接下来还需要考虑的是,教唆、帮助他人实施招募、运送行为的,应否作为教唆犯、帮助犯处罚?答案也是肯定的。因为根据《刑法修正案(九)》所增加的第120条之二、之三与之五的规定,积极参加恐怖培训活动的,宣扬恐怖主义或者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以及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服饰、标志的行为就成立犯罪,既然如此,教唆、帮助特定他人为恐怖犯罪活动招募、运送人员的行为,更值得科处刑罚。
由上可见,《刑法修正案(九)》所增加的第120条之一第2款,对帮助犯实行了正犯化。因此,对于实施本款行为的,应当作为正犯处理,教唆、帮助他人实施本款行为的,应认定为本款行为的教唆犯与帮助犯。基于同样的理由,《刑法》第120条之一第1款的规定,基本上也是帮助犯的正犯化
称“基本上”是因为可能存在例外。亦即,事后资助行为虽然不成立帮助犯,但也可能成立《刑法》第120条之一规定的犯罪。。
顺便指出的是,由于帮助犯是对正犯的帮助,单纯对帮助行为进行帮助的不成立帮助犯,故应区分某种行为是对正犯的帮助还是对帮助的帮助。本文的看法是,只要帮助行为与正犯结果具有因果性(即使正犯没有意识到这种帮助行为),就应认定为对正犯的帮助,因而成立帮助犯。例如,乙得知丙进行恐怖活动培训,便为丙招募人员,甲知道乙的行为真相,为乙招募人员出主意,使乙招募到大量人员并接受了恐怖活动培训。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是甲帮助了乙,实际上甲的行为与丙的正犯结果之间具有物理的因果性。因此,甲实际上是对丙的帮助,因而直接成立《刑法》第120条之一第2款的正犯,而不是成立该款的帮助犯。
二、预备犯的既遂化
一般来说,刑法将准备行为作为基本犯罪构成要件行为(实行行为)之前的行为予以规定的情形,就属于从属预备罪;刑法将准备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类型时,就属于独立预备罪。
在我国,从属预备罪不是由分则规定,而是由总则规定。《刑法》第22条第1款与第2款分别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当行为人为了实行分则的具体犯罪而实施预备行为,因而成立犯罪预备时,不仅要引用分则条文的规定,适用分则所规定的法定刑,而且要适用总则第22条的规定。
独立预备罪的行为则由分则条文具体描述为构成要件行为。由于刑法分则一般规定的是实行行为,而且以既遂为模式,所以,独立预备罪的设立可谓预备犯的既遂化,或者称为预备行为的实行行为化。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第120条之二第1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为实施恐怖活动准备凶器、危险物品或者其他工具的;(二)组织恐怖活动培训或者积极参加恐怖活动培训的;(三)为实施恐怖活动与境外恐怖活动组织或者人员联络的;(四)为实施恐怖活动进行策划或者其他准备的。本款所规定的行为原本是恐怖活动的预备行为,但该款将其规定为独立的犯罪(准备恐怖活动罪),使之成为既遂犯罪,不再适用刑法总则关于预备犯的处罚规定。
关于独立预备罪,有以下几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第一,独立预备罪是否存在实行行为?
德国刑法理论不使用实行行为的概念,日本刑法理论对预备罪是否存在实行行为一直存在争议。否定说认为,预备行为是无定型、无限定的行为,是实行行为之前的行为,因此,不管是从属预备罪还是独立预备罪,都不具有作为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的特点。肯定说认为,从属预备罪与独立预备罪均存在固有的构成要件,因而均有实行行为。折中说认为,独立预备罪中存在实行行为,从属预备罪中不存在实行行为。
本文原则上赞成折中说,认为刑法所规定的从属预备罪的行为不属于实行行为,独立预备罪的行为则是实行行为。首先,如果认为从属预备罪的行为是实行行为,会导致实行行为概念的混乱。日本刑法将从属预备罪规定在分则中,因而有可能认为从属预备罪也有实行行为;与之不同的是,我国刑法将从属预备罪规定在总则中。因此,在我国,既能够以预备罪是由总则规定还是由分则规定来区分从属预备罪与独立预备罪,也可以原则上肯定总则规定的是预备行为,分则规定的是实行行为
但应注意的是,刑法规定的预备罪中的行为是否属于实行行为与实行行为能否成立预备罪,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倘若承认着手与实行行为的分离,主张实行行为可能存在于着手之前,那么,着手之前的所谓“实行行为”完全可能仅成立预备罪。例如,A为了杀害B,于2015年8月1日中午从甲地通过邮局将有毒食物寄给乙地的B,B于8月3日中午收到但没有打开邮件,8月6日中午B正要吃食物时发现异味而将有毒食物扔弃。关于着手的认定,形式的客观说会采取寄送主义,即A于8月1日中午寄送时就是杀人的着手。但这种观点明显使着手提前,为本文所不采。危险结果说既可能采取到达主义(8月3日中午为着手),也可能采取被利用者标准说(8月6日中午为着手)。应当认为,只有当B准备或者开始吃有毒食品时,才产生死亡的紧迫危险,故被利用者标准说是合适的。认定着手后,A寄送有毒食物的行为便理所当然成为杀人的实行行为。(参见:山中敬一.刑法总论[M].2版东京:成文堂,2008:714.)但是,倘若有毒食物还没有到达B手中时案发的,则由于没有着手而只能认定为杀人预备(参见:松原芳博.刑法总论[M].东京:
日本评论社,2013:297-302.),此时没有必要将寄送有毒食物的行为认定为杀人的实行行为。即使有人坚持认为寄送行为是实行行为,也只能认定为预备犯。。其次,从共犯从属性的原理出发,也不应当将从属预备罪的行为当作实行行为。例如,甲知道乙将要抢劫银行而为其准备凶器时,甲在什么情况下成立预备犯?如果认为甲本人实施了预备罪的实行行为,那么,即使乙没有实施任何行为,甲也成立预备罪。但本文难以赞成这种结论。因为按照共犯从属性说的原理,只有当乙至少实施了预备行为时(如携带凶器前往犯罪现场等),才能对甲以预备罪的帮助犯论处。倘若乙着手实行了抢劫行为,甲当然也成立帮助犯。所以,否认从属预备罪的行为是实行行为,可以贯彻共犯从属说的原理。最后,独立预备罪的行为,在分则条文得到了具体描述,并非无定型、无限定的行为,因而从形式上说完全具备实行行为的特点。从实质上说,刑法分则对极个别预备犯实行既遂化,就是因为该预备行为的抽象危险十分严重,值得作为既遂犯处理。所以,独立预备罪的行为也具备了实行行为的实质属性。基于上述理由,本文认为,《刑法》第120条之二第1款所规定的四项行为,均被提升为实行行为,而不能再作为预备行为处理。
第二,规定独立预备罪的分则条文没有描述的其他预备行为,能否适用刑法总则关于从属预备罪的规定?
就上述《刑法》第120条之二第1款而言,似乎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该款第4项规定了“其他准备”。不过,倘若认为第4项中的“其他准备”只是第4项的兜底规定,而不是本条第1款的兜底规定,依然存在上述问题。
从表述形式上看,“其他准备”似乎只是第4项的兜底规定。但是,倘若这样理解,那么,第120条之二第1款前三项的规定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相对于“为实施恐怖活动进行策划”而言,前三项的规定都属于“其他准备”。所以,只能认为,“其他准备”实际上是第120条之二第1款的兜底规定,故其他准备行为都能够包括在其中。亦即,对于“其他准备”行为必须直接适用《刑法》第120条之二第1款的规定,并直接根据该款规定的法定刑处罚,而不必适用刑法总则关于从属预备罪的规定。
但是,不排除以后的立法可能对独立预备罪不设置诸如“其他准备”的兜底规定,也不排除有人认为第120条之二第1款第4项的“其他准备”只是第4项的兜底规定,因而仅限于与为实施恐怖活动进行策划相当或者同类的准备行为。所以,关于独立预备罪的规定总会产生上述问题,因而需要研究。
本文看法是,倘若刑法分则规定独立预备罪是为了限制预备罪的处罚范围,那么,对于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预备行为就不应当适用刑法总则关于从属预备罪的规定。这是容易被人接受的结论。但是,倘若分则规定独立预备罪是为了扩大预备罪的处罚范围,并且加重对预备罪的处罚,那么,对于分则条文没有明文规定的其他准备行为,就必须适用刑法总则关于从属预备罪的规定。从《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例来看,在分则条文设置独立预备罪,不是为了限制预备罪的处罚范围,而是为了扩大预备罪的处罚范围,并且加重对预备罪的处罚。我国刑法总则虽然规定原则上处罚预备罪,但司法实践对预备罪的处罚极为有限。所以,《刑法》第120条之二第1款设置独立的准备恐怖活动罪,就是为了扩大对恐怖犯罪的处罚范围,而且使得恐怖犯罪的预备行为不可能免除处罚。所以,倘若认为某种恐怖犯罪的预备行为没有被第120条之二第1款所包含,仍可适用刑法总则关于从属预备罪的规定,判处轻于独立预备罪的刑罚。
第三,教唆、帮助他人实施独立预备罪的,应当如何处罚?
如前所述,教唆犯是指唆使他人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帮助犯是指帮助正犯者。那么,教唆、帮助他人实施独立预备罪的行为,是否成立教唆犯与帮助犯呢?例如,A唆使B积极参加恐怖活动培训的,是否成立准备恐怖活动罪的教唆犯?再如,在乙为实施恐怖活动而欲与境外恐怖活动人员联络时,甲将境外恐怖活动人员的联系方式提供给乙的,是否成立准备恐怖活动罪的帮助犯?本文对此持肯定意见。
首先,从形式上说,准备恐怖活动罪已经不再是刑法总则所规定的预备犯,它虽然在理论上被称为独立预备罪(这种称谓只是因为条文使用了“准备”或者“预备”的表述),但实际上已经被实行行为化或者既遂化。而且如前所述,准备恐怖活动罪的行为,已经不再是预备行为而是实行行为;实施了《刑法》第120条之二第1款规定的行为的,就不再按预备犯处罚,而是作为既遂犯处理。既然如此,上述A的行为便符合唆使他人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的条件,因而成立教唆犯;上述甲的行为则符合帮助正犯的条件,因而成立帮助犯。
其次,从实质上说,对《刑法》第120条之二第1款规定的准备恐怖活动罪实施的教唆或者帮助行为,与刑法分则其他条文规定的恐怖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相当,因而具有处罚的必要性。例如,《刑法》第120条之二第1款规定的准备恐怖活动罪包括“组织恐怖活动培训”的行为,而《刑法》第120条之一第1款明文将“资助恐怖活动培训”规定为犯罪行为,而资助行为是明显的帮助行为。这足以说明,准备恐怖活动罪的帮助行为,具有处罚的必要性。再如,《刑法》第120条之三将宣扬恐怖主义规定为犯罪,与之相比,教唆特定的他人实施准备恐怖活动罪的行为,也同样具备处罚根据。
第四,为了实行独立预备罪而实施的准备行为(可谓独立预备罪的预备行为),能否适用刑法总则第22条关于从属预备罪的规定?
《刑法》第22条将“为了犯罪”规定为预备罪的主观要件。预备罪中的“为了犯罪”显然是指“为了实行犯罪”。因为预备行为是为实行行为制造条件的,实施预备行为就是为了进一步实施实行行为。“为了犯罪”的字面意义包括为了预备犯罪与为了实行犯罪,但为预备行为实施的“准备”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预备。例如,为了实行杀人购买毒药的行为,可能是预备行为;但为了购买毒药而打工挣钱的行为,不是犯罪预备行为。可见,由于犯罪预备是犯罪,而为了实施犯罪预备行为所进行的“准备”又不是犯罪预备,故应将“为了犯罪”理解为“为了实行犯罪”。由于独立预备罪的行为已经被提升为实行行为,于是产生了另一问题:对独立预备罪之前的预备行为,能否按照《刑法》第22条的规定以预备犯论处?
从形式上说,既然独立预备罪的行为已经是实行行为,那么,为了实施独立预备罪而实施的准备行为,也符合从属预备罪的“为了实行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成立要件。但本文认为,对此还必须进行实质判断。换言之,虽然《刑法》第22条的规定似乎表明处罚所有的预备犯,但对第22条的解释以及对预备犯的认定,还必须以《刑法》第13条的“但书”为指导,不能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认定为预备犯。另一方面,独立预备罪实际上已经扩大了预备罪的处罚范围,如果一概将独立预备罪之前的准备行为认定为犯罪,必然导致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
所以,本文认为,对于为了实施《刑法》第120条之二规定的准备恐怖活动罪而实施的准备行为,只能通过实质判断认定其是否值得科处刑罚。例如,为了组织恐怖活动培训,已经联系了讲授人员与参加人员,或者准备了培训场所的,应按照《刑法》第22条的规定,以预备犯(从属预备罪)处罚。但是,为了准备危险物品而阅读相关书籍或者在网络上查询相关资料的行为,不能认定为预备犯;为了购买凶器而挣钱的行为,也不能认定为预备犯。概言之,只有当行为对法益具有一定的抽象危险时,才可能认定为预备犯。
第五,为他人实施恐怖活动而进行准备的行为是否成立准备恐怖活动罪?
如前所述,犯罪预备的主观要件是为了实行犯罪。从文理上解释,为了实行包括为了自己实行犯罪(自己预备罪)与为了他人实行犯罪(他人预备罪)。自己预备罪没有疑问,亦即,为了自己实施恐怖活动而实施《刑法》第120条之二规定的准备行为,当然成立准备恐怖活动罪。问题是,为了他人实行恐怖活动而实施《刑法》第120条之二规定的准备行为的,是否成立准备恐怖活动罪?亦即,是否承认他人预备罪?对此,日本刑法理论上存在肯定说、否定说与二分说。
肯定说认为,为了他人实行犯罪而实施的准备行为,完全符合预备罪的特征。因为预备与实行的着手具有性质上的差异,两者间存在质的断绝,故预备行为不限于为了自己实行犯罪;为了他人实行杀人或者抢劫而实施预备行为时,如果他人还没有着手,就成立预备罪的共犯(包括共同正犯)。日本也有判例采取了肯定说
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1962年11月8日判决,载日本《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第16卷第11号,第1522页。。众所周知,日本《刑法》第153条规定了准备伪造货币罪(“以供伪造、变造货币、纸币或者银行券之用为目的,准备器械或者原料的,处三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惩役”),日本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为了他人伪造、变造货币而准备器械或者原料的,也成立本罪
参见:团藤重光.刑法纲要(各论)[M]. 3版.东京:创文社,1990:255;大谷实.刑法讲义各论[M].4版.东京:成文堂,2012:436;西田典之.刑法各论[M].6版.东京:弘文堂,2012:333;前田雅英.刑法各论讲义[M].5版.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1:495;山口厚.刑法各论[M].2版.东京:有斐阁,2010:428.。
否定说认为,为了他人实行犯罪而实施的准备行为,只不过是对预备的帮助,而且行为的危险性很小,不应当作为预备罪处理。例如,大塚仁教授指出:“预备罪、阴谋罪本来所处罚的是为了特定既遂犯的实行而实施的准备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说,应认为预备罪、阴谋罪的构成要件是分别对该既遂犯的构成要件进行修正而形成的……因此,预备罪、阴谋罪的故意,原则上与各罪的既遂犯所要求的故意没有区别,预备行为者与阴谋行为者必须以自己实现犯罪为目的进行准备。虽然有见解认为,为了他人实现犯罪而实施的准备行为即他人预备行为(不真正预备行为)成立预备罪,但这样扩张预备罪的观念并不妥当。”但是,大塚仁教授在讨论日本的准备伪造货币罪时也认为,行为人以供他人伪造、变造为目的而准备器械或者原料时,成立准备伪造货币罪的帮助犯。由此看来,大塚仁教授也承认为了他人实行犯罪而实施准备行为的,成立独立预备罪的帮助犯。
二分说认为,只有当刑法条文特别承认为了他人实行的预备行为时,才属于他人预备罪;此外的情形则不成立预备罪。如平野龙一教授指出:“自己预备罪,是指只有以自己(或与他人共同)实施实行行为为目的而实施预备罪的情况……与此相对,像准备伪造货币罪那样,规定‘以供伪造、变造货币、纸币或者银行券之用为目的,准备器械或者原料’时,就不限于以自己伪造为目的的情况,也包括供他人伪造用的情况。”
本文采取限定的肯定说。刑法分则所规定的“为了……”都不限于为了自己,而是包括为了他人。从文理上说,《刑法》第120条之二第1款第1、3、4项所规定的“为实施恐怖活动”,既包括“为自己实施恐怖活动”,也包括“为他人实施恐怖活动”。所以,承认《刑法》第120条之二第1款规定的犯罪包括他人预备罪没有法律障碍。但是,倘若甲以为乙将要实施恐怖活动,而为乙准备凶器时,乙根本不实施恐怖活动的,则难以认定甲的行为具有可罚性(属于不能犯)。换言之,在甲为了乙实行恐怖犯罪而实施准备行为时,只有当乙至少实施了恐怖犯罪的预备行为时,甲才成立他人预备罪。
第六,按独立预备罪论处导致处罚程度轻于从属预备罪时,应当如何处理?
《刑法》第120条之二第2款规定:“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例如,为了实施恐怖活动而非法购买大量枪支、弹药的行为,同时构成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并且属于情节严重。对此,应以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论处,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法定刑。问题是,上述第2款规定的“其他犯罪”是否包括相应的从属预备罪?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第120条之二第1款虽然对准备恐怖活动罪设置了独立的法定刑,而且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但是,由于刑法总则第22条规定对预备犯只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因而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能不从轻、减轻处罚与免除处罚,所以,必然出现这样的现象,即按第120条之二第1款规定的法定刑处罚,可能轻于按从属预备罪(即行为人准备实行的恐怖犯罪的预备犯)处罚,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按从属预备罪处罚?
假如甲、乙等人为实施大规模杀人的恐怖活动进行了策划,准备了大量危险凶器,并且对参加人员进行了培训。在这种情况下,倘若认定为准备恐怖活动罪(即独立预备罪),按《刑法》第120条之二第1款规定的法定刑处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但是,倘若按故意杀人罪的预备犯(即从属预备罪)处罚,并且根据案件事实不应从轻、减轻处罚时,则完全可能判处无期徒刑。如果后者更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则应按后者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预备犯。所以,《刑法》第120条之二第2款所规定的“其他犯罪”包括相应的从属预备罪。
三、构成要件的交叉化
只要阅读《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恐怖犯罪的条文,就会发现条文所规定的构成要件之间存在大量交叉现象。
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第120条之二第1款第2项将组织恐怖活动培训规定为独立的犯罪,如前所述,该行为实际上是预备犯的既遂化,而且根据前述分析,预备犯被既遂化,意味着预备行为被实行行为化,于是,“资助”恐怖活动培训的行为,就是第120条之二第1款第2项的帮助犯。但是,第120条之一第1款将“资助恐怖活动培训”规定为另一种正犯行为。于是,准备恐怖活动罪的帮助犯(第120条之二第1款第2项的帮助犯),同时也是帮助恐怖活动罪(第120条之一第1款)的正犯。
又如,《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第120条之五规定:“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被强制穿戴上述服饰、标志的人,如果并没有丧失自由意志的,是否成立《刑法修正案(九)》所增设的第120条之三所规定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倘若得出肯定结论,那么,对强制者是认定为强制他人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罪的正犯,还是认定为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的教唆犯?在被强制穿戴上述服饰、标志的人丧失自由意志时,虽然被强制者不成立犯罪,那么,强制者是成立强制他人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罪的正犯,还是成立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的间接正犯?概言之,第120条之五的正犯与第120条之三的教唆犯、间接正犯形成的交叉,应当如何处理?
再如,《刑法修正案(九)》所规定的各种恐怖活动犯罪与刑法分则其他章节的犯罪也可能产生交叉关系。《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第120条之四规定:“利用极端主义煽动、胁迫群众破坏国家法律确立的婚姻、司法、教育、社会管理等制度实施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条规定与《刑法》第278条规定的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刑法》第300条规定的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是什么关系?《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第120条之二规定的“为实施恐怖活动准备……危险物品”与《刑法》第125条规定的非法制造、买卖、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及非法制造、买卖、储存危险物质罪是什么关系?
上述问题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情形是,准正犯(被正犯化的帮助犯)或准既遂犯(被既遂化的预备犯)同时构成另一正犯时,以及此罪的帮助或者教唆行为同时构成彼罪的正犯时,应当如何处理?以下将这类情形称为广义共犯的交叉(包括恐怖犯罪的共犯与其他共犯的交叉)。第二类情形是,法条规定的构成要件行为存在的交叉是属于法条竞合还是属于想象竞合?以下将这类情形称为构成要件的交叉。这两类情形的区分也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换言之,前一类情形事实上也存在构成要件的交叉现象。
总的来说,在处理两类问题时,必须以《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恐怖犯罪的立法宗旨为指导,同时实现罪刑相应与罪刑协调(罪与罪之间的均衡)。一方面,《刑法修正案(九)》对恐怖犯罪的规定旨在扩大恐怖犯罪的处罚范围,并且加重了恐怖犯罪的法定刑。另一方面,“罪数论·竞合论是在实体上经过了对某一行为的违法、责任的判断阶段后,为量刑提供基础的领域的讨论。”换言之,罪数论也好、竞合论也罢,就是为了解决量刑问题,“正确的刑罚裁量终究是整个竞合理论的目的。”所以,不考虑罪刑相应与罪刑协调的要求,单纯从形式逻辑出发研究《刑法修正案(九)》中的构要要件交叉现象或者其他分则法条的构成要件交叉现象,为本文所不取。
(一)广义共犯的交叉
《刑法修正案(九)》既有将帮助犯正犯化的现象,也有将预备犯既遂化的现象。可以认为,帮助犯被正犯化后是一种准正犯,预备犯被既遂化后是一种准既遂犯
为了避免混淆,不得不使用准正犯与准既遂犯的概念。。
其一,在正犯的法定刑高于或者同于准正犯(被正犯化的帮助犯)的法定刑时,如果准正犯的行为同时符合正犯的构成要件,应按正犯处罚。例如,为实施恐怖活动准备危险物品的行为(第120条之二第1款第1项)同时属于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正犯时,应适用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法定刑予以处罚
这实际上是构成要件的交叉现象,如后所述,不是法条竞合,而是想象竞合犯。。
其二,在既遂犯的法定刑高于或者同于准既遂犯(被既遂化的预备犯)的法定刑时,如果准既遂犯的行为同时符合既遂犯的构成要件,应按既遂犯处罚。例如,为境外恐怖活动组织招募人员,并且以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运送招募的人员偷越国(边)境(该行为原本属于预备犯,但被第120条之一第2款既遂化),倘若不符合数罪并罚的条件,就应适用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既遂犯)的法定刑科处刑罚
这种情形也是构成要件的交叉现象,属于想象竞合。。
其三,在按帮助犯处罚应当适用刑法总则的从宽规定,而按(准)正犯处罚更能实现罪刑相应与罪刑协调时,应当适用(准)正犯的规定。例如,对资助恐怖活动培训的行为,以及为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的准正犯提供帮助的行为,不应认定为准备恐怖活动罪(第120条之二)中的“组织恐怖活动培训”的帮助犯,而应认定为帮助恐怖活动罪(第120条之一)的正犯。
其四,轻罪的正犯同时构成重罪的教唆犯或者间接正犯时,应当按重罪的教唆犯或者间接正犯处罚。例如,《刑法》第120条之五规定的强制他人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罪的最高刑只有3年有期徒刑,而第120条之三规定的宣扬恐怖主义罪的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如果强制他人穿戴上述服饰、标志的行为,同时成立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的教唆犯或者间接正犯,就应适用后罪的法定刑。
(二)构成要件的交叉
构成要件的交叉是否属于法条竞合,在国内外存在不同观点。德国的法条竞合理论并没有承认法条竞合的交叉关系,日本则有部分学者承认法条竞合的交叉关系。
所谓交叉关系,表现为属于A概念的事项中有一部分属于B概念,属于B概念的事项中有一部分同时属于A概念。换言之,A法条与B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存在部分重合时,就属于交叉关系。例如,日本《刑法》第224条规定:“略取或者诱拐未成年人的,处三个月以上七年以下惩役。”第225条规定:“以营利、猥亵、结婚或者对生命、身体的加害为目的,略取或者诱拐他人的,处一年以上十年以下惩役。”山口厚教授认为,在以营利、猥亵等目的略取、诱拐未成年人这一部分,略取、诱拐未成年人罪与营利目的等略取、诱拐罪就形成交叉关系,适用重法条优于轻法条的原则。
为什么德国的竞合论不承认法条竞合的交叉关系呢?这涉及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别。承认法条竞合的交叉关系时,虽然适用一个重法条,但由于法条竞合时只能适用一个法条,所以其他法条被排斥适用。与之相反,想象竞合时并不是只适用一个法条,而是同时适用行为所触犯的数个法条,在判决中应当明示被告人的行为触犯数个罪名(想象竞合的明示机能),只是按其中最重犯罪的法定刑量刑而已。正因为如此,法条竞合时仍属单纯一罪,而想象竞合原本为数罪只是作为科刑上一罪处理
参见: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M].6版.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5:392,399;山口厚.刑法总论[M].2版.东京:
有斐阁,2007:365,379;井田良.讲义刑法学·总论[M].东京:有斐阁,2008:523,532.。诚然,“如果将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的法律后果相比较,就会证实一个论断,即除了在法条竞合里也可能优先适用较轻的刑罚,它们的法律后果几乎没有差异。”但“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除了特殊关系,法条竞合的其他情况都可以被当作想象竞合处理。”
就日本《刑法》第224条与第225条而言,虽然形式上存在外延上的交叉关系,但是,当行为人以营利、猥亵等目的略取、诱拐未成年人时,如果仅适用第224条,就没有评价其不法目的;如果仅适用第225条,就没有评价略取、诱拐未成年人这一内容。只有认定为想象竞合,在判决中明示行为同时触犯第224条与第225条,才能实现全面评价。不难看出,只要重视想象竞合的明示机能,就可以否认法条竞合的交叉关系。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理论基本上采用了单一的形式标准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甚至通过介入案件事实判断两个法条之间是否存在包容(包摄)与交叉等关系,结局是将大量的想象竞合纳入法条竞合。例如,有学者指出,当行为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骗得财物时,就成立外延上的交叉关系。据此,《刑法》第266条与第279条存在交叉关系,属于法条竞合的交叉关系,适用原则是重法条优于轻法条。可是,第279条所规定的招摇撞骗罪并没有将财物作为保护法益,因而不以骗取财物为要件,如果仅适用其中一个法条,就没有对不法内容进行全面评价。亦即,如果仅认定为招摇撞骗罪,就没有评价行为对财产的不法侵害内容;如果只认定为诈骗罪,就没有评价行为对国家机关公共信用的不法侵害内容。只有认定为想象竞合,在判决中明示行为触犯上述两个罪名,只是适用一个重法定刑,才能全面评价行为的不法内容。
再如,前述为境外恐怖活动组织招募人员,并且以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运送招募的人员偷越国(边)境的情形,倘若不符合数罪并罚的条件,就不得并罚。但是,如果仅认定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就没有评价恐怖活动对公共安全的不法侵害内容;如若仅认定为帮助恐怖活动罪,就没有评价行为对国(边)境管理秩序的不法侵害内容。所以,应当认定为想象竞合,在判决中明示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最后仅适用一个重法定刑。
同样,《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第120条之四规定的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罪与《刑法》第278条规定的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存在交叉关系。即当行为人利用极端主义煽动群众暴力抗拒国家法律实施时,同时触犯了两个法条。如果仅认定为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罪,就没有评价其中的煽动群众“暴力抗拒”的不法内容;如果仅认定为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就没有评价其中的利用极端主义的不法内容。所以,只有认定为想象竞合,在判决中明示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最后仅适用一个重法定刑,才能实现全面评价。
那么,在上述案件中,为什么不能仅适用一个法条,承认二者之间为法条竞合呢?或者说,为什么虽然最终按一个重罪的法定刑量刑,而必须认定为想象竞合,并在判决书中明示其行为同时构成两个犯罪呢?
首先,刑法的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国民自由。对任何一个案件的不法内容,只有既充分、全面评价又不重复评价,才能既保护法益,也保障国民自由。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同时侵害了公共安全与社会管理秩序,而法官仅评价其行为构成恐怖犯罪,便没有对社会管理秩序予以保护,这不利于实现刑法的保护法益机能。如前所述,竞合论或者罪数论都是为量刑服务的。量刑的基准是责任,或者说是有责的不法。如果A法条的不法内容(程度)完全能够包容B法条的不法内容(程度),那么,就只需要适用A法条,而不可能适用B法条。如果A法条的不法内容不能包容B法条的不法内容,当甲的行为同时存在A法条的不法内容与B法条的不法内容时,那么,适用其中任何一个法条,都不能对甲的行为内容进行全面评价。在这种场合,就必须认定为想象竞合。在德国,“一个行为(犯罪事实)的不法内容,只要适用一个刑罚法规就能够穷尽全部评价时,便是法条竞合;在有必要适用数个刑罚法规进行评价时,就是想象竞合(观念的竞合)。”这是因为,“通过设立想象竞合,能够在判决中充分评价行为人的法益侵害态度(想象竞合的明示机能)……对一个行为必须在妥当的、所有的法律观点之下做出判断。”
其次,刑法虽然具有行为规范的一面,但刑法不是针对一般人制定的,而是针对司法人员制定的。一般人实际上是借由媒体通过了解判决内容来了解刑法的。判决是对刑法的活生生的解读,解读得越明确,刑法的内容就越容易被一般人理解,刑法就越能发挥行为规范的作用,从而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就本文所讨论的问题而言,要发挥刑法的行为规范的作用,就必须注重想象竞合的明示机能。想象竞合的明示机能,是指由于被告人的行为具有数个有责的不法内容,在判决宣告时,必须将其一一列出,做到全面评价,以便被告人与一般人能从判决中了解行为触犯几个犯罪,从而得知什么样的行为构成犯罪。例如,在为境外恐怖活动组织招募人员,并且以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运送招募的人员偷越国(边)境的案件中,倘若判决仅宣告被告人的行为成立帮助恐怖活动罪,可能使被告人与一般人误以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反之,倘若仅宣告被告人的行为成立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就可能使被告人与一般人误以为为恐怖活动组织招募、运送人员的行为不成立犯罪。这样的认定显然不利于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再如,《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第120条之六规定:“明知是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而非法持有,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其中的“持有”既可以是秘密的,也可以是公开的,既可以藏于家中,也可以携带于公共场合。倘若携带于公共场合的行为同时触犯了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那么,如果判决仅宣告被告人的行为成立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则可能使被告人与一般人误以为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行为不成立犯罪;反之,如若判决仅宣告被告人的行为成立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就可能使被告人与一般人误以为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的行为不成立犯罪。只有在判决中明示上述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才有利于实现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目的。
总之,在法条之间虽然存在交叉关系,但仅适用一个法条不能全面保护法益时(两个法条的保护法益不同),或者不能全面评价行为的不法内容时(虽然侵害相同法益,但不法内容存在区别),不应当认定为法条竞合,而应当认定为想象竞合。换言之,法条竞合的确定,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逻辑问题。“必须通过对被排除适用一方的构成要件的不法程度进行目的论的考量予以补充的现象并不罕见。”基于同样的理由,对于《刑法修正案(九)》有关恐怖犯罪的规定所形成的交叉关系,通常应认定为想象竞合,而不宜认定为法条竞合。
参考文献:
[1]高桥则夫.刑法的保护の早期化と刑法の限界[J].法律时报, 2003, 75 (2):16.
[2] 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71以下.
[3]曾文科.强迫劳动罪法益研究及其应用[M]//陈兴良.刑事法判解.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207以下.
[4]王燕飞.恐怖主义犯罪立法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64以下.
[5]张明楷.未遂犯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449-451.
[6]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M]. 4版.东京:有斐阁,2008:324.
[7]平野龙一.刑法总论II[M].东京:有斐阁,1975: 350-351.
[8]福田平.刑法总论[M].东京:有斐阁,2001:251.
[9]张明楷.犯罪预备中的“为了犯罪”[J].法学杂志,1998(1):7-8.
[10]正田满三郎.犯罪论或问[M].东京:一粒社,1969:14-17.
[11]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M]. 4版.东京:有斐阁,2008:254.
[12]大塚仁.刑法概说(各论)[M]. 3版增补版.东京:有斐阁,2005:421.
[13]平野龙一.刑法总论II[M].东京:有斐阁,1975:340.
[14]只木诚.罪数论·竞合论[M]//山口厚,甲斐克.21世纪日中刑事法の重要课题,东京:成文堂,2014:73.
[15]Ingeborg Puppe.基于构成要件结果同一性所形成不同构成要件实现之想象竞合[J].陈志辉,译.东吴法律学报,17(3):321.
[16]山口厚.刑法总论[M]. 2版.东京:有斐阁,2007:368.
[17]只木诚.罪数论の研究[M].东京:成文堂,2009:187以下.
[18]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I——犯罪论[M].杨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445-446.
[19]陈兴良.规范刑法学[M]. 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77-279.
[20]张明楷.责任刑与预防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39以下.
[21]只木诚.观念的竞合における明示机能[J].研修,2011,754(4):6.
[22]H.Jescheck,T.Weigend.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llgemeiner Teil[M]. Duncker & Humblot,1996:718.
[23]张明楷.明确性原则在刑事司法中的贯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4).
[24]H.Jescheck, T.Weigend. 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llgemeiner Teil[M]. 5th. Aufl. Duncker & Humblot, 1996:718.
[25]C.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M]. Band II. C.H.Beck,2003: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