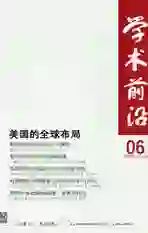美国中亚战略的困境、发展与转向
2016-09-10袁胜育钱平广
袁胜育 钱平广
【摘要】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美国的中亚战略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过渡与铺垫、大举进入与迅速扩张、遭遇挫折与政策调整、走向理性与务实四个阶段。尽管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但美国的中亚战略目标基本围绕了三个核心内容: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人权目标。总的发展趋势是安全利益的重要性趋于下降,经济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人权的重视难以回避,不得不在利益和价值之间寻找平衡。基于美国的全球利益和中亚的战略地位,美国与中亚的接触是顺理成章的,但地缘上的区隔和文化上的差异,又成为美国推进其战略目标的短板。未来美国的中亚战略,势必要在战略愿景与现实利益、可动用的资源之间寻求平衡。
【关键词】美国 外交政策 中亚战略
【中图分类号】D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2.005
不论是出于中亚地区自身独特的地缘位置及其对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性,还是作为维护冷战胜利成果,压制俄罗斯重新崛起、瓦解后苏联空间走向一体化努力的步骤,美国注定要进入中亚。虽然美国在中亚的战略布局,常常伴随着价值目标与地缘政治目标的交替困扰、政策言论与现实的不时脱节,导致其中亚战略的摇摆与不确定,但总体来看,美国对中亚的争夺是持之以恒的,服务于其全球战略部署和价值追求。
对于美国中亚战略的演变,本文进行了四个阶段的划分:以中亚五国1991年独立为起点,1991年至2001年“9·11”事件发生前为第一阶段,2001年至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为第二阶段,2005年至2014年为第三阶段,2014年美军开始撤离阿富汗开启了美国中亚战略的第四阶段。①
过渡与铺垫时期
苏联解体前,中亚五国作为其加盟共和国,被紧紧束缚于苏联的统一大家庭内,美国对中亚尽管觊觎已久,但苦于无处下手。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亚地区的历史突然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苏联这一政治大厦轰然崩塌,中亚五国获得独立,而作为苏联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自身尚未站稳脚跟,更遑论将中亚重新纳入势力范围。中亚地区力量真空的出现,为美国的进入提供了机遇。
在1990年代初期,美国中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消化、巩固冷战胜利成果。1992年10月24日,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涉及中亚的《自由促进法案》(Freedom Support Act),规定向前苏联国家或新独立国家提供援助。②该法案列举了美国在中亚的几个目标:促进地区稳定、鼓励民主化、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实现中亚地区的去核化、确保欧亚走廊的贸易与运输自由、引入国际人权标准等。一年之后,美国在1993年10月20日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北约部长理事会于当年12月2日决定予以接受,并在1994年1月10日的北约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获得正式通过。1994年5月10日,土库曼斯坦在中亚国家中率先参加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之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分别于5月27日、6月2日和7月13日先后加入该计划。塔吉克斯坦于2002年2月20日加入,是最后一个加入该计划的中亚国家。③
随着俄罗斯独立初期俄美短暂的蜜月关系结束,俄美关系龃龉不断。在此背景下,1994年美国主导的矛头指向俄罗斯的北约东扩正式启动,加之里海能源储量展现的乐观预期,中亚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开始凸现。
1995年4月,美国政府成立了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中情局在内的工作小组,研究美国公司参与中亚油气开发的问题。1997年7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就美国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政策发表讲话,强调美国对该地区的目标是:“促进民主,创建市场经济,保征中亚各国内部以及国家间的和平与合作”,“支持这一地区国家对俄的独立倾向;解决这一地区冲突与开发石油资源同时进行,使该地区成为美国21世纪的战略能源基地,遏制并削弱俄罗斯和伊朗在这一地区的影响”。7月底,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中亚和外高加索是对美国具有切身重要利益的地区”。④在此背景下,1997年美国颁布了《丝绸之路战略法案》(The Silk Road Strategy Act),其战略目标是遏制俄罗斯,保证美国的能源安全和实现美国价值观。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丝绸之路战略法案》,该法案授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支持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的消弭冲突、人道主义需求、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边境管控、民主和公民社会的建设。⑤
1997年被认为是美国开始全面介入中亚事务的起点,明确了其在中亚的政治和经济战略目标,但由于受其全球战略部署和战略利益的影响,美国对中亚的重视程度仍比较低,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手段有限,政策执行上相对谨慎。正因为如此,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国内对其中亚政策出现了反思的声音,认为克林顿政府并未形成一种针对中亚地区的连贯政策,甚至并未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形成清晰的认识。⑥
总体来看,2001年之前的10年间,由于找不到合理进入的契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渗透进展甚微,除了将中亚各国纳入“北约和平伙伴计划国”外,其他收效寥寥。但1991年以后的10年,也正是美国中亚战略的重要过渡与铺垫期,美国的中亚战略随着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推进,针对中亚的具体政策也不断明确和完善,一旦机会乍现(如“9·11”事件),美国就有能力快速全面地介入中亚事务。
大举进入与迅速扩张时期
2001年的“9·11”事件是美国大举进入中亚地区的分水岭。“9·11”事件之后美国大幅度调整了其中亚政策,主要是借反恐全面加强了对中亚地区的渗透,从政治、经济、安全、能源、文化、教育等各个路径增进美国的利益。
2001年10月,美国国防部在其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提出基本的安全利益原则,为美国在中亚的外交行动和军事介入提供了政策依据。比如:阻止关键地区被敌对势力控制,保持稳定的战略平衡,保持进入关键市场和获得战略资源的渠道,关注“衰弱国家”领土上出现的威胁,关注可维系的联盟,随时准备对突发性危机进行干预,等等。⑦
2001年12月14日,美国推出中亚新政策,将“防止恐怖主义扩散,为中亚的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保障,确保安全、透明地开发里海能源”确定为美在中亚地区的目标,并强调“即使目前的冲突结束了,美国也绝不会从中亚抽身而退”。⑧在这样的定位下,美国开始了在中亚的全面扩展期,借助反恐合作,大举进入中亚,从政治、经济、军事、安全、能源、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与合作。而且,这种合作与渗透并非权宜之计,美国有着长期存在并掌控中亚的谋求。2002年11月27日,美国国务院欧洲与欧亚事务司发表的报告则指出:美国在中亚的战略利益包括安全、能源和内部改革三个方面。⑨
“9·11”事件促使反恐骤然上升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从而导致了美国在对外关系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美国在阿富汗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后,其中亚政策也发生重大调整。驻阿美军的后勤补给、反恐以及安全合作等具体问题取代经济发展和治理议题,成为美国对中亚政策的主要内容。在这一时期,中亚成为美国向阿富汗输送军事补给及后勤装备物资的中转站。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还向美国开放军事基地,成为美国在安全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获得俄罗斯的默许和中亚国家的欢迎,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迅速上升。
遭遇挫折与政策调整时期
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开启了美国全面进入中亚的历史新阶段的话,那么随着美国在中亚的大举扩张,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固然迅速上升,但物极必反,2005年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重大事件,很快就使美国在中亚的扩张遭遇挫折,不得不进行政策调整。
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与5月发生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事件,引发中亚地区政局动荡,社会出现大规模骚乱。如果说这些事件某种程度上正是美国刻意引导的结果,那么令美国始料未及的是,这两个事件对美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害,中亚各国开始在政治上对美国产生怀疑和警惕,美国自“9·11”事件以来费尽心机在中亚确立的形象和地位随即发生动摇,其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也面临被迫撤出的巨大压力。
在中亚支持发动“颜色革命”使美国得不偿失,给美国的中亚战略敲响了警钟。为重新塑造中亚及相邻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更有效地维护和实现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目标,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着手调整其中亚战略。
实际上,冷战结束后美国政界、学界、智库对美国中亚政策的设计一直没有中断过。1997年,美国参议员布朗巴克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和高加索研究所负责人弗雷德·斯塔尔教授便提出“新丝绸之路”(The New Silk Road)这一概念。2005年,斯塔尔教授对初期的设想进行细化,进一步提出“大中亚计划”,即美国应以阿富汗为中心,推动中亚、南亚在政治、安全、能源和交通等领域的合作,建立一个由实行市场经济和世俗政治体制的亲美国家组成的新地缘政治板块,从而保障美国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尽管斯塔尔教授的设想没有被美国政府直接转化为政策,但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中亚政策必须进行调整和改变。2005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哈萨克斯坦表示,应该把中亚与南亚联系在一起。顺应中亚地区局势的发展和美国的战略布局,2006年1月,美国国务院调整了部门机构设置,将原属欧洲司的中亚五国归入新成立的中亚南亚司,“大中亚计划”全面启动。⑩
2006年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部分修订了1999年法案,新法案继续肯定了美国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追求的能源、安全与民主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该法案同时规定了为促进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民主、宽容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美国需要采取的具体行动。
2009年1月,随着奥巴马政府开始执政,美国对其中亚政策展开了大辩论和大反思,对奥巴马时代美国的中亚政策调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经过近一年的准备,2009年12月,美国国务院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乔治·科罗尔(George A. Krol)在国会听证会上宣布了美国新中亚政策的几个要点:首先是美国需要增进与中亚国家在阿富汗反恐上的合作;其次是使中亚地区的能源和运输线路尽可能地多元化;督促中亚地区推进民主和人权;发展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加强中亚各国的自我管理能力;防止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发生国家失控。这一系列政策基于这样的判断:“中亚地区处于美国关键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支点上。”⑪2011年7月20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金奈正式宣布推出“新丝绸之路”战略,主要有三点内容:继续加强反恐安全合作,维护地区稳定;加强政治对话,增信释疑;加强区域一体化,侧重经济领域。⑫在2011年9月22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期间,希拉里向国际社会进一步描述了“新丝绸之路”计划,声称该计划的实施将使整个地区经济走向繁荣,中亚、南亚地区也将趋向稳定。2014年10月28日,美国南亚中亚事务办公室副助理苏马尔发表了关于“中亚区域一体化前景”的讲话,再次强调了“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重要意义及2014年之后该战略的相关规划。⑬
2011年6月22日,美国宣布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不难看出,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正是为了应对从阿富汗撤军期间和撤军后面临的新形势而做出的战略部署,美国仍然需要中亚国家的合作与支持。不过,与中亚国家努力在大国间采取平衡政策相一致,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令中亚国家对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提出的投资和援助普遍抱有期待。但鉴于各种原因,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式微态势已经显露,追求更加平衡理性和务实的中亚战略成为美国的选择。
打造理性而务实的中亚战略
可以说,阿富汗战争塑造了美国的中亚战略,使得美国的中亚战略在十多年间主要围绕阿富汗战争而展开。同样,随着阿富汗战事结束、美军撤出阿富汗,中亚地区在美国外交和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出现变化成为必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放弃中亚,或者说中亚之于美国的重要性就此大幅度下降,而是美国的中亚战略在过去二十多年间,经过实践的检验不断得以修正,这一修正结果使得美国的中亚战略目标具有了长期性和既定性,美国在处理中亚问题时将趋于理性和务实。
从2015年开始,美国对中亚的政策就出现明显变化。2015年3月31日,美国副国务卿安·布林肯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话,阐述了美国的中亚新政策。布林肯表示,与每个中亚国家的接触旨在实现三个重要目标:加强伙伴关系,以推进共同安全;锻造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推动和倡导善治和人权。虽然布林肯强调:“有些人将我们的部队从阿富汗的缩减视为这个地区对美国重要性的下降,没有什么比这更不符合事实的了。从上世纪90年代到今天,我们观察中亚的视角可能有变化,但我们对在这个地区为推进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而建立持久伙伴关系的承诺丝毫也没有改变。”⑭但显然,美国中亚战略的重心开始转向经济和民生。
这一转变也和对美国外交决策有重要影响力的智库建言相吻合。如2015年5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发布题为《中亚在欧亚重新连通过程中的地位》(Central Asia in a Reconnecting Eurasia)的报告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美国应该重新平衡中亚政策目标,将由安全主导转向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并通过协调合作取得更多成果。⑮报告认为,美国并不是欧亚地区的直接利益相关方,对中亚影响力也相对有限,未来成为地区主导者更不现实。但在地区互联互通和一体化加速的背景下,美国有必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积极介入,帮助中亚地区实现繁荣、安全和稳定。相关政策措施包括:设立直接受白宫领导的负责欧亚事务的高级别职位,加大与中亚国家经济交流和直接投资的力度,重启“新丝绸之路”计划,派出更多高级别官员访问中亚国家,加强与中俄等大国协调,扩展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交流和商务培训项目等。
2016年1月25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的《美国的“中亚政策3.0”》研究报告也指出,随着美国持续缩小其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中亚作为美国进入阿富汗的战略要道的地位不复存在,因此中亚地区在美国战略考量中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在新环境下,推动华盛顿在中亚地区的优先事项需要美国对中亚政策的显著改变。报告对美国的中亚政策提出的建议包括:优先加强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区域事务中的合作;承认与中俄两国在中亚的共同利益关切,寻求将中俄的行为朝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引导;以需求驱动改革,不把民主强加于中亚国家之上;不要以地区国家人权状况作为安全合作的条件;防止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过度反应并将美国的地区政策“军事化”;更有效地使用手中筹码,追求务实的、优先的政策目标。⑯
机遇和挑战:美国中亚战略评估
通过对过去25年来美国中亚战略演变的回溯,我们得以窥见,美国的中亚战略目标尽管在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但基本围绕了三大核心内容: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人权目标。可以说,美国迄今为止的中亚战略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以美国的标准来看,其成功之处反映在,美国确保了苏联遗留核武器撤出哈萨克斯坦,核设施得到妥善拆除;通过实现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存在,美国确保了其军队在阿富汗的供给路线和在阿富汗的行动能力;尽管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仍旧突出,但中亚并没有出现区域霸权国家;俄罗斯对中亚石油和天然气的垄断也不复存在。然而,中亚国家在美国所倡导的民主化、市场经济、法治和人权等事务上进展有限,甚至出现了“倒退”;美国推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雷声大、雨点小,建立连接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新丝绸之路”战略根本未能起步。⑰
正如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地区在地缘战略上对美国的含义十分清楚:美国相距太远而无法在欧亚大陆的这一部分成为主导力量,但美国又太强大而不能不参与这一地区的事务”。⑱考虑到美国的全球利益和中亚的战略地位,美国与中亚的接触是顺理成章的,但地缘上的区隔和文化上的差异,又成为美国推进其战略目标的短板。因此,未来美国的中亚战略,势必要在战略愿景与其现实利益、可动用的资源之间寻求平衡。
追求安全利益仍将是美国中亚战略的一个选项,但其重要性将趋于下降。美国对中亚仍然有安全需求,表现在中亚可以在阿富汗过渡期内成为一种稳定力量;与中亚合力应对麻醉品走私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威胁;通过安全合作为中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稳定创造条件。但随着美国在阿富汗军事存在的萎缩,在中亚之外还存在着更为重要的安全关切,而且可动用的资源有限,因此,美国在中亚维护其安全利益时,其政策可能做如下调整:一是继续反对任何域外国家控制中亚,但不像从前一样以竞争性的姿态去迎接一切挑战,而是采取离岸平衡的手法,作为中亚的一个伙伴,选择性地运用其政治、经济、安全工具,对冲比邻大国的地缘政治影响。⑲二是改变以前那种只要是俄罗斯、中国在中亚的安全存在就必然是有害的认知,与其任由伊斯兰激进势力在中亚得势,不如接受俄罗斯、中国在中亚发挥更大影响力。鉴于阿富汗在中亚与俄、中毗邻,这个地区的安全威胁对俄、中更为直接,这里的地区性“公共产品”对俄、中更加重要,因此,可以考虑将维护阿富汗和中亚安全和提供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任务分给俄罗斯和中国,以减轻美国的负担。
与此相类似的是美国在中亚的经济利益。传统上能源是吸引美国关注中亚的重要因素,但随着油气勘探的进展,中亚的能源潜力被证明远非当初预测的那样大,加之多条西方主导的管道项目遭遇到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地缘因素的拘囿,还有油价的崩溃,这些都降低了美国及西方对中亚能源资源的兴趣。而阿富汗战争则让美国认识到,不可能依靠军事手段铲除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希望通过阿富汗与周边国家形成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来实现阿富汗的顺利过渡。几方面因素叠加,美国在中亚的经济议题主要聚焦在通过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来为美国的商业、技术和创新提供机会和寻求阿富汗问题的最终解决。多年来,美国致力于推动“新丝绸之路”战略,但对安全议题的重视以及对中亚地区有限的经济投入,使得这项战略进展甚微。尽管今后安全利益的重要性趋于下降,但这项战略的推进仍然困难重重。因为中亚复杂的地区形势和国内环境使得美国资本将这个地区视为畏途,美国国内也没有一个现存的选民群体支持发展与这一地区更紧密的联系。或许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让美国看到了振兴其“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机会。在前面提到的布林肯的讲话中,他难得地对中国的计划褒扬有加:“我们支持中国将这一地区连接起来的努力”,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与我们自己的努力完全互补。特别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在支持阿富汗过渡和推进其与更广泛的亚洲地区的融合所发挥的重要作用”。⑳
人权目标是美国中亚战略的第三个核心内容。按照布林肯的说法,“我们的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推进我们与包括中亚在内的全世界所有人共享的民主价值观。在我们与中亚的接触中,这些价值观居于非常核心的位置,是我们追求持久稳定须臾不可或缺的”。美国外交的价值观追求是由其国内政治决定的,而在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美国经常面临价值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矛盾的困扰,在美国与中亚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按照美国的标准,中亚国家有着封闭的政治体制,存在着对基本的公民权利的侵犯,缺少对法治的尊重,这些都是美国力图用它的价值观去改变的。因此,美国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就附加了各种人权条件,如国务院和国防部有《莱希法案(Leahy Law)》以及《贩卖受害者保护法》等法案的限制。但另一方面,出于安全和战略利益的考虑,美国常常又不得不无视中亚国家的所谓“人权”问题,甚至努力去规避国内立法所做出的种种限制,以至于美国国内的人权活动分子批评说:先是阿富汗战争,再是对伊斯兰国的战争,使得美国在中亚的政策“安全化”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被排除在合作的范围之外。
但正如美国学者J.斯帕尼尔所指出的:“我们的政治领袖们反映了国内社会的价值观念,每当他们在执行国家的外交政策中似乎要漠视这些价值观念时,他们总会受到政府行政部门、国会、反对派以及新闻界人士的批评。”这也就意味着随着阿富汗战争趋于结束,美国政府很难再以安全的理由,规避或者“赦免”中亚国家的“人权”问题。利益和价值的矛盾,仍将困扰着美国的中亚外交。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法学高原学科和上海政法学院创新性学科团队项目支持)
注释
对美国的中亚战略进行阶段性划分散见于相关文章著作中,可参见邵育群:《美国中亚政策调整评述》,《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5期;曾向红、杨恕:《美国中亚研究中的“危险话语”及其政治效应》,《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郑羽主编:《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1991~200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杨鸿玺:《美国中亚战略20年:螺旋式演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曾向红:《遏制、整合与塑造:美国中亚政策二十年》,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Andrew C. Kuchins and Jeffrey Mankoff, "Central Asia in a Reconnecting Eurasia," 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legacy_files/files/publication/150507_Kuchins_CentralAsiaSummaryReport_Web.pdf; Eugene Rumer, Richard Sokolsky and Paul Stronski: "U. S. Policy Toward Central Asia 3.0",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6/01/25/u.s.-policy-toward-central-asia-3.0/itlr, January 25, 2016.
George W. Bush, "Statement on Signing on the Freedom Support Act," http://bushlibrary.tamu.edu/papers/19929210240./html.
张宁:《北约与中亚国家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国际资料信息》,2009年第3期。
《华盛顿邮报》,1997年7月30日,转引自王桂芳:《美俄中亚战略及其对中亚安全的影响》,《国际论坛》,2002年第5期。
黄民兴、陈利宽:《阿富汗与“一带一路”建设:地区多元竞争下的选择》,《西亚非洲》,2016年第2期。
曾向红:《遏制、整合与塑造:美国中亚政策二十年》,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页。
潘光:《“9·11”事件前后美国与中亚的关系:变化与挑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孙文中:《美俄争夺中亚地区的前景展望》,《和平与发展》,2002年第3期。
赵良英、沈田:《“9·11”事件以来美国的中亚战略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
2005年3月,斯塔尔教授在一份题为《阿富汗及其邻国的“大中亚伙伴计划”》的报告中,第一次把阿富汗与中亚五国作为一个整体而称之为“大中亚”,就此提出了“大中亚计划”。2005年夏,斯塔尔又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参见Frederick Starr, "A Partnership for Central Asia,"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4, 2005。
Jim Nichol, Central Asia: Regional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RL33458,May 3,2012,p.3; George A. Krol's testimony in U.S.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evaluating US Policy in Central Asia,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December 15, 2009, Serial no. 111-433,pp.14-15. 转引自许涛:《试析美俄中亚政策演变路径与前景》,《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5期。
赵会荣:《2011年中亚地区国际关系》,《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2期。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Prospects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October 28, 2014. http://www.state,gov/p/sca/rls/nnks/2014/233577.htm.
Antony J. Blinken,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Remarks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An Enduring Vision for Central Asia," http://www.state.gov/s/d/2015/240013.htm.
Andrew C. Kuchins, Jeffrey Mankoff, A Report of the CSIS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 "Central Asia in a Reconnecting Eurasia, May 2015," 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legacy_files/files/publication/150507_Kuchins_CentralAsiaSummaryReport_Web.pdf.
Eugene Rumer, Richard Sokolsky and Paul Stronski: "U. S. Policy Toward Central Asia 3.0,"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6/01/25/u.s.-policy-toward-central-asia-3.0/itlr, January 25, 2016.
Eugene Rumer, Richard Sokolsky and Paul Stronski: "U. S. Policy Toward Central Asia 3.0",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6/01/25/u.s.-policy-toward-central-asia-3.0/itlr, January 25, 2016.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7页。
Eugene Rumer, Richard Sokolsky and Paul Stronski: "U. S. Policy toward Central Asia 3.0,"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6/01/25/u.s.-policy-toward-central-asia-3.0/itlr, January 25, 2016.
Antony J. Blinken,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Remarks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An Enduring Vision for Central Asia," http://www.state.gov/s/d/2015/240013.htm.
Leahy Vetting: Law, Policy, Process, April 15, 2013. 该法案因提案人佛蒙特州民主党参议员派屈克·莱希(Patrick Leahy)得名,于1997年首度获得国会通过,当时适逢哥伦比亚军方在美国金援下屠杀平民一事遭到揭发。《莱希法案》禁止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拿美国人民交纳的税金去援助、训练或装备任何据信涉及严重侵犯人权──例如法外杀人、酷刑、强暴和强迫失踪──的外国军警单位。http://www.humanrights.gov/wp-content/uploads/2011/10/leahy-vetting-law-policy-and-process.pdf。
U.S. Laws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相关国家打击人口贩卖的表现作出评估,被列入最差国家名单的国家将面临制裁。但总统可以以国家利益的需要予以赦免。乌兹别克斯坦2013年、2014年即属此例。http://www.state.gov/j/tip/laws/。
Nate Schenkkan, Getting Real (ist) on U.S. Policy in Central Asia, February 1, 2016, http://freedomhouse.org/blog/getting-realist-us-policy-central-asia.
[美]J.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45页。
责 编/樊保玲
Abstract: Sinc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he US Central Asia strategy ha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transition and preparation; large-scale entry and rapid expansion; policy adjustment due to setbacks; and being rational and pragmatic. Although the emphasis has been placed on different area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the US Central Asia policy basically focus on three key aspects: security interests, economic interests and human rights. The general trend of development is that the importance of security interests tends to decline, economic issu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human rights issue is difficult to avoid, so the US has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the interests and values. Considering the global interests of the US and Central Asia's strategic position, it is natural that the US would try to get in touch with Central Asia, but geographical distanc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are the deficiency preventing the US from promoting its strategic objectives. The US Central Asia strategy in the future is bound to seek a balance between strategic vision, real interests, and available resources.
Keywords: US, foreign policy, Central Asia strate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