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工人作家培训经历
2016-09-06郎慕中
郎慕中
建国后工人作家培训经历
郎慕中

1992年8月上海作协小说组赴浙江兰溪等地采风。左二为张士敏,右一为姚克明,右三为作者
悠悠长街上的巨鹿路675号别墅,门楣上挂着上海作家协会的牌子。斑驳的墙面透露出历史的沧桑。过去是豪绅世家府邸,水磨高墙里面建筑高雅脱俗,庭院深深,假山水池,在金灿灿的阳光照耀下,美丽多姿。
每当经过这里,我的心情就会波澜汹涌。这个芳草院落,现为我们文学爱好者的精神家园。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多少诗人、作家在这里交流,碰撞出时代的火花,有多少青年男女,在这里得到扶植而登上文坛。当年我还是热血青年,正是从这里,慢慢成长为“业余作者” 、工人作家。
作协领导对我们业余作者十分重视和关怀,为我们办各类讲座和创作学习班。而今打开我珍藏的日记和听课记录,倏忽虽已过一个甲子,当时的情景,前辈老作家培养文学青年,甘愿为人梯的奉献精神,使我们感受如阳光雨露般的滋润,成了我们学习的楷模。光阴荏苒,岁月无痕,而今我们虽大多已圆了作家梦,而且白发皤然已奔八十,甚至是奔九十的耄耋老者,但沧桑岁月仍磨灭不掉镌刻在记忆里的前辈老作家,他们的音容笑貌仍留存在心间。
聆听吴强同志谈艰苦跋涉的文学创作道路
那时作协大厅创作学习班上大课。路上堵车,我迟到了,讲课即将开始,我找到小组的位子坐下,海麟悄悄告诉我,台上,坐在主持人旁边的就是《红日》 作者吴强同志。这位大家仰慕已久的大作家,穿一身摩尔登呢中山装,戴顶烟灰色列宁帽,气宇轩昂,两条浓眉,目光炯炯。今天听课的人特别多,除了学习班25位学员,还有各报社副刊编辑、记者,大学文科学生、各区文化馆创作室干部和爱好文学的青年。黑压压的一片,把作协大厅挤得满满的。

左图:1965年上海作协党组负责同志和《收获》《萌芽》编辑部同志、培训学员在作协花园合影留念。前排左四为作者右图:1965年6月12日摄于上海作协,业余创作班学员合影。前排右二为作者
会场突然爆发出一阵雷鸣般掌声。吴强报告开始。他主要讲“生活、学习、创作”的密切关系。他先给我们讲了大文豪托尔斯泰的故事:
托尔斯泰是个贵族,他的庄园门前有一棵大槐树,每天有许多农奴来树下等托尓斯泰,托尔斯泰接见农奴,听农奴讲故事。因此托氏的作品中反映了农民的形象,托尓斯泰还为农奴子弟开办一座学校,他自己上课编教材,关心农奴生活,与农奴打成一片,尽力满足农奴提出的要求,托尔斯泰终于在82岁高龄,离开贵族生活,乘马车离家出走了。说明作家,一定要深入生活的底层,不能像水上浮萍,无根也就长不出硕果,一定要像矿工开矿,从多少矿石中才能提炼出晶莹剔透的宝石。因此,贵族出身的托尔斯泰,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吴强接着又谈自己怎样从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在艰苦的生活、学习、革命环境中,奋斗成长的过程。他是江苏涟水人,做过学徒,当过教师,学生时代就爱好文学,在淮安中学他就写下了诗:
楚城有客不胜愁,点点杨花扑小楼。
梦里潺潺慈母泪,小船迷水下扬州。
当年他和几个同学为寻求革命,第一次进上海。那天,船到十六铺码头,刚下船的乘客,黑压压一片,大家正伸长脖颈,在拥挤的人群中,寻找来接的亲友。同伴们都带着行李,有个同伴手提个藤条箱,刚把藤箱放下地,回身已不见脚边藤箱。大家正惊愕彷徨无措,吴强肩头上拴个包裹,腋下夹把油布伞,他一眼瞥见,有个穿长衫的家伙,手提个木箱,露出藤条箱的边缘(这是旧上海流氓、小偷用空壳木箱套偷的手法) ,就一个箭步上前,一伸油布伞的弯柄,用力钩住那家伙的右腿,那家伙刚想拔脚逃离,冷不防一个趑趄绊倒在烂泥地上。因为用劲大,那家伙摔得不轻,沾了一身污泥,爬起来,回头凶狠地吆喝一声:“小赤佬作死!”这时, 大家一拥而上,边喊:“快捉偷箱子的贼骨头。” 随即岸上响起“㘗㘗”哨音,警察也赶来了。那家伙就像一条泥鳅,往人多处一钻,消失得无影无踪。
吴强的绘声绘色,引起哄堂大笑。他却语重心长地说:“这就是一幅旧上海的风情画。作家就是这样,平时要关注周围这样的社会生活,才能运用积累起来丰富的生活碎片,编织成瑰丽真实的图画——文学作品。”
吴强开始在报上发表散文、特写和短篇小说。1933年春参加左联,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曾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发表短篇小说《激流下》、散文《老黑马》,反映抗日军民生活。参加新四军后,在部队做文化宣传工作,解放战争参加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他介绍长期在军旅生活中,和战士血肉相连,在战场上,眼看鲜活的战士在敌人刺刀下倒下,生活就是那么残酷,文字也就倾注了“愤怒、仇恨、至爱,悲痛和激情”。吴强讲到动情时,神情严肃,激昂。正是这些硝烟烽火中的生死战场,促使他拿起笔,文字就像涌泉般倾注在他的笔端。1952年吴强终于完成了巨著《红日》。我们都是怀着高山仰止的心情拜读。因为它真实地再现了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从战略撤退到反攻的历史演变。小说艺术形象生动,生活画面开阔,既有宏伟的战争场景,又有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犹如一幅气势宏大的油画。吴强同志的身教言教使我们深受启迪:作家只有在真正的生活之中,才能积累丰冨的创作素材,提炼升华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红日》不正是整个作品凝聚了作者艰辛亲历的战斗生活和创作辛勤的汗水,成为巨著的吗?
魏老给我们讲文学创作课
著名作家魏金枝,花白的平顶头,亲切、慈祥,上唇蓄一撮短胡髭,衣着朴素,一口浓重的绍兴官话,是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大家都尊称他“魏老” 。他学识渊博,讲课旁征博引,而且善用形象比喻,他给我们讲文学作品创作技巧,人物刻画,情节安排和怎样构思。
他讲文学的真实性,举了郑板桥改诗的轶闻: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老师带学生去郊游,经过一座石桥,发现桥下清澈的溪水旁,躺着一具女尸。老师感慨,吟诗一首:“二八女多娇,风吹落小桥,三魂随浪转,七魄泛波涛。”
郑板桥向老师提出应该改成:“谁家女多娇,因何落小桥,清丝随浪转,粉面泛波涛。”
老师听了连连点头称赞改得对。文学要真实,不能主观主义。
魏老在讲时,又举了“才女写诗” 的故事:
有一位才女,诗写得好,出口成章,遐迩闻名。一次文人聚会,大家想试一试她的才华,有一个士人,随便拾起半爿铜钱为题。才女细看已沾满铜绿还留着“开元”的半爿铜钱,略一沉思,吟诗一首: “半轮残月淹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想得青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
“金钱万能” ,主题鲜明,一矢中的。
魏老讲选材构思,要注意:“文如观山不喜平”,接着他像私塾老先生,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抑扬顿挫,背诵一段诗:
花瓣边沿皆曲线,更添娇艳在枝头。
长虹也覚直乏味,故曲腰肢让人看。
石蹬行回千万曲,似带如环反而复。
碧海晴空明月夜,弯弯眉月耐人看。
接着他讲“罗丹的斧头”故事:法国名雕塑家罗丹,雕塑《巴尔扎克》像,展出时,他的学生参观连声称赞巴尓扎克一双手造型最美。罗丹听了很难过,他从工作室找来一把斧子,砍掉了这双“完美的手”。学生惊异,罗丹说这双手太突出了,它已经不属这个雕像的整体。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一定要集中、和谐、统一,正如写小说,景物要为衬托人物而存在,情节发展中,副线要服从主线而存在。
关于小说中设置“悬念” 问题,他又举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在旧社会,常见马路上变戏法卖老鼠药的。小铜锣“哐哐”一敲,人们都好奇围拢来看热闹。卖药的在马路边一蹲,取出一块包袱布往地上一铺,一会,奇迹出现了,包袱下竟然出现好几只老鼠,吱吱叫着乱窜,观看的都感到奇怪,这些老鼠从哪里窜出来的。这时只见他一边卖药,一边不停抖着右脚。大人们看了一会,没兴趣,有的买了药就走了。小孩们却好奇,都瞪大眼睛:包袱下有几只老鼠?大的还是小的?总想看个究竟,连家里催他们回去吃饭也不肯。等啊等啊,终于等到老鼠药卖完,才吁了一口气。不料卖药的准备离开时,收起包袱布,下面什么也没有,原来这只是利用脚牵动系在包袱下的几根细绳而出现的效果。这就是小说设置的“悬念” 。 当然,小说的悬念必须要有真实内容,也不能“客里空”骗人,悬念是用来吸引读者兴趣,就如说书先生扔“包袱” 。
魏老知道我们学员中很多是从工厂、基层来的,文化不高,他讲文学创作,善用比喻:文人轶事,历史趣闻。语言幽默、生动、趣味,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就像山岩间平静的潺潺溪流,流进我们的心田,真像喝下心灵的鸡汤,有豁然开朗之感。有时也让大家忍俊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这时,他也神采奕奕,眉毛簌簌动了一下,摸着鼻子下一撮小胡须,得意地笑了。
扛着铺盖参加创作学习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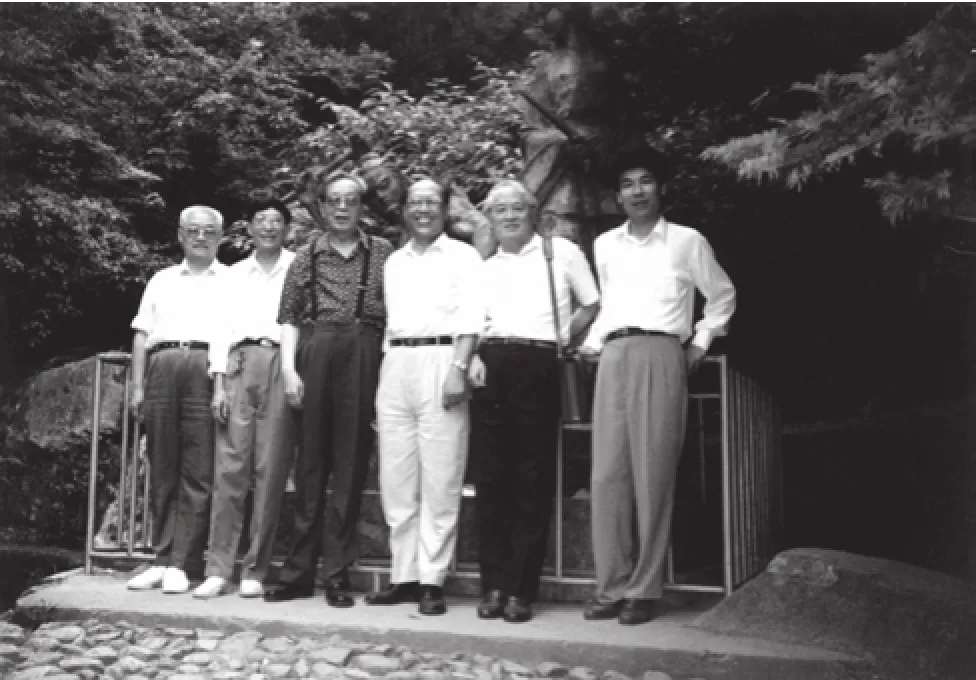
左图:1994年7月上海作协莫干山笔会,从左至右为:施艳萍、沈霞、牟国璋、作者、白桦和作协工作人员
早春三月,还是乍暖还寒季节。接到作协通知:参加全脱产创作学习班。还要求参加学员带作品初稿或构思。一早,我兴匆匆扛着铺盖卷,来到巨鹿路675号作家协会,大家住宿就被安排在西厅打蜡地板的会议室 (当时大厅的西边称西厅),学员来自各方,大多是认识的老朋友,只有一位小伙子,除铺盖之外,还扛着个重甸甸的行李袋。第一次小组见面会上,创作组负责人、作家王道乾同志介绍,他是某机械厂的一位文学爱好者,从未发表过作品,因为父亲是新四军老革命,在苏北一带打游击,他从小耳濡目染,听父亲和父亲朋友给他讲当年的革命斗争故事,他受到感染和激励,决定要把父辈这些抗日斗争故事写出来。他文化不高,三年中却靠查《新华字典》,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写出了四十万字长篇小说,后被工厂宣传部冂发觉,特地推荐参加创作学习班。有天夜深人静,大家都在沉睡中,突然间“哇哇” 几声惊呼,把熟睡的同志都惊醒,我瞥见一个人影正要往门外奔,这时室内电灯亮了,原来是他。他也蓦然觉醒,不好意思地说,我发梦呓了。原来睡梦中仍在构思故事情景,他对写作已到如此痴迷程度。平时他不大说话,总是拿着笔,在本子上写个不停,他告诉我们说,这已成习惯,连在集体生活中,排队买饭莱,下班乘车,用他的苏北话说:“走到哪块,写到哪块。”
作协领导十分重视。学习班除了有王道乾、杨波两位作家负责安排我们的生活学习(请著名作家讲课,参加讨论,面对面指导,或参观访问,观看学习电影等),晚上编辑办公室供大家写作。后阶段正好《收获》《上海文学》两个编辑部均发完稿,魏老、萧岱、罗洪,茹志鹃、欧阳翠、左泥等老作家、老编辑也全部来参加学习班,一对一,或一对二,帮助学员谈构思,反复讨论修改初禞,直至打出小样。现还健在,已105岁高龄的老作家罗洪老师,她当时是两个编辑部小说组组长,她是上世纪30年代与冰心、丁玲齐名的九大著名女作家之一,亲自帮助那位学员,从一堆乱七八糟的用练习簿、毛边纸装订的笔记本写的 40万字的书稿中,沙里淘金,选出15万字,并帮助文字修改,打出小样,准备发表。可是就在这时,作协领导接到上级紧急通知,要开展讨论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创作学习班提前结束。不久一场灾难性的“文革”开始了,巨鹿路675号上海作家协会风云惨变,竟成了文艺黑窝。我们心目中尊敬的老作家,都被批斗,有的竟被迫害至死。
这是个风雨交加的下午,巨鹿路作协大厅,造反派(文艺界造反派进驻作协,这些人是文艺会堂部分职工和京剧院一些武生,专门制造武斗)召开大会,狠批文艺黑线,大会快结束时,站在批判席上的是一群知名作家,其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作家就是我们平时最尊敬的魏老。一个造反派蛮横地按他的头,要他认罪。70多岁高龄的魏老已被整整折磨了一下午,老人脚立不住,往前一冲,一跤跌在地上,当场头破血流。人们都敢怒不敢言。散会了,我拖着沉重的双腿往外走,有人拉了我一把,回头一看是《收获》编辑、作家左泥,他悄声对我说:“你等一下,我到厨房去借辆黄鱼车,我们一起把魏老送回家好吗?”我连忙点头。等人走散了,我忙把魏老扶上椅子。这时,天渐渐暗下来了,门外开始淅淅沥沥下起小雨,魏老的家就住在距作协不远的愚园路愚谷村,我们把魏老送到家里。出来时,心里都像压着一块石头,谁也没有说话。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文革”后期的一个黄昏,我走在愚园路上,迎面遇见一位背部佝偻,步履蹒跚,一头白发的老人,手里提个布袋,一看正是魏老。我忙叫了一声,他端详了我好一会儿,才认出我。他是刚从干校回来,我问候他身体好吗? 他缓慢地说:“上了年纪,体力越来越不行了。” 然后深深叹口气,凄楚地对我说:”我的问题上面还没有作结论,有生之年我总想回一趟故乡绍兴看看。”
为文学事业,忠心耿耿,奋斗一生,做出卓越贡献的老作家,晚景凄凉,我不禁黯然。分別后不久,就传来魏老他没有等到“解放”,抱着终生遗憾而逝世的消息。我怀着无限崇敬、感恩和缅怀之情,禁不住潸然泪下。
(作者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 张 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