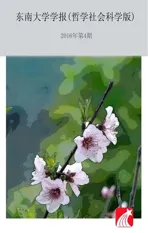中国古代图像艺术中的“异托邦”
——以《神路图》、汉墓帛画和《大威德金刚曼荼罗》为例
2016-08-31郭建平李轶南
郭建平,李轶南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中国古代图像艺术中的“异托邦”
——以《神路图》、汉墓帛画和《大威德金刚曼荼罗》为例
郭建平,李轶南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纳西族的《神路图》、长沙马王堆汉墓画幡和元代藏式缂丝作品《大威德金刚曼荼罗》虽然分属不同的时代、民族、地域与文化,但在空间的谋划布局上却极具可比性,在彰显东方古代社会关于“灵魂”、“秩序”等信念的认识方面也殊途同归,实际上是构想了一个和今世相对的异质空间,即“异托邦”。借助福柯空间理论分析中国古代图像艺术超越时空、族群和文化的特征,可以解释其何以能具有所谓的后现代特征,并探索中国古代绘画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表现规律。①
异托邦;异质空间;《神路图》;汉墓帛画;藏式缂丝画;古代图像
后现代艺术产生于1950年底以后,学者大都认为是对现代主义艺术的反动,没有现代派和现代主义,后现代艺术就不可能产生。但也有一些学者如米勒教授、顾明栋教授等人认为,后现代的艺术特征在前现代、甚至是古代就出现了。[1]我们认为此观点很有道理,因为在中国古代,无论是语言艺术还是视觉艺术都可找到后现代的风格特征。本文仅以纳西族的《神路图》、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画幡和元代藏式缂丝作品《大威德金刚曼荼罗》等为例,分析其超越时空、族群,地域和文化的特征,旨在证明:所谓后现代艺术风格和特征并不一定要以现代性为前提条件,并试图探索中国古代艺术为何会出现类似于后现代的一些艺术特征。
纳西族的《神路图》、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画幡和元代藏式缂丝作品《大威德金刚曼荼罗》是中国不同民族于不同的时代产生的图像艺术,与我们今天所处的后现代社会相去甚远,但根据美国著名理论家詹明信教授在其《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归纳的后现代的几个艺术特征:一、无深度(depthlessness);二、无情感(waningofaffect);三、主体消亡(deathofsubject);四、拼贴与挪用(Pasticheandcannibalization);五、雅俗分野消失(disappearanceofthedividebetween highandlowculture),[2]1-54我们就会发现,后现代艺术的主要特征可在这些古代的图画中找到。既然这些古代绘画中含有后现代艺术的特征,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古代的图像艺术怎么会出现后现代艺术的特征呢?詹明信所说的后现代条件,即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基础与这些绘画的时代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同样,列奥塔的后现代主义的定义“对元叙事的巨大怀疑”也无助于我们找到答案。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的论述也无助于解释古代的艺术。欲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得另辟蹊径。既然图像艺术是视觉艺术,我们不妨从空间和时间的关系方面寻找答案。
《神路图》、汉墓帛画和《大威德金刚曼荼罗》的视觉主体涉及的都是人死后升天的问题,实际上是构想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这一世界既不是一个乌托邦(utopia),也不是一个恶托邦(dystopia),而是一个完全是想象出来的虚幻空间,是一个相对于今世的另类场所,即法国思想家福柯提出的“异托邦”(heterotopia)。在其论文《论另类场所》(OfOtherSpaces)中[3],福柯提出了“异质空间理论”,该理论界定了何谓异质空间,探讨了“异质空间”的内涵,并系统描述了诸如学校、医院、监狱、墓地、剧场、影院、妓院和博物馆等另类场所的六个特点,他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中国古代的图像艺术具有堪称后现代的特征。
一、古代的异质空间
福柯论述的异质空间与基督教的时空观颇为不同,后者把空间看做是时间的附属物,是时间的延续和外在表现,而福柯则为空间加入了历史的维度,认为现代规训权力的形成改变了社会空间的性质与结构,使得空间变为“生命的自由生存权的基本范围”。[4]314福柯“异托邦”的论述,正是在这一崭新的时空观的框架下进行的。他在《论另类场所》(OfOtherSpaces)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异托邦”的概念。福柯以镜子为例指出:与并不真实在场、没有真实位置的乌托邦相反,“异托邦”本身是真实有效的场所,或者说是在真实场所中被有效实现了的乌托邦,它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其实质是空间的权力关系网络。“异托邦”的概念对于思想界的影响极其深远,它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启发:“即我们似乎熟悉的日常空间是可以做间隔划分的,就是说存在着不同的异域,一个又一个别的场合。存在某种冲突的空间,在我们看见它们的场所或空间中,它同时具有神话和真实双重属性。”[5]福柯同时归纳了“异托邦”的六大特点:一是文化多元本身就是“异托邦”;二是不同时代所处的每一个相对不变的社会也是“异托邦”;三是在同一真实空间中同时包含若干自相矛盾、相互冲突的空间;四是异托邦在隔离空间的同时也将时间加以隔离;五是不同的异托邦自身是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系统,相互之间既隔离开来又互相渗透;最后一点是异托邦在创造一个虚幻空间的同时,这一虚幻空间却揭示出真实的空间。[4]我们如果用福柯归纳的几个特征来研究中国传统的一些图像艺术品,如《神路图》和马王堆汉墓帛画等(图1、图2),就会发现,这些图像艺术虽然来自不同的时代、民族、社会、和文化,但两者所传达的思想和艺术表现特征等颇为相似。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相同之处呢?我们认为,使得这些古代图画的视觉表征在内容以至于形式上殊途同归的内在逻辑就是异质空间的思想。
中国纳西族的《神路图》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画幡虽然来自不同的时代、社会、民族、文化,而且在具体造型上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在空间的划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值得注意的是,两幅图像在彰显东方古代社会关于“灵魂”、“死后世界”等信念的认识方面也似乎做到了殊途同归。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两幅图像中又都有灵异动物的存在。通过对二者进行比较,可以找到二者背后规律性的视觉表征原理。《神路图》和汉墓帛画的主题涉及的都是人死后的空间问题,实际上是构想了一个“异托邦”(heterotopia)。“异托邦”的空间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中国古代的图像艺术具有超越时空、族群、文化的特征。

图1 《神路图》地下鬼怪

图2 马王堆T形帛画
西方社会学家古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指出,人类古代社会是“命运”的社会,而现代社会则是一个专家主宰的“风险”社会。在此过程中,那种融聚一团的“命”观念衰落了,[6]而在“命运”主宰的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之一就是:在现实社会中,生命力脆弱的民众有着强烈的死后世界意识,总会采取种种形式确立一个意念中的合理的时空秩序和生命秩序,图像形式就是其中的形式之一,纳西族的《神路图》便是此类图像形式的典范,而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画幡也可以算作此类图像形式的典型代表,二者在具体造型上虽然是有区别的,但在彰显东方古代社会关于“灵魂”、“死后世界”等信念的认识方面却做到了殊途同归,即福科在“异托邦”的理论中论及的一大类——乌托邦(utopia),也就是类似于或曲折地反映社会的真实空间,“乌托邦是没有真实地点的场所,与社会的真实的地点有着一种一般来说直接或颠倒的类比,它们展现的是完美的社会,或者说是社会的颠倒,但是,无论怎么说,这些乌托邦本质上都是非现实的空间。”[6]231《神路图》和汉墓帛画表现的就是这种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存在、但有着类比关系的空间。
二、异质空间的划分
“异托邦”不仅包括“乌托邦,”还包括“恶托邦”(dystopia),即理想世界的反面,再加上人间世界,就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复合空间。三层空间的说法普遍存在于古代社会及受宗教影响的现当代社会。例如“天堂”的概念源自基督教的《圣经》,不论古今,基督教都认同存在天堂、人间、地狱,构成了西方意义上的三层空间;而佛教世界也有对等的空间概念——佛界、尘世和阎罗殿。实际上,此三层空间的概念不只体现在系统的、自觉的、理论化的高水平的社会意识——宗教中,也存在于自发产生的、不系统的、不定型的,属于较低级的社会意识——民间信仰、巫术中。而且,其落实在文字中,也落实在图像里,例如纳西族的《神路图》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画幡。
马王堆汉墓出土画幡可划分为三个空间:上层代表天上,中层代表人间,下层代表地下;而《神路图》也有类似的空间划分概念,全图采用连环画的形式,世界的纵向空间在概念被区别为地狱界、人间界、自然界、神界四个层次,甚至还有二层空间之说,也有学者认为《神路图》天上、地上和地下三界(三层空间说)。天上界住着神灵,地上界所住者为人类,地下界为鬼怪(图1、图2),其实从其画面构图看,更符合三层空间之说,自然界、神界这两个层次在布局上可以视为一体;所以,虽然《神路图》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画幡》画面细节有区别,但二者宇宙时空观还是有契合之处的(至少存在着天地二元之分),二者画面布局都可划分为上中下三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神路图》不单指某一幅图,而是指这一类纳西先民创造的美术作品,指的是一种形式。从图像整体上进行分析,此图中山及动植物的形象是抽象的、二维的,与纳西族的象形文字有“亲缘”关系,色彩对比度强烈,装饰意味明显。图中的神山形象被视为通往“神地”的必经之路,虽然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画幡中没有看到神山形象,但在汉代其他图像中,特别是在墓室遗留的艺术作品中,也寻得类似的神山或者称之为仙山的形象。据巫鸿先生总结,汉墓室中描绘的山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鸟瞰式全景构图,描绘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被称为“理想家园”的组成部分;第二种则是“非写实”性的山,其造型并非取自现实世界里,而是源自文字,与仙道有关的动植物或是抽象装饰的图案。[7]246若将《神路图》中神山的形象与汉代墓室艺术作品中山的形象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神路图》中山的形象属于两种类别的结合体。究其原因,首先,《神路图》整体绘画风格较为抽象,不在于描绘细致的物体造型。这点仿佛能证明七座神山的造型是第二种类型的写照。另外,东巴长诗《鲁般鲁饶》开篇之句说到:“很古很古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从居那若罗神山上迁徙下来”[8]1,而七座神山是围绕着居那若罗山的。由此可见,祖先之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理想家园”,这不仅符合第一种类型的描述,而且带有异托邦的理想类型——乌托邦的内涵。
三、异质空间的功能
异质空间的作用是什么?这可以在福科对“异托邦”的概念性探讨中获得启迪。福科认为,人类生活在空间之中,因为空间的原因人类自身而得到了延伸,生命的结束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就是消逝于曾经栖生其中的空间:“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空间,使我们自身得到延伸,我们的时间和历史在其中发生,那吞噬和侵蚀我们所在的空间自身也就是一个异质空间。换言之,我们并不是生存于某种可以置放个体或事物的虚空之中。我们也不是生存于染上了形形色色的光彩的虚空之中,而是生存于一系列关系之中,这些关系描绘出彼此不可还原和绝对不可重叠的场所。”[6]从空间关系的角度来看,延续生命的一个似乎可行方法就是延续生命栖息的空间,这似乎是《神路图》和汉墓帛画最基本的功能,也就是将个体存在的空间从现世延伸到来世的天堂。这就是二幅图像为何都有“引魂升天”的共同意象。
异质空间延伸人类自身作用在中国古代绘画中得到体现的个案举不胜举,敦煌壁画中有较多鲜明的例子,在此以元皇家藏式缂丝作品《大威德金刚曼荼罗》为例,该艺术品制作于1328年左右,现存于纽约大都会艺术馆,画面坛场中,元帝王的“织御容”显现在曼荼罗的宇宙实相或通灵时空中,并处于捐赠人的位置。曼荼罗中心是野牛形金刚——大威德金刚(意味着不灭),是象征智慧的文殊菩萨的忿怒相。根据藏传统,慈悲的文殊菩萨可化身为具有威慑力的大威德金刚(死亡的毁灭者),去镇伏阎罗王(死神)。”[9]此幅画虽然画的是按尊卑秩序安排位置的帝王家族像,曼荼罗的宇宙实相或通灵时空的中心式构图的位置法,营造了坛场的感觉。还有就是据台北故宫所藏《元代皇后像册》,台北的元代帝后像属小型御容出现的皇领缘纳石失采用的鹦鹉题材也是有“异质空间”含义的。《阿弥陀经》里的西方极乐世界,也即鹦鹉栖身之处。皇后御容用它,或有“(佛)来迎(亡者)往生(西方净土)”之意;而唐卡雏形在远古西藏象雄苯教文化中出现,后来在吐蕃时期形成了唐卡的基本样式和表现形式,公元7世纪唐卡绘画有同时具备宗教的修炼观象和审美功能的艺术,因此在其审美观念和表现语言中由于受藏传佛教文化之影响,人们在“实有”的物象中去把握“空无”的佛性,因此,借助绘画语言表现其内涵和理念时,善用象征性、寓意性语言、采用主观夸张、想象的手法延伸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具有的空间感知。在具体的绘画形式里把三度世界转化成平面中的形象,以色彩、形状、大小或定向的相似性和非相似性互相分离和组合在一西方圣像画的“正中式”布局构图给人以庄重、稳定、饱满与秩序感。在表现本尊佛、菩萨寂静相、怒相和护法神、祖师等形象以及曼陀罗(坛城)的题材中常使用,这种构图根据其表现的内容通把所要表现的本尊佛、菩萨、祖师形象安排在画面中心位置,也就是我们通常刻画心理活动时认识到这一部位是画面视觉的最佳点,也是视觉吸引力最强的地方。其中心形象一般占据画面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空间,从上中至左、右、下的次序依次对称安排绘制相关佛、菩萨的形像,保持完整、无缺,避免重叠,以此体现一种圆满精神观象的神圣感。坛城(曼陀罗,佛教的大圆满和密宗的宇宙中心的寓意),是一种密宗修炼的观相图形,类似唐卡布局法的绘画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恰与福柯所言的异质空间有契合之处。[9]对照《大威德金刚曼荼罗》和《元代皇后像册》的空间谋划布局,我们不难找到相似之处(图3),而这些相似之处正好说明古代那些既反映现世社会又有别于现实生活的场景,都体现了人们为了追求超越今生而构建多种多样的异托邦的想象性创造。

图3
四、结 语
总而言之,纳西族的《神路图》、汉族汉墓画幡和藏族的《大威德金刚曼荼罗》在具体造型上虽然是有区别的,但是二者都表现了强烈的地域特色。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画幡更多地受楚地神秘文化及文学文本的影响,例如《楚辞》;《神路图》受诸多原始宗教、巫术及其本民族象形文字的影响;而《大威德金刚曼荼罗》则明显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但是,促使三者超越其地域性的共同表现动因正是人们对来世的异质空间的猜想。的确,《神路图》和马王堆汉墓帛画的视觉表征涉及的都是人死后的空间问题,实际上是构想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这一世界既不完全是一个乌托邦(utopia),也不是一个恶托邦(dystopia),而是一个完全凭想象虚构出来的异质空间,是一个相对于今世的另类场所,其纷繁复杂的视觉表征所传达的思想和显示的特征与福科的“异托邦”又有所不同,因为福科的理论主要研究的是人类社会中虽是另类、却又基本真实存在的空间。他在其文章中将人类关注的空间分成两大类:“内在空间”和“外在空间”,并坦言,他的文章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外在空间”。而《神路图》和马王堆汉墓帛画主要关注的是想象出来的另类空间,也就是福科所说的“内在空间”。福科对“内在空间”有一段富有诗意的描绘:“我们是生活在充满了种种品质的空间,这些空间也许十分虚幻神奇。我们最初感知的空间,我们梦中的空间,和充满激情的空间,藏匿着似乎是内在的品质;它是一个轻盈的、虚无缥缈的、透明的空间,或者说是一个黑暗的、粗糙的、不通畅的空间。它是一个来自上苍的空间,一个巅峰林立的空间,或者反其道而行之,是一个来自地下的空间,一个泥沼的空间,一个像是闪光流水那样的流动空间,或者是一个像石头或水晶那样坚实凝固的空间。”[6]
显然,《神路图》和马王堆汉墓帛画所展现的就是艺术化以后的“内在空间”,正因为内在空间的视觉表征不必拘泥于对现实空间的模仿或反映,即使是使用现实世界存在的事物,也是不顾时空规律、逻辑次序、因果关系而将其并置,因而颇有点儿类似后现代艺术拼贴与挪用(pasticheandcannibalization)①詹明信教授在其《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把后现代的艺术特征概括为几大特点,其中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拼贴与挪用(Pasticheandcannibalization)。的技法。但总体而言,福科的“异托邦”(heterotopia)理论对于研究像《神路图》和汉墓帛画之类的图像艺术,仍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因为他构思了一个有关异质空间既开放又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有一种与其他空间发生联系的功能,而这种功能散布在乌托邦(utopia)和恶托邦(dystopia)这两个极端之间。以此观察《神路图》、汉墓帛画和《大威德金刚曼荼罗》似乎可以接近古代艺术家在做艺术表征时的原初动机。本文对二者进行初步比较,只是略申管见,“异托邦”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发掘中国古代图像艺术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找出视觉表征背后的艺术规律。
[1] J.HillisMiller.Reading(about)ModernChineseLiteratureinaTimeofGlobalization[J].ModernLanguageQuarterly,2008(1).
[2] FredricJameson.PostmodernismorTheCulturalLogicofLateCapitalism[M].DurhamandLondon:DukeUniversityPress,1991.
[3] MichelFoucault.OfOtherSpaces[M].TheVisualCultureReader,London:Routledge,2002.
[4] 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 尚杰.空间的哲学:福柯的“异托邦”概念[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6] AnthonyGiddens.TheConsequenceofModernity[M].Cambridge:PolityPress,1990.
[7] 巫鸿.礼仪中的美术[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8] 鲁般鲁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9] 方闻.宋元明帝王像[J].郭建平译,艺术百家,2008(8).
J20-02
A
1671-511X(2016)04-0095-05
2016-03-08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成果之一。
郭建平,女,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艺术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