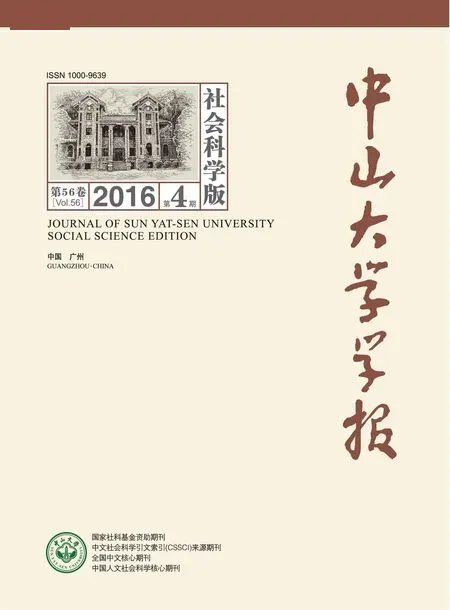二十世纪数学基础论争中的现象学*
——从胡塞尔、贝克尔与外尔的思想关联来看
2016-08-09倪梁康
倪 梁 康
二十世纪数学基础论争中的现象学*
——从胡塞尔、贝克尔与外尔的思想关联来看
倪 梁 康
摘要:20世纪的数学基础论争,不仅在希尔伯特和胡塞尔两位老师之间进行,也在希尔伯特与胡塞尔的学生贝克尔之间、在胡塞尔与希尔伯特的学生外尔之间以及在两位学生之间进行。这个争论不仅涉及数学中的形式主义与直觉主义的分歧,也涉及现象学哲学中的观念现象学、解释现象学和语言现象学的差异与分歧。最后,专业数学家的态度与专业哲学家的态度之间的基本区别与对立,也通过对数学基础的讨论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揭示。
关键词:数学基础; 直觉主义; 形式主义; 现象学直观
一
海尔曼·外尔(Hermann Klaus Hugo Weyl,1885—1955)自1904年起便在哥廷根大学随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学习。由于他对哲学也感兴趣,因而当时在哥廷根去旁听过胡塞尔的哲学课程。他还在胡塞尔的课上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海伦娜。她是地道的哲学生,学习现象学,后来还翻译了西班牙哲学家伽塞特(JoséOrtegayGasset,1883—1955)的许多哲学著作。主要是因为她的缘故,外尔一家与胡塞尔一家保持了相当密切的关系。外尔于1908年2月18日在哥廷根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胡塞尔曾担任答辩委员会的主席①参见K. Schuhmann, Husserl-Chronik. Denk-und Lebensweg Edmund Husserls, Husserliana-Dokumente, Band I, Martinus Nijhoff: Den Haag,1977, S. 113.。在上述意义上,外尔基本上可以算是胡塞尔哥廷根时期的学生。
外尔1908年在希尔伯特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考试,1910年完成任教资格论文考试。此后他在哥廷根担任三年的私人讲师,1913年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获得几何学教授的位置,成为爱因斯坦的同事。外尔后来也是最早出版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教科书的人之一。1920年,母校哥廷根大学聘请外尔去接任费利克斯·克莱因的教席,遭他拒绝②因而胡塞尔1920年6月5日致外尔的信中曾询问:“那么哥廷根呢?!”(E. Husserl, Briefwechsel, 10 Bände, Husserliana-Dokumente, Bd. III, in Verbindung mit E. Schuhmann hrsg. von K. Schuhman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Boston/London, 1994, Bd. VII, S. 289)。1930年,哥廷根大学再次聘请他接替老师希尔伯特的教席,这次他无法拒绝,但几年后他发现这是他的失策,因为此时德国已经处在日益浓烈的纳粹反犹氛围中,而他的太太海伦娜是犹太血统,时时感受到威胁。外尔在哥廷根仅仅工作了三年。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以及同年4月反犹政策出台后,他不得不于这年10月携家离开德国,移民美国,通过爱因斯坦的斡旋而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教职*由于外尔的离去,曾经是数学活动最强中心的哥廷根大学数学研究所基本上名存实亡。纳粹教育部长B.鲁斯特曾于1934年询问希尔伯特:数学研究所是否因为犹太人和犹太人朋友的离开而受到损害?希尔伯特回答:“受到损害?没有受到损害,部长先生,它都已经不存在了!”(参见Hans-GüntherSchroller(Hrsg.),Die Geschichte der Verfassung und der Fachbereiche der Georg-August-Universität zu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Göttingen, 1994, S. 155)。此后,胡塞尔的儿子、罗马法和教义学领域的法学教授格哈特一家1936年3月移民美国,最初显然在外尔那里得到了帮助。马尔维娜在致法伯的信中提供的格哈特在美国的联系地址,便是外尔在普林斯顿的住址*胡塞尔太太在致美国现象学家马文·法伯的信中给出的通邮地址是:Professor Gerhart Husserl, 220 Mercerstreet, Princeton NJ. C/O Prof. Hermann Weyl.她在信中还写道:“外尔的名字您不会不知道,他是目前最重要的活着的数学家之一,并且直至1933年都是哥廷根的教授。”(E. Husserl, Briefwechsel, Bd. IV, S. 71)。胡塞尔自己则在这年3月14日致其家庭朋友阿尔布莱希特的信中写道:“格哈特已经在3月3日到达纽约,并且受到他的东道主外尔的接待。”*E. Husserl, Briefwechsel, Bd. IX, S. 125.外尔在普林斯顿一直工作到战后的1951年。此后他又回到苏黎世,并于1955年在苏黎世死于突发心脏病,享年七十整。
二
通过旁听胡塞尔的课程以及与胡塞尔家庭的交往,外尔受到的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十分深入。它首先使外尔摆脱了他最初持守的实证主义立场,而且此后这个影响也贯穿在他一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思考之始终。“外尔毕生始终是现象学哲学的拥护者,他自己也在极为熟练地运用它。”*D. Van Dalen, “Fourlettersfrom Edmund Husserl to Hermann Weyl”, in: Husserl Studies, 1:1—12 (1984), p. 3.后面我们还会对此问题展开讨论。外尔曾答应胡塞尔将他的重要文章《论数学的新基础危机》交由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发表,后来还因为改登在1921年的《数学杂志》上而使胡塞尔感到“非常遗憾”*H. Weyl, Über die neue Grundlagenkrise der Mathematik“, in:Mathematische Zeitschrift 10 (1921), S. 39—79; E. Husserl, Briefwechsel, Bd. VII, S. 294.。而此前,还在1920年6月5日的信中,胡塞尔就在收到外尔寄赠的《空间·时间·物质:关于广义相对论的讲座》第3版后回信说:“整个空闲的下午我都坐着阅读您的著作,带着递增的喜悦浏览它。这部著作是多么接近我的一门由哲学精神来承载的物理学之理想啊。我们的时代使这样一门普全的、受最高观念引导的对世界的数学形式的认识得以可能,而我居然还可以体验到它,这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事情!”*E. Husserl, Briefwechsel,Bd. VII, S. 289.
除了胡塞尔之外,最早注意到外尔思想与现象学哲学之关联性的很可能是胡塞尔在弗莱堡期间的两位重要助手奥斯卡·贝克尔和马丁·海德格尔。贝克尔与外尔的思想交集与相互影响我们在后面还会专门论及;海德格尔这方面则因为贝克尔的影响,1924年之前便对外尔的研究以及外尔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介绍有所了解。海德格尔在这年撰写的长文《时间的概念》(实际上是《存在与时间》的初稿)中曾就当时自然科学中的时间研究做过一个特别说明:“由于相对论在思义(besinnen)时间定义的基础,因而‘时间’本身必定会在其研究中变得更为清晰可见。尤其是在其原则性思考的过程中受到过现象学的训练的H.外尔,他的研究具有一种将数学越来越源始地指向时间现象的倾向。”*M. Heidegger, Der Begriff der Zeit (1924), GA 64,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2004, S. 79.
海德格尔的这个说明和提示涉及外尔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理解与解释。但在外尔那里,最能体现其现象学训练的应当是他在数学领域中的直觉主义思考方向。从1921年外尔写给胡塞尔的一封信看,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得到了虽然是大致的、但却是直接的表露。
胡塞尔于这年终于完成《逻辑研究》第2卷第二部分(第六研究)的修改,出版了它的第2版。而这本书的第1卷和第2卷的第一部分(前五项研究)的第2版早已在1913年便完成修改并出版。就此而论,《逻辑研究》的第1版和第2版都是分别在两个年份出版:第1版分别为1900年和1901年,而它的第2版分别为1913年和1921年。相隔如此之久,外在的原因自然与在此期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但内在的原因则涉及胡塞尔个人的兴趣转向。他在1931年1月6日致普凡德尔的信中曾说:“在接下来的战争年代中,我无法为逻辑现象学付诸那种激情般的参与,而没有这种参与,在我这里也就不可能产生成熟的工作。”*[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逻辑研究》第2卷第二部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B III。胡塞尔这里所说的“逻辑现象学”,与他在1930年11月16日致米施信中所说的“形式逻辑和所有实在本体论”是一致的。他在信中承认自己1913年之后“只想对一门超越论的主体性学说、而且是交互主体性的学说进行系统的论证,而原先对形式逻辑和所有实在本体论所抱有的兴趣,现在都已荡然无存”*E. Husserl, Briefwechsel, Bd. VI, S. 282.。而在1918年4月10日致外尔的信中,胡塞尔也有类似的表达:“我没有找到时间和宁静来将这些[数学—逻辑学的]思想系列完全贯彻到底(因为超越论现象学的建构对我来说必定是更重要的)。”*E. Husserl, Briefwechsel, Bd. VII, S. 288.
但胡塞尔还是将他的《逻辑研究》结尾卷的第2版寄给了还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任教的外尔。外尔在收到赠书后于1921年3月26—27日致函胡塞尔,在感谢的同时也讨论了他的阅读感受,包括对胡塞尔本质直观的理解:
您的《逻辑研究》结尾卷给我和我的太太带来了极度的喜悦,而我们满怀敬意地感谢您的馈赠!我现在才了解了其中的内容(如果可以将我至此做出的如此肤浅的研究称作“了解”的话);尽管您从现在的立场出发对《逻辑研究》做了所有这些责难,我还是在这部为认识论中的纯粹实事性精神做出如此重大贡献的著作的最终结果中发现,在这里极为清晰和精辟地提出了关于明见性和真理的关键明察以及关于“直观”远远超出感性认识的认识。我基本上具有这样的印象:《逻辑研究》具有一个较之《观念》更为整全的特征,是对一个在某种高度获得的立足点的宁静扩展和确保,而《观念》(就其现在的情况而言)明显具有一种新的在途中的特征。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您也不准备在下一辑的《年刊》中为我们出版它的续篇。——石里克的可笑评论也让我感到恼火,尤其是因为他的著作在引领的理论物理学家那里还以可理解的方式获得了最大的赞同。*E. Husserl, Briefwechsel, Bd. VII, S. 290f.
由于《逻辑研究》的第六研究第二篇将“范畴直观”引入现象学,因此被视作胡塞尔现象学方法论的首次正式表达。外尔对这个部分尤为感兴趣,他理解的胡塞尔的“直观”就是指“范畴直观”,即“远远超出感性认识的认识”。这里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对胡塞尔本质直观的双重领会:其一,直观就已经是一种认识;其二,直观不仅仅是感性的认识。在这两点上,现象学的认识论都与逻辑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处在针锋相对的立场上,后者否认范畴直观的存在,而且坚持认识只能是由判断或命题提供的。因而在当时都十分活跃的现象学与逻辑实证主义两个流派之间难免会产生冲突。外尔信中的这个段落结尾处之所以提到莫里茨·石里克,就是因为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2卷第二部分“前言”中对其提出相关的回应反驳:石里克在其《普通认识论:自然科学的专论与教程》第1卷(柏林,1918年第1版)中带着寻衅的口吻指责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理论。他在那里写道:胡塞尔的《观念》“声言有一种特殊的直观存在,据说它不是心理实在的行为;如果有人无法找到这样一种并不包含在心理学领域中的‘体验’,那么他便会被告知,他没有理解这门学说的意义,他没有深入到正确的经验观点和思维观点之中,因为据说这需要付出‘专门的和艰苦的研究’”。胡塞尔在第六研究的“前言”中对此做了反击:“某些作者做起拒斥性的批评来是多么舒适随意,他们的阅读是怎样的仔细认真,他们会果敢地将什么样的荒谬归属于我和现象学。”并且指出:“M.石里克的案例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偏离,而是他的整个批评都建立在一些歪曲意义的偷梁换柱做法之基础上。”*参见[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逻辑研究》第2卷第二部分,B III—IV;详细讨论,也可以参见倪梁康:《作为先天综合判断的本质直观是可能的吗?——对石里克、维特根斯坦与胡塞尔之间争论的追思》,《哲学与文化》第381辑,2006年2月出版,第3—21页。
外尔的妻子海伦娜在信后的附言中也对胡塞尔做了比她丈夫在情感上更为强烈的声援:“我被迫极为深入地阅读了石里克的《认识论》,并且对它令人发指的不当思考的认识论和现实论感到十分难受,我从那里逃出并进入《逻辑研究》的坚定而明亮的氛围之中,就像是得到了解脱。”*E. Husserl, Briefwechsel, Bd. VII, S. 292.
事实上,外尔在现象学的认识论与逻辑实证主义的认识论的两个分歧方面都曾针对逻辑实证主义表明过自己的现象学立场:在此之前,他在1918年的《空间·时间·物质》中批评实证主义者将意识体验归结为单纯的感觉材料*参见H.Weyl, Raum, Zeit, Materie-Vorlesungen über Allgemeine Relativitätstheorie, 3. Auflage, SpringerVerlag: Berlin/Heidelberg,1919, S. 3.;此后不久,他又发表关于石里克的《普通认识论》的书评,相当强烈地反驳石里克的“符号学”认知观*参见H. Weyl,“Review of M. Schlick’sAllgemeine Erkenntnislehre”, in: Jahrbuchüber die Fortschritte der Mathematik 46, 1923/24, S. 59f.有研究者认为这篇书评是为了维护胡塞尔而撰(参见Richard Feist,“Weyl’s Appropriation of Husserl’s and Poincaré’s Thought”, in: Synthese, Vol. 132, No. 3,Sep., 2002, p. 279)。。
与直观问题相关,还值得注意的是外尔在信中接下来所报告的自己的几何学研究进展,以及其中提出的对直观的有限性的问题:
我最近在努力从最终的、可以进行数学分析的根据出发来领会空间的本质。这里涉及的是与赫尔姆霍茨当时在涉及空间问题时所提出的相似的群论研究;但如今需要考虑由于相对论而变化了的境况,它也使一种更深的奠基成为可能。空间的先天本质以强制的方式区分于它的后天本质,前者表现在主宰着每个空间位置之度量的相同本性中,后者自身是自由变化的,表现在受物质规定而在各个节点中的这些度量的相互定位的本性中。恰恰因为人们将这些定位预设为可自然变化的,而不将那些特殊的、对于欧氏距离几何而言特征性的定位当作固定被给予的,所以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度量的本性就是它实际上之所是,而不是无限多的其他数学可能本性中的一个。我在这里无法抵御这样一个印象,即在现象学的先天之外还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先天,一种必然性,它并不是从给出相关本质的直观出发而得以明了的必然性,而是从这个本质的被把握到的形而上学含义中才产生出来的必然性。但在我看来,在把握含义方面,经验认识也起着原则上不可或缺的作用。*E. Husserl, Briefwechsel, Bd. VII, S. 291f.按,重点号为引者所加。外尔接下来还谈到“物质”的概念:“自《空间·时间·物质》第3版以来,我的关于物质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狭义相对论用来取代‘实体—观’的‘场—观’在物理学上似乎是无效果的,并且在广义相对论中失去了其说服力。我相信,广义相对论迫使人们将物质思考为一种介质(Agens),它本身不是空间的,只有一个特定的空间环境(这个环境是它的作用首先展示于其中的区域,而后这些作用在场中以光速扩散)。这个问题对于因果性的问题域具有重要意义。”
外尔根据相对论而对空间的本质及其把握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里已经可以看出他对几何基础问题的理解。胡塞尔似乎没有对此信做出回应,原因可能在于,如前所述,他将超越论现象学的建构看得更为重要,没有找到时间和宁静来深究数学—逻辑学方面的想法*参见E. Husserl, Briefwechsel, Bd. VII, S. 288.。但一年之后,胡塞尔专门致函外尔,向他介绍自己的学生贝克尔当年的任教资格论文《对几何学及其物理学运用的现象学论证论稿》:
贝克尔博士业已完成并提交到系里的任教资格论文表明,我的弗莱堡圈子对您的研究工作的兴趣是多么强烈。我已经深入研究了他的论文并做了最高认可的评语。它差不多就是对爱因斯坦的和您的发现与我的自然现象学研究的一个综合。它试图在深入而原本的阐释中做出这样一个证明:爱因斯坦的理论,但只有在它们通过您的无穷小几何研究而得到补充和奠基之后,会展示出的自然的“结构规律性”(相对于特殊的“因果”自然规律性)的那种形式,它出于最深刻的超越论—构造的原因而必须作为必然的形式来要求,即:(就其形式而言)惟一可能的和最终明了的形式。如果证明了,一个自然是出于现象学的先天理由而非出于实证主义的原则而在要求一种相对论结构,而且一门完全理解的和最终精确的自然科学惟有如此才是可能的,那么爱因斯坦会怎么说。贝克尔博士认为他在其论文的第一部分也必须深入探究对模糊的经验被给予性连同其模糊的连续性的理论化的一般基本问题并认为必须构想一门连续统的构造理论(通过极限和概算对含糊的连续统的合理把握)。他在那里也试图证明:布劳威尔—外尔的理论仅仅与一种构造现象学的源泉研究的特定的和不可避免的要求相符合。*E. Husserl, Briefwechsel, Bd. VII, S. 293f.
胡塞尔在这里将贝克尔的论文称作“对爱因斯坦的和您的发现与我的自然现象学研究的一个综合”。很难说这只是胡塞尔私下里的玩笑。贝克尔本人在论文中的确仅仅特别感谢了两个人:“首先是埃德蒙德·胡塞尔,他的研究是这篇论文得以立足的基础。其次是海尔曼·外尔,他对数学—物理学问题的阐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对于现象学研究来说如此合适的材料,而且他自己也离现象学如此之近。”*Oskar Becker, BeiträgezurphänomenologischenBegründung der Geometrie und ihrerphysikalischenAnwendungen(Erschienen in: JahrbuchfürPhilosoph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Forschung, Bd. VI, 1923), S. 388.关于贝克尔以及他在其另外两部代表作《数学实存》(1927年)与《论模态逻辑》(1930年)中的相关现象学思想,笔者会在《现象学的数学哲学与现象学的模态逻辑——从胡塞尔与贝克尔的思想关联来看》的文章中另做扼要阐释。
从胡塞尔的信中可以看出,贝克尔与外尔当时尚未建立私人的联系,但贝克尔在这篇任教资格论文中已经对外尔有了十分明确的诉诸,主要是因为外尔的现象学思想背景。还在1918年出版的《空间·时间·物质:关于广义相对论的讲座》引论的开篇,外尔就已经指出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对他的影响:“对这些思想的精准把握最紧密地依据了胡塞尔:《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1卷,哈勒,1913年)。”*参见Hermann Weyl, Raum · Zeit · Materie——VorlesungenüberAllgemeineRelativitätstheorie, Springer: Berlin/Heidelberg, 1919, S. 264.但外尔的胡塞尔思想背景实际上很少被专业数学家们关注。对他与胡塞尔思想的讨论大多出现在科学思想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的著述中。原因何在?很重要的一点可能在于,专业数学家们大都不会关心数学的哲学层面。而外尔对其哲学家的称号是深以为荣的。如果外尔曾说“我们是以一种从希尔伯特那里获得的精神来从事数学”*Hans-GüntherSchlotter (Hrsg.), Die Geschichte der Verfassungund der Fachbereicheder Georg-August-Universitätzu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Göttingen, 1994, S. 151.,那么他也一定会说,我们是以一种从胡塞尔那里获得的精神来从事哲学。在他临终前一年(1954)写下的一篇文章《认识的统一》中,他列出的所有认识所依据的第一个基础就是“直观”,并且同时写道:“直观(Anschauung),心灵原本对被给予它的东西的‘看’的行为;在科学上局限于可指明之物(Aufweisbare),但事实上远远越过了这些界限。在包括这里的胡塞尔现象学本质直观(Wesensschau)在内的直观中我们究竟能够走多远,我现在宁愿按下不表。”*H. Weyl, Mind and Nature-Selected Writings on Philosophy,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a.a.O., p. 202.而在同年于瑞士洛桑大学所做的《认识与思义》的讲演中,他还回忆说:“是胡塞尔将我带出实证主义,使我能够再次随心所欲地观看世界。”*H. Weyl,“Insight and Reflection”, in: Mind and Nature——Selected Writings on Philosophy,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Pesic,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and Oxford, 2009, p. 209.该文最初为德文:“Erkenntnis undBesinnung (EinLebensrückblick)”, in: StudiaPhilosophica, 1954/1955. GA IV, 631—649.
三
无论如何,尽管是希尔伯特的学生,外尔从一开始而且在总体上还是被视作直觉主义者,因而他常常与布劳威尔一起被放在与希尔伯特形式主义相对立的位置上,甚至在贝克尔1927年发表的《数学实存》中也常常如此*O. Becker, Beiträge zur phänomenologischen Begründung der Geometrie und ihrer physikalischen Anwendungen, a.a.O., S. 404, S. 415, S. 432;MathematischeExistenz. Untersuchungen zur Logik und Ontologie mathematischer Phänomene (Erschienen in: 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Bd. VIII, 1927),S. 517.。这应当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尤其是范畴直观的思想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因而外尔在20年代的基本立场也可以被称作“现象学的直觉主义”。胡塞尔的影响最明显地表现在1918—1922年期间。此后外尔已经处在一个很难准确定义的位置上:在“被动的直觉主义”和“主动的形式主义”之间?或在形式主义与构成主义之间?*对外尔的思想发展和变化总体说明,可以参见Norman Sieroka, “HusserlianandFichteanLeanings: Weyl on Logicism, Intuitionism, andFormalism”, in: PhilosophiaScientiae 13 (2):2009, pp. 85—96.实际上,当胡塞尔1922年向外尔通报贝克尔的成果时,外尔已经差不多离开了他的直觉主义现象学的立场。
首先注意到外尔的数学哲学基本立场之转变的是贝克尔。很可能是通过胡塞尔的介绍,贝克尔在任教资格论文发表后与外尔建立联系且交往密切,两人对彼此的立场及其变化互有了解,而且显然也互有影响。贝克尔在1926年8月22日写给他的师兄迪特里希·曼科的信中报告说:“外尔如今已不再是直觉主义者了,而是十分接近希尔伯特,参见他的最新论文《数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哲学》(1926年)。”*O. Becker,“Briefwechsel mit Dietrich Mahnke”, in: Volker Peckhaus (Hrsg.),Oskar Becker und die Philosophie der Mathematik, Wilhelm Fink Verlag: München, 2005, S. 246.但贝克尔也注意到,外尔对希尔伯特的形式主义也仍然抱有疑虑。贝克尔在同一封信中记述说:“8月我曾与外尔谈过,他对我说,他今天仍然完全赞同我对希尔伯特的批评。他也常常问起他(希尔伯特)的‘理想陈述’所指为何,而希尔伯特‘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但尽管如此,即使希尔伯特‘数学’在本体论上的完全不可解,外尔还是认为一种符号的物理学的认识是可能的,但他认为这种认识近似于自由创造的、艺术的活动。”*O. Becker, “Briefwechsel mit Dietrich Mahnke”, in: a, S. 247.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外尔已经不再完全是直觉主义者,但他也不是完全的形式主义者。只是在总体上,他开始从偏向布劳威尔—胡塞尔的—极转而偏向希尔伯特的一极。他在同一时期致贝克尔的信中相当清楚地表达了他的相关立场和想法:
对我来说,布劳威尔—希尔伯特的战斗当然具有十分原则性的意义。我太是数学家了,因而无法隐瞒这样的印象:布劳威尔的数学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且它无法贯彻下去。我在这点上是历史信徒,而且是虔诚的世俗儿童,因而我与希尔伯特一样相信,成功是决定性的。如果希尔伯特战胜了布劳威尔,那么这对我来说同时就意味着,现象学作为哲学的基本科学就完结了……对我来说,作为认识论主要问题的理论构建将会显露出来,它最终不会回到作为绝对无法逾越范围的任何直观基础上。现在我开始会怀疑这样的企图,即用现象学来取代在莱布尼茨那里直观被给予之物建基于其上的形而上学支撑。*O. Becker, “Briefwechsel mit Dietrich Mahnke”, a.a.O., S. 249f.
在这里,外尔将超出直观领域以外的理论建构的形式系统(例如数学中的超穷构成物和超穷数理论)视作某种意义上的数学的形而上学,并因此将它与数学的直观现象学相对置。甚至在外尔的信中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可能需要用数学的形而上学来为数学的现象学奠基,而不是相反。后者看起来已经通过希尔伯特的工作得到了论证:无矛盾性证明并不需要那个有待被证明为无矛盾的领域的直观性*这里需要留意的是“直观性”的确切含义。我们后面还会讨论这个问题。。
贝克尔清楚地看到了外尔指出的可能性,而且很大程度上予以认可。他在给现象学圈内人曼科的信中评论:
这里关系的是现象学方法本身的某种危机。如果外尔在这一点上是合理的,即直觉主义者布劳威尔无法承担理论物理学,那么也就必须认为,胡塞尔“经典”意义上的现象学无力为自然认识的现代形式提供保证和做出最终阐明。*O. Becker, “Briefwechsel mit Dietrich Mahnke”, a.a.O., S. 250.
但在现象学圈外人面前,在给外尔的回信中,贝克尔还是为现象学做了辩护,但这个辩护更像是他在外尔面前对现象学发展近况的介绍:
如果您现在认为,形式主义的这个胜利会毁灭现象学作为哲学基本科学的地位,那么我当然无法赞同您。诚然,您本来就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因为您大概已经几乎不了解现象学哲学的最新发展了。最近在现象学运动本身之内出现了一种在基本立场方面的根本变化,实际上这个流派的所有独立研究者都以某种方式偏离开内在描述的准则,当然是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胡塞尔本人已经过渡到了形式现象学的观念,它在根本上带有不少构成性的特征。舍勒(还有普凡德尔)已经走向了一种明显的、超现象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给出了对人类此在的深刻诠释,它一直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现象表层的下面(他的奠基性的、极为重要的著述的标题为《存在与时间》,将会充满胡塞尔的《年刊》的整个第8卷,并且大约会在秋季出版)。最后,在海德格尔的研究对“精神”和“历史此在”问题域所做的非常广泛的探讨和出色阐述的强烈影响下,我自己试图通过“示明(Deutung)”来使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然得以领会:它是无机的、有机的和原始心灵的(在心理分析的“系统—无意识’意义上的“远古”心灵生活)的“自然(natura)”,即“出生(Geburt)”或“生成(σιε)”,是从其现象的基础出发到超现象之物中的历史精神之界限的彼岸(在过去几个学期的一系列讲座中)。这样,在较老的“观念(ideative)”现象学上开始长出较新的“解释学的(hermeneutisch)”(释义的)和“预言的(mantisch)”(示明的)现象学的较新分支。*Oskar Becker,“Four Letters of O. Becker to H. Weyl”, in: Volker Peckhaus (Hrsg.),Oskar Becker und die Philosophie der Mathematik, a.a.O., S. 189.
贝克尔在这里提供的是他眼中的1926年前后现象学运动发展的大致勾画。这个勾画反映了现象学运动内部的实际局面。虽然两年后舍勒便在科隆辞世而去,胡塞尔从弗莱堡的哲学教椅上退休,海德格尔接任后放弃现象学的概念,但在1926年期间,“经典现象学”与“新兴现象学”之间的关系还是有理由被喻为“老树新枝”。不过即使如此,这里也没有提供对“现象学方法本身的某种危机”的实质辩护,因为外尔所理解的现象学方法是“范畴直观”或“本质的看”,他理解的“危机”也是指这个方法的哲学基础性地位的危机。而贝克尔面对外尔的怀疑所表明的仅仅是:“新现象学”已经不再拘泥于这种方法,而是开始“偏离开内在的描述”的基本立场,进入到“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的超现象之物的领域。就此而论,贝克尔已经不是在为现象学做辩护,而是在为各种意义的超现象学做解释,包括他自己的“预言现象学”*贝克尔多次将自己的现象学称作“mantische Phänomenologie”,并将它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的现象学”相并列。这里将“mantische Phänomenologie”译作“预言现象学”,实际上也可以译作“占卜现象学”或“算命现象学”。“Mantisch”一词与“Mantik(占卜术、算命术)”有关。贝克尔在《数学实存》中曾解释说:“数学、自然科学和医学在历史上产生于古老的占卜术与魔术。这个发展并不像许多人所以为的那样是一个历史上的怪物,而是一个深层的本体论事实情况的外部表达。‘精确的’科学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取代了占卜术和魔术。但数学的预言特征和主宰特征并不仅仅在它的运用中,而且已经在‘纯粹数学’中显露出来。例如,无法忽略的数的关系在更高的数论(一个十分特殊的‘纯粹’数学学科)中受有限的法则的主宰,并且因此而可以预知计算的结果。因而‘占卜’已经是一种内部—数学的事务,并且在这里通过一种由占卜赋予知情者的特别权力感而具有一定程度的诱惑力。因而‘数学活动’作为纯粹的心灵态度已经将‘醒(Wachsein)’和‘时间优越性(Zeitüberlegenheit)’、历史存在和自然存在的特征结合为一。”(O. Becker, Mathematische Existenz. Untersuchungen zur Logik und Ontologie mathematischer Phänomene, in: 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Bd. VIII, 1927,S. 762)由此也可以看出,贝克尔实际上是将他的现象学理解为一种“自然解释学”或“自然科学现象学”的现象学,以对应于海德格尔的“历史解释学”或“精神科学解释学”的现象学。但他强调说明的数学的“历史存在和自然存在的特征结合为一”的能力已经可以解释他后期回归胡塞尔超越论现象学的原因与动机。。在此意义上,贝克尔已经偏离了现象学,至少是偏离了“经典现象学”,就像外尔偏离了直觉主义一样。
贝克尔这里没有回答的问题在于:胡塞尔的“经典现象学”,即以直观为一切原则之原则的现象学,究竟会不会因为形式主义战胜直觉主义而失去自己的哲学基本科学的地位呢?贝克尔在致曼科的信中表现得略有动摇:
这里有一个本质要点对我来说还不清楚:可以(纯粹实事性地从我们今天的问题状况出发)区分:一方面是欧式几何的毫无疑问的(多多少少的)直观性的形态,将它们运用于直观空间(按胡塞尔的看法是质料的、尽管不独立的[抽象的]空间区域);另一方面是非欧几何的构成物,它们(如果想要小心一点的话)只能在“数的空间”中被给予,即以算术—分析的方式被给予,即作为胡塞尔意义上的“形式区域”的本质性被给予,但它们本身还可以为范畴直观所达及。但还要区分(而这第二个区别不能与第一个区别相混淆!!):一方面是可以为布劳威尔的“直觉”数学所达及的算术—分析的对象性,其中包括以过程形式的无限集合,甚至包括康托尔的第二数类的最初的几个数,至少直至最初的“ε—数”;另一方面是希尔伯特的超穷构成物,对它们不能做可以为真或为假的本真的陈述,而是只能做非本真的、“理想的陈述”,它们可以与本真的陈述相连接,类似于复数与实数相联结,射影几何的理想点、代数数论中的理想数与普通数相联结。这些在希尔伯特意义上的“超穷”构成物不再能够被胡塞尔的“范畴直观”所把握。它们因此而从根本上有别于非欧几何的构成物(只要后者不是“超穷的”[希尔伯特],这也可以出现在“欧式几何”的构成物那里)。因为这些构成物当然是无法范畴直观到的。因而必须区分(至少)三种数学“构成物”:1.能够为(理想化了)的感性直观所达及的构成物;2.能够为范畴直观所达及的构成物;3.不能为任何直观所达及的、但无矛盾的构成物。第三种构成物不再属于胡塞尔式的“形式本体论”,而是属于“无矛盾所设(Gesetztheiten)”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没有“真理”,惟有“一致性”。*O. Becker,“Briefwechselmit Dietrich Mahnke”, a.a.O., S. 247.按,重点号是原有的。这里出现的“真理”“一致性”的对立与胡塞尔后期在《第一哲学》和《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中对“真理逻辑”“一致性逻辑”的区分相关。具体讨论,可以参见笔者的另一篇文章《现象学的数学哲学与现象学的模态逻辑——从胡塞尔与贝克尔的思想关联来看》。
扼要说来,贝克尔在这里做了两方面的区分:第一个区分是对欧式几何的直观形态与非欧几何的构成物的区分,前者可以为感性直观所达及,后者可以为范畴直观所达及。第二个区分在于,一方面是可以为布劳威尔的“直觉”数学所达及的算术—分析的对象性;另一方面是希尔伯特的超穷构成物,这些超穷构成物不再能够被胡塞尔的“范畴直观”所达及。这个四重区分较之于以往哲学史上对经验与理智的两分要复杂一些,例如经验论者休谟对“观念的关系”(relations of ideas)与“实际的事情”(matters of fact)的基本划分,观念论者莱布尼茨对“理性的真理”(vérités de raison)与“事实的真理”(vérités de fait)的基本划分,还有布伦塔诺—胡塞尔对“本真表象”与“非本真(符号)表象”、胡塞尔对真理逻辑与一致性逻辑的基本划分等等。
之所以这里的情况更为复杂,主要是因为胡塞尔引入的“范畴直观”打破了原有的二分的局面。如果将贝克尔的双重区分中的第一类“欧式几何的直观形态”与第二类“可以为布劳威尔的直觉数学所达及的算术—分析的对象性”归为同一类数学构成物,那么我们最终就还原到数学构成物的三个基本类型上,它们分别是感性直观的对象、范畴直观的对象和所谓“理想陈述”的对象。这也就是贝克尔在上述引文结尾提出的三种数学构成物。对前两种构成物的把握方式,贝克尔的刻画都是积极的,即都是可以直观到的;但对第三类数学构成物的把握方式,他只是用了消极的表述,即它们不能被直观到,无论是通过感性直观,还是通过范畴直观。显而易见,贝克尔并不想用前面和这里都提到过的“理想陈述”的说法来表达对第三类数学构成物的积极把握方式。因为若果如此,他必定会面临进一步的“理想陈述是什么”的追问,因而也就必定会再次体验在希尔伯特那里已经出现过的不得不“总是顾左右而言他”的窘境。
据此,即便使用消极的定义来处理对第三类数学构成物的把握方式,贝克尔也必须在胡塞尔和希尔伯特之间找到一个可以立足的位置。由于涉及莱布尼茨的普全数理模式(mathesis universalis)的理想,因此贝克尔在给莱布尼茨研究专家的曼科的信中以莱布尼茨作为起点端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的意见如下:在我看来,一方面不可能将莱布尼茨与(至少在至此为止意义上的)现象学相统一,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将莱布尼茨与希尔伯特(以及在其最新阶段中的外尔)相统一。因为,(“经典的”)现象学必定在于:所有对象性(也包括较高序的和最高序的对象性)都是可以通过(范畴)直观而本原地被把握到的(而且是对于人而言),而希尔伯特的超穷陈述不是可范畴直观到的事态,而且它们在元数学中的符号代现绝不是“同构(isomorph)”。(“同构”在这里与形态相似性无关,参见您的论文第214/215页。)我对将神的“绝对的看(infallibilisvisio)”(第43页)与胡塞尔的描述的本质学相结合的做法心存疑虑。因为描述的本质学原则上是模糊的、单纯形态学的、单纯朝向类概念的;而神的“看”则必定会被规定为是直达实无穷的(诚然这也是无法为“理想化了的人的意识”所达及的,参见胡塞尔:《算术哲学》,第246页及以后各页)。我认为,那种神的“看”恰恰是与康德的“原形的智性(intellectusarchetypus)”相同的,而如所周知,它是被胡塞尔立场鲜明地予以拒绝的。尽管胡塞尔假设了在有限的单子与神之间的连续性,但他另一方面却从人出发而想将上帝理解为一个“极限概念”,亦即听任它是不确定的(indefinit),并且不想参与从不定(Indefiniten)到超穷(Transfinite)的跳跃。*O. Becker, “Briefwechselmit Dietrich Mahnke”, a.a.O., S. 249.按,重点号是原有的。
据此,虽然贝克尔还不是信心十足,但他实际上已经对这里的问题给出了一个基本确定的答案。不过这里显然还存在一个对胡塞尔解释的可能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将贝克尔的答案与他对胡塞尔的解释结合起来考察:
1.胡塞尔是否真的会像贝克尔所说的那样认为“所有对象性(也包括较高阶的和最高阶的对象性)都是可以通过(范畴)直观而本原地被把握到的”?*如果贝克尔在这将“通过(范畴)直观而本原地被把握到的”中的“被把握”理解为被“神”把握,就像康德将“智性直观”看作神的能力一样,那么这个说法还是可以成立的。我们可以说:神不需要符号。若果如此,胡塞尔那里就只存在两种对象性的意识行为(甚至可以说:只存在两种意识行为,因为所有意识都是对象性的):感性直观和范畴直观;符号行为作为意识行为的合法性就会被取消。这显然是与“经典现象学”不相符的。在胡塞尔的经典现象学这里,至多可以说,符号意识必须建基于直观意识之上;而且尤其在胡塞尔的“经典现象学”这里,符号行为既可以建基于感性直观行为之上,也可以建基于范畴直观行为之上。与纯粹的符号意识相关的数学形式系统在其抽象的发展中可以远离直观性的领域,但它们最终必须回溯到直观性上,或者说,必须以直观性为出发点。
2.经典现象学的“描述的本质学”是否真的如贝克尔所说“原则上是模糊的、单纯形态学的、单纯朝向类概念的”?在笔者看来,这同样属于对胡塞尔本质学说的一种误释。与(无论高阶还是低阶的)数学形式系统所体现的“精准的思想”相比,本质直观或许可以被视作“不精确的”,但绝不应当是“含糊的”,而只能是“严格的”。如果贝克尔在胡塞尔面前用上述定义来刻画他的哲学之为严格科学的理想,胡塞尔一定会批评贝克尔没有理解“经典现象学”的真谛*哲学和精神科学的“严格性”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精确”之间的关系问题最终导致并实际上构成胡塞尔所说的批评。。
3.胡塞尔是否真的像贝克尔所认为的那样“假设了(annehmen)在有限的单子与神之间的连续性”?对此问题还无法简单地回答是或否。这主要是因为,贝克尔这里所说的“神”与胡塞尔《算术哲学》中的说法有关。它指的是一种可以直接把握无限的精神,即如贝克尔所说的:“神的‘看’则必定会被规定为是直达实无穷的。”贝克尔在1930年为庆祝胡塞尔七十诞辰而发表的《埃德蒙德·胡塞尔的哲学》一文已经指出:胡塞尔在《算术哲学》中的确持有这样的看法,即“人的有限智力的局限性使得数列只能以符号的方式、在无限重复的加一的‘如此等等’中被给予,亦即作为‘潜无穷’被给予”。无法设想能够对我们的认识能力进行某种可把握的扩展,从而使得这个能力可以真实地表象或哪怕是逐渐地穷尽这样的(无穷)集合,因而算术和几何以及整个数学都是人的而非神的*参见Oskar Becker, “Die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Anläßlich seines 70. Geburtstagsdargestellt)”, in: Kantstudien, Bd. XXXV, 9 (1930), S. 121f.。而胡塞尔对在有限人(单子)与神之间的连续性的“假设”就意味着:虽然人无法直接地把握实无穷,但却仍然可以“间接地通过那些明确刻画它的符号”来将其内容给定为“它之所是”*参见E. Husserl, PhilosophiederArithmetik.MitergänzendenTexten (1890—1901),Hua XII, MartinusNijhoff:Den Haag 1970, S. 215.,而且在这种直接的把握和间接通过符号进行的把握之间存在着过渡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对无穷集合的间接的把握与神对它的“看”是一致的,因为说到底前者还是符号运算,而后者则不是:神不需要计算和推导。如果这里可以谈论“连续性”,那么在人的有限能力中这个连续性实际上不是指从人的有限智力过渡到神的无限智力的连续性,而仅仅是指从人对数学对象性的直接直观把握到间接符号把握的可能连续性。
就此而论,胡塞尔已经给出了一个在希尔伯特形式主义和布劳威尔—外尔的直觉主义之间或在这两者之外的立场和对此立场的解释。
我们前面使用了“精准的思想”的表达,这个表达出自数学史家莫里斯·克莱因。这里可以重温他的一个说法,并用它来重审这里的问题域。虽然他使用的概念和表达已经与胡塞尔、贝克尔和希尔伯特、外尔的时代不尽相同,但他对数学活动所做的概括性的理解在总体上仍然处在与上述三人的思考相同的方向上:
数学家的创造是通过明察(insight)与直觉(intuition)的行为来进行的。而后由逻辑来核实直觉的战利品。这是一种使数学得以保持其观念的健康与强壮的保健法。此外,整个数学结构根本上都建立在人的直觉的不确定基础上。这里和那里的直觉都会被挖掘出来,并会被一个稳固的思想支柱取而代之;然而这种支柱是建基于某些更深的,也许是定义更不清楚的直觉之上的。尽管用精准的思想取代直觉的过程并没有改变数学最终立足于其上的那个基础的本性,但却增加了结构的强度和高度。*Morris Kline,Mathematics in Western Cultur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 p. 408.
相信这个说法在经过必要修正后(mutantismutandis)可以为胡塞尔在总体上接受。
四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们还需要反思一下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与数学家之间的关系。它在胡塞尔、贝克尔与外尔、希尔伯特之间的关系上得到了一定的体现,可以被视作思想史上哲学家和科学家同谋共思的经典范例。
相反的例子要多得多。同时代的数学家格哈特·海森贝格曾就这个关系在书信中写道:“如果我可以夸张地说一次的话,那么我会说:专业哲学家在这个领域中所做的工作,在数学家那里得到的关注很少,而且自身也极少是如此完成了的、统一的和可靠的,以至于我们只会让我们恰恰要针对的数学读者圈大吃一惊。这里的数学家所具有的优势在于一笔确定的、虽微少却稳当的、已经无须再做任何讨论并可以在上面继续建构的财富。而在哲学领域中的意见分歧一直还延伸到基本的提问之中。”*Gerhard Hessenberg (1874—1925)an Teubner, dat. Bonn, 29.4.1908.转引自Volker Peckhaus, “Die Zeitschrift für die Grundlagender gesamten Mathematik. Ein gescheitertes Zeitschriftenprojekt aus dem Jahre 1908”, in: Mathematischer Semesterbericht (2007) 54,S. 110.
数学哲学家和逻辑哲学家奥斯卡·贝克尔则在他给外尔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这里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与某些数学研究的竞争。我根本不提供也不想提供数学的东西。相反,对我来说问题在于本体论的东西,数学家们常常漫不经心地将本体论的问题域放在一边。”*O. Becker,“Four Letters of O. Becker to H. Weyl”, in: Volker Peckhaus (Hrsg.),Oskar Becker und die Philosophie der Mathematik, a.a.O., S. 181.
毫无疑问,海森贝格和贝克尔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触及这个关系的要害点。
【责任编辑:杨海文;责任校对:杨海文,赵洪艳】
*收稿日期:2016—02—10
作者简介:倪梁康,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广州 51027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