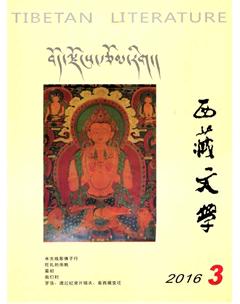结玛,联动的藏族汉语诗歌
2016-08-03祁发慧
祁发慧
诗人才旺瑙乳在《当代藏族诗人诗选(汉文卷)》的序言中写到:在诗神央坚玛那美妙的琴音召引下,当代藏族诗人像朝圣者一样匍匐前进,虔诚地向着那真实的生活追寻。才旺瑙乳的表述是诗意的,但也道出了藏族人在文学创作上的渴望与理想。回顾新时期以来的汉语诗歌写作,藏族汉语诗歌呈现出其独特的文化面相,而女诗人的写作是构成这一文化景观的中坚力量。对于写诗的结玛(Skyes ma),我们会有一个更加具体的定位——当代藏族汉语女诗人,年代分期、族裔属性、身体性别皆得到一定的强调。这种定位或许是出于研究或者批评行为展开的准确性和必要性,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割裂或局限了对其文学创作的深入了解与研究。首先,在藏族人的传统观念中,“洁净观”取代了“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这样的从属观念;其次,在藏族的前现代社会结构中,也不存在以男性为主体的支配范式,女性在德性和知识上与男性几乎是平等的;再次,在藏传佛教中,被称为央金玛的妙音天女主管着音乐、诗歌等艺术形式。因此,在当下以“女性”定位她们的写作身份时,我并不想突出她们的身体性别,反而更倾向于将性别的诗歌与性别分离,透过性别这一概念来谈论她们的诗歌本身,探寻她们如何用语言来表征自己的文化性别,如何处理自己与地方、时代、诗歌之间的复杂关系等诸多问题。
这里,且从康区诗人桑丹的诗歌说起:
流水缓缓停下
从大地的身影里漫出
如花朵繁荣的季节
把我风雨招展的爱上
飘扬的田园的八月
让碧空里掀动的双手猎猎作响
——《田园中的音响》
耿占春先生在《藏族诗人如是说》一文中说,桑丹是“最经常写到八月的女诗人”,众人喜爱八月大多因为时节的爽朗与收获,桑丹的描写却是哀伤的。流水停歇、繁花落尽、麦穗点地,一切喜悦和兴奋似乎都是稍纵即逝的,八月如一张时间的蛛网,由此辐散开来,网罗桑丹对自然事物所有隐形意味的感知与触碰。譬如,她的写作触角时常伸及至“向阳的山坡”、“黑色的大树”、“远山的积雪”、“荡漾的星空”这些藏乡最普通不过的自然之景,但笔触永远锁键在“女人”、“跛马”、“少年”的这样的人生事件与生活场景中,这样的并置恰好回应了她对个人经验和生命感受的提取:
离散的女人,将要与谁相遇
她要带来怎样的讯息
呵,夜色多么虚无
她要隐忍怎样的罪孽
承受那无尽的轮回
——《云朵般的暮色》
离散意味着聚合之后的一种敞开,包含了生命体验的生成、变化等一系列过程,这个“女人”在时间之维靠近宿命般的神圣与疼痛,同时也让自然万物具备某种潜藏的力量,如罪孽、轮回,亦如“那时间深处的黑”、“大地边缘的废墟”、“灵魂的天宇”……桑丹总会在温和而内敛的叙述中构成一个极为细密的情感网络,这或许是为了描绘出一幅真实且完整的生活样态:
他在马厩里添加夜草
马匹的咀嚼声像石头一样滚动
他的马群,喷着响亮的鼻息
仿佛山路间悠长的回声
——《夜草/怀念我的父亲》
桑丹的敏感并不止于季节,更多是对生活迹象和个人情感的交错阅读:某个夜晚与自己的对话,目睹马匹食料时对父亲的思念皆以词语的方式进入诗歌,而这种阅读的展开总是沾染着眷恋与忧伤的音调。当然,这份眷恋或忧伤的根源早已超过了桑丹自我的情感经验,一定程度上它是关于祖地——打折多——根生的情愫。或许正是由于此,桑丹诗歌中所表现的主题总带有强制性的主观选择:
含着眼泪,想起此时的高原
无人经过,无人歌唱
我不断梦见涉水的马群或牛羊
在八月炫目的星空下
淤积雨量充沛的花环我仰起头
看着这坚硬、洁白的容器
将一生静静涌动的血
燃烧成冰雪之前的火焰
——《河水把我照耀》
诗人的笔触在“眼泪”、“歌唱”、“冰雪”、“火焰”的勾勒之间游走于喜与悲、静与动、冰与火的二元对立中,用情至深的文字把所有的坚硬都隐藏了起来,转而用“洁白的容器”建立“物”与“自我”之间的亲密关系,即白色与藏民族灵魂和精神品质的象征关系,它建立在庄严和崇高的基础之上,族人在对白色的执着中演绎出对善的认可,从白色的物质启迪中表现对美的追求。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桑丹写作中的美学追求,其美学功用类似于印度教神祗“湿婆”主司之职,兼具生殖与毁灭、创造与破坏的双重性格,并以不同奇谲怪诞的相貌示现。这恰恰也是诗歌的生命力所在,在赞美和热爱这个世界美好的同时,也会思考一些陌生的未知和不可说的疑惑,每每这时,我们便会求助于另一种神秘的存在——宗教。
不难承认,宗教或者信仰是建构人与世界关系的媒介之一。那萨·索样开始写作的时间并不长,她总会在有意无意中带出一些具体的宗教符号:
傍晚
手里的念珠转完108颗
天亮了
剩下陈旧的空金瓦殿
一只乌鸦
突然失语
——《美丽世界的孤儿》
佛教在藏区是一种神圣而又普遍的日常性存在,说它日常是因为佛教本身就是藏族人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大多数至今都过着焚香、礼佛、转经、磕头、念经的仪式性生活。那萨记录的是她平素的生活,结束一天的忙碌或悠闲——睡前拨动念珠静坐观想——睡去——早起沐手焚香——开始新的一天。这些外部生活都是一种内心的象征,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进行,少了些什么也多了些什么,俗世生活与神性世界并不存在实质的冲突和现实的矛盾,恰如那萨沉稳中递进式的叙述。或许正是由于这种仪式性生活,他们的诗歌存活在浓烈的宗教气息中:
确定,一棵乔装的异树
披着袈裟,经过前世
又邂逅在因果之间
像火焰,烤焦浊世的混沌
灵与魂紧凑
掌心与掌心靠拢
母性的柔软
在子宫里观想
又想象,在腋下开花
——《甄叔迦树》
甄叔迦(梵语kim!s/uka),印度婆罗门教的圣树,其花赤红,形如人手,意译为赤色宝,常作供养之花。青藏高原并不生长这种亚热带的豆科植物,然而,诗人初次见到它时,就看到了一棵宗教意义上的树,从一种自然的动力体系走向了超验世界,灵魂确实是可以出窍的,看树非树,将“母性”、“子宫”这些纯碎的女性经验和“因果”、“袈裟”等宗教遐想联系在一起,这或许是一个人潜意识中具备的某种原初的特性。树和树的象征在诗人内心中生成一种映像,投射向个体生命的自我意识:
爱上一面墙
树叶从树根奔流而下
想起高处的江流
想起太阳城里的某位信徒
一离家
念想就原路返回
——《麦积山》
不管是低处的“树”还是高处的“山”,以及更远处的“城”,始终被宗教性的想象推搡着,而想象能抵达的也始终是宗教的。我猜想,在去往麦积山的路上,那萨的思绪肯定飘飞在藏区的沟沟壑壑,最后集中在海拔3650米的圣地拉萨;拜谒石窟佛像的同时必然在为众生祈祷,就像某位修行的僧人。如若说,桑丹诗歌的力量来自她生活的康区大地的话,那么那萨诗歌的力量源自先天的宗教氛围,她就这样一手打开了词语世界,一手握住了神性世界。毋庸置疑,一种生活模式、生活观念以及生活经验透露的文化意义以及它们对一个写作者的影响绝对是深远的。
因此,作为少数民族的写作者,当有一种天然的写作使命:发现并开掘早已被习惯化、经验化,甚至深埋在基因中的经验的文化性及其独特性。德乾旺姆善于发现它们,描写它们:
当我们手牵着手
轻轻迈出舞步时
你可曾听到那欢快的虫鸣
还有啊!那不曾歇息的欢乐鸟
可爱的羊子,缱绻多日的獒犬
篝火还是几个世纪前的篝火
空气里有众多西藏植物的芬芳
领舞的宣果是高寿的部落女人
但是她的舞步却分外利落
她起步,抬脚,落地
欢快地侧转身,优雅地稍稍举头
欢快地侧转身,婉约地稍稍含胸
蓝色的湖底,舞韵是土林庙墙上红色的壁画
——古格·宣
宣:西藏阿里地区的古典宫廷舞蹈,“宣”舞是据今有上千年历史的古老舞蹈。“宣”即舞蹈之意,在据今有1000多年历史的古格王朝遗址壁画上,有宣舞的表演场面。阿里底雅乡的底雅宣舞最为壮观。
宣舞:分为身前拉手舞蹈的“顿宣”和腰后搭手舞蹈的“布宣”两种,共有13种曲目,宣舞表演时间是每年藏历一月至五月,且每月选一吉日,举行民间祭祀活动时也要进行表演,尤其到了藏历新年时,人们身着盛装通宵达旦表演,以示吉祥和幸福。
宣果:即领舞人,这一身份是世系的,必须是世代担任“宣果”家族后代才有资格领舞,这在西藏种类繁多的舞蹈中比较罕见。
德乾旺姆把古格王朝遗址壁画上的舞蹈用形象的文字呈现在诗歌中,并对“宣”、“宣舞”、“宣果”做出知识性的文字注解,使得诗歌与注解形成一种互文关系,而这种互文关系并不指向诗歌结构或者意义,而是以类似于文化考古的方式对一个民族文化、历史和传统做出相应的回应。古格王朝对今人是神秘的,它在藏族发展史上的辉煌如今只能借助残存于墙上的壁画去想象,但德乾旺姆对它的观察和想象是经验性的,绘画科班出身的她自然会特别关注那些壁画的题材、颜料、布局。她把看壁画的视角转换为一种视觉思维及思想意识,将有意识地看到的图像与无意识的族群情感联系在一起,由静而动,还原出古格王朝极盛时的民风民俗。归回到“宣”本身而言,作为一种舞蹈“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的成份,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娱。”宣舞或是其他舞种,至今都是藏族民间文化中及其耀眼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宣舞所展现的即是藏民族日常生活中舞、乐常伴的本真的生活状态。德乾旺姆用修辞加强了生活背后的原初的生命力,古老的世界在词语中再次变得鲜活:
晒谷场上火药枪鸣
让我们穿上牛皮的铠甲
跳起呼唤战神的舞
临行一别
牛角壶中壮行的酒
部落老人向高天祷告
这里山水适宜作战
适宜被瓜分
产生与众不同的流传
——黑水·卡斯达温
卡斯达温:黑水藏语意为“铠甲舞”。主要流行于四川阿坝黑水县的上黑水和下黑水一带,系穿千叶漆牛皮甲而跳的一种舞蹈,是古代战争时期,出征勇士在出征前所跳的民间祭祀舞蹈。
读德乾旺姆的诗歌,不难发现她会在一段文字中把音乐、绘画、舞蹈这些艺术形式凝结在一起,进而以“物”的形象呈现不同藏区特有的地方性知识,而所有的物质的地方性知识都会“体现在个体的经验之中,(一个人一群人)历史的一部分也会包含在制度——社会结构通过规章制度正式或非正式的方法塑造了个体和企业的观念、准则、期望和实践……”。就此而言,德乾旺姆的文字是通过诸种艺术形式的汇通而探讨一种民族文化心理。她把对日常事物的艺术敏感性转移到文学语言的使用中,把勇士跳舞、饮酒的细节和经验主题化,而不存在直接的观念言说和论证。她用自己的艺术经验控制和调度文字激情的时候,抛出了一个全人类各民族共同思考的问题:在现代性背景下,各种地方性风俗正在不断衰微,如何抢救保护各民族的地方文化呢?
找寻从梅卓笔下的青塘开始:
穿过青唐穿过
由东向西的梦中走廊
行人于相反方向擦肩而过
碰响我的香木耳坠那丢失的
多年前拥有的长长珠子
和你的朱红腰带
在夜岚刚起冬雪未落时
一同认知青唐
——《冬雪之宴:梦中青唐》
藏区自古便有卫藏之佛法、安多之良驹、康巴之人的说法,现在的夏都西宁在藏语中古称青塘(唐)(Gyithang),意为天驹之川,曾为安多(藏区)政治文化中心。如今的青塘(唐)依然是青海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安多藏区最繁华的城市,一切应有尽有,只是没有了良驹和身着传统服饰的策马之人。梅卓关于青塘(唐)的梦由东向西横向展开,连同“拉让的坠子”、“衮本的念珠”、“赶往赤岭以南”。梦中的青塘以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更不是一座无中生有的奇幻之城,而是一种关于族群的历史记忆。一定程度上,青塘(唐)是诗人自我地理学或假以考古之名写作的一座名义上、形式上的城,它意味着族群经验与记忆的共享,特殊的地方意识与情感空间的共享。但是,面对逐渐完成的现代化社会的转变,诗人不由发出这样的感叹:
究竟会有什么改变青唐
你可记得傍晚时分的迎面而遇
高高的楼群遮盖住容颜
那是暗暗的喜悦从心底
开满青唐大树的枝头
伸出左手五指的方向
抵达命运的另端
——《冬雪之宴:梦中青唐》
溯源、对比之后,诗人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被“楼群”遮住“容颜”深陷其中,而不仅仅是一个冷峻的旁观者。在抵达命运另一端的宿命感之外,诗人能做的就是在写作中确立一个新的、更为积极的主体性的话语,从而表现对族群文化记忆的唤醒与眷恋、以及对族群共同体渊源的追溯。当然,这也是转型期以来边疆各少数民族写作者为构建少数民族话语而做的努力,他们以写作的形式确立少数族裔的自我意识和个体意识。德乾旺姆这样写到:
青塘古城,夏季美丽的清凉城池
久远的石板路上有多少人为她明日的某种焕发
奔走,且让我坐下来,在来来往往的红尘中为她设想
——《早安!青塘Gyi thang》
这里的青塘是被人格化的,如一位需要呵护和打扮,需要关爱和支持的女子,曾经的故事骄傲而心酸,未来的发生美好而艰难,且让一切从早晨开始,充满希冀。梅卓与德乾旺姆的青塘糅合了古老与现代,记忆与遗忘,这个地方的建立、发展、变化似乎成为她们自身的一部分。一定程度上,旧时的青塘、现在的西宁集中了无数个体分散的经验,它由一座形式上的“城”成为个体逐渐生成的自我原型,即自我与地方、地方与时间关系表征的辩证意象。某种意义上,她们所写的青塘取消了现代意义,而隐含着对一种文化,一种传统的留恋与怀念。吉登斯说:“怀旧是人寻求保护、抵御危险的一种本能,是在预期未来时对过去的重构,是一种与时间保持对话的策略。”或许,不同形式的怀旧行为也是这个时代与个人的一种基本关系。相比较而言,白玛娜珍更倾向于写不幸与痛苦:
当生命被撕裂
我只想变成飞扬的灰烬
还有别的选择吗
当我穿过白色的严寒
在那房间的底层
在那不透光的空间
用我们的秘密
抵抗所有的谎言
——《我们是失明的鱼》
就时间维度而言,白玛娜珍多写当下正在发生的一切,“还有别的选择吗?”“如果你不允许\我绝对看不到光”,选择本身伴随着一种无奈和挣扎,而且挣扎本身也是抵抗性的,用“谎言”抵抗“秘密”,用“爱”抵抗真相,选择是必须要做的,但是做出选择的同时,个体的自主性和安全感瞬时消失:
那天夜半神走了
拉萨河的蓝光如潜伏的狼
但如果留下
您能洗净一切黑吗
——《神走了》
白玛娜珍所写“神走了”的景象,其实是不同价值和观念的碰撞,她把自己过去到现在的经验感受移入诗歌之中,来探讨切实发生的需要得到应有回应的变化。但是面对已有的变化,她清醒的个人意识中也能透露出尴尬处境中的无力感。
当下,高原本土的任何事物都与其他事物处在一个普遍的联系之中,朝圣者与旅游者、民歌与rap、经幡与单反……交错着成为藏族人赖以存身的基础,她们并不面临太多的精神困境,存有的焦虑也仅仅源于现代的生活空间与传统文化想象之间的落差,好在她们从未远离神圣,在现代社会中遭遇的焦虑被自然事物的象征秩序所消解。因此,即使是在“失去象征”的现代世界,她们依然首肯那些古老的象征和隐喻。或者说,她们在用诗歌做这样一种努力:唤醒古老的象征意识。每每翻阅这些诗篇,一种莫名的想象力似乎总能带领我回到那个诸神栖居的神话时代,妙音天女从众神铺盖的乳白色大海中现身,一边手持乐器弹奏悦耳动听的音乐,一边腾向万里高空,赐予藏族诗人出口成章的灵感和智慧。
①才旺瑙乳、旺秀才丹主编:《藏族当代诗人诗选》,青海人民出版社,第8页。
②结玛(Skyesma)女性一词的藏语谐音及拉丁文转写。
③桑丹:《边缘积雪》,四川文艺出版社,第1页。
④耿占春:《叙事与抒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48页。
⑤汪曾祺:《谈谈风俗画》,《汪曾祺全集》第四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50页。
⑥(英)凯·安德森、(美)莫娜·多莫什等主编:《文化地理学手册》,第164页。
⑦(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第83页。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