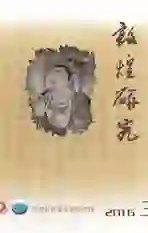从敦煌吐鲁番出土契约看唐代民间土地买卖
2016-07-21顾凌云
顾凌云
内容摘要:唐律严禁民间随意买卖土地。文章通过对敦煌吐鲁番出土契约的考察,发现唐前期民间存在变相买卖和地下买卖两种隐秘的土地买卖方式,表明官府严格执行土地买卖禁令,禁令存在一定的实际效力;中唐以后,民间土地买卖频繁发生,表明禁令的实效逐渐消失,不过民间仍对禁令心存顾虑,往往在土地买卖契约中设置反恩赦条款加以预防。官府对土地买卖缺乏有效的监控手段与民间正当的买卖需求难以抑制是禁令实效消失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契约;土地买卖禁令;禁令实效;敦煌;吐鲁番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3-0074-06
Abstract: Private land sale was prohibited by the laws of the Tang Dynasty. According to unearthed civil contracts from Dunhuang and Turpan, there were two ways to sell land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disguised sale and underground sale. This indicates that in this period the official prohibition on selling land was strictly followed and was effective to some extent. The increasing frequency of private land sales during the middle of the Tang dynasty reflected the growing invalidity of the prohibition, and the“anti-amnesty”articles added to contracts reveals that people still remained cautious about this ban. A lack of effective monitoring methods and the unquenchable need for private land sales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gradual subversion of the prohibition.
Keywords: contracts; land sale prohibition;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hibition; Dunhuang; Turpan
土地作为农耕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其占有、使用、买卖状况向来为统治者所高度关注。李唐王朝对土地买卖实行严控政策,唐律规定“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可以不用此律而“即应合卖者”,疏议中一一列明:“永业田家贫卖供葬,及口分田卖充宅及碾硙、邸店之类,狭乡乐迁就宽者,准令并许卖之。其赐田欲卖者,亦不在禁限。其五品以上若勋官,永业地亦并听卖。”[1]可见对普通百姓来说,无论口分田还是永业田,都不能轻易出卖,除非存在供葬、迁乡等法定事由,此外即为非法。
上揭唐律不妨称之为“民间土地买卖禁令”。关于该禁令的实际效力(简称“实效”)问题,即禁令是否确实对唐代民间的土地买卖存在约束力,由于传世文献中相关记录极为罕见,历来学者殊少关注。直到敦煌、吐鲁番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唐五代契约文书,才为后人探讨该问题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一 唐前期民间土地买卖禁令的实效考察
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民间土地买卖契约集中出现在唐中晚期及仍然实行唐制的归义军时代,而唐前期十分罕见[2],但这不代表唐前期并不存在民间土地买卖活动,也不表明民间土地买卖禁令具备约束力。禁令的约束力应从官府执法态度与民间遵法态度两方面加以考察:官府是法令的推行者,其执法态度是法令约束力的直接体现;而民间作为法令的服从者,其对法令的认可遵从程度则是衡量法令约束力的重要标尺。从吐鲁番出土文书来看,唐前期事实上存在变相买卖和地下买卖两种隐秘的民间土地买卖方式,由此可推知当时官府与民间对土地买卖禁令的不同态度。
1. 变相买卖
变相买卖就是以其他交易方式为名进行的土地买卖。虽然从表面上看交易的目的并非买卖土地,然而实施效果却往往与买卖无异。借贷契约中的牵掣条款就是一种典型的土地变相买卖方式。
牵掣条款约定借贷者以土地为抵押物进行借贷担保,一旦不能偿还债务,其土地即被债权人所占有。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具有牵掣条款的借贷契约为数不少,表明这一方式在唐前期曾流行一时,如:
若延引注托不还钱,任左牵掣张家资杂物、口分田、[蒲]桃,用充钱直。(64TAM4:53《唐麟德二年(665)张海欢白怀洛贷银钱契》)[3]
若郑延引不还左钱,任左牵掣郑家资杂物、口分田园,用充钱子本直。取所掣之物,壹不生庸;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64TAM4:39《唐乾封元年(666)郑海石举银钱契》)[3]216
若延引不还,听牵取白家财及口分平为钱直。(64TAM4:37《唐总章三年(670)白怀洛举钱契》)[3]224
若延引不还,任拽家财杂物及口分□□平充钱[直]。(67TAM363:7/2《唐仪凤二年(677)西州高昌县宁昌乡某人举银钱契》[3]569
如延引不还,及无本利钱可还,将来年辰岁石宕渠口分常田贰亩折充钱直。(64TAM35:15《武周长安三年(703)曹保保举钱契》)[3]524
上揭最后一例,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任牵掣”“听牵取”“任拽”等字样,但所谓“折充钱直”显然也是听任债权人获取用以担保的“口分常田”的意思,其性质与前四例并无不同。
牵掣条款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造成与土地买卖相同的结果,事实上成为一种土地变相买卖方式。但唐王朝始终不曾下令禁止牵掣条款,是由于签订带有该条款的借贷契约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所抵押土地的转让,土地是否为债权人所获得,取决于契约到期之日债务人能否履行债务。换言之,债务人所抵押的土地可能始终都不会转让给债权人。因此,虽然牵掣条款实施的结果往往违反唐代民间土地买卖禁令,但却难以简单定性为违律。
另一形式的变相土地买卖恰与牵掣条款形成鲜明对照,其违反民间土地买卖禁令的性质十分明确。开元二十五年(737)唐令曾规定“诸田不得贴赁及质,违者财没不追,地还本主”{1},其中的“质”即质押,如果借贷契约中设立了土地质押条款,土地即为债权人所占有,除非债务人到期还贷,否则无法收回土地[4]。质押与牵掣虽然都约定借贷者以土地为担保物进行借贷,但与牵掣不同的是,质押要求借贷契约期间内债权人占有土地,也就是说债务人的土地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必然转让给债权人,其性质与买卖几无差别,故被唐令明确禁止{1}。
值得注意的是,牵掣条款在实施时其实也具有相当的法律风险。唐律规定:“诸负债不告官司,而强牵财物过本契者,坐赃论。”疏议曰:“谓公私债负违契不偿应牵掣者,皆告官司听断。若不告官司而强牵掣财物若奴婢、畜产过本契者,坐赃论。”[1]485可见牵掣条款的实施必须通过官府,民间不得自行牵掣;而一经告官,出于同情贫困者的原因,债权人的牵掣主张未必能获得官府的支持。契约双方固然可以私下依约行事,但契约条款本身并不受法律保护,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唐咸亨五年(674)王文欢诉酒泉人张尾仁贷钱不还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该案有两份文书,其中之一为债权人王文欢的诉状(64TAM19:36)[3]269,另一份则是作为证据的张尾仁举钱契(64TAM19:45,46)[3]268。虽然契约残损严重,今已不见牵掣条款,但孟宪实先生通过详细的比勘与严密的论证,认为借贷契约中应当存在牵掣条款[5]。可见当张尾仁欠钱不还时,牵掣条款并未直接生效,债权人王文欢只能被迫告官。而契约双方约定的牵掣之物如果为土地,其实施的风险性就更加不言而喻了。然而上举大量具有该条款的借贷契约均以土地作为担保,契约双方皆甘冒风险,因为这是贫困农民获得经济资助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民间通过非官方渠道取得土地的极少数途径之一。
2. 地下买卖
另一种隐秘的民间土地买卖方式为地下买卖,也就是私下的土地买卖。由于唐代民间土地买卖禁令的存在,作为买卖证明的契约只能私藏于当事人之手,除非检举揭发,否则难以发现。但卢向前先生认为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唐开元(713-741)年间西州都督府处分张奉先赵悟那卖苗案”应当是由土地买卖契约所引发的:
卢先生认为,在赵悟那手中的“元契”便是非法的土地买卖契约:“元契既不仅为卖苗契约,则可推断其必与土地买卖有关。”[2]335这张契约正是本案的关键证据,“今寻检文契知错”,契约内容显然违法;而赵悟那“甘心伏罪”的态度也说明其在签订契约之时早已知晓私下买卖土地实非法令所准许,属于故意为之。可见民间并不认可与敬畏土地买卖禁令本身,忌惮的只是官府的严格执法。
上文所论变相买卖与地下买卖两种隐秘的土地买卖方式,都是民间针对唐王朝的土地买卖禁令所采取的规避措施,从中反映出官府严格执行禁令的态度。显然,民间土地买卖禁令在唐前期具有实际效力,但其约束力比较有限。
二 中唐以后民间土地买卖禁令
实效的考察
中唐以后,民间土地买卖禁令虽不曾废止,但官府与民间对禁令的态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从“抽户状”看官府对禁令的漠视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土地买卖契约从时间上看都在中唐以后,其中S.3877V《天复九年(909)十月七日洪润乡百姓安力子卖地契》{2}(下文简称《安力子卖地契》)是一份保存完整、内容详尽的土地买卖契约,录文如下:
(前缺)
阶和渠地壹段两畦共五亩,东至唐荣德,西至道、氾温子,南至唐荣德及道,北至子渠兼及道;又地壹段两畦共贰亩,东至吴通通,西至安力子,南至子渠及道,北至吴通通。已上计地肆畦共柒亩。自天复玖年己巳岁十月七日,洪润乡百姓安力子及男擖等,为缘阙少用度,遂将本户口分地出卖与同乡百姓令狐进通,断作价直生绢一匹,长肆丈。其地及价当日交相分付讫,一无玄欠。自卖已后,其地承任进通男子孙息侄世世为主记。中间或有回换户状之次,任进通抽入户内。地内所着差税河作,随地祗当。中间若亲姻兄弟及别人诤论上件地者,一仰口承人男擖兄弟祗当,不忓买人之事。或有恩敕流行,亦不在论理之限。两共对面平章,准法不许休悔。如先悔者,罚上耕牛一头,充入不悔人。恐人无信,故立私契,用为后验。
地主安力子
该契约的立契双方均为普通百姓,卖方卖地的原因是缺少用度而非供葬、迁乡等法定事由,其行为显然违反民间土地买卖禁令。但买卖双方对交易充满信心,认为契约能赋予买者土地所有权,“自卖已后,其地承任进通男子孙息侄世世为主记”,民间有权自由买卖土地的思想在契约中表露无遗。
更为重要的是,从契文中可看到官府对民间土地买卖活动的默许。虽然依据唐律土地买卖仍属非法,但官方设立的土地凭证——户状,却可以由买主“抽入户内”,表明官府对买卖不仅不加制止,反而配合民间使其违法行为合法化。此时的官府对民间土地买卖禁令的态度已完全不同于唐前期的严格执法,禁令的实际效力消失殆尽。
2. 从反恩赦条款看民间对禁令的顾虑
中唐以后,官府不再严格执行民间土地买卖禁令,不过禁令毕竟没有废止,理论上依旧存在效力。民间固然能够公开进行土地买卖,但对于禁令的存在,终不免心存顾虑,土地买卖契约中的反恩赦条款正是这种顾虑的具体表现。
所谓反恩赦条款,就是在契约中约定排除恩赦令的效力。敦煌藏经洞所出中唐以后的土地买卖契约大多设有反恩赦条款,上述《安力子卖地契》即其例;P.4017《卖地契样文》同样有“或有恩敕流行,亦不在论理之限”之语{1},更说明该条款流行一时。
民间如此反感的恩赦令,实际上是国家颁布的减免罪犯刑罚、给予官员赏赐、减免百姓债负之类的诏令[7]。而民间私债一旦被免,债权人将蒙受损失。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债权人在签订借贷契约时提前设防反对恩赦,也属正常之理。
令人费解的是土地买卖并非借贷,订立契约之时交易即已完成,买者获得土地,卖者得到相应的财物,所谓“其地及价当日交相分付讫,一无玄欠”(见上引《安力子卖地契》)。减免债负的诏令似与土地买卖并无关系,而土地买卖契约中竟然也设立了反恩赦条款。陈俊强先生认为“这些附带恩赦排除条款的所谓买卖契约,都是以买卖契约作伪装的借贷条款,并非真正的买卖行为”,原因是“债权人为了逃避官方对于利率等的限制”[8]。为逃避利率限制而伪装成买卖契约的情况或许存在,但陈氏的推测却不能解释同时代的其他大件物品交易,如卖牛卖车具等契约中却基本不见反恩赦条款的现象。
土地买卖契约中的反恩赦条款,应当与已经失去实效的民间土地买卖禁令有关。中唐以后,虽然官府对民间土地买卖禁令的态度已然不同于唐前期的严格执法,但在“恩敕流行”的特殊时期,官府势必要考虑皇帝顺应民心、缓解社会矛盾的用意,如果失地农民此时提起诉讼要求官府依律裁判,官府恐怕不敢不加重视;而官府态度一旦发生改变,则意味着土地买卖禁令重新获得约束力,土地的买方大概只能如前举“西州都督府处分张奉先赵悟那卖苗案”中的赵悟那一样“甘心伏罪”了。孟宪实先生曾指出,如果按唐律“去衡量田宅买卖个案,恐怕都不合法。如果政府认真执行法律,或者以制敕大赦等方式要求执行法律,势必对这些田宅买卖造成影响,所以民间契约才如此提前表示拒绝”[5]104,殊具卓识。
至于卖牛卖车具等契约之所以无需设定反恩赦条款,是因为这些买卖与土地买卖不同,本身并不违法,完全不必担心在“恩敕流行”时期沾惹官司。民间在公开买卖土地的同时又“多此一举”地设定反恩赦条款于买卖契约之中,正是缘于对已然丧失实效的土地买卖禁令的顾虑。
三 民间土地买卖禁令实效
消失的原因分析
中唐以后,民间公开的土地买卖频繁发生,土地买卖禁令的实际效力基本消失,不再具备唐前期的约束力。约束力消失的直接原因是官府放弃执行禁令,而根本原因则是民间对禁令的抵触。
1. 官府放弃执行禁令
官府本当严格执行王朝的民间土地买卖禁令,然而禁令所规制的是民事交易行为,只要交易双方意志一致即可完成,理论上并不需要经过官府的同意。如果官府对交易缺乏有效的监控手段,那么禁令必然只能流于形式。
唐代官府用户状的形式将土地占有情况登记在册,并按册获得赋税徭役,以此排除非法土地买卖。然而造册尚不足以有效监控土地占有使用的真实情况,买地者私下买得土地后,是否更改土地登记并不影响买主的占有使用权。如上举《安力子卖地契》所述,买卖双方约定“中间或有回换户状之次,任进通抽入户内”,可见抽取户状需要一定的时机;而在“回换户状”之前,土地虽然依然登记在安力子名下,但实际已由令狐进通占有使用,官府却无从知晓。
至于附着在土地之上的人身义务,在缺乏有效的身份认证措施的情况下,也不具备制约力。从初唐起,如杂徭等人身义务就可以通过契约转让,《唐显庆三年(658)西州高昌县范欢进雇人上烽契》等17件吐鲁番出土的《雇人上烽契》充分说明官府对服役者并没有严格的人身要求[9],官府对于代替服役问题无可奈何。那么附着于土地上的人身义务,在土地转让时显然也可以通过契约约定来解决,上举《安力子卖地契》用“随地祗当”四字清晰地交代了此类义务的分配。民间当然希望土地的转让能获得官方的认可,但即使得不到官方承认也不影响交易的完成,除非一方告官,否则官府无从发现,也不会有干涉的机会。
由于禁令所规制的民间土地买卖行为实际上能够将官府的监管排除在外,官府难以有效控制,在查无可查的情况下,官府只能放手听任买卖的发生,结果直接导致民间土地买卖禁令丧失约束力。
2. 民间抵触禁令
唐王朝的民间土地买卖禁令可使农民免受兼并之苦,本来是一项保护农民利益的措施,然而民间却往往甘冒违背律令的风险进行交易,甚至出卖自己的经济来源,似不合情理。从敦煌出土的土地买卖契约来看,农民卖地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为贫困,二为不便[10]。
贫困是民间土地买卖契约所记录的最重要的卖地原因,如:
洪润乡百姓安力子及男擖等,为缘阙少用度,遂将本户口分地出卖与同乡百姓令狐进通。(S.3877V《天复九年(909)十月七日洪润乡百姓安力子卖地契》)
[赤心乡百姓吕住盈及弟]阿鸾二人家内欠少,债负深广,无物填还,今与都头令狐崇清断作地价每亩壹拾贰硕。(S.1398《太平兴国七年(982)二月廿日赤心乡百姓吕住盈阿鸾兄弟卖地契》{1})
唐代实行均田制,按人口分配土地,并依此收税纳赋。虽然均田制可使农民普遍获得土地,从而取得收入维持生活,但获得土地只是让农民拥有劳动资料,并不代表其生活从此有保障。个人能力和技能的差异,遭遇突发事故等等因素都可能导致一部分农民陷入贫困的境地。在有效社会救助体系尚未形成的时代,为渡过难关,最方便的办法当然是借贷和出卖财物。土地作为最有价值的财物,却因买卖禁令的存在不能变现。而借贷不仅要支付高额利息,往往还需提供担保,在“债负深广,无物填还”(S.1398《吕住盈阿鸾兄弟卖地契》)的情况下,债务人的土地最终也会被债权人依约牵掣。虽然对于农民来说失去土地即意味着失去经济来源,但当生计都无法维持之时,出卖土地或许是唯一的出路。生存需求并非王朝律令可以压制。
耕种不便是敦煌出土的民间土地买卖契约所记录的另一种重要的卖地原因,如:
慈惠乡陈都知为不稳便,将前件空地出卖与莫高乡百姓安力子。(P.2595《乾符二年(875)六月七日慈惠乡陈都知卖地契》)
敦煌乡百姓窦飒伏缘上件地水佃种施往来不便……敦煌乡百姓吴盈顺伏缘上件地水佃种往来施功不便,出卖与神沙乡百姓琛义深。(P.3649V《显德四年(957)敦煌乡百姓窦飒吕盈顺卖地契》
耕种不便实际上是由于农民拥有的土地过于分散所导致的。按照均田制的设计,农民由分配取得的土地,死后须归还官府以供再次分配,“由于不断地授田还田,土地被人为地分割成零星小块,每家分得的土地分散在多处”[11]。另外,由于“田土有厚薄,为了达到均平的目的,分配的最好方式自然是按其地段,各家各户各得一份”[2]77,这样也会造成授田分散的结果。吐鲁番所出65TAM42:54《唐西州高昌县授田簿》记录的正是这一授田情况,如史阿伯仁所授部田,在城南五里白地渠、城西五里神石渠、城东五里左部渠各若干[3]128,相隔甚远。
过于分散的土地给农业经营带来了极大的不便{1},必然使民间产生巨大的土地交易需求,这种需求也非土地买卖禁令可以轻易遏制。一旦王朝的律令与民间的正当需求相互冲突,便不能得到民间的认可与遵从,其约束力必然被消减,甚至完全丧失。即使官府采用一定的监管措施,也难以阻止民间对抗律令的行为。
四 余 论
具有强制力的国家律令,尤其是涉及民事关系的律令,其约束力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来自于官府,但实际上往往受制于民间的需求。当李唐王朝的民间土地买卖禁令与民间正当需求相冲突时,其实际效力不免渐次消亡,最终形同虚设。唐代之后的各个王朝便不再设立民间土地买卖禁令,采取“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的赵宋王朝[12],从制度上认同民间土地自由买卖,因此造就了“千年田换八百主”(辛弃疾《最高楼·吾拟乞归》)、“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袁氏世范》卷3)的局面。
当然,宋代官府对土地买卖也并非完全放任,规定土地买卖必须订立书面契约,并经官府印押。这种被称为红契的契约,才是官方认可的土地凭证,可在土地诉讼中作为所有权依据。红契由官府统一印制,格式由官方制订,类似于今天的“格式合同”,官府通过控制交易过程而获取税收。
税收会增加土地交易成本,买卖双方自行设立而不经过官府印押的白契应运而生。虽然白契不能得到官方承认,在土地诉讼中不能作为所有权凭证,但由于其能满足民间低成本交易的需求,在封建时代一直以黑市的形式与红契共存。白契与唐代民间土地买卖契约可谓异曲同工。
参考文献:
[1]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242.
[2]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29.
[3]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叁[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214.
[4]陈国灿.唐代的民间借贷——吐鲁番敦煌等地所出唐代借贷契券初探[G]//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222,251.
[5]孟宪实.国法与乡法——以吐鲁番、敦煌文书为中心[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6(3):99-101.
[6]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M].北京: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54:图版43.
[7]罗海山.唐宋敦煌契约“恩赦”条款考论[J].当代法学,2013(2):155.
[8]陈俊强.皇权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56.
[9]陈喜霖.唐代烽子上烽铺番期新证[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6(6):5-7.
[10]刘进宝.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8-31.
[11]唐任伍.论唐代的均田思想及均田制的瓦解[J].史学月刊,1995(2):28.
[12]张晋藩.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