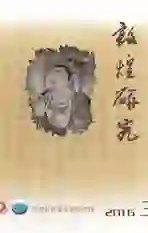敦煌文书《后晋开运二年寡妇阿龙牒》考释
2016-07-21刘进宝
内容摘要:P.3257《后晋开运二年寡妇阿龙牒》由三件文书组成。其中第一件是寡妇阿龙的状稿和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指示,第二件是寡妇阿龙和其兄索怀义关于土地耕种的契约,第三件是归义军左马步都押衙王文通询问土地占有者索佛奴、陈状人阿龙、种地人索怀义的笔录和曹元忠的批示。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文书进行了校释,并对内容进行了考辨。
关键词:寡妇阿龙;索怀义;索进君;索佛奴;王文通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3-0059-07
Abstract: P.3257,“The Complaint Lodged by Widow Along,”written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Kaiyun Era(945 A.D.)in the Later Jin Dynasty, consists of three documents. The first document records the complaint made by Along and the resulting instruction given by Cao Yuanzhong, the governor of the Gui-yi-jun regime. The second is a contract made between Along and Suo Yicheng, her brother-in-law. The third document includes Cao Yuanzhongs final decision and an account of the inquisition conducted by Wang Wentong, an officer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who interrogated the three clients, Suo Fonu, Along, and Suo Huaiyi.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llate and discuss the contents of this manuscript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Keywords: widow Along; Suo Huaiyi; Suo Jinjun; Suo Fonu; Wang Wentong
敦煌文书《后晋开运二年寡妇阿龙牒》,主要是对寡妇阿龙牒状的审查处理。本件文书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
本卷底卷编号为P.3257,由三件文书组成。其中第一件19行,是寡妇阿龙的状稿和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指示;第二件是寡妇阿龙和其兄(自己丈夫的哥哥、儿子义成的伯父)关于土地耕种的契约;第三件37行,是归义军左马步都押衙王文通询问土地占有者索佛奴、陈状人阿龙、种地人索怀义的笔录和曹元忠的批示。文书首尾完整,中间只有少许残损,基本上不影响阅读。
关于本卷的定名,《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2]定名为“寡妇阿龙等牒数件(开运二年有指画押)”,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3](以下简称《籍帐》)定名为《后晋开运二年(945)十二月河西归义军左马步都押衙王文通勘寻寡妇阿龙还田陈状牒及关系文书》,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4](以下简称《释录》)定名为《后晋开运二年(945)十二月河西归义军左马步押衙王文通牒及有关文书》,《法藏敦煌西域文献》[5]定名为《开运二年寡妇阿龙等口分地案牒》;李正宇《敦煌遗书一宗后晋时期敦煌民事诉讼档案》[6]定名为《后晋开运二年(945)敦煌寡妇阿龙诉讼案卷》(以下简称《李录一》),李正宇《敦煌学导论》[7]定名为《后晋开运二年(945)寡妇阿龙地产诉讼案卷》(以下简称《李录二》)。山本达郎、池田温合编《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第三卷《券契》[8](以下简称《山契》)收录了本卷第二件,定名为《甲午年(934)二月十九日索义成付与兄怀义佃种凭》;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9](以下简称《沙契》)也收录了本卷第二件,定名为《甲午年(934)索义成付与兄怀义佃种凭》。兹参酌各家定名,改拟为《后晋开运二年(945)十二月归义军左马步都押衙王文通勘寻寡妇阿龙还田陈状牒》,简称为《后晋开运二年寡妇阿龙牒》。
一 文书校录
本卷《籍帐》第652—654页、《释录》第二辑第295—298页、《敦煌研究》2003年第2期第42—46页、《敦煌学导论》第289—291页等有全篇录文,《山契》第117页、《沙契》第337—338收录了本卷第二件录文。兹据彩图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2册第317—318页影印本,并参考以上诸家录文,重新校录如下。
(一)
1. 寡妇阿龙
2. 右阿龙前缘业薄,夫主早丧。有男义成,先蒙
3. 大王1世上身着瓜州。所有少多屋舍,先向出买(卖)与人,只残
4. 宜秋口分地2贰拾亩已来3,恐男义成一朝却得上州4
5. 之日,母及男要其济命。(义成瓜州)去时〔一〕,地水分料5
6. 分付兄怀义佃种,恰居〔二〕,索佛奴兄
7. 弟言说,其义成地空闲6。更(兼佛奴房)〔三〕有南山兄弟7一人
8. 投来,无得地水居业,当便8义成地分贰拾亩,割与
9. 南山为主。其他(地),南山经得三两月余,见沙州辛苦
10. 难活,却投南山部族9。义成地分,佛奴收掌为主,针草
11. 阿龙不取。阿龙自从将地10,衣食极难。良求〔四〕得处 ,安
12. 存贫命。今阿龙男义成身死,更无丞忘(承望)11处。男女恩
13. 亲,缘得本居地水,与老身济倿(接)12性命。伏乞
14. 司徒阿郎仁慈祥照,特赐孤寡老身,念见苦累。伏
15. 听公凭裁判(处分)〔五〕。
16. 牒件状如前, 谨 牒。
17. 开运二年十二月 日寡妇阿龙牒
18.付都押衙王文通,细与寻
19.问申上者。十七日
曹元忠(签名)
(二)
1. 甲午年二月十九日索义成身着瓜州,所有父祖口分地叁拾贰亩,分
2. 付与兄索怀义佃种。比至义成到沙州得来日,所着官司诸杂烽
3. 子、官柴草等小大〔六〕税役,并总兄怀义应料13,一任施功佃种。若收得麦粟,任
4. 自兄收〔七〕,颗粒亦不论说。义成若得沙州来者,却收本地。渠河口作税役,不忓
5. 自〔八〕兄之事。两共面〔九〕平章,更不许休悔〔一○〕。如先悔者,罚壮羊壹口。恐人无信,
6. 故〔一一〕立文凭,用为后验。
7. 种地人兄索怀义(押)
8.种地人索富子(押)
9.见人索流住(押)
10.见人书手判官张盈润〔一二〕
(签名)
(三)
1. 都押衙王文通
2. 右奉判付文通,勘寻陈(状寡妇阿龙及)〔一三〕取地姪〔一四〕索佛奴,
3. 据状词理,细与寻问申上者。
4. 问得姪索佛奴称:先有亲叔索进君,幼小落贼,已经年
5. 载,并不承忘(望)。地水屋舍,并总支分已讫。其叔进君,贼
6. 中偷马两匹,忽遇至府,官中纳马壹匹。当时
7. 恩赐马贾,得麦粟壹拾硕,立机緤伍匹,官布伍匹。
8. 又请得索义成分地(贰拾贰亩,进)〔一五〕君作户主名,佃
9. 种得一两秋来。其叔久(居部族)〔一六〕,不乐苦地,却向南
10. 山为活,其地佛奴承受14,今经一十余年,更无别人论
11. 说。其义成瓜州致死,今男幸通及阿婆论此地者,
12. 不知何理。伏请处分。
13. 取地人姪〔一七〕索佛奴[左手 中旨(指)节]
14. 问得陈状阿龙称:有(男义成干犯)〔一八〕公条,遣着瓜
15. 州,只残阿龙。有分地叁拾贰亩,其义成去时,出
16. 买(卖)地拾亩与索流住,余贰拾贰亩与伯父索怀
17. 义佃种,济养老命。其他(地),佛奴叔贼中投来,本分居
18. 父业,总被兄弟支分已讫,便射阿龙地水将去。
19. 其时欲拟谘申,缘义成犯格,意中怕怖,因兹不
20. 敢词说。况且承地叔在,(不合论)诤〔一九〕。今地水主叔15却
21. 投南山内〔二○〕去,阿龙口分别人受用。阿龙及孙幸通无路存
22. 济,始过陈状者,有实。
23. 陈状寡妇阿龙 [右手 中旨(指) 节]
24. 问得佃种伯父索怀义称:先姪义成犯罪遣瓜州,地
25. 水立契仰怀义作主佃种,经得一秋〔二一〕,怀义着防马群不
26. 在。比至到来,此地被索进君射将。怀义元不是口分
27. 地水,不敢论说者,有实。
28.立契佃种人索怀义[左手 中旨(指) 节]16
29.右谨奉付文通,勘寻陈状寡妇阿龙及姪索佛奴、怀义
30.词理,一一分析如前。谨录状上。
31.牒件状如前,谨牒。
32.开运二年十二月 日左马步都押衙王文通牒
33.其义成地分赐进
34.君,更不回戈(过)17。其地
35.便任阿龙及义
36.成男女为主者。
37.廿二日 曹元忠(签字)
【校记】
〔一〕“义成瓜州”四字,只存右边残笔,但能看出是此四字,《籍帐》《释录》《李录》已补。
〔二〕 “恰”,原为“更”,从图版看,已将“更”改为“恰”。《李录一》录为“更恰”,《李录二》录为“恰更”。“恰”后一字只存右上部一点点残笔,《籍帐》补为“得”,《释录》《李录》补为“遇”。“居”字的左上部已经残,但从字形看应该是“居”。《籍帐》《释录》补为“房”,《李录一》录为“居”,《李录二》录为“房”。在“恰”和“居”之间约有六七字的残破,《李录一》补为“遇索进君回沙州就”八字,《李录二》为六个空格。
〔三〕“兼佛奴房”四字只存左边残笔,《籍帐》《释录》补为“弟佛奴房”;《李录一》直接录为“弟佛奴房”,《李录二》则为“佛奴房别”。从残笔看,“佛奴房”三字比较明显,而“兼”字不明显,但与同卷的“弟”却有差别。从其前后文义及残笔字形看,似为“兼”。
〔四〕“良求”,《释录》校为“恳求”。《李录一》录为“艮”,校为“恳”;《李录二》录为“良”,指出:“良,实也”,并以《汉书·吴王濞传》“征求滋多,诛罚良重”中颜师古注曰“良,实也,信也”为据作了说明。
〔五〕“处分”,原卷只残存“處”的右上部,从字形和文义可看出为“处”,后面的“分”是根据文义补的。《籍帐》《释录》《李录》已补。
〔六〕“小大”,《释录》录为“大小”,非原文。
〔七〕“任自兄收”之“任”为本行最后一字,已残,《籍帐》《释录》补为“任”。“自兄”,《李录二》校为“兄自”。
〔八〕“自”,是本行第一字,已缺,《籍帐》《山契》录为“□”,《释录》《沙契》补为“自”,兹从之。《李录一》为“自”,《李录二》为“□”。
〔九〕《释录》在“面”后补一“对”字,成“面对平章”;《李录》在“面”字前面补一“对”字,成“对面平间”。不必。
〔一○〕《释录》在此多录一“者”字。
〔一一〕“故”为本行第一字,原卷已残,《籍帐》《释录》补为“故”, 《山契》《沙契》径录作“故”。
〔一二〕“张盈润”,《籍帐》《山契》《沙契》录为“张”,《释录》为“张盈”,李录为“张盈润”。从字形看,应为“盈润”,兹从李录。
〔一三〕 “及”字上部残,《籍帐》《释录》《李录》已补。“状寡妇阿龙”, 《籍帐》《释录》《李录》已补,兹从补。
〔一四〕“姪”, 《释录》《李录》录为“侄”,非原形。下同。
〔一五〕“贰拾贰亩,进”五字有程度不同的残损,《籍帐》《释录》《李录》已补,兹从补。
〔一六〕“居部族”三字已残,《籍帐》《释录》《李录一》补为“居部族”,《李录二》录为“居戎狄”。
〔一七〕“姪”,《释录》未录。
〔一八〕“男义成干犯”,“男”字下部已残,“犯”字只有下部一点残笔,《籍帐》《释录》《李录》已补,兹从之。在“男”和“犯”之间有三字的残缺,《籍帐》《释录》《李录》补为“索义成”。根据上下文义,可补为,“义成干”。
〔一九〕“不合论”三字,右边已残,从字形、文义看应该是此三字,《籍帐》《释录》已补,《李录》径录。
〔二○〕“南山内”, 《释录》未录“内”字。
〔二一〕“得一秋”,原卷右部已残,从字形、文义看应该是此三字,《籍帐》已补,《释录》《李录》径录。
二 注 释
1. 大王:指清泰二年(935)去世的曹议金。清泰二年为乙未年,P.2638《后唐清泰三年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等状》曰:“(乙未年)大王临旷衣物唱得布捌阡叁伯贰拾尺。”索义成“身着瓜州”是甲午年,即934年,正属于“大王”曹议金时期。
2. 宜秋口分地:“宜秋”指宜秋渠。敦煌干旱少雨,完全靠祁连山的雪水灌溉,耕地都在水渠旁边,没有灌溉水的土地不能耕种,因此常常是地水连用。
唐令中的“先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的“口分”,并非指口分田,而是指一口应授之田,此句《白氏六帖事类集》引的授田令为:“先有永业者,则通其众口分数也。”“口分”一词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也多有使用,如大谷3150《康大智请田辞》曰:“大智家兼丁先欠口分不充,今有前件废渠道,见亭无人营种,请勘责充分。”此时(945年)均田制早已瓦解,并不存在永业田、口分田之说,这里的“口分地”,显然是指一口或一户应授之地或所有之地。参阅宋家钰《唐代户籍上的田籍与均田制》,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3. 原文为“贰拾亩已来”,是指大约数,“已来”犹言左右,这与第8—9行“义成地分贰拾亩,割与南山为主”是一致的。当时阿龙上状的目的是追回这一块土地,对具体的数字并没有太在意。《李录一》为“贰拾贰亩来”,与原文不符。
4. 上州:指沙州,因当时归义军的主要根据地是瓜、沙二州,其政权中心在沙州,对瓜州来说,沙州就是上州。“一朝却得上州之日”,是一不确定用语,即哪天义成获释回到沙州之日。如P.2943《宋开宝四年(971)五月一日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氾愿长等状》(《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第186页,录文参阅《释录》第五辑第25—26页;余欣《唐宋敦煌民生宗教与政治行为关系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68页):
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氾愿长与合城僧俗官吏百姓等
右愿长等,昨去五月一日,城头神婆神着不说神语,只言瓜州城隍及都河水浆,一切总是故暮(慕)容使君把勒。昨又都河水断,至今未回。百姓思量无计,意内灰惶。每有赛神之时,神语只是言说不安置暮(慕)容使君坐(座)位,未敢申说。今者合城僧俗官吏百姓等不避斧钺,上告王庭,比欲合城百姓奔赴上州,盖缘浇溉之时抛离不得。今者申状,号告大王,此件乞看合城百姓颜面,方便安置,赐与使君坐(座)位。容不容?望在大王台旨处分。谨具状申闻,谨录状上。
牒件状如前,谨牒。
开宝四年五月一日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氾愿长与一州僧俗官吏等牒衙推泛愿长信紫羊角一只献上大王。
5. “地水分料”,即属于自己的耕地,也可简称“地分”“地水”,如第8行就是“义成地分贰拾亩”,第10行也是“义成地分,佛奴收掌为主”,曹元忠的判词也是“其义成地分赐进君”。在水部式和敦煌契约文书中也有“地分”,都是指“土地”。如P.2507《唐开元二十五年(737)水部式残卷》第112行:“其京城内及罗郭墙,各依地分,当坊修理。”另如P.3394《唐大中六年(八五二)僧张月光博换地契》:“又僧法原园与东庑、地分、井水共用。”由于敦煌降雨量非常少,主要靠灌溉耕种。只有有水并且能够灌溉的土地才能耕种,所以往往“地水”连用,如第13行就是阿龙“本居地水”。参阅朱雷《P.3964号文书〈乙未年赵僧子典儿契〉中所见的“地水”——唐沙、伊州文书中“地水”、“田水”名义考》,载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七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又见朱雷著《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李录一》将“地水分料”分开解释,认为“地水”即田地,“分料”应读为“份料”,“意即土地所有者份内所当承担的各种税役。一云‘承料役次。即下件《索义成田地托付凭》所载包括‘渠河口作在内的‘所着官司诸杂、烽子、官柴草等大小税役。”
6. “空闲”,指没有种庄稼的土地,即荒地。索怀义佃种后,由于“着防马群”而离开家乡,使地抛荒。荒地属于归义军时期请田的范围。参阅刘进宝《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第23—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7. “南山兄弟”,即索进君。
8. “便”是租的意思。
9. “南山部族”,即“南山”,主要出现于归义军时期,指沙州、瓜州南面的祁连山谷地。据《史记·大宛列传》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10]归义军时期的“南山”或“南山部族”,则是指小月氏的遗种——仲云。《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载:“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胡卢碛。云仲云者,小月氏之遗种也,其人勇而好战,瓜、沙之人皆惮之。”[11]敦煌文书中,多次出现“南山”或“南山部族”与归义军之间和战的记载。如《年代不明(964)归义军衙内酒破历》载:“肆月贰拾柒[日]供南山别力逐日酒壹斗”;“五日,迎南山酒壹角”;“六日,衙内面前看南山酒壹斗”;“陆日供衙前仓住南山逐日酒贰斗”;“城南园看南山酒壹角”;“拾陆日,供南山逐日酒贰斗”等。此《酒帐》还有招待甘州、西州、伊州、于阗使臣的许多记载,但南山不称使,可能是其政治势力介于部落与地方王国之间,主要从事畜牧。P.2718《李绍宗邈真赞》有“为国纳效于沙场……破南山”的记载。S.4445《何愿德贷褐契》也有“龙家何愿德于南山买卖小禄”的记载。参阅荣新江《小月氏考》,载《中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1990年;黄盛璋《敦煌文书中的“南山”与仲云》,载《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杨铭《敦煌文书中的Lho bal与南波——吐蕃统治时期的南山部族》,载《敦煌研究》1993年第3期;邵文实《敦煌遗书中的“南山”考》,载《社科纵横》1992年第6期。
10. “将地”,失去土地,即原属阿龙的土地被别人请去。这与后面阿龙陈状中的“便射阿龙地水将去”、 索怀义状中“此地被索进君射将”是一致的。关于归义军时期的请田,请参阅刘进宝《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第21—28页。
11. “丞忘”,本卷第三件第5行为“承忘”,或可释为 “承望”,即指望、想望。也就是说阿龙得知义成已经去世,便不再指望“男女恩情”,即依靠子女供养。第三件的“承忘”是说:索进君从小就落入贼手,没有任何音讯,是死是活也不知道,根本没有指望他会回来。
12. 原卷为“倿”,同“佞”,但文义不通。《籍帐》《释录》录为“接”,仅仅是偏旁的互换,而文义明确。
13. “应料”,承担。即附着于土地上的“诸杂烽子、官柴草等小大税役”都由土地耕种者承担。 “料”有“应役”之意。王梵志诗第279首有“身役不肯料,逃走背家里”。《太平广记》卷32《颜真卿》载:“杨国忠怒其不附己,出为平原太守。安禄山逆节颇著,真卿托以霖雨,修城浚壕,阴料丁壮,实储廪。”[12]
14. “承受”,即继承。承与受为同义复合。参阅《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第59—60页。
15. 这里的“地水主”指土地的实际拥有人索佛奴,“地水主叔”指索佛奴的叔叔索进君。当索进君逃回南山后,其通过请射所获得的土地便由侄子索佛奴继承。
16. 第13、23、28行为指节押,此为古代押记之一种,敦煌谓之“画指为记”。据《李录一》注释第17:盖与脚板、手印同义。其法:比画出男左手女右手中指各节长短,代替本人之签字画押,用备日后验证。所见画法有三:一是画出男左手女右手中指侧视之形,勾勒出中指各节位置;二是比量标画男左女右中指长短及各节位置;三是并不画出中指全长,只点记男左手女右手中指各节所在,呈现距离不等的三点。唐五代各种指节押向无实物传世,唯敦煌遗书中多有保存,堪补传世之缺。
17. “回戈”即回过,它是一俗语词,其义为回还。参阅刘敬林《敦煌文牒词语校释》,载《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1期。陈永胜认为是“办理过户手续”,参阅陈永胜《〈后晋开运二年( 945) 寡妇阿龙地产诉讼案〉若干法律问题析论》,载《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三 内容分析
本件文书是一案卷,其主要内容是:945年(后晋开运二年)12月某日,寡妇阿龙直接呈状沙州刺史曹元忠,请求索佛奴返还已占用十余年的口分地产22亩,以济接生路。原来在十一年前的后唐清泰元年(甲午年、934年)的3月19日,阿龙的儿子索义成因犯罪被流放瓜州。他们原有祖传的口分地32亩,在义成去瓜州前,将其中的10亩卖给了索流住,另外的22亩交与义成的伯父索怀义佃种,并订有契约。约定佃种人索怀义获取土地上的所有收获物,但要承担耕种该地应缴纳的赋税和有关的徭役。如果义成回到沙州,就收回由伯父索怀义佃种的土地。而索怀义在佃种此22亩土地一年后,由于“着防马群”即成了牧马人而离开家乡,再未耕种土地,使此22亩土地抛荒。
恰在此时,又有索氏族人索进君回到沙州。索进君幼小落入贼手,一直没有任何音讯,索氏家族连其死活都不知道,更没有指望他能回来,所以在分割家产时就没有考虑到索进君,也就没有给他预留土地屋舍。当索进君从南山部落偷马两匹回到沙州后,归义军政府收马一匹,并给付了一定的奖励。索进君以定居为由申请口分地,官府遂将原属索义成的这22亩荒地分与索进君。从“割与南山为主”“进君作户主名”、进君“便射阿龙地水将去”“此地被索进君射将”可知,索进君便成了此22亩土地法律上的主人。
当官府在分配这22亩荒地时,阿龙虽想到官府论说争夺产权,但顾虑到她系罪犯家属,恐受斥责而未呈状。种地人索怀义外出牧放官马而不知情,回来后也因为并非是自己的口分地,即不是土地的主人,也就没有到官府论说这些土地的归属。
索进君由于久居南山部族而不谙农耕,在敦煌居住一段时间后即嫌艰苦而复归南山,他的22亩土地就被其族侄索佛奴承受(继承),即索佛奴又成为此22亩土地实际上的主人(并非法律意义上的主人)。
现在,义成已死于瓜州,而年迈的阿龙与年幼的孙子索幸通祖孙二人相依为命,饥寒流乞,无法生活。于是寡妇阿龙呈上诉状,要求索佛奴归还其22亩土地。同月十七日,曹元忠就批交左马步都押衙王文通查核此案。
王文通首先找出了当年(甲午年、934年)索义成流放前夕寡妇阿龙和索怀义关于此22亩土地的佃种契约,并询问了此段土地法律上的主人索进君的侄子索佛奴(目前实际上的主人)、陈状人寡妇阿龙、佃地人索怀义。经过调查取证,将阿龙的申诉、阿龙与索怀义当年的佃种契约、询问索佛奴、阿龙和索怀义的笔录5份文件一同报至归义军节度史曹元忠。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沙州刺史曹元忠亲自作了既维护官府先前决定,又关切弱者权益的批示:分配给进君的土地不能反悔,但进君已回到南山,土地的使用与收益仍由阿龙祖孙支配。这样一个普通的民间地产纠纷,经过提起诉讼、立案受理、调查取证、判决结案等四个基本的审判过程,而且得到了节度使的高度重视,可见当时的经济生活和敦煌社会安定的密切关系。
本卷第一件文书是阿龙要求收回土地的牒状,这是没有疑义的。第二件佃种契约的一方是义成的伯父索怀义,而另一方是义成还是阿龙则有歧义,从《山契》(《甲午年(934)二月十九日索义成付与兄怀义佃种凭》)和《沙契》)定名(《甲午年(934)索义成付与兄怀义佃种凭》)可知,他们认为另一方是索义成。
本件的人物关系比较简单:阿龙是义成的母亲,怀义是义成的伯父、阿龙的婆家兄长。从第2行的“付与兄索怀义佃种”、第3行的“并总兄怀义应料”、第4行的“任自兄收”、第5行的“不忓自兄之事”、第7行的“种地人兄索怀义”可知,怀义并不是以义成的伯父、而是以阿龙兄长的身份来签订此佃种契的,因此,本件可定名为《甲午年(934)寡妇阿龙付与兄怀义佃种凭》。
第三件是王文通的询问笔录,为什么第一个询问的是索佛奴呢?并且索佛奴不是作为主体,而是作为索进君侄子的身份出现的。因为从法律上来说,此段土地的所有者是索进君,官府仍然认为这是索进君的土地,作为索进君侄子的索佛奴仅仅是代为耕种或实际上的占有,并没有经过法律程序或政府的认可,所以王文通所询问的是“取地姪索佛奴”(第2行),这里的“取地”,指从法律上获得土地,也是索佛奴画押中的“取地人”索进君。第13行的“取地人姪索佛奴”都是指取地人(索进君)的侄子索佛奴。本件文书的主体是法律上的土地所有者索进君,第4行的“问得姪索佛奴称”,也是以索进君作为主体的。第29行王文通的牒文也清楚地说明,他所了解询问的三个人:上状人——寡妇阿龙、土地拥有者的侄子索佛奴、土地的租佃者索怀义。
在询问陈状人寡妇阿龙时,第20行的“承地叔”是指佃地人索怀义,这里的“承地”是按契约佃种土地,“叔”是指索义成的叔叔。同行的“地水主叔”又不一样,“地水主”是指现在土地的实际拥有者索佛奴,“叔”是指索佛奴的叔叔索进君。
文书最后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批示:“其义成地分赐进君,更不回戈(过)。”即原属义成的土地分配给了索进君,这是不再改变的。但由于进君早就离开了沙州,土地的主人不在了,由其侄子索佛奴耕种。而寡妇阿龙及孙子索幸通属于老小,没有生活来源,因此,“其地便任阿龙及义成男女为主者”,即由阿龙和其孙子耕种使用。这里的“义成男女”就是指义成的儿子、阿龙的孙子“索幸通”。
本卷文书在归义军经济史研究上有着重要价值,涉及到土地请射、租佃、买卖及耕种土地所应该承担的赋役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案的调查取证方式,与现代审理民事案件的方式有相似之处,即主要通过询问当事人调查取证。此案中不仅有书证(租佃契约),而且有当事人(托付人、受托付人)的陈述。每位当事人陈述完毕后都要签字画押,构成了完整的证据体系。这件契约文书所反映的各种法律制度,包括土地制度、证据制度、契约效力等,为我们进一步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深刻体察其特征提供了佐证。
参考文献:
[1]商务印书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敦煌研究院.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3]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M].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
[4]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5]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2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17.
[6]李正宇.敦煌遗书一宗后晋时期敦煌民事诉讼档案[J].敦煌研究,2003(2).
[7] 李正宇.敦煌学导论[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289-291.
[8]山本达郎,池田温.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第三卷:券契[M].东洋文库,1987.
[9] 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0]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162.
[11]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918.
[12]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