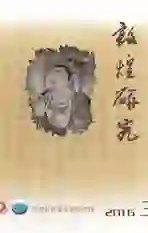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塑像砖墓(二)
2016-07-21戴春阳


内容摘要:敦煌佛爷庙湾墓群发掘的6座唐代模印塑像砖墓中,其中弧方形的墓葬形制参照长安地区唐墓可知属高等级墓葬。文章分析了墓葬年代、墓葬等级及P.2523《敦煌名族志》的编撰年代,认为两者均为开元年间,因而认为M123、124、125等墓为外任归葬的敦煌望族——阴氏家族墓葬,其中阴稠或阴仁协以及阴仁希可能与M123具有对应关系。
关键词:敦煌模印塑像砖;高等级墓葬;敦煌名族志;开元年间;阴氏家族墓
中图分类号:K879.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3-0009-08
Abstract: In the six Tang dynasty tombs made of bricks with impressed statues found at Dunhuang, those in arc-square form can be identified as high-class tombs based on tomb forms from the Changan region exemplary of the perio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ate and class of the tombs as well as the date when P.2523 (Records of the Prominent Families at Dunhuang)was written, and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both date back to the Kaiyuan era. Tombs M123, M124, and M125 were the tombs of the Family Yin, a powerful family at Dunhuang, of whom Yin Chou(or Yin Renxie)and Yin Renxi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M123.
Keywords: bricks with impressed statues from Dunhuang; high-class tomb; Records of the Prominent Families at Dunhuang; Kaiyuan era; tombs of the Family Yi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三 墓主与相关问题
(一)墓葬等级与外任官员葬制习俗
如前所述,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塑像砖墓,其墓葬形制可分两型,即A型:弧方形;B型:方形[1],与唐代严格的墓葬等级制度具有密切联系。西安地区(含周边)发掘唐代墓葬数以千计,作为京畿,其墓葬制度具有规范意义。尤其是其中许多墓葬出土有墓志,对厘定墓葬时代、等级提供了可靠依据。
A型弧方形砖室墓 弧方形规格较高,唐初有着严格的使用限制。李渊从弟李寿作为从一品的郡王,其墓室使用的也只是方形[2]。高宗至玄宗时期,开始见于三品以上的品官,肃宗以后才见于正四品[3]。
B型方形砖室墓 长安地区使用砖室墓的均为中、高级品官[3]43-44 [4]。此外,有唐一代,许多三至四品的高官使用了方形土洞墓,如从三品左卫将军独孤开远墓[5]、正四品上太子左内率司马睿墓[6]、正四品下壮武将军段元哲墓[5]94等。
而大量唐代墓志所反映的唐代墓葬制度、习俗以及敦煌文书所涉相关内容,对我们考察M123、124、121等墓墓主的范围不无裨益。
(二)关于唐代外任官员葬制习俗
古代官员任职有回避本籍的制度,除两京外,多于籍外任官[7]。唐代墓志表明,外官死后埋葬形式主要有葬于任官居住地和归葬、权葬两类。
如葬于任官所在地的屈突通,作为唐初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两唐书有传。《旧唐书·卷59·屈突通传》称:“雍州长安人。” [8]《新唐书·卷89·屈突通传》云:“其先盖昌黎徒何人,后家长安。”[9]《大唐故左光禄大夫蒋国公屈突府君墓志铭》详细记载了其籍贯的变化和卒葬过程:
公讳通,字坦豆拔,昌梨徒和人{1}。高祖恒,中领军,随魏氏迁于洛也。永熙之季,公大父又徙关中,今为雍州长安人也{2}……(武德)九年(626)授使持节十一州诸军事洛州刺史,加左光禄大夫……贞观二年(628)构疾,其年十月十九日薨于官舍……以其年十一月廿八日,葬于洛州河南县千金乡玄门里之北邙山。” [10]
“利于便近”[11],应是就地而葬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任职期间卒故的归葬则为更常见的丧葬现象[12]。归葬,是原始社会族葬制的遗俗,也是古代社会重要的墓葬习俗。回归故里或先辈在致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家族聚集地,如避王莽乱而居敦煌数百年之久的令狐家族,至北周令狐整迁居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因而令狐德棻为其父所撰《令狐熙碑》谓熙“归葬于□(宜)州华原县”[13]{3},故两唐书《令狐德棻传》称其“宜州华原人”[14];而德棻四世孙彰再迁陕西富平,而为“京兆富平人”[15];彰孙梅则“归葬于河南府河南县伊汭乡中梁村之南原,接先公常侍(令狐通)封树之震位”[16]。以上诸事强调的“归”葬表现的似为家乡认同,但其核心,实质仍是宗族或家族的血缘纽带。因而,除特殊情况,即使远在异邦绝域,“扶护神灵”,哪怕“匍匐万里”[17]、“徒跣万里”[18],也要“克遂归窆”[19],即所谓“狐死正丘首”之义[20]。《旧唐书·卷72·李百药传》载,李百药“至性过人,初侍父母丧还乡,徒跣单衣,行数千里,服阙数年,容貌毁悴,为当时所称”[21]。又如《姜谟墓志》称:“公讳谟,字孝忠,秦州上邽人也……拜持节秦州诸军事秦州刺史,转陇州刺史……有诏返公入朝 ……以贞观元年(627)八月六日薨于京第……夫人同郡赵氏……以四年(630)八月十三日薨于京第。粤以六年(632)十月十日合葬于秦州东南岩池谷。”[22]敦煌文书P.2640《常何墓碑》:“其先居河内温县,乃祖游陈留之境,因徙家焉,今为汴州浚仪人{1}也……永徽三年(652),迁使持节都督黔思费等十六州诸军事、黔州{2}刺史……以四年(653)五月十六日薨于府馆……六年(655)八月,反葬于故里。”
此外,还常见官员卒于任所因各种原因不能返乡的权葬、暂厝、权殡、权瘞等,其“权”的目的当然是期冀归葬祖茔。但权葬后有两种结果:一是迁移归葬,但据墓志统计{3},其量仅为四分之一强;更多的则是权葬后并未迁葬,约达三分之二。即不脱以上两种形式,故此不赘述。
(三)佛爷庙湾模印砖墓墓主范围
M123、124等墓的墓葬形制表明其墓主亦应系具有相当品秩的官宦,其时符合这一条件的应有两类:一是在任品官;一是任职异地的品官,以故里而葬沙州。
《旧唐书·卷40·地理志·沙州》载唐代沙州为下州[23],其刺史品秩为正四品下[24]。《新唐书·卷40·地理志·陇右道》载:“沙州敦煌郡,下都督府。”[25]“下都督府,都督一人,从三品”[26]。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0》“沙州”条记其为中都督府[27]。中都督府都督为正三品[26]1315。
沙州最高长官,若依《新唐书》《元和郡县图志》沙州为下、中都督府说,而M123又约8世纪前半叶,则M123墓主与西安地区的墓葬形制的使用规律是一致的。当然,这里还存在一些前提性的条件:首先,需确定是否为相应时限内的都督;其次,是否葬于沙州?因而,首先应厘清沙州由州升都督府的时序问题。
中华书局据武英殿聚珍版出版的宋王溥《唐会要·卷70·陇右道》载:“新升都督府:沙州,永徽二年(651)五月升。”[28]敦煌藏经洞出土钤有“沙州都督府印”的唐代写本,首见于S.0514《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大历四年(769)手实》。池田温先生据此认为《唐会要》所记“永徽二年”当“永泰二年”之误[29]。朱悦梅、李并成先生则认为“史籍中关于沙州于永徽二年升都督府的记载与史实并不相悖”[30]。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会要》则载:“新升都督府:沙州,永泰二年(766)五月升。”[31]证实池田先生之见可谓卓识。关于沙州由州升都督府的时间,刘安志先生曾有专文研究,旁搜远绍,认定“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是在唐代宗的永泰二年(766)”[32]。该文考论精当,其说可从。故M123墓主身份可排除沙州都督。
如前所述,沙州为下州,州刺史正四品下。M123作为客观存在,沙州最高长官依制循例使用弧方形砖室墓也在情理之中。现可知7世纪末至8世纪前期历任沙州刺史有李无亏、陈玄珪、李思贞、李庭光[7]56、能昌仁、杜楚臣、张嵩(孝嵩)、贾师顺等[33]。其中唯李无亏、李思贞卒于任所,但却年代较早且又分别归葬于“稷州武功县三畦原”[34]和“雍州万年县淳风乡务政里”[35]。
这就表明,M123的墓主应为属籍敦煌而任职异地,最终归葬故里的相应品官。
(四)从《敦煌名族志》看墓主范围
敦煌文书P.2625《敦煌名族志》残卷现存部分载敦煌名族张、阴、索氏,其中张氏仅存结尾,索氏仅存起首部分,完整保存的为阴氏。敦煌阴氏,在前凉时期已为大姓,《敦煌名族志》所载阴氏未记族源,仅称“隋唐以来,尤为望族”。可知阴氏乃敦煌地区唐代崛起的新兴望族。《敦煌名族志·阴氏》虽似族谱,但其最大特点,是以在世和出仕作为入志标准。入志者均在世——“五代义居”;所记仅限于族中有功名者,阴稠一支四代17人均出仕为官。其排列,既以辈分先后为序,又以官职高下为依规。因而,我们有必要首先厘定《敦煌名族志》的编撰年代。
1. 关于《敦煌名族志》的编撰时间
P.2625《敦煌名族志》的编撰时间,池田温、郑炳林先生均有系统研究。池田温先生据文书所涉凉州都督郭元振和相关文书中阴仁协、阴嗣瑗的任职经历以及阴稠、阴祖的板授问题等相关年代背景,认为“《敦煌名族志》的编撰年代应在景龙四年(景云元年710)左右”[36]。郑炳林、安毅先生则据文书所涉节度使的设置年代及相关节度使史事,认为“《敦煌名族志》的撰写年代为开元十一至十五年间”[37]。
应该说郑炳林先生“根据阴修己被‘节度使差专知本州军兵马看,这里的节度使指河西节度使,河西节度使设置于景云二年(711)。因此,《敦煌名族志》的撰写不会早于景云二年(711)”[37]5,这样以具有时限意义的节度使的设置来确定《敦煌名族志》的上限,无疑较池田温先生的年代考论更为简洁且鞭辟近里。但接下来,郑炳林先生称文书“只记述节度使而不提姓名”,是“由于王君在当时口碑不好”,遂将阴修己蒙“节度使差”“专知本州军兵马”的时间系之于开元十一年(723)或开元十五年(727),“非为迎接吐谷浑归朝,就是对吐蕃用兵”[37]6,然此结论惜无任何令人信服的依据,仅臆度而已。
即如郑炳林先生所言可能之一的开元十一年(723),“九月,壬申,(吐谷浑)帅众诣沙州降,河西节度使张敬忠抚纳之”[38]。此乃“四海来假”[39]的盛世景象,但《敦煌名族志》也“不提”河西节度使张敬忠的“姓名”,不知应作何解释?
此外,开元“十五年(727),春,正月,辛丑,凉州都督王君破吐蕃于青海之西”[38]6776,乃王君将兵的经典之役,《旧唐书·卷103·王君传》记之甚详,开元十四年(726){1}:
冬,吐蕃大将悉诺逻率众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烧市里而去。君以其兵疲,整士马以掩其后。会大雪,贼徒冻死者甚众,贼遂取积石军西路而还。君令副使马元庆、裨将车蒙追之,不及。君先令人潜入贼境,于归路烧草。悉诺逻还至大非川,将息甲牧马,而野草皆尽,马死过半。君袭其后,入至青海之西,时海水冰合,君与秦州都督张景顺等率将士并乘冰而渡。会悉诺逻已度大非山,辎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侧,君纵兵尽俘获之,及羊马万数。君以功迁右羽林军大将军,摄御史中丞,依旧判凉州都督,封晋昌伯。拜其父寿为少府监,仍听致仕。上又尝于广达楼引君及妻夏氏设宴,赐以金帛。夏氏亦有战功,故特赏之,封为武威郡夫人。[40]
可见王君不仅“骁勇善骑射”[40]3191,更擅为将谋略;是役还使王君的仕途达到巅峰。至于郑文提到同年吐蕃攻陷瓜州,“执瓜州刺史田仁献及君父寿”,此事遂致王君“口碑不好”[37]6。此说颇令人生疑。王君开府于凉州,很难看出千里之外的瓜州陷蕃会使王君“口碑不好”。即便联系吐蕃陷瓜州后,颇富戏剧性地“纵僧徒使归凉州,谓君曰:‘将军常欲以忠勇报国,今日何不一战?君闻父被执,登陴西向而哭,竟不敢出兵” [40]3191之举,似乎也很难影响到王君“口碑”。“所谓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谓之“将善”{2}。此事恰正反映出王君非乃市井放对斗狠徒逞一时之快的莽夫,而是颇善审时度势、深谙为将之道可负重寄的优秀军事将领。因而,本于臆断的所谓“口碑不好”遂“只记述节度使而不提姓名”基础上的“开元十一年(723)至开元十五年(727)间”的年代认定是难以令人信从的。
事实上,与节度使设置类似,阴氏子弟与特定年代背景紧密相联的相关任职,为我们了解文书的编撰年代提供了重要信息。P.2625《敦煌名族志》中阴仁干次子阴嗣监“见任正议大夫、北庭副大都护、瀚海军使兼营田支度等使”。其中“见任”“北庭副大都护”之职,可判明文书编撰的时间。
武则天长安二年十二月戊申(703年元月七日),于庭州置北庭都护府{3}[38]6561,管理天山以北的西突厥故地,在建置上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虽见载于史籍[25]1047,但既无建置时间亦未言具体官员。正史记载担任北庭大都护的唯阿史那献一人{4}。因而有必要以阿史那献为中心,梳理景云二年(711)以降北庭都护府历任都护脉络如下。
阿史那献,亦称献、史献,是贞观降唐的原西突厥可汗阿史那弥射之孙。阿史那弥射显庆二年(657)参加平阿史那贺鲁的战争,次年,以功封“兴昔亡可汗兼右卫大将军、昆陵都护”,统辖西突厥五咄六部落[41],龙朔二年(662),受诬被杀[41]5189。垂拱初,“擢授弥射子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昆陵都护,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六部落……如意元年,为来俊臣诬谋反被害。其子献,配流崖州。长安三年(703),召还。累授右骁卫大将军,袭父兴昔亡可汗,充安抚招慰十姓大使”[38]5189。
《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下》载:“长安中,以阿史那献为右骁卫大将军,袭兴昔亡可汗、安抚招慰十姓大使、北庭大都护。”[42]其结衔中出现“北庭大都护”一职,但其诸结衔显系“累授”的结果{1}。观察阿史那献的仕宦轨迹及相关人物的历职,是可以确定其任北庭大都护的时间的。
长安三年(703),自配流地还,袭兴昔亡可汗,参其祖弥射、父元庆任职例,同时当授右骁卫大将军{2}。
景云二年(711):
十二月,癸卯,以兴昔亡可汗阿史那献为招慰十姓使。[38]6669
先天元年(712):
十一月,史献除伊西节度兼瀚海军使,自后不改。至开元十五年三月,又分伊西、北庭为两节度……瀚海军,置在北庭都护府。[43]
北庭都护领伊西节度等使。[44]
开元初(713):
郭虔瓘……开元初(713),累迁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二年春……瓘以破贼之功拜冠军。
大将军,行右骁卫大将军。[45]
开元二年(714)二月:
西突厥十姓酋长都担叛。三月……阿史那献克碎叶等镇,擒斩都担,降其部落二万余帐。[38]6698
上引表明,最迟于先天元年(712)阿史那献在吕休璟之后接任北庭都护{3},并领伊西节度兼瀚海军使{4}。但其主要使命显然是以其与西突厥的历史渊源,以“招慰十姓大使”的身份重新确保唐对西突厥十姓故地的统治的战略职责{5},因而被授以极重的事权,拥有节制降唐西突厥诸部落和伊吾以西“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外任之重莫比焉”[46]。
开元二年(714)二月都担叛,三月阿史那献即克伊塞克湖以西的碎叶等镇,擒斩都担。可见阿史那献主要精力用于经略西突厥十姓故地,故对都担的反叛能够及时作出反应和处理。这样就不难理解开元初至二年春北庭都护又由郭虔瓘兼署的任职调整。阿史那献经略伊塞克湖地区并率大军西征期间,东突厥可汗默啜乘机“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将兵围北庭都护府,都护郭虔瓘击破之”[38]6696。
阿史那献西征平定都担之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阿史那献不仅完全收复了其祖左厢兴昔亡可汗的原有疆土{6},而且通过讨伐都担,收复了被叛酋都担所占据的碎叶城,深入楚河以西控制了原右厢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府所辖区域{7},有效地保障了唐王朝对西突厥十姓故地的统治,故有“玺书嘉慰”:
十姓部落,比多款附,蕞尔都担,敢违背诞,以卿忠果,令其讨伐,遂斩首丧元,并儿及妻,兼复胡禄屋阙啜等五万余帐。壶浆塞陌,襁负而来,自非信著远番,何以翕然至此?边陲宁谧,系卿是赖。虽郑吉之护南道,班超之临西域,无以过焉。言念勤劳,岂忘鉴寐。[47]
值得关注的是,不仅玺书嘉慰,而且西域地区传统的以安西都护府为主、北庭都护府为辅的军政格局也发生了调整。
开元二年(714)六月:
丁卯,北庭大都护、瀚海军使阿史那献枭都担首,献于阙下,并擒其孥及胡禄(屋)等部落五万余帐内属。”[47]1606
依制大都护府大都护一人,从二品;副大都护二人,从三品[48]。北庭都护府升格为北庭大都护府,开创了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分理天山南北成为并列的西域两大军政中心(图1)。而这显然是伴随着阿史那献对西突厥故地的经营及其地位的上升而出现的新局面。
玄宗赐书嘉慰后,苏颋再代朝廷撰《授阿史那承献特进制》云:
黄门:建官制爵,立化之本;树善崇功,惟能是任。招慰十姓兼四镇经略大使、定远道行军大总管、北庭大都护、瀚海军使、节度巴(已)西诸蕃国、左骁卫大将军摄鸿胪卿、上柱国、兴昔(亡)可汗阿史那承献……茂勋则远,已宠于登坛;厚秩未加,俾荣于开府。亚台湾之典,群议允集。可特进,余并如故,主者施行。[49]
制文中再次确认阿史那献“北庭大都护”并加“兼四镇经略大使”“定远道行军大总管”和“节度已西诸蕃国”。此制文未署时间,参酌开元三年(715)阿史那献转而与北庭都护汤嘉惠互为犄角抗击东突厥的史实及相关人物结衔及结衔的变化,制文显应撰于开元二年(714),限于篇幅此不赘述{1}。可见平定都担,使得阿史那献权倾西域,达到其仕途生涯的顶峰。
值得注意的是,《册府元龟·卷133·帝王部·褒功二》载,开元“三年(715)二月,郭虔瓘为北庭都护”[47]1607。不久,汤嘉惠接任北庭都护[38]6710。郭虔瓘擢“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50]。同年(715)五月,阿史那献以定边(远)道大总管的身份与北庭都护汤嘉惠等“相互应援”以遏东突厥可汗默啜[38]6710。
从郭虔瓘、汤嘉惠先后任北庭都护,可见北庭大都护府的建制已于开元三年(715)取消。由于开元四年(716)起,唐王朝为加强对西域等边疆地区拥有重权的外任军政要员的控制,采取由亲王遥领大都护的措施,如以陕王嗣升为安西大都护,原安西大都护郭虔瓘转“安西副大都护”[51]。北庭再无升格为大都护府的记载。这就表明,北庭大都护府仅存在于开元二年(714)。
由此,我们可以确认,由于P.2523《敦煌名族志》强调阴嗣监“见任”北庭副大都护、瀚海军使兼营田支度等使,故文书编撰年代为开元二年(714)。
2. 模印砖墓与阴氏家族
隋代制丧礼,就丧制中有关葬仪与官员品级联系:“隋文帝初定礼”,以“三品以上”“七品以上”和“八品以下,达于庶人”作为葬礼等级的界限[52],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唐承隋制。但大量唐墓的发掘表明,在墓葬形制上,三、四品官员墓葬并无明显区别。尤其外任官中诸州长官虽多四品下,但在本地却属至尊,这一点在边远州郡更为突出。因而在远离京畿的州郡中其上限可以四品为界。即以M123、124为例,前者呈弧方形,形制属较高等级,但边长约3.5米;后者墓室虽作方形,但边长近4米。参照长安地区墓葬成例,两者均应属较高官员的墓葬。
开元二年(714)《敦煌名族志》所录阴氏一门阴稠、阴祖两支三代21人中,四品以上官员达7人(表2){2}。
古代官、爵、勋、封叠床架屋,但其核心“赋事受奉者,惟职事一官,以叙才能,以位勋德,所谓施实利而寓虚名;勋、散、爵号,止于服色、资荫,以驭崇贵,以甄功劳,所谓假虚名佐实利者也”[53]。其中所谓“职事”以确保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虚名”(勋、散、爵)以保障个人品位级别。尤唐代散阶维系着如薪俸、班序、车舆、衣服、刑罚、给田免课、丧葬等实际待遇,并使其不因职事变动而丧失“品级”。
阴稠以高年获颁授邓州刺史,只要经济能力允许,自可使用相应品级墓葬制度{1}。开元二年(714),阴稠已近“期颐”自是希见;其子仁协、仁希亦当“古稀”以上;其孙嗣业、嗣监、嗣璋当五旬左右,均属迟暮。作为敦煌望族,其丧必聚族而葬。佛爷庙湾模印砖墓在敦煌机场南缘,地貌因施工而改变,故茔圈不存。虽发掘简报未介绍诸模印砖墓的具体分布和排列规律与特点,但据M121、123、124、125的连续编号特点来看,此四墓定相距不远,因而很可能属于某家族墓地。结合阴氏阴稠一支于开元二年(714)所呈现的集中的年龄阶段和应有的相应墓葬等级,有理由相信M123等模印砖墓为阴氏家族墓葬。其中阴稠或仁协抑或仁希之墓与以M123为中心的诸墓具有密切的对应关系。
参考文献:
[1]戴春阳.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塑像砖墓(一):墓葬举要与年代[J].敦煌研究,2015(5):2.
[2]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4(9):71,79.
[3]宿白.西安地区的墓葬形制[J].文物,1995(12):44.
[4]齐东方.试论西安地区唐代墓葬的等级制度[G]//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90,298-299.
[5]孙秉根.西安隋唐墓葬的形制[G]//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152-153,183.
[6]贠安志,王学理.唐司马睿墓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5(1):44-49.
[7]戴春阳. 沙州刺史李庭光相关问题稽考[J].敦煌研究,2014(5):52.
[8]刘昫,等.旧唐书:第7册:屈突通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2319.
[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12册:屈突通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3749.
[10]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大唐故左光禄大夫蒋国公屈突府君墓志铭[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13-14.
[11]白居易.白居易集:第4册:唐故虢州刺史、赠礼部尚书崔公志铭并序[M].北京:中华书局,1979:1471.
[12] 李斌城,李锦绣,张泽咸,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归葬先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93-
295.
[13]令狐德棻.隋故(阙8字)桂州总管武康郡开国公令狐使君碑铭并序[M]//周绍良.全唐文新编:第3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1556.
[14]刘昫,等.旧唐书:第8册:令狐德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2596.
[15]刘昫,等.旧唐书:第11册:令狐彰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3527.
[16]令狐棠.唐故棣州刺史兼侍御史敦煌令狐公(梅)墓志铭并序[M]//吴钢.全唐文补遗:第6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170.
[17]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唐故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张公墓志铭[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2022.
[18]刘昫,等.旧唐书:第8册:刘德威传附孙易从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2678.
[19]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大唐故袁州宜春县尉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2064.
[20]戴圣.礼记正义:卷6:檀弓上[M]//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1281.
[21]刘昫,等.旧唐书:第8册:李百药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2577.
[22]张维.陇右金石录:卷2:姜谟墓志[M].兰州: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1944(民国三十三年).
[23]刘昫,等.旧唐书:第5册: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1644.
[24]刘昫,等.旧唐书:第6册:职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93.
[2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4册: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45.
[2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4册:百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15.
[27]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25.
[28]王溥.唐会要:卷70:陇右道[M].北京:中华书局,1955:1238.
[29]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G]∥榎博士还暦记念东洋史论丛. 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31-35.
[30]朱悦梅,李并成.《沙州都督府图经》纂修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J].敦煌研究,2003(5):62.
[31]王溥.唐会要:卷70:陇右道[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7册:史部365:政书类.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55.
[32]刘安志.关于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问题[J].敦煌学辑刊,2004(2):64.
[33]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500-502.
[34]王团战.大周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及征集到的三方唐代墓志[J].考古与文物,2004(1):24.
[35]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唐故沙州刺史李府君墓志铭并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07.
[36]池田温.唐朝氏族志研究:关于《敦煌名族志》残卷[G]// 夏日新,韓升,黄正建,等译.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677-680.
[37]郑炳林,安毅.敦煌写本P.2625《敦煌名族志》残卷撰写时间和张氏族源考释[J].敦煌学辑刊,2007(1):4-6.
[38]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4册 [M].北京:中华书局,1956:
6757.
[39]佚名.毛诗正义:商颂:玄鸟[M]//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623.
[40]刘昫,等.旧唐书:第10册:王君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3191.
[41]刘昫,等.旧唐书:第16册:突厥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5188.
[4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19册:突厥传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6065.
[43]王溥.唐会要·卷78·节度使[M].北京:中华书局,1955:1429.
[4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6册:方镇表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5:1862.
[45]刘昫,等.旧唐书:第10册:郭虔瓘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3187.
[46]杜佑.通典:卷32:都督[M].北京:中华书局,1988:895.
[47]王钦若,等.册府元龟:第2册:帝王部:褒功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0:1606.
[48]杜佑.通典:卷40:职官[M].北京:中华书局,1988:1094.
[49]苏颋.授阿史那承献特进制[M]//董诰,等.全唐文:卷250.北京:中华书局,1983:2528.
[50]苏颋.加郭虔瓘食实封制[M]//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63:实封.北京:中华书局,1959:349.
[51]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35:郯王嗣直安北大都护等制[M]. 北京:中华书局,1959:152.
[52]杜佑.通典:卷85:凶礼八:丧制之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8:2326.
[5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16册:陆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4921-4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