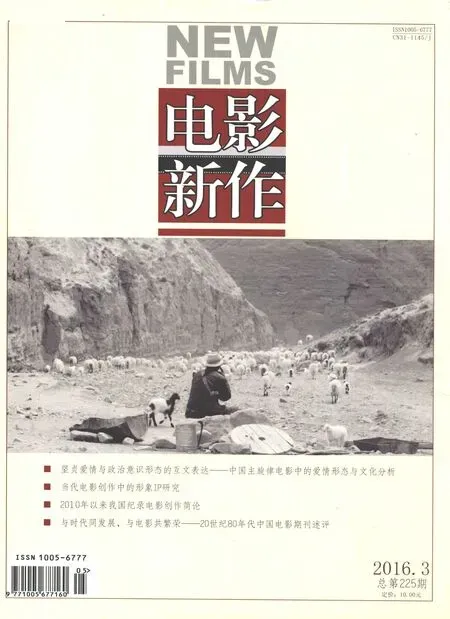侠与武:中国武侠电影和日本武士电影的对比
2016-07-20刘川
刘 川
侠与武:中国武侠电影和日本武士电影的对比
刘 川
【摘 要】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拍摄武侠类的动作片、功夫片。将近一百年过去了,武侠电影在中国的发展可以用长盛不衰来形容。而这一类型的电影,除了华语圈之外很少会有其他国家尝试。同样,几乎在同一时代,日本也开始了武士电影的探索和拍摄,他们对于该类型电影的热情,丝毫不亚于中国人对于武侠电影的偏爱。武侠电影和武士电影,几乎可以缩影为中日两国的国民性格,精神文化的象征。那么,这两大类型的电影有何相同与不同之处,产生这些相同与不同的深层原因又在哪里?
【关键词】武侠 武士 电影 文化内涵 民族性格
引言
侠客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太史公司马迁笔下,甚至还专门给侠客们列了传:《史记——游侠列传》《史记——刺客列传》。描绘侠客的文学作品古已有之,至20世纪50至70年代,武侠小说在香港、台湾等地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作为新艺术形式的电影,也有了一个专门的题材——武侠电影。从20世纪20年代,邵逸夫的哥哥邵醉翁拍摄的第一部武侠电影《侠女李飞飞》开始至今,华语影坛的武侠电影创作几乎从未间断,成为中国电影中一个极为庞大的体系。
在电影界,与中国的武侠电影发展情况极为类似的还有日本的武士电影。正如武侠文化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一样,武士文化也同样是日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在国际上大放异彩的《罗生门》《七武士》开始,60年来日本武士电影的拍摄从未停歇。如同中国的黄飞鸿、方世玉、令狐冲等在国人中拥有极高知名度的银幕侠客形象一样,日本也有很多经典的银幕武士形象。如曾拍摄了近40部的盲剑客座头市、带着儿子四处流浪的武士拜一刀等。
可以说,无论从数量还是影响来看,中国的武侠电影和日本的武士电影在各自国内电影的动作片类型电影中,都占有不容否认的统治地位。由于两国文化上的渊源,武侠电影和武士电影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同样,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这两个类型的电影又有极大的差异。接下来,我们通过这两个类型的一些经典名作,本论文将从“银幕形象”“武打设计”“文化内涵”这三个方面,来具体分析一下两者的异同。
一、银幕形象
中国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就是清朝末年岭南一带的武术大师黄飞鸿。作为一名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武术大师和名医,黄飞鸿的故事被后世的人们加上了无数想象,以他为题材拍摄的电影也是目前为止中国所有系列电影中最多的一部,从1949年关德兴主演的第一部黄飞鸿电影《黄飞鸿之鞭风灭烛》开始至今,仅仅是关德兴一人出演的黄飞鸿电影,就达77部之多。到了1997年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之西域雄狮》,就已经到了100部。一直到去年,由彭于晏主演的《黄飞鸿之英雄有梦》,60多年间《黄飞鸿》系列已经拍了一百多部,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可谓世界电影史的一大奇观。同样,在日本也有一位无人不知的侠客形象,他就是盲剑客座头市。从1962年导演三隅研次拍摄的第一部座头市电影《座头市物语》开始,日本共拍摄了近40部《座头市》系列电影。仅胜新太郎主演、监制的就达26部之多。作为各自国内知名度最高的银幕侠客形象,黄飞鸿和座头市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两者都是武艺高强,身怀绝学。黄飞鸿以无影脚威震敌胆,座头市以逆手一文字闻名于世;两者身上都有浓郁的市井气息,或者说江湖气息。黄飞鸿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大夫,深受佛山街坊邻里的尊敬和喜爱。座头市是一个手法高明的盲人按摩师,与社会底层的商贩、流浪武士打成一片。当然,两人都是嫉恶如仇,善良正直的武者。其实,对于中国和日本两国的民众来说,黄飞鸿与座头市绝不仅仅是两个简单的银幕形象而已。先来说黄飞鸿,50年代关德兴所塑造的黄飞鸿,是一个仁义大侠,沉稳睿智,低调从容,极具中国文化中大家宗师的气度。到了徐克执导的一系列《黄飞鸿》电影时期,这个传统形象则更加人性化,同时还身负国仇家恨,成为19世纪列强环饲下中国民众民族意识觉醒的代表。“飘零去,莫问前因,只见半山残照,照住一个愁人”(《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插曲《惊回晓梦忆秋娟》词),这首插曲,恰如其分地描绘出国家危亡,风雨飘摇的大形势下一位心怀天下的仁人志士心中的不甘与悲壮。我国杰出的电影艺术家谢晋曾说:“作品产生的强烈的社会效果——爱国主义,恰是作品的真正的内涵思想,要透过对主人公内心的揭示,透过对人物心灵的赞美,使人们看到蕴藏在我们民族之中的强大的心灵美、性格美和境界美,给人以积极向上的感受。”①因此,对于很多国人来说,黄飞鸿不仅仅是一个银幕形象,更是一个民族意识觉醒,自尊自强的精神符号。而座头市对于日本民众同样是一种精神图腾似的存在。日本的武士道文化以其独特的“耻感”闻名于世,在勇敢、尚武、忠诚、自我牺牲等精神准则的刺激下,日本的武士阶层对尊严极其重视,而相应的,对于生命,无论是自己的生命,还是敌人的生命,却并没有西方人或者中国人那种生命高于一切、人命关天的思维。因此,在黄飞鸿手下,鲜少看到置人于死地的镜头,甚至连屡次陷害他的对头,黄飞鸿也总是手下留情。在这一点上,“得饶人处且饶人”“仁者无敌”等中国式哲学智慧以及处事理念,在黄飞鸿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反观座头市,虽然一样在别人危难时挺身而出,却从不会手下留情,每每出手,皆是致人死命,甚至在日本的诸多《座头市》系列电影中,皆有暴力美学的成分。乱飞的断肢、滚落的头颅、冲天的血雾,与灿烂的樱花、精美的刀剑一道构成了奇异华丽的死亡盛宴。但不可否认,虽然场面血腥,但大多数时候座头市所杀之人皆为仗势欺人之辈。通过影片前期的铺垫和渲染,能让观众产生“痛快淋漓的复仇感”(胜新太郎语)。正如一些影评人指出的,“隐藏在暴力美学背后的人性关怀,正是众多日本武士电影的特点”。②除了这两个银幕形象之外,中国武侠电影中的侠客形象和日本武士电影中的武士形象也大多有此差异。《太极张三丰》中的张三丰面对背叛自己,屡屡想杀害自己的军官却多次手下留情,《叶问》中的叶问也多次以德报怨,与试图将自己赶走的拳师化敌为友,而在日本的武士电影中,这样的场面却绝少出现,追根溯源,还是两国国民性格的差异。日本是一个惜生崇死的民族,当生命存在时,便要如樱花般绚烂,而当生命失去那最亮丽的色彩时,便要以死亡的形式超度,如此生命的旅程才能更加完整。“这种崇死是积极地向神的归一,因此呈现出对死亡的尊敬、崇拜、病态的美化和爱恋,并以各种形式展现着‘死本能’的强大。”③正因为有着这样的认识,日本的武士电影中,很少出现面对敌人却手留余地的武士形象。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杀”与“不杀”正是武侠电影和武士电影人物形象的最大不同。此外,另一个较大的不同是,武侠电影中的人物大多是一些有通天彻地之能的大侠豪杰,他们不管身份是高是低,境遇是好是坏,电影中都很少展现他们为一日三餐劳累奔波的一面,也极少展示他们所处时代的日常市井生活。而日本的电影中,却常常会以一些为了生计发愁的流浪武士为主人公,纵使身负高强武艺,却仍然有着市井小民的喜怒哀乐。从这一点上看,无疑日本武士电影刻画的武士形象更贴近普通人的形象,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二、武打设计
在中国武侠电影里的武打设计,可分为三个时期。在武侠电影出现的早期,电影中所塑造的银幕侠客形象大多是腾云驾雾、口能喷火、双眼放电的异能之人,而以彼时的电影技术,这些场景和动作的表达大多比较粗糙。20世纪50年代,《黄飞鸿》《方世玉》等一系列刻画近代武人电影的出现,又使得武侠电影的打斗趋于真实。其中,尤其以刘家良等老一辈武术家为代表,他们参与设计的武打动作讲究拳拳到肉,硬桥硬马。其武打动作往往有板有眼,一丝不苟。甚至其一招一式,都可以在现存的拳法武术里边找到影子。而当以徐克为代表的新派武侠电影崛起时,武打动作的设计则在真实功夫的基础上更加华丽。如李连杰在《黄飞鸿之狮王争霸》中所展现的华丽动作套路,令人目不暇接的连环飞腿等,虽然脱胎自真功夫,却更加注重其表演性和观赏性。而如《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新仙鹤神针》《新流星蝴蝶剑》《新龙门客栈》等根据武侠小说改编的电影中,武术和打斗更像是一场华丽的表演,一招一式间并不刻意追求真实有效,而更重于刻画侠客们身手飘逸潇洒的美感。这一点,在《卧虎藏龙》中展现到了极致。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通过镜头表现到了极致,无论是李慕白和玉娇龙的竹林打斗,还是玉娇龙在酒馆和一众武师的打斗,都在一片刀光剑影中透漏出浓郁的中国古典美学影子,折射出中国人对于武学独特的理解和创造。而日本武士电影中对于武打镜头的展现,则相对要更加写实一些。电影中通常两个人的对决在极短时间内就分出胜负,而动作也绝不会花哨,通常都是简洁有力的一刀,敌人便随即倒地。相对于真正交手的瞬间,日本武士电影在描写对决时更加注重渲染气氛,往往通过眼神、步伐、环境等特写,营造出令人窒息的紧张感。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年来中日两国影人互相取长补短,已经开始尝试改变各自的武术动作设计。如中国的《双旗镇刀客》《天地英雄》《刀》等几部武侠电影,展示的武打场面就简洁写实了许多,而日本电影《浪客剑心》《石川五右卫门》等,也开始尝试天马行空、眼花缭乱的打斗方式。

图1.《卧虎藏龙》剧照
三、文化内涵
就最近20年的作品来看,无论是日本的武士电影,还是中国的武侠电影,都在致力于发掘、弘扬各自历史传承和民族文化中侠客、武士的精神内涵。可以说,无论是侠士还是武士,在现在电影中的形象,比起历史上的标准,都有了很大不同。我们先从“武侠”谈起。《史记·游侠列传》中,如此描绘侠客的特点:“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而战国时的法家韩非子也曾说过,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由此可见,中国历史的侠客,是将民间(江湖)中所看重的“义理”,置于政府(庙堂)所弘扬的律法之上的,因此,太史公才会称之“不轨与正义”,韩非子才会称之“以武犯禁”。我们从荆轲、聂政等人的故事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的侠客往往混迹于市井,正所谓“仗义多是屠狗辈”。他们不畏强暴,无视生死,只要是欠下恩情,则不惜以死相报。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些侠士们眼里,很少装有“天下”“万民”等大仁大义。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武侠电影中侠客的形象却有了很大变化。他们身上不仅仅有了惩恶扬善,拔刀相助的江湖豪气,更多了国难当头,人人有责的凛然正气。无论是黄飞鸿,还是方世玉,又或者是《新龙门客栈》中的周淮安、李莫愁,《少林五祖》中的洪熙官,《神龙剑客》中的吕四娘,《大刀王五》中的王五,都是出身江湖之中却心怀天下的仁人志士。他们往往身负国仇家恨,与当权者苦苦缠斗,即使是以卵击石,仍然勇往直前。这一侠客形象的转变,实际上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屡遭遇危机和欺凌,国人心理上产生的一种精神寄托。即使如今国家已经繁荣富强,中国人也早已摆脱“东亚病夫”的帽子,但在国际话语权仍然由西方强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大环境下,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依然需要一个合适的寄托。因此,新浪潮武侠电影中,侠客们往往除了快意恩仇,纵横江湖之外,也主动以国家兴亡、天下苍生为己任,较之以往的银幕形象,侠客们身上的爱国主义成分陡然增多。日本的武士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侠客的存在。两者的精神追求和内涵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如舍身重义,不惧危险,重视名誉胜过生命等。然而,日本的武士阶层说到底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权力阶层,只是由于日本战国时代土地兼并严重,众多武士在失去领地和主君后,成为没有固定俸禄的浪人,不得不放下武士的架子,为生计奔波,逐渐蜕变为市井小民。
因而,日本电影一个重要的命题,便是执著于自身信仰的武士们,面对日渐不同的社会环境,以及逐渐消亡的社会价值,所产生的呐喊与彷徨。这一点,在黑泽明的《七武士》中表现得最为彻底。这部杰出的悲剧,描述了几个失去了存在意义的武士,对抗另一群失去了存在意义的武士。同样是失去了领地和君主,失去了谋生的手段和存在的价值,勘兵卫一行最终选择成为雇佣战士,帮助弱小对抗强权,他们依然坚持了自己的信仰,而山贼武士一伙儿,却成为土匪流寇,彻底背弃了武士所代表的精神内涵。面对可以看到的消亡,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就此浑浑噩噩,放纵享乐,还是坚持自我,寻找新生。这,便是黑泽明抛给我们的问题。最终,那位假冒的“农民武士”菊千代和剑术高手久藏被新时代的代表火枪打死的情节,则更像一个比喻,象征着一个古典时代公正、高贵和英雄主义的消亡。

图2.《七武士》剧照
结语
武侠电影与武士电影,都具有其强大的精神内核——中国的侠客文化,日本的武士文化。然而,我们通过两大类型电影的对比,能够清晰地看出,武侠电影重在“侠”,而武士电影则重在“武”。“侠”是一种情怀,国人独特的“归隐”价值观和“不争”的君子之风,深深侵染在了侠客文化之中,虽然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之志,却不愿身处名利之中。“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间,不胜人生一场醉。”徐克在其代表作《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中,用这首词表现了他对侠客文化的理解。功成身退,浪迹江湖,这也正是侠客们最好的归宿。而“武”则是一种信念。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唯有以武之道来完成自身的修炼,从而达到生命的更高境界,哪怕在这一过程中身死魂灭,也是一段完整的生命之旅。而一旦放弃“武”之信念,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
【注释】
①黄会林.谢晋电影创作论[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1).
②郝建.美学的暴力与暴力美学——杂耍蒙太奇新论[J].当代电影,2002(5).
③[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商务印书馆,1990.
作者简介:
刘川,河南影视集团项目发展部主任,产业发展中心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