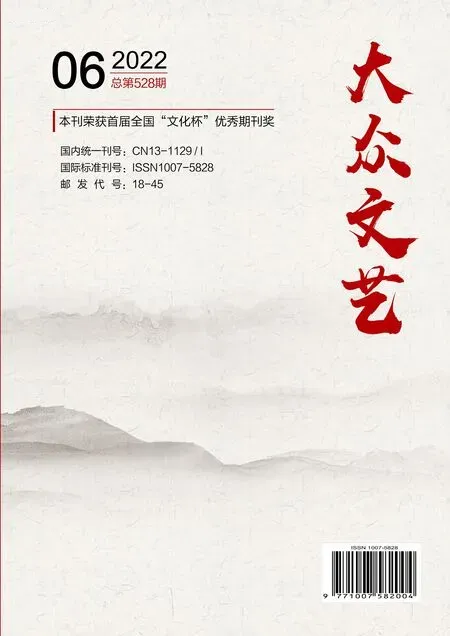应恨此身非吾有
——对娜拉“出走”和“玩偶”一词的重新思考
2016-07-12宋雪莹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610000
宋雪莹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610000)
应恨此身非吾有
——对娜拉“出走”和“玩偶”一词的重新思考
宋雪莹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610000)
《玩偶之家》是挪威伟大的剧作家易卜生著名的“社会问题剧”,以海尔茂的家庭婚姻问题,折射出社会中男女权利的分配和男女地位的现实问题。这部剧在世界范围内提高了人们对于妇女地位的认识,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女性解放思潮和女权主义运动。然而,如果只是单纯的把“玩偶”与出走的女主人公娜拉等而同之,是不全面的。本文将从女性的玩偶地位、婚姻悲剧的成因、以及究竟谁是“玩偶”三个方面展开,重新思考这部剧带给当下人的意义。
《玩偶之家》;婚姻悲剧;出走;玩偶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常被看作是“一篇抨击资产阶级男权中心思想的控诉书,是一篇妇女解放的宣言书”,这部剧的上演也着实对世界范围内的女性解放思潮和女权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芬兰于1906年、丹麦于1915年实行了妇女选举权,1924年丹麦内阁中就有了女教育大臣等等。对我国五四时期影响颇深,使得先进女学生纷纷走出家门,去和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父权社会抗争。然而,这部剧如果单纯的把“玩偶”与娜拉对等,多少有些片面。身不由己的“玩偶”不仅仅,也不应仅仅被理解为依附于男权的女性。对于当下这个时代中的我们,女性解放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且女权主义越来越被社会中人所强调,为避免矫枉过正,我们应警惕过分强调女权而使得男性权益被侵害成。
一、娜拉的“玩偶”地位及其成因
在家中,海尔茂先生很爱自己的妻子娜拉,将之昵称为“小鸟儿”“小松鼠”,在海尔茂的眼中,娜拉是个“乱花钱的孩子”,是需要自己照顾的人,作为“大家长”和“庇护者”海尔茂还对娜拉说 “我常常盼望着有桩危险的事情威胁着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1这种带有大男子主义色彩的爱语。和中国古代女性地位相似,娜拉在家中只需照顾好三个孩子、收拾家务、唱歌给丈夫听使之开心,做一个乖巧听话的贤妻良母就好。不难看出,依照社会标准评判,“女德”与“玩偶”是同义词。
而“女德”与“玩偶”等意,女性附属于男性,是因为女性没有社会职业,只有家庭角色的,“没有经济地位,就没有社会地位”,无法独立生存只能依附于男人的女性,自然只能如菟丝花一般称为乔木的附属。如娜拉,她在经济上完全依附丈夫(偷偷打工是为还债),这使得丈夫在本应该平等的夫妻关系中出于居高临下的地位。
而托伐与娜拉的婚姻悲剧,也是与女性远离社会造成的。他们争吵的导火索是柯洛克斯泰先生手里掌握着的娜拉为救丈夫而伪造父亲签字的借条。娜拉所代表的是远离社会的自然人,而海尔茂所秉持的则是浸润社会规则久矣的社会人的价值观。
娜拉伪造签字的时候,明知这样不应该,但为了挽救丈夫的性命,还是毅然决然伪造父亲签字,借钱带丈夫去意大利养病。情在法前。即便是后来丈夫病愈,娜拉为了“维护丈夫的尊严”,为了不给丈夫“增添压力”,偷偷工作赚钱还债,一切动机均是情字,是人性的体现。
而寄托着娜拉“奇迹”的托伐,平日里总是张口闭口的“我爱的小鸟儿”,看信前还说“我常常盼望着有桩危险的事情威胁着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2,当看完柯洛克斯泰寄来的威胁信,知晓了妻子因为爱他为救他性命不惜伪造签字借钱是,他不但不感动,不但没有关心这几年娜拉是怎么为还债操劳的,没有想着怎么帮娜拉解决困境,反而焦虑于这件事可能危机他的名誉、前途,而破口大骂,骂这个全心全意为家庭、为自己的贤淑妻子为“坏东西”“伪君子”“犯罪的人”,甚至是“下贱的女人”3。这种重视结果,而不问动机、初衷的行为,是法理社会的产物,是社会人的思考方式。
女性与男性不在同一个社会层面,其思维方式也不同——海尔茂是社会中人,思考方式按照经济社会中的“法”,娜拉是家庭中人,没有什么机会接触社会“规则”,故而秉持人性,“情”优先。我认为,这才是这部社会问题剧产生的原因所在。
二、娜拉的觉醒与“半觉醒”
海尔茂看到柯洛克斯泰的来信时的震怒和破口大骂,让本不想连累丈夫而甘愿自杀的娜拉心生寒意,她对家庭的付出,为丈夫的牺牲,在丈夫眼中一文不值,甚至被视为理所应当。她发现丈夫其实并不是真的爱她,而是把她当作一个物件喜欢着而已,婚姻和爱情中,他们并不是她所以为的平等关系。而当海尔茂拿到柯洛克斯泰寄回来的“把柄”签字时,他又笑逐颜开地“宽恕”了娜拉。此时,海尔茂还是高高在上的“宽恕者”,娜拉却在海尔茂的怒气中觉醒了。她回想起他们结婚的这二十多年中,他们从来没有认真的聊过正经事儿,她意识到当自己还未出嫁的时候,是父亲的“泥娃娃孩子”,嫁给海尔茂后,变成了海尔茂的“泥娃娃妻子”4,她意识到自己的不自主,有了自己的思想,并敢于运用了自己的独立判断力去反思、审视、反抗社会中的“惯性认知”——“牧师告诉我,宗教是这个,宗教是那个……我要仔细想一想牧师告诉我的话究竟对不对,对我合用不合用5”。她并不甘心就此继续一生,于是勇敢地拒绝了海尔茂重新为她提供的温暖舒适的安乐窝生活,选择认清自己的心,“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6,拒绝忍气吞声的被牵制的生活而毅然决然的走向未知的门外世界。
剧本结尾处那“砰”地一声,往往被看做娜拉作为女性的自主意识的觉醒,然而,我却不这么认为。我以为,娜拉在和海尔茂的争执中,虽然意识到自己的非自主状态和不独立的依附地位,但她通过默默收拾东西离开家的这个行为本身也是不成熟的——离开让她成为“玩偶”的家,就真的能挣脱开“玩偶”的身份了吗?她该如何生活?该如何使自己再次避免沦为“玩偶”?自己前三四十年究竟因为什么,会成为父亲、丈夫的“玩偶”?她没有搞清楚这中种种实质性、现实性问题,就冒冒失失的离开家门,这略显莽撞的置气行为本身就是“玩偶”的特权,不是吗?所以我认为,即便娜拉在和海尔茂的争执中明白了自己的玩偶身份,却依旧没能摆脱之。
鲁迅先生说的没错,“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7”,易卜生自己也曾断言“也许她会重新回到丈夫和孩子们身边,不过也许做了马戏团的演员四处流浪”。我之所以认为娜拉是“半觉醒”的,是因为她只意识到了自己在家中的“玩偶”地位,而没有想到,即便她离开家进入社会,也不过是从丈夫的玩偶,变成了社会中的玩偶罢了。
三、人人都“玩偶”
所谓玩偶,即身不由己之人,受外在他人牵制,欠缺完整的自主性的人。
在易卜生的这部剧中,娜拉是显然是。玩偶娜拉所代表着的是那男权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及未嫁时遵父,婚后从夫。在学术界的讨论中,娜拉的玩偶身份已经被讨论的太多、太透,但其实,操控娜拉的海尔茂也是“玩偶”。
海尔茂生重病,却因为担心自己无力偿还债务,而几次勒令妻子娜拉不许借钱。生命被放在了金钱之后,又也许是海尔茂怕自己命不久矣而毫无工作能力的娜拉无力还债,出于对妻子和孩子的爱,而作此决定。海尔茂的内心活动,剧作家并未给我们读者明确的答复,但无论出于哪种原因,海尔茂终归是出于经济压力而做出不借钱去养病的决定的。来自金钱的压力,操控着海尔茂的抉择。又或者,经济社会下的讨生活的人们都是玩偶。
再比如海尔茂想要开除柯洛克斯泰,但因为自己妻子的违法借条握在柯洛克斯泰手中,而不得不窝火地另想它法。如若没有林丹太太出面,恐怕海尔茂也只能妥协。可见社会中人,都是不自主的。故而我认为将此剧定性为女权宣言是片面的,至少是折损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作者号召的不仅仅是女性的觉醒和独立,更是社会每一个成员,是人的觉醒和独立。试想,当我们没有觉醒之前,我们谁不是玩偶呢?女人是,男人就不是吗?我们是世俗的玩偶,是宗教的玩偶,是上位者的玩偶,是政治的玩偶……在社会中,每个人都身不由己,都为时局、道德、宗教、舆论、利害关系等种种所限,甚至可以说,连我们自己的欲望都操控着我们,使我们无法做自己、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解放。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之所以能跨越民族、国界,且经久不衰,是因为它反映的不仅仅是19世纪的社会问题,而是人类社会长存的问题,可以说易卜生引发的思考是哲学层面的,人自主性问题,是关乎人类本身的。存在主义者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处于“被抛入”的状态(Be Thrown),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从出生就打上了“玩偶”的标识,在我们参与社会的进程中,“玩偶”的身份被不断深化,即便是现代社会中看似“解放”了的女性,从本质上而言也是“玩偶”。当然,男性亦然。人人都是如此,无论是在家附属于家庭当权者,还是进入社会被当权者操控,或是被社会规则、经济利益、人际关系等等操控,都摆脱不掉“玩偶”身份。这是社会问题剧,更是人类哲学问题剧;是家庭婚姻悲剧,亦是社会悲剧,更是人类无法逃脱的“宿命式”悲剧。
注释:
1.2.[挪威]亨利克·易卜生著.盛世教育西方翻译委员会译.《玩偶之家》第二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3.4.5.6.[挪威]亨利克·易卜生著.盛世教育西方翻译委员会译.《玩偶之家》第三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7.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1923年12月26日.
[1]侯建芳.《<玩偶之家>中的“突转”与“发现”》.
[2]艾尔瑟·赫斯特,袁霞译.《从女人到人——娜拉的转变》.文艺研究,1996(2).
宋雪莹,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