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往拾遗
2016-07-05刘镇
刘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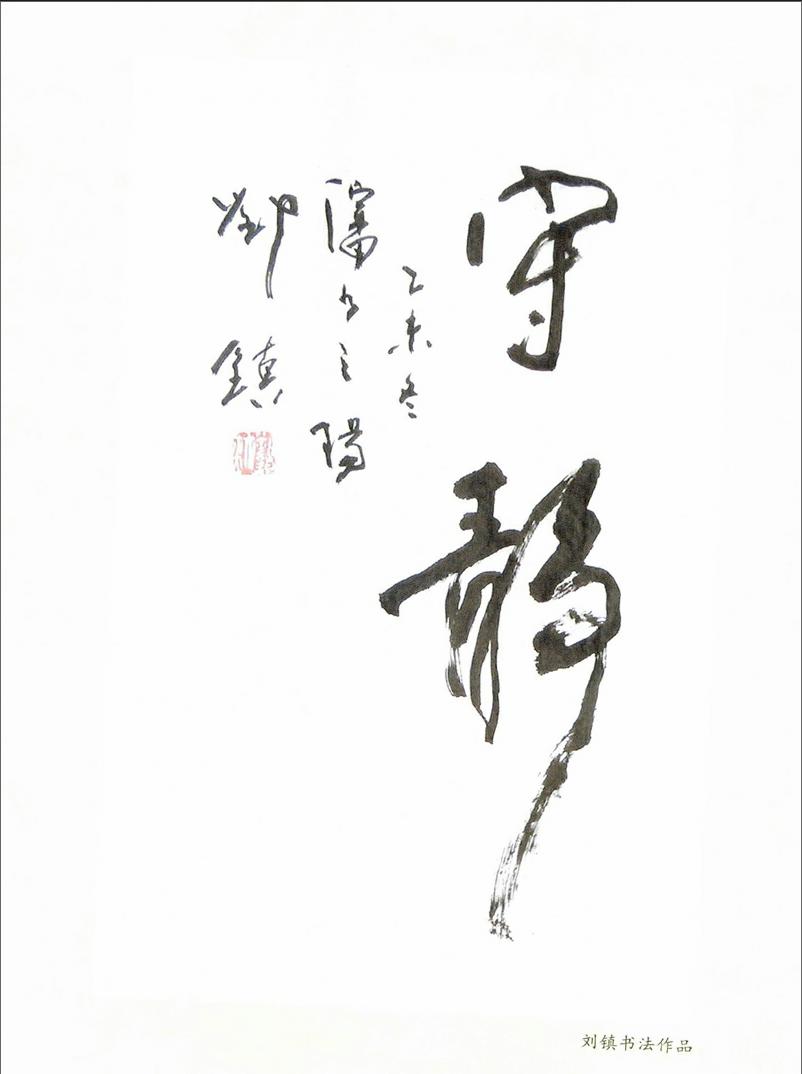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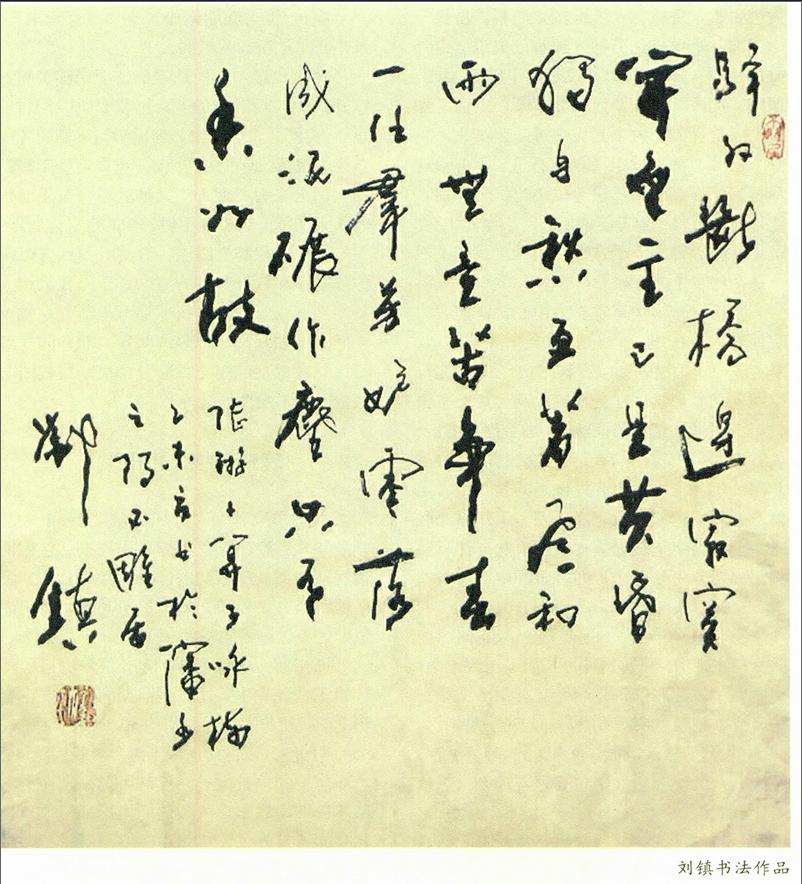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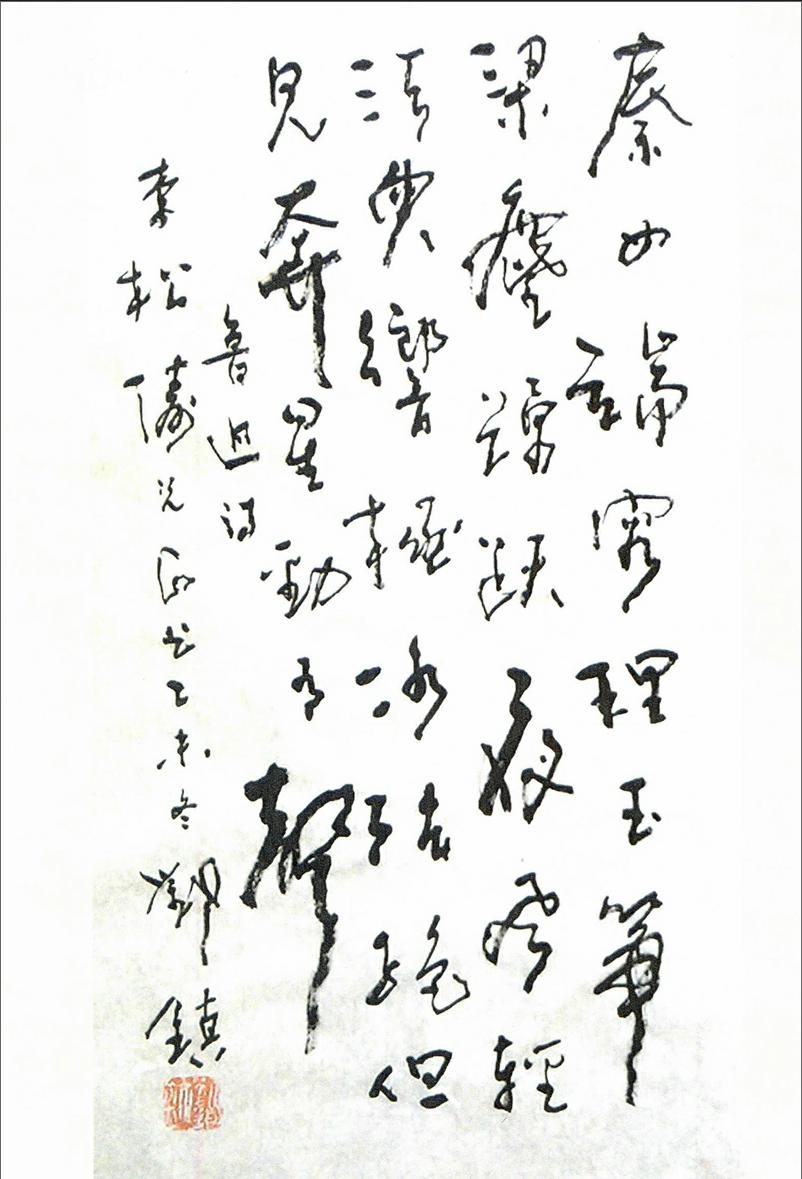
初春的叶子
北方的春天,姗姗来迟,总要经过几番倒春寒的侵袭。但春天的步伐终无法阻挡,它还是如约向我们走来!如果说,还有谁忍不住那份焦盼,不知那坚定里的艰难,或对节令的阳光与风不那么在意:
那么悄然生长的绿叶,便格外引人注目地向世人昭示,使我们确信春的到来了!
春夫的绿叶是可爱的;我尤其欣赏初春的叶子。
初春的叶子很娇嫩。
它们在草地探出头来,在树枝睁开睡眼,开始也许只是茸茸的一星芽儿,使人想起婴儿的胎毛,可随着一段新雨、几丝和风,那油亮油亮、一尘不染、透着鹅黄的叶片,便不禁使眼前一亮,以致不忍触摸,生怕带去什么污渍,或一不小心受到什么伤呢。
初春的叶子也疏落。
或星星点点,如画家随意挥洒中的几笔濡染,然而它不离不弃,生机盎然,只争朝夕,快乐地生长着,好像每一分钟都要带给你一个惊喜!也许就在说话的工夫,就在这刻儿,你回首望去,它便像魔术师手中的那把折扇,“哗”地打开,成团、成簇、成片地伸展开了。
这是生命经过漫长等待射出的响箭!使每颗心灵为之骚动;
这是希望穿越黑暗尽头的辉光!更厚重了阳光雨露的期待。
也许这时候,花,还未开,果,远未坐,但凭着这初春的绿叶,凭着我们对它的信赖:谁还怀疑那随之而来的花潮与硕果呢?
何况,“红花还得绿叶扶”,叶之为德也馨!当人们盛赞花的芬芳、果的甜蜜的时候,朴质、旷达而谦逊的绿叶,不是总默默一旁,欣然微笑吗?而作为护花的使者,初春的叶子,固无夏的浓密,亦壮心不已;虽无秋的深致,亦非将临老境;惟其“敢为天下先”的忠勇,不畏“春寒料峭”的热情奔放,更是可嘉可感了。
春回大地,不可逆转;北方一个迟到的春天,原是更懂得奔跑和超越的!我们将像初春的绿叶,和春天一起出发,美丽成一支凯歌的音符,“欢乐颂”的序曲!
映日荷花
我爱莲。多年来,总想在自家阳台置荷缸一口,植藕赏莲。故每去菜市,都特别希图发现有那带芽的藕,好买回侍养。但藕既入市,便成商品,巳一色的“打造”得白生生、光溜溜,谁还想到这市声沸沸的都市也有人偏爱植藕呢?所以尽管也曾拜托那卖藕的大嫂着意收留,并许以高价,时日萧萧,怕她也早忘到一边了。
“莲藕、莲藕”:莲,藕之花;藕,莲之本也。当荷叶田田,那亦称“芙蓉”、“菡萏”的莲花之下,便是常被人们形容婴儿“藕臂”的藕。记得小时候,老家田头临河的一片浅浅水域;这种多年生植物,都会不动声色地铺开一片生机烂漫的荷图,而我同样爱莲的父亲,春来又总要在天井为植藕忙碌一番的。斯时只见他高挽衣袖,将那带着嫩芽的鲜藕和着肥料……植入荷缸淤泥深处,汗水濡湿的笑容是那么灿烂!对我来说,自此那荷缸边的厮守与期待,亦恍如别开洞天了。
“世间花叶不相论,花人金盆叶作尘,惟有绿荷红菡萏,舒展开花任天真”:这是李商隐《赠荷》中的赞美。宋大哲学家、理学开创者周敦颐,则于其《爱莲说》一文中,在肯定“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藩”后,通过莲、菊、牡丹之爱,进一步走进莲的品性,而特别推崇了其“亭亭净植”、“香远益清”的高洁,鲜明表达了对世俗争名夺利的憎恶。虽难说如此比对是否公允妥适,但就莲而言,无疑颇得深蕴,尤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不是向为世人所标举吗?
这里,莲的天生丽质姑且不论,娇滴展张、翠玉盘般的荷叶,何尝不惹人喜爱?它仿佛更知洁身自好,随时保持着某种警拒:夏日的豪雨,打在上面,“珍珠”四溅,清音一片;便是一掬浊水,洒在上面,亦如水银泻去不留一星污渍。至于那“中通外直”、“不枝不蔓”、“不可亵玩”的茎呢,更总要竭尽全力,将那花叶擎到最后一刻;而其莲子虽经千年沉埋,犹芳魂不死、生机再现的那股精气,更是一个传奇,让人惊叹不已、肃然起敬的了。
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使包括今日之藕的商品价值陡增,本无可非议,丝毫不意味着真、善、美的贬值。相反,在充满浮躁与诱惑的当下,世风的清正廉明,人心莲性的回归,人格品位的再塑与提升,理应视为“宜乎众矣”的想望!有感于此,故笔者曾于一首题为《莲》的诗中写道:“亭亭莲也!出淤泥而不染/清水沐之,清风拂之/潇洒于红日!/有圆圆微苦。含笑于秋雨/而沉埋千载,犹是不败的芳魂/一个妩媚的故事!/而复眼的蜻蜒,相识未必相知/它款款飞来,匆匆离去/算一时佳话/沾尽风流/更能消几许?/因此莲之为莲,/不枝不蔓/不免多思:/成一支清歌,一种秋景/一纸泼墨淋漓的孤傲/枯笔下圆睁的眸子!”
——无论李商隐之诗,周敦颐之文,距今皆至少800余年了。也许800年后,依然一面有“一纸泼墨淋漓的孤傲”,一面有“枯笔下圆睁的眸子”,但杨万里描绘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念中,依然幻成一种社会昌明荣盛的景观呢!
芦苇·蒲剑·唐伯虎
芦苇是一种很普通的植物,多生长在水边地头。从前我家有一片薄田,两面临河,那临水的河坝上下,便丛生着数不清的芦苇,远远看去,像排绿色的屏风。年年“端午”包粽子,家人都取那刚摘的、散发着清香的苇叶;而我们孩子,在春风里,在大野上,则常取那叶子做个笛儿来吹,或偶尔折一支因河水冲刷而裸露于外的、白里透着嫩红的芦根嫩芽儿,嚼得一口清甜。
芦苇有极强的生命力,从不“嫌贫爱富”,“乐”于奉献。春去秋来,随风摇曳,你无需为它的生长发愁,费心照料。它总是一个劲儿地发,一个劲儿地往上长;今年砍去了,明年又冒出来,直至离水很远的地方,离水很远的年月!那“沙沙”的声音,与河浪彼此唱和,在没有人的时候也从不寂寞。除了那根紧紧护卫着河堤,并可入药,不断伸展着的茎叶,亦可用来编席、造纸——便是砍来烧呢,也是“噼噼剥剥”的一把火!不过,倘以为卑微若此,可以冷言相向,似乎就有失公允、使人怀疑应有的善良了。
于是想到了蒲剑,想到了唐伯虎。
蒲剑,亦即菖蒲.生性与芦苇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特别的也许是:它更近于姓“草”!全身的“披挂”,全在挺挺的蒲叶,铮铮然直看去恰如支支利剑!不过小时看惯了,虽也知那蒲叶可用来编筐、编篓,做驱蚊纳凉的扇子,泥腿的庄稼人,还以之“打”鞋暖足;还有编作蒲团的,那是一种坐具;“端午”悬于门楣“避邪”,故“端午”亦称“蒲节”……这些都不曾多“过脑子”。及至近读唐伯虎《蒲剑》一诗,眼前为之一亮,心头为之一震,便不禁对蒲剑刮目相看,为诗拍案叫绝,更走进那位集诗、书、画大成于一身的“吴中奇士”了!
“三尺青青古太阿,舞风砟破一川波。
长桥有影蛟龙惧,江水无声日夜磨。
两岸带烟生杀气,五更弹雨和渔歌。
只恐秋来西风恶。削破锋棱恨转多!”
是多么气象雄奇、生动传神、寓意深刻啊!想不到,早于五百年前,唐伯虎,这位江南豪宕不羁、“依红偎翠”的“风流才子”;桃花坞“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须花下眠”的一代名流;感时愤世,托物言情的“狂生”:便于“风流”之外,“半醒半醉”之间,得蒲剑神韵而别开一境,写下了如此佳作!其格调之新,锋芒之锐,高昂的战斗精神,也突出表现了诗人不甘沉沦、不甘妥协、积极入世的一面。应该说,这为解读那位身在浊流、特立独行的诗人,确实打开了又一个极好的窗口!
芦苇的自得与随和,蒲剑的纯朴与尊严,很少有人真正体悟。诗人的心路情怀,尤其如唐伯虎者辈,更难追赶。所谓“敛迹俯眉心自甘,高歌击节声半苦”,其中的隐痛,几人真正参透?!我也曾以为,人们在功利的驱使之下,在冷漠与匍匐同样茂生的漫长岁月中,在不尽的奔波打拼里,几乎麻木了。然而细想芦苇也好蒲剑也罢,彼者何?此者何?皆大地之子,属百姓人家,原是一样轻漫不得!而诗人的正直,勇为平凡生命鼓呼的侠肝义胆,与乎“贯微洞密”、“孕大含深”的用心之苦,如何不从心感佩呢?!
唐伯虎和他的时代一起早已远去了。但平凡的芦苇和平凡的蒲剑,依然在大地生长着,繁衍着,也让我们怀想着。这是它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幸运!只是如今之我,跻身现代而当都市,不必说已鲜见还有谁挥那蒲扇、拎那蒲篓、穿那蒲鞋,更不知尚有谁,昧得那芦根的清甜、重拾芦笛之遗响否?
乔园夜记
直如坠入古井,又若飘然世外:乔园之夜,静极了也美极了。
乔园,建立在明万历年间,原为太仆寺卿陈应芳私宅园林,位于古城泰州大林桥南之钟楼巷附近。取陶渊明《归去来兮》“园日涉以成趣”句意,初名“日涉”,后一度改称“蛰园”,自清两淮盐运使乔松林入主,遂成乔园至今。这里,白目的市声亦难得侵扰,何况夜静更深呢?
园中并无他客。作家风章兄倒是先我而至的,但日间匆匆一见,欢叙一番,便也于当晚回宁了。于是,偌大园林,斯人独居,伴孤灯一盏,只任那无边的幽静与静谧拥着。
这是“山响草堂”之一室。室内陈设,古色古香,昏昏然,怔怔然。而我,虽经千里奔波,不堪旅途劳顿,却难以成眠。窗外微风拂拂,虫鸣卿卿。我想起了苏州怡园、留园、拙政园,以及无锡之梅园,上海之豫园,以上诸园,说来都曾去过,因其大,且游人众多,都不过走马观花而已,不曾从容尽览。而乔园不同,它玲珑小巧,若将前者比作唐诗大雅,后者便该如一首小令;“小令”虽小,亦“容大千于方寸”尤其对我这孑然一身,已属洋洋大观了。
园即以“山响草堂”为中心,辟前庭后院而建。月门洞开,花墙围合;堂前不远,凿池叠山,柏桧苍苍,石笋兀立,小桥静卧,亭阁翼然。那堂后深处,筑以高台,散布天竹,回廊掩映:情依势而流盼,趣合理而纷披,入胜通幽,暗香浮动,其艺术之巧思,确乎非同凡响!难以置信亦令怅然的是,小时虽曾一度寓居近侧,竟无缘一识,不知有此胜迹!至于当年陈毅三进古城,于此与伪首谈判,梅兰芳先生返里,亦曾于园中小住的情事,又是后来得知的了。
想我近40年来,远走他乡,其间,或跻身关东闹市,或浪迹中原山野,历经沧桑,何曾有幸享此雅静?!而今受泰州市文联安排厚待,感激之余,不能不勾起游子眷情。
是的,今夜的乔园,静得深沉,静得温存,像十七八的女儿,一定也静思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吧?
是的,乔园的今夜,静得出奇,别有韵致,而我若天涯游子拥入母怀,想必她的思念也思念得苦吧?
夜深了,月在中天,我不知此时是醉是醒。仿佛那无涯的静寂,也会因呼吸而紧缩;这“浑圆的和平”,也会因稍一动作而塌碎!当我仿佛为一种精灵所诱,不知何时又忍不住走出“草堂”,移步庭中,流连桂花树下,仰望朗月,俯视桂影,依稀见渊明先生飘然而至,一篇《归去来辞》,情采沛沛:
啊,“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那不正是他捋须吟哦的么?
然而我想,先生是不是过于伤感了呢?远却红尘,陶然遁世,又岂我辈所取?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历史终未沉落,追求依然执着,世界何其年轻!作为后之来者,今天,又谁能不兴奋于当代的伟大变革,并投身于更辉煌的创造呢?
于是,我静立庭中,分明听到远方汽笛的呼唤,和自身血液的流动;于是我见诗人复飘然而去,乔园一抖,那万里清光,顿令人间天上如水洗了一般的明丽。而乔园之湖石,与我相视而笑:乔园之柏桧,与我两心依依,竟不知鬓丝露冷!
魂牵梦绕“平山堂”
“人事有代谢,江山留胜迹”。宋大文学家、著名政治家欧阳修早已离去了,但他谪居扬州期间所营建的“平山堂”犹在。那是他昔年公余晏游之所,遥想其盛,此次返里,怎不以一瞻为幸?!
扬州有“平山堂”,扬州亦有我记挂多年的王式曾先生。幼时战乱期间,一度在泰州上学,便曾随家兄寓居他家“公馆”。一晃50余载过去,现得知这位当年曾教我们跳“新农作舞”的“五少爷”已移居扬州,便自然顾不得细雨霏霏,按照信址先行拜访。只是此时的式曾先生,年届古稀,已不复当年年青俊逸,岁月的沧桑,显见留下了深深印痕;而提到“平山堂”,精神绝好的他,亦兴致盎然。于是,承先生相邀,先去盛名扬州的“富春楼”用过早点,便驱车径往“平山堂”赶去了。
“平山堂”,建于扬州蜀岗之巅,西接“御苑”,东邻大明寺。至山麓,适细雨消歇,天色放晴,抬眼望去,山路弯弯,浓荫夹道,煞是雅静。许是终因阔别多年,总有说不尽的话题,我们一边拾级而上,一边叙谈,任积雨从头顶的枝叶间滴落,任时光倒流、空间转换,由自身而及广大,历史的距离,也仿佛在脚下一步步缩短。
认识式曾先生的那年,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中,表面的“繁华”下,透着白色恐怖。而我其时终是年幼,只知他终日在家,看书,“养病”;只知他蜇居那小巷深处,白天几乎足不出户,惟偶尔晚间出去夜深方回:原来那时的他,作为上海复旦大学的进步学生,也是一为避捕,更为迎接古城的解放呢!至于他弟弟延曾,曾在北平发生“沈崇事件”的第四天,写有《读<资治通鉴>淝水之战书后》一文,借古论今痛斥了当局以夷制华的政策。以及作为地下党员,以后又被派往武汉,开辟红色据点的统战工作,后又不幸于1948年被捕,最终英勇就义。紧急关头,将一团机密吞入口中的细节等等,更只现在才从先生口中知道的了。
而关于他自己,先生却谈的不多:尤其解放后,在历次“运动”中的坎坷,以及如何流落江西,娶“村姑”为妻,又加丧妻之痛等等,亦寥寥数语。惟,先生虽早从扬州市文联退休,身心硬朗,乐观持志,儿女不在身边,亦每以诗为伴;倒是对另位至今犹滞留江西的“正直战友”,流露出更多同情,说前年探访一回,不知现下如何……
不觉已至蜀岗之巅,踏入“平山堂”敞厅。但见堂前,古藤错节,秀竹滴翠,两厢案几,序列如初,依稀留有当年众宾余温。而立丹墀南望,深深呼吸,也不由得再次走进《醉翁亭记》!这千古不朽的瑰丽之章,音情顿 挫,明畅爽丽,读来荡气回肠,让人微醺薄醉,即不才如我,亦恨不早生而身入其境呢!
然而,《醉翁亭记》的欧阳修,与“平山堂”的欧阳修,其境遇显然不同。我们知道,这中间,为了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状况,他曾因参与了范仲淹、吕夷简为首的新旧两 党之争,疏言直谏坚定站在开明进步的一边,而“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先由龙图阁直学士左迁夷陵令,继而出知滁州;及至庆历八年,又谪居至此,其仕途光景已几近日薄西山了。只是欧阳修毕竟是欧阳修!以他坦荡开阔的胸襟,“志气自若”、“不为世俗所羁”的洒脱,即令官位大降,总会以风骨自持;除施政“蹇简而不扰”,放怀山水,纵情诗酒,“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即在扬州期间,亦曾写有《平山堂记》的。有关于此,我们虽无从考证,想必又一番气象!面前的一切,亦似足可佐证了。
蜀岗之巅的“平山堂”,不愧为令人惊叹的游目骋怀之所。据载:当年在此,天气晴好的日子,可远眺瘦西湖依依垂柳,岛上松林塔影,甚至那“长江静如练,青山崎如屏”的画境,亦生动隐现!而欧公爱荷,每宴必采荷花置众宾之侧,然后令歌妓取一花相传,依次摘其瓣,谁到最后一片,则必饮酒一杯、赋诗一首,“往往至夜,载月而归”,可谓风雅至极!这样,“平山堂”而与山平,其超拔不仅是真实图画的写照,且如那楹联所书:“过江诸山到此堂下,太守之宴与众宾欢”般令人神往了!我想,此时的欧阳修,纵然屡遭摧击,壮志难酬,自号“醉翁”,实质正当盛年、原是“饮少辄醉”的他,所谓“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不过活画出一代正直文人的郁闷与无奈而已。
“平山堂”,让我魂牵梦绕!它像一卷诗书,打开在人们面前,咀嚼中有无穷回味。当我与式曾先生一起离开,转而又去大明寺一游,归时已夕阳西坠、天色向晚,那暮色苍茫中的“御苑”,便只好留在身后了。
